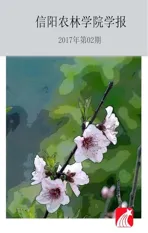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
——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自然生态思想
2017-02-26胡卫治
胡卫治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系,福建 泉州 362000)
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
——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自然生态思想
胡卫治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系,福建 泉州 362000)
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从生态主义的视角解读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可以看出劳伦斯对生态环境的极大关注,对人性的莫大关怀。小说反映了作者超前的自然生态意识。劳伦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对和谐社会关系的严重摧残以及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异化。通过康妮的选择,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只有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获得拯救和重生。
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自然;工业化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 是20世纪英语文学中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在小说中对性爱场面的描写过于直白,且毫不隐晦,这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为此劳伦斯曾被人称为“色情小说家”。 但是,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坚持不懈地对人性进行探索,且极具艺术色彩。他憎恨机械文明,崇尚大自然,思考死亡与重生,因此,他的作品从他生前直到现在都一直被世界文坛所重视。这位文学巨匠被弗吉尼亚·沃尔夫称为“以先知、神秘的性欲理论的阐述者、隐称术语的爱好者、放手使用‘太阳神经丛’之类词语的新术语学的发明者而著称于世”[1]。劳伦斯一生短暂,但创作成果丰硕,创作了12部长篇小说、70部中篇小说、8部戏剧、近1000首诗歌。
生态文学研究或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2]。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被认为于1978年创造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用来描述一种强调“文学与生态学”的关系的文学批评形式(Glotfelty, Reader, 105)[3]。劳伦斯于1928年完成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这也是他最具争议的一部小说,作者在小说里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了生态哲学问题。虽然该小说曾因大量露骨的性爱描写而遭到禁止出版长达三十余年,但小说的寓意却是严肃而深刻的,“劳伦斯颂扬的是那种‘生气勃勃’的生命个体,是‘灵与肉’合二为一的性爱,是‘人类幸福的欢歌’”[4]。是“一个纯粹生命的美”,是“某种温柔的火光”,是“一个生命的剪影在袒露自己,对燃烧着温暖的白火苗,这火可以触摸,因为那是一个肉体”[5]。小说《查》反映了作者劳伦斯对工业文明和机械文明给自然环境造成的极大破坏以及对人类美好天性的摧残的强烈谴责,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忧虑。劳伦斯通过康妮走入森林,接触大自然,从而获得再生,表达了他“回归自然”、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态哲学思想。
1 战争和工业革命污染了田园般的自然环境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就不拿它当悲剧了。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开始在瓦砾中搭建自己的小窝儿,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期盼。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坦途通向未来,但我们还是摸索着蹒跚前行,不管天塌下几重,我们还得活下去才是。”[5]这是小说《查》开篇的一段话。劳伦斯所说的这样一个“废墟中的悲剧性的时代”其实就是小说女主人公康妮的生活状况,也是劳伦斯所生活的时代人类生活的现状。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资本主义文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工业文明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是巨大的。茂密的森林、绿色的田园被煤矿、工厂所取代,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煤矿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土地上充斥着机械文明的喧嚣,人们渐渐远离宁静和谐的乡村生活。更严重的后果是人类因被冷漠的机器控制,使人性受到压抑,人的精神世界渐渐遭到扭曲。这正是劳伦斯一生生活的时代背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一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深深感受到了西方社会不断加深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他痛恨战争和工业革命,对工业革命对人性的严重摧残深感不安和忧虑。
小说的第二章,劳伦斯向我们描述了战争和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拉格比府附近到处都是“煤矿烟囱里喷出的烟雾”[5],整个村子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在康妮眼里,这个中部的煤铁世界丑陋无比,毫无生机、灵魂。康妮生活的拉格比府环境也极其恶劣——房间里阴阴沉沉,耳边充斥着筛煤机、卷扬机、火车、铁轨和矿车等各种嘈杂声,鼻子闻到的尽是硫磺恶臭,空气中弥漫着地下冒出来的煤炭、硫磺、烂铁、硫酸等杂味。小说的第五章,克里福德和康妮去拉格比府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林子里的空气也被污染了,弥漫着硫磺味,“远处的地平线上灰蒙蒙一片”[5]。林子里的动物也失去了自然生机,“羊群在杂乱的干草丛中咳嗽着”[5],松鸭刺耳的叫声吓飞了许多小鸟儿,而林子里也没有供狩猎活动用的山鸡,因为“山鸡在战争期间给捕杀一光”[5],空地上尽是乱糟糟的枯蕨丛,细弱的树苗东倒西歪,“马道左边微微隆起的小山丘上树木都砍光了,看上去出奇的悲凉。山丘最高处曾经生长着橡树,现在则是一片光秃”[5]。因为这里是乔弗里爵士(克里福德的父亲)在大战期间砍伐树木修战壕的地方。战争简直是场大灾难,大自然被破坏得满目疮痍,克里福德深有体会,对战争无比愤怒。地球也被工业革命摧残得乌烟瘴气,康妮生活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拉格比府,感到快崩溃了。而在小说的第十五章,劳伦斯借梅勒斯之口道出了他对工业革命的强烈谴责:“即使到了月亮上,我还是能回头看到地球,肮脏、龌龊,是所有星球中最恶心的地方,是让人类给弄得如此恶臭的。”[5]
2 战争和工业革命破坏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英国从田园般的农业社会飞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煤炭的开采和大量的燃烧造成空气严重污染,隆隆的火车和机器的马达声打破了乡村的安宁。自然环境恶化的同时,社会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人们之间友爱的关系受到破坏,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纯真美好的关系亦遭受摧毁。在小说的第二章,康妮和克里福德生活的拉格比府代表的是“贵族阶级”,而特瓦萧村则代表“农民和矿工阶级”,两个阶级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都暗自怀有抵触情绪”[5]。拉格比府和特瓦萧村的村民关系冷漠,人与人之间从来不来往,因为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劳伦斯在小说中这样写到:“这简直是违背普通人性、莫名其妙的事。”[5]在小说的第五章,劳伦斯更加具体地描写了两个阶级的对立:“特瓦萧的矿工们又在谈罢工了。可在康妮看来,这并不是活动的展示,而是隐藏在深处的战争伤疤在渐渐浮出水面,……那创伤过于深重,那是虚伪而非人的战争造成的。融化这些凝结在灵魂中的黑色血块,需要几代人的鲜血和多年的时间才行。”[5]
与此同时,我们在小说《查》里可以看到,工业文明不仅破坏了和谐的社会关系,而且造成了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小说中描写了几对典型的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比如:麦勒斯和他的妻子芭莎关系不和谐,用麦勒斯的话说,妻子在夫妻生活中是一种“低级的自我意识”;克里福德的护士伯顿太太二十几岁时丈夫就死在矿井里,年纪轻轻的她成了寡妇;康妮的姐姐希尔达天生与男人不和,她和丈夫也离婚了。而康妮和克里福德的夫妻关系更是“异化”,克里福德因参加战争,其腰部以下的身体永远地瘫痪了,失去了男人应有的活力,年轻的妻子康妮只能守活寡。
3 战争和工业革命扭曲了人性
工业革命使英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消极的影响也是惨痛的——英国往昔田园风情的乡村不见了,人类社会的关系不再和谐,最严重的后果是人性被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畸形,这也是劳伦斯倾其一生努力在探索的主题之一——人性。小说《查》中,主人公克里福德在战场上被炸成重伤,战争虽然没有夺取他的性命,但是却使他腰以下部分瘫痪,丧失了性功能,失去了生育能力,成了“一个毫无感觉的空壳”[5]。他的身体瘫痪了,但更可怕的是他从此远离大自然,崇拜精神活动,埋头写作,可写出来的东西空洞无力,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表面高傲、冷漠,但内心恐惧、没有激情,他追求名利、追求金钱,从不关系妻子康妮作为女人的原始本能行为,夫妻间并没有“实实在在地过日子”[5],他对性的满足毫不在乎,在他看来,“性不过是心血来潮的事,或者说是次要的事:它是正在费退的人性器官笨拙地坚持进行的一个奇怪程序,真的是可有可无”[5]。他每天晚上给康妮读一些乏味的书刊报纸,试图用空洞无聊的精神生活守住妻子,自以为这种精神上的亲昵可以取代肉体上的亲密。更为荒谬的是他把康妮看作是生育的工具,为了传宗接代,竟然同意康妮可以和另一个男人生孩子,他“并不在意是不是当亲生父亲”[5],只要能在拉格比府养大这个孩子,就视为自己的孩子,就可以传承家业。康妮对克里福德这种非人性的、不可理喻的论调感到愕然。克里福德生理上及精神上的“异化”,其实就是战争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他的瘫痪象征着那个阶级的人在情感和激情深处的瘫痪”[6]。同时,克里福德的朋友们,如汤米·杜克斯、哈蒙德,他们都信仰精神生活,整日无所事事,在拉格比府高谈阔论。他们就像行尸走肉,毫无情感,内心是一片无爱的荒原。在小说第十一章里,劳伦斯更加具体地描述了生活在机械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古怪”人。矿工们“一个个蓬头垢面,没了人形”[5],他们是“煤层里奇怪的动物”[5],可怕的是男人们只是半个阴暗的人,因为男人与生俱来的活力在他们身上被消灭了。“他们个个如同怪物、精灵,他们属于煤、铁、泥土,就像鱼属于大海,虫子属于枯木一样。他们是矿物质蜕变而成的精灵。”[5]劳伦斯厌弃这些被工业文明“异化”的人类。人类社会扭曲、变形、异化,人类正在腐朽、失去活力,劳伦斯对此深感担忧。
4 拯救措施:回归自然,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
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生态文学是一种反映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学。19世纪美国历史上“第一自然阐释者”亨利·大卫·梭罗认为,自然是实实在在的大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子秀,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7]。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认为,自然带给人愉悦,它并非为人开发利用的目的而存在。爱默生指出,任何企图扰乱自然和它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做法都是徒劳和无知的[8]。卢梭主张人与自然的亲和,发出“回归自然”的口号。生态深层运动的先驱约翰·缪尔认为,自然是人的精神源泉,要成为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就必须不断与自然保持接触,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真正恢复自我[9]。纵观这些生态思想家的言论与主张,可以看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只有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回归自然,人类才能像大自然一样,活得生机勃勃。
在小说第七章,作者描写了住在死气沉沉的拉格比府、与自然隔离的康妮,日渐消瘦,她的身体变得“枯燥无味”,如同“行尸走肉”。而她的丈夫克里福德的精神世界却极其“异化”,是工业革命造就的“异化”的人类。相比之下,生活在空气清新、生机勃勃的森林里的麦勒斯则浑身散发着生命与活力,他是劳伦斯眼中的“自然之子”。小说《查》描写了康妮认识自然所经历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小说第三章,康妮感到自己躁动不安,于是她逃离拉格比府,第一次走进树林。此时她并没有融入大自然,只是把树林看成是她的避难所,甚至“树林并非真的是一处避难所,因为她跟树林没有联系。它不过是一个她躲避到别人的地方而已。她从来没有接触到树林的灵魂,……”[5]在小说第十章,她又逃避到了林子里去,当她看到母鸡时,她感觉母鸡能温暖她的心田;当她看到小雏鸡时,她觉得这些是“生命”,“纯粹,充满活力”,“新生命”。此时,作为一个女性,她感到了一种“母性的忧伤”。渐渐地,她喜欢去林子。与自然接触越来越多的她逐渐感到自然的力量,她觉得林子里“到处都是花蕾,处处生机勃勃”,在林子里,她会有一种奇怪的激动,她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她可以呼吸新鲜而自由的空气,感到一种奇异的、有力的、向上的生命力。她在林子里邂逅了后来成为她的情人的麦勒斯——克里福德雇佣的守林人。后来,她与麦勒斯发生性关系,并频繁相约在林子里幽会,她深深地体会到,“她出生了,作为一个女人”[5]。在这片“未被工业文明奸污”的伊甸园,康妮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这对情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两情相悦中,进行了“灵与肉”的交融,恢复了人的本性,获得了重生,实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性爱关系。劳伦斯通过康妮“重生”的经历告诉人们,人是自然的生态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大自然能使人性返璞归真,能抚慰人的心灵。康妮从拉格比府走向小树林,象征着人类从“死亡”走向“生命”,这也意味着人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重生。劳伦斯“回归自然”的自然生态思想在小说《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应该多亲近大自然,回到大自然里去,恢复生命的生机与活力,找到最纯真的自我,从而幸福快乐地生活。
5 结 语
《查》是一部极富生态自然思想的小说,而作者劳伦斯是一位颇具前瞻性、生态责任感强的作家。通过小说《查》,作者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仅破坏了绿色的自然环境,摧毁了和谐的社会关系,而且扭曲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这点不难看出,虽然小说有诸多篇幅描写了男女主人公极具艺术色彩、“灵肉合一”的性爱场面,但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真正用意在于谴责工业文明给环境、人类带来的灾难,通过康妮的选择提出了只有“灵与肉合一”、“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男女关系才能使人类恢复本性,获得重生,从而走出无爱的荒原,获得幸福的生活。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虽然我们已经无法返回原始社会那种纯真、自然的生存环境中,但是生态主义作家们还在执着地追求着他们的理想: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自然生态危机已对人类的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我们从生态主义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对我们重新认识自然、珍惜自然、保护自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唤醒人类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1] [英]弗吉尼亚·沃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刘青汉.生态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田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5] 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M].黑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6] 王凯军,穆宝清.《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生态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24(6):48-51.
[7] 彭威.论梭罗和老子思想的契合之处[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4):354-355.
[8] 张晓玲.爱默生的自然观[J].时代文学(下半月) ,2008(10):49-51.
[9] 程虹.寻归荒野[M].北京:三联书店,2001.
(编辑:刘彩霞)
To Return to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 Natural Ecological Thought ofLadyChatterley'Lover
HU Wei-zhi
(Depart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Quanzhou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Quanzhou 362000, China)
Ecological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literature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From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e the novelLadyChatterley'Lover,it can be seen that Laurence's great concern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reat concern for human nature.The novel reflects the author's natural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Laurence condemned the great damage to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serious damage to the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distortion of the natural human nature.By Connie's choice, the author tries to tell us that only respect for nature, return to nature,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human beings can be saved and reborn.
Laurence;LadyChatterley'Lover;nature;industrialization
2016-12-25
胡卫治(1979—),女,福建泉州人,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育教学与研究.
I106.4
A
2095-8978(2017)02-00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