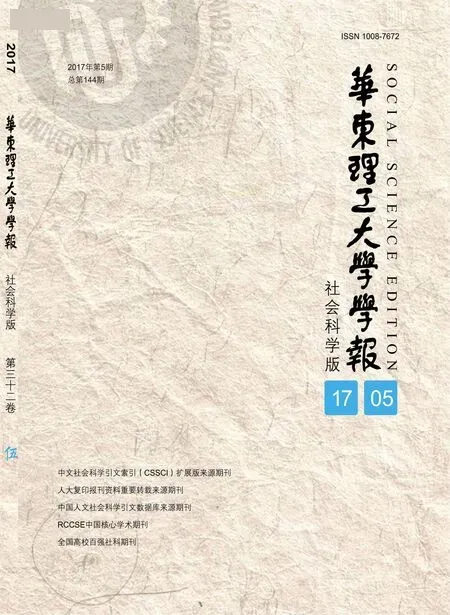论郡县制国家的强大与脆弱
——中国古代学者的观点
2017-02-25曹正汉
曹正汉
论郡县制国家的强大与脆弱
——中国古代学者的观点
曹正汉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有一个特点: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和天下大乱。所以,中国历史既有王朝循环,同时,也有治乱循环(Yang,1954;Usher,1989)。不过,受“天命观”的影响,古代学者似乎对王朝循环不太在意,因为“天命无常,唯德是依”,天命转移终将带来政权转移和王朝更替。但是,为什么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这一问题更能引起古代学者的深思,因为这一问题是对“天命观”的一大挑战。①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即王朝更替和政权易手,对此,顾炎武并不多言,因为那是帝王的家事;但是,“亡天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瓦解和社会秩序崩溃,顾炎武却有彻骨之痛,不得不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见顾炎武:《日知录》(上卷),《正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西周创立“天命观”,以统治者的“德”解释政权转移,宣称周人克商乃顺应天意(Creel,1970;Cook,1995;王爱和,2011)。此后,历代王朝均以“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君王声称自己是天命所归,同时,也要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天下太平的绩效,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Zhao,2015)。然而,“天命观”却留下了一个大漏洞:既然天命无常,政权难免易手,那么,天命转移之后,国家怎么办?如果每一次天命转移和王朝更替都带来国家瓦解,这种代价实在太大了。
一、强政权、弱国家
在思考上述问题上,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这一现象是由郡县制国家的缺陷所导致的。他们认为,郡县制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加强君权;但是,国家本身却比较脆弱,易于瓦解。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宋代。宋代罗泌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指出:
“世人徒见晚周诸侯之疆(强),而不知天下之势合;见后世守令之弱,而不知天下之势散。故论封建失之弱,而实以疆;郡县失之疆,而实以弱。……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②(宋)罗泌:《究言》,载罗泌:《路史》。
李纲也指出:
“(郡县之制)举千里之郡而命之守,举百里之县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督察之,片纸可罢,一言可令,而无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财赋、甲兵皆归之于天子。……内有乱臣贼子之祸而勿能正,外有夷狄盗贼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动,有土崩之势”。③(宋)李纲:《论封建郡县》,收入《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李纲也认识到,封建制有它自身的缺陷,那就是中央政府相对微弱,可能不足以管束地方诸侯,容易出现地方反叛或相互征伐之事。所以,李纲谓:“(封建)至其弊则强侵弱,大并小,僭礼乐,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蚕食之患”。见李纲:《论封建郡县》,收入《李纲全集》。
至明清两代,这种观点又有新的发挥。明代陈邦瞻著《宋史纪事本末》,说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朝廷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陈邦瞻评曰:“主势强,国势反弱矣”。④(明)陈邦瞻:《宋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12页。清代颜元更指出,天命本无常,政权难免易手,在封建制之下,政权易手较易,所谓“一战而天命有归,无俟于数年数十年之兵争而处处战场也”;在郡县制之下,政权易手较难,一旦面临易手,则有天下土崩之难,所谓“闻京城失守而举世分崩,千百成群,自相屠抢,历数年而不能定也”。⑤(清)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0-113页。
本文无意评论中国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而是指出,上述观点揭示了郡县制国家的一个特征:郡县制有助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有助于形成强大的统治能力,所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天下之势一矣”;但是,却弱化了国家本身的凝聚力,以至于“天下震动,有土崩之势”。我把此种观点概括为“强政权,弱国家”,即陈邦瞻所言“主势强,国势反弱矣”,也是罗泌所说的“郡县失之疆,而实以弱”。
所谓“强政权、弱国家”,是指这一类国家拥有强大的中央政权,中央政府的权力又最终集中于一人之手,形成强大的统治能力,所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但是,国家作为各地区和所有民众组成的共同体,其本身却比较脆弱,它主要依赖中央政权的支撑,一旦中央政权衰落,国家就面临瓦解。“强政权,弱国家”的典型例子就是秦王朝的兴起和速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同时,在县以下建立乡亭制等社会管理和控制系统,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郡县制国家。始皇自己则“忧恤黔首(庶民),朝夕不懈”。依靠这种郡县制的国家体制,秦王朝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发劳役,从事浩大工程和大规模征伐战争。⑥仅伐匈奴和征南越,征发兵丁和力役总数就在200万人以上(张荫麟,2005,第167-168页)。然而,陈胜、吴广一次小规模的造反事件,却引发了各地区大反叛,秦王朝及其建立的郡县制国家随之崩溃。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陈胜起兵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卷四八《陈涉世家》:“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其中,起兵响应的重要者有:陈婴起东阳,刘邦起沛县,项梁、项羽起江东,英布蒲将军起江中,张良起下邳。参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 51,333,535页。
二、郡县制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
我们所关注的是,古代学者提出的“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郡县制国家与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关系,而且具有更一般的理论分析价值。
首先,它提示我们在研究国家的建构和国家转型上,要注意到政权与国家共同体(或曰“天下”)之间的区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区分至少到顾炎武这一代学者,已经有了清晰的意识。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①顾炎武:《日知录》(上卷),《正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97页。
其次,“强政权、弱国家”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认识郡县制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②本文把国家建设分为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这两个维度,与埃特曼(Thomas Ertman)把国家分成两个构成性部分,有一定的关联。埃特曼所区分的两个构成性部分,一是政权类型(political regime),一是国家基础结构的特征(the character of state infrastructure)(Ertman,1997)。不过,埃特曼的分类仍与本文有区别。在我看来,国家的政权类型从君主制向宪政体制演变,主要属于国家共同体的建设;国家的基础结构从世袭制向官僚制的演变,既属于政权建设,同时,也是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部分。
所谓“政权建设”,是指统治者在领土上建立统治权和加强统治权的建设,也是统治者及统治集团强化统治能力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政权建设包括两个方向相反的过程:一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内,权力向中央政府和统治者集中的过程,一是中央权力向各地区延伸和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过程。在前一个方向上,政权建设是指权力在领土内向一个中心集中、建立中央政府和官僚系统,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又进一步向统治者集中,形成以统治者为核心、并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国家(state)。在后一个方向上,政权建设是中央权力向各地区和基层社会延伸的过程,以建立对各地区的控制及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建设的开端是“打天下”。此时,旧王朝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国家陷入混战之中,谁能成为新政权的主人,依赖于谁在战争中最终战胜所有的竞争对手。经过数年或数十年的厮杀,最终出现一支最强大的武装集团,打败了主要的竞争对手,所谓“天下初定”。这时,政权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得胜一方的领导人开始称帝、定都、建国号,着手建立中央政府。此时,中央政府未必能统治全国,因为仍有部分地方武装尚未臣服,各个地区也需要重建地方政府。因此,政权建设的第三个阶段是平定尚未臣服的地方武装,划分地方行政区,在全国各地区建立地方政府。至此,新的政权才算是稳定地建立起来了,开始统治整个国家。第四阶段是巩固政权和维护政权,这一阶段将持续到王朝的终结和新一轮“打天下”的开端。对统治者而言,第四阶段的政权建设是一项既持久又艰巨的工作,包括的主要内容有: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以控制民众思想,建立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系统(如户籍制、乡亭制、或保甲制),以管理和控制民众的行为,建立政府专卖或专营制度以汲取资源,建立察举制或科举制以吸纳民间精英,建立监察系统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等等。
所谓“国家共同体建设”,是指在国家领土内,把分散的个人和地区联结成统一的、具有内聚力的共同体的过程。这种共同体的最高形态是由所有国民组成了一个共担国家责任、共享国家收益的国民共同体。这一过程包含着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发展,如:国民对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国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共享国家利益的政治制度之形成与发展,国民共同遵守的法律之形成与发展,等等。当然,从情感和心理上说,国家共同体表现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所谓“想像的共同体”(Anderson,1991)。但是,这种认同可能很微弱,也可能很强烈,其强弱程度不取决于国家认同本身,而是依赖于在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维度上,国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状况。这些不同维度上的国家共同体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联结所有国民的纽带。
当然,政权建设和国家共同体建设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也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推进的(Finer,1975)。例如,权力在领土内适度集中,建立有效运作的中央政府,既是政权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就难以抵御外部入侵,难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内和平,国家共同体必定非常脆弱。反过来,国家共同体建设也有助于政权建设。如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国家认同,使得中央政府更容易统治国家。再如,全国性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既有助于形成经济共同体,也提高了政权合法性。
然而,在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冲突。此种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两者目标不一致所导致的。政权建设的目标是统治者及统治集团建立对国家的统治权,及加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控制权,以提高统治能力,确保政权安全。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目标是把国家建设成所有国民共同的家园。为此,需要建构国民共同参与、共担责任、共享国家利益的政治制度;同时,也需要把政府建设成受民众控制和监督的公共服务机构,为民众提供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并保卫国家共同体的安全。为了实现政权建设的目标,需要限制国家共同体的发展,特别是限制在社会和政治维度上国家共同体的发展。这是因为,国家共同体的发展将削弱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控制权,并产生约束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力量,因此,不利于统治者强化统治权。所以,如果政权建设不受限制,统治者及统治集团将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分化或阻止国家共同体的发展,使得民众处于分散状态,难以采取协调行动;与此相反,为了实现国家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就需要限制政权建设,约束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权力扩张行为,削弱其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以保障国家共同体的发展不受统治者的权力扩张所阻挠。
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之间的冲突将导致何种结果,依赖于统治者、地方精英、普通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郡县制国家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结果,是政权建设居于支配地位,甚至压倒了国家共同体的建设,这就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大困境:它的兴盛依赖于政权的强大,而政权的强大又难以持久,所谓“天命无常”,所以,国家难以摆脱治乱循环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国家面临着周期性的瓦解和重建,无法形成永久国家。①永久国家(perpetually lived state)指不随政权转移而瓦解的国家。也就是说,永久国家的特征是,政权可以更替,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可以更换,但是,国家不会瓦解。“永久国家”的概念来源于诺斯(Douglass North)等论述专制国家向宪政国家转型的前提条件,其中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着永久性的精英组织,包括国家本身”(Perpetually lived forms of public and private elite organizations,including the state itself.)(North,John Loseph Wallis,and Barry R.Weingast,2009,pp.26,158-169)。这种困境揭示了“天命观”在理论上所留下的一个大漏洞:如果统治者可以自由地从加强政权和确保政权稳定出发,建构出严密的郡县制国家,那么,天命转移之后,国家怎么办?②如清代陆求可所述:“夫天下不能长治而无乱,一姓而不移。然而,制度之善,尤足以维持而不至于太甚,而民亦得以小安而不尽至于肝脑涂地,凡以屏翰中国也。”陆求可:《封建论其一》,载《密庵文集》卷二,康熙二十五年王霖刻本。
三、郡县制国家的转型方向
在思考上述问题上,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认识到郡县制与封建制都会导致暴政,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为此,他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③(清)顾炎武:“郡县论一”,载《顾婷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这一观点含有地方自治的精神。到清末,学者们在顾炎武开辟的方向上,开始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国家建设理论。如黄遵宪所述:“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矣。……(如此)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至一省,由一省推至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④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卷),第406-407页。康有为重新解释“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意义,说:以前所说的“封建”,就是今天说的地方自治,其中的变化仅在于,由“封建其一人”转变为“封建其众人”。⑤康有为:《官制议》,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74-275页。据此,康有为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的趋势是由封建制,到郡县制,再到郡县自治。“凡封建之后必行郡县,大约封建世及,行于草昧初开之时,据乱之制也;郡县派官,行于大国一统之时,升平之世也;郡县自治,皆由民举,太平之世也”。⑥康有为:《日耳曼沿革考》,载《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252页。
上述观点主张用地方自治改造郡县制国家,寄希望于在地方层面生长出制约政权建设的力量,以推动国家共同体的发展。限于篇幅,对于此种观点,本文恕不展开讨论。
[1]曹正汉,2017,“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即出。
[2]陈邦瞻:《宋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3]顾炎武:“郡县论”,载《顾婷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4]顾炎武:《日知录》(上卷),《正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5]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康有为:《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李纲:《论封建郡县》,收入《李纲全集》,王瑞明点校,岳麓书社,2004年版。
[8]陆求可:《封建论其一》,载《密庵文集》卷二,康熙二十五年王霖刻本。
[9]罗泌:“封建后论”,“究言”,载罗泌:《路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0]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张荫麟,2005,《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2]Creel,Herrlee G.,1970,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Ertman,Thomas,1997,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Usher,Dan,1989,The Dynastic Cycle and the Stationary Stat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79(5):1031-1044.
[15]Yang,Lien-Sheng,1954,Toward a Study ofDynastic Configur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17(3):329-345.
[16]Zhao,Dingxin.2015.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