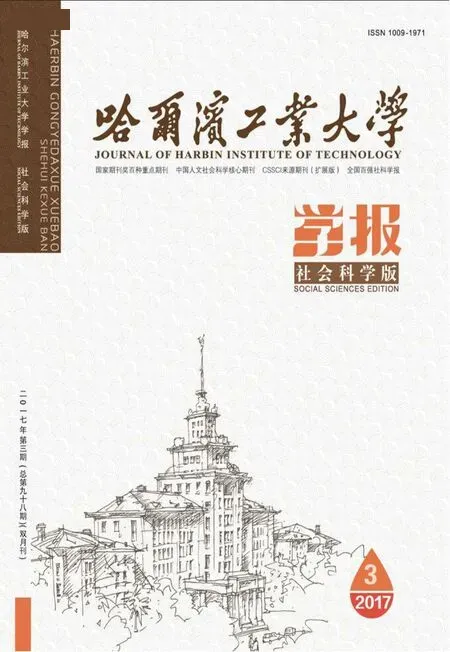清代前中期严羽“以禅喻诗”说之争
——基于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的考察
2017-02-24党晓龙
党晓龙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清代前中期严羽“以禅喻诗”说之争
——基于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的考察
党晓龙
(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2)
清代前中期,诗学领域围绕着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为数众多的参与者中,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所持立场、相关论说代表着此期对于严羽“以禅喻诗”说接受的三大主要面向,其各自观点分别折射出此期诗人、诗论家们对于严羽诗学思想的合理性反思、理论延伸与经典解构。透过这场论争,能够侧探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思想脉络,进而体认文学、思想的互动与交融。
清代前中期;严羽;以禅喻诗;熏习;诗禅一致;儒家诗教
“以禅喻诗”是严羽极为重要的诗学主张,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有言:“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1]251诚然,“以禅喻诗”并非严羽首创,皎然、司空图、苏轼等人早已借参禅来谈诗。但是,严羽在承袭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日臻完善,堪称“以禅喻诗”说之集大成者。纵观元代宗唐诗法、明代复古诗学、清代神韵诗论等,均与此说关联甚密。清代前中期,诗学领域围绕着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展开了激烈论争,代表有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三位诗坛巨擘,钱谦益乃批判、矫正并举,王士祯则积极肯定和继续深化,李重华却全盘否定与重新立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折射出此期诗人、诗论家们对于严羽诗学思想的反思、延伸和解构,凸显文学、思想的互动与交融。
一、钱谦益:将“以禅喻诗”导向借“熏习”言诗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蒙叟、东涧老人,清初著名诗人,主盟诗坛数十年,世称虞山先生。钱谦益针对严羽的“以禅喻诗”说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认为严羽不知禅、不通禅,其诗学理论涉及的佛法禅理存在诸多矛盾与缺失,进而否定了严羽以“妙悟”为主的论证方式;同时,借用唯识宗的“熏习”概念言谈诗歌创作原理,矫正严羽诗论,探索阐释诗歌与佛教交涉的崭新路径。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曾说: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1]11-12
依此说法,严羽将“大历以还之诗”与“晚唐之诗”视作两类,分别为“小乘”和“声闻辟支”;又将学汉、魏、晋、盛唐诗歌的人归为临济宗门下,将学大历以后诗歌的人列为曹洞宗门下。然而,从佛学视角而言,“声闻”、“辟支”实则均属小乘佛教,都是小乘佛教的果位;况且临济、曹洞二宗究竟有无高下之分,千百年来众家也是莫衷一是。正因有此论述,故严羽的禅学知识常常受到后人质疑,如陈继儒(1558—1639)就以“杜撰禅”来讪笑严羽:
严沧浪云:“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禅论诗,瞠目霄外。不知临济、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剿其门庭影响之语,抑勒诗法,真可谓杜撰禅。[2]
这一说法被钱谦益采纳与延伸,其于《唐诗英华序》有云:
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谓汉、魏、盛唐为第一义,大历为小乘禅,晚唐为声闻辟支果,不知声闻辟支即小乘也。谓学汉、魏、盛唐为临济宗,大历以下为曹洞宗,不知临济、曹洞,初无胜劣也。[3]707
而深得钱谦益赏识的徐增(1612—?)也积极附和牧斋对于严羽“不知禅”的批评,指出:
愚谓沧浪未为无据,但以宗派硬为分配,妄作解事。沧浪病在不知禅,不在以禅论诗也。恐人不解钱先生意,特下一转语。[4]
当然,针对严羽“不知禅”这一论题,亦有学人持反对意见,如郭绍虞(1893—1984)、王梦鸥(1907—2002)就为严羽鸣不平。郭绍虞指出,据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所示,“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当中并无“小乘禅”、“小乘禅也”字样,如此,便为“若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正因如此,郭氏认为“案钱谦益与冯班均讥严氏分别小乘与声闻、辟支之非,据玉屑则沧浪原不误。”[1]14而王梦鸥则以宋代临济、曹洞两宗流行的情况为例,证明严羽所说临济胜于曹洞并非妄言[5]。有关这一论题的版本考证、宗派源流姑且不论,不过,“以禅喻诗”作为严羽诗学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诗学主张,如果其赖以存在的佛法禅理出现混乱与矛盾,那么其诗学理论的合理性必然会遭到质疑。钱谦益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严羽诗学思想展开批判性思考,着意探寻严羽诗论中可能存在的致命瑕疵,试图动摇乃至推翻严羽“以禅喻诗”说的理论架构,进而否定其论证方式的合理性。
又如,严羽在“以禅喻诗”的基础上标举“妙悟”,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12,“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12。于此论说,钱谦益亦极力批判:
严氏以禅喻诗,“其似是而非,误入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议论,不涉道理,不事发露指陈,所谓玲珑透彻之悟也……今任其一知半见,指为妙悟,如照萤光,如观隙日,以为诗之妙解尽在是,学者沿途觅迹,摇手侧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义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将夷而为中为晚,盛唐之牛迹兔径,佹乎其唯恐折而入也。”[3]707-708
可见,否定严羽“以禅喻诗”的诗文释解之道,反对其以“妙悟”为主的诗文论证之法,是钱谦益力证严羽不知禅、不通禅的旨归所在。
为了摆脱严羽“以禅喻诗”、“妙悟”等诗学理念、论证方式的影响,钱谦益另辟新径,采用“熏习”概念释解诗文之道。“熏习”一词,乃唯识宗的重要理论术语,《成唯识论校释》有云:“如是能熏与所熏,识俱生俱灭,熏习义成。令所熏中,种子生长,如熏苣蕂,故名熏习。”[6]在《高念祖怀寓堂诗序》中,钱谦益又将“熏习”划分为世间与出世间两种,其云:
余谓诗文之道,势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已。有世间之熏习,韩子之所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是也。有出世间之熏习,佛氏所谓“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法水润泽自心,应以境界净治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坦荡自心,应以智证洁白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者是也。世间之熏习,念祖胚胎前光,固已学而能之矣。出世间之熏习,则念祖于琮公,谘决扣击者,故当朝夕从事焉。而世间诗文宗旨,亦有外乎是乎?[7]
由上观之,世间熏习,钱牧斋引用韩退之《答李翊书》里的话语加以论证,意谓重在涵养;出世间熏习,则转引自《华严经·入法界品》,言善财童子询问菩萨修行之道,而对治对象均为自心。钱谦益将唯识宗的“熏习”概念引入诗论,展现出与严羽“以禅喻诗”说不同的论证方式,而这至少也传递出两重信息:首先,清代前中期诗歌与佛教交涉的必然性仍是众多诗论家的共识,但严羽理论的合理性却不断遭到质疑,“熏习”说即在此种背景下产生;其次,“熏习”说可视作清代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对明代复古派诗论的反驳,诚如廖肇亨所言:“相反的,正因为在钱谦益等人看来,严羽是明代诗论(特别是复古派)的重要基石,打击严羽,也就等于向复古派宣战。”[8]71
二、王士祯:从“以禅喻诗”到“诗禅一致”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清初著名诗人、诗论家。王士祯被称为“严羽最忠实的信徒”[8]68,一方面,他对严羽的“以禅喻诗”说予以积极肯定和高度认同,于极力维护的同时加以佛理层面上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在承继的基础上将“以禅喻诗”说进一步衍生为“诗禅一致”说,把诗禅交涉的论题引向更为绝对的视域。
王士祯对《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说推崇备至,曾言: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9]83
又云:
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如谓盛唐诸家诗,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乃不易之论。[9]65
严羽“以禅喻诗”的主张得到了王士祯的极大肯定、认同。王士祯以清远蕴藉的山水田园五言诗歌为参照,释解禅境与诗境的相通之处。在这里,“字字入禅”、“妙谛微言”如同“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神韵天然且不可凑泊。此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1]12,“妙悟”实为“以禅喻诗”之旨归。针对此说,王士祯认为严羽藉由禅宗教理中理想的妙悟境界,来形容盛唐诸家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极致之境。而禅理中内蕴有诗悟,如水月镜像般玲珑剔透、不即不离。
在高度肯定、认同严羽“以禅喻诗”说的基础上,王士祯又专注于两个层面的努力:一是对其相关学说进行大力维护,二是借助佛教义理予以理论肯定。以下分而述之。
面对钱谦益、冯班(1602—1671)等人提出的反驳严羽诗学乃至否定其“以禅喻诗”说的思潮,王士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给予了不折不扣的维护,他在《带经堂诗话》指出:
而钱牧斋驳之,冯班《钝吟杂录》因极排诋,皆非也。[9]65
又在《分甘余话》中讲道:
昔胡元瑞作《正杨》,识者非之。近吴殳修龄作《正钱》,余在京师亦尝面规之。若冯君雌黄之口,又甚于胡、吴辈矣。此等谬论,为害于诗教非小,明眼人自当辨之。至敢詈沧浪为“一窍不通,一字不识”,则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10]
钱谦益对于王士祯有着知遇与擢拔之恩,王士祯对于钱谦益的赏识亦颇为自得。然而一旦涉及严羽诗学,王士祯便与钱谦益划清界限,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性。另据现有历史文献记载,王士祯很少与时人争辩,但冯班却是一大例外,原因无外乎冯班对于严羽诗学思想予以严厉驳议,有时甚至近于谩骂。王士祯极力和知遇钱谦益争论,并与冯班展开激烈争辩,从中可见其对严羽“以禅喻诗”等核心诗学思想不遗余力的维护。
同时,王士祯引经据典,借助佛教义理论证严羽“以禅喻诗”说的合理性,进一步丰富其理论体系,肯定其理论价值。这在《师友诗传续录》中可见端倪:
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理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黏不脱;曹洞宗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知之矣。[11]
以佛教“不即不离”、“不黏不脱”的般若观,借曹洞宗“参活句”之方便门,印证严羽诗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可靠价值。
王士祯对于“以禅喻诗”说的肯定、认同、维护及义理论证,乃因其诗学主张与严羽的诗学思想有着十分明显的承继关系。其一,王士祯倡导清远冲淡的诗歌风格,崇尚含蓄蕴藉的意境构建,强调兴会神到的创作过程,其清闲淡远、含蓄蕴藉的“神韵”说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严羽的“以禅喻诗”说;其二,他对严羽的诗学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出“诗禅一致”说,认为诗禅等同佛法妙谛。例如,《带经堂诗话》有言:
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9]83
而其在《渔洋诗话》中提及的“华严楼阁”之喻,亦是“诗禅一致”观念的生动体现:
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12]
由此可见,王士祯“诗禅一致”说是对严羽“以禅喻诗”说的深入承继与不断拓展。在严羽看来,诗、禅具备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故其借禅喻诗,以期获得诗歌理论方面的更多突破。而在王士祯这里,于“以禅喻诗”说的基础上则进一步强调诗要入禅,直至诗禅一致,达到禅家所谓色相俱空的境界,从而将诗禅交涉引入到愈加绝对的视域。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于王士祯而言,其“诗禅一致”的理论观念不仅用以阐释精微细致的诗禅关系,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甚至意味着一种超然无争、恬静悠游的处世态度。《带经堂诗话》有曰:
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豺再寻他不著,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9]83
妙契佛理的诗论在这里被引申解读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无怪乎“渔洋于党争炽烈的康熙一朝得以全身而退,原来严羽于此亦大有功焉”[8]70,足见严羽诗学对于王士祯全面、系统、深刻的影响。
三、李重华:全盘否定“以禅喻诗”,回归儒家诗教传统
李重华(1682—1755),字实君,号玉洲,雍正甲辰进士,负有诗名。李重华作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儒学大家,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自然成为其诗学思想的核心与主轴。因此,他全盘否定“以禅喻诗”说,通过标举儒家诗教以重新立论。在李重华这里,严羽论说招致反对乃至攻击的根本原因在于严氏诗禅理念与清代前中期相当一批文人、士大夫信奉的儒家经典诗教传统相违背。比如其在《贞一斋诗说》里就曾谈道:
严沧浪以禅悟论诗,王阮亭因而选《唐贤三昧集》,试思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堕入佛事?[13]937
阮亭选《三昧集》,谓五言有入禅妙境,七言则句法要健,不得以禅求之。余谓王摩诘七言何尝无入禅处,此系性所近耳。况五言至境,亦不得专以入禅为妙。[13]929
因王士祯对于诗禅关系的论述承继于严羽,堪称“严羽精神苗裔”[8]92,故李重华在批评严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王士祯。王士祯将禅家所倡导的静寂悠远、恬静自然的意趣视为诗歌创作的最佳境界,王维的诗歌淡泊静远、绝尘脱俗,内蕴着丰厚的禅理、禅韵和禅趣,被王士祯称作“字字入禅”[9]83。综合上述材料来看,李重华认为诗教传统始自孔儒,渊源于儒学,与佛教无关,且于诗歌评价方面绝不应该“专以入禅为妙”。
李重华全盘否定“以禅喻诗”,主张回归儒学,发扬儒家诗教传统,倡导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强调诗歌在歌咏盛德、讽谕末流等治世方面的强大功用,其诗论主张的核心是对“诗教”、“六义”一以贯之的秉持。“诗教”一词来源于《礼记·经解》篇,其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4]而“六义”则最先见于《毛诗序》,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15]关于“诗教”、“六义”,李重华在《贞一斋集》自序中即有论述:
世之评诗,类曰:才思若何?学力若何?风调、品式若何?至诗以立教,未暇析焉。于六义果无憾欤?古之为诗,其词显而易见,其要眇微而难言;无论浅学者不及知,即善学者有未尽知。盖自尼父删述以后,其绝续明晦,未易一二道矣。……盖余诗前此凡五变,最后取笼罩沈著,动合雅正为尚,蕲进,又廿年于兹,欲满志,曾未逮也。咦!诗之长,始则油然而生,究则诎然有节。要惟六义为其指归。[16]
“诗以立教”、“六义为其指归”,体现的是李重华论诗的基准。也正因其崇尚“雅正”、以“风雅”为宗,论诗侧重于政教伦理层面,所以认为诗歌不应当牵涉仙、释二家,《贞一斋诗说》载:
匠门业师谓:平生所抱歉者,仙释二氏书,篇中罕能运用。余曰:以某管见,诗以风、雅为宗,二氏原不入局。以故少陵引用特鲜;义山始参半拦入,坡公则随手掇拾,不以为嫌。究其实,与删诗之旨显然悬隔。且如昌黎专辟二氏,今其诗卓然为一代宗师。是则运用阙如,正属好处,安得自以为歉?业师闻此爽然。[13]938
在李重华看来,杜甫、李商隐、苏轼所涉仙、释之诗,与“删诗之旨”相去甚远;而韩愈辟佛,故“其诗卓然为一代宗师”。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前中期,佛教在诗论史上的地位逐渐衰落,李重华极力摆脱佛教影响的尝试,恰好映衬出时代思潮转移的迹象。
李重华对严羽“以禅喻诗”不以为然、推崇儒家经典诗教的相关论说,与明末著名儒学家郝敬(1558—1639)的诗论主张有着显著的内在一致性,兹录郝敬《艺圃伧谈》中涉及严羽诗学评论的话语二则,其一:
严仪卿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天下无理外之文字。谓诗家自有诗家之理则可,谓诗全不关理,则谬矣。诗不关理,则离经叛道,流为淫荡。文字无理,则无意味、无精彩。三百篇纯是义理凝成,所以晶光千古不磨。今之诗,粉饰妆点,趁韵而已。[17]5909
其二:
严沧浪借禅喻诗……诗本性情,禅宗见性。可以相通,其实不同。禅主空寂,无言为宗。诗者,声音之道,全仗言语动人。……禅耳,与诗何预?[17]5938-5939
郝敬认为《诗经》“纯是义理凝成”,其价值在于可理解性与可实用性的功效,且诗歌依托于动人的言语,与强调高远玄妙、超越形上、无言为宗的禅学并无关联。可见,在李、郝看来,诗禅不能相通,“以禅喻诗”的诗学主张无法成立。矫正诗论,必须回归儒学,重拾儒家诗教传统的理论基石,才能确保逻辑性、实用性的文字在诗学国度的地位、席次。
结 论
综而观之,清代前中期诗人、诗论家们围绕严羽的“以禅喻诗”说,或支持、或反对、或兼而有之,共同开拓出诗学研究的新路径、新领域、新气象;同时,透过这场论争,亦可侧探当时的文学思潮和思想脉络,深入体认文学、思想的互动与交融。
首先,钱谦益、王士祯、李重华所持观点代表着清代前中期诗学领域对于严羽“以禅喻诗”说接受的三大主要面向,清晰呈现出围绕严氏诗学话语系统所展开的合理性反思、理论延伸和经典解构。在此之中,钱谦益秉持批判、矫正并行的方式,王士祯乃积极肯定和继续深化,李重华则全盘否定与重新立论。值得注意的是,就合理性反思而言,钱谦益没有否认诗歌同佛教交涉的合理性,只是反对严羽的论证方式,因此采用唯识宗的“熏习”概念,重新释解诗歌与佛教的关系,尝试二者交涉中不同诠释话语的开创;从理论延伸来看,王士祯作为严羽诗论的坚定支持者与维护者,其“诗禅一致”理念是对“以禅喻诗”说的进一步引申和发展,将诗禅关系的揭示与阐发推进到更为绝对的视域;在经典解构方面,李重华从根本上反对“以禅喻诗”,极力倡导回归儒学,重视儒家诗教传统,强调论诗须以风雅为宗,其观点恰好印证出严羽“以禅喻诗”说作为诗学领域里的经典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解构与演化。
其次,清代前中期严羽“以禅喻诗”说的流变和衍异,与此期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紧密契合。明代后期,复古派于文坛独占鳌头,其理论基石即以严羽诗学为最,而公安、竟陵两派亦受严羽诗学影响颇深,这在诗词、散文甚至戏曲创作当中均有体现。诗禅合流成为当时文坛的共同趋向,禅学更是当时认识诗学的关键门径。入清以后,伴随着文学思潮的渐变,广大文人对于严羽诗学的热衷开始减退。纵使号称沧浪嫡传的王士祯倾力维护与弘扬,但仍难掩严羽在清代前中期诗学国度的黯然失色。钱谦益虽未完全否定严羽诗学,却于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丰富了其他诠释的可能性。在李重华等人的不懈倡导下,儒家诗教重新回归文坛,并且逐渐占据上风,成为莫之能御的文学潮流。
再次,明末清初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深刻影响着文人士大夫们对于严羽“以禅喻诗”说的接受与扬弃。日本学者荒木见悟曾经指出,晚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超越既有的教学藩篱与界限,直探人类存在的本源[18]。此期诗学国度的价值取向印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譬如严羽“以禅喻诗”说中妙悟的目的即在于探求自我内在未曾发现的场域,而非重新转向外在法度的靠拢,这与当时心学的盛行息息相关。清代前中期,思想界经过“经世致用”思潮的洗礼,复归于讲求“温柔敦厚”传统的理学时代。与此相应,诗学走向亦是回归正统,强调切近儒学旨归的雅正创作,典雅与庄重日益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自觉追求。至此,“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口号和主张,重新弥漫于文坛[19]。
[1]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陈继儒.偃曝谈余[M]//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892.
[3]钱谦益.唐诗英华序[M]//钱曾,钱仲联.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徐增,樊维纲.说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0.
[5]王梦鸥.严羽以禅喻诗试解[M]//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4:373-394.
[6]玄奘,韩廷杰.成唯识论校释(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8:128.
[7]钱谦益.高念祖怀寓堂诗序[M]//牧斋有学集(卷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751.
[8]廖肇亨.沧浪诗话与明清诗学论争:以“法/悟”关系为中心的讨论[M]//中边·诗禅·梦戏: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展.台北:允晨文化,2008.
[9]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0]王士祯.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
[11]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50.
[12]王士祯.渔洋诗话[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99.
[13]李重华.贞一斋诗说[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十)[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1609.
[15]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
[16]李重华.贞一斋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3册.影印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17]郝敬.艺圃伧谈[M]//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8]荒木见悟.邓豁渠的出现及其背景[M]//廖肇亨,译.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4.
[19]焦宝.从古诗研究转向反思百年文学史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07-112.
Debate on Yan Yu’s Analyzing Poetics Metaphorically with Zen in the Early and Medium-term of Qing Dynasty——Based on Qian Qianyi,Wang Shizhen and Li Chonghua Examples
DANG Xiao⁃l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Early and Medium-term of Qing Dynasty,there was an intense debate on Yan Yu’s Ana⁃lyzing Poetics Metaphorically with Zen.Among the numerous participants,Qian Qianyi,Wang Shizhen and Li Chonghua are outstanding.They can represent the main
orientation.Meanwhile,their viewpoints re⁃flect the theory explanation,meaning reflection and classic deconstruction of the poets and the critics in this period.
the Early and Medium-term of Qing Dynasty;Yan Yu;analyzing poetics metaphorically with Zen;edification;poem and Zen are consistent;Confucian poem teaching
I206
A
1009-1971(2017)03-0059-06
[责任编辑:郑红翠]
2017-03-28
党晓龙(1988—),男,山西大同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文学、佛教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