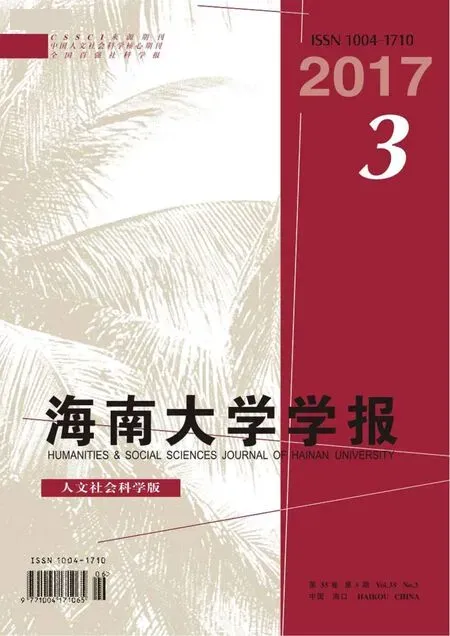战争的现代转向
——卡尔·施米特论战争的概念
2017-02-24方旭
方旭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2)
战争的现代转向
——卡尔·施米特论战争的概念
方旭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2)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一步一步背离传统战争法的规矩。这已经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不是教际之间的圣战,战争的形式已经开始发生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内涵发生改变。卡尔·施米特对“战争概念”研究的跨度长达四十年,他以“划分敌友”作为其战争理论之基础,研究“总体战争”“战争中立性”“游击队理论”等相关论题,考察古典战争与现代战争差异之实质,反思当下国际秩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卡尔·施米特;敌友之分;总体战争;中立性;游击队理论
“9·11”恐怖袭击仍然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它并没有如世贸中心散去的烟尘那样从我们生活中散去,直至今日,恐怖主义的阴云仍笼罩在本是自由女神庇佑之地。这一次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动,以三千余人灰飞烟灭为代价,让美国,或者让整个世界认清了一件事情:即便是武器装备最强大的国度,也抵挡不了来自“例外”力量的致命攻击。核武器、导弹防御系统、航空母舰等等曾经认为可以巩固国家边防的武装力量,在恐怖袭击面前都成为了不堪一击的“摆设”。几次越洋战争也证明美国“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无助于使其国民免于恐惧,去年(2016年)纽约的爆炸事件和明尼苏达州的持刀伤人事件对原本草木皆兵的美国政治生活造成巨大冲击。
事到如今,这已非传统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非各教际间的圣战。我们口头上常常说“反恐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那我们交战的“敌人”是谁?就连受到战争胁迫的法学家们都还在考虑,到底应该制定何种法律定恐怖分子的罪?可如今潜伏在欧洲各处的、随时可能发动超限战的那些人可能压根儿没有把自己看作犯罪的参与者。这是一场战争?抑或是犯罪?这是当前非常迫切要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考察施米特的作品后发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施米特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战争问题,这些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阅读思路,我们将尝试跟随他对战争概念变化的解读,来理解战争概念的转向。
一、战争概念的古今之变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人以传播基督教信仰为由,开启了对美洲新大陆的掠夺战争。实际上,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至少存在三种战争理论传统:一种是以圭恰尔蒂尼、马基雅维利和黎塞留为代表,将“国家理由”(ratio statis)作为“正当性”,从而发动战争的理论传统;另一种是以维多利亚、苏亚雷茨经院神学家为代表,将“万民法”(jus gentium)作为发动战争“合法性”的理论传统;第三种则是以贞提利、格劳秀斯等新教神学家为代表,声称以“正义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战争理论传统。后两种战争理论的最终走向是以“世界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无论哪种传统,他们都属于“无主地”扩张性的战争理论。
1963年,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序言中愤怒地说道,“请神学家们闭嘴!”(silete theologi)[1]95他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时代处境,毕竟德国是两次大战的战败国。他对战争处于“被动观察”状态,而神学家们则规划制定“扩张计划”。另一方面,他显然更加厌恶“神学家们”建立的,打着宗教、道德、自然等旗号,以掠夺为目的的国际秩序,而这些战争法,或者战争规矩制定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他所在的时代。
作为“守势”的施米特开始关注“总体战争”。这个名词是在1935年鲁登多夫的《总体战争》这本小册子中率先提到:“由于人口普遍增长,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战争多样性时代已经过去,总体战时代已经到来。”国家应在各个方面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反对侵略国土的敌人。除了日常战斗,还应该包括精神战,宣传战,甚至采取极端野蛮的手段开展捍卫领土的战争。可敏锐的施米特发现,在他的时代,原本由德国人提出的“总体战争”开始了某种形式的变化,动员举国力量应对敌国侵略发起的“总体战争”演变成了“总体制裁”,而这种制裁存在政治性的双重标准。
要支撑这个论断,还是要回到历史语境:战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老老实实按照威尔逊“十四点计划”放下手中继续征战的武器,逼着德皇退位之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家。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失去了领土、人口、耕地、矿产,还严格限制德国的军备和国防,规定德国支付天价的赔偿。照以往战争法的理念,战争就是掠夺,而如今战争不仅要掠夺,还要“赔款”,甚至还要对战争参与者,乃至整个民族“定罪”。表面上,施米特跟希特勒一样质疑《凡尔赛和约》的正义性,可真正触碰他神经深处的是:战争的内涵是否发生了变化?
战争本身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方式。陆地与海洋之争是世界战争之内涵。一面是以普鲁士-德意志为代表的军队和武装组成的陆军力量,另一面则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经济战争”为主体的海上力量。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获胜,带来了“海洋式”的裁决,“海战在整体上迄今一直是一种针对敌方贸易和经济的战争,因而是一种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战争,是一场经济战,一场通过虏获权、走私权和封锁权同时将中立的贸易卷入战争的经济战……由此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自成一体的国际法体系。”[2]271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本质不过是海上霸权对陆地势力获胜的产物,同时拉开了自由主义法学家们改造“战争概念”的序幕。
仅仅是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仍不能从法理上论证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法律秩序的存在。战争只能建立某种国与国的和平秩序,建立某种超越的秩序必然存在超越国家的人类公敌(hostis generis humani)。自由主义法学家的改造工程需要添加“海盗”这一味元素。
1937年9月11日召开的尼翁会议引起了施米特警惕,“本来混乱无序的人类却突然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反对这个作为人类公敌的海盗,这尤其令人感到奇怪”[2]248。将代表无政府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海盗纳入国际法的管辖,理由就是海盗的强盗意图不加区分地针对所有国家。这样的结果导致,共同的敌人必然引起共同的抵抗,由此可以形成某种共同对付人类公敌的普遍意志,人类公敌的标签要求每个国家得而诛之。我们只需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即可明白,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被拔高到人类公敌的位置,接受某种超越国家的国际法体系的审判。现在理解了,只有超越国家的公敌才配得上超越国家的审判。
自由主义法学家的论证逻辑开始显山露水。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套超越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苏联,泛美联盟,以及日内瓦国际联盟之上的世界秩序,将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一种去国家的、去价值的国际秩序。通过一系列从低到高的规范层级,直到最高规范这一终点,形成一套完整精致的法律体系,保障每个国家在这种规范体系之下正常运行。日内瓦国际联盟扮演的角色便是充当国际秩序纷争的裁决者。
施米特的观察并未结束。一战过后,所谓的国际法,或者日内瓦公约的地位是一种建立在强者的基础之上的“上位法”,已然不是传统战争所说的“契约”。按照国际法对战争的裁定,战争的传统意义不复存在,战争就是国际法意义下的“犯罪”。施米特心中清楚得很:所谓的“总体战争”实际上是战争概念形式上的转变,决定战争的关键仍然是强大国力(武装力量),法庭裁决不过是掩盖在国家强力之外的一件法律袍子。可是,国际法庭表面上的“中立”,是对“敌人”概念的否定,它们希望通过“中立”的理性秩序实现法律规范秩序,从而终结政治性的“敌人”。可是——理性秩序是否是中立的?抑或,战争期间是否存在中立立场?
二、战争期间是否存在中立?
所谓“中立”原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特征。他们认为“中立”原则的本质是一种“对各种不同的善的平等的尊重”,并实施不偏不倚的判断。后世甚至有学者将中立性原则视为自由主义内在的本质之一。那么,在敌友区分之外,是否还存在某种“中立”的概念?
施米特在《新的“哀哉,中立者”》中借用但丁《神曲》的描述,提到了一群对“神”“既不叛逆,也不忠诚,只顾自己”的天使,这群天使“不受天堂所容,也不为地狱所接纳”,“他们盲目的生命是那么卑鄙,凡是其他命运他们都嫉妒,慈悲与正义摈弃他们。”*本段内容选取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第三章25~51行。据朱维基在译本中的注解所述,《圣经》内并没有提到这类天使,或许是但丁依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2]260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提倡把是否存在正义的问题交托个人,这种中立立场无力实现政治决断。施米特评论道:“但丁,这位在英语世界中著名学者,他描述了神与魔鬼的征战中,遭受到常人不可承受的试探和惩罚的天使,即便如此,天使仍然恪守中立:不仅仅是因为天使判了罪,违背了他们承担的为正义而战的义务,还因为他们对最为切身、真挚的利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换句话说,战争下中立者所遭受的这般命运,不仅但丁、甚至马基雅维利都表示赞同。”[3]
据此,施米特注意到对于“战争”而言,不存在什么“中立”,只存在“要么中立,要么不中立”的原则,绝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半中立或者局部中立。除此之外,还存在某种“伪中立”——他发现在某些特定场合,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立性的概念批评对方具有政治性,而这种“伪中立”政治性更强。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举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将法国向德国强行索要款项称为“赔款”,而非“纳贡”的例子[1]136,认为,“赔款”听上去要更有法律意味,更具非政治性色彩。但实际上,“赔款”要价更高,更能够出于政治性从法理上和道义上谴责“敌人”。如此,即便号称“中立”的“中立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中立国”如何对道义上的“全民公敌”保持“中立”?
施米特用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为例。他认为1907年10月18日第五次海牙协议将“中立”作为军事上的关系对待,但现实是,1907年之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军事上的中立,并不能代表其作为“总体战争”下的经济制裁中立,“至于瑞士——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它加入日内瓦联盟的‘中立条件’是一个只是生存上的意义,而并非恪守19世纪中立概念的内容的义务”[2]262。实际上,只需要稍稍读一点二战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尚未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施米特慧眼独具,瑞士中立的实质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尽管瑞士在口头上谴责纳粹的侵略行为,实际上他们不仅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瑞士银行还向纳粹源源不断输送黄金,成为纳粹征服欧洲的动力。
施米特论及“中立”问题时,特别谈到了美国,并提醒读者们注意比较威尔逊总统1914年8月19日与1917年4月2日的声明之差异,从而看看威尔逊是如何通过玩弄“中立”的字眼来获取美国国家利益的。1914年的威尔逊通过宣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趁着各交战国对军需物资的巨大需求,以及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减弱的机会,拼命扩大工农业生产,加速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发表了一战后的著名和平纲领“十四点计划”。实际上,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体现了美国企图冲破长期由欧洲列强主宰的国际格局,以争夺世界领导权,建立美国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在他看来,威尔逊的态度转变得很快:从对第三方参战国“不敢发出声息的被动态度”转向了“代表人类、民主和国际法,以裁判身份出现,就战争的正当和不正当作出裁决”。威尔逊的这种态度具有“从此一极端到彼一极端过渡的典型意义”[2]260。
反观战败后的德国,因为对和平的渴望选择了民主议会制国家,但严苛的《凡尔赛条约》使得当时的德国人产生了巨大挫败感。可以说,对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的“殷切盼望”与《凡尔赛条约》的现实打击是魏玛共和国成立时面临的国际背景。对于民众而言,一方面他们认为《凡尔赛条约》是强加的和约,这是一纸并未经过任何谈判,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卖国文书。另一方面,德国人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防御性战争,即便是要签订合约,也不应该由德国独自为战争负责,他们只是因为战败而不得已接受了《凡尔赛条约》。当象征君主制的哈布斯堡王朝崩溃,随之“舶来的”民主化制度,再加上《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屈辱,这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得德国人极度反感一战战胜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也是导致魏玛共和国局势动荡的直接因素。既然现实政治空间从来就容不下某种战争的“中立”,那么对于战争法而言,是否会按照自由主义法学家们预想的那样,建立某种国际法律秩序呢?施米特发现了一种冲击古典战争法的“例外”。
三、游击队理论:政治是战争的延续
“1927年,那时还没有人会料想到游击队问题”[4],施米特曾在1969年回忆道。在这里,肢解古典战争形式似乎有了两股力量:一是此前所说的自由主义法学家极力构建的“总体制裁”下的国际秩序,另一个则是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他们作为一种“例外”突破了人们对古典战争法的认识。
《游击队理论》的一开头就说明,之所以说“游击队”是现代的,是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古典游击队理论,即便是“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游击队只可能是边缘现象”,按照以往的国与国之间的古典战争法作战,也根本不会给“游击队”留下任何空间。施米特注意到,只有内战和殖民地反抗战争与游击战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欧洲公法定义的战争,是一支国家正规军与另一支国家正规军展开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公开内战被视为可以靠警察和正规部队围剿镇压下去的武装起义”[1]274。游击队理论以自己独树一帜的战法终结了古典战争法。
游击队理论可以追溯至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中就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涉及游击队理论的重要命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区分“游击战士”与“海盗”“恐怖分子”,虽然他们的服装都与正规军队不同,游击战士的穿着使得他们贴近人民,进一步依靠人民,他们的身份既是“战士”,同时也是“人民”。“海盗”“恐怖分子”决然不具备游击战士“人民性”的政治品格。
游击战士因外敌入侵而产生,以将外敌赶出国土为目的。游击战士在“原则上始终都是守势”,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基于对母国土地的捍卫和依恋,在战术上具有极强的“依托大地的品格”。游击战士不可能依靠任何条件从守势地位变成某种绝对进攻,所以他们要紧紧依托“大地”:山脉、森林、热带雨林或者沙漠,等等,正如瑞士军事协会《游击战指南》所说,作为一名抵抗的游击战士,他们“只在夜间活动,白天在森林里休息”。施米特借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对俄国游击队抗击法国军队的描述,淋漓尽致地描述了游击战士的特点,“托尔斯泰将1812年的俄国游击队员升华为俄罗斯大地自然力量的代表——俄罗斯大地抖落盖世皇帝拿破仑及其声名显赫的军队,就像抖落自己身上可憎的害人虫”[1]275。
“政治性”是游击队员的第一特性,他们作战的对象是“敌人”而不是“罪犯”。施米特已经嗅到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者故意模糊“敌人”与“罪犯”之间的区分,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列宁和毛泽东正是通过游击队理论将“敌人”这一概念复归战争,从而明确战争不是“犯罪”行为。
列宁在1906年9月30日和10月13日的《无产者》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游击斗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意识到暴力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并将游击队战争拔高到革命要素不可缺少的部分:“游击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使用这种形式无需教条主义或者预定原则,正如人们根据事态必须运用其他合法或非法、和平或暴力、正规或不正规手段和方法一样,目的是在世界各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凡是服务于这个目的,便是好的和正当的。”[1]301
除此之外,列宁是第一个将游击战士改造成“革命者”的职业革命家。他将阶级斗争哲学与游击队员的属性结合,具有阶级性觉悟的游击战士攻击的对象是无产阶级绝对敌人——资产阶级,“现代游击队员是真正的非正规者,并因此成为对现存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否定,成为敌对关系的真正的贯彻者。”[1]303自此,游击队理论不仅仅属于一种战争的概念,更体现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他的游击队理论逻辑框架之内,继承了列宁关于“绝对阶级敌人”的预设,广泛结合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将绝对的阶级敌人与“实际敌人”结合,通过对“敌人”概念的建构,广泛发动“大地上”的群众,造成一种全民皆兵的局面,游击战士“在人民中运动,隐匿其间,如鱼得水”*施米特对毛泽东的这段引文暂时找不到原文出处,不知是否因为德语译本转译导致,但基本符合毛泽东游击队理论要旨。。
同列宁的游击队理论一样,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也在改变传统的战争概念。游击队理论的实质在于区分敌友,熟读克劳塞维茨的毛泽东——他的游击队理论更接近“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内核。
对于毛泽东而言,和平只是一种实际敌对关系的表现形式,是战争创造和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本质便是要求战争为政治服务。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转述毛泽东的话“革命战争只有十分之一的公开的军事战争”,以此来说明毛泽东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1962年,施米特在《第二次战争之后的国际秩序》一文中详细阐释毛泽东这句话,并区分了“冷战”和“热战”:“换句话讲,革命战争是十分之九的冷战和只占十分之一的热战,即使这十分之一非常关键。当我们思考冷战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注意到的比例。因为,只有敌意才构成每一场战争的实质,而它在十分之九的冷战中并不少于那其余的十分之一,不少于所谓的热战。”[5]施米特将毛泽东游击队理论置于极高的理论地位,二者的共契在于他们都认为“战争服务于政治”。施米特在1963年写了《游击队理论》,其副标题便是《政治概念的附识》,可见其游击队理论仍是基于政治的概念,尽管战争概念的形式发生了转变,但是政治上的敌友之分并未消失。
四、“人类的最后一战”
无论如何,自由主义法学家执意在欧洲公法基础之上构建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取消传统意义上“热战”的做法。他们天真地认为,“若想最终实现普遍和平与建立新世界秩序,只需要消除像希特勒德国这样的障碍就行了”,他们将“世界秩序的成立”视为“人类最后一战之终结”,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若这种方案当真可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裁决就理应带来世界和平秩序了,但情况并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只要消灭了传统的战争,就会带来真正的和平,甚至认为取消了正规军就意味着和平”,这就是和平主义者政治幼稚病灶之所在。就以当时世界公认的最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魏玛共和国为例,在她的襁褓中诞生了欧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我们由此而见微知著。大洋彼岸的列奥·施特劳斯对这个问题看得最为真切:
如果人们试图取消政治,就必然陷入无措的境地。当且仅当取消政治的力量变成政治性的,这种努力才有望成功;也就是说,只能它强大到足以把人群分成“朋友和敌人”,从而“能够促使和平主义者与非和平主义者开战”,“以战争反对战争”时,取消政治的努力才有望成功。由此,这场战争确定无疑成为人类的最后一战……以人性为借口消除政治性的努力无非就是非人性的增长……[6]
如果说16世纪开启的殖民活动宣告了瓜分地球空间的浪潮的开始,那么,由之产生了约定俗成的“战争概念”,即通过“热战”确立地球空间的新秩序。二战后,美、苏两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秩序的根基,在世界真理的裁决权的追逐中,两者从世界秩序的同盟分裂为意识形态差异的敌人,从而形成“冷战”局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地域空间逐渐被工业发展打破,传统的“热战”开始从人们的生活中渐渐远去,这场悄无声息的“冷战”让人产生了“战争终结”的错觉。
施米特嘲讽和平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冷战”并不意味取消了政治中的“敌友之分”,就连二战后成立的“普世和平的崭新机构就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两人疑窦重重的友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建构起来的所有限制和监督战争的传统体系的概念口袋被捅破了,冷战是对战争与和平和中立、政治与经济、武力与文明、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的一切古典区分的嘲讽,而不仅仅是对敌友的古典区分的嘲讽,尽管敌友区分的逻辑一贯性成了冷战的源头和本质”[1]306。
如果把国际政治视野聚焦在战争这一维度,我们认为造成“冷战”的局面不单单“归功”于世界战争后的政治均势,还受制于游击队战法的兴起:这一战法从1932年中国以之进行抗日战争起受到关注。因为职业革命家列宁和毛泽东运用游击战法大获成功,此一战法为各国所重视。游击队理论所创造的多维作战空间、以少量的游击队员钳制大规模的正规军队的战法已然成为武装战斗常识,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的 40 万法国军队被 2 万阿尔及利亚游击队员打败,最终导致法国放弃了阿尔及利亚,更加彰显了这一现代战法对传统战争概念的冲击,也降低了武装力量均等的双方启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工业技术迅速发展,尤其在二战之后,离岸开展的大规模的海战、空战甚至核战——仍然存在着灭绝人类的可能性。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将人类置于最为危险的境地,人类的命运在苏美两国的核按钮器下苟延残喘。工业-技术将武器的毁灭能力提高到纯然毁灭人类的程度,“一半的人成为另一半人以原子武器武装起来的当权者的人质”[1]327,既然是一种“绑架态势”,就能造成某种程度的战略威慑下的均势平衡,大型杀伤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反倒降低了大规模灭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冷战”带来的是“和平”掩盖下的潜在战争,这种战争包含经济战争、意识形态渗透、语言文化入侵……这同样会带来某种敌友之分下的残酷战争。施米特向读者表明,对战争这种代表国家意志的极端方式的考察绝非限于规范法律体系的框架,而应该将其放在政治概念的本质下理解。“冷战”并不等同于“非战”,眼下的“暂时的和平”也并非代表“热战”的戛然而止。只要国家存在,政治存在——战争便会以各种面貌在各种领域呈现。
五、 余论:作为人类生存必要之战争
根据施米特“政治就是命运”的教诲,“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政治都使得人们处于历史和最终审判的境地,人们超越其私人意图进入到精神与精神作战、生命与生命搏斗的伟大事件”[7],只有在命运裁决的战争之中,才能诞生新的秩序。
这个教诲提醒我们:不要受到自由主义者的中立性外表迷惑,只要战争触及到其生存空间,立马就会显现出其政治本性。和平主义者 “战争反对战争” 的口号恰恰证明了和平主义者已经拥有政治性,并且能够通过划分敌友找到自己的阵营。另外,我们也要意识到斗争的永恒性并不代表要将敌人绝对化,所谓政治的敌人是一种特定情势下的敌人,多元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斗争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现状,如果不能保证世界多样体形态,而采取一种全盘否定和决然消灭的敌对关系,对当代社会秩序是一场灾难。
无论战争的形式和概念如何转变,关键还是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争便是保存国家生存的最极端的形式。除了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力量能够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如果国家不具备战争法权,那就意味着国家的死亡。自由主义法学家采取的迂回策略——通过建立某种超越国家的“上位概念”,将政治从国家中抽离,使得国家成为法律秩序中平等的一份子。要实现这一策略,首先要瓦解维持国家秩序之根基(武装力量)。要从根本上转变战争概念,说到底就是要拔除国家生存的最后保障,取消国家的正当战争法权。这群声称取消战争的战争分子,他们一边谴责别人发动的战争,一边又发动自己认为“捍卫和平”的战争,这种“永远消除战争”的口号,简直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和平永远不会自行降临,和平只有靠战争才能换得,眼下的暂时和平之根本在于国家之间的国力制衡,而非依靠国际法的约束。
到了这里,再来反观世界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机,该如何重视恐怖主义与战争概念之间的联系?不能将恐怖袭击视为一种简单的“海盗”攻击,因为他们作战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不仅是为了谋财害命,这是一场“战争”,不是“犯罪”。将某国定为恐怖主义国家,再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已是过时的战争“套路”。
战争概念又要发生转向?反恐战争的思考又一次拉开国家权威与人类生存之间富有张力的政治之弦。如何对待施米特对战争概念,特别是政治概念的解释,事关如何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大问题,值得深思。
[1]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M].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Schmitt C.Die Wendung zum diskriminierenden Kriesbegriff [M]. Berlin:Duncker & Humblot,2003:51
[4] 施米特,什克尔.与施米特谈游击队理论[M]∥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卢白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5] 施米特.第二次战争之后的国际秩序[M]∥吴彦,黄涛.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李柯,译.未刊稿:44.
[6] 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 [M]∥刘小枫.施米特与政治法学.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3.
[7]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M].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8.
[责任编辑:孙绍先]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War: Carl Schmitt's Concept of War
FANG Xu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ongqing Party Institute of CPC, Chongqing 400042, China)
After the two world wars, “war” has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the rules of traditional war. Rather than being a traditional war between countries nor a Jihad among religious denominations, the forms of war have transformed, which,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e change of its connotations. Carl Schmidt’s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war” lasts about forty years. With “telling enemies from friends” as his theoretical basis of war, he studies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otal war”, “existence of war neutrality” and “Partisan Theory”, investigating the essenc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lassical war and modern war while reflecting on real problems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is confronted with.
Carl Schmitt; friend-or-foe theory; total war; neutrality; Partisan Theory
2016-12-31
方旭(1984-),男,湖南衡阳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古今政治哲学方向研究。
D 505
A
1004-1710(2017)03-00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