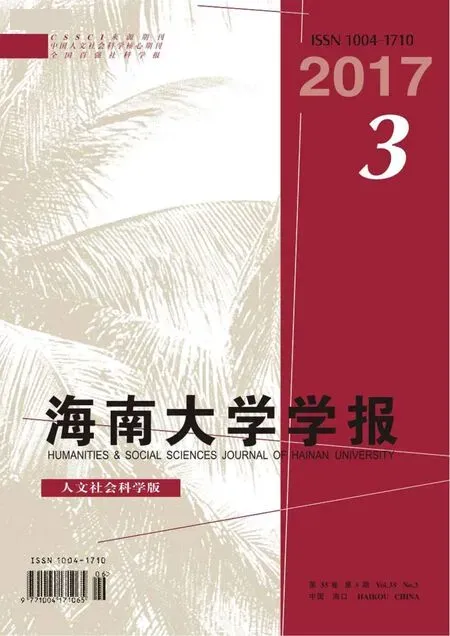语言、历史与霸权: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建构
2017-02-24李永虎
李永虎
(1.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安外国语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28)
语言、历史与霸权: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建构
李永虎1,2
(1.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2.西安外国语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28)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开创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理论的先河,由此他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双重兴起汇聚于一身。其语言学思想较之西方现代语言学,一个突出之点是将语言的历史性放在首位,由此他批判了三种错误的语言观:美学性的谬误、建立普遍理想语言的乌托邦和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葛兰西建立的语言政治学是解读其霸权理论的不可忽视之维。在对民族语言形成的路径研究中,葛兰西发现了资产阶级收拢个体分散意志并使之保持统一的秘密。这种语言政治学,在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扩展至对权力运作的微观分析的同时,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出现的“符号学转向”埋下了伏笔。
葛兰西;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文化霸权
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2012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如何改变世界》中,曾这样评价葛兰西的历史地位:“葛兰西已经成为我们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他作为原创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在我看来是1917年以来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除了继续发掘葛兰西政治哲学、文化批判理论与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关联外,他的语言观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之相关的背景是,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语言学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是否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语言本身的理论上贡献甚微”[2]。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其奠基者卢卡奇也只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脚注中暗示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3]。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这个概念的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提的呢?至此,笔者认为,展开对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别具理论意义:与同时期其他无产阶级理论家相比,葛兰西不仅有自始至终研究语言学的高度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还开创了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社会政治理论的先河,由此在无形之中将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双重兴起汇聚于一身,并最终向世人表明,在对人类语言的解释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研究方法,因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而其自身的语言学思想则构成续写这一理论传统的关键一环。
一、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缘起
在葛兰西的理论著述中,语言问题始终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论及他对语言学研究的志趣,有学者曾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贯穿葛兰西的一生——一个撒丁岛人、一个都灵大学语言学的学生、一个政治家、一个狱中作家、一个理论家——以及在他所发展并被其称为‘活的语言学’的实践哲学之中,都涉及语言。”[4]那么,主要身份是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非语言学家的葛兰西为何会如此重视语言问题呢?笔者认为,除了葛兰西独特而可贵的品质——从不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尝试通过对语言和霸权关系的思考,以努力探索打开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的可能方式之外,他在1929年2月8日列于笔记本1中两个有关语言研究的题目——“新语法学派和新语言学派(‘这个圆桌是方的’)”、“意大利的语言问题(曼佐尼和阿斯科里)”,为我们寻找其自身语言学思想的缘起提供了原初的线索。具体而言,前者指向葛兰西求学时期所接受的语言学学术训练背景,而后者则与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语言统一问题相关。
首先,就葛兰西的早期求学经历来看,他在1911年冬进入都灵大学文学系现代语言学专业学习时,遇到了意大利当时著名的新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巴托利(M.Bartoli)教授。巴托利不仅发蒙了葛兰西语言学的研究兴趣,而且对他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托利在驳斥新语法学派“语言孤立、自发发展”的机械实证主义的观点过程中,受早期语言学家阿斯科里(G.Ascoli)和吉列隆(M.Gilliéron)“语言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启发,对语词相互竞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两个分属不同文化的语言单位,如两个近义词或短语,当它们汇集到一个语言系统中时,因相互竞争关系会导致一个语词被保留而另一个将不再被人们使用。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中一个语言单位能胜过另一个呢?在巴托利给出的五种影响因素中,他着重强调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两种语言发生接触后总会产生冲突,正如它们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两种文化会发生冲突一样。到底哪种语言单位能够胜出,最终取决于它所负载的文化影响力的作用。巴托利的此种“文化冲突论”对葛兰西的影响是显见的。如,“语言习得就是学习特定人群的文化表达方式”,“语言不存在单性繁殖,语言生产着其他语言。创新产生于不同文化的碰撞”[5]177-178,这些不时出现在葛兰西早年著述中的词句,说明了他在青年时期就已形成“语言是文化和社会历史概念”的判定。
不过,不能就此认为葛兰西一直都是新语言学派的忠实拥趸,相反就像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一样,新语言学派之于葛兰西只是他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导引。在汲取了新语言学派合理的历史主义方法和分析语言变化的社会学视角之后,这位被巴托利盛赞为“被派来一举剿灭新语法学家的天使”[6],还是离开了语言学家之间的这种学术攻讦——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的葛兰西从来无意成为一名学院派的语言学家,而在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研究中,他也从未将语言问题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相反,从研究语言学时起,他就将语言学范式和社会现实联系了起来,正如意大利学者皮帕诺(Franco Lo Piparo)所言:“‘语言’、‘世界语’和‘词汇’等术语的隐喻使用,以解释严格意义上语言领域之外的现象,这是葛兰西智识游历的一种显示。语言本身及其共识功能,既被间接地认为是社会生活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被当作是这个广大而复杂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7]135
其次,葛兰西语言学思想的发轫还离不开意大利一直存在的“语言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意大利境内语言状况可谓复杂多样。虽然早在14世纪随着但丁、彼特拉克、薄迦丘等人作品的传播,以托斯卡纳方言为主要书写形式的文学标准语已基本形成,但迟至19世纪中期意大利半岛统一,一个真正通行全国的民族语言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仍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使用本地区的特定方言,以至普通人的交际都成问题。日益严峻的“南方问题”所导致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本已使意大利的现代性畸形发育,而统一民族语言的匮乏则加剧了意大利发展的痛苦——民众迁徙、义务教育、城市化等无一不深受阻滞。作为一个二十岁时从南方落后的撒丁岛来到北部工业重镇都灵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对这种南北方之间、各社会阶级之间由于缺乏沟通而显得毫无凝聚力的现实,无疑是有着切身感受的。他在将其定义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分裂”状态的同时,对语言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当同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布哈林将阶级对立归结于经济的因素,语言被归之于并不对现实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观念上层建筑时,葛兰西则从意大利“语言问题”所加深的分裂现实中看到:阶级差异不仅仅源于利益的分化,还有文化的、观念的,特别是以不同语言为代表的异质世界观所引发的冲突。“某个只讲方言或者对于标准语言不甚知晓的人,则与之相联系的,比起在世界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潮来说,是或多或少狭隘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和不合时宜的。”[8]325至此,语言批判不仅成为葛兰西理解意大利社会转型矛盾的一个入口,更成为他全部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1916年初,葛兰西就在社会党周刊《人民呼声》上发表文章,强调了文化活动和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文化,无产阶级永远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启蒙运动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已很好地说明了革命必须以文化批判为先导。具体到语言来说,统治阶级只是在为自身利益辩护时,才会给予他们的压迫政策以“人民”的语言外壳。因此,祛除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语言学家笼罩在语言上的“迷雾”,必然要求知识分子对语言采取严肃而科学的态度。
二、语言的历史性及其批判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现象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他虽不否认历时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语言状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个时期的投影”[9]127,语言学研究的就是这个已成静止的“投影”的逻辑关系,即语言的共时结构。与索绪尔相仿,现代语言学家大多假设了一个静止、无历史结构的语言,如乔姆斯基认为结构是由理性人的思想构成的;哈贝马斯主张理性意味着语言能力和一套交往准则。换言之,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中,语言结构不仅是可决定的而且已被决定。葛兰西则拒斥这种结构观念,相反他认为整个语言结构是向未来开放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语言结构。因此,强调语词意义的历史生成性与流变性,成为他历史唯物主义语言观的核心。他也由此反对任何先验的、在先可被把握的“语言本质说”:“‘语言’实质上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根本不会预先假定存在于时空之中的某种‘唯一的’东西。”[5]174也即,葛兰西对语言基本性质的理解,正如他对巴托利所评价的那样,后者的语言观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改变了语言学,将语言学从一种狭隘的自然科学转变为了历史科学,它的根源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寻找”[5]174。
葛兰西认为,如果对语言现象缺乏批判的历史性概念,就有可能在科学和实践的领域造成许多谬误。在笔者看来,他主要指出了以下三种:
其一,美学性的谬误。这种谬误以克罗齐“语言学与美学统一说”为代表。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提出,“声音如果不表现什么,那就不是语言。语言是声音为着表现才连贯、限定和组织起来的。”[10]191克罗齐认为,语言作为人精神活动的创造物,其美学特征远远超过它的交流功能——语言和艺术一样都是纯粹的表现,都是有关心灵的科学。因此,“世间并没有一门特别的语言学。人们所孜孜以求的语言的科学,普通语言学,就它的内容可化为哲学而言,其实就是美学。任何人研究普通语言学,或哲学的语言学,也就是研究美学的问题;研究美学的问题.也就是研究普通语言学。语言的哲学就是艺术的哲学。”[10]191而在葛兰西看来,尽管克罗齐高度肯定了人在语言发展史上的创造作用,并从人和动物声音之别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和审美维度,但克罗齐所说的创造主要是历史上伟大人物对语言的影响,如穆罕默德、但丁和路德等人分别对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形成所起的奠基作用,至于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人民群众则是在他视野之外的,从而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语言史是语言创新的历史,但是这些创新不是个体行为(如同艺术的情况)。它们是全社会共同体更新自身文化并历史性地‘发展’的结果。诚然,这些创新成果会化为个体的,但不是艺术家意义的个体,而是作为完成了的、确定的历史文化要素的个体。”[5]177-178
其二,建立普遍理想语言的乌托邦。鉴于困扰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语言问题”,著名作家曼佐尼作为官方代表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以行政强制、公共教育等方式将托斯卡纳地区的佛罗伦萨方言升格为“国语”,以此来结束意大利方言众多且使用混乱的局面。不过,曼佐尼的此种单一语言规划方案受到了包括阿斯科里、克罗齐在内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广泛批评。意大利社会党为抵制这一方案,甚至转而主张以柴门霍夫发明的人工语言——世界语作为意大利的标准语。葛兰西则在1918年以一名“正在尝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应用到语言史研究中”的大学生身份,发表了一篇名为《单一语言和世界语》的文章,对这两种语言统一方案同时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这两种语言解决方案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都试图脱离语言的历史生成性而欲图建立一个普世语言的乌托邦,“现在创建单一语言的这些尝试没有超出乌托邦的界域。它们都是法伦斯泰尔和幸福乐园般心态下的产物。”[5]30正如马克思所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1]。葛兰西也认为,某种语言的传播是由操此语言的人通过写作、贸易和商业等生产活动促成的。因此,他赞成阿斯科里的观点,一种民族语言或国际语言的形成应建立在既存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基础上,而人造语言方案因其无根性只会招致失败。但葛兰西超出阿斯科里之处在于他将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方法贯彻到底,指出语言本身从来不是“与内容无涉的文字语法,而是已有观念和概念之总体”[8]323,人工理想语言的本质是“在百科全书派极力鼓吹下妄图形成资产阶级思想一统天下的产物”,而其带来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观念——或为生意、或为休闲而四处奔走,而不是稳定创造财富的市民”[5]27,从而刺破了语言深层的意识形态维度。
其三,生造新词的武断倾向。这种倾向根源于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和实用主义者普雷佐里尼(Prezzolini)等人提出的“语言是谬误的渊薮”的命题。他们认为哲学的混乱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引起的,据此他们或致力于创造一种有着数学一般清晰、严密的“词典”,或编出一套抽象的语言形式理论。而在葛兰西看来,这种割裂语言史,意图把语言的比喻义和引申义剔除出去的做法只会把语言变成一堆毫无生机的、僵死的材料。因为按照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是一个连读不断的隐喻过程”[8]450。语言隐喻的现象是指一个新概念替换了先前的概念,但先前的语词还继续在使用,只不过是在衍生的意义上使用。或者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说,语词符号的能指没有变化,而其所指已改变。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以“disaster”一词举例说明了语言发展的这种历史继承性。在词源学上,disaster原是占星术术语,指星宿出现星位异常的现象,意指“天灾”,而现在人们则用它指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新旧对比,人们发现,disaster虽已失去了它的原指——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个占星术的概念,但它的现在义“自然灾害”显然包含着它原本所指“灾难”这个基本义。也即,disaster的现在义是在它古义基础上通过隐喻的方式扩展而来的。不仅这一个词是这样,葛兰西认为,整个语言本身“总是隐喻的。如果或许不能说所有的话语在所涉及事物的物质的和感性的(或抽象概念)方面都是隐喻的,以便不去过分地扩大隐喻的概念的话,那么却可以说,现在的语言,在所用的语词具有先前的文明时期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是隐喻的。”[8]450因此,在他看来,生造新词的做法正如寻求一种普遍理想语言一样荒谬。
三、语言与霸权
目前,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最具代表性的霸权理论探讨繁多,但论者往往忽视了解读其霸权思想的语言之维。而在笔者看来,研究葛兰西的语言学思想将成为开启他霸权理论的一把密匙——“铸就葛兰西霸权哲学原初的铸模不应在马克思、列宁或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而应在语言科学中找寻。”[7]21具体而言,葛兰西对语言的研究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双重批判、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等多个方面,而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即是如何形成底层阶级的新文化并重新组织霸权的问题:“语言问题每一次浮出水面,无论怎样,都意味着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涌现:统治阶级的形成与扩大,要求在统治集团和民众之间建立更紧密、更稳固的关系,换言之,即是去重组文化霸权。”[5]183-184
在葛兰西的政治哲学中,霸权主要是指一个阶级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的能力。在此概念发展上,他最为突出的贡献是考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制与共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其核心问题是:资产阶级是怎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权力使用方式去影响和组织共识的。换言之,资产阶级霸权不仅表现为一般意义的政治统治,同时还表现为资产阶级在日常生活和话语实践等领域,以获取下层集团同意的方式来实现其统治。具体来说,透过市民社会领域,资产阶级将自身的哲学、道德等渗透入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实践,并最终使他们“保存了统治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8]52,上层集团的统治与压迫由此被转化为对普通人的常识进行塑造的话语实践和策略。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正是以语言为突破口来分析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是如何被收拢并保持统一的。彼得·艾夫斯(Peter Ives)认为,尽管葛兰西并未明确说明语言和霸权的关系,但从其研究笔记,特别是第29笔记本关于语言问题的解析,可以推论语言在葛兰西那里是对霸权的一种隐喻[12]。
首先,语言是促成共识形成的文化工具。当索绪尔提出语言学的任务是“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9]26时,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是不关心语言现象背后所折射的诸如社会权力结构等政治问题的,而在葛兰西看来,语言问题应该用“历史语言科学”来看待——语言不能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相分离,正如克罗齐以合乎语法但不合逻辑的命题“这张圆桌是方的”来否定语法存在意义时,他不知道该命题在被放置到一个宽泛的社会语境中时具有指涉疯人癫语的表现意义。同理,葛兰西认为不同语言系统,如方言和民族文学语言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政治、伦理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构成了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霸权,而其霸权地位又与一个社会阶级和智识阶层的霸权是密切关联的。换言之,社会关系变化是促成语言系统与语言规范变革的动因,反过来语言规范经常成为收拢并统一不同阶层语言用法、形成共识的文化工具。“语言是通过新阶级带来的文化、并以一种民族语言对其他语言行使霸权的方式等,随着整个文明的变化而变化。”[8]451
其次,自发语法与规范语法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霸权的动力学基础。葛兰西在《能有多少种形式的语法》一文中区分了两种语法类型:自发语法和规范语法。自发语法是“人们依据语法言说而不自知”的语法,并且它的“数量不可胜数,理论上说,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语法。”[5]180而规范语法指人们有意识遵循的、使言说无误的语言规则。它们二者的关系是:一方面,自发语法虽名为自发,但不真的是个体的创造,相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宗教、阶级、种族等因素的影响,不断受到某些规范语法的影响。就像在乡村,人们试着模仿城里人的言谈;底层阶级尝试像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那样说话。上层阶级的规范语法对民众如何组织语言和思想施加了很大影响并留下了无数痕迹,但人们通常日用而不自知;另一方面,规范语法并非像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那样,来源于自然或逻辑的法则,相反,它本身来源于自发语法,正如现代意大利语本质上是托斯卡纳地区的方言一样。
因此,自发语法和规范语法的区别不在内容上,而在其形成方式上——较之自发语法,规范语法的形成并不总是由语言本身的因素所决定,而更多的是政治意志的产物:“规范书面语法因此总是一种文化方向的‘选择’,它是统治阶级统一集体意志的一种方式,意图将社会中自发的和散乱的意志统一起来”[5]183。不过,如果我们仅从葛兰西对这两种语法类型的辨析出发做出推论:“规范性”是强制的隐喻,而其反题“自发性”应是共识的隐喻,实则是一种误解。相反,葛兰西从对语言史的考察中看到:作为下层集团历史特征的“自发性”暴露出的只是“他们最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他们没有达致任何‘自为’的阶级意识,他们的历史也因而从未对其自身产生过任何可能的重要性,或留下任何文本痕迹来表明他们的一些价值”[8]196。北方工业资本家联合南方地主正是利用下层集团常识领域的此种“自发性”,在他们中间,特别是在农民和无产阶级中制造矛盾而能始终维持着反动的霸权。
至此,我们也就理解了葛兰西为何既反对曼佐尼的语言政策,又赞成创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立场。实际上,两人真正的分歧并不在民族语言统一本身,而在于霸权的争夺上。就像葛兰西批判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消极革命”不能激起意大利人民的团结一样,曼佐尼激进的“语言雅各宾主义”带来的仍只是资产阶级霸权的维系,而那种真正能唤醒民众、创造进步文化霸权的民族语言创建路径应该“来自于国家或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8]52,通过自下而上的、“一整套复杂的分子化合(聚合)的过程”产生。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在充分尊重民众创造性的前提下,以“有机干预”的方式去引导、催化这个分子反应的过程。即,有机知识分子应借助报纸、流行刊物、电影、电台、聚会等,在与广大民众真实的语言、文化需求的交互对话中,推动某种可能成为标准语的民族语言的形成和传播。
总之,民族语言形成的现实路径问题促成了葛兰西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进一步应用于语言学的研究。其成果,一方面是将当时意大利统治阶级弄颠倒的“语言-民族”间的关系重新正立了过来;另一方面则建立了一种与其文化霸权理论相互支援的“语言政治学”。在这种“语言政治学”中,葛兰西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扩展至对政治权力运作的微观分析,在揭示“语言是促进阶级共识达成的工具”的同时,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符号学转向”,特别是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拉克劳、墨菲将其霸权理论发展为话语理论埋下了伏笔。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M].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96.
[2]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9.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5.
[4] Peter Ives.Gramsci’s Politics of Language: Engaging the Bakhtin Circle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M].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4.
[5]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M]. Trans by W. Boelhower.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5.
[6] 葛兰西.狱中书简[M].田国良,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15.
[7] Franco Lo Piparo. Language, Intellectuals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M] .Bari: Laterza, 1979.
[8]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M]. Eds and Trans by Q. Hoare & G.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9]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12] Peter Ives. Language and Hegemony in Gramsci [M].London: Pluto Press, 2004:84.
[责任编辑:张文光]
Language, History and Hegemony:On Gramsci’s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nguistics
LI Yong-hu1, 2
(1.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m, Antonio Gramsci firstly initiates the study of socio-political theory with the linguistic methods, incorporating the rise of both Marxism in the early 1900s and modern linguistics around the world. Unlike modern Western linguistics, a particular point in his thought of linguistics is the top priority of language historicity, which is further used to criticize three incorrect views on language, namely aesthetic fallacy, building of a utopia with universally ideal language and tendency of subjective assertion for neologism. Linguistic politics constructed by Gramsci affords an inevitable perspective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theory of hegemony. In the study of approach to forming a national language, Gramsci discovers the secret that the bourgeoisie collect and unite dispersive will of individuals. While extending critique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classic Marxism to the micro-analysis of power operation, this kind of linguistic politics sow the seeds of “semiotics turn” that later appears in Western Marxism.
Antonio Gramsci; Marxist linguistics; cultural hegemony
2016-10-1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602766)
李永虎(1980-),男,湖北十堰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后,西安外国语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B089.1
A
1004-1710(2017)03-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