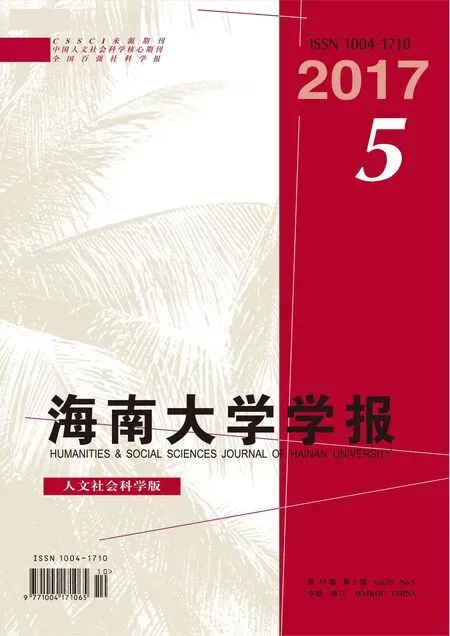“裸”行为概念之提倡——从结果无价值与行无价值关于行为要素的争论谈起为
2017-02-24陈文昊
陈文昊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1)
“裸”行为概念之提倡——从结果无价值与行无价值关于行为要素的争论谈起为
陈文昊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1)
行为要素在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下的意涵有所不同,前者偏向存在论上的自然行为,后者偏向于规范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以此为基点,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在“对物防卫”的认可与否以及“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取舍上采取不同的态度。采取存在论意义上的、客观中立的、未定型的“裸”的行为更符合刑法行为视角的立场。“有害性”、“有意性”都不是行为的要素,应当将主观要素与价值判断从行为的考量中剔除出去。这样的行为观对于“对物防卫”的主张与过失共同犯罪的证立有所裨益。
结果无价值;行为无价值;行为;存在;规范
行为作为犯罪构成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对于犯罪的认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张明楷教授在其2016年的著述《刑法学》(第5版)的行为一章中指出,“将有意性作为行为的特征不具有现实意义”*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143页。。毫无疑问,相比其著述的《刑法学》(第4版)而言,这一立场的转变是十分鲜明的。巧合的是,另一位结果无价值的坚决主张者黎宏教授早在1994年第4期《中外法学》的“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一文中就力主“从行为的概念中抛弃意思要素”*黎宏:《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中外法学》1994年第4期,第80页。。显然,“去除行为有意性”的观点与通说的观点是扞格不入的,这样的提法可谓开辟了行为理论的另一块战场。
两位结果无价值论者在行为概念上的统一不禁让人思考这一巧合背后的必然性,或者说,结果无价值论者视阈下的“行为”是否与行为无价值者眼中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笔者看来,应该给这一问题以肯定的答案。诚如下文所述,结果无价值论者眼中的“行为”是偏存在论意义上的、发散的、开放的、客观的、中立的;与此相对,行为无价值论者所称的“行为”是偏向规范论意义上的、定型的、闭合的、主观的、价值色彩浓厚的。这一核心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两大体系的整体理论走向和学说脉络大相径庭。例如,张明楷教授在正当防卫的问题上指出,“动物自发侵害他人时,即使管理者主观上没有过失,也是其客观疏忽行为所致,仍应认为管理者存在客观的侵害行为,打死该动物的行为,属于对管理者的防卫”*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第201页。;黎宏教授也指出,“不法侵害就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受加害人主观意思内容、年龄、精神状态及其行为形态的影响”*黎宏:《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如下文所述,两位结果无价值论者肯定“对物防卫”,也深刻受到了结果无价值论体系下“行为”概念的影响。再如,在共同犯罪的问题上,张明楷教授由2007年《刑法学》(第3版)所主张的部分犯罪共同说转向了2011年《刑法学》(第4版)所主张的行为共同说*相关论述参见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319页;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版,第358-359页。而黎宏教授在其2012年于《法学》发表的“共同犯罪行为共同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一文中也力主行为共同说*黎宏:《共同犯罪行为共同说的合理性及其应用》,《法学》2012年第11期,第112-117页。。这是结果无价值论视阈下对行为概念的独特解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由此可见,“行为”概念的不同理解不仅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之争的理论暗线与隐蔽战场,更是左右整个犯罪体系与教义立场的轴心力量。因此,合理界定刑法中行为的概念显得尤其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行为要素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争论,学理上存在诸多争论。在贝林的古典犯罪体系中,行为要素是作为前置性要素得以存在的,“在方法论上,人们按照合目的的方式提出了六个犯罪要素,起顺序和结构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需要置于‘行为’之后,然后依次是‘违法性’—‘有责性’—‘相应的法定刑刑罚威慑’—‘刑罚威慑的处罚条件’”*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北京: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除此之外,大谷实教授也认为应当将行为作为犯罪论的基础加以看待*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另一种观点创设出了“实行行为”的概念,将行为要素置于构成要件当中加以评价*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第144页。。在笔者看来,这两种处理方法中均涉及到对行为概念的解读与对行为要素的解剖,因此,无论如何对行为在犯罪论中的位置进行界定,都不影响本文对于行为理论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行为作为构成要件之要素看待展开下文的讨论。
一、行为概念的裂变与发展:存在论与规范论的角力
在行为理论的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当然是自然行为论与有意行为论。其中,纯粹的结果无价值论者完全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为就是“身体的动静”*平野龍一:《刑法概說》,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35页。,也就是所谓的“自然行为论”。与此相对,“有意行为论”在纯自然意义的行为之上加入心素,使之变成立体的行为概念。例如小野清一郎教授指出“在自然主义的思考下,行为就是意思与神经的内部刺激下身体的运动与静止”*小野清一郎:《犯罪構成要件の理論》,东京:有斐閣1953年版,第51页。;藤木英雄教授也将行为界定为“基于外部世界发现的意思的身体动静”*藤木英雄:《刑法》,东京:弘文堂1971年版,第43页。;泷川幸辰则是教授认为“行为就是犯意向外的表现发生符合行为人目的的外界变化”*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王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不难发现,以平野龙一教授为代表的自然行为论者眼中的行为纯粹客观中立,它不仅不含有任何的价值评价于其中,连心理层面的认知也被抽去。应当说,这样的处理方式与纯粹存在论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对此,周光权教授指出:“极端的结果无价值论即唯结果论,它仅通过对实存现象、经验的判断来限制处罚范围;而现代的结果无价值论吸纳了部分新康德主义的内容,承认实质主义刑法观,但是价值判断程度明显受限”*周光权:《价值判断与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134页。。从这个思路出发,结果无价值论与存在论具有极高的亲和性,这体现在行为论上就表现为,结果无价值论者试图将价值判断的成分从行为的概念当中驱逐出去,仅留下中立可见的自然行为,从而生发出“自然行为论”。
与自然行为论与有意行为论采取截然不同进路的是“把社会这个概念看成是行为核心因素”的社会行为论*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例如,内藤谦教授主张“行为是人的外部态度对社会外界有方向的影响”*内藤謙:《刑法講義総論》(上),东京:有斐閣1983年版,第201页。;山中敬一教授指出“行为是具有人的、社会的归属可能性的人的动静”*山中敬一:《刑法総論》,东京:成文堂2008年第2版,第147-148页。。而野村稔教授认为行为是“可能受意思支配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的态度”*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社会行为理论与行为无价值或者二元论具有着紧密的亲和性,他一改以往从存在论视角审视行为的做法,着眼于规范的、与社会价值意义相关的“社会性”,其中的价值评价作用不言而喻。然而,究竟何为“社会重要性”,社会行为论者却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就使得社会行为的内涵过于空洞和泛化。正如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的评价:“失之太泛,是这一理论的根本缺陷,因为用来确定行为范围的标准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相关论述参见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106页。应当认为,这一缺陷与行为无价值论者看问题的视角是密不可分的:行为无价值论者在构成要件当中就对行为做了十分具体的界定和限缩,试图将不具有刑法意义的生活化的行为在构成要件阶段就尽早地排除出去,这一考量显然是规范导向的。
比较结果无价值论者与行为无价值论者视阈下的行为概念不难发现,前者更偏向于一种“裸的”、“泛化的”、尚未定型的行为概念,更偏向于存在论的立场;而后者已然受到了价值判断的浸染,在主观要素的加入之后也趋向于定型与明确,具有浓厚的规范论色彩。
二、行为理解的差异对犯罪论体系的渗入
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对行为的解读的差异弥散和扩大到整个犯罪论当中,对犯罪体系的构架与所持立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存在论上的自然行为更容易得出肯定“对物防卫”的结论。例如,行为人看到一个举刀砍向自己(行为人)的侵害者,如果按照结果无价值论者的观点,仅要求侵害是一个“裸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就可以认为,行为人对其可以进行防卫。与之相反,行为无价值论者在考察行为人的防卫权之前首先会检验侵害行为的规范价值。例如,侵害者是否具有过失、是否具有行为的有意性,都是行为无价值论者在判断防卫条件时需要考察的问题。
这样的逻辑进路差异就导致,针对动物的自发侵害的问题,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者也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例如,结果无价值论者承认客观违法论,认为只要是客观上的不法侵害均可以防卫*相关论述参见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版,第58页;曽根威彦:《刑法の重要問題》(总论),东京:成文堂2005年版,第101页。;而行为无价值论者井田良教授就主张,“正当防卫中的侵害只能由故意或者过失构成”*井田良:《刑法総論の理論構造》,东京:成文堂2005年版,第166页。。当然,大塚仁教授虽然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但考虑到如后文所述的“对物防卫”理论的合理性,也改变以往的观点承认“准正当防卫”,认为针对没有罪过的侵害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东京:有斐閣1975年版,第253页。。但是不得不说,结果无价值论者对行为概念的“非定型化”更容易在正当防卫中“侵害”的认定上采取更宽的解释进路,进而承认“对物防卫”的概念。一言以蔽之,肯定“对物防卫”的结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者所持的行为观休戚相关。
其次,在共犯问题上,结果无价值论的行为观更容易导出行为共同说的结论,而行为无价值论的行为观与犯罪共同说具有亲和性。例如,甲、乙、丙三人约定去“搞一下”被害人,三人对被害人施加暴行导致其死亡,后来查明,甲的“搞一下”是指劫财,乙的“搞一下”是指劫色,丙的“搞一下”是指故意伤害。根据结果无价值论者的观点,如果将共犯成立基础的行为理解为自然意义上的“裸”的行为,那么不考虑故意支配的、纯粹客观的暴行行为就可以成为三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桥梁与纽带,进而可以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甲、乙、丙三人。与之相反,行为无价值视阈下的行为是规范意义上的、定型的。因此,行为无价值论者在讨论共犯问题之前,首先将甲、乙、丙的行为分别界定为抢劫行为、强奸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由于在构成要件之上不存在重叠和包纳关系,就难以认定共同犯罪的成立。由此可见,结果无价值论者与行为无价值论者对于行为概念的解读不同最终导致了共同犯罪理论的立场差异。
在日本,主张结果无价值论的学者认为,共犯的成立仅以“意思的互通为必要”*相关论述参见前田雅英:《刑法総論講義》(第4版),第412页;松宫孝明:《刑法総論講義》,东京: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266页。;而行为无价值论者主张在“共同目的范围之内考察数个构成要件的关系”*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191页。,这也就是两大学说体现在共同犯罪理论上的核心差别。进一步说,这一差别又会导致对过失共同犯罪结论上的本质分歧。申言之,行为共同说在逻辑上会导致对过失共同犯罪的认可,例如,行为人甲对被害人施暴的过程中对乙大喊“快来帮我打抢劫犯”,不明所以的乙加入对被害人的暴行,最终导致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着眼于甲、乙二人的暴行这样一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合致,就可以很容易得出二人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进而将死亡结果归责于甲、乙二人,甲成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乙由于存在容许的构成要件错误,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甲、乙二人成立共同犯罪。而与之相反,行为无价值论者由于在认定共同犯罪之前就对行为进行定型化的处理,在逻辑上很难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这一体系性差异的根源还是落在结果无价值论者与行为无价值论者对行为的理解不同之上。
三、本文的立场:“裸”的行为概念之提倡
笔者赞同结果无价值论者所主张的行为概念,它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发散的、开放的、客观的、中立的行为,或者说是“裸”的行为概念。这样的安排不仅在犯罪论体系上自洽,而且有利于在个案处理中达到平衡。
(一)构成要件中的行为是客观、中立的
我国传统理论中对刑法中的行为划定了边界,认为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在客观上是人的身体动静、在主观上基于行为人的意志或意识支配、在法律上对社会有危害*相关论述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版,第70-71页;黄明儒:《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页;陈晓明:《刑法总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有学者将其总结为“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三个特征*刘艳红:《刑法学》(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85页。;也有学者将行为的特征界定为“体素、心素和效素”*张小虎:《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82页。。
1.行为要素中“有害性”的理解
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何为行为的“有害性”?对此,传统理论指出,“人类行为不外乎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和无害于社会的行为两大类,只有有害于社会的无价值行为,才可能被视为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4版),第71页。。问题在于,论者在整段论述中使用的“行为”概念到底是指广义上的犯罪,还是狭义上的作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倘若采前者的理解,这一段论述只是重申了“犯罪是有害的”这一观点,并无实益可言;倘若论者是从狭义的、作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出发,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脱离不法的整体评价体系单独证成行为的有益抑或有害?在笔者看来,恐怕难以做到。例如,杀人的行为单独来看是“有害”的,但如果是成立正当防卫的话,那么从整体的不法判断来看,行为又是有益的。
有学者指出,从存在论意义上的行为观“完全依赖于外部因果演化事实掌握行为,使得行为的概念变得界限模糊、没有轮廓,甚至将生育一个杀人犯的行为也包摄进去”*邹佳铭:《刑法中的行为论纲》,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其实,这样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即使舍弃“有害性”而证成了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也完全可以从主观层面限制入罪。例如,母亲对所生育的孩子成为杀人犯这一点没有预见可能性,因此生育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罚。即使在意图杀死仇人而培养孩子成为杀人犯的场合,只要坚持实行与着手的分离*陈文昊,郭自力:《着手的剥离与重建:英美法系的类型化视角》,《行政与法》2016年第7期,第92-100页。,也不会导致处罚的过于提前。相反,将生育行为纳入行为范畴的实益在于,不轻易在客观要件中否定行为要素的成立,而是留待到主观要件中再对“有害性”进行判断。例如,在行为人生育孩子就是为了培养其作为杀手杀害特定人的场合,如果认为在行为要件上就可以阻却犯罪,到了主观阶层又发现行为人具有强烈的故意与预谋,由于在客观阶层已经阻却犯罪的成立,因此无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妥当。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劝诱他人去坐飞机的行为看似不具有“有害性”,但如果后来查明行为人明知飞机上有炸弹仍然劝诱被害人坐这架飞机的,当然可以评价为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还如,传统理论认为诸如跑步这样的纯个人化身体动静不具有刑法意义*相关论述参见刘士心:《刑法中的行为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但如果行为人怀有杀人的意图追赶他人,就可以认定为需要受到刑法评价的行为。由此可见,行为的“有害性”概念试图对本应是价值中立的行为要件生硬地填充价值色彩,结局只能是徒劳无功。
因此,任何行为一旦脱离主观要件的限制,就不能说明其“有害性”,这是因为,处在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应当是客观而价值中立的。换言之,在没有进入有责性阶层的检验之前,任何行为都不应当从评价的评价对象中过早地驱逐出去,否则就会过于草率地得出无罪的结论。
2.行为要素中“有意性”的理解
其次,在行为的界定当中,是否需要“有意性”的要素作为支撑,也是一个重要的论题。赞成“有意行为说”的立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陈兴良教授指出:“没有意思支配的行为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刑法上的行为,是因为不能将这些行为看作是行为人的作品,也不能使行为人对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陈兴良:《教义刑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02页。。传统理论也指出:“人的无意志和无意识的动静,即使客观上造成损害,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不能认定这样的行为人构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4版),第70-71页。。
笔者承认以上论者的最终结论,即在单纯的梦游、条件反射过程中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行为人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但问题在于,即使在构成要件层面承认其行为性,也完全可以在责任层面出罪。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的:“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之一,其中的行为并不等于犯罪。”*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第143页。相反,如果在构成要件层面检验行为的有意性,在责任层面再重新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反而有重复评价之嫌疑*相关论述参见黎宏:《刑法学》,第79页。。
第二,认为刑法对于不受意志的行为无法实施有效的规制,且不能通过规范遏制其发生。例如有学者指出的:“假如无意识的行为构成犯罪,人们就不能避免刑法的损害。”*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游粱式抽油机具有结构简单和可靠性高等优点,使其在采油设备中有广泛的应用。抽油机都采用较大功率驱动电机来解决启动问题,但正常运行时效率低下。抽油机的数量巨大,因而抽油机的节能降耗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些探索工作可以分成两类,对抽油机机械结构的优化和对电机运行特性的改善。当抽油机上冲程时电机处于电动状态;下冲程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会产生“泵升电压”。这部分能量通常采用外接功率电阻,以能耗制动的方式将这部分能量消耗掉。虽然这种方案结构简单,容易实现,但是功耗电阻的发热有可能引发安全问题并缩短设备寿命,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能量的浪费不利于油田的节能降耗。
问题在于,刑法不仅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刑法纵使不能对梦游、条件反射此类的单纯身体动作进行预防,但完全可以对此类行为作出不法的评价,告诉其他公民在面对这类情形的时候如何去应对。如下文所述,将这类行为确立为不法,即是赋予了一般公民面对此类侵害时候的防卫权。由此可见,对此类行为做符合构成要件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相反,主张将“有意性”逐出行为的成立条件,具有其本身的优越性:
首先,传统理论一方面承认精神病人、醉酒者等心神丧失者的行为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行为的有意性,难免有自相矛盾的嫌疑。显然,心神丧失者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对自身的行为没有认知,但通说对于此类行为的处理是,承认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同时在责任层面讨论行为人的责任能力与故意。既然如此,为何不能对不具有意思支配的身体动作做相同的处理呢?
其次,将单纯举动界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有利于解决正当防卫的问题。如果将单纯的梦游行为、条件反射行为排除出构成要件行为的范畴,进而排除其不法,并站在行为无价值论者的一贯立场否定“对物防卫”理论,面对此类侵害的行为人就没有防卫权,但这样的结论恐怕不妥当。显然,面对梦游中举刀砍杀的人、或者因为癫痫导致驾驶失控的司机所生发的侵害行为,没有理由剥夺行为人的防卫权。
再次,瓦解行为的“有意性”概念有利于故意论体系的统一。根据构成要件的故意规制机能,行为人成立故意,必须对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认识,否则阻却故意的成立。这就产生了问题:根据传统观点,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他构成要件要素,则阻却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行为”要素,则整体排除行为的成立。毫无疑问,这样的处理和安排会导致体系的不协调。例如,在奸淫幼女的场合,“奸淫”和“幼女”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存在,但是,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奸淫的行为,导致的效果是阻却构成要件,而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对方是幼女,则阻却犯罪故意。这样的突兀的体系安排是毫无必要的。
最后,否认行为的“有意性”有利于解决原因不法行为的问题。由于我国通说理论中还没有“原因不法行为”概念的引入与探讨,而原因自由行为只限于责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自然行为论更对我国的刑法理论而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日本的一起母亲在睡眠中压死婴儿的案例中,如果认为母亲的动作是睡眠中的动作,因而不具有行为性的话,由于缺少“原因不法行为”的理论支撑,恐怕难以对母亲的行为定罪。与之相反,如果承认母亲的睡梦中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但缺乏责任的话,就可以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的原理将其入罪。
日本的司法判例中出现过类似的案例,在昭和39年大阪地方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因为迷幻剂中毒产生了被害焦虑症。一日在家和妻子就寝时,被告人梦见有人卡住自己的脖子,意图将其杀害,在极度的恐惧中,被告人卡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其窒息身亡。关于这一案件,大阪地方法院的第一审以“被告人的动作由于没有意思支配并非行为”为由宣布其无罪。这一判决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导致上诉审即大阪地方高等法院改变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本案中被告人有行为,但是没有责任能力而裁定无罪*山口厚:《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0-41页。。
我国也有学者举出了由于行为不具有“有意性”而出罪的实例,即“夏某被强迫杀人案”。本案中,夏某被犯罪嫌疑人蒙住双眼,强迫其与被害人王某发生性关系,并用绳子将被害人勒死*《河南平顶山一团伙劫持检察人员 逼其强暴女生》,《新京报》,2009年7月22日第3版。。陈兴良教授指出:“夏某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是因为缺乏心素,不存在刑法中的行为。”*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2版),第103页。但问题在于,如果基于“有意性”否认行为的成立,再采用行为无价值论者一贯的逻辑否定“对物防卫”理论,导致的结论将是,被害人在受到强奸时无法对夏某进行防卫,而是具有忍受的义务。毫无疑问,这样的结论不能让人接受。在笔者看来,针对本案,没有必要在行为阶层就急于为夏某出罪找到理由。在责任阶层,无论是责任能力理论、罪过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都可以成为夏某出罪的解释进路。
综上所述,构成要件中的行为应当是客观且中立的,不应当将主观评价要素纳入到构成要件当中加以讨论,在此意义上,去除“有意性”的要素十分必要,这一处理也有利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的贯彻。
是否存在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将论者卷入行为无价值论者与结果无价值论者对战的漩涡之中。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与本文有关的一个问题展开论述:是否需要在构成要件层面就通过主观故意的内容对行为进行“定型”?或者说,在构成要件层面保持行为的开放性与发散性,是否妥当?
如前文所述,结果无价值论者所主张的构成要件中的行为是自然意义上的、未定型的行为,笔者称之为“开放的、发散的”行为。行为无价值论者周光权教授指出:“结果无价值论弱化构成要件的价值,可能笼统地得出因为存在损害,所以具有结果无价值论的结论,至于是什么具体犯罪的结果无价值,在所不论,因此会得出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致死的违法性相同的观点。”*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法益观》,《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第956页。
在笔者看来,这一指摘并不妥当。一方面,犯罪构成的逐层检验最终决定了犯罪的最终性质,要求在构成要件阶段就完成犯罪个别化的机能,是赋予了构成要件过高的要求。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的:“结果无价值认为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致死的违法性相同,是因为三者侵害的法益完全相同。而刑法根据行为的方式、样态将侵害相同法益的犯罪规定为不同的罪名,并不能说明立法者注重行为无价值。因为即使是侵害相同法益的行为,为了避免构成要件的高度抽象与概括,也必须尽可能进行分类,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可能实现。”*张明楷:《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另一方面,行为无价值论者的论述反而暴露了行为无价值论本身的短处。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会在行为阶段就体现出来,只有从即成的结果反推行为人当时的行为,才能够确定行为人的具体故意内容。例如,行为人因为工作不顺,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进而在街上对被害人进行暴行和殴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到底是怀有杀人的故意,还是伤害的故意,抑或是寻衅滋事的故意,恐怕行为人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脱离结果要素单纯对行为定型的做法,恐怕只能以失败告终。再如上文所述,甲、乙、丙共谋“搞一下”被害人的场合,如果事后查明甲、乙、丙分别持有抢劫、强奸、伤害的故意,这种情况下,如果从自然意义上将三人的行为界定为“暴行”,很容易承认共同犯罪的成立,进而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责于三人。但如果将三人的行为过早定型为“抢劫行为”“强奸行为”“伤害行为”,无疑对共犯的成立与归责的实现是有所影响的。
由此可见,在抽象意义上理解构成要件中的行为,意味着将其定位为一种开放的、发散的行为,且在客观上完全具有符合数个构成要件的可能性。至于对其具体定型,必须借助于行为要素以外的,例如结果要素以及主观要素加以限定。这样的处理无论对于体系的构建,还是具体问题的解决都是颇有裨益的。
四、结果无价值中“裸”行为理论对于犯罪论体系的裨益
(一)“对物防卫”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如果在构成要件中采用客观的、中立的、开放的、发散的、自然意义上的行为,自然会得出“对物防卫”的肯定结论,因为只要承认了违法绝对客观性,就可以认为对于一切客观上具有侵害性的行为均可以实施防卫。实际上,承认“对物防卫”的观点,对于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在笔者看来,行为无价值论者在判断防卫要件的时候将动物的侵害类型人为地割裂为“饲主故意支配下的动物侵害”、“饲主过失下的动物侵害”以及“动物的自发侵害”三种,在前两种的场合肯定防卫权,而在第三种的情况下否定防卫权。问题在于,照理来说,国民在面对人的侵害与面对动物侵害时,对于后者的反击理当更容易成立阻却违法事由。然而,主张成立紧急避险的观点却相反:针对人的侵害行为可以实施条件较为缓和的正当防卫;针对动物侵害只能成立条件更为严苛的紧急避险,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恰当*张明楷:《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第201页。。
更重要的是,关于以上问题的探讨处于我国更具特殊性。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由于存在“属无主物的保护动物”的概念,因而在“对物防卫”问题的处理上要考虑侵害的主体问题。但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这就意味着,完全可以在野生动物侵害的背后拟制和描画出一个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概念作为侵害发生的主体,进而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肯定行为人的防卫权。
当然,除了有人饲养的动物和属国家的野生动物之外,如果是无主动物,例如流浪狗、流浪猫或其他情况下发生的袭击,公民则无权进行防卫,只有可能成立紧急避险。这是因为,所谓正当防卫,针对的一定是“人”的侵害,“行为”本身也必需是人发出的,而无主物的侵害中无法找到“人”这一要素,因此只有适用限度更为严格的紧急避险。当然,如果行为人误将无主动物认定为有主动物进行“防卫”的,由于没有侵害法益的故意,超出限度的部分不宜评价为过当。
由此可见,在对违法行为的刻画中,采取完全客观、中立的态度,将主观罪过的问题放到恰当的位置加以解决,对于“对物防卫”理论的构建具有意义。
(二)过失共同犯罪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采取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概念,在共犯理论中更容易得出行为共同说和过失共同犯罪的结论,采取这一立场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犯罪,一向持否定态度。但随着德日理论的渗入,这一结论开始存在疑问。
首先,教唆犯中的被教唆者也可能不具有犯罪故意,这也就变相承认了过失的共同犯罪。在传统理论的框架中,教唆犯被称为“造意犯”,教唆犯的成立以引起被唆使者的犯罪故意为要件。然而,这一结论并不绝对,例如,医生将毒药交给护士,让护士将病人毒死,但护士因为走神没有听到,以为是营养品给病人注射的,医生在客观上利用他人的不知情实施杀人行为,成立间接正犯;主观上引发他人犯意,成立教唆犯。由于间接正犯可以评价为教唆犯,所以医生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而护士由于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中,即使被唆使者没有犯罪故意,唆使者仍然成立教唆犯。因此,应当肯定没有“造意”的教唆犯。事实上,误将精神病人当做正常人,唆使其实施犯罪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唆使者成立教唆犯。既然精神病人都可以被教唆,那么唆使没有犯罪故意的人成立教唆犯也就不应存在任何障碍。由此可见,唆使他人过失犯罪的依然可以成立教唆犯,在此意义上,过失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过失共犯的缺位造成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甲、乙比赛射击,结果导致路人死亡,但无法查明子弹由谁射出。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否认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就无法归责于甲、乙当中的任何一人,这样的结论恐怕不妥当。反过来,如果承认过失能够成立共同犯罪,甲、乙共同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答责。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例如,徐某在任央视新台址办主任期间,擅自决定于2009年2月9日晚在央视新台址工地燃放烟花。沙某在徐某的授意之下,与刘某、李某某等人购买A级烟花,耿某带领刘某某、沙某进入新台址工地燃放烟花,造成严重大火,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八人受伤,建筑物过火过烟面积21 333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李翔:《刑事疑难案件探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35页。。本案也涉及过失共同犯罪的问题。
因此,从实质上看,只有承认过失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才可以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至于需要对《刑法》第25条第1款与第2款,需要在教义学上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传统理论之所以从理论上不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就是基于上述的立法规定。但实际上,《刑法》第25条并非没有可以解释的空间。
第1款中,“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似乎已经为共同犯罪划定了故意犯罪的界限,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但是,倘若将这里的“故意”理解为行为的“有意性”,恐怕就可以承认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毫无疑问的是,所有的犯罪成立都需要行为具有“有意性”,也就是行为人对自身实施的行为知道。也就是说,只要通过了不法性阶层的检验,完全可以说此时的行为具有“有意性”。因此,将“故意”解释为行为的“有意性”,完全可以认为,共同犯罪的成立不需要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具有任何的要求。这样一来,过失当然也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第2款中,“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也并非没有解释的空间。毫无疑问,共同犯罪体系建立的目的在于归责。例如,在以上甲、乙比赛射击的案例中,倘若能够成立共同犯罪,就可以将难以查明的结果归责于各行为人。因此,否定过失成立共同犯罪相当于切断了一条对所有行为人进行归责的进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行为人无法进行归责。第2款使用了“共同过失犯罪”的语词,基于这一点,完全可以认为,“共同过失犯罪”虽然不成立共同犯罪,但具有与共同犯罪相同的效果,即将结果归责于各行为人。如此理解的话,完全不影响对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理方案,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过失的个体犯罪,在效果上可谓殊途同归。
由此可见,在构成要件上采取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概念,对以上问题的解决都有着指导意义。
总结而言,古典犯罪论体系以实证主义为哲学根基,新古典体系视新康德主义为拥蹩,规范论奉功能主义为圭臬,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体系,再到功能主义犯罪论体系,无不体现出作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根基嬗变与规范评价对犯罪论体系的渗透。从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思想,再到功能论,古典的犯罪构成体系最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犯罪构成,价值评价的渗透使得李斯特鸿沟被彻底跨越。从对构成要件理解的对立,到违法性判断的阵地与底线,再到有责性中的争讼,存在与规范两大阵营将刑法理论之争引向深处*陈文昊:《从存在到规范——犯罪论体系的流变与对立》,《犯罪研究》2016年第1期,第2页。。
在古典的犯罪体系已然在新的哲学思潮被鲸吞蚕食的今天,规范论的兴起与存在论的消解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另一方面,规范论强调国家规范的权威性,可能会将人完全作为工具进行评价,这也正是雅各布斯“敌人刑法”遭到广泛批判的原因。说到底,刑法相比其他的部门法,对事实和存在的偏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完全将行为视角转换为义务视角,在刑法教义上过于强调规范意义上的行为,恐怕会导致刑法统域的泛化,导致刑法阵地与底线的失守。因此,在作为刑法理论核心的行为理论上,对面采取偏向规范意义的改造应当采取相当慎重的态度。
AdvocatingtheConceptofNullActfromtheDebateoverElementsofActintheEyeofErfolgsunwertandHandlungsunwert
CHEN Wen-hao
(School of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Elements of act mean differently in the eye of Erfolgsunwert and Handlungsunwert. While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natural act in the ontology, the latter prefers the social act in the respect of norm. This distinction leads to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Erfolgsunwert and Handlungsunwert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and denial of “defense against objects” as well as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monness” and “the theory of action commonness”. Taking the “null” act that is of ontology, objective neutrality and undecidednes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sition of criminal law act. Neither “harmfulness” nor “intentionality” is the elements of act, and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value judgement should be deleted from the consideration of act. Such a view of act is of help to the proposal of “defense against objects” and justification of negligent joint crime.
Erfolgsunwert; Handlungsunwert; act; fact; norm
D 924.11
A
1004-1710(2017)05-0133-09
2016-12-31
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责任编辑: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