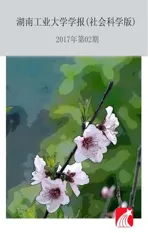可疑的“90年代”
——评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
2017-02-23唐伟
唐 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可疑的“90年代”
——评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
唐 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面对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侵袭,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固化的生存现实,杨庆祥博士的《80后,怎么办?》一书,尝试提出80后一代人的生存际遇问题。80后要面对的“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并非判然有别的两样东西,而实乃统一于90年代发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制当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追溯80后“失败感”的成因,我们应该首先回到可疑的“90年代”的历史现场。
《80后,怎么办?》;80后 ;90年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意欲尝试以一种如作者所言的“有效的抵抗”方式来回应我们这代人的生存处境。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80后亦不例外。而杨著的意义则在于,作者以一个历史在场者、亲历者的身份,来质询身处其中的时代与国度,在引起同代人强烈共鸣的同时,也不禁让人想起布莱希特那首著名的《致后代》来:“当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请你们也记得∕你们逃脱的∕这黑暗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80后,怎么办?》道出的又不仅是80后一代人的问题,而毋宁说是中国青年人的问题,或根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症候。
一 历史是怎样虚无的?
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历史”无疑是一个核心关键词。若做一个化约的理解,诸如“历史”“现实”“时代”等此类词汇,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学理界限(也没那种必要),而应该是有着如出一辙的所指。换言之,在一个语用的经验层面,“历史”“时代”“现实”等大致是可以通约通用的。杨著遵循历史化的思路当然可取,但问题在于,“历史”,究竟从何谈起呢?基于80后的成长经历(出生时间、高校扩招)而设定的时间节点,能否作为“重新回到历史现场”的起点?或换句话说,代际经验的线性分割,是否足以让我们确证80后的历史位置?更何况“历史”本身即是一个讨巧的说法,它貌似指出了问题的方向,但含糊其辞的语焉不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这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80后,怎么办?》甫一发表就引起热议,但相关回应也仍停留在了指向不明的“历史”上,后续深入的讨论却没了下文。
对80后一代人来说,成长的轨迹,并不需追溯太远,打我们记事起的历史,其实就近在咫尺。相对于模糊不清的“历史”托辞,我更倾向于从“历史”堆中寻找一处清晰可靠的标记。在书中,杨庆祥谈到了80年代、90年代及新世纪,各不同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对80后有着不一样的历史记忆。80年代,80后年龄太小,还未成年,历史认识尚不具备成熟的历史主体;新世纪还才刚刚展开,历史化的意味似乎还不够充分;对80后一代人来说,真正具备那种参与性历史感的当属90年代。
但90年代在何种意义上对80后构成一种对象化的历史认识,也并非不证自明。在《80后,怎么办?》中,杨庆祥也提到了90年代,对于1992年启动的“市场经济”,“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1]25但问题在于,对没有辍学并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的杨庆祥来说,“市场经济”或许并没什么实质性影响,但另一方面,对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辍学的杨的同学而言,他们的历史从辍学那一刻起,已然开始改写——我相信辍学打工的那一年,必定会进入这些人的成长记忆之中。
在《80后,怎么办?》中,“90年代”同“市场经济”大约可以划等号。当然,若仅就90年代“市场经济”的历史叙事而言,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杨庆祥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绪论中,贝尔一开始就援引尼采《强力意志》序言中的一段话带出“虚无主义”的话题,并进而探讨了“虚无主义”的理路。在贝尔看来,正是“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才是导致尼采所谓虚无主义的根源所在。抛开中西方语境转换的繁琐论证,概而言之,“市场经济”的“理性和算计”无疑也是助长中国人虚无主义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对80后而言,或许是某种“双重的遗忘”:既没有意识到“时间开始了”的历史起点,同时又小看或者说弱化了经济理性虚无的一般功能。也就是说,对80后而言,“90年代”首先开启的是一段分化、分解80后命运的历史——以绝大多数80后们的学习经历为例,尽管1986年4月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适龄儿童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80年生人6岁入学为例,完成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起码也要等到1995年。杨庆祥的同学辍学南下打工,有的可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但也极有可能因“市场经济”提供的机遇,早早辍学加入了南下打工的行列。换言之,“80前”们之前那种统一的历史形态,对这一代人而言已不再可能,而在此历史分化分解的过程中,经济理性则进一步强化了历史虚无的进度。
源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今天仍在继续,但对置身其中的80后来说,在“市场经济”润物细无声的历史足音中,如若仍想寻找那种与宏大历史共振的切入点,无异于缘木求鱼。在此意义上,“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或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社会如何结构?
不管怎么说,借“90年代”和“市场经济”来分析80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成因,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的意味,这对杨庆祥在书中讨论到的高房价、韩寒郭敬明以及小资产阶级等诸多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难免有一叶障目的嫌疑,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偷换了杨庆祥所谓的“历史”概念。但这种“简单粗暴”直奔主题的方式,并不是为打捞起“市场经济”的真身,而是只为阐明这样一个题旨:“90年代”可能远比我们经历的要复杂,也更鬼魅。
《80后,怎么办?》一书的另一关键词是“失败感”。在书中,杨庆祥一再提到“日益板结的社会结构”,并试图“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清理出成因起源。也就是说,杨庆祥所谓的“失败感”,其实是在社会结构以及宏大历史的意义上来言说的,质言之,80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稳固的位置。在杨庆祥看来,一些80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最终不过证明是幻梦一场。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文最终的努力正是为唤醒“80后厘清自己的阶级”意识,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或许也是《80后,怎么办?》一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但前提性的问题在于,“社会结构”又从何说起呢?或换句话说,对80后而言,中国自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是否很大程度就是由“市场经济”来一手完成的呢?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杨著或本文所谓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或城乡结构之类,而是一种现代文化意义的社会结构。对于后一问题,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考察日耳曼和地中海史前时期最古老的社会分化时,他的做法倒是对我们有一定启发意义,韦伯认为,日耳曼和地中海史前时期的社会分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部分是由宗教因素决定的,无论如何都不是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贝尔在分析社会结构时比韦伯更进了一步,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反思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经济决定论,他把现代社会分解为经济—技术体系、政治、文化三个并不相一致的领域,认为这三部分各有其独特模式,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也正是这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所谓的社会结构也唯有在顾全这三者的意义上才能得以确证。
我们注意到,杨庆祥在书中描述的80后的“失败感”,始终是放在“财富快速增长、GDP领跑世界”的大国语境中来展开的。与其说这是毫不相关的两件事,不如说是同一件事的一体两面,这跟作者在文章后来所说的80后要面对的“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两个庞然大物一样,这两个庞然大物很可能也是如出一辙。这正如黄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虽然改革三十多年来,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国家体制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而杨庆祥在文中也这样指出:“经过三十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1]102如果杨庆祥所言非虚,那么要问的是,权贵资本阶级垄断地位的合法性,究竟是谁赋予的呢?权贵资本阶级积累起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难道是90年代所谓“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性后果?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无法绕开“市场经济”来谈90年代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仅仅借助“市场经济”的单一叙事,又无法解释清楚一些问题(在此以往,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即大小问题无一例外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的原罪)。而恰恰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无比吊诡的一个现象是,尽管中国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规划于90年代初已启动,但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在谈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时,总是习惯于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剥离开来,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减为“市场经济”,或将“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纵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运行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划等号。
这里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概念差异性,当然不是玩文字游戏,也不仅仅是为凸显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前提限定,而是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表述,既不能被随意缩减为“市场经济”,也不能被解读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看到,在官方正式的会议与文件中,从来都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1994年12月,江泽民就曾重申过这点:“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性质。”套用邓小平的那句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所“搞”的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自9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制规划中,“社会主义”无疑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规定性。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框架中,不管社会结构的全部复杂性能否充分展开,至少,政治的维度被引入了进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来理解80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成因,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谱的检视下,我们能更加清晰地观察到所谓80后“历史虚无主义”的真相所在:“历史”从一开始就被人动了手脚,“虚无”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一书中提的真实“抵抗”问题,重要的或并不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抵抗,而是去指认并寻找到一个真实的抵抗对象。
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被经济地简称为“市场经济”,以及这一简称究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规划的结果,还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共谋?质言之,90年代“市场经济”的政治规定性,是如何丧失而趋于隐匿无形的?这已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任务了。
[1] 杨庆祥.80后,怎么办?[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e Suspicious “1990s”:Review on Yang Qingxiang’s Post-80s, How to do?
TANG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Facing the ideological invasion of relativism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living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olidified social structure, Dr. Yang Qingxiang’s bookPost-80s,Howtodo?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survival problems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The "globalized capital exploitation system" and "increasingly rigid bureaucratic machinery", which is faced by the post-80s, are not two different things, but they are unified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gimes that began in the 1990s. In this sense, in order to retrospect the “sense of failure”of the post-80s,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suspicious "1990s" first.
Post-80s,Howtodo?;post-80s;1990s;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28
2016-12-05
唐 伟(1983-),男,湖南东安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C912
A
1674-117X(2017)02-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