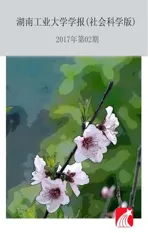反抗与亲近
——论白红雪诗歌中的自我拯救主题
2017-02-23孙晓娅
孙晓娅
(1.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2.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反抗与亲近
——论白红雪诗歌中的自我拯救主题
孙晓娅1,2
(1.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2.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诗人不能拯救世界,但能拯救自我,白红雪就是一位企图通过反抗与亲近来拯救自我的诗人。他一方面在反抗中自我拯救:面向个人的自我反抗和谴责,通过严酷的自我解剖在重拾信仰中实现自我拯救;面向他人和社会,将自身融入到“他者”或集体里进行“一体批判”。另一方面他在亲近中自我拯救:不拒斥现代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有益成果,从对现代文明病的拒斥出发,进一步走向对旧日家园、身体和那些具有同一性质的精神巨人的全面亲近。通过反抗与亲近,白红雪完成了具有某种超越个人、集体或时代意义的自我拯救。
白红雪诗歌;自我拯救;反抗;亲近
白红雪曾在一首名为《荷花》的诗中写道:“吃到莲子和藕的时候/你的形象便顺流而下/轻轻洗涤我心中的污渍//你的千年华诞已过/没有什么频道宣传你/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庆祝//莫非‘出污泥而不染’/已成了众矢之的?”在这里,精神的追求被无情抛弃,而不断泛滥的物质主义,不仅成为人们逃避精神的借口,甚至成了人们攻击精神的武器。诗人无比痛惜地感到这是一个价值颠倒的时代。当其他人在痛悼着现代社会信仰的崩塌,并且企图通过某种艺术的或政治的方式,来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的时候,诗人却敏锐地发现,现代人恰恰是以对精神家园的背离来成就他们自己的。这一点, 戴望舒的朋友,诗人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这样说过:“本来, 像我们这年岁的稍稍敏感的人, 差不多谁都感到时代重压在自己的肩上, 因而呐喊, 或是因而幻灭, 分析到最后, 也无非是同一个根源, 我们谁都是一样的, 我们底心里都有一些虚无主义的种子……所以,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 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1]换言之,他们把漂泊当做归宿,把路上当做终点,他们用虚无主义来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标榜。在一个以虚无主义为根基的时代,一切所谓的价值重建不是一个悲剧,相反,它是一个笑柄。
白红雪认为诗歌是不能拯救世界的,正如他在自己的核心诗学观念里所表明的那样,“诗歌不可能拯救正在陨落的彗星”。但这并不是犬儒主义式的推卸责任,因为诗歌虽然不能拯救世界,诗人却可以拯救自我。而且不能拯救世界之后,诗人唯一能做的,也就剩下自我拯救而已了。这也正是诗人在其诗学观里所极力彰显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但她完全可以拯救尚未绽开的昙花。”
实际上,从广义上讲,一切生活在技术社会和消费社会中的诗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只是一件,即自我拯救。只是他们对于旧的精神价值的态度不同,一派人选择通过诗歌去清除、遗忘,和过去决绝,为的是可以无所留恋地一往无前,不管前面是有路无路,是什么样的路,他们在乎的首先是行走本身。另一派人刚好相反,他们企图在诗歌中重建一个旧文明的精神王国,把旧精神从现实的存在转移到语言的存在中,在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之家”中重新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白红雪就是这样一个自我拯救的诗人。而诗人的这种自我拯救,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在《死亡的雷是甜甜的苹果》里,诗人曾感叹道:“生活在这片水深火热的土地/我们不能反抗什么/也不能亲近什么”,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诗人的激愤之辞和自谦之语。它恰恰向我们透露了诗人自我拯救的两种方式,即反抗和亲近。
一 在反抗中自我拯救
诗人曾说:“我之所以一直坚持着诗歌创作,其动力主要是企图彻底摆脱苦难这种欲望的驱使。”又说:“因我的日常生活与诗无关,更缺乏诗意,然而,也正因为缺乏诗意我才写诗。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大地!”可见诗人的自我拯救工作,首先是从反抗苦难和反抗日常生活的无诗意状态开始的。诗人出身于湖南农村,贫穷而苦难的现实环境不仅直接损害着一个人的物质生活,也严重损害着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使其精神趋于贫瘠化和荒芜化。战胜苦难后,诗人面对的则是物质充裕却粗糙平庸、缺乏诗意的日常生活,这使得他不得不又一次走上追求“诗意地栖居”的道路。但是,比苦难和平庸生活更可怕的敌人,却是“物欲”。诗人曾说:“现在只剩下‘物欲之鸟’‘审美之鸟’已经中弹,伤势很重,能否活下去?恕我只能偶尔创作一点小诗去疗治她。”更概括一点说,便是人性中那贪婪和邪恶的本性。这种贪婪和邪恶的本性,诗人又曾形象地譬喻为“人类精神内核的虫子”,并且认为这种精神内部的病变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晦隐不显的,科学家和政治家都无法感知,“唯有诗人感知到了世界‘深处’的病变,感知到了不可名状的虫子在咬噬人类心灵”。这一论断虽然有夸大诗人能力之嫌,但它实际上充分肯定了艺术尤其是诗歌的拯救功能,为诗人利用诗歌进行自我拯救提供了某种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
而诗人的自我拯救,正是通过对这种贪婪和邪恶本性的暴露、谴责和反抗来完成的。这种反抗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直接面向个人的自我反抗和谴责。如诗人反抗自己对“黄金”的贪欲:“这里的黄金也在闪电/并且常常灼伤我的信仰/飞过城区的翅膀/因镀满金色而变得沉重无比”(《深圳无雪》),深圳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一度使诗人出现迷恋和彷徨,以至精神的信仰被闪电般的欲望所灼伤。然而通过大胆且严酷如鲁迅式的自我解剖,诗人最终在重拾信仰中实现了一次自我拯救。
在另一首诗《狗腿和手》里,诗人反抗的则是自己的“食欲”。诗人在诗中叙述了自己在寒冷的初冬周末约请朋友共吃狗肉的经过。本来,请朋友吃狗肉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当这是一条童年时代曾经与诗人朝夕相伴的狗时,这条狗“昨天回家时,它还猛摇着尾巴/朝我异常友善地拥抱过来/眼睛里充满了比忠诚更浓的温暖!”诗人终于受到了不可遏制的自我良心的谴责:“以前不知道尝过多少回/却没有哪一次令我如此心酸”。诗人感到人性中那不可填满的欲望沟壑是伤害其他生命的根源,而这种伤害,又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铁血逻辑之上的。从这种良心觉醒出发,诗人才在诗的最后发出了这样一种奇想:“如果狗腿也可以进化为手/这世界会不会发生太多的雪崩?”可以说,这种设想狗进化为人,并且为了自卫而和人类发生血战的图景,正透露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尊重动物与人类享有平等生命权利的自然主义意识。同时,通过对自己戕害无辜生命的深刻谴责,诗人也尊重了自己的精神: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自我救赎。
诗人不仅反抗自己的“黄金欲”和“食欲”,更致力于反抗现代都市文明病对自己的侵袭和毒化。在《我走进黑暗痛饮阳光》中,诗人写道:“我们的心灵 只生长毒草/我们的面包 已染上爱滋病/在这里 失乐园得而复失/真实甜蜜的谎言 一次次盛开//山那边不是海 也不是上帝/着火的稻草人 随意飘散/荷枪实弹者 赤裸裸播下仇恨”。面对现代都市里乱象横生的纵欲、谎言、暴力等毒雾的围困,诗人发现的出路是“痛饮阳光”,用纯洁、勤劳、勇敢等品质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抵抗,哪怕孤军一人在黑暗里独饮精神的阳光,也不愿在随波逐流中与众人一起沉入无边的黑暗。
诗人反抗的另一种情形,不是直面自己,而是面向他人和社会。一切美好生命的消逝都使诗人无比惋惜,而一切损害和毁灭着美好生命的邪恶势力,都遭到了诗人深深的斥责与痛恨。他哀叹一头即将被宰杀而无力挽救自己命运的牛(《站在屠宰场旁边的牛》),他讽刺用“导弹”猎杀天鹅的丑恶者(《天鹅与导弹》),甚至在一般人都愿意原谅的孩子那里,诗人也看到了这些幼小心灵中所潜藏的黑暗:在《秋天的鸟声及枪声》一诗中,诗人把鸟视为与人“同祖同宗”之物,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根,就是自然和生命。然而,正当诗人的思绪沉浸在寻根的快乐之中时,“冷不防听觉的门 被枪声击中/邻家的孩子打落了小鸟”,使诗人由寻根的快乐一下子堕入了生命毁灭的悲愤之中。诗人反对一切戕害生命、忤逆自然的行径,因此不仅成人猎鸟他要诅咒,孩子猎鸟他同样诅咒,以至在最后发出要提醒鸟类学习人类召集军队和设置监狱的手段,以便“以其人之道治其人”的诗人式的痴想。
这种向外的批判似乎与“自我拯救”无关,其实仍然可以视为一种间接的自我批判。一方面,这是自我批判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另一方面,诗人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也会选择将自己融入到一个“他者”或集体里,去进行“一体批判”。“一体批判”同时具备了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功能。我们知道鲁迅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一体批判”,其中是潜藏了很深刻的自我批判精神和某种浓重的自我批判成分的。而诗人显然在有意无意间继承了前人这种独特的批判传统,从而构成了一种间接的“自我拯救”。
二 在亲近中自我拯救
海子曾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提到现代人失去土地后的漂泊无依状况:“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大地本身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己经丧失了多少东西。”[2]现代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必须抛弃他们的本原,然后才能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正如诗人所写的:“应该是惊心动魄的一会呵/就这样含泪 背井离乡”。历史的无可逆转的力量如洪水般挟裹着他们滚入到另一种生存的海域,以便去成为历史的主人,生活的主人,物质的主人,而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旧有的精神家园的失落。在精神和物质、守旧和堕落之间,诗人感到的是尖锐的对立。正如诗人在以下两首诗中所昭示的:
从月光下背井离乡的人
又饮恨归来
泪珠 棉桃一般沉重!
(《棉花》)
现在 流浪如歌
被诗歌染红的叶片呵
已背叛了良心和故乡
令我渴望终生!
(《樱花》)
在这种尖锐对立之下,留个我们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是“饮恨归来”,在回归和守旧中求得良心的完全和精神的安宁;要么是“背叛良心和故乡”,在前进和堕落中实现那与生俱来的欲望的满足和人性的生长。前者的直接后果是“饮恨”,后者的直接后果则是一种“渴望终生”的对土地的饥饿感。
但在这样的两难选择面前,诗人最终走出了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他并不拒斥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成果,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像现代人那样,把灵魂像一条船一样停泊在肤浅的欲望的水洼里,在精神的“荒原”上匍匐爬行。他把自己精神的一瓣心香,投给了早已被现代人抛弃的旧日的土地。只不过,那已不再是一片贫穷落后、愚昧封闭的封建宗法制土地,而是一个被诗人的精神之水所充分净化和纯化了的圣土仙乡,一个在纸上被搭建起来的完整的精神家园。在《蒲公英的白》中,诗人写道:“今夜,那小木屋里的灯光/仍然黄狗一样把黑暗守望”,那在长期的孤寂中独自把茫茫黑夜守望的小小的灯光,正是诗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隐喻和象征。借助对这一亦真亦幻、已实复虚的心灵故乡的亲近,诗人得以抵御现代都市文明病的侵袭和毒害:“今夜,我把洞庭湖从记忆里挤出来/并苦口婆心引导她与一只萤火虫相恋/这城市的灯光太脏,也太忧伤/我决不让她投入你的怀抱!”(《我所怀念的洞庭湖》)短短几行诗,不仅使我们充分领略了诗人的倔强个性,看到了诗人独力和污浊现实苦斗的艰辛,而且钦佩于诗人苦斗背后那一坚定而有力的精神信仰。
诗人对精神家园的亲近,在其诗中不仅通过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通过隐性的方式渗透出来。诗人的创作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便是对身体意象的迷恋和大量书写。其身体意象或身体情境出现的频繁性和持久性,甚至使人误以为这是一位下半身的写作者。但诗人并非是为身体而写身体,他的书写不单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也不仅仅是出于某种词藻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其动机亦应存在于对某种本原性存在一以贯之的皈依和热爱中。“白红雪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疼痛感是白红雪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它既来自现实的体认,也来自诗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白红雪诗歌的‘身体书写’背后有着诗人的关怀和生命思考,身体不仅仅是生命的符号,同时也是生活文化的载体。”[3]精神家园和身体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某种本原性的东西或者具有某种本原性。这种内在的相似性,使诗人由对一方的亲近毫无保留地变成了同时对另一方的亲近。实际上,在诗人那里,回归身体是可以作为回归家园的某种隐喻或象征而存在的,如他对一枚桔子的书写:“我终于乘车回家/累极了,多想躺进你那/柔软多汁的怀中”(《重写桔子》),就是这种转化可以存在的证明。因此,诗人对身体意象的书写,就不仅是一种艺术经验的体现,还在根本上具有了一种美学理想或精神家园的意义。有论者就曾指出:“肉身的冷暖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经验。肉身的痛苦或幸福是人最基本的生命经历。肉身的创造与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创造与生产。肉身是人的生命支柱,没有肉身,生命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因此衡量人生应该以肉身为准绳,人生思考须从肉身开始,诗意创造必须从肉身出发。”[4]这即表明了从肉身出发达到诗意的可能性。肉身一方面被自然、社会、文化所构成,充当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又成为打造自然、社会、文化的根基,只有当文化的背景、氛围和理念都有机地溶入其中时,它才能显出深层次的活力。”所以,亲近身体,也由此成为诗人自我拯救的一个手段。
同样,由于连类而及的作用,诗人在亲近自己精神家园的同时,也通过亲近那些具有同一性质的精神巨人以实现自我更新:
呵 春天来了
你的笑容仍然憔悴
最圣洁的部分呈紫
像黛玉大咳之后的咯血
多么顽强的鲜艳!
让忧郁深藏心底
爱与恨扎根泥土之中
哦 紫云英
那只翩然飞来的蝴蝶
是不是改变命运的风帆?
(《紫云英》)
诗中蝴蝶的意象,含有某种自我批评和自我警醒的意味。把蝴蝶比喻为“改变命运的风帆”,无疑是一种反讽手法,讽刺如蝴蝶式的现代人的见风使舵,虽然改变了命运,却终于不免精神上的漂泊无依。与此相反,紫云英的意象则寄托了诗人对那些虽付出巨大牺牲,却仍然不离不弃他们的精神净土的圣徒式人物的感佩(按诗人自己在《另一次梦中的采访》中所列举的,就包括圣琼·佩斯、帕斯捷尔纳克、马拉美、屈原、昌耀、海子等)。诗人把紫云英比喻为“林黛玉”,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是与薛宝钗所代表的世俗主义者截然相反的形象,她是一个由于持久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高地而最终为残酷现实所无情碾碎的悲剧性象征。林黛玉的形象本身隐喻了人类的某种宿命。在另一首诗《我的新娘林黛玉》中,诗人把林称之为“火中取栗的妹妹”,表达的也正是同一个意思。但和曹雪芹不同,诗人虽然同样看出了这种宿命,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通过亲近那些精神领域的巨人,通过语言和诗歌,作为一种消极的抵抗,诗人至少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拯救。
通过反抗和亲近的两种姿态,诗人完成了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个体的自我拯救。但除此之外,是否诗人就真的无所作为了呢?诗人说:“诗歌即使可以卸下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放弃对人类精神苦难的稀释与调和!”可见诗人虽然在现实的层面上承认了诗歌拯救社会的无能(所谓“可以卸下”,实质是无力担当),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却仍然坚持着诗歌可以改进人类精神的传统信仰,因此才特别强调了诗人“稀释与调和”(实质就是担当)人类精神苦难的天然而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精神改进的层面上,改进社会与改进自我具有了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改进社会永远不等于改进自我,但改进自我永远是改进社会的第一步。从这个角度上看,诗人的自我拯救就具有了某种超越个人的集体的或时代的意义。
[1] 戴望舒.望舒草·序[M]//戴望舒.望舒草.香港:现代书局,1933:1.
[2] 海 子.海子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7.
[3] 王士强.“扎根于梅山,而又超越了梅山”:“天下梅山·白红雪诗歌研讨会”综述[J].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4(1):231-234.
[4] 段建军.肉身化的思与诗[J].唐都学刊,2000(4):196-197.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On the Self-redemption Theme in Bai Hongxue’s Poetry
SUN Xiaoya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e poet can not save the world, but can save himself. Bai Hongxue is a poet who attempts to save himself through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 On the one hand, he saves himself in resistance: for the individual, he makes self-resistance and condemnation, realizing self-redemption through harsh self-analysis in the faith restoration; for the others and society, he integrates himself into the "others" or collective to receive criticism together. On the other hand, he saves himself in proximity: he does not reject the beneficial results of modern socia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refusal of modern civilization disease to the overall proximity toward the old home, the body, and those spiritual giants with the same nature. Through resistance and proximity, Bai Hongxue completed a self-salvation with some sort of personal, collective or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Bai Hongxue’s poetry; self-redemption; resistance; proximity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03
2016-12-02
孙晓娅(1973-),女,吉林长春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
I207.2
A
1674-117X(2017)02-0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