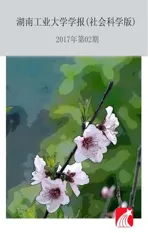“义无反顾的光芒穿过寒冷”
——白红雪诗歌的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
2017-02-23霍俊明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部,北京 100875)
“义无反顾的光芒穿过寒冷”
——白红雪诗歌的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 创研部,北京 100875)
白红雪的诗歌充满无限可能的悖论空间和强烈的尴尬与反讽意识。这种强烈的悖论性紧张、矛盾修辞和尴尬抒情,源于他提前用理想情怀的冲动领受了一个时代难以想见的寒冷,并以一束义无反顾穿越寒冷的光芒的姿态在诗歌的世界中探寻。其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悖论性修辞的话语方式,同时呈现了个人生活体验、想象方式、生存方式的某种尴尬、冲突。诗人要表达真理只能用悖论的语言,作为一个真正的与语言、想象、经验、现实、历史不断发生摩擦的诗人,白红雪的充斥着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的诗歌彰显出了悖论的强大力量。
白红雪诗歌;悖论;修辞;尴尬;抒情
在这个看似越来越自由的时代,诗歌的写作、发表、传播、获奖甚至成名都显得如此容易,容易得让人心惊。但是,当我细读完白红雪的诗歌后,我决定应该为之写下一些哪怕是零碎的感受。对于白红雪这个湖南诗人本身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样也好,能够让我在诗歌中完成一次纯粹的对话。而白红雪的诗歌写作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了强烈的悖论性的紧张、矛盾修辞和尴尬的抒情,正像是那束光芒在义无反顾中穿越寒冷,诗人提前用体温和内心的理想情怀的冲动领受了一个时代难以想见的寒冷。而可怕的是,这种寒冷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暧昧的天鹅绒监狱般的寒冷。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似乎任何的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被用得滥俗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吗?”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有形或无形的奥斯维辛,有的是用机枪和毒气制造的集中营,有的是用柔软的天鹅绒制造的监狱,区别可能只在于此。
白红雪的诗歌给我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悖论空间和强烈的尴尬与反讽意识,这是否印证了当年克林思·布鲁克斯曾认为浪漫主义的典型风格是“悖论的惊奇”,而古典主义尤其是玄学派诗歌的典型风格则是“悖论的反讽”,尽管布鲁克斯的这个总结在很多人看来都有草率的嫌疑,但是基于中国当代诗歌在90年代以来的写作事实,我认为诗人写作中的悖论修辞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维度,尽管可能我的这一概括同样是充满草率的。因为,在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急速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物欲狂潮在城市的高大灰色建筑对郊区和农村的蔓延与吞噬中,作为生存个体都不能不空前地强烈感受到尴尬、悖论、困惑和矛盾的基本体验,而当这种体验以个人乃至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呈现出悖论修辞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在不同类型的诗人身上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或许,对于那些永远在光线暗淡的书本阅读中进行玄学写作和无限的耽溺于内心的不及物写作的诗人而言,悖论、紧张和生存的瓜葛都永远与他们无关。相反,只有那些真正的与语言、想象、经验、现实、历史不断发生摩擦的诗人才能够彰显出悖论的强大力量。
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布鲁克斯将悖论看作是诗歌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他认为诗歌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因为“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1]白红雪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悖论修辞的话语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同时呈现了个人生活体验、想象方式、生存方式的某种尴尬、冲突。正如他的名字,白红雪自身一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悖论,而其诗集《鱼和刀的罗曼史》就是一个有关悖论的最有力的证明。
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渊中,诗歌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到来。索尔·贝娄不无失望而满含悲辛地说:“从事于诗歌,哲学与绘画等等,在技术社会中不过是人类的托儿所游戏,在科学的时代到来之后这台游戏便不得不被抛在后头。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科学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2]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无限提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得诗人无形中对以城市为象征的工业化场景有着本能性质的排斥。“蚂蚁常常把一些沉痛的往事/挂在橡树枝丫上,并耐心等待/那只啄木鸟前来确诊//但啄木鸟的嘴唇呵/压根儿只亲吻橡子……”(《橡树和蚂蚁》)白红雪患上了深深的时间焦虑症,往事的记忆成为病痛,犹如体内的桃花短暂的饱满、红润过后就是长久的荒芜、无尽的迷乱与哀愁,加之城市作为一种商业和工业文明的强大阴影的遮蔽,诗人不能不在尴尬中排拒这种焦虑和遮蔽,甚至在诗学的意义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黑色象征,城市,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符号,“那天下午红酒一样缠绵/整个黄花机场停满了小轿车/就像沉淀于红酒底部的药渣:/把广场内的矮树醉得东倒西歪!//风其实并不大,阳光中的白鸟//却无法站稳脚跟。她们浮萍一样/在机场上空漂泊,竟把我们的信仰扯断//亲爱的!如果我俩是一对白鸟/也有可能在这城市上空漂浮/但上帝呵,会不会把咱们做为药引/分别投放到两瓶红酒之中?”(《黄花机场上空的白鸟》)这让我想起当年的波德莱尔和他诗歌中的城市、街区:“穿过古老的郊区,那儿有波斯瞎子/悬吊在倾颓的房屋的窗上,隐瞒着/鬼鬼祟祟的快乐,当残酷的太阳用光线/抽打着城市和草地,屋顶和玉米地时/我独自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追寻着每个角落里意外的节奏/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3]白红雪的诗歌是否印证了那句话——真正的诗歌从来都不是妥协的产物?面对着轰然加速的市场时代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无限膨胀,诗人不能不处于一种巨大的焦虑之中,“今夜,我把洞庭湖从记忆里挤出来/并苦口婆心引导她与一只萤火虫相恋/这城市的灯光太脏,也太忧伤/我决不让她投入你的怀抱”(《我所怀念的洞庭湖》),铁轨、城市,市场,共同打开的是当代人的飘泊和孤独、茫然的状态,再升华点说就是象征了一个农耕文明的挽歌,所以诗人想“拯救”,拯救被异化的个体,因为工业时代的生活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在公路上高速行驶的人只关注于速度本身而忽略了两旁景观的真正面目,而理想化的挽留显然是不能刹住那无限加速度的工业火车的,而工业化的代表城市则成为诗人批判的对象,“哦,远方田埂上的哇鸣和狗吠/是否还在掩护走私毒品的萤火虫?/这城里的灯光呵,已经淤血一般/在黑夜体内悄悄凝固和沉淀”(《午夜月光的颤抖》)。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晶体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汹涌奔突的河流上的宁静或不安的火焰,照彻和呈示着个体存在和内心深处的黑暗场阈。歌德曾警告世人——谁不倾听诗歌谁就是野蛮人。精神大哲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往澄明的晦暗的林中路上不时提醒人们: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我们就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因为这个时代遮蔽存在,因而隐藏存在。
可悲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温润的农耕庆典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理想情怀,那大地上延展不息的本源性依托在诗人海子的黑色的死亡事件中撕裂成一个个碎片。诗人作为大自然的歌者,本可以直接传达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但诗人的言说往往会陷入一种困境之中。“言说的窘境,真正来说,即是灵魂窘境的表征;更进一步地说,诗灵魂窘境的来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们也许无法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但我们至少能够改造我们的语言。”[4]诗人通过改变语言(词语)来改变世界,缓解灵魂的窘境。所以在80年代甚或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诗”曾大量涌现,而其中不乏拙劣的仿写使包括“乡村”在内的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受到了戕害。对于中国诗人而言,土地、庄稼、自然意象恰恰能够彰显出诗人的复杂经验和想像力。但是,真正的从乡土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再次遮蔽。而白红雪的一些关于乡村的诗歌写作却让我重新感受了乡土的力量,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歌元素的苏醒,“今夜。那小木屋里的灯光/仍然黄狗一样守望黑暗/而蒲公英的白/又把远方的风雨烫伤//母亲内心的疤痕/却永远不会发光/更不能远走他乡!//但她的白发似草药/可以给我的思念止痛”(《蒲公英的白》)。我不知道在这个无限暧昧而又强夺的时代,还有多少个诗人能够从骨髓深处歌颂和怀念那些逝去的乡村事物,还有谁能够在冷漠工业的复制罗网中吟唱关于本源性质的纯棉般的乡村情愫。
对于白红雪以及当下部分义无反顾穿过寒冷的诗人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和停泊地;不幸的是,诗人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永远的宿命般的漂泊者和异乡人,当无家的潮水在工业时代日夜奔涌的时候,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望乡者,“站在屠宰场旁边的牛/突然哞一声,低下头去/把命运之蚁狠狠踩灭!//但草的尖叫呵/仍然在牛角内奔突/企图扎破一节盲肠回家?//而每一条路都露珠一般/从起风以后的叶间滴落”(《站在屠宰场旁边的牛》)。在我看来,这屠宰场旁边的牛不容置疑地成为现代人有限生存的真实写照与象征。那么,人类究竟该栖居何方?出路何在?城市已然淤血一般,乡村也先天性伤痕累累。因为对于白红雪而言,出生地的乡村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见证,而一个普通家族的历史却是用无边无际的痛和刺目的死亡写成的,这种触目惊心的家族谱系叙事是在历史与现实、生存与死亡、回忆与遗忘中同时完成的,“一觉醒来,我被多年前的夏天/直呛得想哭;那天中午/栀子花在河岸上裸体转身/竟被一只牛虻撞成重伤//然后。姐姐也从邻村归来/进门后便与母亲抱作一团/其哭声,若缤纷闪闪的蝶/落满我幼小心灵的每一寸矮墙//现在又是榴花般热烈的夏天呵/母亲仍然在乡下的小木屋里/弱不禁风地做些事情,通夜点灯/而她内心的怀念比灯光还亮!//因为姐姐自杀的晚上/狗吠熄灭了所有灯光……”(《夏日往事》)闷热的夏天,死亡的阴影,家族的沉闷故事带来了生命存在的诸多难以规避的悖论甚至宿命,这种黑暗的生存与死亡的细密纹理当诗人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抚摸的时候,那种毛糙的刺痛仍叫人惊心得难以释怀。
当然,白红雪的一些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总觉得他的诗歌似乎还有一个地带一直没有被开垦,是经验的视阈限囿还是诗歌语言的需要继续淬炼?白红雪的有些诗歌尤其是一些几行的短诗过于强调了一时一地的即时性感受而缺少了诗意和时间的沉淀。在此前提下,我更喜欢白红雪的《短剑与长裙》《时间深处的白蚁》《第二十种鸟声》《时间的马群》等长诗,其中既有诗人本体性的关于生命、时间和生存的多重探问性的挖掘与思考,而且同时容留了个人性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于是,彼岸世界长满了谎言/花谢之后还是花谢啊/被马踏过的土地已枯萎成海绵/匆匆吸干了时间/时间吸干了真理/真理又吸干了我们的生命”(《时间的马群》)。
希望这个春天窗外正在盛开的白玉兰和席卷北京的沙尘暴能够给这个时代的诗人带来更多的叩问与反思;而白红雪的诗就如这场玉兰与沙尘暴的悖论之争,不断地纠结和互否,不断地在排拒中向前奔走。可令人揪心的是,其终极问题仍然不容乐观:白玉兰能否远远地甩掉黄沙?
[1] 克林斯·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M].郭乙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
[2] 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492.
[3] 波德莱尔.恶之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56.
[4] 张 闳.声音的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A Light Proceeding through the Coldness Unswervingly:On the Paradoxical Rhetoric and Embarrassing Lyric in Bai Hongxue’s Poems
HUO Junming
(Department of Creation and Research,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875 China)
Bai Hongxue’s poetry is filled with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paradoxical space and strong embarrassment and irony consciousness. This kind of strong paradoxical tensions, contradictory rhetoric and embarrassing lyric, originates from his feeling of the unimaginable coldness of an era with the impulse of idealism ahead of time, and his exploration in poetry as a bunch of light unswervingly proceeding through the coldness. There are a lot of paradoxical ways of discourse in his poems, and it presents some embarrassment and conflicts of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imagination and survival modes. To express the truth, the poet can only use the paradoxical language. As a poet constantly rubbing with language, imagination, experience, reality, and history, Bai Hongxue’s poetry, which is full of paradoxical rhetoric and embarrassing lyric, shows the great power of paradox.
Bai Hongxue’s poetry; paradox; rehtoric; embarassment; lyric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02
2016-12-01
霍俊明(1975- ),男,河北丰润人,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诗歌批评以及现当代文学。
I207.2
A
1674-117X(2017)02-0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