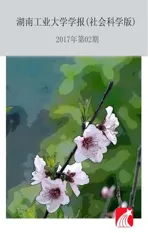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及启示
2017-02-23王志谋
王志谋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及启示
王志谋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邱华栋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重要代表,其小说中游荡者系列形象的塑造是作家试图以边缘化的审美生存为现代都市人在商品与技术的牢笼中重新唤回情感与个性的一个尝试。游荡者们摆脱了生活必然性的限制,以审美的眼光悠游于都市,其生存挣扎及其价值追寻方式为我们探索新价值的重建提供了启示:边缘化为价值探索提供了合适的角度与场所,游荡所表征的现代审美意识为在理性化都市中重构日常生活结构提供了一种可行性。
游荡者;理性都市;精神生态;边缘化;现代审美意识
人类是自然界生物圈的一员,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精神决定了人类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与行为实践。考察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并寻找与发现价值重建之途径,是生态批评的一项首要任务。
199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说全景式地反映了现代都市人的物质与精神状态,对认识现代人的精神生态有着重要作用。其中,邱华栋作为“当代最早自觉”[1]的都市文学写作者之一,和“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2],其写作集中于城市的“地理学”与“病理学”,力图“在浮华的都市表象描摹和迫切的生存焦虑缓释中”逼近“人的存在之核”,[3]对各类都市人群的精神状态都有着深入的了解与刻划。基于此,其小说中以一系列游荡者形象为价值问题作出的探索,对我们平衡现代人的精神生态与寻求价值重建之路就有了启示性的意义。
一 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
邱华栋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大体可分为三类:“闯入者”系列、“都市新人类”系列及“游荡者”系列。因其处境与追求的不同,他们的信仰、需要、动机、情感,包括人生观、价值观等当然各不相同,但概而言之,每类人物的各精神要素之间在其主要趋向上又存在着明显的一致。大体而言,“闯入者”们以情感的商品化标注了消费社会的价值失范,“都市新人类”以生活的同质化呈现了技术时代对个性的无情宰制,游荡者形象的塑造则是邱华栋试图以边缘化的审美生存在商品与技术的牢笼中重新唤回情感与个性的一个尝试。
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最为明显的身份标识,就是他们终日在繁华商业街道或城市皱褶中无所事事地游荡。如果说闯入者努力要把握商品法则以寻求城市规则的认同,都市新人类在城市规则下清醒而麻木地生存,那么游荡者们则试图以其东游西荡来打破效率与时间的概念,对抗冰冷的城市理性规则对柔软人性的压抑,在都市的水泥森林中重新召唤情感与个性。
情感作为人类精神要素中最为柔软的部分,是衡量人类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张扬理性的启蒙时代,休谟就曾对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定位:“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4]也就是说,理性不过是实现启蒙的手段,启蒙的最终目的在于人的全面实现、人的感性力量的舒展,而理性的片面发展,不过是对启蒙本末倒置的挟持。闯入者们的情感商品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是对自身的背叛。可悲的是,这种情感的商品化其实不独是闯入者们才面对的现实,大量泛滥的商品化情感已经将情感本身柔软丰盈的内质抽空,也就是说,这种情感的物化进而导致了情感的扁平化,而建基于丰富情感的个性也随之干瘪,现代都市人由此变得自我缺失、个性匮乏、面目模糊,呈现为一种无差别的同质。
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正是从跳出商品化编织的物质主义牢笼出发,试图恢复人的情感、个性与尊严。他们“摆脱了现代人的实用需要”,[5]不再汲汲于货币与商品的得失,而是对城市中一切作用于心灵的新奇与美的东西投注了巨大的热情,这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对理性的狙击。《天使的洁白》中的袁劲松、《城市战车》中的流浪艺术家群体、《鼹鼠人》中的叙述者以及《闯入者》中的吕安及拾垃圾者等都是这类游荡者,事实上,邱华栋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荡者。这些游荡者们不满于商品世界的欺骗性光泽与情感世界的麻木与荒芜,竭力想要从工具理性无处不在的规约中突围出来,力图以艺术的新鲜活泼的经验来抗拒被异化得日益程式化与平庸的生活,“他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美是永存的,只有那种附着于事物之上的美才是他惟一值得信赖的。”(《天使的洁白》)但他们又不以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方式为旨归,而是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直接将审美精神引入了都市生活,践行一种以游荡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化生存方式,这显然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
《天使的洁白》中,袁劲松对美与美感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在一个时尚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兼美术编辑,他对这份“拍出物的充满欺骗性的光泽”的工作心怀不满,认为自己所供职的杂志“在吊着城市中所有人的胃口”,因而经常“不务正业”地用镜头记录生活中点滴片断美的显现。他拍了一组叫《曲线》的照片,“偷拍的全部都是在大街上行走的女人的后腰与大腿之间的剖面”,“比一张张人脸还生动。”他认为这组照片呈现了一个观察女人的新视角,并期待着能在喧闹的街区展览。因为阻挠了主编与一个女下属之间的肉体交易,他被除职了,继而进入一个广告公司工作。但当认识到广告与物欲之间的勾搭时,他毅然辞职,“他想,这种基于生存意义上的工作只能使我不断丧失”,他不再工作,而是每天背着相机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发现与记录生活中摆脱了物欲纠缠的悠远宁静与驳杂多采,“尽量地捕捉着城市中的光芒”,他变成了一个城市面貌的匿名记录者,并在发现与捕捉城市之美中重新实现了久违的自我。与袁劲松一样,邱华栋小说中的其他游荡者们也都摆脱了生活的必然性,不再“跟着机器的节奏舞动手臂”,而是让自己在城市的理性之网中游弋出来,以发现与捕捉都市中的激情与美感来充实日益贫瘠的生活。《城市战车》中,流浪艺术家们在繁华的商业街区以其富于挑战性的行为艺术让丧失了想象力的城市“局部发炎、红肿”;《鼹鼠人》中,“我”学会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城市,掌握着城市中的各种秘密;《闯入者》中,捡垃圾的老人用捡来的香水瓶在他的住所构筑了一个“被香化了的世界”……可以说,“审美”,是这些深感物化城市压抑,并不同程度地“摆脱了生活必然性限制”的人们为其存在找到的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在游荡者们无所用心的游荡中,隐匿于都市中不为人知的美被偶遇与发现,而游荡者们也在对美的追寻中拥有了更为丰盈的情感与自我意识,曾经的紧张被舒缓,与世界的关系也从对立迈向了和解。
“在机械论所构建的新环境里,只有机械、机器能找到舒畅如回家的感觉,因为它们只需要秩序、目的、规律性;它不需要与机械无涉的爱,不需要同情,更不需要审美。”[6]由神灵崇拜转向了金钱崇拜的城市,其都市理性与商品法则以无处不在的规约力将现代人的生活纳入了一个庞大的异化之网,它吸纳了非都市人的进入,决定了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将他们变成了“正宗”的都市人,又以其严密的规范化组织将一个个的都市人纳入一个以商品与交换为中心的系统,预设了他们的生存规则与生活方式,因此,现代都市人在以商品为中心的城市规则之下普遍迷失了自我。“生态危机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棘手也最为艰巨的生存考验”,[7]都市人群的这种精神生态失衡则是人类面临的最为切近的生存困境。邱华栋小说中的游荡者们以审美为旨归,以意图重建新价值的方式,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向度。
二 邱华栋小说人物价值探寻的方式与启示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先驱鲁枢元认为:“走出生态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现行的经济制度,再往深层追究,在于那种‘纯粹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说到底,那种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造成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8]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努力去寻求新价值观的重建?以邱华栋为代表的新生代都市小说中的价值探寻,特别是游荡者们的生存实践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边缘寻找:价值探寻的新视角
“人链”是邱华栋城市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所有的人只是构成了一个个链环,一环套一环,所有的人都可以由那种关系的链条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了城市中奇异的人链。”《天使的洁白》与《闯入者》等小说中都有着这一意象,每个单个的人都被作为人链中的一环而纳入了体系,它形象地表明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性存在对人类所形成的巨大吸附力与控制力。而要摆脱这种控制,就需要打破这种关系,从人链中挣脱出来。这意味着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从价值探寻的角度而言,这种边缘化恰好为其提供了合适的角度与场所。
首先,边缘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置身其中者所缺乏的视角,从而展现了被铺天盖地的商业化所遮蔽的生活的另一面。波伏娃在论述“边缘”时说:“要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它。……略为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9]可见,对急功近利价值观的批判需要一个抽身而出的边缘的位置,这样才能对其作出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此外,边缘作为中心的对立物,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挑战中心的力量。边缘化“指的是那些建立而后又瓦解主要价值标准和传统的自相矛盾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在于对我们文化中的那些‘自不待言的东西’提出疑问和挑战。”[10]《鼹鼠人》就是于边缘处观察与思考现行价值观的一部奇特作品。文中叙述了一个城市规则的反抗者隐居于下水道中观察与思考人类命运,并试图改变人类发展方向的故事。故事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大学毕业的计算机高材生不适应现代城市的快节奏生活,认为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因为“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我们自己”,他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络之中发现了一种“在而不属于”城市的缓慢生活方式,并隐居于此,“通过静坐和冥想”,达到了气功师常说的“辟谷”状态,借助城市发达的下水道网络,他“利用别人的电源和线路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并随意穿行于城市之中,以了解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通行的物质标准来衡量,鼹鼠人纯属自讨苦吃,他过的是一种臭气熏天而又暗无天日的日子,但正是置身于繁华世界的地下,他触摸与认识到了无处不在的系统化力量之巨大和可怕,并试图以其行动来“刹住现代社会疯狂前进的车轮”。鼹鼠人隐居于城市下水道显然是一个隐喻,一种边缘化的极端状态。但正因为他对被“纳入社会非常机械的系统中去”的坚决拒绝,他才能于边缘处有所发现与行动(当然,是不可取的行动)。
其次,边缘正因为外在于主流文化,其价值标准与行为方式必然有与“中心”相悖之处,其中丰富的秩序外生存方式可为新价值的重建提供借鉴。
卡里斯玛解体之后,社会发展似乎越来越趋向多元,不同的观点得到承认,不同的态度得到尊重,不同的生存方式得到认可,不同的行为方式得到理解,由此,出现了主流与边缘的分化;但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潮流又试图以其不可思议的集中化与理性化特点将一切逸出其规范的现象纳入潮流之中,从而又促生了主流与边缘的种种颉颃。当主流文化出现问题时,“边缘”则成了主流一个可资借鉴的补充,因为“边缘”是“文化种种对立二元之间或多元之间相互对话和交流、不断生发出新气象的地带……不同要素在这儿接触和融合,滋生出新的东西,并迅速向周边扩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和文化本身。”[11]《天使的洁白》中,袁劲松主动从人链上消失后,发现了城市中所不为人识的美,并达成了一种“没有目的地生活”的状态——没有目的的生活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一种真正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二)都市审美意识:重构日常生活结构的重要元素
经典马克思主义将“革命”作为改变旧有社会结构、建设新的社会人群关系、并全面解放人类自身的手段。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12]城市社会的总体结构固然是“异化”产生的重要前提,但使人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却是日常生活结构从“神圣”向“物化”蜕变而产生的“现实”衰败,这不是可以通过革命解决的,而必须重构日常生活现实。日常生活结构是内在主体意志向客观生活层面投射、结晶而成的社会框架,由此,“现实重构”必然根源于一种内在的、想象性的建构,其建构的材料是内化于精神、再现于符号的现实碎片,其建构的冲动则在于克服内在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分裂,寻求主体与客观的和谐平衡,以此来安顿城市人的心灵,因此“现实重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审美重构”行为。“家园意识”,对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来说,是这种审美重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望废墟中的家园’可以说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而在世俗的生存之痛的体认中向往超世俗的诗性理想,可以说是新生代小说的共同主题。”[13]
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一大批理论家都论及了艺术的救赎功能,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平庸的,因此需要用艺术那种新鲜活泼的审美经验来抗拒日益异化的生活。但他们往往将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对立,把艺术作为一个乌托邦世界来理解,它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有着烛照日常生活的超验之光,二者有着明确的界限。这种与日常生活泾渭分明的审美由于其遥不可及而只能表现为一个梦想,从而削弱了其作用。事实上,新生代小说中的诸多价值探寻文本都呈现了这种脱离现实的归家之旅无可奈何的衰败,如韩东的《新版黄山游》、朱文的《关于九0年的月亮》、毕飞宇的《是谁在深夜说话》等。这些试图以“回到自然”“回到中世纪”的方式追求人性完满的小说文本其结局都证明了这种以“返回”为特征的归家之虚妄。“我厌倦了这座城市,但又无法回到乡村。”(《我们是自己的魔鬼》)这种清醒的意识表明了归家之旅的双重无奈。邱华栋小说中游荡者们直面城市化现实的审美化生存为我们弥合二者之间的分裂提供了启示。这些徘徊游荡于街道的形象,他们感受着都市的嘈杂、奢华与混乱,也体验与撷取着它的美感与丑陋,并在这种内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中,将生活与审美相结合,为日常生活的审美重构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标本。其都市审美精神,可从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他们以其走走停停的步态,打破了效率与时间的概念。如前所述,以现代理性为基础构建的城市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它以服务于工业生产与商业运作而不是人类生存质量提高的需要为中心,从而导致了城市的标准化与均质化。在这样的城市中,人们被束缚在有限的几个点上,严格遵循机器的作息时间,日复一日、毫无悬念地生存,城市似乎包蕴了无限秘密,但对大多数人们而言,城市只是公司、厂房、住宅和连接它们的街道。在这一秩序化的生存环境中,无目的的漫步以一种打破标准化的异质性,显示出一种超然与舒展。“步行将会创造窥看、观察的机会,搅乱和打碎稳定的城市秩序。步行开辟了新的空间,能创造传奇和故事,并把街道号码和建筑以及意义焊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步行使窥视者得以从城市的管辖中创造他/她自己的空间和意义。”[14]在本雅明的描述中,19世纪巴黎的游荡者们正是以漫步逃离了“脑满肠肥的反动政府的邪恶目光”,并在拱廊街中获得了“无穷的补偿”。邱华栋笔下的游荡者们,同样也从这种对抗于功利主潮的姿态中获得了一种逃逸的快感。
其次,游荡者们将好奇心投射在现代都市的意象符号与生活情态之上,以一种“拾垃圾者”的眼光,将这些碎片化的符号与情态进行组合与意义的运作,合成现代都市人生图景,并直指人的心灵。“在我看来,当代的生活,当代的情感,网络时代的爱情,更多地呈现了碎片的性质。”而游荡者们的兴趣,就在于“把它们拼凑起来”。(《遗忘者之旅》)在这种摄取与拼凑中,既有着都市丰富的物质所带来的奢华之美,也有现代城市密集的人群所内蕴的震惊,有对气息消散的缅怀,也有对丑恶作为一种真实审美体验的提升。对现代世界的美学表现,不单是对美的正面表现,也包括对消极美的表现,包括对“现代性中的粗糙垃圾”加以过滤、从邪恶中提取美,而且后者更为重要。《闯入者》中,拾垃圾的老人可堪成为一个现代都市中以审美精神贯注日常生活来发现意义的寓言。捡拾垃圾的老人代表着游荡者,垃圾中的香水瓶是他在碎片化的世界中搜检的素材,那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造型奇特别致的香水瓶”构成的“奇幻的世界”则是游荡者在彻底解构经验世界的表象之后重新组合成的想象性世界,一个“被香化了的世界”。
其审美精神的进一步表现是游荡者们对行为艺术的痴迷。他们在繁华的商业街区用铁笼子将自己锁起来表演《饥饿的艺术家》;或将骡子穿上丝袜,抹上口红,再披红挂彩,并与它成亲;或在身上涂满蜂蜜,然后一丝不挂地走进厕所,让苍蝇爬满全身。如果说游荡的姿态与碎片世界的拼凑体现的是现代都市人自得其乐的可能途径,行为艺术则是以各种富于挑战性的手段来刺激与唤醒新人类们的生活感觉。
总体而言,游荡者们的审美观不再是以“静观”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审美观,而是建立在“过渡、瞬间、偶然”之上的现代审美观,它以本雅明所谓的“震惊”为核心质素, 以碎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又以其片断式审美境遇的缀连指向对现代生活的总体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与以“返回”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家园之思相比较,这种面对都市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更为切实可行,因为前者在提倡回到自然的同时也回避了另一个更具扩展性的“自然”:日益复杂丰富与混乱的现代都市生活,而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
回到鲁枢元关于现代生态灾难源头的言论上来,价值观的重建显然不是一个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改革,日常生活结构的审美化调整是一个更为细微、重要而又切实的环节,唯其审美精神贯注了整个日常生活现实,“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统领性地位才能受到威胁,而这,就要求我们多持一点边缘心态,在“现代社会疯狂前进”的潮流中多一点悠游的、审美的立场。
[1] 谢有顺.爱情有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恶习[N].南方都市报,2002-10-30.
[2] 陈晓明.生活的绝对侧面[M]//邱华栋.夏天的禁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276.
[3] 林 舟.生命的摆渡[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229.[4] 休 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53.
[5] 陶东风.关于浪荡子、知识分子及现代性的对话[DB/OL].[2016-12-03].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0817.
[6]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74.
[7] 龙其林.经典与模型:试论《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5(5):75.
[8] 鲁枢元.开发精神生态资源:《生态文艺学》论稿[J].南方文坛.2001(1):21.
[9] 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4-155.
[10]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6-17.
[11] 滕守尧.文化的边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5.
[1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75.
[13] 吴义勤.在边缘处叙事[J].钟山,1998(1):56.
[14] 伍 端.空间句法相关理论导读[J]世界建筑,2005(1):29.
On the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Straggler Image inQiu Huadong’s Novels and Its Implications
WANG Zhimo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idea ,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generation writers, Qiu Huadong described a series of characters named the stragglers in his works, which reflects his attempt to use the marginalized aesthetics to recall the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of people living in modern cities and in the cage of merchandise and technology. The stragglers have got rid of the limitations of life’s inevitability. Struggle of survival and value seeking offer us revelation to explore the new value: marginalization can offer right angle and position for value seeking, moder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loitering represents offers a kind of feasibility for the reconstitution of daily life structure in rational city.
straggler; rational city; spiritual ecology; marginalization; moder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17
2016-10-29
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新时期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15GZYB63)
王志谋(1978-),男,湖南双峰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I207.2
A
1674-117X(2017)02-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