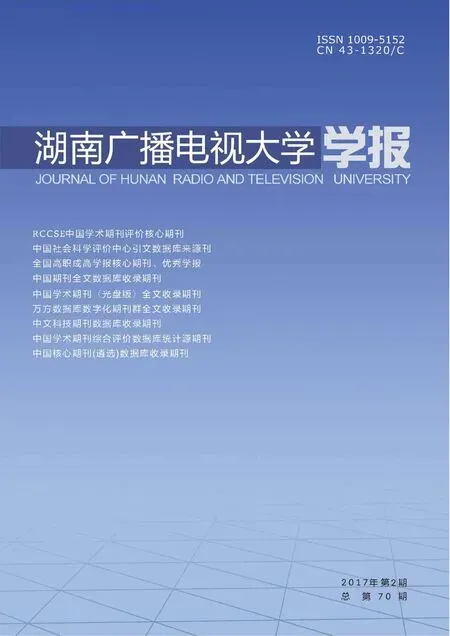宋代禅僧临终偈中的般若观
2017-02-23王嘉宁
王嘉宁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宋代禅僧临终偈中的般若观
王嘉宁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临终偈不仅是僧人生死观的最终呈现,更是其对所悟佛理的阐发。宋代禅僧临终偈从人生幻梦、来去转换与回归自然三方面,阐释了禅宗般若观中“不厌生死,不乐涅槃”的法空思想,遣荡矛盾、不落形式的同一观念以及无束无碍、得大自在的自性般若观。
禅宗;临终偈;般若观
临终偈是僧人偈颂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又称示寂偈、辞世偈、临终辞众偈等,通常创作于僧人临终之际,也有僧人预知圆寂时间,提前一段时间进行创作的情况。临终偈往往会反映出僧人面对生死的态度,以及对一生修习所得的总结。而禅僧创作的临终偈,既蕴含了禅宗生死观,更是禅宗基本思想的具体呈现。从禅僧所作的诸多临终偈中,其意象特点、内容选择等,都能折射出最为正宗的禅家思想。
般若思想作为禅宗核心思想之一,从根本上影响着禅僧对自我修行所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般若”一词来自于印度梵文,本义为“智,智慧”,在佛教用语中引申为“圆满无缺的超越智慧”。而在中国禅宗的思想发展中,受《文殊说般若经》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般若经》影响,以及历代祖师的具体诠释,般若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在禅宗“五家七宗”最为兴盛的宋代,禅僧临终偈的创作也呈现出繁盛的状况,创作临终偈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禅林传统。观察这些禅僧们所作的临终偈,可以窥见禅宗般若思想之一斑,并了解禅宗思想是怎样融入禅宗文学、体现在禅林创作之中,进而可以通过观察偈颂文本中的一些特质,对禅僧临终偈及其中禅宗般若观的具体内涵进行解读。
一、人生幻梦与“不厌生死,不乐涅槃”的法空思想
般若在多种《般若经》中都被解释为“空”的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明确指出:“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般若波罗蜜。”[1]将般若解释为“无所有、不可得”,并在其后列举了“十八空”即“空”的不同形式。“空”在宋代禅僧的临终偈中,表现为幻梦的意象,如“六十九年一梦身,临行何用忉二说”(释净如),[2]“八十七春,老汉独弄。谁少谁多,一般作梦”(释宗印),[2]“六十九年,一场大梦。归去来兮,珍重珍重”(释妙印)[2]等。在许多临终偈中,禅僧会以“今年几十几”一类的句式,交代自己临终之际的年龄,而把这几十年的人生视作梦境,何尝不是将人生、将过往一切都认为是“空”,这也正是般若观的基础要义,正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3]即所有的“有为法”,本质上都应该看作“空”,将一切都予以否定。
在许多诗歌创作中,“人生如梦”的比喻往往会被理解为是带有一种悲观色彩的描述,更偏重于对个人悲凉心境、人生幻灭之感的抒发。但禅僧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之时,将人生看作“空”,比作大梦一场,并不是将一切都视为虚空、虚无,以消极的态度去面对死亡,这一点可以追溯到般若观的原本内涵中来进行观察。《般若经》中“空”的概念在大乘与小乘佛教中演化出了不同的理解,大小乘佛教都能够体悟到“我空”的层次,即追求自利解脱的最终目的,但只有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派才能走向不急求于解脱的“法空”层面上来,即“不厌生死,不乐涅槃”[4]的终极境界。在禅僧临终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人生视为幻梦的同时,禅僧并没有以悲观的姿态去面对、畏惧死亡:“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2]临济宗黄龙派创始人黄龙慧南法嗣报本慧元的这首《示寂偈》,在感叹“五十五年梦幻身”的同时,回顾游历四方的过往,面对死亡,却选择描绘白云散尽、新月当空的开阔景象,亦是对此刻坦然、超脱心境的书写。临终之际,勾勒“云开月明”之景,对五十五年的生命视为梦幻,也以平和的心态将死亡也视为“空”。这首临终偈对于以般若法空观的观念去面对生死的心态书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心态在其他禅僧的临终偈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牧庵法忠禅师的《示寂颂》:“六十六年,游梦幻中。浩歌归去,撒手长空。”[2]六十六年的时间好像在梦中游历,在梦醒时分,伴以长空、浩歌,撒手而去,可以说是以更为达观、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归去”、迎接死亡。
禅僧对死亡无所畏惧,但也不会去积极追求涅槃解脱之境,不会在临终偈中表现出欢欣之情,而更偏重于将面对死亡的心情都隐藏、消融于解说禅理或物象譬喻之中。将禅僧们的临终偈与天台宗祥符可久法师的临终偈进行对比:“生老病死,乐在其中。已矣乎,传语风华雪月。”[5]而在禅宗僧人笔下,绝不会直接抒发“乐在其中”的解脱之感,“声闻、独觉厌怖生死、欣乐涅槃,不能具足福德智慧。”[4]禅僧们对生死之事以无畏的姿态来面对,将法空观一以贯之,将生死都视作是“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圆寂之际不再考量生死之事:“咦,从来生死不相干。”[2]了悟真正的法空境界,也就不会对涅槃的所在有向往之意,更不会对即将到来的涅槃之境产生主观上的情感波动和临终表达。
二、来去转换与遣荡矛盾、不落形式的同一观念
在宋代禅僧所作的临终偈中,还可以看到禅僧经常使用“来”“去”的概念来理解生死问题:“来未尝来,去未尝去。七十四年,月印寒渚”(释元聪)[2]。“来无所来,去无所去。瞥转玄关,佛祖罔措”(释崇岳)[2]。“来时空索索,去也赤条条。更要问端的,天台有石桥”(释师范)[2]。“来亦无所从,去亦无所至。来去既一如,春风满天地”(释行源)[2]。
在这几首有代表性的禅僧临终偈中,“来”与“去”已经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两种概念,“来”“去”二者之间、“来去”与生死之间的关系都变得更为复杂:“未尝来,未尝去”,否定“来去”的发生过程,归结于“既未尝来,亦未尝去”的一切空无;“空索索,赤条条”对作为独立事件的“来去”本身进行特征上的书写,强调的是“来去”本身都具有“空”性;“无所来,无所去”与“无所从,无所去”,是禅僧对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困惑,是对“来去”本身的归宿感到迷惘,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来去”的目的。总的来说,把“来去”归于“空”之中,仍然是以般若观中的法空观来看待生死问题。
但在这里出现了“来去既一如,春风满天地”的认知,认为“来”“去”等同,即认为生与死具有同一性,就能够达到“春风满天地”的豁然境界。这种认知并不是囦叟行源禅师的个人体悟,在其他禅僧的临终偈中也有相似的禅家思考:“生本无生,死本无死。生死二途,了无彼此”(释祖珍)[2],“来说生兮去说灭,二人证龟成一鳖”(释显端)[6]等临终偈,将来去、生死同等看待,消除对立因素中的差异性,这也正符合《坛经》对般若观的进一步解读:“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3]在禅家所追求的真正的“大智慧”中,形状、数量、颜色、尺寸、情感、道德判断等等因素,其中存在的常识性的对立观念,它们之间的矛盾性都被消解在虚空之中,不是按照习以为然的理解,而是打破二元对立的绝对模式,构成没有边界的“大”智慧。正如杨惠南先生所说的,禅宗般若观包含着“遣荡一切矛盾、对立,而表现出世间一切皆为美善,乃至不落入固定形式、固定价值判断”[7]的精神。只有真正认识这一点,才能洞彻“烦恼即菩提”[3]的转化机制和内在含义,才能认识到生与死之间的共通之处,才能看到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
禅宗般若观中的这种同一观念,在禅僧笔下还有更为丰富的演绎与解读。如五代入宋时期的荐福承古禅师就在临终偈中写道:“天地本同根,鸟飞空有迹。”[6]临终之际想告诫后人的是天地同根同源的道理,也是对生死一致的别样阐发。还有禅僧以“反常”的方式来解读生死、来去:“衲僧家生死事大,去来是常。去去实不去,途中好善为。来来实不来,路上莫亏危。无缝合子盛将去,无底篮子盛将来”(释慧宪)。[6]用无缝盒子、无底篮子,怎样能够盛来盛去?正是用这些违背物理的反常现象,来解说去即不去、来即不来,来去之间互相转化而合一的观念,因此才会当“生死事大”到来之际,坦然认为“去来是常”,把生死同等对待,既不畏生,又何畏死?把生死都看作是平常之事。而宋代临济宗杨岐派的大德大慧宗杲禅师,其临终偈对这种般若观的阐述更是简单明了:“生也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2]生也如斯,死也如斯,临终之时写不写只言片语,留不留下给后人的禅思,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了。生死都是如此,有无本来也是一样的,强调矛盾主体的一致性与共通之处,正是禅宗般若观在思辨方式上的具体表现。这些临终偈想传达给诸位法嗣的,就是这样遣荡一切矛盾、不落于二元对立形式之中的同一观念。
三、回归本真与无束无碍、得大自在的自性般若
报本慧元禅师的临终偈描绘了“云开月明”之景,在其他禅僧所作的临终偈中,也有相近的景观书写:“雪鬓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尽诸缘。廓然笑指浮云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源禅师)。[2]“四大既纷飞,烟云任意归。秋天霜夜月,万里转光辉”(释智策)。[2]“八十二年,驾无底船。踏翻归去,明月一天”(释普度)。[2]“月”意象在佛教文学中出现,更多情况下是对其澄澈、清净特质的强调。浮云消散、明月显现、遍照大千世界的景象,既是禅僧临终之际开阔、超然心态的具象描摹,也是彼时回顾一生修行,对自性般若的终极领悟与阐发。
“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3]自性般若是般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性般若本是个人寻得的佛性,但在宋代禅僧的临终偈中,为了对毕生所了悟的佛理进行总结、给后学以开示,自性般若通常会与对自然景观的书写紧密相连。据《五灯会元》记载,云门宗尊宿蒋山法泉禅师“晚奉诏住大相国智海禅寺,问众曰:‘赴智海,留蒋山,去就孰是?’众皆无对。师索笔书偈曰:‘非佛非心徒拟议,得皮得髓谩商量。临行珍重诸禅侣,门外千山正夕阳。’书毕坐逝。”[8]且不论法泉禅师对“去智海”还是“留蒋山”的选择是什么,临终一偈将无尽的佛理都寄托于万千层峦的夕阳之中。视角上的转变,由屋内转向了室外,空间也变得更为开阔,不再局限于眼前的生死,而是回到了更为广大的自然天地去,告诉后人自性的真正所在。
“自从南宗禅兴起,早期佛教的人生哲学便逐渐由禁欲苦行转向了适意自然。”[9]将临终的寄托交予自然,正是对自性般若的终极发掘。“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3]可以说自性是般若的根源所在,寻求自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大智慧”。在临终、接近涅槃之境的时候,悟得更为明晰的禅理,就会进一步发掘出自身的自性般若,书写自然景观也是对禅宗般若观的另一重阐释:自性般若就在自然之中,不能在重重执念与障碍里去寻求。因而有的禅僧所作临终偈,读来并不像圆寂之前的创作:“昨日离城市,白云空往还。松风清耳目,端的胜人间”(释道初)。[2]禅意、禅思就在白云、松风之间。“太白峰前青海尾,一目秋光弥万里。渔翁醉入芦花深,白鸟不飞天在水”(释慧空)。[2]极目秋光,水天一色,大智慧就在这包容万事万物的无尽造化之中。
在死亡面前,禅僧更容易打破所有的迷惑和障碍,去除种种绝对对立的观念,使自己的本心更为清净,更能够了悟“空”的本质,从而能够进入无束无碍的“大自在”境界。“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释道楷)。[2]“五阴山头乘骏马,一鞭策起疾如飞。临行莫问栖真处,南北东西随处归”(释梵卿)。[2]无所畏惧,随处而安,进入法身无生无死的境界,去除那些束缚思维的执念,走向自性般若的本质。正如石头希迁禅师的精妙回答:“僧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谁缚汝?’问:‘如何是净土?’师曰:‘谁垢汝?’问:‘如何是涅槃?’师曰:‘谁将生死与汝?’”[8]既没有束缚,又何谈解脱?抛下这些蒙蔽本心的观念,才能达到更高的般若境界。
但并不是所有禅僧都能在临终之际回归本真、得大自在。“霜天云雾结,山月冷涵辉。夜接故乡信,晓行人不知”(尼法海)。[2]霜天、云雾、山月、冷辉、夜信、晓行,这首临寂偈在宋代禅僧临终偈中,呈现出少有的冷境,但依然存在“回归”的主题,将圆寂比作回归,只不过是归乡、归家,而非回归自然。不过,回归故乡也是在强调自性般若需要破除障碍、走向原初才能获得,还是没有离开自性般若无滞无碍的根本特性。
通过对宋代禅僧临终偈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对禅宗般若观的具体内涵呈现出三个层面的解读:首先是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上来看,以人生幻梦的比喻,诠释般若法空的禅家思想,将生死视作“空”,达到“不厌生死,不乐涅槃”的心境;在此基础上看待生死之间的关系,以“来去”论生死,消弭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对遣荡矛盾、不落形式的般若同一观的阐发;选择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主题,是对无碍、自在的自性般若观的具体阐释,强调的是打破执妄才能获得大智慧。由此我们能够看到,禅僧的生死观念与禅宗般若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平生的修行、悟道,都早已深深渗透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之中。在死亡面前,更容易破除执妄、悟得更为深刻的禅理,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境界中去。从僧人创作中选择宋代禅僧的临终偈,对其中所蕴含的般若观进行探讨,也提供了从佛理角度理解佛教文学创作的一个具体的观察角度。
[1]鸠摩罗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卷8[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
[2]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金刚经·心经· 坛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A].大正新修大藏经:卷7[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5.
[5]张艮.宋代天台宗僧诗辑佚77首[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6).
[6]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7]杨惠南.禅史与禅思[M].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8]普济.五灯会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9]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OnthePrajnainZenMonks’DyingVersesintheSongDynasty
WANG Jia-ning
The dying verse of Zen monk is not only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but also an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Zen monks’ last verses in the Song Dynasty,from aspects of life being dreams,the transition between life and death,and returning to nature,explain Zen wisdom,that is,no hate of life and death and no joy with nivana.
Zen; last verses; view of prajna
2016-12-28
王嘉宁(1995— ),女,兰州大学文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I207.22
:A
:1009-5152(2017)02-0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