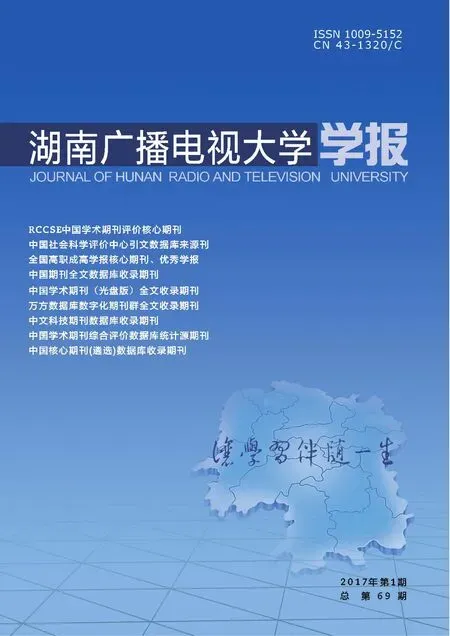长沙存在中共早期组织的考证
——与质疑者商榷
2017-02-23黄爱军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
长沙存在中共早期组织的考证
——与质疑者商榷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存在,不时有人撰文提出质疑。文章从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等六个方面,对质疑者进行反质疑,认为质疑者的观点不能成立,长沙中共早期组织客观存在。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考证
在1921中共正式成立前,国内先后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六个城市建立起党的早期组织,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这在党史界已形成了基本共识。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存在,一直有人存在质疑,又因之衍生出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时间的质疑。本文将对质疑者提出质疑,并围绕质疑者所提基本理由逐一展开讨论。
一、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
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论者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至今未发现任何有关长沙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1]。实际上并非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完全缺乏,而恰恰是论者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视之不见。
有关长沙早期组织最权威的文献资料,当属长沙早期组织主要创立者毛泽东留下的材料。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2]P5651939年5月12日在延安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对萧三讲:“1920年7月,我从上海回到长沙后,恢复长沙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发动长沙自治运动,成立共产党长沙分部(总部设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陈独秀负责),然后,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从事新闻工作。”[3]P240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中,毛泽东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此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6月21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中,一再提到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
除了毛泽东留下的材料外,其他当事人也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在《被遗忘的中共建党人物》中说:“一九二○年九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未能亲自了解它。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五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五人中无可争辩的首领是贺民范,第二位是船山中学教员李浑,第三位是何叔衡,……第四位是毛泽东,……第五位是易礼容”[2]P599。青年毛泽东好友、新民学会核心成员萧子升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中回忆说:“一九二○年,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暗中进行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他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希望我也能参加。同时蛮有信心,他认为我决不会出卖他们,虽然我对他们并不表赞成。”[2]P575新民学会成员萧三在《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中亦回忆道:192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加入了团或党的小组,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2]P584此外,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李达、张国焘、周佛海等人的回忆材料,均提到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二、正确解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记载
最能反映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情况且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当属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献提供了长沙早期组织最重要的信息。该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4]P20质疑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认为,前面说“共有六个小组”,后面又说“来自七个地方”,这里必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小组。没有小组的地方正是长沙。[5]这种解读显然曲解了历史文献的本意。七个地方,六个小组,必有一个地方不在“六个小组”之内。笔者认为,“六个小组”是指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党组织,没有把上海的党组织包括在内。上海的党组织,今天人们称为上海发起组,并不是历史上的名称,当时的名称就是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所提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指的就是上海发起组。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先后在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建立了六个小组。正因为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所以当上海发起组确立在上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才会向上述各地的党组织发出开会通知并寄去路费,各地代表克服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前往上海赴会。对这次会议的发起、组织及与会人员的食宿安排,上海发起组作了认真准备和精心谋划。新近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最迟在1921年4月份已开始启动[6]P59,北京小组还专门派张国焘提前到上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很难设想,对这样一次意义重大、十分严肃的会议,上海发起组的李达、李汉俊等人会错发与会通知,使没有党组织的长沙,甚至还不是党员的毛泽东、何叔衡与会。
三、正确解读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
否定长沙早期组织存在论者的一条重要理由是,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没有提到长沙组织。[1]该报告记载:截止1921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北京组织、天津组织及唐山站分部、汉口组织、上海组织、广东组织、香港组织、南京组织。[7]P552-554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张太雷报告是否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实际?
众所周知,张太雷早在1921年1月即离开中国前往俄国,并于1921年3月到达俄国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或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显然,张太雷报告中所涉及的1921年1月以后中共创建的内容,不是出自张太雷自己对中共创建情况的了解和掌握。那么,张太雷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这方面的新材料呢?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了一种假设(同时又基本上否定了这一假设):张太雷在入俄以后从中国得到新的信息——考虑到当时中俄间的通讯状况,一时难以相信。[8]学者冯铁金认为,是杨好德提供了国内情况方面的重要内容,还有其他人也可能提供过内容,如维经斯基[9]。学者叶孟魁、赵晓春认为,是由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所提供。俞秀松于1921年4月下旬抵达伊尔库茨克,与张太雷会合。[10]这两种推断,因缺乏文献材料的支撑,同样难以让人相信。
资料显示,张太雷所获得的新材料,正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次克,为了与东方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六月离开伊尔库次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1]P78-79“为了与一切冒险组织划清界限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我作为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指舒米亚茨基——引者注),和张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报告。……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12]由此可知,张太雷报告中所反映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应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华活动及其工作思路的情况。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在华活动及其工作思路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实际进程有着明显的差异,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情况的记载,未能反映中共早期组织的实际状况。张太雷报告中所列出的天津、南京、香港等地,并没有党的组织。张太雷报告中没有列出的长沙、济南等地,不等于就没有党的早期组织。
四、如何解读毛泽东与蔡和森的通信中未提及长沙建党之事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不仅对蔡和森提出的建党主张表示完全赞成,还向蔡和森通报了国内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版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3]P4但毛泽东并未提长沙建党情况。否定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据此认为,如果当时长沙已经建党或正在筹备建党,毛泽东绝不会不告诉蔡和森。[5]这虽让人匪夷所思,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长沙不曾建党。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回信中虽然没有直接介绍长沙建党情况,但还是间接反映了长沙早期组织的存在。首先,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3]P4。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吾党”,只能是指已经建立的党组织,如果长沙早期组织不存在,如果此时毛泽东尚不是党员,“吾党”之说从何而来?其次,毛泽东对陈独秀发起组织共产党很了解,说明他与上海发起组保持着密切联系。上海发起组为何适时将建党情况向毛泽东通报,并及时寄来团章、《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宣言》等?在当时党处于秘密的环境下,唯一的解释就是指导毛泽东等在长沙的建党建团工作。因此,李达、包惠僧、张国焘等人关于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在长沙建党的回忆是可信的。
从毛泽东早年创立新民学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到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中提出“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14]P59,到11月给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变为主义的结合”[14]P97,再到给蔡和森的信中对蔡和森的建党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4]P170,“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4]P225的思想轨迹来分析,受约在长沙建党后,毛泽东不可能无动于衷只是坐而论道,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实行家”的个性。
五、如何理解长沙新民学会年会未提及建党问题
1921年年初,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举行了有名的新年大会,会议讨论了新民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等问题。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时,毛泽东在发言中对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作了一番比较后认为,其它方法均行不通,只有“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5]P141会议经过讨论后付与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何权衡等12人,赞成德谟克拉西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1人,未定者 3人。[15]P143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通讯中说得十分清楚。[4]P225但值得人们推敲思考的是,在这次新年大会随后围绕“即刻如何着手”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何叔衡等并没有顺势将建党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毛泽东对会员提出的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筹措经费、办事业等着手进行的方法均表赞成,提出在研究一项中须增加“修养”,联络应是“联络同志”而不是非同志。同时又提出须要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并认为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而对陈启民、熊瑾玎、彭璜、陈子博等所提“组党”方面,毛泽东却没有提及。[15]P145-146最后主席何叔衡将各人所述着手方法归纳为六个方面付与表决,其中包括“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未涉及“组党”方面内容。[15]P146否定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认为,彭璜、陈子博都是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提出应该建党,可见在1921年1月之前长沙肯定不存在共产主义小组。[5]按照论点推断,新年大会上会员提出并最终表决通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否意味着在此之前长沙肯定就不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呢?答案是否定的。资料显示,1920年10月,毛泽东就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日记提供了这方面极为宝贵的资料。[2]P381另据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载,1920年年底前,长沙地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数达14人。[2]P360-361因此,彭璜、陈子博提出应该建党,不等于此前未建党;毛泽东、何叔衡未将“组党”列入表决内容,更非意味着他们还未开始着手建党。笔者者认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党处于秘密状态,即使在新民学会内部也不宜公开进行讨论,而青年团则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二是党已处于组织之中,已不是要不要组党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党组织的问题。
六、怎样看待李达、易礼容等人的有关回忆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中,毛泽东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所填写的入党时间,在无法找到相关文献资料印证的情况,与其他非当事人的说法相比当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但否定毛泽东1920年入党的论者以毛泽东的说法是孤证为由,对毛泽东1920年入党这一事实提出质疑,并以非当事人李达、易礼容的说法来引证。[16]否定长沙早期组织存在的论者,亦以李达、易礼容的说法为佐证。[5]实际上,李达、易礼容的说法经不起推敲。1957年李达在《回忆党的早期活动》中,说“长沙那时可能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法[17];1962年“七一”前,李达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讲“一大”报到时毛泽东是团员的说法[18]P465,均与此前他自己多次回忆中的说法相矛盾。1949年李达在自传中说:“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19]P4。1955年李达在回忆“一大 ”时说:“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据我的回忆,当时国内和东京七个小组”[20]P10。“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他各地小组却比较散漫些。”[20]P12显然,李达这里所说的“七个地方单位”、“七个小组”,当然包括长沙小组在内。很难设想,在长沙无党组织、毛泽东尚不是党员的情况下,负责组织、联络召开一大的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怎么会把会议通知寄给毛泽东?①至于1979年易礼容回忆中的说法[20]P280-284,显然是把中共湖南支部建立的时间与长沙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给混淆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60年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易礼容不仅没有否定长沙早期组织的存在,而且对“一大”前长沙早期组织的活动,特别是文化书社在长沙建党中的作用作了详细介绍。[21]
如果长沙党组织果真迟至1921年10月才产生,且最初仅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三人,那么,在1921年11月由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要求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四区一样,“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7]P26。将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各地作同样要求,岂不太令人匪夷所思?
综上我们认为,否定长沙早期组织存在论者的理由不能成立,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长沙早期组织未能留下建党方面的材料,党组织处于极秘密姿态,长沙早期组织成员大多未能留下相关回忆材料等原因,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具体时间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鉴于建党之初党团不分,党、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20]P441的情况,考察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与建党关系十分密切的系列活动,参照彭述之回忆中的说法,我们认为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应在1920年八九月间。
注释:
①据《李达评传》载,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见王炯华著:《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79页。
[1]曾长秋.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各地早期组织的考证[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唐振南.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的诞生与陈独秀的关系[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 [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胡庆云,肖甡.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J].近代史研究,1984,(2).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R].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0,(5).
[9]冯铁金.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新考[J].党的文献,2008,(2).
[10]叶孟魁,赵晓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考[J].中共党史研究,2015,(11).
[11]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K·B·石克强.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J].百年潮,2001,(12).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5]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新民学会文献汇编[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6]向继东.毛泽东入党年月考[J].炎黄春秋,2009,(10).
[17]李达.回忆党的早期活动[J].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0,(1).
[18]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李达.李达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1]唐振南.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问题[J].求索,2001,(3).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CCP in Changsha
HUANG Ai-jun
Since 1980s, some people have been questioning?the existence of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CCP in Changsha. This paper?debates against this query?from six aspec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arly organization of the CCP in Changsha existed undoubtedly.
Changsha; the early CCP; textual research
2016—11—20
2016—2018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改革计划立项建设项目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党史研究工作室”(Szzgjh1-1-2017-7)。
黄爱军(1960— )男,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D231
A
1009-5152(2017)01-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