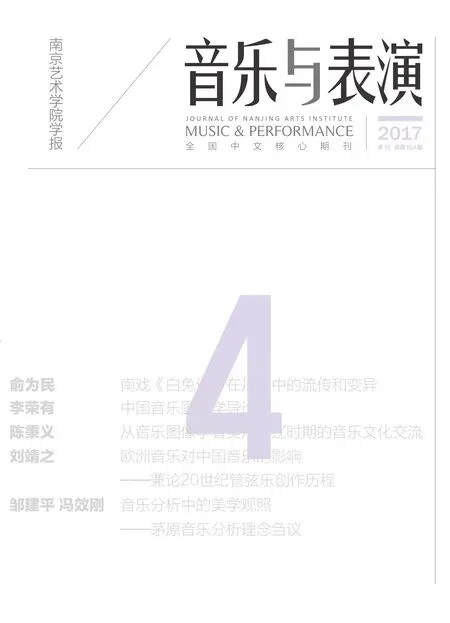论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①
2017-02-14刘建东嘉兴学院师范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刘建东(嘉兴学院 师范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丰子恺一生共出版音乐理论著作38部,发表音乐研究文论百余篇,其中介绍西洋音乐基础理论知识的著作占了大多数,无论是当时学校音乐课堂教学的需要,还是社会各界人士出于对西洋音乐的兴趣和爱好,人们都需要具备正确地识读乐谱的能力,理解并掌握旋律、节奏、节拍、和声等音乐要素的表现,所以这方面的著作其受众面广、读者众多,相应地这些著作的销售量大,社会影响广泛,1920年代出版的《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就是这方面著作的突出代表,它们不但是丰子恺音乐著作中最受人欢迎的书籍,也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西方音乐理论著作中的佼佼者。此类基础音乐理论著作还有《音乐初步》《西洋音乐楔子》《音乐初阶》《音乐十课》《音乐的基本知识》等,这些著作在近代中国社会音乐知识的普及以及学校音乐教学水平的提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丰子恺的音乐理论著作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基础技术理论的传授层次,也非仅仅是西方音乐理论的中国译介,在外国音乐史学理论及音乐美学理论的阐述方面,他也有辛勤的耕耘。丰子恺先生胸怀我国社会的音乐艺术普及工作,不但在20世纪20—30年代为起步中的近代中国新音乐发展作了很多音乐推广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气象,丰子恺也一样,他更加自觉地为新中国的社会音乐文化事业做一番贡献。通过他辛勤的笔耕,更为深入地阐释、传播音乐基础理论,为外国音乐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为发展新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是丰子恺音乐理论的一大贡献,而在以往的丰子恺音乐理论与实践贡献研究中,国内还没有同行对此进行过论述与研究,以下就循着丰子恺先生的论述,来一探他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究竟和原委。
一、社会主义音乐的特征
20世纪50年代,丰子恺转向了对苏联音乐历史的介绍和评论,1951年,在《进步青年》②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 时代号召“进步”,人人要求“进步”,让“中学生”成长为“进步青年”献给新中国,也是最好的进步,就此,创刊于1930年、已经出版了215期的《中学生》杂志改名为《进步青年》。连续发表了《苏联的音乐》《苏联的音乐家——阿雷桑得罗夫》《阿萨菲耶夫》《杜纳耶夫斯基》等文章,同年在《人民音乐》杂志发表了译文《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1953年,还出版了译作《苏联音乐青年》[1],显现出对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音乐事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其实,对俄罗斯音乐及音乐家的关注,在丰子恺笔下已经有过不少的论述,譬如在《音乐知识十八讲》《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著作中对俄罗斯民族乐派的详细介绍,对格林卡、鲁宾斯坦、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家以及他们创作作品的介绍等等。但20世纪以来,具体来说自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一方面,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并未得到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苏联在音乐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却让世人不得不承认是首屈一指的,对苏联在音乐文化方面的建树,也引起了丰子恺的高度关注,我们首先从《苏联的音乐》一文入手来考察丰子恺在1950年代的音乐观。《苏联的音乐》一文的关键词有两个:社会主义音乐和写实主义。在论述苏联社会主义音乐的特征时,丰子恺是这么定义的:
苏联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音乐怎么也有社会主义呢?有的!和政治无关,和社会脱离,为少数人享乐,而为大多数人民所不解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音乐;反之,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政治社会及全体人民密切关联的,是社会主义的音乐。[2]
文中将“社会主义音乐”定义为和社会、政治高度关联的,并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艺术形式。既然有社会主义音乐,那就自然有与此相对的资本主义音乐,《苏联的音乐》一文中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统统划为资产阶级音乐的阵营,也就是将丰子恺此前所高度青睐的、所讴歌的欧洲自17世纪以来的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音乐、浪漫主义音乐等,视为是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所脱离的、为少数人享乐服务的资本主义音乐。从音乐的本质特征来看,音乐本无社会主义音乐、资本主义音乐之分,显然,“社会主义音乐”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对音乐艺术的深刻影响,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苏联、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20世纪30—7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也渐渐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而系统论述“社会主义音乐”的理论著作,当数“1932年9月周扬(周起应)的译作《苏联的音乐》一书的公开出版”[3],1950年代,由于我国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所以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音乐及其创作原则在文艺创作中再次得到强有力的推行,因此,丰子恺的“社会主义音乐观”不是空穴来风,它明显受到时代社会风潮的影响。丰子恺发表的《苏联的音乐》一文中的观点甚至跟他之前一贯坚持的音乐艺术超现实的观点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由此可见政治力量的强大、时代风潮的普遍影响。
丰子恺关于音乐艺术社会功能的以往论述,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界,有前后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1937年之前,丰子恺对音乐艺术功能的论述总体上体现出纯审美的思想,倡导人们对音乐的观照要专注形式的审美,不必探求音乐的外在意义,甚至提出了音乐艺术“绝缘说”的论点,认为音乐艺术的创作、鉴赏只有与现实世界的功利关系绝缘,才能真正发现音乐的美,丰子恺在多部音乐著作中不时流露出钟情于音乐艺术的超现实性特征,强调音乐艺术的力量致使人们忘情于现实的矛盾和痛苦,并由此高度重视音乐的审美作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迅速转向民族救亡和驱除日寇,社会各界包括文艺界的救亡情绪空前高涨,作为一个有爱国责任感的艺术家,丰子恺也不例外,通过艺术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强调音乐的道德教化功能,成了丰子恺从事艺术活动的新的理念,此一时期,即使是丰子恺以《护生画集》为代表的漫画创作,也鲜明表现出其“政治志向与社会功能,即要以艺术培育新的道德,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培养共和国新人。”[4]对音乐艺术的认识就更不用说了,1938年,陆续发表的《谈抗战歌曲》《谈抗战艺术》,以及编选出版《抗战歌选》,充分表达了丰子恺积极投身抗战文艺的爱国情怀。所以,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音乐观,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后期的音乐功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苏联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影响,促成了丰子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的形成与确立。
《苏联的音乐》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音乐”的表述,其主要立足点是音乐艺术的“人民性”,苏维埃政府带领全体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和光明,所以苏维埃政府是苏联人民的政府,苏联的音乐是人民自己的音乐,反过来说,苏联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必须是保持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艺术形式。由此,丰子恺反对“艺术之外的活动妨碍艺术创作”[5]237的传统说法,明确提出了与自己以往观点相反的结论,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音乐树立新的标杆,排斥那种孤立、机械地埋头于音乐技术之中的纯音乐创作行为。从《苏联的音乐》一文中我们自然可以观察到苏联社会主义音乐乃至建国初期我国社会音乐道路的狭隘和偏颇,但是,也并非说丰子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音乐”一无是处,掺杂了现实政治的音乐也并非一定是不良的艺术,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譬如“提倡音乐家必须接触社会种种问题,必须接近人民,必须博学广问,必须过问自己的政府的事”[2];“艺术家不把艺术看作他个人的利益,而看作对全体人民的责任”[2]等等,这些艺术创作的普世价值观不但应和了1950年代的社会潮流,对任何时代的中国音乐家来说也是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的,“即便是在当下,有些理论学者不断强调‘艺术至上’,认为掺杂了政治的艺术形式产生不了好的作品,也不是真正的艺术,这种理论显然有着相当的局限性,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的大环境之外,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社会需要的情况下。”[6]只是“社会主义音乐”在中国一度滑向了政治的附庸、宣传的助手,而这并不是丰子恺笔下“社会主义音乐”的本质,而是丰子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音乐”在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全面异化,得另当别论。
二、写实主义的音乐创作手法
丰子恺《苏联的音乐》一文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写实主义”,什么是音乐中的写实主义呢?“就是拿现实的事体作题材”[2]。早在1936年,革命音乐家吕骥就明确提出:“中国新音乐的创作方法是来自苏联的新写实主义(或译现实主义)”[7],在写实主义音乐的方针指引下,为了和着音乐表现社会现实的宗旨,声乐自然成了音乐中最有力的表演形式,歌曲也就成为音乐中最主要的体裁,丰子恺依照苏联写实主义音乐的本质特征,阐述了歌曲创作在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的突出重要性,认为音乐和文字或者文学题材的结合是最“自然的合理的要求”[5]241,而同时期吕骥的观点更是将我国社会主义的音乐理解成必须完全建立在声乐体裁的创作基础之上,因为器乐音乐作品虽然能够给予人们积极的情绪感受抑或精神鼓舞,但没有明确表现内涵的器乐曲无法在思想内容上鲜明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的现实斗争与生活,所以我国当代音乐中声乐艺术(群众歌曲)的独领风骚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是器乐音乐的创作,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基本上也遵循标题性、革命化的原则,综观1950—1970年代的器乐创作,即便是比较成功的创作作品,也时常会出现创作中大量引用现成革命歌曲的现象,俗称“贴标签”,以求得政治上合格或迎合人们的普遍接受。为了阐明音乐的写实主义,丰子恺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文艺的发言:“文化的发展,必须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是民族的。”[5]243文艺作品的社会主义实质,简而言之就是内容上要表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与生活,而形式上的民族性,就是利用大众所熟悉的民族化的艺术形式,以利于民众接受和社会普及。在这里,丰子恺笔下的“写实主义”就是音乐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而这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耳熟能详的一个音乐观点。还是以周扬的译作《苏联的音乐》一书为例,在该书的“译后记”中,作者从1930年代中国革命音乐的艺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出发,对苏联革命音乐中的大众歌曲的艺术形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大众歌曲是阶级斗争和人们劳动热情的最有力的表现,丰子恺在《苏联的音乐》一文中提出的“声乐是音乐中最有力的表演”等观点,事实上跟周扬的观点一脉相承。再看周扬对现实主义音乐的具体阐述:“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3]作为“左联”文艺界的代表,周扬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具备广阔的视野和全面的修养,而且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学艺术界的领导者,他的话语带有鲜明的官方指令性,因此,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意识形态性质的文艺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音乐”的宗旨无论是思想引领还是在音乐艺术中的实践,都在我国得到了继承并发扬。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继续在我国发酵,翻看那一时期的音乐批评和音乐理论文章,不时会出现有关现实主义音乐理论的探讨文章,音乐创作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也得到了全面深入地贯彻,“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组第二次代表大会,则最终以决议的形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准绳确定下来。”[8]所以,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紧紧追随了时代的潮流,虽然他深知音乐艺术超现实性的特征的一面,但政治对人的影响是强大的,谁也无法脱离干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以聂耳、星海等为代表的左翼音乐家发起‘救亡音乐’在国内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对文艺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影响尤深,而中国 ‘救亡音乐’是受到苏联‘普罗音乐家联盟’的‘布尔什维克大艺术’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强调一切文学艺术是革命事业的螺丝钉,强调音乐的战斗性、武器性,这一思想对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的丰子恺来说,自然也对他的音乐功能观产生了莫大的影响。”[9]
除了《苏联的音乐》文集中阐述了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点之外,同年连载发表于《进步青年》上的四篇文章《苏联的音乐家——阿雷桑得罗夫》《阿萨非也夫》《布洛西罗夫斯基》《杜纳耶夫斯基》,介绍的正是苏联时代自觉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理论和创作原则的作曲家。透过对上述苏联音乐家的创作与思想的介绍,其中折射的正是丰子恺对一方面专心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又关注社会主义事业的音乐家的推崇;还有丰子恺发表于1951年5月《人民音乐》期刊上的译文《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文中介绍苏维埃音乐的题材应当是“现实主义观点的、人类重大要求的、人类普遍呼唤的”[10];批评“西欧的古典音乐已经和人民失却联络,它只生存在极少数的音乐听众上面”[10]等等,其主题也是对苏联现实主义音乐的介绍,以及在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良苦用心。
三、对新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指导与教训
如果说丰子恺在《近世十大音乐家》《音乐知识十八讲》等著作中基本上还是处在对西洋音乐知识的译介和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阐发的话,那么《苏联的音乐》一文完全可说是他个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理论阐述,以及对新中国音乐艺术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全面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现象、特征之后,丰子恺对我国的社会音乐生活提出了他的观点:
我国现在已经解放,应该向苏联学习,从前那种悲叹感伤,啜泣呻吟的腔调,现在都用不着了。‘无病呻吟’,即并无苦痛而假装忧愁以为风雅,更是过去时代的笑话了。我们中国的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具有优良的民族特色。今后我们要在这种民族形式中灌注社会主义的,写实的,乐观的内容,创造新中国的人民音乐。[2]
丰子恺深入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其理想是要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音乐,号召音乐工作者创作全面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音乐新篇章。事实上,翻看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创作在中国也有过成功的实践,首先,1930年代起,聂耳、冼星海的革命音乐创作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创作的道路;1960年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是建国后音乐创作的突出代表,两部作品创新艺术表现手法,热情讴歌了长征精神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功勋。作品一经演出,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并成为了近代中国音乐史上的经典。此外,现代京剧音乐的创作实践也是例子,肇始于1940年代延安平剧运动的对传统京剧的改革,其主要成就就在于地方戏曲、曲艺音乐与中国革命现实斗争的结合,从而打造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而即使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革命“样板戏”阶段,其艺术形式依然是传统戏曲音乐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结合。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创作不但讴歌了火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宣扬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也丰富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文化生活。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前后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及其他艺术形式,西方学者也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兴趣,克莱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指出:“在毛主席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把日常的生活光辉化了,那些农民的双颊泛着粉红色,在他们的土地上欢快地劳动”[11],精确概括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表现特征与内涵。
当然,客观地看,近代中国参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原则,狭隘片面地贯彻音乐与政治高度结合的方针,造成了很多后患,譬如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歌曲虽然数量上占据了新中国音乐创作的绝对优势,但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式的现象非常突出,降低了群众歌曲的艺术性;音乐批评领域对社会主义音乐对立面的所谓“资产阶级音乐”的不当批判,例如1950年代末对黄自艺术歌曲的批判,完全背离了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政治人物与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是评价与解释音乐作品的最主要群体,在此主导下的音乐创作逐渐发展为高度单一的革命模式。而追求作曲技法、追寻审美性质的音乐创作被无端地受到压制甚至批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创作原则由音乐创作要为全体人民服务逐渐狭隘地理解成为为工农兵服务,进一步上升到苛刻地要求为阶级政党服务、为政治形势服务。最终使得音乐艺术全面异化为政治的工具(我国1960年代一时甚嚣尘上的“文革”歌曲、毛主席语录歌就是异化的代表)。尽管主观上的良好初衷是出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新音乐,但丰子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观”客观上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音乐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创作,它必须容许作曲家自由的思想信仰和艺术信念,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近代中国,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信奉为音乐创作的原则甚至唯一原则,显然是反艺术的行径。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时代的音乐艺术是首屈一指的,究竟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或许“艺术往往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出于这样的客观环境,艺术家或者不得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他的心灵内部,建立自己独立的自由王国;或者就不得不冲破樊笼,争取自由。”[12]流亡西方的俄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在1930年代就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艺术越是受到控制,越是自我限制,越是深思熟虑,就越是自由的”[13],言下之意,他是否是在结合自己以及同时代苏联音乐家的创作境况,从而数落自己国家音乐界的庸俗政治化倾向呢?无论是欧洲历史上宗教统治时期音乐艺术的大繁荣,斯大林时代苏联文学艺术的盛极一时,还是我国近代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文学艺术的绝境逢生,都能印证这一客观现象,对自由的压制往往令艺术家产生对自由强烈渴望的巨大创造力,从而诞生不朽的艺术精品。
结 语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使得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使得社会主义中国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都受到其深刻影响,进一步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理论,深刻影响新中国的社会音乐发展。然而,1950年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高度模仿苏联社会,但不同的国情、民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与苏联完全一致的发展道路,丰子恺论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也并非意在中国倡导完全一致的苏联音乐模式,更不是希望复制苏联的集权社会制度,虽然说严酷的社会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艺术家强烈的创作欲望,但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我”,“苏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包括音乐)等各方面有过特殊的影响,因此,研究苏联音乐的历程、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来说,就有着特殊意义”[14]。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对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要科学借鉴国外音乐艺术的优秀部分,海纳百川,从而融合于中华民族音乐艺术奔腾不息的发展洪流之中,丰子恺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其愿望显然是想借鉴苏联音乐的成功经验,在发扬我国优秀民族音乐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新的人民音乐。
[1](苏)高罗金斯基.苏联音乐青年[M].丰子恺,译,上海:上海万叶书店,1953.
[2]丰子恺.苏联的音乐[J].进步青年,1951(233).
[3]居其宏.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乐坛的莺声初啼[J].音乐研究,2016(6).
[4]杨肖.艺术为“方便”,绘画为新民——论20世纪20至40年代丰子恺具佛教意味的漫画[J].文艺研究,2014(2).
[5]丰子恺.子恺谈艺,下[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6]项阳.黎锦晖:时代弄潮与世纪悲情[J].中国音乐,2007(4).
[7]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M].哈尔滨:哈尔滨光华书店,1949:7.
[8]冯长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音乐思潮[J].音乐研究,2016(6).
[9]刘建东.丰子恺的音乐功能观[J].嘉兴学院学报,2010(2).
[10](苏)摩伊孙可.社会主义哲学对音乐的影响[J]. 丰子恺,译,人民音乐,1951(5).
[11]钱丽娟.宽容的主流——中国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9.
[12]毛宇宽.苏联音乐的历史启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3).
[13](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M]. 姜蕾,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9.
[14]蔡良玉.西方国别音乐史的又一新开拓——读黄晓和著《苏联音乐史》[J].人民音乐,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