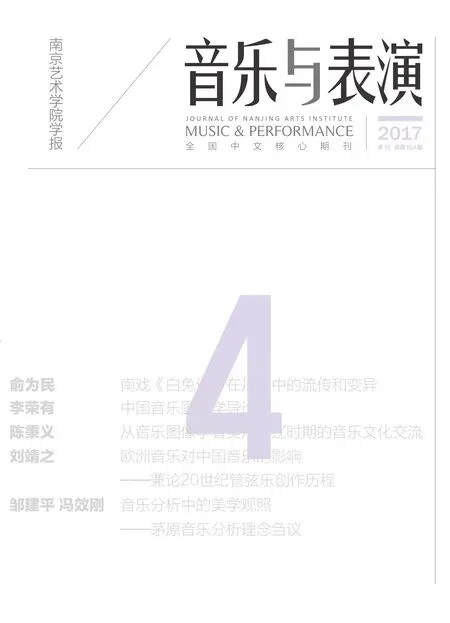音乐分析中的美学观照
—— 茅原音乐分析理念刍议
2017-03-07邹建平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邹建平(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冯效刚(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茅原教授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音乐理论家之一,他从1956年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学习,期间随姚锦新教授系统学习了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他一生在诸多领域奉献了卓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作品分析是其中重要的领域之一,展现了他独特的研究风格和音乐分析理念。虽其代表作《曲式与作品分析》[1]是本科教材,然而他的思考是建立在对音乐本质规律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茅原教授对音乐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认知呢?笔者认为,探寻茅原教授的音乐分析理念需要结合他对音乐美学的文章来解读。
一、对音乐内容与形式的阐析
与国内同类音乐作品分析教材相比较,茅原教授的不同理念在于,将音乐的技术分析与美学分析有机结合。他在“教材”的《绪言》中写道:“作品分析是把乐曲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一门课程,必须处理好技术分析与美学分析的关系。”“技术分析”包括曲式、和声、复调、配器等,“美学分析,指的是把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统一起来进行的分析。这涉及音乐与生活,社会、人生的关系、音乐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观念”。“二者的关系是,美学分析指导技术分析,技术分析支持美学分析。”他强调技术分析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技术与“一定的内容存在着有机联系”,提出,单纯的技术分析如果“不上升到美学高度”,很难如实反映作品的真实内涵。[1]1
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艺术研究领域常议常新的话题,特别是对于内容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一直存在着争议。
(一)音乐内容
由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音乐能否客观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历来是争执的焦点之一。的确,音乐与其它艺术(特别是绘画、戏剧与影视等)相比,其反映客观现实的手段非常有限,并且往往“是主观化了的,是通过人的精神面貌反映出来的”[2]40。所以许多人认为,音乐的内容主要是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早在1983年,茅原教授通过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解读后认为,音乐内容“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精神状态反映出来的”。他曾撰文提出:
承认音乐是一种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承认音乐也是一种人化的自然,那么,把音乐的内容理解为在音乐中反映出来的现实的人的精神状态(面貌),可能是比较恰当的。[2]40
既然如此,音乐内容在作品中是如何显现出来的呢?茅原教授结合具体分析,将作品中的音乐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作品具有反映的是什么对象、反映的是什么思想、感情、精神气质等多方面的特征。第二类作品仅只具有感情、情绪和精神气质的特征。第三类作品连情绪特征也很难说,只有一种精神气质特征。[3]110
如:贝多芬《第三》和《第五》、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李斯特《b小调钢琴奏鸣曲》以及《二泉映月》,在“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方面凸显出作曲家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属于第一类作品;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仅仅反映出他那“优柔寡断的气质”,属于第二类作品;而“从《平湖秋月》《寄生草》这样的音乐作品中”,我们恐怕“只能感受到一种平静、柔和、优美、温文尔雅的精神气质”了。[2]40-41
事实上,人们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往往能够感受到作曲家千差万别的性格和气质,这说明音乐作品存在共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存在着内容的个性特征”[2]41。那么,音乐内容具有普遍性吗?如果这种普遍性存在,其规律是什么?反之,人们又是如何从千差万别的“个性特征”中感受到相同(或相似)的音乐内容呢?也就是说,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作曲家的个性是如何融入共性中,他是如何表现出符合规律性的音乐内容的呢?
茅原认为:“没有内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没有形式的内容也是不存在的”。音乐本身就有其“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感情、艺术家的个人艺术气质,属于内容的范畴”[3]111,而音乐形式本身,存在着不同的规律。
(二)音乐形式
茅原教授从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观念出发,对音乐形式美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音乐“具体的形式律”,阐述了“整齐一律、平衡对比、符合规律、和谐”等在音乐“作品结构中的表现形态”。他认为:
“整齐一律”体现在音乐作品“节拍的规范化”、“乐段(或初级复合单位)”的结构上,主要表现在“服从于统一乐思的表现手段”相对统一。
“平衡对称”有三种形态,第一种是“为反映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或一对形象或两组形象服务的”“对比并置曲式原则”,如“乐段、单二、三部曲式,复二、三部曲式”等;第二种是“为反映一系列不同的生活面服务的”“组曲原则”,各结构之间在对比中形成一定的“呼应关系”,从而“构成平衡感”;第二种是“回旋原则”,尽管非中心段落的每一部分之间形成对比,同时“又与中心段落构成主要对比”,但这是为了反映“一系列不同的生活面”中“有一个主要的中心”,被隔开段落之间的平衡由中心段落来实现,仍有“隔段平衡的趋向”,“体现了对立面的交替”,这种结构特征服从于“对立形象”“交替运动”的内容。
“符合规律”体现了对立面的并存,表现为变奏原则,“是为反映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服务的”。其中,或旋律保持一致,而节奏各异;或旋律、节奏都一致,而和声、织体各异;……总之,“与事物发展不同阶段之间内容上的相互关系是一致的”。
“和谐”“是为反映对立统一的复杂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服务的”,“奏鸣原则”中集中体现了相同与相异的互相渗透,其结构图式①茅原说:“A代表主部主题,B代表副部主题,T表示主调性,D代表副调性,T D表示在矛盾中呈示,T T1表示在统一中得到归宿,中间则是展开阶段,呈示部与发展部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展部与再现部以至呈示部与再现部之间亦复如此,这里与变奏的区别就在于,相同面和相异性不再十分清楚地加以区别,虽然二者都存在,却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甚至某些作品,主部副部之间也互相渗透。”(茅原.人化的自然和音乐的耳朵——《巴黎手稿》与音乐美学[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3,(03):42.)为:

茅原认为,形式律是古典美学家对所处时代音乐创作实践富有指导意义的总结,但是,“所有的形式律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完全符合形式律,比如最平衡对称的音乐反而是不美的?”他根据马克思“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全集42卷129页)解释了这一疑问:“要真正实现形式美,不仅仅是要借鉴形式律(前人的经验),而且要体现创造性!”音乐家的“智慧、才能、技术、深入认识对象的程度、自由自觉的创造能力和在劳动上花的功夫不同”,产生出的结果大相径庭:“包括好的演唱演奏的声音素质,也是在正确指导下经过一定积累而获得的训练成果”;并且提出:“历史既然还在发展,人们就会去创造更新的形式律”[2]42-43的观点。由此出发,茅原教授进入了音乐语言的解析中。
二、对音乐语言的解析
茅原教授首先提出,音乐语言是一个借用来的名词,其中既含有“语言”的本质属性,又必须考虑到音乐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他写道:
……斯大林把语言称为思维的形式。但是,从逻辑上来分析,形式是类概念,语言是低一级的、范围更小一些的种概念,语言与形式的关系类似于整体结构和局部材料的关系,或者说表现手段的体系和个别表现手段的关系。形式是由音乐语言的体系构成的,二者相互联系,却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2]41
茅原教授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4]129,并进一步解析道:
音乐语言这个借用意义上的语言,也是人类交流认识的信息,与本来意义上的语言的区别,就在于音乐的信息是一种抽象的具象。……所谓“抽象”就是抓住主要特征,舍弃次要特征,所作的概括。[2]41
茅原教授通过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举“鱼的形象的例子”,解析了艺术抽象的过程,并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主题旋律的产生为例,解析了作曲家音乐创作中进行艺术抽象的过程。越剧中不论是对“贤妹妹”“充满深情的呼唤”,还是用“叫头”喊“贤妹”都还不是音乐,只有当“我想你,哪天不想你到天明”(谱例略)的唱段出现时才具有音乐的属性。然而,此时作曲家还要舍弃歌词(次要属性),深化感情,从而产生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的爱情主题(谱例略)。当然,在这个主题中,已听不到贤妹妹了,可是它抓住了思念贤妹的情绪,进一步作了发挥,它的具象也抽象化了。[2]41
这段旋律更为深刻而充分地揭示出深深的思念之情。由此了解符合实际的“音乐语言”产生的特殊规律,从而揭示了音乐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本质属性:在音乐艺术中,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同时,形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把音乐语言界定为基本(或局部)的某一方面的表现手段;把音乐形式界定为整体的表现手段。
虽然我们从以上解析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茅原教授缜密的逻辑性以及入木三分的音乐分析功力。但他并未就此止步,提出了音乐语言与“生活音调”的关系问题。他以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精神反思了自己以前观念的局限:
我曾长期相信和宣传过一种理论:生活音调;进入音乐逻辑,形成音乐音调。这种理论,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有许多问题,它不能自圆其说。
随后,他的一系列追问发人深省:
……生活音调难道不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吗?难道不是第二性的吗?它能与现实生活等同起来吗?如果说生活音调与音乐音调都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只是在不同范畴内以不同方式作出的反映,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需重新加以研究。音乐音调的根据就应当到人的思想感情中去寻找,而人的思想感情的根据则应该到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2]42
接着,茅原教授继续问道:
为什么生活音调的变化在历史发展中相对缓慢,而音乐音调的变化却相对迅速得多呢?人类的哭声和笑声几百年之内,能有多大变化呢?音乐上却早已千变万化了,这难道只是作曲家主观加工的差异引起的吗?这主观加工的差异又是如何引起的呢?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现出他对马克思哲学精要的理解,凸显出新中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求实精神。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社会现实和音乐文化”的关系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随时向社会吸取什么,又给予社会什么”?毋庸置疑,“物质与精神”“社会和音乐”的发展是各自独立的,如此,两条线索在发展中之间互相发生反馈吗?事实证明,“音乐传统中隐伏着无数的生活与音乐之间的中间环节,它们对音乐创作所起的作用必须给予重视。”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
是否任何音乐必须从对生活音调的加工开始呢?为什么许多音乐是找不到它的生活音调的呢?如果不能直接找到生活音调,是否音乐就不反映现实了呢?是否音乐就纯粹由作曲家的主观噫造而产生,就不受物质制约精神这一规律的支配了呢?
茅原教授从马克思“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4]129出发,阐述了“人的感情和整个内心世界,都存在着运动的特性”这一基本规律。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乐音运动与人“心理(主要是感情)”运动的相似性方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音乐不是生活音调的反映,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自然)的心理运动的反映。
然而,“在音乐作品中,有时确实有明显的生活音调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茅原教授认为:“能够反映人的心理状态的生活音调,是一种现实生活之中的反映形态,音乐音调则是艺术中的人的心理状态的反映形态,因而,二者能互为参考系或参照系 (参照架 )。”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作品都必须处处以生活音调”为参照,“即使在以具体生活音调作为参照系的情况下”,还有作曲家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参与其中,不仅仅是“去粗取精”,而且“带有作者的理解(理智因素的表现)和爱憎(感情因素的表现)”;“在这个抽象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音乐传统中不知多少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就是说,在前人所作抽象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音乐作品中到处找到生活音调的痕迹,即使发现了这类痕迹,它们也是随着社会生活和音乐传统的发展和个人独创性的贡献而采取千姿百态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直接地反映人(自然的一部分),还是以生活音调为参照系来反映人的心理状态,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即音乐语言,总归是人化的自然,即经去人的主观过滤所反映的自然的映象。”
正是因为音乐创作中存在着抽象的过程,因而
“无论就音乐与心理,音乐与传统,音乐与生活音调各方面的关系来说”,在具体加工(抓住本质特征而扬弃许多次要属性)的过程中展现出各种可能性,“这也就给音乐的概括性、具体性、确定性、不确定性等问题提出了研究课题。”[2]42
三、论音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由此,他展开了对音乐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分析。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茅原教授从更为广阔的视野谈到艺术的普遍规律。他首先解析了拉波泡泡尔特对艺术内容①茅原说:“在1987年出版的《音乐美学原理》(杨洸译)中,拉波泡泡尔特把艺术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实物方面,二、感情方面,三、思想方面。”([1],第111页)的看法,认为:
他的第一方面大体相当于我所说的第一方面,他的第二、三方面相当于我所说的第二方面。他没提到的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方面——艺术家的个人艺术气质。至于有的作品三个层次都反映得比较明显,有的作品只反映到一、两个层次,那是具体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的差别。[2]111
进而,茅原分析了斯坦尼戏剧理论“角色中的自我和自我中的角色”以及我国戏曲艺术中“我演我、我亦非我。演非我,非我有我”两种说法,提出“演员是第一自我,角色是第二自我”,表演中“深入角色、深入环境”是一个演员必须要达到的“无我”境地;然而,如果沉入角色之中不能自拔,必然无法控制自己,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其“创造者的才能”,演员要控制自己,时刻保持“有我”的清醒状态;“破坏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则不能很好地“反映对象”,就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艾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某些看法上是相当接近的”:
进入角色,出不来,心理距离就太近了;根本不能进入角色,心理距离就太远了。两种情况,都是偏颇。朱光潜先生说:“艺术的理想是距离近而却不至于消灭”。我以为,是有道理的,这正是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之间应当保持的心理距离。
茅原教授从作曲、演唱和欣赏三个方面分析道:作曲家在创作中如果“一味感情倾泻,不能控制自己……可能是高潮基础上再加高潮,十个八度的音域也不够用,结构也会散乱无章,飞翔无度,难于成功。”反之,如果作曲家十分冷静,往往容易“不动感情”,虽然 “结构处理可能有条有理,音乐却不感动人”。“要使二者有机统一,应当在深入环境的同时,保持一定心理距离,角色中有自我,自我中有角色,在体脸中,充分施展表现的才能。”演唱者也是一样,“情绪高度激动,失去控制,荒腔走板”在所难免,假如“丝毫无动于衷,可能音色纯正,板眼准确”,但常常会“不感动人”。“欣赏也是如此,忘记了是在欣赏艺术,才会发生观众向演员砸石头的事,心理距离太近了;反之,过于冷眼旁观,根本不为艺术所吸引,心理距离太远了,也得不到美感享受。”[2]42-43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心理距离:“心理距离太近了,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心理距离太远了”,“冷若冰霜,根本不能深入环境”,同样也会失败。他以著名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1953年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期间介绍演唱《刘巧团园》经验时的一个细节为例来说明,“忠实于反映客体对象和表现主体创造才能的有机统一,是艺术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
刘巧听说她将要被迫嫁给包办婚姻所指定的从未见过面的男人时(她不知道这正是她自由恋爱选择的那个对象),十分伤心,连唱了多少“直哭得……”,达到高潮时,是“直哭得……鸟无声”。他解释说(大意):为什么伴奏突然强奏呢?因为演员哭了很长时间了,听众已经很难过了,再哭下去,就不再有艺术效果了。他用三弦唤醒听众:“你是在听说书呢!”听众松一口气,再听下去,才能继续接受演员的表演。可见,他在深入角色同时,始终控制着自己,这难道不正符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要求吗?[2]43
以上所有论述都给我们指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面对着同样的客体对象,艺术家高于平庸的艺术工作者之处,难道不就在于艺术家本身的素养和才能吗?”[2]44
由此可见,在茅原教授看来,音乐内容、音乐语言、音乐形式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他说,黑格尔称方法为“形式的一般者”,认为方法同样是手段,那么,音乐手段中就包含着音乐语言和形式。然而,作为“个别的、局部的、某一方面”表现手段的音乐语言和作为“作品整体结构”表现手段的音乐形式是什么关系呢?
音乐语言与音乐形式的关系,好比建筑材料与建筑物整体结构的关系。音乐语言比如钢骨水泥等建筑材料,当它们被组建成长江大桥时,就发生了一次飞跃,我们就不再把这一建筑物的整体叫做钢骨水泥,而叫做长江大桥了。[3]110
在此基础上,茅原教授又提出音乐内容与形式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有人说,音乐中的“内容和形式可以相分离”[5],并以黑格尔的话“形式就是内容”和“同一个东西即内容,作为发展了的形式”为据。不错,这两句话都是黑格尔说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黑格尔的语言是否准确?二是拥护这说法的人在观点上是否与黑格尔真正一致?”黑格尔还说过:“因为形式在这种同一性中,它就被当作本质性的持存,所以,形式就是内容”。
首先,黑格尔在这里并不是谈“音乐的特殊性”问题;其次,黑格尔说:“辩证法永远把同一的东西与差别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有限的东西与无限的东西、灵魂与肉体分离和区别开来”。“而一旦分离,就成了两个东西了”。黑格尔“永远把矛盾双方分离和区别开来”。[3]110也就是说,黑格尔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处于统一体中,形式是“内容得以保持和存在的物质载体”,并没有当作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全部结论。可见,就此认为内容和形式可以分离是“形而上学”的结论。但是,“为什么这个人、这一次写出来的音乐非常美,而另一个人、另一次写出来的音乐就不美呢?”关于这个问题,茅原先生认为,这是“音乐在差异中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差异中存在着同一性”[3]110也是客观事实,我们需要探寻的正是这种“同一性”符合实际的存在方式。正如茅原先生借维特根斯坦所说,这是“部分相似和一种交叉相似的网状形态”。音乐作品大致处于这一范围内,就是同一个东西,内容和形式就没有分离[3]110。
由此可见,茅原教授的音乐分析理念是建立在作曲技术和美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综合性分析。
……美学分析如脱离了具体音乐现象,就很难说是有根据的分析,美学分析需要技术分析提供的数据。……在这一点上,正是技术分析证实了美学分析。[1]1
目前,茅原教授的这本教材还没有在专业音乐院校被普遍使用,“对于学习音乐的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音乐作品分析是一门关系到他能否真正懂得音乐的基础课。学音乐就必须懂得前人的艺术创造,才谈得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音乐专业的学生增强技术修养固然重要,但“一定的美学思想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1]1
[1]茅原.庄曜. 曲式与作品分析(上、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
[2]茅原.人化的自然和音乐的耳朵——《巴黎手稿》与音乐美学[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83,(03):38-45.
[3]茅原.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J].中国音乐学,1988,(04):110-11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
[5]王宁一.简论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兼对某些成说的质疑[J].中国音乐学,1986,(02):1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