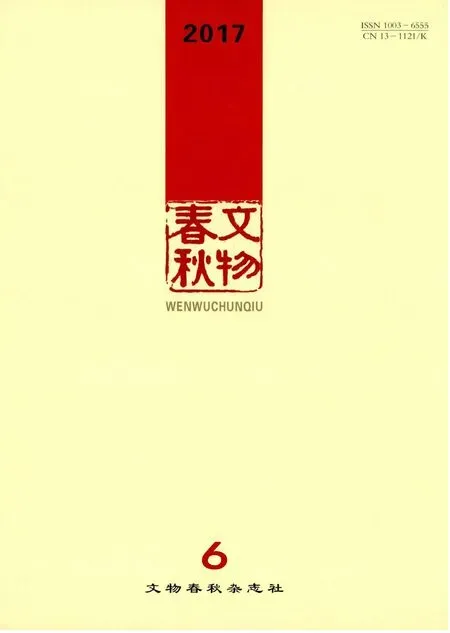“文化滞后”理论再商榷
2017-02-12尚友萍
尚友萍
(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河北 保定 071000)
近年考古学中有一种“文化滞后”的理论,称为“文化滞后性”,也称“文化滞后观”“文化滞后论”,其代表性的观点是这样表述的:
“无论是夏王朝抑或商王朝,在其肇建王朝之初的物质文化均保存着前一时期文化的面貌,而在考古学方面所反映的一个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只能是在新王朝建国之后又经过一段开创的时间才能成就的。结论是王朝建国之时在前,其所产生的新文化在后。”[1]
上面结论中的“其所产生的新文化”,指新王朝建国之后又经过一段开创的时间所产生的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当无疑义。我们将其简称为“王朝文化”,也应该没有疑义。所以,“文化滞后理论”又可以表述为“王朝文化滞后于王朝建立的理论”。本文标题之所以用“再商榷”,是因为笔者写过与“文化滞后理论”商榷的文章[2],故本文以“再商榷”名之。
“文化滞后”理论产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配合夏商文化分期的讨论提出的,最初只是为自己的分期方案寻找理论依据;后期则脱离了产生它的母体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理论,并被写进了培养考古专门人才的教科书中,从而在更大范围得到了传播。当然也不乏质疑者。我又一次拜读了双方的文章,有一些新体会,写下来向各位师长请教。
最早使用“文化滞后观”或“文化滞后论”称呼这一理论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程一凡先生[3]。在此声明。
一、新王朝的物质文化是新王朝建立的标志
文化滞后理论可以用一种更通俗的语言表述:社会变革或王朝更替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事,而建立与之匹配的王朝文化却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需要一个过程。——初看还真觉得有些道理,可联系考古材料的实际,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商汤在“三千诸侯大会”上就天子位以后,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重大建国举措,表现出一个开国君主的雄才大略。这些建国举措包括:郑州商城开始扩建[4],偃师商城开始兴建,同时大规模向外围尤其原夏朝的要地调派军队,建立军事据点。这些据点包括:山西垣曲商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河南焦作西南郊的府城商城、湖北盘龙城商城、关中地区的北村遗址等[5]。这些被派往四面八方的军事力量,既肩负着拱卫新生政权的职责,也负有开疆拓土的任务。这些建国举措是举全国之力的浩大工程,这个浩大工程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属于“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就像没有在实践中兑现的诺言只是空话一样,如果商汤只是在“三千诸侯大会”上举行了就天子位的仪式,而没有在实践中落实他的建国举措,商汤建国就是一句空话。在这里,新王朝的建立靠新王朝的物质文化来体现、证明,而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则依赖新王朝的建立而存在。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去掉其中一项,另一项就不复存在。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新王朝建立与其所产生的物质文化是如影随形般同时发生的。
让我们用商王朝初期的都城材料来考察“王朝的物质文化”与“王朝兴立”之间的关系。
前边说过,商汤就天子位后,便开始运作郑州商城扩建与偃师商城兴建的宏伟工程。目前我们所说的郑州商城的内城与外郭城均为商汤灭夏后扩建[4]。扩建后的郑州商城周长约6960米,城内总面积300余万平方米,内设宫殿区,这还不算更为庞大的外郭城。偃师商城由宫城、小城和大城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6]203—231。礼制在先秦时期是逐步完善的。在周代,城的大小已经有了明确规定:“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传·昭公十九年》)夏商时期的都城也必然有其相应的规制。考古材料证明,无论在郑州商城还是在偃师商城,一座座宫殿陆续建成,巍峨高耸;高大城墙龙盘虎踞,雄伟壮观!——所有这些,都是目前所发现的其他商城所无法比拟的。由此观之,这两座商城无论从规模大小还是功用性质看,自然已具备都城的条件。但考虑到建筑历史与规模大小之间的差异,它们应该是主都、辅都的关系。郑州商城的扩建与偃师商城的兴建都发生在商王朝建立初期,都是商王朝建立的标志性设施,都属于“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它们同样伴随着商王朝的建立如影随形地出现了!
让我们利用西周初年燕国的建国——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建国模式,来考察建国事件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国有42代燕侯,关于早期燕侯,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其中8世燕侯史料无载,燕国是否在西周初年建国成了历史之谜。这个谜是从考古学中的墓葬材料入手解开的。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2.5公里处,由城址和墓地两部分组成,其中墓葬材料十分丰富。墓地被现在的京广铁路分隔,铁路东侧既有大型燕侯墓,也有中小型墓,铁路西侧只有中小墓,为殷遗民墓。其中早期大墓M202和M1193最能说明问题。
据报道:“M202是墓地迄今所见的惟一的双墓道的大型墓。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南北长7.2米,东西宽5.2米,深7米。南墓道为斜坡,长14.8米,宽6米。北墓道为曲尺形台阶状,全长12米,有5级台阶。椁室长5.2米,宽2.3米,高1.7米。”发掘者的结论是:“此墓被盗掘一空,但按墓葬的规格推测,墓主人应是一位燕侯。”[7]
关于M1193,发掘者说:“在黄土坡发掘的墓葬已有多座,有的一条墓道,有的两条墓道,但像M1193带有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同时,就其规模来说,这也是迄今这里发现的最大的一座。从商代和西周发现的大型墓葬看,有墓道的墓,都是些贵族身份的人所用(近年在丰镐遗址中发掘的大墓,也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有四条墓道的,其墓主人的身份更高,属王侯一级人物使用。因此,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必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此墓虽经盗扰,仍出土两件重要的青铜礼器——克、克,器盖有“令克侯于”的珍贵铭文。墓中还出有“成周”铭文的戈以及有“燕侯舞”“燕侯舞”的铜泡,研究结果是:铜器铭文与文献中召公封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的记载相合,“进一步确认此处为周初所分封的燕,克为第一代燕侯”[6]78—85,[8]。
历史资料所云周初所封燕国是真实存在的,周初第一代燕侯名克,也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所有这些结论都是用考古资料证实的。发掘者根据琉璃河大墓的规格与城墙的同时存在,确认了琉璃河遗址为燕国早期都城的性质。
燕国是殖民国家。第一代燕侯克带领殷遗民若干族,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琉璃河一带,其首要任务自然是“安营扎寨”。琉璃河遗址就是燕侯克最初建国时的“寨”,亦即燕国早期都城。最初的燕国还谈不上领土,因为燕国的领土是以琉璃河遗址为中心逐步向四围扩张的。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毫不犹豫地说燕国已经建立,而证明燕国建立的证据主要是以墓葬与城墙为主体的考古材料。这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有所不同,——证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都城性质,依据的主要是宫殿与城墙。由于考古遗存或深埋于地下,或遭风雨剥蚀、地壳变迁,或遭人为破坏,所以它的出土一般都存在或然性。也就是说,有些我们需要的材料或许找不到,但这并不影响“王朝建国必然产生与它相应的物质文化”这个判断的成立。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证明王朝建国的考古材料并不是日用陶器。
日用陶器虽然不能用来证明“王朝建国”,但日用陶器却是建立考古学文化内部联系并进而判定其年代不可或缺的证据材料。从出土的陶片看,琉璃河遗址存在三种文化因素:姬周文化类型、殷商文化类型、土著的张家园上层类型。我们利用类型学的办法,分别将其中的两种外来遗存与周族、商族的同类陶器比较,自然就能从它们在各自文化系列中所处位置判断出琉璃河遗址的时代。
考古学所说的文化遗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遗迹,包括居址、墓葬和窑址等;二是文化遗物,包括陶器、青铜器与石器、骨角器等。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是由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的。胡谦盈先生针对前者说:“一种考古学文化是由居址及年代相应的茔地中的墓葬两类不同遗存资料构成的,如果缺少其中一种资料,遗存的文化面貌就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具有典型性和标尺性的作用及学术价值。”[9]这就是说,一个可靠结论的得出,必然是在各种材料的联系中综合考查的结果。对比各种考古材料,如果说“陶器最富于时代特征”,其实青铜器同样富于时代特征,包括居址和墓葬在内的文化遗迹就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目前考古学界在论证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及文化性质时,往往只重视陶器尤其是日用陶器,连青铜器都很少提及,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陶器毕竟只是考古文化遗存的一个门类,是整个文化遗存的组成部分,它不可能反映一个事物的全部面貌。除了陶礼器之外,低规格的普通陶器本不属于“新王朝”建立后“新出现”的物质文化,让它去代表“新王朝的物质文化”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考古学家在论证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时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更值得重视的是出土了青铜武器、工具、牌饰和一批我国最早的青铜容器(爵、鼎)。铜器与玉器、漆器及某些陶器配组成反映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群。凡此,都展示出二里头遗址恢宏的王都气势和独特的文化面貌。”[10]由此可以看到,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由“反映贵族等级身份的礼器群”证明的,不是用普通的生活陶器证明的。
文化具有传承性,一个时代的文化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以筷子打比方吧,《史记·宋微子世家》有“纣始为象箸”的记载,箸的实物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出土,说明筷子的出现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筷子本身对于朝代的兴亡确实不能说明什么,但你不能因为新王朝仍在使用筷子,就说属于新王朝的物质文化没有出现。也就是说,不能以筷子这个从前朝传下来的“物质文化”的存在,来证明新王朝本身的物质文化“滞后”。商王朝建立之初,商汤臣民中的商族人煮饭、吃饭使用的仍然是下七垣文化时期传下来的陶器,新归顺的夏遗民使用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传下来的陶器,但他们的工作却是筑城、筑宫殿,从事着建设“新王朝物质文化”的事业。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正是凭着这些并不代表“新王朝文化”的普通陶片,确认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建立的时间。文化滞后论只看见了商汤臣民手中的旧饭碗,而没有看见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否有点以偏概全呢!再说,那些参与筑城的商族臣民手中的饭碗已经属于二里岗类型商文化,而不再属于下七垣文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商族人由漳河型先商文化南渡黄河来到豫东发展为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然后西进郑州发展为先商至早商的二里岗类型商文化,也是在“与时俱进”,又何来“滞后”之说!
新王朝的建立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物质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的结论。
二、商汤建国于二里岗下层C1H17开始阶段
“以郑州二里岗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商文化”,即被文化滞后论认定为“王朝建国之时在前,其所产生的新文化在后”的商王朝的新文化。
文化滞后论这个所谓的“早商文化”,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早商文化概念不同,——它与早商历史并不同步。在文化滞后论的体系中,“早商文化”并不出现在商朝历史的早期,因为它的形成要“滞后于王朝的建立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
文化滞后论认为,在夏商交替时期的郑洛地区存在着五种面貌独特的文化遗存,它们分别是: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洛达庙三期遗存、南关外期遗存、郑州化工三厂遗存、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等。认为这五种遗存都能分析出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于是统称其为“过渡期文化”。并认为其内部的多种文化因素需要经过“整合”,才能过渡到“以郑州二里岗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商文化”。在他们那里,过渡期文化属于“过渡性质的遗存”,即性质未显现的文化,只有在它们过渡到“以郑州二里岗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商文化”时,才是“成熟”的早商文化。在文化滞后的理论体系中,从先商文化到早商文化过渡的历程是这样的:下七垣文化→过渡期文化→早商文化。
按照这样的观点推论,其结果是:商汤建国事件发生前后的文化背景,是“过渡期文化”并存的“战国”时代;其时,“以二里岗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商文化”还孕育在“过渡期文化”的茧蛹中,而未完成蛹化蝶的蜕变。
商汤立国时的文化背景果真如此吗?要讨论商汤立国时的文化背景,首先需要确定商王朝立国的时间。
古文献对商汤建国有明确记载,据《逸周书·殷祝解》:“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座右。汤退,再拜,从诸侯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汤“复薄”之“薄”(亳),自然是郑州之亳,因为偃师商城此时还没有动工兴建。由此可知,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的大本营与根据地。商汤在郑州商城即天子位,使得郑州之亳在一夜之间由先商都城跃升为早商都城,商王朝的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早商文化的历史也由此开始计算。只可惜《逸周书》没有记下汤即天子位的具体时间,再加上这件事在郑州的文化遗存中没有留下直接证据,所以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距离商汤建国时间最近的事件做参照物。这个参照物我们选定二里头夏都被商族人攻占,因为商汤复亳就天子位必定在二里头夏都被攻占以后,而且二者相隔的时间不会太久。
岳洪彬先生首次指出二里头原四期文化偏早偏晚两个时期“有着质的区别”,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偏早时期及其以前的二里头文化为同一文化体系,可能是夏人的遗存,而偏晚时期已进入商代。”[11]这个结论把二里头四期偏晚时期排除在夏文化系统之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属于夏遗民文化,已经不是夏文化在“主流”状态下自身的延续,而是变成了附属于商文化的支流。
岳先生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商族人来到二里头遗址的时间发生在二里头文化四期,而不是在这个阶段结束以后。这就是说,在二里头遗址夏商易手的时间发生在二里头四期文化早晚阶段之间。但是,我们能否以二里头遗址发生夏商易手的时间——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作为夏商分界的时间呢?不能。因为二里头四期早晚段之间只是一个相对时间,而不是绝对时间。
讨论夏商分界可利用的考古材料,除二里头遗址外,还有荥阳市大师姑遗址[12]和薛村遗址[13]。笔者在解读大师姑遗址考古材料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人是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时来到大师姑,而且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才使二里头四期文化进入偏晚阶段的。”[4]它的立论基础是: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与最早来到大师姑的商文化是重叠的,并不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商族人攻占大师姑以后,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两种文化前后相继的局面,即夏族人被全部杀死或全部离开,唯有商族人单独留在该遗址。反之,只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同时在大师姑遗址存在,反映在文化关系上就必然是夏商两族文化重叠。薛村遗址与二里头遗址在夏商易手以后的文化关系,也应作如是观。
首先需要确定这样一个前提:这三个遗址不可能同时被商族人攻占。大师姑遗址东南距郑州20余公里,西距二里头70余公里。薛村遗址东南距郑州约40公里,西距二里头约50公里。郑州与二里头之间的距离是85公里。三个遗址夏商易手的时间都发生在二里头四期文化早晚段之间,但三者不可能同时被攻占,自然有先后之别。按照商族人从东到西的进军路线,商族人首先攻占的应该是大师姑遗址,薛村遗址次之,最后是二里头遗址。从三个遗址现存最早的商文化看,大师姑遗址是以H55为代表的相当于二里岗下层C1H9阶段的“早商文化一期”[12]。——这个时间自然就是大师姑被攻占的时间。薛村遗址存在由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上层的连续文化。该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形态分别是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阶段、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商文化分别是:二里岗下层一期、二里岗下层二期、二里岗上层一期。其最早的商文化,报告说:“考虑到ⅡT1314M29∶1鬲的沿面前端已比较平,整体呈梯形,口部形态介于郑州二里岗遗址C1H9∶36和 C1H17∶118之间,可将ⅡT1314M29的年代定在二里岗下层一期。”[13]按照邹衡先生的商文化“三期七段14组”[14]的分期框架,郑州二里岗遗址C1H9属于先商文化最晚一组,C1H17则是早商文化最早的一组。因此,虽然发掘者将遗址最早的商文化“年代定在二里岗下层一期”,但由于其形态“介于郑州二里岗遗址C1H9∶36和C1H17∶118之间”,可知薛村遗址被商族人攻占的时间要晚于大师姑遗址,更接近C1H17所代表的时间,也就是先商文化向早商文化过渡时期。
关于二里头遗址中最早的商文化,引起人们关注的典型单位是1981年在Ⅲ区发掘的一座属于四期偏晚阶段的灰坑H23[15]。此灰坑出土的陶器很明显地分为两组,一组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物,另一组具有鲜明的商文化特征。岳洪彬针对后者说:“这组器物在已确认是商文化的偃师商城一期早段遗存、郑州商城宫殿区内所发掘的最早的商文化遗存中很容易找到其‘孪生兄弟’。”[11]这就是说,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四期晚段的商文化,与偃师商城一期早段遗存,以及郑州商城宫殿区内所发掘的最早的商文化遗存,在文化形态上是相同的,都属于二里岗类型商文化。对于二里头遗址上的商文化来说,由于商汤攻占二里头夏都是大师姑战役与薛村战役的继续,二里头遗址的商文化与大师姑及薛村遗址的商文化形态相同,都属于二里岗类型商文化,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二里头夏都被攻占的时间应该晚于大师姑与薛村遗址,更接近二里岗C1H17所代表的时间,也就是说,更接近商汤建国即早商文化开始的时间了。
在商族人征服夏族人以前,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是分属两个民族的文化。随着大师姑、薛村、二里头三个遗址先后被商族人攻占,或者说随着夏族人被征服,作为夏遗民的二里头文化也就失去了作为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从此融入商文化并变成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二里头四期文化只包括过去所说的二里头四期早段,而不包括过去所说的二里头四期晚段,因为二里头四期晚段已经是夏遗民文化。从二里头四期晚段开始,二里头文化是作为另一种生存状态——商文化的附属状态存在并延续的。所以说,夏商文化交替时间发生在二里头四期文化早晚段之间。
需要强调的是,大师姑、薛村以及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四期晚段还只是被商族人占领,但没有进入商纪年,因为商汤还没有在“三千诸侯大会”上就天子位。此时,属于夏遗民的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所对应的商文化是先商文化,处于二里岗C1H9向二里岗C1H17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生夏商王朝的交替。所以说,二里头四期早晚段之间是夏商文化的交替时间,而不是夏商王朝的交替时间。夏商文化交替时间与夏商王朝交替时间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说二里头四期早晚段之间是夏商文化的交替时间,那么,夏商王朝交替时间只能确定在郑州二里岗商文化C1H17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夏商王朝交替时间发生在二里岗下层早晚段之间。
夏商文化交替时间发生在二里头四期早晚段之间,夏商王朝交替时间发生在二里岗下层早晚段之间。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结论:
第一,商汤建国以前,大师姑夏城、薛村遗址以及二里头夏都遗址,其中的商文化因素已经是二里岗类型商文化。
第二,大师姑夏城、薛村以及二里头遗址被商汤攻取的时间发生在商朝建国以前,具体时间在二里岗下层C1H9向二里岗下层C1H17过渡时期,即先商文化向早商文化过渡时期。说明二里岗下层C1H9遗存属于先商文化,是商汤来到郑州地区最早的商文化。同时说明二里岗类型早商文化直接由二里岗类型先商文化过渡而来。
总之,文化滞后论关于“以郑州二里岗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商文化”,它的形成要经过所谓“过渡期文化”的“整合”,从而“滞后于王朝的建立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的判定,在这里被证伪。
三、遗民及遗民文化的历史命运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商王朝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周王朝的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16]。这两个年份当然也是新旧王朝的更替时间。
王朝更替以后,被灭之国的国民自然也就成了遗民。这些遗民的历史命运如何呢?文化滞后论认为这些遗民与主流族群融合成了“非此非彼的族群”,那时,“全体国人都已经是同一种文化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在王朝更替以后,新王朝对前一个王朝的文化采取的做法基本有两种:一是因袭继承,二是允许存在,但处于弱势状态下的遗民文化会被同化。赵芝荃先生曾经从陶器、青铜器、宫殿建筑、墓葬诸方面,论述了商王朝对夏王朝文化的承袭。以青铜器为例,赵芝荃说:“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是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展而来,二者在器类、形态、花纹、铸造与合金成分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17]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日本学者饭岛武次研究,“二里岗下层的殷王朝青铜器,极有可能是夏王朝的青铜器工匠被迁徙到殷都,在那里铸造了这些青铜器”[18]。正因为商王朝全盘接受了前朝工匠,从而因袭继承了前朝的文化。第二种类型,即允许遗民文化在新王朝存在。李维明先生在分析“白家庄期商文化”的文化因素构成时,肯定其主体“渊源于二里岗上层文化”,同时指出,“在其文化因素构成中有两种因素引入注目,一种是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因素),表明夏文化影响之久远。另一种是岳石文化因素”[19]。其中的岳石文化因素的来源,可以从商王仲丁至河甲“征蓝夷”寻找答案,但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只能前推至商汤灭夏事件。也就是说,白家庄期商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伴随商文化已经存在百余年之久了。再如西周燕国的殷遗民文化,存在时间更为久远。据雷兴山先生对琉璃河遗址文化因素的研究,“早期的殷商文化因素与周文化因素的比例相若,并相互交融。在西周一代漫长的文化整合中,殷商文化因素逐渐占据优势,至西周晚期,燕文化竟发展成为殷遗民文化因素为主的状况”[20]。殷遗民文化在琉璃河遗址贯穿始终并在晚期一家独大,这与燕国迁都而姬姓王族迁出琉璃河遗址有关,正如任伟先生所说,“西周中期燕国可能已迁都于蓟”[21]。虽然如此,殷遗民文化的长期存在,总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任伟先生通过对琉璃河遗址墓葬群Ⅰ区(引者按:殷遗民墓葬区)和Ⅱ区(引者按:姬姓墓葬区)的分析比较,得出结论说:“首先Ⅰ区墓地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这说明虽然周人给予了殷遗民一些优待政策,但并没有让他们进入燕国的统治核心阶层,故也没有相应级别的大型墓葬出现。Ⅱ区的大型墓主要集中在该墓地的西南部。”他还将Ⅰ区与Ⅱ区的小型墓进行了比较:“Ⅰ区小型墓整体上看是不如Ⅱ区小型墓的。他们这一层次应是燕国的平民,部分随葬兵器的可能是燕国的士兵。虽同属平民阶层,然而殷遗平民的社会地位、富庶程度整体上还是要比周人差一些。”[21]另外,雷兴山先生还研究了洛阳、鲁国、卫国及关中等地殷商文化因素的变迁,其命运有与琉璃河遗址的殷遗民文化类同者,如卫国与成周之地的殷遗民文化,但大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殷遗民文化,逐渐被强大的周人文化融合了[20]。
以上事实证明,在一个新王朝内部,不但遗民阶层长期存在,遗民文化也曾经长期存在。
在中国早期国家时期,新王朝要分封前朝的王族为诸侯,以保留前朝族系的祖先祭祀。如周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史记·殷本纪》)。商灭夏后商汤也曾经封夏人于杞。商汤封夏人于杞事件,除古文献有相应记载外,我们还可以从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看出端倪。
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是所谓的五种“过渡期文化”中的一种。前面已经说过,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依附于商族人的夏遗民文化。大师姑夏城有这种遗存,薛村遗址有这种遗存,二里头夏都也有这种遗存。实际上,凡是在商汤建国前(先商时期)被商族人攻占的夏人遗址都有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文化滞后论所说的作为“过渡期文化”之一的“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特指二里头遗址上的同类遗存。
我们现在讨论“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的去向,也就是要讨论二里头夏都被商族人攻占以后夏遗民的结局。
岳洪彬先生将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的陶器按文化因素分为五组,主体是前面的三种:A组,是继承原二里头四期偏早时期的典型器类;B组,系成组出现的下七垣文化因素;C组,是源于岳石文化的因素[11]。这三组遗存按性质分为两类,B组、C组是征服者商夷联军的遗存,A组是被征服者夏人的遗存。
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因为当时夏商的军事较量已经结束,或者说胜负已见分晓,所以无论在大师姑遗址还是薛村以及二里头遗址,其中的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无论各占怎样的比例,商族人都是战胜的一方,夏族人都是战败的一方。二里头夏都被攻陷以后夏族人的命运如何,我们可以从古文献中找到依据。这就是“迁夏社”“屋夏社”和商汤封夏人于杞。——笔者对其所包含的本事已有专文讨论[22],兹不再赘。
新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二里头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晚段的遗存,表明聚落此时全面衰败、人员稀少”[23]。“二里岗下层晚段”是什么时候?当然是二里岗下层C1H17时期,亦即商汤建国后早商文化开始的时期。这说明“迁夏社”“屋夏社”以及商汤封夏人于杞的事件,均发生在“二里岗下层晚段”以前。也就是说,征服者对夏遗民的安置工作在商汤建国以前就已经处理完毕。二里头遗址是夏都,居住在二里头夏都的夏人是王族,他们战败后被商汤封于杞,从此离开了二里头遗址,负责处理夏王族事宜的商族人也相继离开,——这是二里头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晚段遗存”的事实真相。
就这样,夏王族带着他们的二里头文化离开了二里头遗址,商族人也离开了二里头遗址,——夏商文化并没有因发生碰撞而“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所谓“以二里岗下层C1H9为开端的早商文化”,是由“二里头四期晚段遗存”与下七垣文化及岳石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过渡而来[24]的判断,是一个假命题。
四、为“早商文化”概念正名
文化滞后论对于传统的“早商文化”概念的“改造”,也是值得商榷的。
“早商文化”概念的内涵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族别。其中的时间要素指的是商朝历史上的时间,而不是二里岗下层遗存的时间。后者的时间是用14C测出的,这个时间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示的是此种遗存存世的年数,并不表示它在商朝历史上所处的位置,甚至它的文化性质是否属于商文化,都不在它的内涵要素之中。但“先商文化”“早商文化”概念中的时间要素却与之不同。如果说后者的时间要素——单纯以数字表示的考古遗存的年代,还只是解决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关系的条件,那么“先商文化”“早商文化”概念中的时间要素“先”“早”,则是在解决了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表示考古学中的商文化某一阶段遗存与商朝历史的相互对应关系。具体说,其中的“先”“早”是“商”——以商部族为主体的商朝历史——的限制词,所以它对应的是商部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它对应的是商朝历史上的时间。“先商文化”一定发生在商部族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商文化”一定发生在商汤建国以后的早期,没有商量的余地。
早商文化概念内涵的另一个要素——族别,也被文化滞后论进行了改造。在他们看来,早商文化时期已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商族人以及依附于商族的夏遗民和其他族人的区别,而是混合成了统一的“非此非彼的族群”。
显然,文化滞后理论体系中的“早商文化”概念,只是借用传统概念的名称而置换了其内涵,属于和传统的早商文化概念无关的“山寨”概念。同时,由于他们以商文化属性是否“成熟”作为“早商文化”的判定标准,于是在他们的理论中出现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过渡期文化”阶段,并使它在商朝历史上占据了本应属于“早商文化”阶段所处的位置,于是早商文化阶段被挤到了过渡期文化的后面,从而造成了早商文化与早商历史在时间上的严重错位。不仅如此,由于他们重新定义了“早商文化”概念,连类而及,他们也只好重新定义“先商文化”概念。他们的“先商文化”概念的定义是:“所谓早于‘早商文化’的‘先商文化’,也应有一部分已延续于‘商汤灭夏’以后;所谓‘先商’并非先于‘商汤灭夏’,而是先于早商文化。”[25]这种远离传统概念本义的“山寨”概念的存在,无疑会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埋下混乱的种子。
商文化从先商到早商、中商以及晚商的各阶段,其内涵既存在传承上的联系而又互相区别,都是商文化在特定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说,商朝建立以后一定时段内商部族的文化——无所谓“成熟”与“不成熟”——就已经是“早商文化”了。就如同一个人从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已经属于“人”这个范畴,而不必等到他18岁成年后才承认他是“人”。
关于事物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曾这样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26]纵观商文化从先商到早商,再到中商、晚商发展的各阶段,都表现为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存在形式的否定。由此我们看到,各阶段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时空上的“先后”,而不是代表事物发展过程中断的“滞后”。文化滞后论在商汤建国前后的历史上插入一个所谓的“不是早商文化”的“五种过渡期文化”的做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既不符合商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1]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期文化[G]//赵芝荃.赵芝荃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38.
[2]尚友萍.关于王朝文化滞后于王朝建立理论的商榷[J].文物春秋,2011(1):3—12.
[3]程一凡.亳与偃师二遗址的关系[C]//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5—63.
[4]尚友萍.论夏末商初的“汤之亳”在郑州[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9):26—33.
[5]尚友萍.偃师商城一期一段的相对年代疑议[J].文物春秋,2009(1):9—14.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9—80.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
[9]胡谦盈.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28.
[10]高炜,杨锡璋,王巍,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J].考古,1998(10).
[11]岳洪彬.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相关遗存再认识[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38—256.
[12]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32—334.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 年度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7(3):3—21.
[14]邹衡.试论夏文化[G]//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06—117.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 1980—1981 年Ⅲ区发掘简报[J].考古,2000(7):582—590.
[1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M].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86—88.
[17]赵芝荃.探索夏文化三十年[G]//赵芝荃.赵芝荃考古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9—70.
[18]饭岛武次.二里头类型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都邑与文化:“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91.
[19]李维明.郑州二里岗下层与南关外中、下层文化遗存分析[G]//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26—227.
[20]雷兴山.试论西周燕文化中的殷遗民文化因素[G]//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51—253.
[21]任伟.从考古发现看西周燕国殷遗民之社会状况[G]//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56—262.
[22]尚友萍.“二里头四期为夏遗民文化”置疑[J].文物春秋,2007(5).
[23]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J].考古,2004(11).
[24]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J].考古,2009(12):47—55.
[25]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38.
[26]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