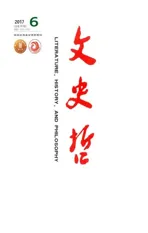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2017-02-07周炽成
周炽成
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周炽成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荀子;孟子;孟荀关系;汉唐
中国人性论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人们早已熟知,但“性朴论”确实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概念。本文拟以它为中心对从先秦到西汉的中国人性论史进行一些新的叙说,以冀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性论史进行新的认识。
一、孔荀均持性朴论
虽然性朴的思想早已存在,但“性朴论”作为一个专门概念被加以使用却比较晚。刘念亲曾在20世纪20年代质疑历史悠久的荀子主张人性恶之说,认为:在荀子看来,“性的本体的断案,只是‘本始材朴’四字”*刘念亲:《荀子人性的见解》,《晨报副刊》1923年1月18日。。他在研究荀子人性论时注意到了“朴”字,但并未使用“性朴论”一词。到了70年代,日本学者兒玉六郎则明确地以“性朴说”来概括荀子的人性论*[日]兒玉六郎著,刁小龙译:《论荀子性朴之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原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六集,1974年)。。在21世纪,更多学人开始以“性朴论”讲解荀子人性论*周炽成:《荀子韩非子的社会历史哲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周炽成:《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光明日报》2007年3月20日,第11版;周炽成:《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林桂榛:《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现代哲学》2012年第6期。。不过,总体上看,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认为,此一概念对于客观把握中国人性论发展史很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流传甚久的误解。
从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于以善恶论性。常见的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混善恶论、性无善无恶论等都含“善”字或“恶”字,而性朴论则不含这两个字。性朴论不以性本身的善恶问题作为争论焦点。事实上,最早说到人性的先秦哲人,也不都关注这一问题。孔子就是突出的例子,他的名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显然未对人性作善恶评判。这句语录所蕴含的性朴论信息,已久被埋没。当然,该名言中未出现“朴”字,至《荀子·礼论》“性者,本始材朴”*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6页。,则明确以“朴”说性。可以说,孔子的性朴论思想,被荀子继承了下来。

先秦性朴论的最鲜明代表是荀子。《荀子·礼论》有言: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366页。
这些话,很多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都注意到了,但是,罕见有人注意到它们与《荀子·性恶》以性为恶的说法之不同。极个别人看到两者的不同,但千方百计协调之。我们先细细弄清楚这些话的意思,再看学者们的协调何以不成立。
“性者,本始材朴”是性朴论的明确表达。从其本义来说,“朴”是指未加工的木材,意味着一种最初的、本然的、未受人为影响的状态。“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简朴与玉璞。一方面,简朴意味着素色、原初、可塑等。郝懿行在解释“性者,本始材朴”的时候说:“朴者素也,言性本质素。”*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366页。这样的解释很精当。因为人性简朴,后天的作用就得到凸显。性朴论非常重视后天人为的作用,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也是上引孔子的名言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未加工的木材类似于未加工的玉璞(玉石)。含玉的石头和不含玉的石头当然非常不同。正如玉石含玉质一样,天生人性已有不少潜质,包括善的潜质,这些潜质当然不是完备的、完成的、最后的状态。善的潜质不是完备的、现成的善,故性朴论不同于性善论。众所周知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亦可谓性朴论的名言,而不是性善论的名言。《楚辞·九章·怀沙》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性朴论: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王承略、李笑岩译注:《楚辞》,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这里的“材朴”与《荀子·礼论》之“材朴”文字上完全相同。不过,此处“材朴”不侧重“简朴”,而侧重“玉璞”。“文”是动词,“质”是宾语;“疏”是动词,“内”是宾语。故“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就是指,外在的东西掩盖了内在的“异采”。顺此意,不难理解“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就是指玉璞般的材朴或朴材堆在一边而不被人发现。我们知道,《韩非子·和氏》记载了楚人和氏得璞玉楚山中,奉献给厉王,却被玉人误以为普通石头的故事。璞玉(玉石)还不是玉,它可能被人误认为普通的石头(这与“和氏之璧”不被知类似),但它毕竟含玉质而不同于普通的石头。
与“本始材朴”之性相对的,是“文理隆盛”之伪。伪一般地是指诈、假、非诚等,但《荀子》中的“伪”,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却并非如此,而是指“人为”。孔子将性与习相对,荀子将性与伪相对,其义一也。他们都是在性的本义上讨论人性。在先秦时期,性与生同,这就是性的本义。在这种意义上,性当然是指先天的、生而具有的东西。它们是简朴的,“文理隆盛”的人为则转化这种简朴性。“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表明与生俱来的人性之不自足性、未完美性。不过,不能以恶来说不自足的、未完美的朴之性。性朴论与性恶论实在差别太大。梁启超在解释荀子的“本始材朴”时说:“专靠原来的样子,一定是恶的,要经过人为,才变得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9页。他把“朴”解释为“恶”,乃是极大的误解。
由善变恶,是走完全相反的路,但是,由朴而善,是走同一方向之路。朴之性含有向善的潜质,正如玉石中含玉质。从玉石变为玉,是走同一方向而不是走相反的方向,从朴之性到实现善,也同样如此。“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玉石,则无论如何做不出玉来。因此,虽然性朴论相对地重习轻性,但并不否定性的意义。
孔子所说的相近之性,主要是指简朴之性;荀子所说的“本始材朴”之性,也是偏重简朴之性,但已融入了玉璞之性。到了西汉,董仲舒的性朴论则凸显了质朴之性的玉璞性,同时也兼重其简朴性,对此,本文最后一节再详论。
二、性朴与性恶不相容
《荀子》一书中既有性朴的说法,却又有一篇著名的《性恶》,人们正是依此篇而断定荀子是性恶论者。如何协调性朴与性恶(《性恶》)*在本节,我们暂时依照惯例,视《性恶》与性恶或性恶论为等义词,但下一节会加以区分,因为《性恶》篇的内容或观点不全是主张“性恶”。呢?多数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不认为存在个问题*例如,发表于2015年的一篇荀子研究论文,在“性朴论”已经在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论的情况下,仍然写道:“如上所陈,人皆因不加限制的欲望而具有趋恶的本性。”此足见以“性恶”定位荀子人性论何等根深蒂固。参见王毓:《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周易研究》2015年第4期。。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不能回避。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以《性恶》来解释性朴,或者以性朴来解释《性恶》。上引梁启超的说法,属于第一种思路。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行不通。当然,第二种思路同样也行不通。但这种思路被不少人暗中持有,其基本看法是:(1)所谓性恶,不是指性本身恶,而是指欲望的过度之恶;(2)所谓性恶,是指性中有恶的倾向,而未有现成的恶。这些解释者未明说性恶事实上就是性朴,但按他们明说的,则可以推出性恶就是性朴或接近性朴的结论。他们在作这样的解释时,均忘记了性恶论是针对性善论提出来的。性善论当然主张性本身善,性恶论正是与此针锋相对:性本身恶。《性恶》篇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是在明示这种针锋相对。当然,或者也可以说,上述解释者们也许实际上认为性本身恶之说不成立。但无论如何,《性恶》解释者的主张不能替代《性恶》作者的主张。在解释者心中不成立的主张在作者心里完全可以成立。
暗中以性朴解释《性恶》的人相对多一些,而明确地这样做的人则很少,日本学者兒玉六郎和中国学者路德斌是其中的两例。兒玉六郎非常鲜明地以性朴说来说荀子的人性论:“荀况认为,人之本性、禀性乃素朴而毫无修饰,因后天修为的有无,乃化为后天的善、恶……将荀况人性论的本质理解为‘性朴说’而取代‘性恶说’,应当更恰当。”*[日]兒玉六郎:《论荀子性朴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刁小龙译,《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原刊于《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二十六集,1974年)。说荀子主张性朴论,而不主张性恶论,这种新颖的看法是合理的。但是,兒玉六郎以性朴说解释《性恶》,则难以成立。他认为,《性恶》只是主张后天之性恶,而不主张先天之性恶:“以好利、疾恶、好色之情欲等存在作为《性恶》篇开头一段论述先天性恶论的根据,并不恰当……肆意放任性情的结果,造就了桀跖、小人等恶,这也是后天性恶的论调非其他。”*[日]兒玉六郎:《论荀子性朴说——从性伪之分考察》,《国学学刊》2011年第3期。在兒玉六郎看来,《性恶》实际上主张先天之性朴,这样就与《礼论》所说的“本始材朴”一致了。但是,他并未具体、细致地解释后天之性这个关键概念。事实上,此概念是兒玉六郎自己的概念,而不是先秦语境中的概念。在中国先秦语境中,性与习、伪相对,性是先天的,习、伪是后天的,故不存在所谓后天之性,后天的东西属于习、伪范畴。《性恶》的性伪之分,显然就是先天与后天之分。该篇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明示恶是先天的,而善是后天的。所谓化性起伪,就是以后天的人为努力改变先天之性恶。兒玉六郎认为《性恶》主张性朴说,在我们看来这是很难说得通的。然而,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性朴说对于理解荀子人性论的意义,这是很有贡献的。鉴于兒玉六郎对《性恶》的解释很成问题,后面我们将尝试把《性恶》篇与《荀子》其他涉及人性论的篇目区分开来,这样既能吸取兒玉六郎的贡献,又能克服他的问题。
在国内学者中,路德斌与兒玉六郎一样,明确地以性朴来解释《性恶》。他把《性恶》所说的性一分为二:本原之性(未发之性)和发用之性(已发之性),前者朴,后者恶。路德斌指出:“从‘人生而静’看‘性’,‘性’即朴也,天然合理,无善无恶;从‘感于物而动’看‘性’,顺性自然,贪欲无度,‘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性’乃恶矣……所谓‘性朴’是从存有、本原的意义上讲的,而所谓‘性恶’,则是从发用、经验的层面说的……‘性朴’与‘性恶’绝不可以矛盾、不兼容视之,相反,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荀学的理路中,二者圆融无碍,逻辑一贯,可以同时成立而并存。”*路德斌:《性朴与性恶:荀子言“性”之维度与理路——由“性朴”与“性恶”争论的反思说起》,《孔子研究》2014年第1期。路德斌所说的本原之性接近于兒玉六郎所说的先天之性,而发用之性接近于后天之性。然而,根据《性恶》篇性伪二分的逻辑,所谓发用之性,恐怕不是性而只能是伪。《性恶》有性与伪之二分,而无性本身之二分。路德斌突出性朴,这使他与一般研究荀子人性论的人不同,但是,他与兒玉六郎一样都未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理解《性恶》。
或明或暗地援用性朴论来解释《性恶》的人,忽略了该篇的针对性。众所周知,《性恶》乃是为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作。孟子所说的性善,显然是性本善,即“存有、本原的意义上”之性之善。在孟子看来,善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外铄的。现实中人之不善,是违背了与生俱来之善性的结果。他以山的本来状态来比喻性本善:“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5页。一座光秃秃的山,原来有茂密的森林覆盖,但因砍伐、放牧等而改变了。与生俱来之性善,正如原来的山有茂密的森林覆盖一样。人们自暴自弃,改变善的本性,就像砍伐、放牧等改变了山的本来面貌。《性恶》与孟子的性本善说针锋相对,它不是用性朴论批评性善论,而是用性恶论来批评性善论。如果《性恶》主体部分主张性朴,为什么文中会反复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不说“人之性朴,其善者伪也”呢?
林桂榛认识到《荀子》一书中的性朴说与性恶说不相容,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对《性恶》作性朴的解释:荀子在写该篇时事实上主张“性不善”,与孟子的“性善”相对,但刘向在编《荀子》时把该篇中的“不善”改为“恶”。他指出:“《荀子》一书‘性不善’字眼讹为‘性恶’约在西汉末年刘向对《荀子》的首次编校整理。”*林桂榛:《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现代哲学》2012年第6期。在林桂榛的解释下,性不善的主张当然就与性朴的说法吻合。他与兒玉六郎、路德斌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性朴说与性恶说不相容,而后者认为二说相容。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性朴说与《性恶》篇相容。兒玉六郎和路德斌就现有的《性恶》文本解说这种相容,林桂榛则在对现有文本略作改动的前提下进行解说。但是谁能接受这种改动呢?相比之下,梁涛的“性恶心善”说更加别出心裁而独具一格。但考虑到此“心”很难说是后天之“伪”的结果(而是“伪”的执行者),此“性”亦总是对应着情欲、观念等心理现象,“性恶心善”实际上近于“性善恶混”*参见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
三、《性恶》是荀子后学的作品
以上考察表明,试图协调《荀子》中的性朴思想与该书《性恶》篇的方案,均难以成立。换个思路,如果我们不再坚持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而将《性恶》篇视为其后学所作,那么,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以上我们讨论《性恶》时,仅涉及其主体部分,也即其主张人性恶的部分,而尚未涉及其他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对该篇作整体考察,尤其要论及这些其他部分。
今天读到的先秦子之书,皆经过了汉人或更后之人的整理。以某子命名的书,其成书经过了长时间的过程,往往有多人的贡献,是某一学派的集体作品,而不可全归于某子一人。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对此讲论甚明。先秦子书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人之手,乃为确论。例如,现存《庄子》一书,肯定不是庄子一人写的,一般认为庄子仅作了内篇,而外篇、杂篇是其后学所作。冯友兰亦持类似的观点,并以《荀子》为例,认为:汉朝及以后的人将相关篇章编辑成为一部书而题名为《荀子》,并没有说这是荀子亲笔写的,而仅意味着它们是属于荀子一派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1页。。
《荀子》是荀子学派的作品,而非出自荀子一人之手,大概不会有人否定这一点。唐代注《荀子》的杨倞把《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放在该书的最后。他注《大略》时说:“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85页。注《宥坐》时又说:“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520页。被杨倞置之于《荀子》后面的多篇,在写作风格、表达方式、思想内容等方面都确实不同于该书的其他篇。《大略》的作者肯定不是荀子而是他的弟子,这正如《朱子语类》的作者不是朱子而是朱子弟子。其他几篇的作者,就更加复杂了。它们不是论说文,而是对话、小故事的汇集,杨倞称之为“记传杂事”,为荀子及其弟子的讨论素材、教学素材,在荀子之前可能就以口头的方式存在,也可能以书面的形式存在,更可能是荀子后学整理而成。它们肯定不是荀子本人所作。
汉代的刘向在整理、编辑《荀子》时,也把上述多篇放在书后面。他当然意识到了它们的特殊性。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向把《性恶》也编排在后面,将之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杨倞认为,《子道》和《法行》这两篇属于“记传杂事”,但《性恶》不是,故将这一篇提前。他在注《性恶》时说:“旧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议论之语,故亦升在上。”*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34页。在刘向编辑的版本中,《性恶》为第26篇,而杨倞将它提升为第23篇。
刘向把《性恶》编在《子道》和《法行》之间,实在太意味深长了。他编的《荀子》最后9篇是:《宥坐》、《子道》、《性恶》、《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赋》。《宥坐》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杂言杂语,而它的前一篇为《礼论》,明显是论说文。在刘向的编排中,《宥坐》与《礼论》之间事实上有明显的分界线。在此界线之前的23篇是论说文,而之后的9篇则是各种小故事、短论、对话等的汇集。这样,全书就分为两部分:论说文部分(从《劝学》至《礼论》共23篇)、杂言杂语部分(从《宥坐》至《赋》共9篇)。用汉代惯用语来说,前者可称之为内篇,后者可称之为外篇。按照这样的编排,显然,前一部分基本上为荀子所作(后学可能对之有增删),后一部分则非荀子所作。
与刘向的版本相比,杨倞的版本也把《荀子》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从《劝学》至《赋》,共26篇,后一部分从《大略》到《尧问》,共6篇。他显然以前者为荀子所作,后者则是他人所作。两个版本最突出的不同是《性恶》由后往前的位置变化,此外也有其他变化,如《赋》也从后一部分升入前一部分。也就是说:刘向把《性恶》和《赋》看作非荀子作品,而杨倞则把它们看作荀子作品。
面对两人的分歧,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刘向。刘向先于杨倞七八百年,前者离荀子两百多年,后者离他近千年。古书不用标点符号,作为人的荀子和作为书的《荀子》无法区别开来。在从汉到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们因而就会逐渐认为《荀子》一书都是荀子所写,这样,荀子不是《性恶》作者的历史实情也就被遮蔽了。作为《荀子》最早的整理者和编辑者,刘向清楚地看到《性恶》与《劝学》、《礼论》等论说文有极大的不同,故而将它置于杂言部分。
细致研究《性恶》可见,它确实不是一篇论说文,而是荀子后学对人性或与人性有关的问题的多种看法的汇集。人性恶的看法,只是本篇的一种看法(主体部分的看法),其中还有与此不同甚至与此矛盾的其他看法。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它为性恶论的代表作,其中与性恶论不一致的看法则被忽视、淡化、埋没。如果我们重新正视其杂言性,而不以之为一篇论说文,上述其他看法就可得到客观的看待。
大体上说,《性恶》由七个模块构成,其中只有一个模块明确主张人性恶,多数模块则并无此主张。模块一从开始到“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模块二从“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到“慢于礼仪故也,岂其性异哉”。模块三从“涂之人可以为禹”到“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模块四从“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到“唯贤者为不然”。模块五从“有圣人之知者”到“是役夫之知也”。模块六从“有上勇者”到“是下勇也”。模块七从“繁若、钜黍,古之良弓”到结尾。
在上述七个模块中,最显眼的当然是模块一,其文字也占了《性恶》全篇的一半以上。本模块反复论证人性恶,以《性恶》篇名概括本模块的内容当然非常合适。但是,这一篇名并不能概括所有模块的内容。在其余六个模块中,只有模块四的“人情甚不美”*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44页。表述接近模块一的思想。模块三鲜明地陈述了与模块一相反的看法:人人皆可以为禹,因为人人皆有“知仁义法正之质”和“能仁义法正之具”*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43页。。此质、此具当然是善的,而不是恶的。根据性伪二分,此质、此具当然属于性,而不属于伪,这就完全否定模块一多次说的“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参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35、437、439、440、441、442页。。如果把《性恶》作为一篇论说文,其作者是同一个人(荀子),就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结论:“荀子并没有因此全盘否认性善说,也没有妨碍肯定人性的中性、可塑性。这样,人性中就既包含着善的可能性,也包含着恶的可能性。现实的善恶,都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其潜在的根据。”*李景林:《荀子人性论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2期。“尽管他一再力图证明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的,然而在事实上却是把善和恶都当作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荀子这种前后不一的矛盾,表明他只是注重性恶的一面,但很难说他就是性恶论。说的再明白一点,与其说他是性恶论,莫如说他是人性有善有恶的二重论,更为贴切……荀子在这里所说的普通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正法之质’,并非后天人为的……是人性里面本来就有的。由此可见,在荀子的思想中,善和恶实际上是作为人的二重性而存在的。”*李经元:《荀子的人学思想》,《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荀子在强调性恶的同时,还承认并且一再肯定过人性中还有非恶的一面存在。”*廖名春:《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说这些话的人注意到《性恶》对人性论有不同的说法,但他们一定要把它们都视为荀子本人的看法,这就使他成为性有善有恶论者或性有恶有不恶论者了。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放弃荀子是性恶论者的传统看法,另一方面又把他说成性有善有恶论者或性有恶有不恶论者。事实上,是论者们混乱、自相矛盾,而不是荀子本人混乱、自相矛盾。《性恶》的不同模块,显示的是荀子后学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不是荀子本人的看法。如果我们真的要坚持《性恶》的作者是一个人(荀子),《性恶》是一篇完整的、前后一贯的论说文,我们就无法解通它。

但是,若说模块七体现性朴论,则完全说得过去。上面已经说过,可以从玉璞的角度理解性朴论。与生俱来之性,既可说是简朴的,也可说像玉璞那样含有善的潜质,但没有完备的、现成的善,也就是性善论所肯定的善。故性朴论与性善论的区别很明显。性质美即玉璞美,不过,这种美尚未处于完备的、现成的状态,而需要磨练,需要开发。如果像有些论者那样,认为模块七表述性善论,那就言过其实了。姜忠奎在20世纪20年代作《荀子性善证》*姜中奎:《荀子性善证》,台北:文昕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据民国十五年铅印本影印)。,特别突出该模块,对之作了过度解释。现当代学者中也有人对这个模块进行过度解释,认为荀子主张天生之人性中有完善的、绝对的、先验的仁*曾振宇:《“性质美”:荀子人性论辩诬》,《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这就说过头了。以“道德形上学”、“客观精神”这些来自西方的术语来说荀子对仁与人性的看法,难以令人信服。他高扬荀子的性质美说,内心可能倾向于以荀子为性善论者而又不敢像姜忠奎先生那样明说,这倒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
模块二也表明荀子后学继承老师的性朴论:“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42页。作者比较曾参、闵子骞、孝己与众人,比较秦人与齐鲁之民而得出结论:他们在天性方面没有差异,其德行之不同,完全是后天修为不同之结果。本模块丝毫没有显示性恶,而是显示性朴。
模块二对人性的看法,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也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性近习远论。曾参、闵子骞、孝己与众人性相近,秦人与齐鲁之民性相近,而他们习之不同致使其在德行上不同。杨倞对本模块的解释显然不成立:“綦礼义则为曾、闽,慢礼义则为秦人,明性同于恶,唯在所化耳。若以为性善,则曾、闽不当与众人殊,齐、鲁不当与秦人异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42页。很多读者会像杨倞那样顺着模块一来看模块二,以为是在继续说人性恶。实际上,把此模块同第一模块区隔开来单独解读,就会发现用性朴论来理解它,要比用性恶论来理解它更合理。
模块五讨论四种知: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役夫之知。模块六讨论三种勇:上勇、中勇、下勇。两种讨论都未直接牵涉到人性。这两个模块的存在,突出地表明了《性恶》的杂言性。如果把它看作一篇连贯的论说文,此两节之存在尤其不可解。作为先秦的文章大家,荀子如果真的作《性恶》,又真的把上述五、六两个模块放进去,实在不可思议。从杂言的角度看,这两个模块也许间接地体现对人性的看法。笔者猜测,它们可能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四种知、三种勇与先天人性相关。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毕竟两模块完全未说到人性。这两个模块也许是后来性三品说的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以《性恶》为荀子后学的杂言杂语而不是荀子本人的论说文,可以找到较强的证据。该篇反映了荀子后学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有人继承老师的性朴论,有人将老师的性朴论发展为性恶论……“性恶”实在无法概括全篇的内容。相形之下,至于《荀子》一书之《劝学》、《礼论》、《天论》、《正名》等论说文,篇名对于该篇内容的概括则准确而全面。《子道》、《性恶》、《法行》等杂言杂语篇则不同,篇名不能涵盖全篇之内容。《性恶》之命名方式,与《子道》、《法行》等是一样的,只是对开头的内容(第一模块的内容)的提示。《子道》、《法行》等也是由多个模块组成,每一模块相对独立,各模块之间关系松散,不存在逻辑、内容、时间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性恶》大体上也一样。《子道》、《法行》不是论说文,夹在其中的《性恶》因而也不可能是论说文。
《荀子》中的《性恶》是荀子后学所作,但我们不说它是伪作,正如《庄子》的外篇、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但我们不说它是伪作一样。前面已经说过,《荀子》其书不全出自荀子其人,其中肯定有荀子后学的贡献。作为荀子学派的代表作,它不存在伪的问题。因此,林桂榛认为,周炽成主张《性恶》是“伪书”*林桂榛:《“材朴”之性又谓“性恶”?——驳为〈荀子〉“性恶”曲辩者》,《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
四、性朴论支持荀子的学论、礼论、政论
《性恶》为荀子后学所作,《荀子》全书只有这一篇显示性恶论。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它显示于《荀子》的多篇之中。性恶论与荀子的整体思想严重冲突,而性朴论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荀子的其他思想非常一致,并提供支持。性朴论尤其支持荀子的学论、礼论、政论,这三论是其最重要的思想。
以荀子为性恶论之代表的强大惯性事实上曲解了荀子的学论,而唯有回到性朴论才能客观、公允地理解它。荀子学论最集中、最系统地表述于《劝学》,它是《荀子》首篇,任何一个研究荀子的人都读过此篇。但是,在性恶论视野下读之,就会明显地误解它。王博在《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学中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学的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是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至于这种缺陷是什么,以及到什么程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荀子那里,当然是其性恶的主张。性恶代表着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因此需要转化。而在化恶为善的过程中,学就构成了重要的枢纽。”*王博:《论〈劝学〉在〈荀子〉及儒学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5期。王博认为,荀子之所以在《劝学》中强调学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人性中的根本缺陷,即人性恶。人之持续不断地学,就是为了转化人性中的恶。王博以《性恶》解读《劝学》,对之作了很大的误读。认真通读全篇《劝学》,能找到对人性恶的明述或暗示吗?只要撇开荀子是性恶论者的先入之见,应该说完全找不到。客观看《劝学》,不难发现其性朴论意识,兹将其性朴论的典型论述梳理如下:
(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2页。这段话明显继承了孔子之富于性朴论色彩的名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生而同声”意味着“性相近”,“长而异俗”意味着“习相远”。性朴论相对地重习轻性,在这点上,荀子与孔子非常一致。当然,性恶论也重习或者说伪,但是,性恶论所说的伪是完全逆性、反性的,而性朴论所说的伪则不如此。“长而异俗”或“习相远”都是自然的过程,而非逆性、反性。
(二)“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4页。王念孙解释说:“生,读为性。”*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4页。君子之性不异于众人之性,不同的地方仅在于君子比众人善于借助外物。而这种“善于”当然是后天的作为。此与上一段的“生而同声,长而异俗”,表达的都是性朴论的意思。
(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1页。杨倞对此的解释是:“以喻学则才过其本性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1页。这种解释甚为精当。“过”是顺着同一方向的“超过”,而不是沿着相反方向之“逆行”。这里表达的恰恰是与性恶论相反的东西。日本学者田虎敏锐地看到《劝学》此名言破性恶论:“推此蓝、水之喻,则恐性恶之说破也。蓝之性青,故出之愈青;水之性寒,故为冰益寒。然则人之性恶,修之将益恶也。若性恶以修以为善,则蓝亦出白,水亦生碳。故蓝、水之喻,非所以劝其学也。”*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蓝与青、水与冰的性之相似,意味着天性与人为(学)的方向相同。学的过程不是化性起伪的过程,而是顺性而为、据性而练的过程,这就像玉石加工为玉的过程。显然,蓝、水之喻是性朴论之喻,而不是性恶论之喻。前面已说过,性朴就像玉璞。依据荀子的学论,学的必要性确实不在于性恶,而在于性朴。学使人的天性完善、再完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造人的天性。是性朴论而不是性恶论支持了荀子的学论。
(四)“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5页。这番话最符合性朴论之简朴义。王念孙在解释本句时指出,“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5页。。蓬在本性上不直,但如果它生在直的麻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变直;本性是白的沙,如果被放置于黑色的矿物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变黑。性朴论强调环境的重要性,蓬沙之喻也同样如此。如果说荀子的学论以性恶论为指引,怎么解释上述此喻呢?
性朴论不仅支持荀子的学论,而且也支持他的礼论。荀子以重礼出名,他的礼论在其整个思想中当然处于重要地位,相关思想集中体现于《礼论》篇。其中之名言,上面已经讨论过:“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366页。《礼论》上述文字,可谓性朴论最经典的表述。礼就是伪的基本内容,这段话中的“伪”甚至可以用“礼”来代替,“性伪合”也可以说是“性礼合”。人性朴,需要礼的“文理隆盛”来完善,但是,朴之性毕竟是礼作用的根基;无性,则礼就失去了作用的根基。
性朴论的思想是荀子礼论的关键指导思想。但是,以荀子为性恶论代表的强大历史惯性,却使论者们以为性恶论的思想才是荀子礼论的关键指导思想。这样的看法确实适用于《性恶》篇,但不适用于《荀子》一书中的其他篇。《性恶》的说法大家都熟悉:
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435页。
在《性恶》篇中,因为人性恶而圣王生礼义,礼义的功能在于克服人性恶,故礼义与性相悖、相逆。这些看法实在是荀子后学的看法,而不是荀子本人的看法。如果以之为荀子本人的看法,则会极大地误解他的礼论。
《礼论》开头有一段很著名的话:

这里完全没有性(欲)恶的意思。争与乱这些恶,不是人性本有的,而是后天的行为(“求而无度量分界”)带来的。依据荀子的礼论,礼义给欲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以便让它们不会导致争和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让欲得到满足。尤其要注意以上引文中的这些话——“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者,养也”。此外,《礼论》还说“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349页。。但是,在《性恶》中,礼义则纯粹是一种跟情欲相违、相悖的力量;正如伪是跟性“对着干”一样,礼义也是跟情欲“对着干”的。《性恶》的作者显然背离了荀子《礼论》中的礼义养情欲的思想。《性恶》之反性悖情与荀子礼论之养欲给求,无论如何是不相容的。荀子礼论对性的看法,用性朴论解说很合理,用性恶论来解说则很荒谬。
荀子的性朴论也支持他的政论。荀子的政论具有丰富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君道》、《王制》、《富国》、《王霸》等篇中。其中,《君道》言:
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237页。
荀子对君的职责的看法,与上引《礼论》“人生而有欲……礼者,养也”对人性的看法密切相关。君之四方面的职责(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可概括为遂民之欲,而欲就是性或性的体现。这与性恶论尖锐冲突,而与性朴论相容。《性恶》一开头就对性持否定性的看法:“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这些看法无论如何是极悖于荀子政论的。
荀子对君王的职责还有更简洁的表述:富民与教民。《荀子·大略》记载:

孔子也主张先富后教。养民情与理民性相提并论,这当然意味着性不恶。以教来“理”的性跟《礼论》、《劝学》等篇所说的性一样都是朴的,既不可以善名之,但又可以说含有善的潜质;既不可以恶名之,但又可以说离完善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理”的原义是加工、雕琢玉石,“理民性”之说因而显示了鲜明的性朴论色彩。玉石含有玉的材料,人性含有善的素材。但是,与玉石含有杂质一样,先天人性也非十全十美,通过教来理民性,则可去掉其中不完美成分。把理民性与养民情联系起来,非常重要。荀子主张以良好的经济政策来富民,从而满足他们的自然欲望,这与他的礼论是一致的。
总之,性朴论与荀子的其他主要思想如学论、礼论、政论等相一致,而性恶论则与这些思想相冲突。以上分析进一步表明,荀子是性朴论者,而不是性恶论者。
五、贾谊与韩婴的性朴论
先秦孔子、荀子等人所持的性朴论,一直传承到汉代。西汉性朴论的代表人物有贾谊、韩婴、董仲舒等,其中以董仲舒最为重要。本节先讨论贾谊和韩婴,下一节再讨论董仲舒。
贾谊是荀子的三传弟子,因为他的老师吴公(吴廷尉)是李斯的学生。而且,贾谊明显继承了荀子的《春秋》传:“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梁武帝:《答刘之遴上〈春秋义〉诏》,参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968页。由于这种学术背景,贾谊继承荀子的性朴论就是很自然的事。把他的著作《新书》与荀子的著作相比较,从形式到内容,两者都有太多一致的地方。例如,《新书》有些篇名与《荀子》完全一致(如《劝学》、《君道》);有些非常接近(《新书》有《礼》,《荀子》有《礼论》)。贾谊的性朴论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于《新书·保傅》中:

在给教育太子提建议时,贾谊的论述充分展示了他的性朴论思想。开始第一句即与孔子性相近的看法一致。后面通过比较周太子之善与秦太子之恶而总结历史经验。这方面的经验,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概括,当然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性朴论。在贾谊看来,太子的早年教育确实太重要了,如果太子周围接触的人皆为好人,他就自然会好;反之,则自然会坏。好坏非天生,而是教成。贾谊明确否定胡亥生而恶,此即否定性恶论;不过,他也不认同性善论,不认为胡亥生而善。“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则教习然也”与《荀子·劝学》的“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高度一致,它们都可被看作性朴论的名言。
很多论者以性善论来解释贾谊的人性论。例如有论者以“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为根据而说贾谊“关于性善恶的言论接近孟子”*马晓乐、庄大钧:《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这种说法肯定不成立。贾谊不认为胡亥生而恶,也不认为他生而善,以生而朴说之,则比较合适。然而,认为贾谊继承了孟子性善论的说法却又比比皆是。例如,又有论者指出:“他把后天养成的善性看成是‘天性’与‘自然’,正表明人性本身即为善。而且,贾谊最后还作设问:‘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集[习]道之者非理故也。’就是说,胡亥的本性并非天生为‘恶’,其‘性恶’是在后天‘集道’过程中,受赵高误导丢失了‘理义’的结果,而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高正伟:《贾谊对孟子学说的因革》,《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贾谊引用孔子的话“少成若天性,习贯若自然”,并不表明天生之性是善的,而是表明:年少时形成的东西就像天性一样,习惯的东西就像自然而有的。这恰恰显示了与人性天生为善之性善论相反的看法。这位论者把贾谊所谓“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与孟子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相提并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贾谊并不主张胡亥生而具有“理义”,生而善,只是被赵高误导而变坏的。
还有一些论者以性恶论来解释贾谊的人性论,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有人说:“贾谊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基础制定礼。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无限制的发展,就会对统治者产生威胁。所以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限制人性的恶,由此他列举了许多有关人性恶的实例来充实自己制礼依据。”*王利明:《荀子“性恶论”对贾谊礼学的影响》,《参花(上)》2014年第8期。在这位论者看来,贾谊用来表明人性恶的实例就是《新书·藩强》中说到的淮阴王、韩王、贯高、陈豨、彭越、黯布、卢绾等诸侯王的反叛,而长沙王不反叛,是因为他弱,“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贾谊撰,卢文弨校:《新书》,第10页。。根据这位论者的解释,贾谊认为诸侯王的人性都是恶的,长沙王也不例外。其实,贾谊在此并未涉及到天生之人性善还是恶的问题。虽然这里出现了“性”字,但它在这里不是指人的天性之性,而是指人的性质之性、特性之性。这种意义上的性,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如果有人在这些诸侯王初生时就断定:他们长大后一定会谋反,谁会相信这种断定呢?贾谊会相信这样的断定吗?又有人说:“贾谊认为‘性者,道德造物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存在是由道德形成的,是通过后天环境培养起来的,这与荀子的‘性恶论’有所相似。”*林文昌:《略谈贾谊的教育思想》,《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10期。这位论者所引贾谊的话出自《新书·道德说》。他把古之道德与今之道德混同,对此话作了非常严重的误解。在先秦两汉语境中,一般来讲,道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原则,表现于某物的原则就是德,故那时的道德与今天的道德完全是两码事。贾谊自己在该篇中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解释:
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明其润益厚矣。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为物莫生,气皆集焉,故谓之性。性,神气之所会也。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於外矣,与外物之感相应,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贾谊撰,卢文弨校:《新书》,第86页。
这样的解释表明,“性者,道德造物”*贾谊撰,卢文弨校:《新书》,第86页。与性恶论绝对无任何瓜葛。这话倒与性善论看起来有点瓜葛。蒙文通指出:“以‘道德造物’言‘性’,是以造物之始,道德与性谐也,故可通于性善之义。”*蒙文通:《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事实上,如果我们明白贾谊在此说的是性的形成、产生的自然过程,他并未下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其与性善论的瓜葛就可以解开了。
贾谊在《新书·连语》中对三种君王的叙述事实上也表达了性朴论的思想:
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桀、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耳,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
如果用性善说上主,用性恶说下主,那么,只能用性朴说中主。显然,贾谊最为关注的是中主,因为他认为关注中主才有意义。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上主、下主少,而中主多。他的师叔公或师伯公韩非子就说过,尧舜这样上君和桀纣这样的下君“千世而一见”,而中君则太常见了。更关键之处在于,在贾谊看来,上主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坏,故不用忧,而下主无论如何都不会变好,故忧也没用,可忧的是中主,他们受周围影响甚大。贾谊用染丝来比喻这种影响,“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这自然令我们联想到前面讨论过的荀子《劝学》中的性朴论名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总之,以性善论或性恶论来说贾谊的人性论均不合理,以性朴论来说则比较合理。作为荀子的三传弟子,他继承了师祖的思想,是汉初性朴论的代表人物。
比贾谊稍晚的韩婴也是荀学的传人,也继承了荀子的性朴论。因其《韩诗外传》大量引用《荀子》,称他为荀子后学并不为过。汪中指出:“《韩诗》之传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上册,第21页。前面说过,性朴论之朴主要含简朴义与玉璞义。韩婴的性朴论侧重玉璞义。他说: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韩婴编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5页。
不少论者以这里出现“人性善”为据,而断定韩婴为性善论者。认真看全文,我们认为,把这里的人性论概括为性朴论似更合理。这里的“人性善”,不是指人性中具有现成的、完备的善,而是指具有善质、善能。这种意思,联系蚕之性、卵之性来理解,很容易看得出来。“茧之性为丝”不是指茧之性中有现成的丝,而是指其中有成丝的素质、潜质。同样,“卵之性为雏”不是指卵之性中有现成的雏,而是指其中有成雏的素质、潜质。事实上,韩婴强调的不是这些素质、潜质,而是强调女工加工的作用、良鸡覆伏孚育的作用。与此类似,他注重的不是“人性善”,而是外在的“明王圣主扶携”,和个人的“内之以道”。如果以性善论来解释之,就把他所不注重的,误解为他所注重的了。我们以性朴论来理解,则能把他所注重的客观地呈现出来。从茧到丝的过程、从卵到雏的过程,正像从玉石到玉的过程。玉人不能把一块普通的石头加工为玉,但没有玉人的加工,再好的玉石也成不了玉。在性朴论视野下,天生人性的状态就像玉石的天然状态。没有玉人的加工,玉石永远是天然状态的玉石,而不是玉;没有后天的努力,人就永远处于朴的状态而不能成为善的君子。以性朴论来解释韩婴的话,不是要比用性善论来解释之更好吗?
韩婴的其他话也可印证以上解释:“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韩婴编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295页。“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虽有旨酒嘉殽,不尝,不知其旨;虽有善道,不学,不达其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韩婴编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98页。这些话,与上一段引的话属于同一类型。上面讨论过的《荀子·性恶》第七模块的话“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也属于这一类型。像姜忠奎那样把《荀子》此言视为性善论,则是过度解释;现代许多学者把上引《韩诗外传》话语视为性善论,同样也是过度解释。而我们用性朴论来说这些话语,则是适度解释。朴或璞的状态肯定不是一种现成的、完备的善的状态,而是一种待开发、待加工、待完善的状态。
《韩诗外传》确实多次肯定孟子,但并无明确肯定孟子性善论的文字表述。有人认为,以下的话明确表达了性善的意思: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韩婴编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第219页。
严格来讲,这里说的是心,而不是性。“仁义礼智”与“顺善”的关系,不应该是并列关系,而是主谓关系。顺是指顺从、遵照。其意思很明显:人天生有一种心,在这种心中,仁义礼智顺从善,认识到这种心的,就是君子,认识不到这种心的,就是小人。这里讨论的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而小人无此心。韩婴在此不讨论君子与小人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如果一定要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与典型的性善论者的回答应该是不同的:君子与小人没有共同的人性。
六、董仲舒的性朴论
董仲舒与韩婴同时,但二人对孟子的态度有所不同。韩婴不批评孟子而有接近他的倾向,董仲舒则明确地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当然,董与韩一样都是性朴论者。董仲舒对性朴论的典型论述包括:
论述1:“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3页。
论述2:“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务明教化民,以成性。”*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5页。
论述3:“以麻为布,以茧为丝,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故不可谓性。”*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311页。
论述4:“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312页。
这些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人性朴或质朴。论述1非常接近《荀子·礼论》中的话:“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第366页。两段论述从文字到内容都高度一致。在中国人性论史上,两者是性朴论的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它们对质朴人性与人为的关系阐述了完整的看法。论述2直接以质朴为性,表明教化对于成性的意义,天生质朴之性还远不能算“成”,只有经过长期的教化才能“成”。所成之性与天生质朴之性有明显的距离。论述3以具体例子阐明如何在质朴性情之基础上形成善。善是需要“为”的,而不是天成的。以性为善之“为”,是长时间的人为,而不是瞬间的“看作”、“以为”。将麻做成布,将茧织成丝,将米做成饭,这些都是“继天而进”之人为的结果。善也是人为之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质朴之性所固有。论述4继续发挥论述2和论述3的看法,其所谓“教训”即论述2所说的“教化”。
董仲舒所说的性朴,与荀子的性朴一样都具有简朴与玉璞两方面意义。不过,他可能更突出玉璞的一面。董仲舒说:“玉出于璞,而璞不可谓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谓善。”*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312页。璞还不是玉,但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假如玉相当于人性善的状态,璞则与这种状态有一定的距离,这说明初生人性是不够完美的,因而董仲舒不赞成性善论。不过,他也不会赞成性恶论,因为璞的状态只是不够完美而已,不能说是恶。璞石毕竟不是顽石,不是恶石。如果说人性恶,这就是以朴石为顽石、恶石了。
董仲舒是荀子之后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两人的性朴论一脉相承。董仲舒的性朴论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区分善与善质。善是指现成的善,善质是指善的潜质。董仲舒反复说,天生人性有善质,但没有现成的善。他举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例如,目与见就是一例:
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97页。
睡觉时的眼睛与觉醒时的眼睛是同样的眼睛,但前者有“见质”而未有见。与之类似,天生人性有善质而未有善。再如:

天生之性有善质的状态,是性朴的状态,而不是性善的状态。董仲舒非常明确地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在他看来,孟子说人性善,便相当于说目即见、茧即丝、卵即小鸡。如前所述,卵与雏、茧与丝之例,韩婴也说过。看到董仲舒的阐述之后,我们当更能明白以性朴论解说韩婴之是,与以性善论解说韩婴之非了。
其次,不能以过低的标准来理解善。董仲舒批评孟子对善的要求太低,不符合圣人对善的要求。在孟子眼里,人善于禽兽,这就表明人性善了,但是,董仲舒则对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说:

以“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等高标准的善来评判天生人性,董仲舒得出结论:性只是朴而未到达善。
再次,不能混淆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董仲舒指出: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97页。
董仲舒认为,天之所为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天质之朴所能达到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的,就是人之所为了。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把人之所为看作天之所为。天之所为,只提供善质,而不提供善。善完全是人之所为的结果。
董仲舒持性朴论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据笔者所知,以前研究其人性论的人,似乎一直没有把他作为性朴论者。人们对董仲舒的人性论充满误解。最早的误解可能来自王充:“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也。”*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8页。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于先入为主地影响了人们对董仲舒人性论的了解。由此,人们对董仲舒的性朴论述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解,并形成了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几种常见解释:(1)调和或综合孟荀人性论;(2)性善情恶;(3)性有善有恶。这些解释都或多或少与王充的说法有关。
持第(1)种解释的人,是受了王充的“董仲舒览孙、孟之书”等话语的影响,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在调和或综合孟子的人性论和荀子的人性论。例如,冯友兰说:“董仲舒之性说,按一方面说,为调和孟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17页。刘国民说:“仲舒认为,性非全善,性有善有恶,善主恶从。这是对孟、荀人性论的整合。”*刘国民:《悖立与整合——论董仲舒对孟子、荀子之人性论的解释》,《衡水学院学报》2006第3期。事实上,从研究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材料《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我们看到他明确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调和或综合论者如何面对这些批评呢?我们同样也只看到了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的继承,而看不到他对所谓荀子性恶论的任何援引,调和论或综合论者又如何面对这方面情形呢?
持第(2)种解释的人受王充的“人之大经,一情一性”等话语的影响,认为董仲舒坚持人之性是善的而情是恶的。例如,徐复观说:“董氏则显然将性与情分开,认为性善情恶;此一分别对后来言性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黄开国说:“由阴阳所生之性包含性与情两个方面,阳善阴恶,故天生人性包括善恶。”*黄开国:《董仲舒的人性论是性朴论吗?》,《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然而,我们在《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看不到董仲舒援引或化用王充“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这一番话,也看不到有类似的思想存在其中。如果董仲舒主张性善,他为何反复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呢?他赞成性有善质(善的潜质),而明确反对性有现成的善。性善情恶者如何面对他的批评与反对呢?
持第(3)种解释的人受王充整段话的综合影响,认为董仲舒坚持与生俱来的人性不纯是善的,也不纯是恶的,而是善恶兼有。例如,曾振宇说:“善恶、仁贪等人伦观念先在性地包容于抽象的人性范畴之中,同时又完好无损地外现于每一个认知主体的人性之中。人性既不能单纯地评判为善,也不能片面地归纳为恶,而是善恶仁贪兼备……世上人有千千万,但每一个人的本性中都全息地兼容着善恶仁贪等伦理观念的‘因子’。在董仲舒看来,善恶等人伦观念,是先验性的实有,是类似于莱布尼茨哲学意义上的‘预定和谐’。”*曾振宇:《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王琦、朱汉民说:“人性所含善质与恶质的多少则取决于阴阳之气相济相成之比例,天通过阴阳之气的互动而将善质或恶质赋之予人。”*王琦、朱汉民:《论董仲舒的人性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董仲舒说过性有善质,但未说过性有恶质。把西方哲学的术语“先在性”、“先验性的实有”、“预定和谐”等套在董仲舒人性论身上,不能令人心服口服。董仲舒在讨论人性时反复举麻成布、茧成丝、米成饭、卵成雏等例子,明显旨在展示从善质到成善的过程性。上述西学术语则抹杀了这种过程性。
以上对董仲舒人性论的三种常见解释都是从王充的论述中演绎出来的,但我们理解董仲舒的人性论不应该以王充的话为准,而应该以董仲舒的话为准。抛开王充,而直接从《春秋繁露》的《深察名号》和《实性》这两篇被公认为董仲舒集中、系统地讨论人性论的经典作品入手,我们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上述三种看法都很难在这两篇文章以及整部《春秋繁露》中得到可靠的支持,也无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得到支持。而我们以性朴论来说董仲舒的人性论,则可以在这些文献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本节开头所引的四种董仲舒性朴论论述,都出自这些文献。此外,董仲舒还有其他性朴论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论及。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是温和的,而《性恶》对它的批评是激进的。《性恶》因而很有可能出现于西汉后期。就学术演变之一般情形而言,先有对某一理论的温和批评,然后才有对它的激进批评,这是比较自然的。可能有人看到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太温和,不够过瘾,于是便用更猛烈的言辞、更极端的立场来批评之。这人或这些人可能就是《性恶》的作者*周炽成:《董仲舒对荀子性朴论的继承与拓展》,《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性朴论的思想,从先秦延续到西汉,而且还在往后延续。例如,东汉《潜夫论·赞学》、南北朝《刘子·崇学》都继承了《荀子·劝学》中的性朴论思想。因篇幅及论题所限,东汉及以后的性朴论思想,当另文详之。
[责任编辑李梅邹晓东]
周炽成,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教授(广东广州 51063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性论通史”(15ZDB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