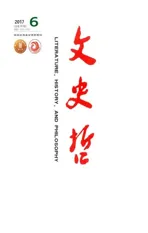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2017-02-07胡旭胡倩
胡 旭 胡 倩
唐景龙修文馆学士及文学活动考论
胡 旭 胡 倩
唐中宗景龙年间设置修文馆学士一事,见载于多种典籍,但矛盾之处颇多,似乎没有绝对准确的记载。通过对相关典籍的比勘考证,可知景龙二年、三年、四年皆有选任修文馆学士之事,在这三年中任过学士的共有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所云学士数吻合。但《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等典籍中所说的“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只是景龙二年设置修文馆时计划员数,在随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三类学士的确切员数都与原计划不符。景龙修文馆学士重形式尚技巧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在当时影响甚大,在唐代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总体上价值不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
景龙;修文馆学士;宫廷文学;盛唐文学
一、相关文献梳理
唐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学士。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月。游宴悉预,最为亲近也。*朱胜非:《绀珠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2页。
这则材料中,学士总员数二十四。《旧唐书·中宗纪》的记载,则有所不同:
(景龙二年夏四月)癸未,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页。
这则记载的明确信息是修文馆设置学士的时间是“四月癸未”,员数为“大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总员数二十。
随后,比较详实的记载,见于《唐会要》卷六十四:

仔细解读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信息如下:首先,景龙二年(708)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增置三类学士及员数的计划出台。其次,仅仅过了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中书令李峤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并为修文馆大学士。也就是说,此时只设立二名大学士,尚有二名空缺。再次,又过了二日(四月二十五日),修文馆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正好八人,符合既定员数。复次,又过了十日(五月五日),修文馆直学士人选出台,他们是: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只有五名人选。最后,差不多又过了五个月(十月四日),赵彦昭、苏颋、沈佺期一起递补为学土。
比《唐会要》稍晚的《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亦有相关记载:
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李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48页。
这则记载看起来很清楚、系统,后为《唐诗纪事》所本,越发流传深广。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皆有具体对应,直学士对应了十一人,少了一个。
《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亦记此事: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22页。
此处直学士员数与学士员数与上文诸则记载相较,正好颠倒。
《玉海·艺文》叙录《唐景龙文馆记》云:
中宗景龙二年,诏修文馆置大学士、学士、直学士凡二十四员,赋诗赓唱,是书咸记录为七卷。又学士二十九人传,为三卷。记云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时。*王应麟辑:《玉海》卷五十七《艺文》,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093页。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虽然规定学士总数为二十四员,但《景龙文馆记》中“传”的部分却出现了二十九位学士,这是此前文献没有提及的。
综合以上记载,可归纳出如下信息:首先,诸文献或云“置”,或云“始置”,或云“增置”,三个词语意义是不同的,个中真相,不应含糊,尚需揭示。其次,各文献记载修文馆学士员数有偏差。《新唐书》记载三类学士二十三人,较理论员数二十四人少一人;《唐会要》记载三类学士十九人,较理论员数少五人;《玉海》云学士有二十九人,较理论员数多五人。第三,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设置,是有步骤的,这一点《唐会要》的记载相对详赡,有一定说服力,其他文献在这一方面给后人带来一些误导。第四,学士种类尚有分歧。《旧唐书》只云大学士和直学士两类,其他记载则分为大学士、学士、直学士三类。第五,各类学士的员数不同,《旧唐书》云大学士八名,其他文献云大学士四名。《资治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而其他文献皆云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正好相反。第六,某些人选究竟属于何类学士,记载有互为矛盾之处。如《新唐书》云赵彦昭为大学士,《唐会要》则云赵彦昭为学士;《新唐书》云韦嗣立为大学士,《唐会要》则未提及此人;《新唐书》云沈佺期为直学士,《唐会要》却云沈佺期为学士;《新唐书》不提及苏颋,《唐会要》却云苏颋为学士。
相关问题错综复杂,深入考证十分必要。
二、景龙修文馆学士入选时间及总员数考辨
《唐会要》所记修文馆学士十八人,《新唐书》所记修文馆学士二十三人,将两者所记合在一起,可得二十四人,即李峤、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唐会要》所记十八位学士,入选时间比较明确,《新唐书》所记的韦嗣立、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入选学士的时间,尚不明了,当进行考察。
韦嗣立。两《唐书》本传不云韦嗣立为修文馆学士,然张说《东山记》云:“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修文馆大学士韦公……是日即席拜公逍遥公,名其居曰清虚原幽栖谷。”*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二六张说《东山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77页。此韦公即韦嗣立,其拜逍遥公一事,诸书皆云在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参见《旧唐书》卷七《中宗纪》、《唐诗纪事》卷九、《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因为修文馆大学士一般为宰相,而韦嗣立始为宰相在景龙三年二、三月间*《旧唐书》卷七《中宗纪》云:“(景龙三年二月)太府卿韦嗣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记为“二月”。《新唐书》卷四《中宗纪》:“(景龙三年)三月……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所记为“三月”。,所以他为修文馆大学士的时间,或当与此同步,不会迟得太久。

徐坚。张九龄《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云:“(神龙)二年,敕公修则天圣后实录及文集等,绝笔,中宗嘉之……迁刑部侍郎,加秩银青光禄大夫,转礼部侍郎,兼判戸部。”*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九一张九龄《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第2954页。《新唐书·儒学中·徐齐聃传》附《徐坚传》云:“俄以礼部侍郎为修文馆学士。”*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徐齐聃传》,第5662页。考察景龙中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发现徐坚景龙二年(708)秋季与宋之问、李适、李乂、卢藏用、薛稷、马怀素同作《饯许州宋司马赴任》*诸人诗见《文苑英华》卷二六七。,诸人皆修文馆学士,从徐坚官职及深得唐中宗赏识的情况来看,其时他可能已经成为修文馆学士。
韦元旦。《旧唐书》无传,亦未提及。《新唐书·文艺传》为其立传甚略,虽然《新唐书·李适传》云其为修文馆学士,但本传却没有提及,只云“舅陆颂妻,韦后弟也,故元旦凭以复进云”*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韦元旦传》,第5749页。,把韦元旦与韦后的关系作了交代,说明其进阶之由。考韦元旦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及作品系年情况,他在景龙二年(708)十二月曾与李适、阎朝隐、沈佺期、卢藏用、马怀素、崔日用等侍唐中宗游禁苑,疑其时已为学士。
徐彦伯。《旧唐书·徐彦伯传》云:“入为工部侍郎,寻除卫尉卿,兼昭文馆学士。景龙三年,中宗亲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赋》以献,辞甚典美。”*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四《徐彦伯传》,第3006页。《新唐书·徐彦伯传》云:“会郊祭,上《南郊赋》一篇,辞致典缛。擢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四《徐彦伯传》,第4202页。二者的差异在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作《南郊赋》前,已为修文馆学士;《新唐书》则云徐彦伯因《南郊赋》写得好,才被擢为修文馆学士。考两《唐书·中宗纪》,“南郊”事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唐诗纪事》卷九云:“(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幸温泉宫,敕蒲州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学士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九,第263页。后二者时间、空间都吻合,当无疑。至于《旧唐书》云徐彦伯为“昭文馆学士”,大概因其较其他学士任职时间长,在景云二年“修文馆”改为“昭文馆”时,依然在职。然即便如此,这样书写也甚不妥。
刘允济。《旧唐书·文苑中·刘允济传》云:“中兴初,坐与张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长史,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潜甚称荐之。寻丁母忧,服阕而卒。”*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刘允济传》,第5013页。《新唐书·文艺中·刘允济传》云:“坐二张昵狎,除青州长史,有清白称,巡察使路敬潜言状。以内忧去官。服除,召为修文馆学士,既久斥,喜甚,与家人乐饮数日,卒。”*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刘允济传》,第5749页。路敬潜巡察青州,在神龙元年(705)八月*《旧唐书》卷一百《尹思贞传》云思贞神龙初为御史大夫李承嘉所劾,出为青州刺史。“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特表荐之。”(第3110页)刘允济为尹思贞属官(长史),得路敬潜称荐,必当在此时。,刘允济母亡在其后,究竟何时亦不详。《新唐书·李适传》既云刘允济与徐坚、韦元旦、徐彦伯等为递补,且排于末座,其为修文馆学士不当早于诸人。《册府元龟》卷八九五云:“唐刘允济为青州刺史,中宗景龙四年征为修文学士,录才行至道,病卒,深为时人惜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八九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598页。说刘允济为青州刺史是错误的,但云刘允济景龙四年(710)被召为修文馆学士,却与事实相距不远*贾晋华先生认为刘允济卒于景龙二年(708),未知何据。参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于诗人群研究》,第44页。。刘允济虽然被召为修文馆学士,但未及到任就去世了。遍考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皆无刘允济,可见他虽称修文馆学士,但景龙年间并未进入过修文馆*王溥《唐会要》卷十一云:“垂拱三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左史直弘文馆刘允济上《明堂赋》。”可见刘允济曾当值于弘文馆(即修文馆),但其时非学士。。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此六人都是递补进入修文馆为学士的,徐坚、阎朝隐、韦元旦入选于景龙二年(708),韦嗣立和徐彦伯入选于景龙三年(709),刘允济入选于景龙四年(710)。
除了《唐会要》和《新唐书》记载的二十四位学士以外,景龙年间还有一些人任过修文馆学士,他们是李迥秀、褚无量、韦湑、崔日用、张说。为理清相关线索,亦作简考。
崔日用。《旧唐书·崔日用传》云:“时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递为朋党,日用潜皆附之,骤迁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第3087页。《新唐书·崔日用传》说得更详细:“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一《崔日用传》,第4330页。《唐会要》卷五十五载:“景龙三年,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曰:‘酒酣各为《回波词》。’众皆为谄佞之文,及自邀荣位。”*王溥撰,方诗铭等标校:《唐会要》卷五十五,第1115页。《唐诗纪事》卷十:“上宴日,日用起舞,自歌云:‘东馆总是鹓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万卷,何忍不蒙学士?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其日以日用兼修文馆学士,制曰:‘日用书穷万卷,学富三冬。’日用舞蹈拜谢。”*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十,第309页。《资治通鉴》卷二○九系此类事发生于景龙三年(709)二月,崔日用为修文馆学士当始于此时。
李迥秀。《旧唐书·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景龙中,累转鸿胪卿、修文馆学士。”*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2391页。《新唐书·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云:“中宗即位,召授将作少监。累迁鸿胪卿、修文馆学士。”*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九《李大亮传》附《李迥秀传》,第3914页。考李迥秀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与相关诗文,发现他于景龙二年(708)九月九日与诸学士侍中宗游慈恩寺,有诗《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景龙三年(709)八月、九月、十月皆参与修文馆学士活动数次。李迥秀身份特殊,地位甚高,疑此时已为修文馆学士。
褚无量。《旧唐书·褚无量传》云:“景龙三年,迁国子司业,兼修文馆学士。是岁,中宗将亲祀南郊,诏礼官学士修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皆希旨,请以皇后为亚献,无量独与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固争,以为不可。”*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褚无量传》,第3165页。《新唐书·儒学下·褚无量传》记载略同。明言褚无量为修文馆学士在景龙三年(709)。
张说。《旧唐书·张说传》云:“景龙中,丁母忧去职,起复授黄门侍郎,累表固辞,言甚切至,优诏方许之。是时风教颓紊,多以起复为荣,而说固节恳辞,竟终其丧制,大为识者所称。服终,复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第3051页。《新唐书·张说传》云:“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累迁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丧免。既期,诏起为黄门侍郎,固请终制,祈陈哀到。时礼俗衰薄,士以夺服为荣,而说独以礼终,天下高之。除丧,复为兵部,兼修文馆学士。”*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第4406页。据陈祖言《张说年谱》,张说景龙元年(707)十一月始丁母忧,两《唐书》既云“终制”,则复出当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杜佑《通典》卷八十一、卷八十七、卷一百等多处皆云古制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五个月。《旧唐书·张柬之传》载张柬之驳王元感,引《春秋》、《尚书》、《礼记》、《仪礼》等典籍,力证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时人皆认为张柬之所言合于礼典。,其为修文馆学士,也当在随后不久,很可能在十二月,此时他开始多次参加中宗及修文馆学士的活动。
韦湑。《新唐书·外戚·韦湑传》云:“湑初兼修文馆大学士,时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湑兄弟颇以文词进,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湑虽为学士,常在北军,无所造作。”*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六《外戚·韦湑传》,第5844页。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九云幸温泉事发生于景龙三年(709)十二月十二日,韦湑既在此时被毒杀,其为修文馆学士当更在此前。既云“帝方盛选文章侍从,与赋诗相娱乐”,韦湑已为学士,疑其入选在景龙二年(708)。
至此,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人选和入选顺序,已经相对明了。景龙二年(708)入选者有李峤、宗楚客、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乂、刘子玄、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赵彦昭、苏颋、沈佺期、阎朝隐、韦湑、李迥秀、徐坚、韦元旦,共二十三人。景龙三年(709)入选者有韦嗣立、徐彦伯、褚无量、崔日用、张说,共五人。景龙四年(710)入选者为刘允济,共一人。三年入选修文馆学士总数二十九人,与《玉海》所说的“学士二十九人”完全吻合。这似非偶然,景龙修文馆学士人选问题,并无太大疑问*《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韦叔夏传》云:“(神龙)三年,拜国子祭酒。累封沛国郡公。卒时年七十余……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文。”(第4965页)《新唐书》卷一二二《韦安石传》附《韦叔夏传》亦云:“(叔夏)卒,赠兖州都督、修文馆学士,谥曰文。”(第4355页)追赠修文馆学士,非实际授官,不当入“二十九人”之列。。
三、景龙修文馆各类学士员数考辨
景龙修文馆三类学士的实际员数,可能与最初计划并不一致,有必要进行考辨。
第一是景龙修文馆大学士的员数。《绀珠集》、《类说》、《唐会要》、《新唐书》、《资治通鉴》、《玉海》诸书,皆云大学士四员,《旧唐书》却云大学士八员。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旧唐书》记载有误,但从我们统计的情况来看,景龙年间至少有五位修文馆大学士,他们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韦湑。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因为大学士有资历上的要求。《新唐书》记修文馆时云:“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号馆主。”*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第1209页。馆主实即大学士,可见要做大学士,首先要有宰相的身份。据两《唐书·中宗纪》,景龙三年(709)三月,太府卿韦嗣立守兵部尙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兵部侍郎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见景龙二年(708)他们还不是宰相,不当为大学士。《唐会要》云景龙二年十月四日兵部侍郎赵彦昭为学士的说法,有一定依据。事实上,与赵彦昭、韦嗣立同时升为宰相的,还有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景龙四年(710)六月,修文馆学士岑羲,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见,整个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而为宰相者有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崔湜、郑愔、岑羲七人。韦湑虽非宰相,但身为外戚,为左羽林将军、曹国公,地位甚高,品秩不亚于宰相,为修文馆大学士也在情理之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修文馆学士的设置,背后的操纵者是上官婉儿,她与崔湜的关系又十分密切,崔湜因此为大学士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
但是,崔湜和郑愔只做了两个月的宰相,就因铨综失序,为御史所劾,黯然下台。韦湑本非以文采见长,景龙三年(709)为韦后所杀,岑羲为宰相不过七日,李隆基就发动政变,一举摧毁韦氏势力。因而,真正为当时人认可的修文馆大学士,其实还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四人。

学士一职,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五品已上,称为学士。”*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4页。上述十八人,全部满足了这一条件。所谓八人、十二人乃至十八人者,各有依据:八人是最初所定员数,十八人是实际任过学士的人数,十二人乃为十八名学士中因升格或其他原因退出学士后所余学士数*《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纪二十五》:“(景龙三年十一月)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湜、郑愔入陪大礼。”(第6637页)既云“前”,可见此时崔湜、郑愔二人已非修文馆学士。。
第三是景龙修文馆直学士的员数。《资治通鉴》云直学士八员,其他诸书皆云直学士十二员。《唐会要》中给出了五名人选: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新唐书》中除了此五人外,还增加了沈佺期和阎朝隐。此外,还有刘允济。恰好八人。《通鉴》所言,实有根据。需要说明的是,直学士也有资历要求,《唐六典》卷八云:“弘文馆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八,第254页。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五人皆符合六品以下这个标准,其他三人则需要考证。《唐会要》云薛稷为修文馆直学士时,官吏部侍郎,这可能是错误的。据《唐六典》,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与直学士一职相距太大。前引苏颋文云“门下中散大夫行尚书礼部郎中修文馆直学士河东县开国男薛稷”,陈冠明先生云:“授谏议大夫前为礼部郎中,则初为直学士时当是吏部郎中。”*陈冠明:《苏味道李峤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意即吏部侍郎为吏部郎中之误,此说可从。吏部郎中、礼部郎中皆从五品上,也已达到学士的资历要求,他为直学士是个特例。另外两位,阎朝隐为著作郎,刘允济为上州长史,皆从五品上,按照惯例,亦可为学士。但他们与前面的诸位学士相比,则品秩偏低,故只能为直学士。由此亦可看出,景龙年间修文馆直学士的地位不低。
《唐会要》及《新唐书·文艺中·李适传》中关于修文馆学士种类和员数的记载,一向为人所重,多被引证,而出自《景龙文馆记》的所谓三类学士象征“四时、八节、十二月”的说法,在学界也甚为深入人心。然而,由以上考辨可知,这些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倒是在此事记载上令人困惑的《资治通鉴》,给出的信息虽然有限,却相对准确,符合司马光著史的谨严作风。至此,关于三类学士及其员数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给出大致清楚的结论: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学士,最初的计划可能是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或意外,三类学士实际员数都与原来计划不符,甚至出现一定的反差,这导致后代史书记载此事的讹乱。完全复原虽不可能,但大致面貌依然可以辨析。
四、景龙修文馆宫廷文学之评价
修文馆不是唐景龙年间突然出现的,它从唐初就有了。据《唐六典》卷八,武德初置修文馆,学士无定员,武德末改为弘文馆,神龙元年(705)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为昭文,神龙二年(706)又改为修文,景云二年(711)改为昭文,开元七年(719)又改为弘文,隶门下省。其职能是典校理,司撰著,兼训生徒。显然,修文馆学士本质上是学者而非文学家。
但是,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及其学士与此前有了一些显著不同。第一,学士员数在理论上固定了。固定学士员数的意义,在于学士选拔的标准提高,学士成为崇高的荣誉而为官员所格外歆羡。如《旧唐书·宋之问传》云:“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宋之问传》,第5025页。又如前文所引《唐诗纪事》卷十所载崔日用求为学士一事,崔日用身居御史中丞,却羡慕修文馆学士,而且有“鹓鸾”、“杞梓”之喻,不难看出成为修文馆学士是何等荣耀的事情。第二,修文馆学士的职能已经不再是校理、撰著典籍及教习生徒,而是大量参加文学活动。说到这一点,不能不说一下唐中宗。唐中宗自己的文学水平如何,很难判定*《全唐诗》收唐中宗诗七首,是否有他人代笔,不详。《全唐文》收唐中宗文二卷,主要是朝廷公文,当非其自作。,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对文学活动的扶持、推动,令人称奇。从景龙二年(708)四月增置修文馆学士起,到景龙四年(710)六月他被鸩杀止,短短两年余,以他为中心的大型文学活动近六十场。这个时期的修文馆学士,主要任务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游乐活动,并用诗的形式将其记录与描写。创作于这两年间的数百首宫廷诗歌,目前依然在流传。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贾晋华先生和陶敏先生已经做得非常深入,不再赘述。
有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有这么多天才文人参与创作,景龙宫廷文学本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而事实上却大谬不然。
首先,景龙宫廷诗人本身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创作出什么优秀的作品。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张说、苏颋等人,在整个唐代,都算得上优秀的诗人,然举凡李峤的《汾阴行》,宋之问的《度大庾岭》、《度汉江》,张说的《邺都引》、《灉湖山寺》、《蜀道后期》,苏颋的《汾上惊秋》等,这些代表性的优秀诗篇,几乎无一产生于景龙年间。虽然杜审言此间作有《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为人称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他此前所作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度湘江》、《送崔融》等相比。沈佺期的《奉和韦嗣立山庄应制》,是景龙年间奉和应制诗的代表,如将其与他的《独不见》、《夜宿七盘岭》、《杂诗·闻道黄龙戍》等比较,质量上的差距亦不啻云泥。可以这样说,景龙修文馆的文学活动,至少在创作的题材上没有给文学家带来刺激,千人一面的颂扬,迫于情势的阿谀,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和活力。景龙修文馆学士的生活面十分狭窄,他们几乎成年累月地生活在以唐中宗为代表的聚会游宴中,辗转于宫廷、贵族庄园、游乐场所,醉生梦死。当文学家被“饰以金镳,飨以嘉肴”式地“圈养”之后,就失去了创作所必需的“长林丰草”,野性渐失,纯真渐去,只按照“套路”来粉饰太平,虚应故事,灵感的钝化在所难免。
其次,以景龙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风气,压抑了此前出现的进步文学潮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从梁代中期到唐景龙年间,宫廷文学走过了近一百八十年的历史,其弊端早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初唐四杰不仅以创作上的实绩,向宫廷文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而且都有理论批评,卢照邻的《南阳公集序》、《乐府杂诗序》,骆宾王的《和闺情诗启》,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的《王勃集序》等虽然各有侧重,但无一不在表达对流行于世的宫廷文学的强烈不满。盛唐以来,初唐四杰获得了崇高的文学地位,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却一直沉沦下僚,这当然有多重原因,然与主流文学观念的分歧,也是不得不予考虑的因素。四杰并不孤独,一定程度上,“方外十友”呼应、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文学主张。“方外十友”中包含了高宗后期到武周年间非常著名一批文学家如陈子昂、宋之问、杜审言、卢藏用,他们曾经意气风发,以文学之天下为己任。陈子昂在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文学现象大加挞伐,标举汉魏风骨,其《感遇诗》三十八首及《登幽州台歌》等作品,则全面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卢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比陈子昂更公开、直接地指斥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文学:“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卢藏用对陈子昂的创作推崇之极:“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三八《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第2402页。至于宋之问和杜审言,虽没有什么创作理论名世,但却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呼应着陈子昂们的文学主张。
然而,历史显示出极具讽刺性的一面。陈子昂死后,卢藏用、宋之问、杜审言无一例外地加入宫廷文学作者队伍,并在景龙年间成为修文馆学士,创作他们曾痛加贬斥的那类没有性情、堆砌辞藻的官样作品。大约人到中年,面对人生挫折,仕途蹭蹬,曾经的锐气与锋芒已大为减弱,甚至为了功名利禄不免讨好、谄媚那些能决定他们命运的权贵。此时此刻,距离他们曾经慷慨激昂地追求的“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不仅非常遥远,甚至完全对立了。显而易见,以陈子昂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活动,在武周时期已备受摧残,在景龙时期则全军覆没。有鉴于此,说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延缓甚至阻碍了初唐文学的健康发展,大约是不该有什么疑义的。
第三,修文馆学士为代表的宫廷文学活动,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文坛创作风气,部分屏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妨碍了新兴文学的发展。《旧唐书·文苑中·贺知章传》云:
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朝万止山阴尉,齐融昆山令,若虚兖州兵曹,巨监察御史。融遇张九龄,引为怀州司户、集贤直学士。数子人间往往传其文,独知章最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贺知章传》,第5035页。
来自南方的一批优秀诗人,其中不乏贺知章、张若虚这样留下千古绝唱的诗歌圣手,在神龙、景龙年间几乎湮没无闻,如果不是开元诗歌春天的来临,也许文学史上都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须知,贺知章在武周证圣元年(695)已中进士,到景龙年间已入官场十数年,年已半百,在文坛却寂寂无闻,很可能是他的创作与当时宫廷文学的趣味不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整个唐朝都不为人所重,可能是此人在宫廷文学甚嚣尘上的时代,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旧唐书·贺知章传》还记载了一件事:“神龙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诗,蹉跌不偶,六十余,为宋州参军卒。”*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中·贺知章传》,第5035页。一个擅长五言诗的诗人,于今却一首诗都没有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著名诗人员半千,也是此中典型,他在武周初期,两为弘文馆学士,因忤张易之兄弟和武三思,先后被外放,景龙年间增置修文馆学士,亦无其份,作品零落殆尽。李登之、员半千跟南方文人一样,因为他们的为人与创作皆与上层宫廷文人异趣,不可避免地遭到排斥,作品只能在小范围流传,亡佚在所难免。
景龙修文馆学士在唐中宗扶持下大搞宫廷文学活动的时候,著名诗人张旭、张九龄、王之涣、孟浩然等皆已成年,但其创作成名皆在开元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与景龙宫廷文学风尚格格不入。
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的文学创作,说到底是应酬文学,是游戏文学,真感情不多。喧嚣浮躁的景龙文坛,没有产生经典名作,这是不争之事实。景龙文人诸多集会,相互交流,大量创作,使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高。但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究竟从景龙宫廷诗歌的形式和技巧上得到多少助力,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 论
关于景龙修文馆学士的记载,现存文献互相矛盾之处颇多。一些典籍拘泥于《景龙文馆记》所谓的“大学士四人,象四时;学士八人,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象十二月”的记载,将员数与入选为学士者严格对应,结果方枘圆凿。事实上,增置学士的计划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过程又是一回事,两者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同一人可由学士升大学士,如赵彦昭;可由直学士升学士,如薛稷。经过考证,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总人数为二十九人,皆可一一对应到具体人选,其中可考大学士五人次,学士十八人次,直学士八人次,共三十一人次,但其中赵彦昭与薛稷一身二任,所以依然为二十九人,与《玉海》叙录《景龙文馆记》中的学士数完全吻合。景龙年间的修文馆学士,地位很高,影响甚大,历代史家都不可避免地予以关注。但是,修文馆及学士的设置,是持续进行的,计划的同时,常常又有变化。用静止的眼光,仅仅依据某一特定时期的记载,来推断修文馆大学士、学士、直学士的员数和人选,往往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即便是躬逢其时且入选修文馆直学士的武平一,所记也不能完全体现此期学士设置的具体实际。因而,结合存世的相关文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恢复历史事实的原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兼具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景龙年间的宫廷文学活动,延续了武周时期的繁荣,甚至在频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充分体现了以唐中宗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热情。正是他们的积极提倡,才使当时社会上弥漫着崇尚文学创作的风尚,这对于初盛唐文学的良性发展,具有宏观引导的意义。但是,景龙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质量,较之此前的武周时期,并没有什么提升,更不能与随后的盛唐文学相提并论,在文学史上难免地位尴尬。景龙修文馆学士中,不乏文学名家,但他们在景龙年间鲜有佳作,可见此时的文学生态出了问题。一些不利于文学发展、创新的因素,日渐凸显,制约了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客观而言,景龙修文馆学士的文学活动只能算是应酬与游戏,没有产生经典作品。不仅如此,还压抑了此前出现的创新性文学潮流,使进步的文学家及相关创作理念,逐渐走向边缘化,部分屏蔽了与之旨趣相异的文学创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文学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渭卿]
胡旭,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倩,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