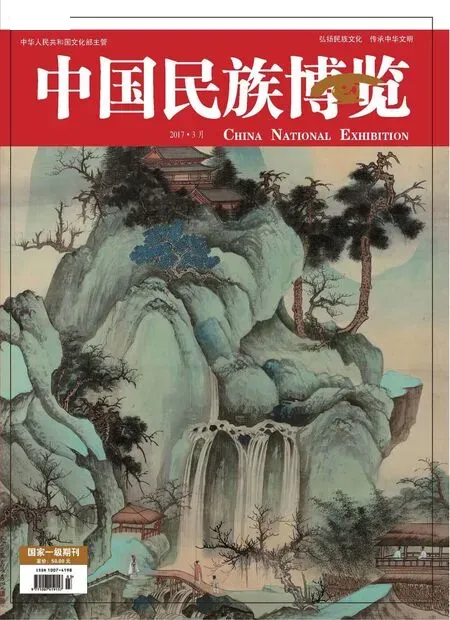山峡行者与沙漠孤驼
——艾芜与三毛流浪情结比较
2017-02-01高玉珠
高玉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山峡行者与沙漠孤驼
——艾芜与三毛流浪情结比较
高玉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流浪情结是古今中外作家热衷表现的原型母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艾芜依托滇缅流浪经历创作的《南行记》中短篇系列大放异彩,流浪情结贯穿异域之行。时隔半个世纪,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的台湾女作家三毛凭借《撒哈拉的故事》等作品再掀“流浪热”,流浪情结同样流溢于字里行间。同为红极一时的流浪文学,却包含迥异的流浪情结,艾芜如同山峡中乐观的行者,三毛则似沙漠里孤独的骆驼,本文从流浪的缘起、心态、归宿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二者的流浪情结。
流浪情结;艾芜;三毛;缘起;心态;归宿
曹文轩曾说“流浪是人类自可以被称为人类的那一天起,就与身俱来的命运”[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游走于绮丽神秘的滇缅边境,创作了独具特色的流浪名作《南行记》系列。时隔半个多世纪,流浪情结在台湾女作家三毛那里再放异彩,足迹遍布亚非欧美五十多个国家的三毛,创作了《撒哈拉的故事》一系列异彩浓郁、斑驳陆离的流浪作品。
一、流浪的缘由
不同的流浪经历背后蕴含不同的心理机制,曹文轩将流浪文学作品中流浪的缘由归结为五种:将流浪作为体悟人生、识其真面目的一种方式;由文化的衰竭与断裂生成的流浪意识;浪漫主义者的大情趣; “边缘人”的流浪;形而上的精神追求。[2]这种分类较全面地概括出不同价值取向下的流浪行为,若将三毛和艾芜的流浪缘由加以比照,艾芜的流浪回应了现实主义者渴望认识社会的责任感,是一种乐观的“入世”态度,三毛的流浪则倾向于形而上的精神求索,蕴含孤独的“出世”的情怀。
(一)艾芜——坚定的光明追求
生逢战乱、长于川西的艾芜与同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深受五四新风的洗礼,“科学、自由、民主”等激奋人心的信念激荡在年轻气盛的艾芜心中,“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人生哲学的一课》)而婚姻包办直接触发了他行走他乡的行动,年轻的艾芜注定在滇缅边境留下独特的脚步。带着对自由的信念与对理想社会的渴望,艾芜的脚步勇敢且坚定。艾芜的流浪源于一种“不甘屈从于固有环境的限制,挣脱命运摆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漂泊者的价值取向”。[3]
激励艾芜扬帆起航的是他对新世界的向往与对光明的希望。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流浪有具体事件的触发——婚姻包办。婚姻包办对新青年艾芜来说不仅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之事,更是对自由精神、平等人格的压迫,这种流浪因而有一种愤然而起的反叛意味。另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流浪只会短暂歇脚但没有永久停留。或驻足在西南边陲小镇、或扎脚于松岭上的木屋、或徘徊于克钦山中的茅草地、或混迹于山峡密林中的强盗团伙……目睹“吃人”旧社会的不公和下层人民的举步维艰,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艾芜向往着红日初升的地方,他像目光坚定的行者,奔向朝阳冉冉的理想国。
(二)三毛——形而上的精神求索
如果说艾芜的流浪带有一种西天取经式大团圆的自信,三毛的流浪则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本源意识和宿命选择。“流浪是三毛的灵魂,三毛的骨子里有着彻底的流浪意识,这是非常纯粹的风格,包含了三毛所有的真情实感”。[4]不同于艾芜怀抱着斗士般的乐观上路,三毛的流浪显示出一种生命必然性和孤独气质。
与艾芜不同,生长于和平时代、家境殷实的三毛,不具备非流浪不可的外在诱因,三毛的流浪产生于她早谙生命的孤独本质。三毛小时候曾患有自闭症,不愿与人交往,对于颜色、线条与旋律的热爱远胜于生活俗事,熟读红楼,精通音乐,早味生命本质,人生逃不过的失落感和孤独感早已看在眼里。因此即便太平盛世,歌舞升平,锦衣玉食,也如她自己所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对生命虚无的敏锐知觉让三毛明白,孤独是个体存在的必然状态,而流浪则是她抵御和消解孤独的方式选择,黄沙滚滚的撒哈拉沙漠、宁静平和的加纳利海岛、生机勃勃南美洲高原,中东文化、西洋文化等大千世界的风情以生命的本色充实着三毛对人生的体验,极具浪漫情怀的三毛如同沙漠孤驼注定踏上流浪之路,在流浪中寻找慰藉心灵的一方绿洲。
二、流浪的心态
同样身在流浪之途,艾芜与三毛却持有近乎迥异的心态。艾芜如同山峡行者,斩荆除棘,且行且歌,热衷于表达对生命力的建构;三毛则如同沙漠孤驼,形只影单,长途跋涉,常常体现为对存在的解构。
(一)艾芜——斩荆除棘的行者
艾芜的《南行记》系列中渗透蓬勃的生命力和原朴的自然力,流浪生活险象环生,但艾芜在作品中表现出愈挫愈勇的“铜豌豆”精神,正如《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说“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地顽强生存”。
这种勇敢自信的心态集中体现在作品塑造了一个顽强坚韧的流浪者形象。艾芜笔下的流浪世界以其异域色彩引人入胜,但新奇瑰丽是建立在乱世西南的险山恶水中的,一路上流寇、小偷、强盗甚至杀人犯比比皆是,“我”甚至为求生存不得不加入强盗团伙,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芜杂的社会环境的双重威胁下求生,没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单枪匹马很容易沦为自然或社会的俎上羔羊。而“我”却是怀着勇气与悲悯深入其中,体味底层的民情民怨,见识大千世界的真模样,始终不忘初衷。
(二)三毛——甘苦人世的体味者
对应于三毛流浪缘由中的生命悲情意识,三毛的流浪作品始终萦绕一种“诚惶诚恐”、挥之不去的隐忧,即便中途稍作停靠,对于归宿的渴望与对生命的怀疑总使流浪平添几分甘苦清味。
首先,从情节来看,在表现底层人民疾苦生活的同时,艾芜会突出生命的张力,具有导人向上的倾向,“注重揭示现实生活中可爱的一面,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使人热爱生活”,[5]三毛笔下则没有那么多的强悍与自信,去除口号式的宣传,带着心绣莲花的细腻和与生俱来的悲悯,真实朴白地记录所见所感,悲情意识贯穿始终,孤独,是自由如三毛也无计可施的结。《撒哈拉的故事》中,三毛不吝笔墨描写了一群撒哈拉人,他们是属于沙漠的最原朴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原始而粗劣,带有脱离现代文明的野蛮,如果按照艾芜的方式,应该用现代精神予以开化,而三毛选择做冷静的旁观者,《芳邻》里蛮不讲理的邻居、《沙漠浴记》里肮脏的洗澡方式、《娃娃新娘》里的十岁新娘,三毛以理解与同情的笔触记录生命、尊重生命原貌。其次,从作品流溢的情感来说,三毛的不安定感从未随着流浪甚至是定居有所稀释,即便回到前世故乡撒哈拉,有挚爱荷西相伴,三毛的灵魂亦从未定居,如她所说:“谁喜欢做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呢?”(《万水千山走遍》)漂泊之感始终萦绕眉头心上。
三、流浪的归宿
日归西,鸟归巢,落木归秋,流浪的人儿也将投往心中的归宿。艾芜走向心中光芒万丈的明天,是食指《相信未来》的节奏;三毛则返璞浪漫的心灵境界,流浪于齐豫《橄榄树》的旋律。
(一)艾芜——遒劲古树生山峡
坚持体味社会、寻找光明的初衷,怀着对未来的乐观,艾芜的归宿清晰明朗,如同山峡两侧遒劲生长的古树,坚韧挺拔,决意迎接那束灿烂的朝阳,艾芜最终将定居在他向往的光明社会。
作品中已有象征性意象隐含这种归宿意愿。一方面,赞颂自然的蓬勃生机,树木葱茏盘曲遒劲、江水奔腾咆哮汹涌、山峰高耸直插云霄……自然意向充满原始野性,越是萧森冷寒,生命越是恣意喷薄,艾芜贪婪呼吸着这大口的生命气息,这也是他心之所向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可以与黑暗社会相抗衡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上,尽管生逢战乱、身世坎坷,艾芜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强盗,也唱出自己倔强的向往。
(二)三毛——橄榄一枝入梦来
契合于流浪心态上的悲情意识,三毛流浪的归宿染上了渺远而模糊的味道,那不是一个具体清晰的所在,这种精神层面的、超越具体现实的流浪,终归要落脚到自然浪漫的心灵上。
在1967至1991之间20年的流浪生涯里,三毛盘桓于亚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值得注意的是三毛流浪撒哈拉沙漠的一段经历,三毛确曾在这一被她称为“前世的故乡”里体会过一生稀缺的归属感,即便这停留对于孤独的生命本质杯水车薪,却可从蛛丝马迹间窥见三毛所向往的理想归宿。她曾说“我不是刻意流浪……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中安定下来”。(《梦里花落知多少》)这种“安定”就是精神的归属。荷西的陪伴与守护带给三毛前所未有的踏实,坚实的臂弯使漂泊的灵魂感受到融融暖意,炽热诚挚的感情抚慰了心中的不确定。另外,撒哈拉这片故土也给了三毛归属感,三毛的灵魂与自然产生了共振,生命找到了舒服适宜的存在状态,“敏感的心灵以内在情感的律动感应着自然万物,在这种溶合境界中,三毛已脱开了物身人形,超越了时空域限,获得了精神生活的充分自由”。[6]这种归宿摆脱了娜拉式离家的低级,呼应海子麦田式的守护。
四、总结
艾芜如山峡行者,行走于绮丽神秘的滇缅边境,准备拥抱红日初升的第一缕阳光,步履坚定地走在寻找光明的漂泊之路;三毛似沙漠孤驼,找寻于黄沙漫漫的滚滚红尘,自由的灵魂终将沉眠于梦中橄榄。尽管蕴含不同的流浪情结,却怀揣着相同的浪漫情怀,做着同样清澈澄明的梦,流浪者永不停歇。
[1][2]曹文轩.论近二十年来文学中的“流浪情结”[J].文学评论,2002(4):151-157.
[3]黄建章.从《南行记》透视艾芜的“漂泊情结”[J].新世纪论丛,2006(2):127-130.
[4]孙予青.沙漠中飘扬的影子——论流浪意识在三毛作品中的独特性[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3):45-48.
[5]张效民.艾芜谈他的创作[J].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2(1).
[6]吴娜.三毛的流浪情结[J].咸宁学院学报,2007(5):89-90,125.
I206.7
A
高玉珠(1995-),女,汉族,吉林省集安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