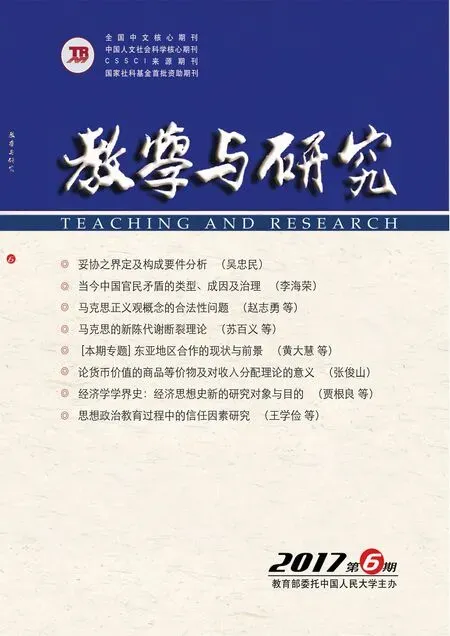劳动与工作,可以是“政治的”吗?
——阿伦特《人的境况》批判解读
2017-01-31文兵
文 兵
劳动与工作,可以是“政治的”吗?
——阿伦特《人的境况》批判解读
文 兵
劳动;政治;工作;阿伦特
阿伦特对劳动、生产与(政治)行动在概念上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劳动只表明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同之处,因而与政治自由无关;而生产过程是离不开“目的—手段”范畴,也必然与政治自由的特性相抵牾的。她对马克思提出了相应的批评。从根本上来说,阿伦特概念分析是反历史的,她要求回到古代希腊的原初政治经验中去,即在政治中排除劳动与生产。这不仅与古代希腊的真实历史相违,而且其理论自身亦有不少谬误。
阿伦特在1958出版的《人的条件》一书,认为人类的“积极活动”包括了劳动、生产和行动,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条件。她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了著名的区分。她认为,劳动是与人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提供的只是生存所需的消费物品;工作则是与人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提供的则是“人造”的事物世界;行动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创建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公共空间。阿伦特认为,在古代希腊,只有行动,即政治生活,才被视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不仅如此,劳动、工作都是不能纳入政治之中的。但是,现代的思想颠倒了全部的传统,颠倒了积极生活之中的各种活动的等级。阿伦特认为,古代希腊的原初政治经验才是政治概念的本真意义,而现实的一切都是远离它而去的。阿伦特长于概念的分析,她在概念上对劳动、工作与行动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对于思维的严谨来说是必需,但概念的严格区分绝不是现实的绝对对立。但可惜的是,虽然她提出了极有意义的问题和极有启发的思想,但用概念去剪裁现实、用概念的关系去取代历史的逻辑,必然使理论难以令人信服。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最近二三十年来在西方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人的境况》是其最为哲学、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值得我们对其进行必要的考察。
一、劳动与政治
阿伦特在谈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时,曾有这样的判断,认为马克思对于劳动充满着“颂扬和误解”,而他的颂扬基于他的误解,即“根本没有看到人类生活的最根本的现实”。[1](P113)这个最根本的现实,在她看来,就是政治行动所特有的“自由”。她进而断言:马克思“对自由或正义并没有兴趣”。[1](P12)应该说,马克思对于劳动(也包括阿伦特所区分的“工作”)确实充满着“颂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劳动规定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并提高到人的本质这一高度。虽然马克思其后放弃了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表述,但一直是把现实的生产劳动视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内容和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很清楚:“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P22-23)阿伦特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是在劳动中看到基本的人性,而这就使他与传统区别开来,因为“传统总是排斥劳动,认为劳动和完整而自由的人类存在互不相容”。[1](P112)因此,阿伦特声称,将人界定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马克思是第一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马克思提及“劳动动物”的时候,并不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而恰恰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也就是在劳动异化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他在批评国民经济学时所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3](P125)阿伦特则认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劳动并不是人的特性,“人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动物生命共有的东西,都不被看成是属于人的”。[2](P62)“劳动”与“动物”是可以直接划上等号的。阿伦特虽然说这是“古代希腊”的观点,但确实也是她所维护的。但这样一来,从逻辑上来看,阿伦特就有些混乱了:劳动既然不被看成是属于人的,何以列入到人的“积极生活”的三种形式之中呢?
阿伦特把劳动与行动对立起来,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严格划分开来,宣称:“在希腊政治意识的根底处,我们发现这两种生活的区分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清晰阐述。所有只服务于谋生或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被允许进入政治领域。”[2](P22-23)阿伦特的“政治”概念与我们的理解不同,她是在古代希腊所理解的“政治”概念上加以使用的。她认为,在古代希腊,“政治”与“城邦”具有相同的意义,指的就是城邦的公共生活。但是,不论她如何理解,这种对立在事实上并非古代希腊的政治经验。普鲁塔克对于梭伦有这样的记载:“他看到本国土地只能维持耕种者的生存,不能维持大量没有生业的闲人,因此,他把一切行业都看得很高贵,要元老会议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没有行业的人。”[4](P19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希腊的实际的政治经验中,生计、谋生、劳动就是政治的问题。在一百年后的雅典由盛转衰的关头,在面对伯罗奔尼撒人的入侵时,伯里克利就是这样来动员他的人民:“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5](P145)在伯里克利这里,保护国家的安全,是人们利益所在,城邦政治关乎着人们的生计、谋生和劳动。阿伦特对伯里克利演说的实质却是这样的阐发:“在伯里克利的表述中十分清楚的是……行动和言辞的最内在意义与成败无关,与最终结局无关,也不受效果好坏的影响。”[2](P161)按她的说法,伯里克利诉诸“伟大”就可以把雅典民众煽动起来。可以说,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反直觉的。在古代希腊,劳动并不是被完全交付给奴隶。按照艾伦·伍德的研究:“历史学家通常都赞成大多数雅典公民为生计而劳动的观点”。[6](P185)虽然希腊城邦完全符合“奴隶社会”的特点,但自由劳动者仍然是雅典民主的支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中,就曾探讨过以农民或以牧民为城邦主体的各类“平民政体”。如果人数远远超过奴隶的为了生计的自由劳动者,在他们的政治讨论之中根本不涉及利益,不涉及生计、谋生和劳动,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将出于生计的劳动与出于政治的行动进行概念上的区分,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现实中将两者截然分开,把两者当成“截然有别、独立存在”的实体。阿伦特只是承认了劳动是政治的前提,但就是不承认劳动也是政治的议题。阿伦特就是要反对政治的功能化,也就是反对政治为经济服务。因此,她就反对“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提法,认为它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因为,任何“经济的”事情,即与个人生命和种族繁衍有关的一切,都是非政治的。
二、政治与经济
政治是否可以与经济脱离开来?经济领域中的剥削、贫困、分配不公等,是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艾伦·伍德有一个批评:把政治与经济脱离开来,正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而这一发明也是使“政治”更好地为“经济”服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是由政治所造成的,生产者遭受着“超”经济力量的剥削。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遭受着独立于其政治地位之外的“纯”经济力量的强制,这就造成人们这样的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们在社会经济上的也就是实质上的不平等可以与在政治上的也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共存,似乎经济与政治可以脱离开来。在艾伦·伍德看来,这种脱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任何经济关系都是受法律保护的。经济与政治的这种脱离,实际上是更加无视了生产与分配领域的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经济的分离实际上是政治领域内部的分化,这种概括从某些方面来说更适于解释西方发展的独特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特性。”[2](P31)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经济科学”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极度的傲慢,因为这样的表述暗示了它比其他社会科学更高的科学地位。他更喜欢“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表述,因为这样的表述“传递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唯一区别:其政治、规范和道德目的。”[7](P592)他宣称,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在研究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国家的理想作用,要解决的是何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领我们更加接近理想的社会。
阿伦特认为,如果经济与政治两者的界限模糊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政治组织会依照家庭形象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必然使可以自由行动和言说的政治空间丧失。古代的“一人统治”的君主制(one-man ,monarchical rule),正是按家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其表现形式正是只有一人观点、一人利益的专制主义和绝对主义。这种“一人统治”君主制后来又转化为“无人统治”的官僚制,但这种官僚制可以说是“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2](P26)因为这种制度期待它的成员遵从某一行为,并用过程规则来“规范”它的成员,进而消除各种自发的行为和出众的成就。阿伦特对于劳动的轻视,根本地还在于劳动建立在人的同一性之上,抹煞了人的差异性。在她看来,正是在劳动中,生物节奏与集体劳动的统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感到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跟所有其他人相连的一份子。”[2](P167)这也就是消除了人的复数性,而复数性正是政治的特性,因为政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中的人,是一个独特差异中的人,是在言说与行动中确证自己的。阿伦特的这个比附有些简单了。在一些简单的谋生劳动中,也是存在着分工上的差异。而在复杂的政治行动中,也应该存在着协同上的一致,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说,政治行动中必须有人们聚集在一起“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如果没有这种“一致”,任何政治的目标都是达不成的。
阿伦特贬低劳动,还因为在她看来,劳动受生命必然性的支配,因而具有奴性,而行动则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就是自由的。她认为,政治行动总是具有不可预期性,具有开端启新的作用。这里的问题是,政治领域是不是就不存在必然性?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妇女就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至少她们没有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妇女的政治解放才成为可能。“因为资本正在努力地把人们吸引到劳动市场,并把他们简化为从所有特殊身份中抽象出来的可相互交换的劳动单位。”[6](P263)政治领域的必然性,其实就是政治领域的被制约性。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P699)这种“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正是人们政治行动中的必然。
三、工作与政治
阿伦特认为工作与劳动的区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工作与行动的区分。她反对以工作来取代行动。因为,工作的制作过程完全是由手段与目的的范畴来决定的。目的不仅证明手段的合法性,目的还创造和组织手段。对于技艺工匠(homo faber)来说,目的证明了对自然施加暴力以获得材料的正当性。阿伦特的推论是,如果以制作来解释行动的政治规划或思考,必然要把暴力置于核心位置。在现代的观念之中,暴力本身受到了颂扬。在她看来,除美国革命之外的所有现代的革命,都是充满着对于为新政治体奠基的热情,也充满着对于暴力之作为“制作”它的手段的颂扬。阿伦特对于暴力的使用及其结果,是极为警惕的。她对权力(power)与暴力(violence)等进行了区分,认为权力是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东西,因为“权力是从一块行动的人们中间发出的力量,他们一分开散开,权力就消失了。”[2](P157)阿伦特对于“权力”的阐释与传统政治哲学很不相同。这个权力,在她那里,其实就是人们在言说与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力量,是由人们“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阿伦特接着指出,暴力很容易摧毁权力,但并不能代替权力。唯一可以取代权力的就是强力(force)。强力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用它反对他的同胞的,是可以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通过暴力加以垄断的力量。而一旦强力与暴力结盟,那就是出现“专制政体”。暴力虽然与革命有关,但是,暴力之被颂扬,则完全有可能导致极权政体,这正如她在后来的《论革命》中说的:“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不仅法律……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8](P8)她之所以对美国革命有较高评价,是因为在她看来,在美国的立国者眼中,“新政治体乃是为人民而设计”,而这个“人民”是复数的。因此,在美国的立国者那里,他们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没有效仿法国革命者乐此不疲的对“公意”的追求,因而也就避免了法国那样的“恐怖统治”。在她看来,让语言交流沉默,让复数的人消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制作”本身的特性。制作,就是个人“从头到尾是他行为的主人”,“以制作代替行动的尝试,体现在所有反‘民主制’的论证中,这些论证无论多么铿锵有力和首尾一贯,都会转化成一种拒斥政治之本性的论证”。[2](P172)
“制作”,其实也就是“创造”,故而,阿伦特不同意马克思关于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观点,因这种“制作”是以目的—手段的范畴进行思考的,除了导致现代以来的对于暴力的颂扬之外,还会衍生一种乌托邦的政治体制,因为这种乌托邦正是“一个由精通了人类事务技艺的某个人依照模型而造的”。[2](P177)这种乌托邦的构想,虽然鲜有成功,但却构成了一种政治思想的传统。我们在这里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目的-手段”范畴是否根本不可能存在于政治思考之中。
如果“创造”历史的“人民”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主体,有着特殊的人格,有着自己的头脑,有着清醒的目的,就像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工匠一样,那就真如“上帝”一般了。如果是这样,阿伦特把“人们创造历史”说成就如“上帝创造自然”一样,这种比附就完全是可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人民”事实上是找不到的,是不可想象的。就“人民”之中的每一份子来说,他在参与历史活动过程中没有自己的意识和目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不追求自己的目的,言语表达就成了纯粹的自说自话,而政治行动就成了纯粹的布朗运动。事实上,“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295)而且,在历史过程之中,目的从来不是结果,人们像工匠一样“制作”出预期的历史结果,从不是马克思所坚持的。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历史活动中的许多个人的意志相互之间的冲突,“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9](P605)在这一点上,阿伦特也肯定政治行动一旦开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无法预料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每一个体或某些集团在政治行动中都有着自己的明确的目的。
按阿伦特的说法,在政治领域中,言说与行动仅是为彰显行动者“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身份。”[2](P142)而马克思的基本错误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按她的说法,如果不是彰显行动者的这个“who”而只是他的“what”,即不是彰显他的人格而只是他与其他人共有的属性,行动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质而变成了诸种成就之一,也就是变成了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正如制作成为生产一个对象的手段一样。她也肯定,在言语与行为中,人们必定会关涉到他们活动于其间的事物世界(阿伦特对劳动与工作的区分,最重要的一点是,劳动的产品直接进入了消费,没有持久性,因而是“无世界性”,而工作的产品具有持久性,因而构成了一个“事物世界”),而正是从这个世界之中产生出人们特定的客观的实际利益,但言语与行为仍然不失其揭示行为人的能力。我们要追问的是,言行与利益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在她那里,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她反对政治的功能化。这样一来,政治就完全漂浮在空气之中了。
阿伦特反对政治功能化的这些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被人们所重视。很多论者认为,她的理论术语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了自1989年“天鹅绒革命”以来的历史事件和政治现象,即人们似乎只是“为了政治自由而战”。[10](P106)这种说法,不仅是有些行动者所声称的,而且也是有些观察者所描述的。但事实果真如此?所有的这些所谓的“革命”,皆是要实现明确的政治主张,要达成明确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要获得所谓公民权利。哈维尔在领导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之前,就在其1977年作为政治鼓动即所谓“七七宪章”中,明确地宣示他们的“宪章”就是为了促进“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实现”。这里不仅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而且把“生活”与“工作”也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
阿伦特非常看重政治行动所具有的开端启新的能力,认为这个行动过程一旦开始就带有不可预测、不可逆转的复杂后果,因而是人们所不能主宰和把控的。这样一来,政治行动中的人,似乎有一种存在的荒谬:既是自由(freedom)的但不是自主(sovereignty)的。她认为,这种荒谬,只是因为传统思想将自由与自主相等同。阿伦特声称,在行动能力本身中就包含着某种潜能,可以让它幸免于非自主的无能:对于不可逆性来说,则是给予宽恕的能力,它可以让我们摆脱我们无法补救的后果,可以中止无休止的相互伤害行为;对于不可预见性来说,则是信守承诺,以契约和协定为中介把人们约束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共同同意的目标。阿伦特关于宽恕与承诺这部分论述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就宽恕来说,虽然具有宗教的背景,但将它直接转到政治领域,则是她的重大贡献。她的学生杨-布鲁尔声称:“自从1958年《人的条件》问世以来,阿伦特对于宽恕的思考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2](P78)杨-布鲁尔甚至认为,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就是她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就承诺来说,阿伦特则认为,它是人建设世界的能力,而美国人在革命行动中发现了正是“通过一项承诺,即宪法来确保自由的可能性。”[2](P88)她认为这是美国政治中的“最伟大的发明”。阿伦特认为,宽恕与承诺“就像是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全新的、无尽的进程。”[2](P191)更为重要的是,由嵌入了宽恕与承诺的行动和言说能力,赋予了人类事务以信心与希望,但是,“信心与希望这两个作为人存在的根本特征,却被古希腊人完全忽视了”。[2](P192)如果宽恕与承诺只是由政治行动开端启新出来的“伟大发明”,给人以信心与希望,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回到古代希腊的原初的政治经验中去呢?
[1] 汉娜·鄂兰.政治的承诺[M].台北:左岸文化,2010.
[2] 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6] 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7]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 阿伦特.论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 霍尔等.阿伦特手册[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孔 伟]
Can Labor and Work Be “Political”?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TheHumanConditionby Arendt
Wen 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Labour; politics; work; Arendt
Arendt made a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labour,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She believes that labor only shows the common grou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and therefo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al freedom.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means of purpose and consequently conflic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freedom. She made a corresponding criticism of Marx. Fundamentally, Arendt’s conceptual analysis is anti-historical. She requir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ancient Greece, namely, to exclude labor and production in politics. This is not only on the contrary to the re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but also has many fallacies in the theory itself.
文兵,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