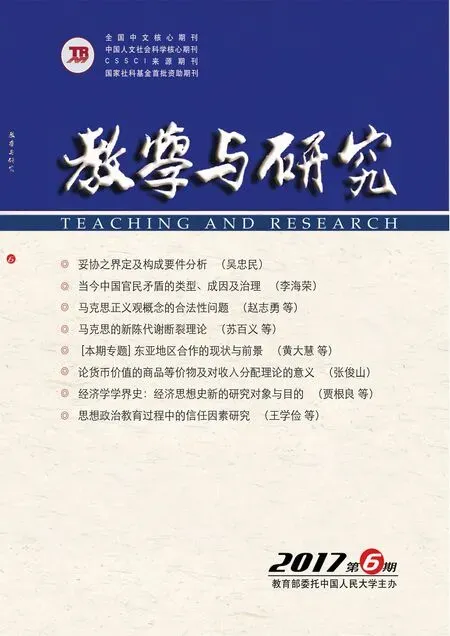TPP向何处去:美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嬗变*
2017-07-05贺平
贺 平
TPP向何处去:美国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嬗变*
贺 平
TPP;美国;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嬗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则标志着美国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政策嬗变。当前,TPP主要存在搁置、瘦身、变型、分解、消亡等五种变化可能。五种情境中,美国维系TPP的意愿不断下降,对TPP的解构和对奥巴马时期亚太政策的偏离依次递增,由此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加大。在“后TPP时代”,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压力有所缓解,但内部动力也随之降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政策博弈和更为困难的谈判进程。“加入TPP”固然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但当务之急仍是在RCEP等谈判上达成较高水平的阶段性成果,循序渐进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不确定性”或许是国内外预测其内政外交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正是由于这一“不确定性”,各方在对其政策取向充满疑虑的同时,在政策主张真正落地之前又不免心存侥幸,希冀其政策选项的变更,争取自身政策回旋的空间。特朗普入主白宫已期满百日,然而上述“不确定性”带来的正反效应却有增无减。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际经济政策上,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几乎是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唯一一个已经兑现的重大承诺,其他如大幅提高关税、货币操纵指控、重启既有经贸协议乃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均尚未付诸实施。TPP是美国主导和塑造亚太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载体,而经贸关系又是亚太各国对美关系的关键领域,深刻影响着区域稳定和地缘政治。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已经成为美国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的分水岭,而TPP的后续发展态势又与这一政策进一步嬗变的方向、力度和步骤息息相关,也必将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美国政局变动下的TPP
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或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有望成为奥巴马政府两届任期乃至冷战之后美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政治遗产”。在2010年美国加入后,TPP的成员逐渐拓展至亚太地区的12个经济体,谈判在历尽波折后于2015年10月最终完成,并于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协议。
TPP签署之后,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其他成员,都曾是一片庆幸和欢呼之声。不少学者乐观地估计,对美国而言,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批准与否,而在于批准的时机,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还没有一个重大的贸易协定在美国国会遭到否决,而民主共和两党对贸易的支持态度似乎也颇为喜人。他们甚至断言,“如果TPP失败,历史将不会原谅”。[1]尽管希拉里·克林顿也曾在竞选期间对TPP提出批评和质疑,但绝大部分政策评估都暗自坚信,她执政后势必改弦易辙,推动TPP的渐进落实。
当然,早在特朗普胜选之前,也曾有极少数预测对TPP的前景相对悲观,开始讨论“TPP如果无法执行该怎么办”。[2]主要原因在于全球贸易的政治气氛时过境迁,“时代精神”(zeitgeist)骤然降温,保护主义在与全球主义的胶着中渐渐取得了上风。这一派观点认为,TPP如想存续,最乐观的估计也是在新的美国总统任期内获得重新调整。[3]在哈佛大学2016年9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29%的美国人表示听说过TPP,而在对TPP有所耳闻的群体中,63%的受访者对其表示反对,高达61%的受访者误认为中国是TPP的成员或对中国加入与否并不了解。[4]尽管各种民调数据有所差异,但这似乎已经预示了TPP的命运多舛。现实恰恰印证了悲观论的观点,奥巴马政府放弃在退任之前寻求国会批准TPP,而胜选的特朗普已于2017年1月23日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转向通过双边谈判“促进美国的产业,保护美国的工人,增加美国的工资”。
二、TPP的命运与走向:美国的政策嬗变及其区域影响
2017年3月15日在智利召开了美国宣布退出之后的第一次TPP高级代表会议,但会议除了重申若干原则精神之外,并未就TPP的身后事达成任何协议,5月在越南再行商议。综合各方的政策动向,TPP的命运存在以下五种主要的可能。
第一,搁置。作为一种“保守治疗”,其他11国可选择将TPP暂时冻结,静观美国政局变化。
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因素的左右,重大贸易协议在签字后长期冷却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2年由布什政府签署后,后任的克林顿政府重新添加了关于劳动和环境合作的条款,才勉强提交参议院审批。又如,美韩FTA于2007年签字后几经反复且重启谈判,于2010年才重新签字并于2011年获得两国国会批准。而在国际贸易组织(哈瓦那宪章)、京都议定书等案例中,美国政府代表签字后,协议本身始终未得到国会的批准。这些先例的镜鉴似乎使TPP的“休眠”背后不乏复苏的希望。
另一方面,自胜选后,特朗普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以盖洛普的民调为例,在2017年5月8—14日的每周民调中其支持率已从2017年1月20—29日的最高点(45%)降至38%,上任之后的平均值为41%,这已经创下了战后美国历任总统的最低值,且仍存在继续下探的可能。[5]鉴于特朗普政府引起的巨大争议和面临的超低支持率,不免使人设想有可能打破近几任总统纷纷连任两届的常规而勉强完成一届任期。而如果这一迹象逐渐清晰,事实上复苏TPP的政策酝酿不需要等待四年,在其任期的后半期即可启动。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美国无望从退出TPP中获益,而与日本等国建立双边FTA带来的收益尚不足以抵消这一损失。[6]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内经济成绩单越乏善可陈,其经济政策的负面教义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中“独善其身”的警示作用也就越强烈,后一任美国总统在TPP政策上再度“回摆”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正如摈弃奥巴马的话语体系(“重返亚太”等)、“奥巴马医改”、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一样,决议退出TPP也可视为特朗普政府对其前任政策的刻意反动。美国在主导TPP谈判时曾引发激烈的国内论争,同样,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决定也激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批判,只不过攻守双方彼此易位而已。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在这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7]在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声音认为,放弃TPP无助于美国就业环境的改善,[8]美国对于亚太的经济影响力也将受到显著削弱。[9]而从价值链整合、规制协调等视角而言,区域乃至跨区域的一体化仍是大势所趋。因此,如何通过某种TPP的变体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议题塑造和规则制定能力,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外交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贸易政治学的个体主义视角而言,美国选民大体认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一旦将利益指向从国家聚焦到个人,其态度和立场就往往出现显著的分化。此时,就业安全而非国家福祉往往成为首要考虑。最新于2016年9月进行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意调查,再度印证了这一判断。[10]鉴于仍有高达65%的美国民众支持全球化,在美国整体经济形势和就业率起伏的背景下,如何塑造议题成为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重要挑战。在TPP政策上,美国是否以及何时能够“回摆”,需看产业界的呼声和选民的意见如何逆转现有政策的天平。
第二,瘦身。此即通常所谓的“TPP-1”或“TPP 11”方案,但并不排除其他经济体步美国后尘决意退出TPP。根据协议文本的第30章第5条,TPP将在所有初始缔约方通报其国内法律批准程序结束后的60天内生效,但如果在签字后的两年内未能满足这一条件,则将在至少六个初始缔约方(其GDP超过所有初始缔约方的85%)批准协议后,在两年期间结束后的60天内生效。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或日本这两个最大的成员不批准,TPP就无法生效。换言之,由于美国的退出,即便剩余11国的全体或部分国家希望继续在原有协议框架内实现TPP的既定目标,也必须在重新谈判后对第30章最终条款和其他相应部分做出修改。此时,不排除部分国家先行实施TPP,留待美国后续加入。
除了成员数量的缩减之外,“瘦身”方案同样可以表现在议题领域上,即若干“志同道合”的成员选择部分而非所有TPP的协议成果,率先达成某种“诸边协议”。在这一方面,电子商务、反腐败、监管透明度等某些共识度较高而国内政策敏感度和抵抗度又较低的议题不失为可行之选。[11]药品的特许权、严苛的食品安全标准等主要反映美国利益的条款有可能被暂时舍弃或降低标准。
这一情境近似于在取得部分议题突破的前提下,TPP又“回缩”到其成员渐次扩大和谈判不断进展的某一个阶段,或变为TPP的前身“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SEP,又称P4)的某种“加强版”,关键在于由谁来扮演美国(或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主导者角色。一方面,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承担起单独或携手挽救TPP的重任,目前还缺乏清晰的图景。主要大国在纷纷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又不免坦言“美国缺席的TPP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对于越南、马来西亚等后续加入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既要如约在规制改革、市场开放等领域做出重大调整,又将失去原先期盼中的美国市场,在短期内收益和成本高度失衡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加入没有美国的TPP值得考虑。而在经贸收益之外,美国缺位导致的地缘政治影响更是制约这些国家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三,变型。这一情境与“瘦身”类似,同样需要重新谈判,其差异在于前者仍保留原有12国的既定成员框架,“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而后者则允许新成员的加入。新成员或全盘接受既有的协议文本,或与原有成员再启谈判,但无论哪种情况,均保留TPP的名义和大致内容。新加入的成员可能是泰国、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此前明确表示过加入TPP意向的国家,也有可能是之前置身TPP世外的其他国家。
作为这一情境的又一种变体,有学者呼吁,美国应重起炉灶,谋求“扩大版”的TPP,即除了邀请韩国、哥伦比亚等非TPP经济体加入之外,将货币操纵、修改完善后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等原有TPP忽略或有所缺陷的议题领域也加入其中。[12]这或许可以视为美国国内部分势力“以攻为守”力图挽救TPP的一种策略,尽管看似在“不可能”的路上走得更远,但在理论上也不失为TPP的一种出路,特别是特定议题的增加和修改,直指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TPP的批判和关切。
第四,分解。这一情境比前一种更进一步,即TPP的多边框架完全瓦解,分化为数个双边或诸边FTA,由“扩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重新转向“特定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特朗普政府似乎对此方案颇感兴趣,已多次主张所谓“更公平、公正的双边FTA”。在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等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团队看来,双边谈判有助于解决TPP等多边谈判中谈判割裂、效率低下以及“原产地规则”缺陷等问题。[13]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则指出,TPP的最大弊端之一在于,相比美国其他成员获得了过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因此,“一对一”的双边而非多边谈判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保障美国利益。
需要看到的是,在12个成员进入TPP谈判之前,这些国家两两之间就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双边FTA网络,特别是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澳大利亚、新加坡建立了FTA。这也意味着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待补充的双边缺位寥寥无几。拟议中的美日FTA是其最重要的一环,两国占到TPP所有成员GDP总和的79%。新生的美日FTA有望从TPP协议中继承大部分规则条款,同时精简国有企业、环境保护、劳动标准等在两者之间并不突出的议题,成为某种“简化版”的TPP。[14]而在汽车、牛肉等少数产业上,日本有可能面临远比多边谈判更为严峻的美国压力。面临大幅修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视为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两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又一次双边谈判,具有显著的风向标意义。吊诡之处在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要旨恰恰大量源自TPP。而与日本不同,鉴于特朗普政府带有强烈“美国至上”和“公平贸易”倾向的经贸政策,马来西亚等其他中小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美国开展双边FTA谈判尚且存疑。
第五,消亡。作为一种最为悲观的情境,TPP有可能在历经数年艰辛谈判后回到原点,已有的谈判成果和政治投入前功尽弃。这既可能表现为所有成员在某一时间一致宣布最终放弃TPP,也有可能表现为“无疾而终”,即由于难以寻找各方均能接受的出路,TPP的生效在事实上被无限期拖延。

表1 TPP命运的五种政策情境
从根本上而言,美国的立场决定了TPP的走向,而这一立场又是其亚太区域合作整体战略的产物。五种情境中,美国维系TPP的意愿不断下降,对TPP的解构和对奥巴马时期亚太政策的偏离依次递增,由此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格局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加大。当前的主流判断是,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不可能“重返”TPP。毋庸讳言,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瘦身、变型、分解等三种情境事实上也意味着TPP的名存实亡(表1)。当然,上述五种情境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存在一定交叉和转化的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酝酿和利益博弈过程中,域内各个利益攸关方势必与美国形成程度不一的双向互动。
三、“后TPP时代”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价值取向总结为两点:不会为了外交政策而牺牲美国经济;重拾里根的理念,坚定地“以实力求和平”。[15]由此,拉升经济增长率成为特朗普政府经济方略的最大目标,而表现在具体政策上则以创造就业为圭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实现了合流。2017年的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提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四大优先政策事项:在贸易政策上捍卫美国国家主权;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律;利用所有的杠杆力量打开外国市场;谈判新的、更佳的贸易协定。[16]在现实中如何体现这些政策优先度,“后TPP时代”的美国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嬗变成为一块试金石。整体而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压力有所缓解,但同时内部动力也随之降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领导人对于美国自甘懈怠纷纷表示强烈失望,为其信用丧失而扼腕。尽管将TPP失去美国后的亚太比喻成19世纪末期和二战之前争夺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有夸大之嫌,[17]但美国的这一行为确实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主导国的丧失,加剧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混沌和迷茫的状态。
“全球主义”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18]无论是TPP,还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是这一“全球主义”在特定议题和区域的集中体现。而特朗普则并不讳言“美国主义”才是其信仰,强调“把就业岗位和产业重新拉回美国本土”。在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向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转变的过程中,美国的亚太合作政策极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及对经济全球化的挫伤。亚太地区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减速甚至倒退将严重制约亚太地区的后续发展。
第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面临更为复杂的政策博弈和更为困难的谈判进程。
在TPP和RCEP倡议相继问世后,两者之间的差异与互补、博弈与整合成为探讨FTAAP前景的重要视角。在美国退出TPP之前,各界关于FTAAP实现路径的讨论皆以TPP和RCEP两项谈判的达成和并行为前提假设,这在2015年TPP达成协议之后尤为明显。整体而言,在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水平上,相较于RCEP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成员的照顾及分阶段设计,TPP更加体现了发达工业国家对于区域自由贸易的全方位的高标准。鉴于这种差异,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两种协定的直接融合较为困难,但可分别将RCEP与TPP视作实现FTAAP的初级和高级阶段,区域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可以首先加入RCEP,而在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并做好了接纳更高标准的准备后再行加入TPP。[19]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之后,TPP的后续发展及其对于FTAAP和RCEP的新的意义亟待重新评估。
当前,RCEP谈判在服务贸易和投资等议题上仍面临一时难以弥合的分歧。而TPP的搁浅有可能造成RCEP的所谓“TPP化”,即部分参与两大谈判的国家在面临TPP付诸东流之时,有可能将更大的政治抱负投向RCEP,希望由RCEP部分扮演起TPP原先在市场开放、规制改革上所起的作用。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希望RCEP能够借鉴TPP的透明度标准以及投资等议题的规则。这虽然在无形中提高了RCEP的水平,也进一步增加了其谈判难度和悬而未决的风险。
第三,“加入TPP”固然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但当务之急仍是在RCEP等谈判上达成较高水平的阶段性成果,循序渐进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美国退出TPP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欢迎中国加入。2016年11月召开的APEC会议上,东道主秘鲁提出以“排除美国,中俄参加”的新型经贸协定替代TPP。2017年3月15日,中国政府又派代表出席了在智利召开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高级别对话会。一时间,中国是否参与TPP的话题再度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也与上述第三种“变形”的情境息息相关。
无论是从市场开放水平与TPP高标准的落差等经济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博弈等政治角度而言,在中短期内,中国加入TPP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纸上谈兵或政策层面的沙盘演绎而已。在技术层面上,尽管TPP的第30章第4条“鼓励”接受现有条款和条件的后来者申请加入,但鉴于既有成员的否决权、申请审批的冗长过程,中国这样一个着意规则制定者角色的超大新成员面临着后续加入的巨大困难。[20]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如何脚踏实地地推动双边和地区层次的一体化深入向前发展,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至关重要。有学者将中国对待TPP的态度形容为“三位一体的战略”,即观望的态度、在亚太地区推动其他的FTA模式、加速市场导向的国内经济改革。[21]这是相对全面的。应该看到,中国即便在短期内不加入TPP,在RCEP及其他FTA谈判中也无法回避TPP产生的间接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做好新型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发展趋势的研究,尽早完成国内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的制度性积累。
四、结 语
在相当程度上,贸易已经成为美国经济颓势的“替罪羊”,或者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恶果的“罪魁祸首”。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理念中,“贸易失衡”被放大和等同于“贸易扭曲”,似乎只有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才能彰显真正的“公平贸易”。中国和日本现为美国的头号和第二号贸易赤字来源国,而作为奥巴马政府时期最主要双边FTA成绩的美韩FTA又被视为造成美国贸易失衡状态恶化的最新证据。换言之,东亚主要经济体均是新一届美国政府贸易报复的重点对象。降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成为中美领导人会晤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的核心议题,尽管如此,对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势的恶化和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张仍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尚未完全成型,TPP也不能涵盖美国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的全部。虽然这一政策正在经历从规则导向到结果导向、从注重多边到强调双边、从积极主导到消极自保、从主动进取到被动防御的转变,但并非木已成舟、积重难返。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面对如此变局应如何妥善引导,发挥更大的建设性和主动性作用,既是前所未有的政策挑战,也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重大机遇。
[1] Michael J. Green, Matthew P. Goodman. After TPP: the Geopolitic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4,2015.
[2] World Economic Forum. Will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eshape the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ystem?Regional 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 Issues and Options[R].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Trade & FDI, July 2016.
[3] Byung-il Choi. Whither the TPP? Political Economy of Ratification and Effect on Trade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J].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Vol. 20, No. 3, September 2016.
[4] Americans’ Views on Current Trade and Health Politics[R]. POLITICO-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olls, September 2016.
[5] Gallup, Inc. [EB/OL].http://www.gallup.com/poll/203198/presidential-approval-ratin-gs-donald-trump.aspx.
[6] Kenichi Kawasaki. Emergent Uncertainty in Regional Integration-Economic Impact of Alternative RTA Scenarios[R].GRIPS Discussion Paper 16-28,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January 2017.
[7] Charlene Barshefsky et al. Reinvigorating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M]. CSIS/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8] Alana Semuels. TPP’s Death Won’t Help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J]. The Atlantic, November 15, 2016;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ssue Brief. Industries and Jobs at Risk i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Does not Pass[R]. November 2016.
[9] Hunter Marston. Is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a Pacific Power?[J]. The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7, 2016.
[10] Dina Smeltz, Craig Kafura, Lily Wojtowicz. Actually, Americans Like Free Trade[R].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2016.
[11] Shiro Armstrong. A New Deal in Asia: Can RCEP Pick up Where the TPP Left off? [J]. The Foreign Affairs, March 17, 2017.
[12] Jeffrey J. Schott. US Trade Policy Options in thePacific Basin: Bigger Is Better[R]. Policy Brief,Number PB17-7,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17.
[13] CNBC Transcript: Steven Mnuchin and Wilbur Ross Speak with CNBC’s’Squawk Box’ Today[EB/OL]. November 30, 2016, http://www.cnbc.com/2016/11/30/cnbc-transcript-steven-mnuchin-and-wilbur-ross-speak-with-cn-bcs-squawk-box-today.html.
[14] Michael Auslin. Time for a U.S.-Japanese Free Trade Agreement? How to Proceed if the TPP Is Dead[J]. Th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9,2017.
[15] Alexander Gray,Peter Navarro.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J].Foreign Policy, November 7, 2016.
[16] The President’s 2017 Trade Policy Agenda[R].The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March 1, 2017.
[17] Robert A. Manning, James Przystup. Does Trump Want a 19th-Century World Order? [J].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9, 2017.
[18] Hal Brands. Barack Obama and the Dilemma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J].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9, No.4, Winter 2017.
[19] Shujiro Urata. A Stages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Pacific: The RCEP, TPP, and FTAAP[A]. in Tang Guoqiang,Peter A. Petri(eds.). New Directions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C]. East-West Center, 2014.
[20] Shintaro Hamanaka. Accession Clause of TPP: Is It Really Open? [R].IDE Discussion Paper, No. 606, IDE-JETRO, June 2016.
[21] Ming Du. Explaining China’s Tripartite Strategy towar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8, No. 2, 2015.
[责任编辑 刘蔚然]
Whither the TP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cy
He Ping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and Center for BRICS Studies,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TPP; 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cy transformation
TP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s Asia-Pacific, howev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 of with drawing from TPP has symboliz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U.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olicy for Asia-Pacific. At present, there are mainly five scenarios for TPP’s future, namely abeyance, diminution, transformation, decomposition, and demise. In the order of these five scenarios, the willing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TPP declin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PP an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policy increases, and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gradually grows. In the “post-TPP era”, the external pressure on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ease to some ext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l dynamics will also lose its momentum.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and the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FTAAP) will face more intricate policy game and more difficult negotiations. While “joining TPP” providesan additional policy option for China,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achieve a relatively high-level progress in RCEP negotiations and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 progressive way.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RCEP与TPP背景下的中国亚太跨区域开放合作战略研究”(项目号:13CGJ029)、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指向性课题“推动金砖国家经贸领域务实合作研究”(项目号:17GBQY041)的阶段性成果。
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