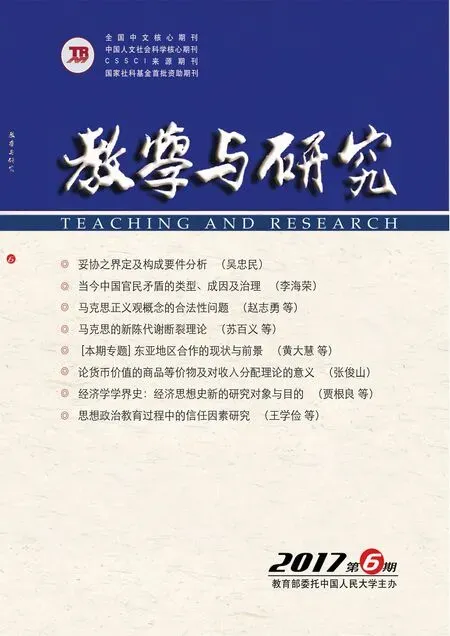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因素研究*
2017-01-31王学俭杨昌华
王学俭,杨昌华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因素研究*
王学俭,杨昌华
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信任倾向;可信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综合系统,不同的过程要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发挥着不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和受教育者信任倾向共同构成信任的前因变量;教育者的功能作用、第三方人际信任、教学管理、组织氛围以及学校外部信任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境因素构成信任的中间变量;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结构均衡和不信任的功能失调构成信任的结果变量。
信任是人们日常例行互动的必要基础,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维度。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指涉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属性的一种接受和信赖,表征着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信赖关系。而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根据社会的要求,充分调动各个要素协调运动,对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形成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期望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过程。”[1](P132)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展开、运行和发展的流程,而是围绕着社会发展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需要,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不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素的要素效能和要素间结构匹配的渐进性、动态性的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要素说”(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介体)、“四要素说”(主体、客体、介体、环体)、“三体一要素说”(“三体”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一要素”包括媒介要素)、“五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情境)、“六要素说”(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情境)。本文基于信任的视角,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实施和结果三个阶段对不同要素进行梳理,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因素、受教育者信任倾向因素、教育开展的情境因素、教育结果因素等方面来探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要素效能和结构匹配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复杂的过程要素及其关系中,信任始终发挥着简化、衔接和融通的作用,这主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性和动态性体现出来。
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构性来看,不同的要素效能和要素匹配关系中都内含着基本的信任因素。单个要素关系作为基本的组合单元,它与其他单元相联系,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信任关系网络,这种复杂和多元的要素关系不仅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信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其次,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动态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持续的关系中进行,而且也在持续的关系中生成新的机构、功能与系统,以及新的良好稳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包含着多种要素和环节作为信任生成的中介,而且也需要信任来简化这些中介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因此,从这重意义上来讲,复杂多元的信任关系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性的表现,而且也是其超越性的表现。
考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机理,首先需要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前因变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性和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为出发点;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中间变量——教育者的功能作用、第三方人际信任、教学管理、组织氛围以及学校外部信任等因素为关键点;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果变量——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结构均衡和不信任的功能失调为研究着力点,尝试通过多元复杂信任关系来还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信任的形成机理。
一、信任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性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中,普遍地认为主客体二元关系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本结构,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主体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客体既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也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方式和载体等要素;[2]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主体是教育者,客体是受教育者,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3]还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是作为主体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双向或多项互动关系;[4]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主体是人(组织或个人),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对象。[5]另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层面,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6]尽管不同学者对于信任的主客体划分有些许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结构要素得以逐渐清晰,也使得主客体关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础范式。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基础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并不能涵盖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关系的现实图景就是在信任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地衍生出多元和复杂的信任关系,并且在一个系统和动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交互作用。
由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前因变量,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多元复杂信任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发生的基础与核心。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较多地将研究的聚焦点和落脚点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可信维度,即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容、目标、主体、机制、载体、方法、效果等方面的调整和建构,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更加稳定、可靠和高效,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另一维度——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却鲜有考察。
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信任调适来赢得受教育者的信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在这一研究视阈中,“可信度”[7](P233)成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核心要素。按照西方社会心理学家梅耶(Mayer)对可信度的三个基本维度的划分——能力(一方在某一领域产生影响的技能、特长或特征的集合体)、善意(能够为另一方利益考虑)、正直(行为是否符合合理规范),[8]思想政治教育可信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能力层面上能够有效实现其责任和目标的综合胜任能力与特点;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开展能否真正意义上彰显主体性的价值与地位;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规范与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以及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的一致性。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的基本策略来看,主要涉及了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任的约束策略和信任的展示策略,即不信任的约束策略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制度和规范,以评估、监督、惩罚、奖励等方式,降低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评判和预期;信任的展示策略就是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值得信任的因素展现给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体,以建立积极的评判和预期。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维度的分析和研究较为集中和成熟,但是从信任的意涵来看,可信度并不等价于信任,信任不仅包括了被信任方的可信度,而且也包括了信任方的信任倾向。考察信任在不同学科视野中的理论面向,在心理学中信任强调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情境刺激反应,在社会学中信任强调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学中信任注重交互关系中的“理性计算”,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视野来看待信任问题,在信任基本意涵中的信任方与被信任方的交互关系是具有通约性的,信任关系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这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情境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基础范式。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仅仅关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维度,从单一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信任问题,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方——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显然有失偏颇。在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中缺少了对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考察,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时思想政治教育在可信的三个维度(能力、善意、正直)均处于较高水平时,思想政治教育思维信任层次和教育效果却参差不齐,而有时在思想政治教育可信的某个维度表现不足时,也能够取得较好的信任与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只有从可信维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维度,才能够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研究视阈。
信任倾向是对受教育者人格、情绪情感、社会交往以及自我价值等内在特质的涵括。个体的心理信任倾向在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看来,是组成信任的基本维度,个体给予信赖和抱有怀疑来自于成长过程中家庭、群体、兴趣团体和组织等社会交往的历史中,“是个人信任的历史经验的痕迹,固化在信任的行动者的人格中”。[9](P94)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是较为稳定的因素,这种构成信任的基本前提会潜在地影响到受教育者信任意愿的确立和信任行为的选择。“不同个体由于成长背景、人格类型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信任倾向”。[10](P37)
总体来讲,影响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受教育者的社会交往因素和人格特质两个方面。首先,在受教育者的成长过程中,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与稳定性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熟悉性和交往经验,熟悉性在卢曼看来,是能够简化世界的复杂性,使简单性在相当狭窄的界限内得到保证,强化了期望的可靠性,从而形成了信任的前提。[11](P25)同时,受教育者通过社会交往的方式不断凝练和总结成长经验,并将其迁移到新的社会交往情境中,使得信任得以强化。例如,家庭交往就为“特别亲近和强烈信任的日常经验提供了背景”。[9](P174)反之,受教育者的社会交往不足则会形成不信任的个体倾向。其次,受教育者的人格特质也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影响受教育者信任选择的主要因素,这主要包括了受教育者的公正性、开放性、公平性、连贯性、忠诚性、活跃性等个体内在因素。受教育者的情绪和情感因素也是影响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主要因素,即受教育者积极的情绪情感倾向于依靠先验的知识图景形成开放的信任观,而消极的情绪情感则较少依赖先验知识,倾向于较为谨慎的信任观。此外,受教育者成长的地域差别、经济状况、自我效能感等个体状况也是影响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重要因素。
考察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并不能止步于静态地认识其影响因素,而是需要系统地、动态地将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纳入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情境当中,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可信度,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认知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内在倾向性并不能直接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结果,而是在基于个体认知和情感的双向互动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在能力、善意和正直三个维度上的可信度作出评判,形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意愿,最终通过受教育者信任意愿的强弱来表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水平。
在这里,构建系统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认知过程需要引入四个基本环节。首先是由受教育者内在信任倾向性形成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认知过程的基础,并且二者在形成信任基础的过程中存在着交互和转化作用;其次是包含了认知和情感信任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可信性作出评估和预测;再次是形成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意愿;最后是受教育者信任意愿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水平。由以上四个环节不难看出,包含了认知和情感因素的信任基础与思想政治教育可信度之间并不能独立于对方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结果;受教育者的信任意愿中介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基础、可信度与信任结果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认知环节中,信任意愿的作用最为显著,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结果的直接变量。
二、过程追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情境因素
单纯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可信性和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两个基本要素并不能够完整地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形成过程,从动态性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素的多样性,就决定了这一过程中的情境因素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些情境因素作为中间变量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结果。具体来讲,这些情境因素就包括了教育者的功能作用、第三方人际信任、教学管理、组织氛围以及学校外部信任等因素。
首先是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由专业知识和专家队伍所构成的现代抽象体系与非专业的普通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知识鸿沟,而抽象体系的专家或者代理人就扮演着沟通二者的角色,非专业人士对于抽象体系的信任一方面来源于抽象体系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来源于抽象体系的代理人士或操作者的品行与技能。[12](P75)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现代抽象体系”的一部分,取得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教育者的专业技能、道德品行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人际沟通和知识分享的主动性。具体而言,教育者的专业技能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理论特质、实践操作以及研究方法等专业性知识的熟识程度,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和理念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激励、启发和动员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氛围的能力。教育者的道德品行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重要因素,“就教师群体而言,那些为学生所信任的教师首先是有着良好道德的教师,他们大都言而有信、坦荡无私、公平公正”。[13](P29)此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人际沟通和知识分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因素,形成教育者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动因不仅包括了教育者的人格特质(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而且也包括了促进积极教学情绪的相关技术和管理机制。
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第三方人际信任。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双方都处于多重复杂的人际和组织结构中,并不能脱离这一情境而单独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信任也是嵌入在现有的或者潜在的人际关系或者组织氛围的复杂网络中。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信任意愿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第三方意见的影响,在这里,第三方意见有可能来自于受教育者社会交往中的个人意见,也有可能来自于组织意见。一般来讲,第三方意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受教育者的信任意愿,一是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人际行为或组织行为,二是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信任判断。[7](P21)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第三方意见普遍存在,例如,来自于同辈群体、兴趣小组、亲戚或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意见等,这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意见对于受教育者的信任意愿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要综合考察受教育者的直接经验与第三方判断。
再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学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管理系统中的信任是一个综合多维体,从不同信任视角来看,具有不同的信任类型。例如,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的人际信任视角来看,主要包括了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从事教学管理的组织或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的组织信任视角来看,又可以分为水平信任关系和垂直信任关系。所谓水平信任关系是指“地位平等的信任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垂直信任关系“则存在于地位不平等的信任主体之间”。[13](P33)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管理中,水平信任包括了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之间、同级别的教学管理人员之间的信任等;垂直信任包括了教学管理人员与教育者之间、教学管理人员与受教育者之间、不同级别的教学管理人员之间的信任等。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的制度信任视角来看,又可以分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管理准则、管理模式、管理决策、管理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软硬件教学资源的信任。总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管理中的信任关系是教育主体对于教学管理人员的责任心、教学管理组织的规范性以及教学管理环境的熟悉性的认知反应,这一过程中的任何一对信任关系都将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结果。
最后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组织氛围。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氛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的信任文化,这种文化氛围是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实践过程中集体经验的沉淀物,“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者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行为”,[9](P95)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文化的约束力对于受教育者给予信任的要求、对于可信度的估计以及对于内在信任倾向是一种促进作用。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并不是纯粹的人际信任或者学校教育信任,而是一种渗透着复杂制度、规范等社会因素的“社会信任”,因此,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情境因素还应当包括学校与家庭、社区、社会组织间的多元信任关系。
三、结果考量: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 结构均衡与不信任的功能失调
具有动态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结构,由前因变量(可信性与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奠定基础,经过中间变量(情境因素)的影响,最后形成的结果变量就是受教育者的信任与不信任。
一方面,从受教育者付诸信任意愿的结果视角来看,这不仅表征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处于一个高水平的信任层次,而且也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复杂多元的要素关系也是处于稳定、高效的状态,以及由各个要素关系所引申出来的信任关系也是处于一种正序的、均衡的、互动的关系,即随着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主体间的积极互动,其逐渐积累的经验和积极行为会逐渐增加受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可信度的感知,信任也会互惠更快地发展,信任促进信任,“当信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与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便产生了信任文化”,[8](P148)内含着规则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文化,不仅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公信力,而且也促使受教育者实现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成长要求。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结果信任的角度来看,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结构是有序均衡的,这一信任结果也将会以文化的形式积淀和反馈,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结果不信任的视角来看,不信任也是客观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情境中的现象,“信任是需要精心守护的东西,任何一个小小失误就可能使可信性受到伤害,甚至彻底丧失,使双方的关系陷入僵局”。[13](P194)不信任作为信任的对立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导向中往往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怀疑性”的态度,这种“怀疑”是介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与不信任的中间变量,是悬而未决的,表现为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清晰的预期和评判,是处于信任建立和信任丧失的动态中间阶段;另一种是“否定性”的预期和评判,包括了负面的、防御性的和悲观主义的意识和行动,不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可靠性的暗示,或不积极地进行评估,这一结果的直接表现就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能动性和积极精神的保留与消减。与产生信任意愿的结果输出不同,不信任有可能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各个环节当中。例如,在前因变量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信度与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相互关系中,就有可能产生不信任;在中间变量中,任何一项情境因素都有可能产生不信任。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出信任要比导致不信任更难。
尽管不信任的现象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信任的逻辑考察,提出消减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任的基本策略。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任本身来看,其存在着功能性的失调,即一旦使受教育者形成不信任的意愿,便会使受教育者不再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可靠性的暗示和进行积极评估,也限制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潜在地互动伙伴范围,阻碍了受教育者交往互动的启动,这不仅使受教育者抛弃了已存的有益关系,而且也意味着其丧失了一系列的行动机遇。其次,根植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规范系统的信任文化,能够形成激励合作与参与的文化氛围,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够释放信任,而且对于不信任的现象形成强烈的道德制约和文化导引。第三,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可信度的不断调适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信任情境的积极影响,以及良好的教育情境和社会风尚感染熏陶,这种不断增强的信任基础和现实性,将会对于受教育者不信任的意愿起到很大的扭转和改变作用,也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不信任逐渐丧失现实基础。面对这些持久的、反复值得信任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表现,没有被证明是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信任将被终结。
余 论
信任作为人们日常例行互动的必要基础,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西美尔认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会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14](P178)作为一项既相当复杂,又十分重要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使得信任应然地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们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15](P5)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门类,是一项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其中的主体性活动。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展过程中,信任问题也必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起步较晚,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待于探讨的问题仍较多。笔者在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研究的视野中,进一步探讨受教育者的信任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性的交互关系,由此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动态性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复杂多元信任关系。这一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的研究:一是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形成过程中,引入了受教育者信任倾向的因素,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研究提出主客体二元关系,却单方面地注重可信性研究进行了补充,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基础;二是系统动态地考察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种情境因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尝试通过多元复杂的信任关系来还原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的真实图景。
[1] 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 范碧鸿.思想政治教育信任理论初探[J].学术论坛,2010,(3).
[3] 谢光绎.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信任关系[J].湖南社会科学,2008,(4).
[4] 黎玉明,侯波.思想政治教育信任形成机理与信任培育[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1).
[5] 孙凤.思想政治教育信任、信度与可信性之辩[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9).
[6] 向征.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信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7] 姚琦,马华维.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信任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8] Mayer R. C, Davis J. H,Schoorman F. D.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3).
[9] [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 翟学伟,薛天山.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 [德]尼可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3] 曹正善,熊川武.教育信任:减负提质的智慧[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5] 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李文苓]
Research on the Trust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Xuejian, Yang Changhu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rust; trust tendency; credibility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complex and pluralistic system. Different process factors exert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trus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redi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trust tendency of the educated constitute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trust.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function of the educator, interpersonal trust, teaching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and external trust of the school constitute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of trust. The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irrational function of trus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itute the outcome variable of trust.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前沿发展研究”(项目号:16FKS010)、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风险视阈下的社会信任培育研究” (项目号:15LZUJBWYJ019)的阶段性成果。
王学俭,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昌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