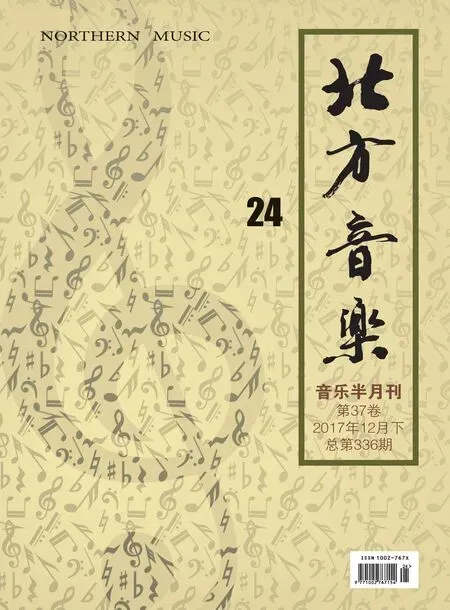实践探究,体验感悟
——谈花鼓戏音乐的喜剧性
2017-01-29梁玲芝
梁玲芝
(湖南城市学院,湖南 益阳 413049)
湖南花鼓戏的传统音乐,属曲调联缀体。它与宋元南北曲以及明清昆弋诸腔的曲牌联套体虽同为“牌子音乐”,但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较多地保存了地方民间歌舞的“民歌小调”风格,其曲调连接无固定模式,而后者则较多地保持着文人“倚声”“倚曲”的“词曲音乐”特色,曲牌连接有一定的套数、官调等章法。但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每首曲牌或曲调均有相对稳定并具一定形象感的标题。所以“牌子音乐”多为标题性音乐。以京剧为代表的皮黄声腔通过节奏、节拍变化而繁衍出互有关联的声腔系统的“板子音乐”,多由说唱音乐演化而成,以板数及板式的节奏特点为其曲名。因此,“板子音乐”实际上属于非标题性音乐。
一、传统曲调的标题性
湖南观众对花鼓戏音乐的偏爱,正如广东人对粤曲、河南人对梆子一样,那种饱浸泥土芳香和乡音情调的音乐,交织着当地人们心理的各方面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这便是一种人的体验,其本身就反映了人对周围现实的态度以及关于生活其他方面的观念。由此可见,人的精神领域最易于为音乐所表现。在中国过去长期封闭的社会条件下,农村劳动者创造了戏曲艺术,反过来戏曲又给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和美的享受,表达了他们的冀求和愿望,其中戏曲唱腔更为他们所接受和传唱。唱腔含有音乐和文学(词)两大因素,唱词虽然缩小了音乐形象的意义并使它“具体化”,但当音乐语言与唱词内容有机地融和之后,便能产生一种更为典型、生动的艺术形象。所以,某些传统花鼓戏标题性曲调,是与某些典型的戏剧人物和谐统一、血肉相连的。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将舞台形象化为具体的印象,并且迅速地与一定范围的生活中的具体观念联系起来。比如长沙观众决不会将《张先生讨学钱》的“学钱调”称之为《接姨娘》的“姨娘调”。这不仅仅因为观众熟悉它们,而且是这类标题性曲调的音响感受及其所表现的内容,给人们带来“具体的”形象的联想。前者有一种压抑而空虚的幽默感,后者却表现出粗犷而轻浮的幽默感。
二、喜剧因素的客观存在
花鼓戏的发展史表明:先有歌舞情节的演唱,再出现简单性格的人物。这就是自清嘉、道年后一直延绵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而至今仍有其余响的“二小戏”和“三小戏”。同时,花鼓戏音乐发展史亦表明,当逐渐戏曲化的民歌与有个性的戏剧人物有机地结合之后,在不断的实践中,随着剧目的完善而形成专用曲调。这种专用曲调被艺人冠上戏剧人物或剧目的名称,便成为现在具有行当特征和具体情节内容的标题性曲调。可以说,标题性曲调是与早期的剧目同步产生并随同剧目的丰富而发展。
湖南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据初步统计,约有470余出,其中“二小戏”“三小戏”约有270余出。这个数字说明了此类型剧目在花鼓戏中占有的特殊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类中小型剧目中,喜剧性的剧目约占2/3以上。正因为有如此分量的喜剧剧目,便为花鼓戏奠定了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郁的艺术特色。
喜剧性的“笑”的效果是由角色来完成的。丑行是花鼓戏早中期剧目中举足轻重的行当,那些使观众开心的“戏”多发生在他(或二旦、丑旦)的身上,这与花鼓戏的前身地花鼓中小丑惯使插科打诨之技不无关系。花鼓戏的小喜剧中,丑角所扮演的人物大多是善良、机智、幽默的劳动者,他们或许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在花鼓戏观众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一般都是可爱的喜剧角色的形象。
传统的戏曲音乐没有象大型器乐曲或歌剧所具有的和声、织体、配器等立体式的表现手段,它是一个有着明确乐思和音乐造型能力的单独的声部,它的表现手法是曲式、旋律、节奏、调式和简陋的伴奏以及各具特色的演唱技巧。这几种手法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那变幻多端、个性鲜明的旋律,喜剧因素存在于表情丰富的旋律之中。就戏曲音乐而言,旋律还包含节奏型、语言音调、润腔技巧乃至主奏乐器的表现特色等诸种成分。花鼓戏唱腔中的喜剧因素从演员开口之前,便在其过门中得到一定的体现。
三、喜剧因素的发展
如果说《王婆骂鸡》和《打铁》等喜剧是前人留下的遗产,那么今人创作的喜剧中,其音乐的喜剧因素又是怎样继承和发展的呢?笔者对长沙花鼓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各时期有影响的喜剧性剧目进行了抽样比较,发觉这些剧目在选曲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姑嫂忙》、五十年代未的《刘海戏金蟾》、六十年代的《打铜锣》、《真的对不住》、七十年代的《对象》、八十年代的《喜脉案》《郑老倌分房记》等七个剧目,跨越四个年代,题材不同,剧本风格不同,排演单位不同。但各地音乐编配者在数以百计的传统曲调中,几乎都将撷取的目光集中在“姨娘调”“山川调”“洞腔”“花石调”“讨学钱”“洗菜心”“安童调”“采茶调”“补缸调”“杂货调”等十余首曲调之上。
这决不会是偶合,而是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即喜剧性的剧本多采用含有喜剧因素的标题性曲调来表现。
社会生活的变革,影响到人们的审美观念。所以,音乐描绘手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要求而不断更新的。上述各剧目在选曲方面虽然表现出较多的共性,但在各时期中对这些基本曲调进行再创作时,却又明显地表现了不同的特征。
五十年代喜剧剧目中,基本上是继承、沿用传统的具有喜剧因素的标题性曲调,但对原曲进行了规范和整理。如长沙《姑嫂忙》中的“山川调”“洗菜心”;衡山《新双采莲》中的“板浆调”“采莲歌”“采莲调”“四季歌”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 湖南花鼓戏的喜剧创作演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音乐作为刻画新时代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进入了“变形发展”的阶段。其特点是突破了原有的基本腔句结构,将原上下腔旬反复的曲体,变成乐句落音丰富但调式明确的多乐旬曲体,加强了人物的形体动作性,其过门或唱腔间隔均注重描写性音乐。但是,从整体而言,这些经过改编后的曲调,俱保持了原曲的音乐风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京剧现代戏唱腔中特型音调的贯串和主导音型的发展,加之乐队交响性的怒置和写作,使中国戏曲音乐从传统的“线描式”国画风格向对立体式”油画风格靠拢。花鼓戏亦不例外地受其冲击,即从传统曲调情绪的单一性转向复杂性,部分含喜剧因素的标题性曲调,在进行改编时,均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就是在“变形发展”基础上向纵深开拓的“综合发展”阶段。其特点是使曲调具有多种情绪、色彩以及鲜明个性的音调。
当今,人们对花鼓戏音乐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个性强烈、形象鲜明、音调新颖、节奏丰富。花鼓戏音乐中喜剧因素的发展进入了“更新换代”的新时期。“更新”不仅只是乐旬材料的伸延和扩充,而是:(1)突破了传统曲调民歌体那规整对称的双乐句结构;(2)改变了乐汇的旋法与节奏;(3)重新确立了音乐语言的意义。如“安童调”在《喜脉案》中,是品格正直而性情诙谐的太医胡植的音乐形象。其旋律十分新颖,但从中可以看出原曲特型音调的痕迹,这些音调通过夸张与强调,使曲调有鲜明的动态,对骑驴上朝、属正丑行当的胡植,从外形到性格均表现得十分深刻。“山川调”在上述的每个剧目中曾多次出现,从上例四组旋律可知,每首曲调仅只保留了原曲最有特色的乐句的结束乐汇,而整个曲调的旋律别开生面,已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打鸟》中保守型的婆旦形象分别演化成了具有复杂性格的丑旦形象和有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
[1]周勇.湖南益阳花鼓的正悲剧声腔问题研究[J].中国音乐,2008(05).
[2]周勇,刘新敖.时间态:地方戏曲的一种现代样态[J].城市学刊,2016(6).
[3]周勇,刘新敖.湖南花鼓戏鉴赏[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