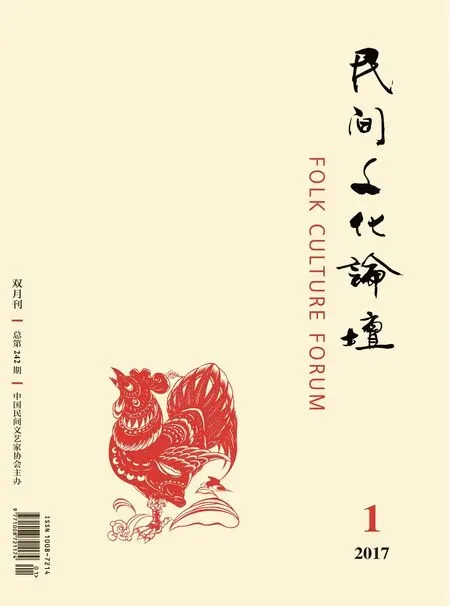西王母国游记*
2017-01-27卢梦雅杨文文
[法] 沙 畹 著 卢梦雅 杨文文 译
西王母国游记*
[法] 沙 畹 著 卢梦雅 杨文文 译
译者按: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曾是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普及了现代汉学。他首先是位史学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翻译了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①沙畹未完成整部《史记》的翻译,仅译介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5-1905年由巴黎Editions Ernest Leroux陆续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1967年由巴黎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再版时出版了第六卷(《孔子世家》卷四十八至五十)。在译作第五卷中,写有一篇附录名为《西王母国游记》,展示了沙畹对《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古籍中关于穆王西游的多个问题进行阐发,尽管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但如穆王西游的历史记载是结合异域口头传说而来、“穆王”原型本为秦穆公等主要观点极具启发意义,其观点曾被我国现代历史学家杨宽在著作《西周史》中所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沙畹对于这些直到晚清时期史学界仍持有的固有观念提出异议,并非单纯针对传统经学,这种颠覆性意见的提出更多地是针对当时西方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批判。沙畹所译《史记》,并非单纯翻译,译著中包括大量注释、介绍、综述、论文,是一部以西方史学角度对《史记》的综合性研究。
最近一篇德国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于190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穆王和萨巴王后》的文章,旨在将西王母论证为萨巴王后。我无意反驳这个理论,但是既然佛尔克在文章结尾驳斥我的见解——拜见西王母的故事是外来故事的译文,是被穆王人为地附着于中国历史,原来的传说中并没有穆王——我在这里想明确几点个人意见。①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tome II, Paris, 1967, p. 6, n. 自法国汉学家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以来,人们习惯于引用白大卫(Abdallae Beidavaei,即Beidawi)撰写的《中国史》(Historia Sinensis)中关于穆王的段落(参见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注释171),希望从中找出中国传说是波斯传说再现的证据。这个段落是由缪勒(André Müller)翻译于1677年以拉丁文发表、后为白大卫引用的波斯文章(实际上是另一个人百纳凯迪(Benaketi)的第八个作品——由Quatremère第一个确认了这一点——Benaketi的书只是波斯史家拉施丁(Rashid ED-DIN)《史集》的一个概要,写于1317年(参见H.M.Elliot, 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 vol.III, pp.55-56.)。下面是缪勒关于穆王游记的译文:( historia Sinensis, 2e édition, Iena, 1689, pp.43-45):“Porro Gai-vango Movang rex succedebat. Huic Emirius erat, Zacu nomine. Qui praeclara exequebatur opera. Mandato, exempli gratia, regis, in carpentum se dabat. Quod sex equi trahebant, de die centum parsangas cursu conficientes. Sic, ut terrarum conditionem exploraret, et ultro citroque means Regi deferret. In nostram etiam Persidem terrasque Iran venit. Cujus itidem statum et temperiem, quae ibi est aëris, regi aperuit. ”很明显,这段只不过是中国文本的一个变形,“他甚至一直达到了我们波斯国伊朗地区境内(In nostram etiam Persidem terrasque Iran venit)”这一句,明显是拉施丁(Rashid ED-DIN)或者百纳凯迪(Benaketi)加上去的。在这段中根本看不出,虽然正如鲍狄埃和拉克伯里希望并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与中国传说毫无关系,而是来自于波斯的口头传统。拉克伯里还采用了鲍狄埃的另一个更没有意义的假说。在一篇成文于1126年的波斯文本(Modjmel al-Tewarikh)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段落(据摩尔的法译文Jules Mohl, Modjmel al-Tewarikh, Journal. Asiatique., fev. 1841,Ier volume, p. 155.):“他(Djemchid)从Peritchehreh那里得到了Zaboulistan国王的女儿,一个名叫Tour的儿子,从Mahenk那里得到了Madjin国王的女儿, 还有两个名叫 Retoual和Houmayoun。”鲍狄埃认为应该译为:“Djemchid有另外两个Mahenk的女儿的儿子”(Histoir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Paris, 1849, pp. 14-15)。鲍狄埃利用这个修正,拼凑出一整段故事:“这个Mahenk,就是大中国的国王穆王,于公元前1001至公元前946年执政,中国历史学家指出,穆王征讨亚洲西部蛮人并使其归顺。西部蛮人向其进贡双刃大刀和亚麻布料。之后他便游历了亚洲西部,欣赏到美轮美奂的瑰丽艺术(很可能是Ninive和伊朗地区的古迹,这都是Djemschid建造的)。”真是荒唐的想象!仅仅是发现Mou-wang 和Mahenk两个名字的相似,并没有注意到关于Djemchid的叙述是属于神话范畴,也没有意识到天子或者Fagfours经常出现在波斯史诗中,但从没也无法确定与中国历史的年代一致,至于所谓的Ma和Mou,henk和 wang的对等,鲍狄埃声称,这是由于中国和波斯文献中均绝妙一致地提及穆王到波斯并将其女儿嫁给Djemchid而断言的!《史记》之前提到穆王传说的主要文献有《穆天子传》(穆王造访西方王后,蛮族首领古书中称之为西王母,这段传说保存在《穆天子传》一书中,埃特尔博士将其译成英文Eitel, China Review, vol. XVII, p.223-240 and 247-258)、《列子》(第三章,只是将《穆天子传》中一部分故事加以再创造)。这些文献中都提及了“西王母”这个名字,但这是一个西方蛮族部落名字,与其他旅途中出现的地理名称没有重要联系(Eitel, China Review, vol. XVII, p.223)。穆王拜见了首领西王母,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君王,但这不是他游历的真正目的。另外,这些文献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王母是一位女性,司马迁也对西王母闭口不提。在《竹书纪年》(见理雅各legge,Chinese Classics,tomeIII,Prolégomènes, pp.150-151)中,只有:“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之后,“西王母”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外来词的音译,而被逐字解释为“西方女王母亲”。于是所有关于这位“西方女王母亲”的传说都与穆王西游的典故联系起来。再扯远一些,不但这个叫做西王母的人物与这段游历无关,就连穆王本人也不见得真有此游历之事。在《史记•周本纪》( 见Edouard Chavannes, 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 p. 265, n. 3)中,穆王执政时期司马迁没有谈到这次游历,相反在《秦本纪》中却谈及此事。这说明,司马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辑录者,这段游历故事在周国是闻所未闻的,而是发源于秦国。那么这个传说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造父和他神奇的马车队,这些马都有别致的名字。而造父被认为生活在穆王时期,文人们便将其西方的游历与穆王结合起来。当时秦国还是蛮族,这个发源于山西的传说,先是根据穆王与造父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年代关系,被人为地与中原王国的历史结合起来,之后便围绕对西王母名字的各种曲解,发展形成了各种奇闻怪谈。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西王母”来自于西方蛮族部落的名称。《竹书纪年》中写道:“舜九年,西王母来朝。”《大戴礼记》中亦写道,舜帝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琯”。舜帝是上古时代的一个神秘人物,传统编年史认为其生活在穆王之前一千多年。因此,如果同时在舜和穆王的时代出现西王母,就像《竹书纪年》中记载的那样,那就可能暗示着西王母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以其民族命名的君王。16世纪末中国学者胡应麟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西王母在舜统治时期就已经在此地有显赫地位,因此并非在周代穆王时期首次出现。我认为,这个名字应该是指一位外国君王。”①引自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三•三坟补逸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虞九年,西王母来朝……西王母已见于此,不始周穆也。以余考之,盖亦外国之君……《穆天子传》所交外国之君甚众,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经》但言蓬发虎齿有尾,如陆吾、泰逢之属,余别有辩。”——译者注〕这个假设在《尔雅》中得到证实:“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②注疏者认为“日下”是指日落之处的国度。(《释地篇》)
与《竹书纪年》一样,《穆天子传》亦出自汲冢,定早于公元299年成书。这是一本记载穆天子远游西王母国的旅行日记,我们可以利用这本书来确定这个国家的位置。仔细看来,书中涉及到两次相继的游历:第一次持续了643天,天子行至被认为是镐京的宗周③Edouard Chavannes, 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V, Paris, 1967, p. 93, n. 4.(现长安,属西安府)。四天之后,天子离开镐京开始新的游历,634天之后到达南郑。镐京与南郑两地距离不过160里,可见天子的两次游历都到达了同一地区,这应该是穆天子常驻的地方。这里我们只关注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西王母国位置的第一次游历。我们沿其路线,即从黄河壶口至黑水,应该是沙州的党河。38天之后,一行人到达西王母国,正如拉克伯里在其最有份量的著作中④见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chap.VIII, pp. 264-275 : The Si Wang mu and Muh Wang’s Expédition to Turkestan in 986 B. C.。所述,这个王国似乎被定位于焉耆(Karachar)⑤新疆塔里木盆地古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译者注与库车(Koutcha)⑥今新疆库车县,距离焉耆县约345公里。——译者注之间。
据《穆天子传》,来回一共643天。而据《竹书纪年》,穆王在位第十七年造访西王母国,且西王母同年回访了穆王。《穆天子传》应该是比《竹书纪年》更可信的,但是后者至少表明西王母国应该距离不是很远,至少不像佛尔克推测的那样,将西王母国定位在Arabie Heureuse⑦希腊、古罗马及阿拉伯半岛南部一带(今也门),是古萨巴文化中心。——译者注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穆天子传》中的游历时间之所以那么长,很有可能是由于途中走走停停,穆王不断受到当地部落首领的接见、宴请,一起狩猎以及祭祀。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穆天子传》还是《竹书纪年》,都没有证据表明西王母是一位女性。⑧佛尔克反对基于《山海经校注》中的一段《穆天子传》的异文而做出的论断。佛尔克错误地认为这些引用出自毕沅(1729—1797),而实际上出自郭璞(276—324),郭璞注写于《穆天子传》发现后四十余年,不能作为对该作的最终训诂结论。同时,郭璞是一位道家学者,与其他道家学者一样,给予历史著作较大的自由度。另外,他将西王母视为一位女性也不奇怪,因为公元4世纪时,道家传说中已经有女神西王母的说法了。再多说一点,即便我对《穆天子传》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也正是关于穆王与西王母这个人物的段落,因为这些文字与下文口吻不符,内容上亦打断了上下文,在我看来,完全像是窜入的。然而,用来翻译这个外来词的汉字却成为了流行词汇,衍生出各种关于“西方女王母亲(M è re reine d’Occident)”的神话。同样的现象出现在近代民间想象的“八百媳妇”老挝侯国(Xieng-hong 和 Xieng-mai)中,很有可能汉字“八百”是当地土语“男人”一词的音译⑨见Devéria, La frontière sino-annamite, p. 157, n. 1.。“西王母”一词转化成人物似乎早于司马迁时期,因为在司马相如(卒于约公元前117年)的一篇赋中①“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大人赋》,《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0页)——译者注。,西王母代表了长生不老,且白发载胜②颜师古注:“胜,妇人首饰也。”,俨然女性打扮。
如果《穆天子传》是一次真实发生的游历,并且最终到达焉耆和库车地区,我们就能认定穆王是这次游历的主人公吗?我不这样认为,理由如下:《周本纪》中,司马迁谈到穆王时[《司马迁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卷一,第250—265页],没有提到这次著名的旅行,仅以寥寥数语回顾了穆王远征犬戎的不愉快之行。相反,在讲述秦国(卷二,第5—9页) 和赵国(卷五,第8—10页)的章节中花费大量篇幅讲述了这次旅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是一位十分谨慎的编纂者,绝不随意篡改其原始资料,尽管他在秦国和赵国搜集到了有关这次游历的富有生命力的口头传统,却未从源于周国的资料中抄录到有关穆王西游的情况。我们由此可以推知,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源头。
自公元前8世纪秦国就盘踞在现在的山西境内。赵国尽管后起,也自公元前5世纪起统治了现在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这两大家族,领地毗邻,司马迁指出,两国源于同一祖先③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V, p.7〔《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9页):“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译者注。〕。在诸国中,这两国连接了华南和华东;而极有可能属于突厥的游牧民族,位于华北和华西。那么这两个种族的人民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两国有可能是深受中原影响而最终同化为中国人,但大量事实表明,这两国本身就来自于浩瀚的突厥部落中,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迁徙,时而占领时而败退于中国北方。④这是理雅各的意见(C.C.,vol. IV, p.141):“我认为毫无疑问,秦国人民主要来自于蛮族部落。”比如以下事实:直至公元前4世纪中期,秦国仍被视为蛮人,未被中原国家所认可。⑤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I,p. 62, 第3-6行〔《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译者注。〕同样,公元前307年,赵国武灵王正式采用北方胡人的服装和习俗,尽管历史学家考虑这是出于政治目的,但这也极有可能是重新回到老祖宗的风俗习惯。⑥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V, pp. 70-84,〔《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06页):“……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及后文——译者注。〕又如公元前678年在秦国第一次出现了亲近和宠幸的大臣妻妾跟随陪葬的可憎做法⑦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I, p. 22, n. 3;p. 45,n. 2;p. 58,n. 6. 正如高延(M. De Groot)指出,这种做法在中国出现,并不能说明此惯例始于中国(见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vol. II, pp. 723-724),毕欧(Biot)也赞成此习俗来自鞑靼地区的说法。(参见C.C, vol. IV, proleg., p.141-142)。这种习俗是匈奴人的标志做法⑧Mém. hist., ch. cx, p.5〔《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92页):“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译者注。〕,希罗多德也指出过这曾是塞西亚人(Scythes)的惯俗。在赵国,君王用死去敌人的头颅作杯饮酒,这也是匈奴人的明显特征,而匈奴人正是突厥民族的一支⑨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V, p. 49, n. 5.。所有这些指徵都说明,秦国与赵国这两个邻国和亲属国,属于一个庞大的突厥家族移民。
我们现在回到穆王西游的传说上来。这个故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以四或者八的数量出现的骏马。这些骏马各有其名,然而这些名字在中文里没有任何意义,在《史记》和《穆天子传》中的用字也不同:这完全是外来词中译的表现。另外,这些战马与旅者的功绩紧密相连。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突厥王阙特勤(Kul tegin,公元732年)的碑文上,显示了每一次战役中马的名字及其主人所立战绩。因此,这样一个出现在突厥民族文化厚地区的传说,亦具有明显突厥特征的情节,难道不足以证明这个故事并非源于中国?
那么这样一个异域传说又是如何与有关穆王的中国历史融合在一起,而在故事原文中穆王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大致的回答:如果我们明白中国的上古史是吸收了各地传说,并且其中很多反映了异民族文化的话,那么中国上古史是很好理解的。比如,夏朝开国君王禹帝,天下诸侯皆对其朝拜,却如何死于浙江省绍兴府的会稽山①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p.162, 末行;p171, 8-12行;tome V,p. 312-314, p. 313, 注释1末。上?整个上古时期此地都距离中国人民居住的地域十分遥远。在我看来,对此唯一解释是:当中国人与居住在中国南部属于现今安南人的一支发生联系时,便在那里遇到了一些有关一位伟大君主的传说,同样曾经汇集诸多属国君主并且死于会稽山。这个故事与禹帝的事迹有很多相合之处,于是中国人便在中国的环境下,无意识地吸收了一个越国英雄的事迹。当儒勒•凯撒(Jules César)入侵高卢,给当地神明取名为墨丘利、阿波罗、玛斯、朱比特、密涅瓦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②De bello gallico, vol. VI, 17. (《高卢战记》)还有公元前1000多年前中国派箕子统治朝鲜的故事,而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也就是秦始皇统治时才出现“朝鲜”这个名字。这种异常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中国人抵达朝鲜后,发现了颁布“八条之教”③“制八条之教”,参见《后汉书》,第一百一十五章,第4页。的开明君主的传说,便赶紧将这位朝鲜立法者的身份与编写了“洪范九畴”的箕子等同起来。就这样,箕子被搬到了朝鲜,即使其余的生平事迹与此并不相符④可以注意到司马迁在讲述箕子的章节中提及朝鲜时是很刻板的(tome IV, p. 230, 17-18行),参见《洪范九畴》的内容及箕子造访古都殷的故事。。
穆王之游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这是秦国和赵国的突厥民族传说,而中国人将之与造访犬戎的穆王联系在一起。
通过这种移位现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并极大可能地推测在原本故事中,穆王替代的真实角色究竟是谁。这里我们不去考虑外来民族口头收集的这样那样的轶事,我们只考察《穆天子传》中有关这次游历的详细的中文记载,这些记录不会欺骗我们,因为中文当时应当是秦国和赵国的官方语言,就像现在的朝鲜亦是如此。即使书写文本不像口头传统那样容易变形,如果《穆天子传》是后来与周代穆王关联起来的话,也应该有些事先巧合。而如若《穆天子传》的真实主角并不是这个周穆王,而是同音的秦国穆公(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在位),是不是就能验证各种巧合了呢?因为《史记》中告诉我们,公元前623年,秦穆公大败西方蛮人的国王(绵诸王),合并了十二个小国,拓展疆域千里,称霸西戎。⑤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tome II, pp. 44-45.《穆天子传》很有可能是秦穆公凯旋之行的记录,在其西部新的地盘上,接受各属国首领的朝拜。这个故事一路上编写,直到穆公回到自己国家时完成,而秦穆公死于公元前621年,刚好是这次巡游之后,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这篇故事的题目中,使用了这位君王的谥号“穆”。总而言之,《穆天子传》应该是完成于公元前621年或者是之后。这个日期要比生活在3、4个世纪之前的周穆王更加真实。因为公元前1000年时,中国文学还远达不到能撰写出如此科学性的恢弘著作。
反对这个看法的理由往往是由于“天子”二字,法律上这个称号只能用来称呼周朝国王。但是我自问是否因此无法得出后来以“穆王”替代“穆公”的理由。实际上,很可能由于穆公当时权力所达到的高度,可以窃取“天子”之称,而几代人之后,人们忘记了“穆天子穆公”,而自然地认为“天子”只有可能是穆王。说到底,这里提出的问题与激烈争论的周代石鼓问题十分相似:我认为很有可能石鼓上的刻字出自秦国一位晚于惠文王(公元前337—公元前331年)的君主,但是大多数中国书法家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或者周成王(公元前近1100年),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出现在这些刻字中的“天子”以及“嗣王”的称号只能使用于周代君王。事实上,这些正统的论据都赋予了无论《穆天子传》还是石鼓以不可接受的古老历史,但却压倒了《穆天子传》编纂于公元前621年以后以及石鼓铭文刻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历史可能性,而在这两个年代里,两者的出现是很自然的。总之,我们只需假设秦国君主的权力能担得起“天子”称号即可,其他推论都无法成立,但是中国学者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来证明,只有周代君王才能与游记和铭文作者相匹配。
对于佛尔克先生关于穆王游历乃发生于公元前10世纪并且造访阿拉伯萨巴女王的论断,我的反对如下:公元前623年左右,一位突厥的强大首领统治着现今陕西、甘肃和东突厥一带。为了接受新臣民的朝拜,他巡游至库车地区,根据突厥习俗,其马车队由骏马所驾,这些骏马在讲述者口中与英雄的功绩相连:马的名字透露出并非来源于中国。负责驾车的车夫是穆公的一个亲信,也是赵国突厥君王的祖先。他回来不久,穆公便死于公元前621年,而这时名为《穆天子传》的游记用秦国官方语言——汉语编纂完毕,也是中国关于这次游历各种故事的最早版本。这本小册子中,穆公可能被擅自命名为天子。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人将这个故事融入中国历史时,毫不犹豫地将穆公替换为生活在3、4个世纪以前的同音的穆王,因为穆王才真正有权被称之为“天子”。但是,这个穆王只是个僭越者,因为:第一,司马迁编写《史记•周世家》所使用的来自周王室的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及穆王之游。第二,关于这次游历的传说,都被定位在有明显突厥血统印记的秦国和赵国,且大量有突厥血统的人民居住在这两国。第三,鉴于我们所知的中国文学形制的发展,公元前10世纪时绝对不可能出现如《穆天子传》这样的游记。这就是我用以证明这次西方游历与周穆王无关的主要理由,而秦穆公却符合所有条件,应当为本次游历的真实主人公。
[责任编辑:王素珍]
I207.7
A
1008-7214(2017)01-0083-06
卢梦雅,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所博士研究生;杨文文,济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
*本文按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 Edouard Chavannes, tome V, Appendice II, LE VOYAGE AU PAYS DE « SI-WANG-MOU », Paris, 1967,pp.480-489 版本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