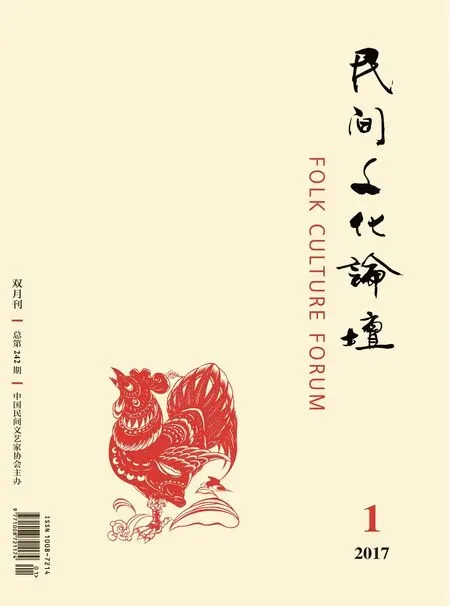试论活形态神话的传承
2017-01-27李子贤
李子贤 李 莲
试论活形态神话的传承
李子贤 李 莲
神话传承研究的重心,主要是探讨活形态神话及口头神话的传承。除了探讨传承人、传承场之外,更要关注神话传承的深层动因及机制,即价值取向、信仰体系、祭仪系统、文化心理结构等文化要素的参与状态;关注族群成员参与神话传承的程度,即人们对神话的依赖感及需求度。此外,还要探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神话传承状态及其构成因素的差异性。
神话传承;活形态神话;传承状态及机制;传承场域;传承主体
神话的传承是一个值得讨论却在神话学界少有讨论的论题,是一个已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却探讨得还不够深入的论题。对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而言,这更是一个绕不开的论题。
美国学者戴维•利明(David Leeming)与埃德温•贝尔德(Edwin Belda)在其合著的《神话学》中,专列了一章《神话的创造者》,涉及了活形态神话的传承。该书写道:“神话往往产生于这些巫师降神时唱的歌曲”。又云:“巫师一丝不苟地用行动把他的神话经验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因此说巫师的仪式歌曲是神话故事的根据,这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对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巫师的确是活着的神话人物”。“古代诗人是人神之间的媒介……荷马和赫西俄德认为,古希腊人在力求揭示神和英雄的神秘交往,而且正是荷马和赫西俄德能突破人类生存的界限,用语言把‘道’说出来”。①[美]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李培茱、何其敏、金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4—142页。其实,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巫师,不仅是神话的创造者,而且更多的是神话的传承人。当从巫师中分裂出了更高层级的祭司之后,祭司更是掌握和传承神话的核心人物。至于引文中提及的古代诗人如荷马、赫西俄德,他们不仅参与了神话的创造,也是神话重要的传承人。引文中所谓的“道”,就是神话思想与神话思维这一神话创造的母胎。该章的论述不乏独到之处,却没有说清楚神话是在何种具有某种规定性的文化语境中被创造出来。当然,该章主要讨论的是神话的创造者,没有过多提及神话的传承,是可以理解的。孟慧英教授在《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一书中涉及了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承。例如将少数民族神话讲述的仪式场合分为四类:祭天祭祖仪式、丧葬仪式、结婚仪式及其他仪式。②孟慧英:《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179页。杨利慧教授在《神话与神话学》一书中也列了专节探讨了神话讲述的场合和神话的讲述者,提出了一些颇有创意的见解。③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4—179页。上述两位学者的相关论述,都为进一步探讨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承提供了某种启示。
神话的传承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存活于特定的社会民俗生活之中,作为一种“活体”,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这一“母体”中存活下去的活形态神话。一般而言,活形态神话的传承必须与民间信仰的存续、祭仪系统的存续以及作为群体的整个社会成员对神话功能的需求度的存续等要素相连属。活形态神话传承的载体,是某种特定的民俗生活环境中的族群成员及与活形态神话相连属的祭仪系统,并有特定的传承场。离开了上述载体,活形态神话的传承将失去根基。
第二,口头传承的神话。通过存乎于心,口耳相授,经老一辈人的讲述,将神话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口头传承的神话也具有活形态神话的某些特征。不过,它已经只是一种“讲一讲”的故事,不一定与原始信仰和民间信仰、宗教祭仪以及特定的吟诵场域等相连属。应该指出的是,它仍然是一种集体记忆,神话传承的主体仍然是该族群的全体成员,只不过它已经是由个体讲述、相关受众在悉心接受而已。这种口头传承的方式与作为典型的活形态神话传承的方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活形态神话的传承虽然是由个体吟诵或讲述,但是,此时参与其中的所有成员早已将神话的叙事内容谙熟于心,已在与吟诵者发生某种互动,早已进入了神话叙事内容所规定的情境之中。吟诵者也许只开了一个头,或只吟诵其中的某一个片段,但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对整个神话叙事内容所述的一切已了然于心,而不是要等讲述者讲完或吟诵完神话的叙事内容之后,才明白该神话讲的是什么。我们曾经提到过所谓的“潜隐神话”,这仅仅是对非我族族人之外的人而言,才被视为“潜隐”的。因为对本族群的族人而言,在某个象征符号背后隐藏着的神话叙事内容,大家都十分清楚。口头传承的载体是存乎于心,口耳相授。离开了上述条件,口头神话的存续就难以维系。
第三,以文字记录下来作为书面文本形式传承的神话,其传承的载体就是书面文本。例如在我国的《山海经》《楚辞》等文献中,就有许多被记录下来并传承至今的神话。此种传承方式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以后才出现的,而在文字产生以前,只可能有上述两种传承方式。因此,书面传承的方式是相对晚近才出现的。虽然用文字记录的书面文本神话也有许多重大研究课题,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谱》是如何写定的,《神谱》究竟是记录当时传承的神话呢,还是赫西俄德的创造?日本的“记纪神话”在被记录下来之时,日本神话的具体存在形态是什么的等,都是些值得研究的论题。不过,当它一旦被用文字写定之后,就少有发生变异了,而且只要它不是孤本而被丢失,就一直会以书面文本的形式传承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研究神话的传承,主要是研究活形态神话是如何传承的。
当我们进入研究活形态神话是如何传承下来这一论题的时候,还必须就神话的发展历程分阶段进行梳理。概括起来,活形态神话的传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始氏族社会去观察活形态神话是如何传承的,但通过考古学、原始社会史、原始文化史以及相关资料,是可以窥视或推测出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神话的传承状况的,这是一条途径。还有一条较为便捷并且可以直接观察、研究的途径,便是从“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那里去加以考察。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并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典型的原始氏族社会,但它毕竟是保留原始氏族社会基本特征较多的观察、研究对象。
在云南,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期的少数民族,有长期生活在贡山县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有长期生活在怒江大峡谷的怒族,有长期生活在西盟县阿佤山中心区的部分佤族。上述几个地区的少数民族是我们直接观察、研究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期的神话传承之理想考察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本书中已有专节对独龙族神话的概貌及特色作了综合的介绍和论述,这里就不赘言。讨述独龙族神话的传承,首先要弄清20世纪60年代以前独龙族社会的整个人文环境及相关民俗。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整个独龙族社会中仍弥漫着原始信仰的氛围,巫师还在不断地产生,以巫师为中心的祭仪仍在传承①参阅蔡家麒:《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编印,第75页。。笔者于1963年9月到12月在独龙江河谷进行田野调查时的强烈感受是,构成对人类最大威胁的是各种自然力、自然灾害的化身——“布蓝”,它被视为一种对人类极为凶恶的鬼,似乎人们认识了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布蓝”(鬼)。例如石崖鬼、山鬼、水鬼、肚子疼鬼、头疼鬼、牙疼鬼、脚疼鬼等等。据说“布蓝”看得见人,人却看不见“布蓝”。对付“布蓝”的办法只有一种,即请巫师将其驱逐之,杀灭之。然而“布蓝”却是赶不尽、杀不绝的,因此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布蓝”。反映在神话中便是有许许多多人与鬼(“布蓝”)作斗争的神话广泛流传。在独龙族的观念中,还未出现神的概念,但是某些居于天界或山上且能庇佑人间的鬼具有神的性质。人们对此种类型的鬼怀有虔诚之心、敬仰之意,总是通过某种仪式祈求保佑。其中最典型的祭仪就是每年一度的“卡雀哇”(祭天仪式,又视为年节)。据笔者的调查,类似独龙族的“布蓝”在佤族中也有传承,佤族将其称为“内”,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据说有些是独脚的,对人类危害极大。此外,在日本冲绳诸岛的民间信仰中,也有类似于“布蓝”这样的鬼或精灵存在。
独龙族信仰的神主要有:天上的鬼和南木(人神之间的信使),以及司风调雨顺的山鬼、司狩猎的猎鬼等。在独龙族的巫这一系统中,祭司阶层处于初始的产生阶段,在笔者的印象中祭司只是一些能与具有神的性质的鬼打交道的巫师开始具备了祭司的性质,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称谓。一般来说,他们能够从事与神交往、沟通的仪式,谙熟本氏族、本民族的神话,而一般的巫师则只与“布蓝”打交道,或为人治病,或为人驱鬼,对于与神界相关的祭祀虽然已有所了解,却不专于此道。在独龙族的宗教祭仪中,大型活动极少,除了剽牛祭天仪式,即“卡雀哇”之外,似乎就没有大型的仪式,而不像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以及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至少有十多种大型的祭祀活动。张桥贵先生在其《独龙族文化史》中,除“卡雀哇”之外,将独龙族的宗教习俗及相关祭仪概括为以下八类:辟邪祟、禁忌、释梦、丧葬、神判、占卜、婴儿取名仪式、保命仪式②张桥贵:《独龙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9—91页。。以上,便是独龙族神话赖以传承的文化语境。这是一个神话在不断产生及传承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对神话的需求度很高的时代,也是一个神话的功能开始彰显的时代。独龙族神话的传承,有的是在氏族内部展开,如氏族起源神话;有的则是在包括氏族、家族在内的整个民族中传承的神话,如人类起源、天地分裂以及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等。由此可见,神话传承的主体是该族群的全体成员。综合考察独龙族神话传承的状况,大致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人们对神话的态度具有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鲜明特色,神话确乎是一种“神圣的历史”,是人人皆知且必备的知识体系,是人人都必须明白的各种事物(自然及社会现象)由来的权威性解释,在人们的心目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诸如,人们笃信克木克当山曾经是连接天与地的天梯,是天地分裂的地方;人们笃信卡俄卡普神山是洪水时两兄妹的避难之所,两兄妹生下的九对兄妹是从这里分手,成了散居于各地的各个民族。由此也可以看出,神话是深藏于人们的心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或掌握一些神话,神话确乎是一种集体记忆。
第二,在独龙族的民俗生活中,与祭仪相关的神话并非独龙族神话的全部。比较突出的有天地分裂神话与“卡雀哇”由来神话,祭仪与神话二者互相支持,融为一体。此外,关于祭祀“几布蓝”(崖鬼)与“几布蓝”神话相联系,猎神祭仪与猎神神话相联系,以及对卡俄卡普神山的祭仪与卡俄卡普神山创造万物及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相联系。一些与祭仪没有明显关联的神话,如人类起源神话、人与鬼(“布蓝”)斗争的神话,还有一些否定性的文化起源神话,如独龙族为什么没有药、独龙族为什么没有文字等,都与祭仪没有明显的关联,但与某些生活理念、生活习俗相关。笔者1963年在孟顶村拜访了一位百岁老人孟斗,他对笔者讲述了许多独龙族的神话,其中当讲到独龙族的人类起源神话时,郑重地对笔者说:“我们和傈僳族不一样,傈僳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我们独龙长(音zháng,即‘人’)是天神嘎美嘎莎用石岩上搓出来的泥巴捏成的。”每年,人们在刀耕火种的山地里收获粮食时,总是要将地里的一小块粮食留下,不收割,用以敬献天神。原因是:天神的女儿与地上的一个男子结婚后,天神给了他们谷种带回人间,人间才会种庄稼。
第三,独龙族神话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家族或氏族长老大多会在一些重要活动时在火塘边讲述相关的神话。据笔者1963年的考察,独龙族神话的传承人、讲述者并不只局限于主持宗教祭仪的巫师,大凡上了年纪、在家族或氏族中享有威望的老者,都知晓神话。一些民间艺人如歌手、故事家,都掌握相当数量的神话。不过也有一些不成文法的禁忌,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不会轻易讲述神话。即便是当地有名的女性歌手,虽然她也谙熟本民族的神话,却不参与神话的讲述。笔者当年曾在丙当村拜访了一位著名的女歌手丙当妮。村民都说她知晓独龙族神话。笔者在旁敲侧击中也深知她谙熟独龙族神话,可是当笔者恳请她讲述神话时,她总是笑笑,一言不发。当父权制取代了母系制之后,具有某种神圣性、话语权的神话之讲述,已成了男性的一项专利。
第二阶段: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历史阶段。在云南及周边地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前,尚有一些长期停滞在文明社会初期阶段上的少数民族,如大、小凉山的彝族,西盟的佤族,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以及景颇族、基诺族、哈尼族等。在上述民族中,祭仪系统日臻完善,许多大型祭仪已发展起来。驱鬼与侍神两个领域的分工日渐明显,于是原来的巫师系统便逐步分裂为地位越来越高,专门侍神、敬神,专门主持各种求神、娱神仪式的祭司;原来巫师中的一部分仍然从事驱邪送鬼的各种具有巫术性质的活动,与祭司相比,地位相对低下。在纳西族中就有了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在大、小凉山等地的彝族中就有了祭司毕摩或贝玛,有了巫师苏尼;在西盟佤族中就有了祭司巴猜(又称魔巴),以及巫师巴斯保。大自然的沉重压迫,阶层的分化与对立,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化与多样化,使得人们不仅需要一种心灵的慰藉,而且还强烈地期待能在心理上和现实生活中建构一个“安全屏障”和保障体系,因此,人们对祭司、巫师的依赖感、需求度日趋强烈。其中,祭司不仅被视为与神沟通的媒介,是传递神意的信使,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被视为具有半人半神的现世神。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元江县大羊街乡拜访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哈尼族大莫批(祭司),当谈及莫批在哈尼族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时,他说:“如果没有莫批,哈尼族不会过日子了,娃娃生了长不大,老人过世了送不走。”莫批在哈尼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民族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政祭合一的情况,即地位最高的祭司也是最高的行政长官,诸如部落酋长等,在唐代前后彝族中出现的大鬼主就是典型的例子。之后,政祭分离,但是祭司在民间仍然拥有崇高的地位。直到近代,在哈尼族中仍然将头人、祭司与工匠视为地位最崇高的三种“能人”。祭司地位的上升,体现在宗教民俗里面,不仅表现在只有祭司才能主持重大的宗教祭仪,成了唯一能与神对话沟通的人,而且也成了该民族神话传承的主导性人物。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主持各种祭仪中都要分别吟诵各种类别的长篇祭辞,而这些祭辞则大多与各种神话内容交织、融合在一起。这就要求祭司必须谙熟本民族的神话。不过,此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神话传承的主体依然是该族群的全体成员这种格局。这是因为,人们不仅对神话的需求度仍然较高,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然留有神话的重要位置,而且每个人从小到老在各种祭仪中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祭司们的对相关神话的吟诵,已逐步将本民族的神话纳入自己的心灵之中而被储存下来。
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神话的传承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神话传承的场域已出现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性,即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场域吟唱神话而不能在其他场合随意吟唱神话;只能在某个特定的场域吟唱什么神话而不能吟唱什么神话。例如丧葬仪式与婚嫁仪式都分别吟诵不同的神话内容,这在大、小凉山彝区就形成了“白勒俄”与“黑勒俄”之分。楚雄彝族也有类似的现象,因此才有各种各样的《梅葛》出现。
第二,一定的祭仪都以特定的神话内容为注脚、为依据,这样,某种特定的祭仪与某种特定的神话内容互为表里,融为一体,这就有利于某些类别的神话传承。例如,历史上纳西族的祭天仪式,几乎就是创世纪神话的重演。历史上佤族的从拉木鼓仪式到祭木鼓换人头仪式,不仅与“司岗里”神话相联系,而且也是“司岗里”叙事内容的重演。每当我们想到神话讲述的时候,大多只想到祭司一字不漏地把整个神话内容吟诵出来,即把神话的叙述文本全部讲述出来。这当然是神话传承的主要方式。然而许多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神话传承方式,即在某种重大祭仪中,人们已在无声无息地演绎着某种特定神话的叙事内容,对于非我族群的旁观者而言,则全然不知其所展现出来的神话叙事内容是什么,必定要通过一定的田野调查才能了解其中的奥秘;而对于主持和参与仪式的当事人而言,则一切已了然于心,个个心知肚明。这也是潜隐神话的一种表现形态。
第三,传承人多元化。这个历史阶段也当属于“神话时代”的延续期。神话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强大功能,人们仍然将神话视为必备的知识体系,仍然将神话视为神圣事物的由来及历史,因此,神话传承人的多元化就是必然的了。除了祭司以外,巫师也了解一定的神话,在驱邪送鬼等巫术活动中,也离不开某种神力的支持,也同某些神话息息相关。因此,巫师也是神话的传承人之一。一些家族长老、头人也大多谙熟本民族的神话。每个家庭中的长者也能够多少讲述一些神话。很多民间艺人如故事家、歌手等也或多或少地了解和掌握该民族的一些神话,这是他们成为民间艺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第四,神话传承载体的多样化。神话的滥觞,神话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象征符号的拓展与丰富,神话依然深入人心并占据了心灵世界中的重要位置,就使得神话传承的载体丰富多样起来。不仅有外显的各种文化符号,也有许多潜隐的文化符号随之出现。例如,某座山、山洞、某块祭石、某种动植物如鹰如虎如鱼如蛙如葫芦如树等,都成了某种神话的象征符号。鱼成了哈尼族的创世神;鹰成了彝族英雄神“支格阿鲁”的化身;青蛙成了壮族民间信仰中雷神的信使;虎成了楚雄地区彝族某一支系神话中万物始创的本源;葫芦成了各民族神话中母体的象征。
第五,创世史诗的出现强化了神话的传承。虽然尚处于原始氏族阶段上的独龙族已经产生了创世史诗,但笔者认为,创世史诗的产生和形成大多是属于这一历史阶段。创世史诗的出现不仅是从氏族神话、部落神话向民族神话过渡的重要标志,不仅是将各自独立、相对分散的各种类别的神话加以系统化之后而形成了体系神话之重要的一步,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该民族神话在民间的传承。
第三阶段:传统农业社会阶段上的神话。传统农业社会指的是直到现当代仍较相对完整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广大农村。这种传统农业社会在云南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90年代。与上一个阶段相比,神话的传承又有了新的变化。神话传承的主体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知晓本民族神话的人在逐步减少,除了年长者之外,在许多青年人中已逐步失去了对神话的需求度和依赖感。这样一来,神话的传承就逐步转移到了祭司、民间艺人和某些家族长老的身上。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些重要的民间信仰仍在存续,例如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农业神崇拜、村寨守护神崇拜等。因此,与上述民间信仰相连属的宗教祭仪仍在存续,从而在许多民族中,祭司仍然没有“下岗”。许多与祭仪相关联的神话依然在祭仪中重演,例如纳西族的祭天,彝族、哈尼族的丧葬仪式等,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90年代。至于广泛传承于哈尼族、彝族等许多民族中的祭竜仪式,即祭祀村寨守护神则一直延续至今。一般而言,竜神都有相关的神迹在民间传承。一些口承的神话依然有人知晓,还在民间传承,但讲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在这一阶段上,神话的传承出现了新的特点。
第一,与神话相关联的祭仪逐步减少,神话的传承场开始萎缩。例如在西盟的佤族中,自20世纪50年代革除了猎头习俗之后,《司岗里》及相关的讲述猎头功能的神话便逐渐失却了传承的重要载体——拉木鼓仪式和祭木鼓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神话逐渐退出了人们的集体记忆,除了祭司、民间艺人、家族长老等少数人员之外,能系统讲述神话的人便越来越少了。在沧源地区,由于猎头习俗革除的时间较西盟早,以致在十多年前就已无人能吟诵《司岗里》;知晓本民族神话的人也越来越少。
第二,这就导致了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仍以佤族为例,由于与猎头祭祀相关联的祭仪逐步消失,连接文化生态系统诸要素的链条出现了断裂,讲述猎头非凡功能的神话也就逐步失传。同样,由于拉木鼓仪式、人头血祭的消失,系统吟诵《司岗里》的传承场已日渐萎缩,最终导致了与《司岗里》传承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链之断裂。
第三,这又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某些神话的功能正在日渐消退乃至丧失。一旦人们对神话的需求度减弱,即神话功能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消退,那就离某些神话的失传为时不远了。
第四,如前所述,在这个阶段上,神话传承的主体已不再完全是该民族、该地区、该村落的全体成员,那么,能够了解、掌握本民族神话的人,就只有祭司、民间艺人和家族长老等少数文化精英了。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农业社会这个阶段上,在很多民族中有些支系、有些地区、有些村落,祭司早已不复存在。例如《梅葛》的故乡大姚县马游村,祭司早已消失;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石屏、开远、蒙自等地居住在坝区的彝族,大约在20世纪60、70年代前就已没有了祭司。当然,这并非是神话的绝唱阶段,只是与上一阶段相比较,神话的传承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点:该民族的一些主要的神话,特别是以创世神话、洪水神话为主轴组织起来的创世史诗,仍得以存续;许多与民俗生活中的祭典、婚丧嫁娶相关联的神话也还在存续。
那么,当下云南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还在传承吗?其传承的状态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和特点呢?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乃至某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及差异性,其聚居地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就使得有些民族或有些民族的支系直到当下仍然维系着自己独特的民间信仰,维系着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某些宗教祭仪与民俗,仍然存续着与民间信仰、宗教民俗相关联的活形态神话。例如,大理白族聚居区的一些本主神话,宁蒗县永宁乡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干木女神神话,红河州哈尼族与昂玛突祭仪相关联的神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红河州开远市彝族支系仆拉人中仍在存续的竜神神话、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及洪水型天婚神话等。这里我们拟以仆拉人的活形态神话为例,对其传承现状及传承特点进行讨论。关于祭竜及其神话。在开远仆拉人中,都普遍传承着祭竜仪式。除了每年定期举行的集体祭祀之外,还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不定期的对竜神的祭祀。前者是祈求竜神即村寨守护神保佑村寨平安、六畜兴旺、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后者则是求子求福,或者当家庭遇到某种灾祸时祈求竜神的保佑,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人们认为,竜神都具有特殊的神力,能够斩妖除魔,驱邪禳灾,而且都有相关神话叙述其神迹。直到当下,在碑格乡的仆拉人中,“祭龙习俗仍保留其原生形态,主要特征有三:一是龙树为村寨守护神的象征;二是祭龙多为群体性之祭仪;三是皆有一则解释祭龙由来的神话。其母题是:当时,村寨附近出现了一个恶魔,给人们带来灾祸。后来,有一个神制服了恶魔,为民除害,被尊为(非汉族之龙)神,并为其举行祭祀”①李莲、曹定安、李子贤:《开远市彝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适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页。。关于洪水神话与相关民俗事象。笔者在2008—2010年间对开远市仆拉人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大凡有婚丧嫁娶等仪式都会由贝玛(祭司)吟诵洪水型天婚神话或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值得关注的是,洪水神话还与当下的某些民俗事象互为补充,融为一体。例如,在一则洪水神话中讲到:“几天后洪水退下,两兄妹藏身的木桶落在了溶洞旁边。两兄妹出来后看到木桶被两棵树挡着才没有掉进溶洞。其中一棵叫‘撒玛石’树,一棵叫‘师石’树。由于这两棵树救了兄妹俩的命,被称为是能够给人带来吉祥幸福的两棵树。后来,仆拉人祭龙的‘龙门’就必须用这两棵树搭建,祭龙的龙树也要从这两棵树中选出”。人们仍将洪水后剩下的两兄妹视为始祖,因此,在“架吉村祭龙开始时,贝玛所念咒语的头句必须是:‘男神与男祖,女神与女祖……’”。另外,洪水神话还与 “祖宗木刻”所用的树木联系在一起。在宗舍村仆拉人的洪水神话中讲到:洪水后两兄妹是落在了多依果树上,才未被逐渐退去的洪水卷入溶洞中。后来人们就视多依果树为一种圣树,将其用来制作象征祖先的木刻,即祖灵牌,供奉于家中。②参阅李莲、冯熙:《开远彝族地区洪水神话与传承》,见李子贤、李存贵主编:《形态•语境•视野——兄妹婚神话与信仰民俗暨云南省开远市彝族人祖庙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6、357页。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探讨神话的传承,是一个极具魅力的论题。一般而言,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神话的传承场和载体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神话在短期内不会消失,然而它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已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但就开远彝族地区而言,还保留着有利于神话继续传承的民俗环境,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村民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彝族神话传承的主体。其二,仍存续着各种祭仪、节庆等较完备的传承载体。其三,在开远彝族的许多村寨中,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场和积淀场。其四,在一些山区村落中,贝玛(祭司)的存在,是各种祭仪、节庆维系和传承并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关键因素,也是包括神话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得以继续传承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五,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当下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参与对包括神话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之保护、传承与弘扬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即在当地工作的一些本民族的中、小学教师以及文化干部③参阅李莲、冯熙:《开远彝族地区洪水神话与传承》,见李子贤、李存贵主编《形态•语境•视野——兄妹婚神话与信仰民俗暨云南省开远市彝族人祖庙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4—355页。。由此可见,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民间信仰还在存续,人们对神话还有着某种程度的依存感和需求度,活形态神话的余波就会依然在荡漾。
神话的存活必须依附于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活形态神话的传承也必须依存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与活形态神话传承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系统有哪些构成要素呢?第一,某些原始信仰、民间信仰仍在存续,某些崇拜形式如天神崇拜、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守护神崇拜等,仍然是人们宗教、民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人们对神话的依赖感、需求度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神话的功能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得以发挥,以满足人们的某种心理需求。讲述事物神圣起源的种种神话依然是人们民俗生活中的必备的知识系统之构成要素和权威性解释。对于许多生活习俗、宗教祭仪,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是由某种神话来规定的。第三,由于神话与某些原始信仰、民间信仰相连属,有的神话便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及话语权,这样,神话的吟诵场合就必须是某种特定的场域。例如节日庆典、宗教祭仪或婚丧仪式。虽然有些神话的讲述或吟诵并没有严格的场域规定性,但也有讲述的严肃性、严谨性特征。第四,由于以上要素的参与,神话的吟诵者、讲述人就拥有了某种特别的身份。也许该族群、该社区、该村落的全体成员都知晓某些神话,但只有祭司、民间艺人和德高望重的长老才能充当神话讲述、吟诵的角色。第五,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或多或少都留有神话之存在空间。换言之,人们对神话有着一种尊重、敬仰,乃至笃信的态度。正是以上要素之整合,构成了神话赖以存活、赖以世代相传的文化生态系统。
如果说活形态神话的传承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那么,为什么千百年来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活形态神话赖以传承的文化生态系统又一直得以延续下来呢?据笔者初步归纳,主要有以下几项缘由:
一是在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其原生性的文化一直得以传承下来,大多没有被外来的异质文化所覆盖①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只有傣族在传入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之后发生了重大的文化转型,许多原生性的文化被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相关民俗所取代。不过也有许多傣族的原生性文化保留了下来。例如与稻作祭仪相关的某些文化习俗仍有传承。傣族周边的部分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也转而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不过,他们的很多原生性文化依然有所存续。。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开始传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拉祜族、佤族等民族地区,但远没有达到将其原生性文化覆盖的程度。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中仍然存续着许多非常古老的原始信仰,如万物有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动植物崇拜等。
二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历时久远的与其他民族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中,已逐步形成了一种文化自我保护机制,即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中大多能做到丰富自我,提升自我,而又不丢失自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白族、纳西族,至迟在唐代就产生了与我国中原地区汉儒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他们都能够在吸收汉儒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文化特质,却又依然鲜明地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征。即便是傣族,至迟在明代中叶以后就已开始了佛教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化。其二,某些属于傣族原生性文化的原始信仰与相关民俗依然被保存至今。谷神信仰及谷神奶奶的神话,勐神、寨神信仰及相关神话等的存续就是一些典型的事例。
三是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该民族自身的传统因素对其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其历史主要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这就使得某些民族的文化形态及构成要素极为古老。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怒族,滇南地区的佤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就属于此种类型。其中以佤族最具代表性。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佤族的社会民俗生活中,仍存续着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的古老民俗。有学者指出, “獠即濮”,再将《魏书》中的相关论述梳理出古代濮人之以下民俗事象:“无姓名,男女称呼按出生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名;房屋为‘干栏式’建筑;族群首领推举产生,称其为‘王’,‘王’者有二鼓,牛角一对;纺织‘兰干细布’(桐桦布);祭鬼神;猎头习俗”①段世琳:《佤族历史文化探秘》,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我们由此看到,以上古代濮人的诸种民俗事象,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仍在西盟等县的佤族中存续。
四是特殊的“文化—地理单元”也为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性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载体。在云南历史地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分布格局,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许多既相对独立又自成体系,宛如星罗棋布的“文化—地理单元”。以西盟佤族自治县为例,这里虽然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但还居住着少量的傣族、拉祜族。在现今西盟县城所在地的附近,有一个叫勐梭的傣族寨子,虽然只居住着近百户的傣族,周边几乎都是佤族(距离最近的佤族寨子只有几公里),而距离孟连县傣族聚居区却有数十里之遥,犹如浮悬在佤族文化海洋之上的一座文化孤岛。然而至今依然完整、鲜活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又如在拥有上百年工业化历史的开远市,虽然这里自明代以后由于汉人大量移入,汉儒文化极为发达。一百年前通车的滇越铁路早已为开远传入了西方文化,导入了工业文明。然而在离开远市区仅80公里的碑格彝族乡,时至今日还较完整系统地存续着彝族支系仆拉人的传统文化。让人惊讶的是,碑格乡村村有贝玛,而且新的贝玛还在不断地涌现。作为祭司,贝玛经常被人请去主持各种祭仪,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比较崇高,受人尊敬,许多古老而具有仆拉人特色的神话还在民间传承。在离开远市区仅20公里的彝族老勒村,虽然周边都是汉族村寨,却一直存续着具有彝族鲜明特色的“人祖庙”,仍传承着与“人祖庙”相对应且具有当地彝族特色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②参阅李莲、曹定安、李子贤:《开远市彝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适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类似勐梭傣寨、碑格彝族乡、老勒彝族村这样的文化孤岛,在云南比比皆是。她们凭藉着这种特殊的“文化—地理单元”,在顽强地维系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让本民族的文化既连接着古老的历史,精准地定位着自己的民族属性,却又与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相互接纳与交融。这样就使得许多分散居住的少数民族村落成为了一块块神奇、迷人的文化绿州。
[责任编辑:丁红美]
I207.7
A
1008-7214(2017)01-0055-09
李子贤,云南大学教授;李莲,普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