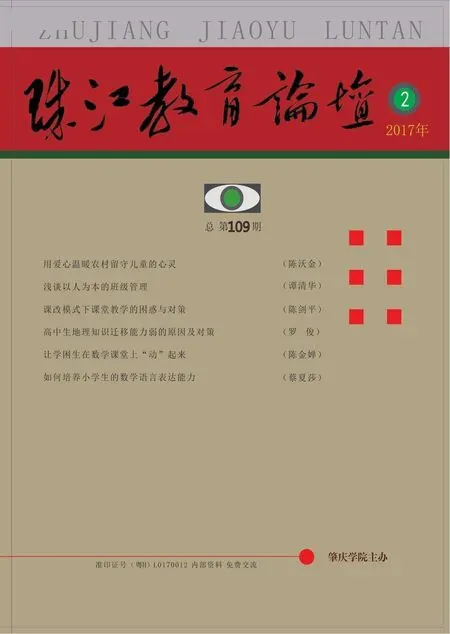真善美的追求与自由环境的营造
——余易木作品评析兼论繁荣文艺创作的问题
2017-01-27胡应泉
胡应泉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7)
真善美的追求与自由环境的营造
——余易木作品评析兼论繁荣文艺创作的问题
胡应泉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7)
余易木是一个被文学评论界长期忽视的作家。他作品具有很深的思想内涵和很高的艺术境界,需要充分地挖掘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给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回顾余人生的人生以及创作经历,会给人们以许多深刻的启示,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余易木;作品评析;兼论文艺创作
余易木,这是一个在当今文学界显得相当陌生的作家。他于1980年代初在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十月》上先后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春雪》和一部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在社会上曾经引起过极大的反响。此后就没有再公开发表作品了,文学界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然而,文史学者丁东先生却对余易木的作品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的小说,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是那些套着当时意识形态枷锁的作品所能比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信以后的史家会认同余易木的价值。”[1]笔者经过细读他的作品,发现其文学创作水准确实非同凡响,其作品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也是很少有作家能够企及的,因而认同丁东先生的判断。这样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不应当长期被埋没,被忽视,而应当引起评论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充分地挖掘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给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同时,结合他的人生以及创作经历,也会给人们许多深刻的启示,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余易木作品
《春雪》写于1962年8月,讲述的是一对对革命以及未来充满天真理想的年轻恋人,因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而不得不分手,相隔五年后又在北京的一家电影院相遇的故事。在当时青年的心目中,革命是最崇高的,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情都要服从于它。他们当初的爱情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欢乐。“1956年国庆节的夜晚,就在这里,就在这寂寥的广场上,我拉着她的手,在狂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到处都是喜悦的脸,到处都是友谊的手,到处都是奔放的热情,到处都是忘我的沉醉。”[2]22可是到了1957年,当男主人公被打成右派时,他的恋人却只能选择结束他们的爱情,并且真诚地认为考验的时刻到了,为革命牺牲爱情的时刻到了,真诚地认为他对人民犯了罪,尽管他是她最亲的亲人,真诚地认为没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不可能存在纯洁的爱情[2]25。然而世事难料,在1958年年底,女主人公因为向她所在的研究院党组写了一份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在随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变成了院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被开除了团籍,下放到农场劳动两年多以后才回来。政治运动的残酷和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过来,“现在,我明白了。我不怪你。现在,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但是,当时,当时我是那么的年轻,幼稚,那——么——的——年——轻!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得:在这时兴真理的时代里,多的却依然是谎言!”[2]26他们的心里都留下了永远的创伤,但又从来都没有真正忘怀对方。他们再次重逢之后,互相理解了对方,却不能再重新结合在一起了,因为横在他们之间的,不是一般的五年,而是一道深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1957[2]29。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先是男女主人公意外地重逢,然后回忆起他们过去的遭际,最后又只能无奈地告别。小说的篇幅并不长,故事的情节也不复杂,重在表现两位主人公各自的心路历程,却把那个时代政治上的风云动荡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细致地体现了出来,语言哀婉凄美,意境深沉幽远,让人叹息,又久久深思。
《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至1965年4月,讲述了周冰、梅雁、杨芸三个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心灵所受到的压抑,所遭受的苦难人生。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之中,但又相濡以沫,心心相印。男主人公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几句话被打成了右派,9月初被校长作为所谓的“废品”,处理到了青海。他在青海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经历了大跃进狂热的浪潮和接踵而至的饥饿岁月,经历了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时刻,也经历了不幸的初恋的意外欢乐[2]91。在这里,他遇到了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拒绝揭发别人而被开除团籍的梅雁。在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他们工厂来到青海湖边的刚察垦荒。当周冰因为饥饿得浑身脬肿的时候,梅雁慷慨地送给了他四两粮票。他们之间因为互相怜悯而逐渐走近,并逐渐相知相爱。梅雁关心他的生活,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并帮助他把论文翻译成俄文,投到苏联的一家著名科学刊物上发表,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的处境。当她在为是否要回到内地而犹豫不决时,他虽然对她充满了深情与不舍,但是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以及为她的幸福着想,他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毅然叫她回到内地自己的丈夫身边。他无法忍受感情上的苦苦煎熬,决定为了她的幸福跟她割断关系,但又无法做到。“我是人!我为什么要冒充圣人呢……”[2]148他调到福州工作后,经过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杨芸。经过近半年的相处,他们俩建立起了爱情,并准备结婚成家。但在结婚前一个星期,他却离奇地失踪了。原来梅雁回到并不关心她的丈夫身边后,怀孕生下了女儿,自己却难产而死。周冰匆忙赶回上海与她见了一面,决定承担起照顾她留下的女儿以及老母亲的责任,同时只能选择与杨芸分手。他曾经想过要向她解释一切后再分手,但却缺乏足够的勇气,怀疑一个姑娘能够原谅自己未来的丈夫心里爱着另一个女人[2]162。后来杨芸出差到上海,在一个公园意外地遇到了周冰。周冰把她接到家里,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地向她解释了一遍。过去这几年,她虽然饱受心灵的折磨,心里仍然深深地爱着他。听完他的讲述后,她道出了自己并未结婚成家的真相,又接受了他。相对于《春雪》,在《初恋的回声》中政治的氛围没有那么的浓厚(但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也得到了准确的反映),主要讲述男女主人公虽然面对巨大的人生困境,面对现实生活的各种打击以及束缚,却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构思十分精巧,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是一部出色的爱情小说。
余易木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归入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伤痕文学一类,但是在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上,在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表现上,在对人性和道德的挖掘上,在结构的营造和语言的运用上,又在那些同类的作品之上。尤其是他的作品是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半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了,让人们对他写作的超前性和无畏性更加钦佩。须知就是到了新时期以后,许多作家在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以及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等方面都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同时在他的作品中,也丝毫看不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而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理智与情感以独特的艺术方式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即使就是到了新时期以后,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政治上也仍然与主流政治亦步亦趋,并没有超出它所设定的框框,在语言上也仍然充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并没有多少鲜活的具有个人风格的语言。在那样一个充满禁锢的年代,他大胆地描写和讴歌爱情,对压抑和扭曲人性的极左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控诉,执著地追求着真、善、美。他的作品所讲述的都是爱情故事,但是在这些爱情故事中,政治上的波谲云诡,现实的残酷与荒谬,人们对生活的绝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人性的高贵、卑劣与脆弱,乃至我们民族的隋性和劣根性,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故事大都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令人黯然神伤,长久叹息,同时又给人以远处微渺的希望,让人们对未来执着地追求下去。
二、余易木成功的背后
至于余易木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文学成就?笔者也尝试着做点分析。首先是他具有极高的天份和文学修养。他在中国现代文明的潮头上海出生成长,天资聪颖,精通多国语言,因此能够广泛地吸收人类的现代文明成果,这使得他在写作时能够登高望远,比常人看得更深更透,比常人更富有思想和艺术的底蕴。其次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使他开始反思,逐渐大彻大悟。惨痛的人生经历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而是成了他写作的财富和源泉,以作品进行探索和思考,此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再次是他本人淡泊的生活追求。他一生饱经苦难,穷困潦倒,却又安贫乐道,不以物质生活的困顿为意。改革开放之后,他有机会调回上海或去其他条件更好的城市,从而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却选择了终老青海。他的作品发表以后,青海省文联曾想把他调来当一位专业作家,但他却认为正是工厂需要自己的时候,走了就不仗义了,再说进入作协体制以后也未必就能写出东西来[3]。一个人在物质上的获得多了,就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而既得利益者总是患得患失的。他放弃了物质上的追求,却获得了更多精神上的自由。他没有物质利益的牵绊之后,反而可以在精神上进行艰苦的跋涉,更好地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此可谓“文章憎命达”。
余易木这两部作品是在1962年8月到1965年4月这一时期写的。那时候,我们国家经过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时期之后,政治局面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最高领袖先后发出了两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令文艺界的气氛顿时严峻了起来。然而,在那样险峻的环境下,余易木仍然坚守自己的艺术和良知,专心致志地进行探索和写作,把自己对社会和时代的真实认识记录了下来,把自己的真实情感记录了下来,把自己的控诉和追求记录了下来。他当时已经完全没有公开发表作品的可能,这反而可以“茫洋在前,顾忌皆去”,以一颗自由的心灵进行思考和写作。在那个年代,进行这样的写作是要冒着巨大风险的,许多人就因为私人材料被揭发或者被抄出而使自己陷入了灭顶之灾。但是他没有畏惧不前,而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勇敢地抒发自己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过去的这个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世纪,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社会灾难,遇到了无数的发展挫折,付出了无数的大众牺牲,有着太多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入地总结吸取,在文学界也需要有许多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来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深刻地反思这个时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真正厚重和大气的作品却很少,像余易木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北边的苏俄与我们也有着类似的历史经历,他们那里的客观环境也与我们类似,但他们却产生了许多深刻地反映和反思那个时代的大作家和大作品。这除了我们缺少一种像俄罗斯那样深厚的文学传统之外,也与我们的作家在主观方面的贫乏分不开的,也与我们的作家内心不够强大有关。因此,我们的作家要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首先必须具有一颗博大而自由的心灵,能够坚守自己的艺术和良知,以无畏的勇气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执著地追求真、善、美,大胆地鞭挞假、丑、恶。同时,我们的作家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在各方面的素养,特别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和艺术修养,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以艺术的形式和文学的语言真实地反映这个时代,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与追求。
三、余易木被长期埋落的原因分析
(一)评论界的短视。至于余易木为何长期以来不为人知,成为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当那些写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轰动,变得炙手可热时,余易木的两部作品也发表了,虽然其品位和价值要在其他人的作品之上,但是除了在读者中获得巨大的反响之外,评论界并没有关注到他。而此后他也不再有作品发表,于是就逐渐被遗忘了。这个中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也许是正确的,即正因为他的作品在深度和境界上都超出了同时期那些当红作家的作品,他的被遗忘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这样的作家如果成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其他作家无疑就会相形见绌。而文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名利场,评论谁,不评论谁,以及如何进行评论,往往会受到一些文学之外因素的干扰和左右。
但是我们也不妨换个角度看待问题:如果文坛上树立起了一个更高的标杆,就会给人们以更多的启示,就会给人们提供一个更高的超越目标,这无疑十分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相反,当那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文坛上大量地充斥着迎合时尚、吸引眼球却又平庸、肤浅的作家和作品时,文学的生态环境就会变得十分恶劣,文学发展的道路就会越走越窄。作为评论家,除了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追求,还应当具备一种专业精神和社会担当,即要对那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其价值充分地挖掘和阐释出来,给其以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同时也通过批评,即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为文学创作提供一种导向,促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此之图,从事文学评论就与普通的买卖没有区别了。从评论家自身的角度说,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评论,才能更好地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实现自身的价值。当今文学的不景气,与评论界的缺少担当也是大有关系的。当评论界对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视而不见,对时下流行的却品位不高的文学作品却热情有加,与并不争气的创作界进行媾合的时候,文学的发展就停滞了,评论家的声誉也就下降了。因此,评论界应当开阔自己的心胸,拓宽自己的眼界,对余易木这样的作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打捞那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二)出版环境的限制。我们无法苛求作家都能像余易木那样可以不为发表而写作,也不能苛求作家都能像余易木那样无所畏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人性毕竟是有弱点的,人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要使大量的优秀作品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从根本上说就要依靠一种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制度,营造出一种健康宽松的创作环境。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种环境,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文学发展的繁荣景象;我们什么时候失去这样一种环境,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文学萎缩和退步的局面。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时期,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这离不开当时所具有的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新时期以来的十年,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繁荣兴旺的局面,这与我们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善分不开的。余易木的两部作品在1980初发表,正值当时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界相应也出现了解冻氛围,产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样一种潮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文学创作环境总体上是较为宽松的,也正因此而带来了文学发展的繁荣局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仍然不时地穿插进各种政治运动,从而干预了文学创作,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同时,长期以来我们在出版管理方面并没有走上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化管理的轨道。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余易木1980年初发表两部小说后就也没有再公开发表作品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我们的创作环境之一斑。而一个作家倘若只发表过极少的作品,即使这些作品属于上乘之列,也很难保持足够的影响力,这大概也是他长期以来被文学界冷落和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主动地放宽文学创作的环境,为作家们营造畅所欲言的氛围,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建立起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出版管理制度,保障人们应当享有的自由权利。
另一方面,人们在追求自己创作自由的同时,还应当不要滥用自己的自由。自由意味着责任,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如果不负责任地行使它,就会歪曲自由的本义,最终得不到自由[4]。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作家当然可以关心政治,也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文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它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有自己的范围和任务,而不能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内心,遵循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用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余易木这两部作品是在不考虑发表的情况下,完全以一种自由的状态写出来的,如果要议论起政治本可以淋漓尽致地进行,可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而是具体入微地表现那个时代人们的遭遇,人们的生存和情感状态,人性所受到的伤害以及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文学如果过多地偏离自己的轨道,直接地进入到政治的场域,承受起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就会迷失了自身,使文学不成其为文学。从文学史上看,无论从左的还是从右的方面,文学倘若过多地介入政治,都会给自身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伤害,都不会留下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同时在政治立场上,如果我们无法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而且意识到以激进的方式改变现状并不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相反还往往使社会的发展出现倒退,我们就应当秉持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以一种与权力既保持一定的张力又积极寻求对话合作的方式去推动社会的改良。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也许就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社会的转型,更能够营造出一种自由宽松的文学创作环境,我们的文学事业就能够繁荣起来。
[1]丁东.我和王小波的交往[J].社会观察:北京,2005(12):60-62.
[2]余易木.初恋的回声[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
[3]王贵如.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青海新闻网.[EB/OL](2009-09-11)[2016-05-11]http://www.qhnews.com/index/system/2009/09/11/002805366.shtml.
[4]胡应泉.言论的自由与边界[J].社会科学论坛,2014(07):166-173.
(责任编辑:邢建勇)
胡应泉,男,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中国现代政治与经济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