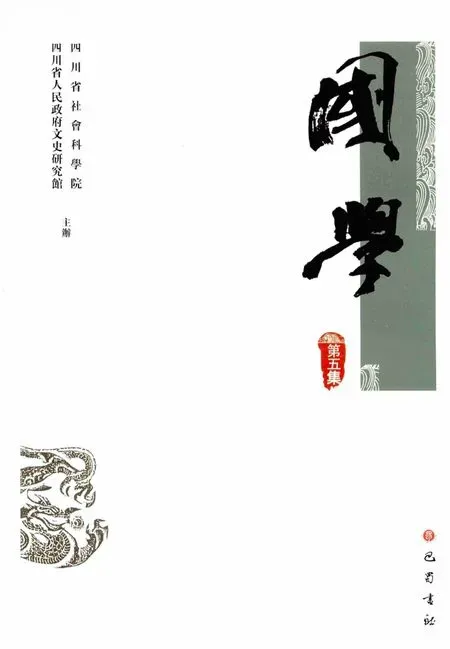趙吕甫先生的學術人生及其學術成就①
2017-01-25劉朋樂
劉朋樂
趙吕甫先生(1919—1999),當代知名學人,唐史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學者。在改革開放後的新時期裏,其先後校對出版了《史通新校注》《雲南志校釋》等高水準論著,發表了《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鄉”的職權地位》《整理〈史通〉的體會》等一批學術論文,對史學史研究、唐史研究、西南史地研究、少數民族史等領域的革新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然而目前學界對趙吕甫學術人生、學術成就的關注還較為單薄,尚未有專文述評其學術成就。有鑑於此,本文將以趙吕甫已出版的論著(文)為基礎,總結概括其主要學術成就,對其學術成就做一初步的探討,以就教於學界。
一、趙吕甫的學術人生
趙吕甫,本名趙岡,1919年出生於四川成都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其父趙少咸(1884-1966)乃民國時期著名語言學家,與時賢章太炎、黄侃等先生頗有往還,曾先後任教於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等高校,1949年後任四川大學教授。
受家庭環境的影響,趙吕甫自幼便喜愛文史,亦時常從事寫作。1937年,趙吕甫從成都私立成公中學畢業,時值日本侵略中國,趙吕甫遂與同學洪潤芳、吴庚密、趙爾宏、楊生環等人創辦《怒潮》不定期刊,疾呼抗敵,並以“紅嬰”筆名發表《蘇聯婦女的生活》一文,“揭露當時蘇聯婦女生活之實際”[注]趙吕甫:《成都四中教職員登記表》(1955年),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1939年春,由於其父趙少咸調任中央大學教授,舉家遷渝,吕甫遂赴渝補習,其年秋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1940年秋,因患病,返蓉就醫,請假休學一年。1944年,趙吕甫畢業於復旦大學,但由於中學畢業會考尚有一門需要補考,以至並未如期取得大學文憑,其大學文憑直至1951年纔獲得。
1945年春,由復旦大學史地系同學孫道遠介紹,趙吕甫來到合川國立第二中學任教。1946年,攜家眷由合川返回成都,但由於抵蓉時已是舊曆臘月二十四,學校人事安排已就緒,不得已由杜仲陵介紹到眉山中學擔任訓導主任兼國文教員。1947年,趙吕甫長兄幼文赴西北大學任教,遂將華陽縣中、建國中學兩校國文課程交與吕甫。之後,趙吕甫還先後任教於省立女子職業學校、南薰中學、榮昌縣中等中學。1949年,由其姐夫殷孟倫介紹,改任成都石室中學國文教員、歷史教員[注]以上生平,均參見趙吕甫:《成都四中教職員登記表》及“個人自傳”(1955年),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
1956年至1964年,趙吕甫任四川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先後講授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及金元史、歷史典籍介紹及選讀等課程,並以高要求嚴格要求自己,勤勤懇懇從事教學工作,“期望能以嚴肅的備課和科學研究態度影響學生,使學生能够得到啓發”[注]趙吕甫:《1985年教授任職資格申報表本人總結》,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在此期間,趙吕甫寫成了《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對〈關於武則天評價的問題〉一文的兩點意見》《歐陽修史學初探》等多篇學術論文,逐步確立起了其嚴謹的治史風格。1964年,趙吕甫轉任南充師範學院歷史系講師,但隨著極“左”思想的影響和“文革”的爆發,趙吕甫和廣大舊知識分子一樣“受到了不少不公正待遇”[注]趙吕甫:《南充師範學院獎勵登記表》(1985年4月),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其歷史研究遂陷入停滯狀態。
改革開放後,趙吕甫在“文革”中被下的錯誤結論得到了徹底的糾正,因而“趙老師精神更加旺盛,不計前嫌……一面為本科生開設《校讎學》,一面帶研究生”[注]同上。。趙吕甫進入其學術生涯的蓬發期,先後發表了《唐代的實録》《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誤》《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整理〈史通〉的體會》《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鄉”的職權地位》等一系列高水準論文;出版了《雲南志校釋》《〈史通〉新校注》等多部巨著;擔任了四川史學會理事、唐史學會理事等社會職務,為唐代財政史、史學史、西南史地等領域做了積極的貢獻。進入90年代後,趙吕甫著力於整理其父趙少咸的遺作,與其父的學生余行達、易雲秋共同完成整理其父的遺留著作《廣韻疏證》,同時單獨整理完成了其父的大量遺留論文。1999年,趙吕甫逝世,享年80歲。
二、趙吕甫的主要學術成就
趙吕甫長期對唐史的相關問題有著深入的研究,在唐代史學史、西南少數民族史、校讎學等領域有著自己獨特的貢獻,其學術上的成就令人驚嘆。作為晚生,余難以通識,在此僅談點個人體會,管窺所及。
(一)趙吕甫的主要著作
趙吕甫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雲南志校釋》。唐人樊綽所撰的《雲南志》又稱《蠻書》《南蠻記》等,為“著述雲南史地之專著僅存於世者,亦為考究南詔史事最重要之典籍”[注]方國瑜:《樊綽〈雲南志〉考説》,《思想戰綫》1981年第1期。。自清代的學者從《永樂大典》中輯録付印以後,學人紛紛進行校對。是書詳細介紹了雲南界内的山川江源、風俗習慣、交通狀況等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西南歷史地理以及南詔國歷史極為珍貴的史料。因此,對該書的整理、校對也受到當代史家極大地重視。20世紀60年代,著名歷史學家向達便“收羅版本,拾遺補缺”[注]木芹:《雲南志校補序》,《思想戰綫》1980年第5期。,寫成《蠻書校注》。與此同時,趙吕甫也經三十餘年之考究,於1985年出版了《雲南志校釋》一書。趙版《雲南志校釋》有如下兩特點:
第一,旁徵博引,為原書中的内容增加了詳細的材料。
校訂古書首先必須掌握豐富的材料,正如趙氏在是書的《序言》中的夫子自況:“凡此拙撰並擇善而從”[注](唐)樊綽著,趙吕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5頁。,趙吕甫在校釋《雲南志》的過程中,以校語最完備、訛誤較少的《琳琅密室叢書》本為底本,旁徵博引,廣泛參照《華陽國志》《太平寰宇記》《唐書》《唐會要》《資治通鑑》等二百餘種書籍,吸收前人校釋的可取之處,對《雲南志》做了精確詳盡的點校注釋,校釋後的雲南志由原來的二萬餘字,擴充至約三十七萬字之規模,内容更為精詳。
比如,《雲南志·蒙舍詔》在介紹蒙舍的地理位置時僅有“蒙舍,一詔也。居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注]同上,第110頁。,寥寥數語,晦澀難讀。而趙吕甫《雲南志校釋》中則引用了《新唐書·南詔傳》“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桂海虞衡志》“蒙舍詔在諸部最强,故號南詔”、《滇史略》“唐始稱南詔,因蒙氏吞五詔,居永昌、姚州之間,地在五詔之南,故曰南詔”[注]趙吕甫:《唐樊綽〈雲南志·蒙舍詔〉校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等三種不同的史料進行對比,大大擴充了原書的可讀性,易於理解。再如,在緊接著介紹蒙舍詔族群歸屬時,《雲南志·蒙舍詔》僅有“姓蒙”二字,理解難度很大。趙吕甫於是將所有能見的介紹南詔族群歸屬的著述一一列舉,如是説道:
蒙氏家族究屬何種民族,自來論説紛紜,莫衷一是。兩《唐書·南詔傳》、《唐會要》卷九九、《册府元龜》卷九五六俱謂烏蠻之别種。曹樹翹《滇南雜志》謂:“蓋哀牢之蒲種也。”馮甦《滇考》又謂:“不過苗獠一種耳……”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白族簡史簡志合編》謂是白族。惟淩純聲《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馬長壽《南詔國内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劉堯漢《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方國瑜《彝族簡史長編》、李紹明《巍山文物與南詔歷史》等則皆謂為彝族,亦以此説最有理據,讀者可自參覽[注]同上。。
此種列舉不僅使讀者對南詔族群研究現狀有了直觀的認識,而且大大豐富了對《雲南志》的解釋,減小了閲讀的難度。
第二,考證細緻,訂正舊説,益以新知。
除了對《雲南志》的内容進行補充解釋外,趙吕甫還考證出了該書許多訛誤之處,並進行了修訂,糾正了先前版本的一些不當之處。
比如,《雲南志》卷一介紹雲南界内的途程開篇便説道:“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注](唐)樊綽撰:《蠻書》,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第1頁。趙吕甫經過自己細緻的考證後,認為:“卷一第一段話在總述交阯與安寧之間的里程,而安寧城在前,交阯城在後,則與下文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説法不相符合。”[注]參見(唐)樊綽著,趙吕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頁。同時,趙吕甫借鑒木芹先生《雲南志校補序》一文 “衹有安寧城與交阯城互改,纔能與文意”的説法[注]木芹:《雲南志校補序》,《思想戰綫》1980年第5期。。此外,趙吕甫還依據《後漢書·馬援傳》及《南蠻傳》認為“後漢元鼎二年”是版本的訛誤,應改為“後漢建武十九年”。在這一番考證之後,遂將原文校對為:“交阯城,後漢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去安寧城池四十八日程。”[注](唐)樊綽著,趙吕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2頁。諸如此類的考證與修改,使得樊書中的許多訛誤得到糾正,為該領域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著名歷史學家、文獻學家來新夏在其論著《中國近代史述叢》中寫道:“在專題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績……趙吕甫的《唐樊綽〈雲南志·蒙舍詔〉校釋》等,都是專門性的學術研究論文。”[注]來新夏:《中國近代史述叢》,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383頁。當代著名民族學家余宏模在回顧彝族研究歷程時亦如此評論道:“南詔史是彝族史的一重要部分,也取得相當進展。在史料方面……有趙吕甫《雲南志校釋》等書,根據調查史料,為探討南詔歷史問題,開闢了研究的新途徑。”[注]余宏模:《余宏模彝學研究文集》,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
趙吕甫學術研究主要的著作之二是史學史領域的《史通新校注》。
從1947年起,趙吕甫便著手開始其《史通》的校勘工作,歷時40餘年,參考相關專著、論文200餘種,終於在1990年由重慶出版社出版。該書是研究《史通》的集大成專著,全書按照内容、體系,將《史通》分為八組進行校勘,總共注釋達6300餘條,其中校勘約2200餘事。全書行文力求通俗易懂,契合一般讀者的需要。在校釋方面,對時賢的有關評論“悉擇善而從”[注]參見(唐)劉知幾撰,趙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6頁。。
為了修訂後世對《史通》隨意纂改之處,趙吕甫以浦起龍的《史通通釋》為底本,繼而廣泛收集評論《史通》的相關資料。趙吕甫對照陸深、張鼎思、張之象、王惟儉等人的刻本進行校對,基本解決了浦起龍的《史通通釋》許多錯字、纂改的地方。但《史通》這部巨著包含了許多史實,再加上劉知幾行文多用駢文,如不加以進一步解釋,理解《史通》也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趙吕甫還採取當代史家陳漢章、楊明照、彭仲鐸等人的注解,從而使閲讀《史通》的難度進一步降低。除此之外,《史通》還包含了劉知幾獨到的史學見解,但也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因而,趙吕甫還收集洪邁、王應麟、王夫之、顧炎武、趙翼、魏源等人對《史通》的評價,將這些評價摘抄下來,付於文中相應部分,同時還收集了當代學者朱希祖、金毓黻等人的評論,一併摘抄於文内[注]參見趙吕甫:《整理〈史通〉的體會》,《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
通過上述工作,趙吕甫便將《史通》這本史學巨著進行了綜合性的整理,不僅使《史通》中的謬誤之處得以改正,還讓讀者更易把握《史通》的内容與思想。難怪乎著名歷史學家、古文獻學家張舜徽教授贊其“彌嘆功力深厚,非數十年精誠所聚,殆不足以臻此。求之當世,未可多見也”[注]《書訊》,《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當代著名學者程千帆也評論其“大著《史通新校注》甚佩,蓋自有此書之注以來,無有如尊著之博洽者”[注]同上。。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教材上也評論道:“今人趙吕甫作《史通新校注》,反映了《史通》研究的新成果。”[注]白壽彝主編:《新世紀高等學校教材 面嚮21世紀課程教材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歷史學專業基礎課程系列教材 中國史學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26頁。
(二)唐代史事的研究
除了上述兩本專著外,從20世紀50年代起,趙吕甫在各類雜志上發表了論文20餘篇,其中大部分是關於唐代史事的研究與考訂。如:《唐代使館考》《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唐代的〈實録〉》《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誤》《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鄉”的職權地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補》等,對唐代的史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以《唐代的〈實録〉》一文為例,是文首先系統地介紹了唐代《實録》編撰體制以及歷史沿革,指出就編寫體制來説,實録屬於編年史的一種,而六朝則為《實録》的創立時期,唐代為其茁壯成長的時期。然後,趙文對唐代實録的特點進行了歸納,認為有“每一項事件,都必須綜述其較詳的原委”“記載詔誥敕册的全文”“人物傳編寫詳細”[注]趙吕甫:《唐代的〈實録〉》,《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三個重要特點,這些特點是唐代《國史》所不具備的,可與國史相互印證,為後世研究唐史提供重要的史料。緊接著,趙文還廣泛論證了《實録》的重要史料價值,認為《實録》的内容包括整個國家的軍國大事,又有中央權力的支援,資料來源非常廣泛,六部、太史局、鴻臚寺等機構均需按規定定時報送,“取材的方面和數量是極其廣闊和繁富的”[注]同上。。另外,唐朝統治者對史官的甄選是相當注意的,編寫《實録》的大多數史官屬於德才兼備的“績學之士”,因此所記載的事情可信度較高。《實録》的記事也較為翔實,在編纂過程中,史官對民間傳聞、野史這些内容進行了謹慎的選擇,相比於其他野史雜文更令人信服。最後,趙文還著重評論了《實録》的不足之處,認為存在“隱惡飾非”“詳略互異”“紀事混亂”“殘缺散佚”“浮詞虚美”“訛脱舛誤”這六弊,告誡後人在史料選取時還應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注]同上。。在趙吕甫之前,學界還尚未有人對唐代《實録》的價值作專門探討,趙氏開創性地對唐代《實録》的歷史沿革、史料價值、優點弊端等做了詳細的介紹,無疑對唐《實録》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再如趙吕甫1984年發表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一文,就提出了自己對“部田”與“常田”的獨到理解。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著吐魯番文書的發現,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吐魯番文書的熱潮,以至有“吐魯番學”之興起。日本學者在其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具體到唐代土地制度方面,西村元佑在其《中國經濟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一文中,將“部田”解釋為“劣等的土地”,將“常田”理解為“良質的土地”;我國學者馬雍則認為“部田是需要輪休的土地,常田乃是常年耕作,不需休耕的農田”[注]馬雍:《麹斌造寺碑所反映的高昌土地問題》,《文物》1976年第12期。;楊際平對這兩家的觀點進行評述,認為西村元佑與馬雍二人的觀點“根據都不够充分”,提出“部田”是某州、某縣的屯田土地,也是唐代屯田的土地,而“常田”就是民田[注]楊際平:《試考唐代吐魯番地區“部田”的歷史淵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1期。。
趙吕甫通過自己對吐魯番文書的研讀認為“部田”不是籠統的州、縣境内的農田,也不是屯田,而是具有特殊意義的田地。
趙吕甫指出,第一,“部田”的主管不是隸屬屯田的官府。趙吕甫引用了《敦煌資料》一三八的一件文書,上面記載有“當鄉剥籍”[注]趙吕甫:《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的字樣,由此認為部田的主管應為鄉一級的主管部門,而非屯田官員。第二,部田可以出租。趙吕甫又引用另一段史料載“天授元年壹月……海多邊租取棗樹渠部田畝,麥小壹斗就中交付三畝價訖”[注]同上。,由此可見,部田是允許民間租賃的,而唐代的法律規定屯田絶對不允許農民私自交易,因此部田與屯田性質是有明顯差别的。第三,部田有“剩退”“死退”的規定。趙吕甫通過自己對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發現了大量關於“部田”退田的記載,如“開元廿九年死及剩”、“剩退一段壹部田”、“死退貳畝部田城南五里”[注]同上。等,而屯田的土地為國家所有,不存在“有剩追收”的情況,這些不同點都表明了部田與屯田有著明顯差别。第四,部田内分永業、口分兩類,其性質是私有的土地。通過以上論證,趙吕甫斷定“部田”必定不是屯田,楊際平所言部田是唐代屯田的説法缺乏依據。在論證何為常田時,趙吕甫認為楊際平“常田是民田”的説法也是缺乏根據的,而認同西村元祐“常田是良質的土地”與馬雍“常田是常年耕種不需要休耕的土地”的説法[注]同上。。
趙吕甫關於“部田”“常田”的討論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積極的響應,楊際平先生也於1988年在《中國史研究》上發表了《再談麴氏高昌與唐代西州“部田”的歷史淵源》一文與趙吕甫進行再探討,極大地促進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著名唐史專家金寶祥教授評價趙文稱:“作者根據大量文獻資料,對國内外學者對吐魯番文書中有關‘部田’‘常田’的解釋提出了新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注]金寶祥等:《趙吕甫同志教授任職資格申報表專家鑒定意見》(1985年),見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
(三)其他相關問題的研究
趙吕甫是當代著名的唐史專家,但其治史的廣度遠非如此,現僅將趙吕甫其他方面的研究作一鋪衍堆砌,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較早地研究了歐陽修史學的貢獻。1963年,趙吕甫在《歷史教學》雜志上發表了《歐陽修史學初探》一文,較早對歐陽修的史學貢獻做了全面的評述。在此之前,學界對歐陽修的關注主要在其文學成就上,還未有專文對其史學成就做研究,因此,趙吕甫《歐陽修史學初探》一文無疑開啓了60年代對歐陽修史學研究的先河。
趙吕甫從“歐陽修的重要史學著述”、“歐陽修對歷史編纂學的貢獻”以及“金石考據學和古籍辨偽”[注]趙吕甫:《歐陽修史學初探》,《歷史教學》1963年第1期。三個方面評價歐陽修的史學貢獻,認為“歐陽修是我國古代著作豐富、貢獻偉大的傑出史學家,是第一個繼承和具體運用了王充、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和歷史編纂學的優良傳統來編纂正史的優秀史學家”[注]同上。,並且“歐陽修以反神學的疑古精神積極從事金石考據和古籍辨偽,這又對宋代疑古求實新學風的樹立和發展曾起過巨大的促進作用”[注]同上。。由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陳高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如此評價趙文:“60年代,趙吕甫《歐陽修史學初探》全面、高度地評介了歐陽修的史學成就。”[注]中國史研究編輯部:《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3頁。應該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氛圍較為保守的時候,趙吕甫能對歐陽修的史學成就作比較中肯的評述,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在文學、藝術方面有著獨到研究。除了上述史學研究外,趙吕甫在40年代,曾撰《南宋的移民文學》《近代成都兩詩家》《關於亂彈名義的商榷》[注]以上三文分别發表於上海《宇宙風:乙刊》,1940年第34期、1940年第35期、1941年第36期。《新津觀音寺的明代佛教藝術》等文,在文學、藝術方面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以《新津觀音寺的明代佛教藝術》一文為例,趙吕甫在1951年“土改”中偶然發現新津永商鄉九蓮村保存一座明代古刹,遂多次造訪,記録該寺廟裏廟宇建築、佛龕造像等藝術風格,發現該寺廟第八殿的建築風格與其他殿的風格迥然不同,寺廟裏的和尚稱其為“魯班所造”。趙遂詳細記録第八殿的建造風格,發現該殿雖然是明代修建,但其風格是模仿唐、五代的舊制而建造的,並且此種風格在國内並不多見,在國外也衹有日本尚存少數類似的寺廟。因而,趙將自己所見之景詳細記録下來,並期望考古界予以重視[注]參見趙岡:《新津觀音寺的明代佛教藝術》,《旅行雜志》1952年第3期。。如今,新津的觀音寺已成成都周邊著名的景點,而趙吕甫對觀音寺的記載與傳播,則逐漸被人淡忘。
第三,對先秦典籍中某些城池位置進行考證。為更好地瞭解桂陵之戰齊、魏兩軍交戰的路綫,趙吕甫曾撰《〈孫臏兵法·擒龐涓〉中幾個城邑問題的探討》《再論〈孫臏兵法·擒龐涓〉篇中幾個城邑的位置》兩文,對文中城池的位置做了深入討論。趙文認為《擒龐涓》開篇“梁軍將攻邯鄲,使將軍龐涓帶甲八萬至於茬丘”中的“茬丘”並不等於人們所説的距衛國首都濮陽城西南十五里的“沮丘”;魏、衛、趙三國並没有同時佔有東陽的一隅,東陽實為趙國一城邑;桂林之戰平陵、平陸、平丘三城分屬宋、齊、鄭三國,其間無任何關係[注]參見趙吕甫:《再論〈孫臏兵法·擒龐涓〉篇中幾個城邑的位置》,《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這些觀點的提出不僅充分證明了《孫臏兵法·擒龐涓》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可與一些先秦典籍相互印證,糾正人們的常用史料如《漢書》《水經》等注釋上的不當之處,很具有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趙吕甫還撰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考證》(重慶《時文新報》,《學燈》周刊第274期)、《世説新語劉注義例考》(上海《圖文月刊》第82期)、《對〈關於武則天評價的問題〉一文的兩點意見》(《四川日報》1961年8月12日)等文,趙氏治史之廣度由此可見一斑,在此便不贅述。
三、趙吕甫學術成就之地位
在談及自己的治史態度時,趙吕甫如是説道:“我欽佩胡適、董作賓、錢穆、張西曼、吕振羽諸人考史論文的内容是旁徵博引,方法也甚為科學,但我對他們分析史實的觀點卻極不同意。我認為學術必須獨立而無所依附,文學作品衹宜抒寫一己的性靈,論史也應就事論事,絶不該受某一派社會學家的學説去批評問題。”[注]趙吕甫:《思想彙報》(1957年),見南充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的確,“獨立而無所依附”是趙吕甫治史最大之特點,趙吕甫所寫的大部分文章是以考證、校讎為基礎,通過廣泛的閲讀史料、對比史料得出結論,並且趙氏堅信“以成見研究歷史,猶如戴上墨鏡看事物,難乎免於歪曲史實”[注]同上。。於是乎,以考證為主要手段,寫出不帶主觀色彩的文章便是他畢生所追求的真理。
在評論趙吕甫的著作《雲南志校釋》時,山東大學著名歷史學家王仲犖稱贊説:“在抗戰期間,北京大學向達教授著有《蠻書校注》,《雲南志》就是《蠻書》的别名。趙吕甫同志在前人整理的基礎上,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注成此書,注釋得非常細緻,大部分結論都切實可靠,為人們所能接受。是一部很出色的著作。”[注]金寶祥等:《趙吕甫同志教授任職資格申報表專家鑒定意見》(1985年),見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四川省南充市。著名歷史教育家吴景賢也贊其:“就中惟以《琳琅密室叢書》搜訪最完備,趙吕甫同志用作底本,依據舊籍文獻,參照時人新解,亦予逐一訂正。堪稱樊書之功臣,諸家之諍友,亦當代研究西南歷史之巨著也。”[注]同上。而對於趙吕甫另一本著作《史通新校注》,當代史學史學者周文玖如此説道:“對劉知幾的研究,趙吕甫的《史通新校注》是一個重要成果。在版本上,該書以蒲起龍的《史通通釋》為底本,利用明清兩朝的多種版本,對通釋本進行校勘,糾正了通釋本的一些錯誤。作者充分吸收了前人對《史通》的評論和近人對《史通》的研究成果,注釋更加翔實,並對劉知幾的史學思想做了細緻的評述。”[注]周文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産生和發展》,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3頁。
在科研教學方面,趙吕甫也得到同行的認可,知名的秦漢史、宗教史、巴蜀史研究專家龍顯昭稱贊:“他在科研方面的成績特别突出,他的學識廣博、功力深厚,對唐代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表了一批高品質的論文。他對唐代的史學史、財政史和幾部重要的典籍都有深入的研究。”[注]金寶祥等:《趙吕甫同志教授任職資格申報表專家鑒定意見》(1985年),見南充西華師範大學人事處藏《趙吕甫檔案》。據趙吕甫指導的碩士畢業生、四川師範大學三級教授黄修明回憶稱:“趙老師每日總是獨來獨往,生活習慣很好,每晚看完‘新聞聯播’後必須入睡,早上四點左右便起床工作,勤勤懇懇,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注]黄修明教授(趙吕甫先生指導的碩士生)口述:《趙吕甫先生之學術》,筆者採訪整理,四川師範大學第六教學樓内,2016年11月16日12時。上海大學教授陳勇在其《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一書中也表達了對趙吕甫老師的敬意:趙吕甫師是我大學時期的老師,1986年我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隨趙師學習隋唐史。在趙師的家中,我和他的研究生一道聽他講授“唐代經濟史”“唐代財政史”等課程,所記筆記至今猶存,我研究唐代經濟史的興趣,實由趙師開啓[注]陳勇:《唐代長江下游經濟發展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1頁。。這些評論字裏行間流露出對趙吕甫教學、科研的肯定及欽佩。
縱觀趙吕甫的學術人生,他以考證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方法,對唐代史學史、財政史、西南史地、少數民族史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是一位出色的唐史研究專家。然而,趙吕甫的研究也非盡善盡美。處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背景下,其雖然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比較新穎的論述,但這些論述大多是對古籍、書本的研讀,缺乏實地的考察瞭解,因而其結論往往會與實際情況相左。作為新時代的學人,學界對此不必苛求。
附:
趙吕甫先生主要論著(文)目録
一、論著:
1.(唐)樊綽著,趙吕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2.(唐)劉知幾撰,趙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
3.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編纂委員會[注]趙吕甫擔任編輯,並作隋唐部分辭條編寫。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
二、論文:
1.《南宋的遺民文學》,《宇宙風:乙刊》1940年第34期,第7-12頁。
2.《近代成都兩詩家》,《宇宙風:乙刊》1940年第35期, 第9-12頁。
3.《關於“亂彈”名義的商榷》,《宇宙風:乙刊》1941年第36期, 第11-12頁。
4.《亂彈名義詮真》,《平劇旬刊》1943年第10期, 第5頁。
5.《唐代使館考》,《文化先鋒》1948年第10期, 第17-21、8頁。
6.《〈世説新語〉劉注義例考:〈世説新語〉叢考之一》,《國文月刊》1949年第82期, 第20-26頁。
7.《新津觀音寺的明代佛教藝術》,上海《旅行雜志》1951年第3期,第47-49頁。
8.《初中課本〈中國歷史〉第三册一些問題的商榷》,《歷史教學》1954年第11期。
9.《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文史哲》1957年第4期(總56期), 第26-32頁。
10.《對〈關於武則天評價的問題〉一文的兩點意見》,《四川日報》1961年第8、12卷, 第3頁。
11.《試談我國封建社會内部分段問題》,劉靜夫、趙吕甫(著),《四川日報》,1961年,第6、8卷, 第3頁。
12.《歐陽修史學初探》,《歷史教學》1963年第1期,第2-14頁。
13.《〈孫臏兵法·擒龐涓〉中幾個城邑問題的探討》,《文物》1976年第10期,第51-56頁。
14.《唐樊綽〈雲南志·蒙舍詔〉校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第13-25頁。
15.《唐代的〈實録〉》,《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第1-16頁。
16.《唐樊綽〈雲南志·六詔〉校記》,《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1輯,第270-291頁。
17.《敦煌發現隋大業三年記帳殘卷考釋》,《四川省史學會史學論文集》,1982年,第121-139頁。
18.《牛僧孺·李德裕史事辨誤》,《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第52-59頁。
19.《唐代吐魯番文書“部田”“常田”名義釋疑》,《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第105-113頁。
20.《整理〈史通〉的體會》,《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67—72頁。
21.《讀金毓黻〈敦煌寫本唐天寶官品令考釋〉書後》,《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第67頁。
22.《金文識小録》,《中華文史論叢·語言文字專輯》,1985年,第204頁。
23.《再論〈孫臏兵法·擒龐涓〉篇中幾個城邑的位置》,《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第89-95頁。
24.《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鄉”的職權地位》,《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19頁。
25.《讀〈新唐書·樊興傳〉書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第1-2頁。
26.《關於唐代前期軍屯田經營管理的幾個問題》,《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第42-48頁。
27.《〈新唐書·地理志〉考異》,《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第1-7頁。
28.《敦煌寫本唐乾元〈水部式〉殘卷補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第1-7頁。
29.《〈雲南志校釋〉中之地名考證》,載《唐至清代有關維西史料輯録》,1992年,第368-369頁。
30.《〈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補》,《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第2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