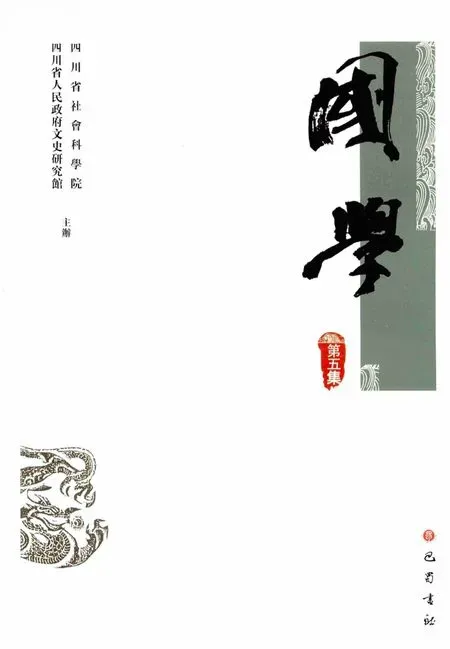從柳宗元為“韓門罪人”説看歷代文人對陳子昂的評價
2017-01-25孟丹
孟 丹
陳子昂作為“古文運動”先驅,一度備受其同時和稍後的文學家的推崇,如盧藏用、李華、獨孤及、梁肅等都對其作品做出了肯定。盧藏用在《陳氏别傳》中説:“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注](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412頁。盧藏用作為陳子昂的摯友,贊賞陳子昂的作品,對其評價較高。盧藏用還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中稱贊了陳子昂對於文章革新的功績,他説:“卓立千古,横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注]同上,第2402頁。在陳子昂去世後,盧藏用廣搜其作品,並編撰成集,以便流傳,足見盧藏用對陳子昂作品的重視。李華在《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中云“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注]同上,第3197頁。,李華此處以“文體最正”肯定陳子昂的文體風格的價值。獨孤及在《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中云“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注]同上,第3946頁。,高度贊揚了陳子昂以《雅》革新鄭聲的不朽功績,認為在陳子昂革新的影響下文人的創作風格纔逐漸歸嚮正道。梁肅在《補闕李君前集序》中云:“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注]同上,第5261頁。,同樣肯定了陳子昂革新靡麗文風的功績,肯定了陳子昂對唐文的貢獻。以上古文家對陳子昂的評價皆是站在陳子昂對散文文風革新的角度來肯定陳子昂作為“古文運動”先驅的實踐與貢獻。
日本學者筧文生、筧久美子編著的《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中收録了筧文生的《關於陳子昂散文的評價》一文,就梁肅評陳子昂散文地位的“唐文三變説”進行了溯源,認為梁肅的説法是模仿《宋書·謝靈運傳論》。文中梳理了各代對陳子昂散文有代表性的評價,並探究盛唐古文家和柳宗元對陳文的極力推崇的緣由。文章認為,由於韓愈對陳子昂的散文態度的含糊曖昧,又因為宋以後學者多有認為柳宗元是“韓門罪人”者,因此,學術界對陳子昂的散文長期以來比較忽視:
作為散文改革者陳子昂的評價,後世不太注意,這和無視柳宗元的主張有很大關係。而且如已經看到的,韓愈關於陳子昂的散文,並没有給後世留下明確的意見[注][日]筧文生:《關於陳子昂散文的評價》,[日]筧文生、[日]筧久美子著,盧盛江、劉春林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0頁。。
筧文生以小見大,主張通過作品檢討陳子昂散文的價值是極為必要的,這對一直以來人們偏重於陳子昂的詩歌、文學理論和駢文成就的研究現狀來説,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補充。然而筧文生在本篇論文中的主要觀點又是與中國學者的傳統觀點存在著差異性的,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可是目前學界尚無學者對他的觀點給與關注或討論。由於本文對陳子昂散文[注](唐)陳子昂撰,徐鵬點校:《陳子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的認識與之有些差異之處,故而嘗試進行簡單的商榷,以求教於大方之家。
一、韓、柳對陳子昂散文態度再辯
中唐時期,韓愈、柳宗元對陳子昂皆有評價。如唐德宗李適貞元十八年(802),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云: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注](唐)韓愈著,(民)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2頁。。
序文是韓愈在送孟郊前往溧陽赴任縣尉時而作。在文中,韓愈首先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觀點,並把這種大自然的現象引申到文人通過自己的詩文歌賦等多樣的形式,把個人際遇的不幸或者是生民、社會的苦難呼籲出來,以發人深思,啓人嚮善:“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既然人的語言也往往是心中不平的發泄,那麽“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注](唐)韓愈著,(民)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2頁。。韓愈認為人的文章更是這種為個人遭際、為蒼生哀嘆的精華之言。故而他肯定古往今來的仁人志士,都是這樣敢於呐喊、敢於不平則鳴者。如唐堯、虞舜,咎陶、夏禹、夔之《韶》、夏之五子、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旦、《詩》、《書》六藝、孔子之徒、莊周、屈原、臧孫辰、孟軻、荀卿、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李斯、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等,皆為最善鳴者。即使是魏、晉氏以下,文風開始華豔,但其實鳴者亦未嘗絶。至於有唐以來,如初唐的陳子昂,盛唐蘇源明(預)、李白,中唐杜甫、元結、李觀等人,韓愈無不肯定他們為善鳴者,認為皆能够憑藉自己的才華,以詩文的形式來闡述時代問題的主題,表達自己的心聲,將對社會不公的憤慨情感訴諸筆端。則韓愈是把陳子昂放在與古往今來的盛達賢哲的並列地位而肯定的了,其態度非常鮮明,並没有含糊之處。韓愈接下來甚至認為,包括陳子昂在内的這些唐代文人,他們的詩文成就實際上“高出魏、晉”[注]同上。,不僅可以及於古人,甚至可説是超越漢人。而其好友如李翱、張籍、孟郊最為出色。當然,就今天的文學史觀點來看,韓愈的這些論點當然有其誇張不實之處。然而僅就韓愈對陳子昂文章價值的態度而言,毫無疑問是肯定和欣賞的。
唐憲宗李純元和元年(806),韓愈作《薦士》,詩云: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彌漫,派别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捲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强箭射魯縞。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郜。幸當擇瑉玉,寧有棄珪瑁?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菢。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犒。微詩公勿誚,愷悌神所勞[注](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27-528頁。。
《薦士》一詩是韓愈為嚮鄭餘慶舉薦孟郊而作。其詩先言《詩經》“雅麗理訓誥雅”,而五言詩出自漢代。五言詩一改《詩經》四言體的創作體式,後西漢的蘇武、李陵嘗試以五言古詩的體式創作,後世遂將這種五言古詩稱為“蘇李體”。隨著東漢五言詩的發展,在中原政權的政治中心洛陽附近,形成“派别百川導”的局面。如建安時期的三曹、七子、蔡琰們“卓犖變風操”,開始關注戰亂的民生現實,以激昂悲歌的基調,大力反映那樣的痛苦的時代。形式上,曹操既保持四言詩的傳統,又開始創製五言詩。曹丕在以五言詩為主的同時,開始嘗試七言歌詩。曹植的五言詩更是在三曹和七子中堪稱最好。七子和蔡琰等也以五言詩為主,真實地再現了時代的苦難。到晉、宋時期,詩歌的現實性發展出現了衰敗的氣象,文人在險惡的政治高壓下,轉嚮了玄言詩為主的創作階段,或者是以親情、友情、愛情等較為狹小的題材為表現内容。直至晉宋之間的謝靈運、陶淵明為首的山水詩和田園詩興起後,再到劉宋時期的鮑照、宋齊之間的謝朓,詩歌纔有了一些新鮮的活力。顯然,在韓愈的心裏,謝靈運和陶淵明的詩還在鮑照、謝朓之下,故他没有點出大謝和陶詩的意義。之後,韓愈認為整個齊、梁、陳、隋和陳子昂以前的唐代詩壇,詩歌都風格華豔浮靡,内容淺薄狹窄,形式陳陳相因。直到陳子昂,開始提倡詩歌應該追求高遠的思想境界,而盛唐的李白、杜甫的出現,纔使得“萬類困陵暴”,即人世間的各種不平之聲,都能够得到盡情的抒發。李、杜之後的作家,開始各自沿著這樣的路子,“各臻閫奧”,各具特色,繼續馳騁在詩歌的文學性和思想性並重的軌道上。直至孟郊“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的險怪詩風形成,在韓愈看來,那樣的詩既能冥觀洞古今,也能象外逐幽;既能在形式上嚴守詩歌的格律,也能在思想上如孟軻一樣保持邪正分明的公正眼光。正因如此,所以兵部尚書歸崇敬、中興名將張建封均對他表示贊賞。韓愈認為這樣的詩歌,纔可以挽回中晚唐以來詩文華靡浮躁風氣的不良走嚮。所以,在對孟郊詩歌、人品進行舉薦後,韓愈傷其志不遂、才不彰,猶如“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希望鄭餘慶能够提拔提拔孟郊,不至於其才華被埋没。對照詩文前後,韓愈應是從《詩經》以來的詩歌史的角度進行的文學批評,在推崇孟郊詩歌的同時,也對建安七子、鮑照、謝朓、陳子昂、李、杜等文人詩歌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創新,給予了熱情的肯定與推崇。尤其是他認為唐代詩歌的繁盛,正是由於陳子昂“始高蹈”[注](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28頁。,這無疑是肯定了陳子昂對唐代詩歌的深遠影響和陳子昂在詩歌創作上先行者的地位。
因此,本文認為,韓愈對陳子昂的文章的先驅地位的肯定,態度是十分鮮明的。而且這主要反映在他對陳子昂詩文的思想性和形式上兩個方面的肯定。前者,韓愈肯定的是陳子昂不平則鳴的為蒼生為天下呼籲奔走的精神;後者,韓愈肯定的是陳子昂詩文中的不同於流俗的“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的文風,以及格外倡揚、實踐的“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捲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注]同上。的剛健文風。
我們再來看看柳宗元對陳子昂的具體態度。據學者們的研究和推測,大約在唐德宗李適貞元二十一年(805)[注]施子愉:《柳宗元年譜》,《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7年第1期,第115頁。,柳宗元有《楊評事文集後序》,其文云: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誇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盈滿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湧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願、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游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578-580頁。
楊君即楊淩,據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載,楊氏兄弟楊憑、楊凝和楊淩,乃弘農(今河南三門峽、靈寶一帶)人,皆以孝友稱,有文章傳世。楊淩則官至大理評事,最善文[注]同上,第300頁。。本文最主要的觀點在於柳宗元認為,文章的功用在於它的辭令褒貶、導揚諷諭。所以即使是那些言語鄙陋粗野的文章,也可以因為其能褒貶、諷諭,“以備於用”。另一方面,如果文章過於缺少文采,則不能够震動當時,更不能嚮後學者誇示。這也即是孔子所謂“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注]同上。的意思。所以君子是不能容忍“立言而朽”、毫無思想意義的作品的。故君子作文,必定緊緊抓住文章對現實的思想意義這一根本源頭以追求“立言不朽”,這是一條文章被後世認可的必由之道。所以孔聖人作文,以立意為根本,故其言論,被後世奉為經典;這些經典被後世的才子們進一步以各種文學手段進行闡述,於是形成所謂的“文采”。辭令褒貶源於孔子等人的作品,這類作品强調文章的思想性和原創性,追求高壯廣厚、詞正理備的風格,是儒家典籍成為經典的必備條件。導揚諷諭源於《詩經》,比興本屬《詩經》“六義”,這類作品重視文章的文采性,追求華麗清越、言暢意美的文風,易於廣泛傳誦。思想性與文采性相互背離,難以融合,很難有人能够調和二者在作品中的關係。唐自建國以來,作品能够兼具思想性與文學性的作家衹有陳子昂一人。燕文貞即張説,善著述;張曲江即張九齡,善比興。即使是他們的作品,其實也不能很好地調和著述與比興的關係,即立意和文采之間的關係。其他文人就更難平衡二者在作品中的關係了。柳宗元由是認為,兼具在作品中融合思想性與文學性對於作者來説是不易的。而陳子昂的作品,在柳宗元看來,則既有思想内涵,又詞美意暢、擅長比興;不僅可以成簡册保存,也可傳誦流傳,是大家之作,故具極高成就。柳宗元稱贊楊淩“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柳宗元對楊淩文章評價極高,或有過譽之嫌,然而對陳子昂的推崇則是顯而易見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柳宗元對陳子昂的態度也是非常肯定的。這種肯定主要是集中在對陳子昂詩文的兩個特點:1.勇於褒貶,故詞正而理備。2.言暢意美,故宜流謠誦。因此,他對楊淩文章之妙,其實也是從這兩個角度來肯定的,“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湧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並認為楊淩的這種文風,也是追隨陳子昂而來的。
綜上,本文認為韓愈和柳宗元對陳子昂的文風是充分肯定的,而且這種肯定一定是包括了對陳子昂散文的貢獻的肯定。此後唐中晚期的裴敬在為李白所做的《翰林學士李公墓碑》中云:
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注](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7846頁。。
有意識地將詩、文分開論説,肯定了王昌齡、宋之問、韋應物、王維、杜審言等人的詩。將陳子昂歸於“以文稱者”,把他與蘇源明、元結、蕭穎士、韓愈並稱。可見中唐以後的文人,對陳子昂在散文上的貢獻,更加明確了。而晚唐人陸希聲在為李觀集子所作的《李元賓文集序》中説:
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注](唐)李觀撰:《李元賓文集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頁。。
陸希聲認為陳子昂“始復古制”,開始去除隋之故態,實為復古之先驅,衹是其文尚未能完全去除六朝駢體的諧靡一面。這是客觀公正地看待陳子昂散文貢獻的代表者。
接下來,本文擬分析歐陽修對柳宗元的評價,以探討筧文生文章所提到的所謂歐陽修斷言柳宗元是“韓門罪人”的具體情況。
二、“韓門罪人”説非宋人論柳宗元主流
接下來我們來看筧文生所謂的歐陽修斷言柳宗元是“韓門罪人”的提法是否合理。筧文生在《關於陳子昂散文的評價》一文中,首先提到了歐陽修的《〈唐南嶽彌陀和尚碑〉跋》。在這篇跋文裏,歐陽修提到過“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注]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7册,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27頁。這樣驚世駭俗的判斷。然後筧文生評價説:
歐陽修這樣斷言的背景,是韓愈排斥佛教和老莊思想,以明古人之道作為己任。而柳宗元則與此相反,他容忍佛教,主張佛教的真理與《易》和《論語》是互為合一。柳宗元在政治上又加入了王叔文一黨。今天來看,歐陽修的意見明顯需要糾正。但是北宋一代文宗歐陽修的判斷,限制了後世很多人的想法[注][日]筧文生:《關於陳子昂散文的評價》, [日]筧文生、[日]筧久美子著,盧盛江、劉春林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0頁。。
筧文生在這裏强調了歐陽修有關柳是韓的罪人的説法産生的原因:一則是與韓愈排佛而柳宗元佞佛有關,二則是因為柳在政治上加入了王叔文政黨的緣故。他認為,由於歐陽修對柳文的輕視和貶斥,所以北宋以後的很多人對柳文的成就評價都不高。那麽,筧文生的這種見解到底合不合理呢?欲明乎此,尚需從柳宗元的這篇《唐南嶽彌陀和尚碑》文談起。
《南嶽彌陀和尚碑》 是柳宗元於唐憲宗李純元和五年(810)為承遠和尚所作的碑文,其文敘述代宗時期的國師名僧法照,曾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承遠和尚的卓異的功德,和天子曾經對他的“南嚮而禮”“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的待遇。柳宗元深情地敘述承遠和尚始居南嶽西南巖石之下時的艱苦生活:“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羸形垢面,躬負薪槱。”[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53頁。以至於來嚮他求佛法的人路上偶遇他,還以為是一介僕役而媟慢地對待他。然而承遠和尚卻能以“中道”度化衆生,教衆生在社會上行靈活權變之法,而不是嚴格的佛門戒律。直到他病重期間,纔特意指示衆生專念“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並把這個法門書之塗巷,刻於溪谷,殷勤誘掖,以援引後來之人。由於承遠和尚素日的謙卑品德,所以其道德感化之力,盛極一時:
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户,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屍其功。
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州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
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
虚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
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
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宫。始自蜀道至臨洪,諮謀往復窮真宗。
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
立之兹石書玄蹤[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53-154頁。。
可見,柳宗元的碑文是對佛教名僧大德承遠和尚事蹟的宣揚和肯定。其中後半部分更提到了僧法照和承遠和尚的一段神奇因緣:僧法照還在廬山修道時,在禪定中,得趨如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是時,他看見佛背後的侍者中有一衣著極為粗陋的和尚,而阿彌陀佛告訴他,此人即是衡山的承遠和尚。僧法照從禪定中出來以後,遂往衡山尋訪承遠和尚,以求教佛法。一見承遠和尚的面,發現果然與禪定中所見的那人肖似,於是拜從學習。可見,柳宗元此文的最大特色乃在於對佛門大德的德行和佛門不可思議的神通的贊頌。而歐陽修則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其《〈唐南嶽彌陀和尚碑〉跋》云:
右《南嶽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並書。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蓋世俗不知其所學之非,第以當時輩流言之爾。今余又侈録其文,懼益後人之惑也,故書以見余意[注]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7册,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27頁。(注釋:“今余又侈録其文”句原文作“今余又多録其文”,“侈録”指依照原文抄録下來,筆者不知“多録”於此是何意,故認為“侈録”更為合適。)。
歐陽修此段嚴厲的批評,主要是針對柳宗元“所學之非”而進行的。所謂“所學之非”,當即前文韓愈所謂的文章的思想性。歐陽修和韓愈一樣,早期大力排斥佛教,晚年轉而親近佛教。歐陽修此文,寫於北宋英宗趙曙治平元年(1064)。此時的他,正處於政治生涯的高峰時期。先是在宋仁宗趙禎嘉祐二年(1057)二月,他做了禮部知貢舉的主考官,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文風,先後録取蘇軾、蘇轍、曾鞏等人,對北宋古文運動的成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對北宋險怪的“太學體”文風和歌功頌德的西昆體文風起到了徹底的扭轉作用。其後他以翰林學士身份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拜樞密副使,任參知政事,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直到英宗趙曙治平二年(1065)以後再歷政治風波而漸退政壇,最後晚年自稱“六一居士”而顯示出皈依佛門的跡象。所以,治平元年(1064)的時候,應該是歐陽修轉變對佛教態度的前夕。他對柳宗元的批判,主要不是針對柳宗元的古文文法而言的,相反,是針對柳宗元對佛法的好感和信仰而説的。
無獨有偶,也是在北宋英宗趙曙治平元年(1064),歐陽修還作了《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跋》一文,同樣也對韓、柳並稱的文學批評現象提出異議:
右《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並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為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為“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所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為道不同,雖不言,故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為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治平元年三月廿日書[注]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7册,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26頁。。
可見,歐陽修雖然承認韓、柳“皆以文章知名一時”,然而他並不認可後世將韓、柳並稱的説法,以為這是平庸人的俗見。歐陽修以。為二者“為道不同,猶夷夏也”。則所謂的“道”,仍然是指韓愈所宗為儒,而柳宗元乃儒、釋、道所共宗。儒、道為中國本土學説,而釋乃外來宗教。因為,柳宗元的這篇《般舟和尚碑》所稱述的,仍然是佛門大德的行跡。這篇碑文作於唐憲宗李純元和三年(808),柳宗元始敘衡山佛法的傳揚,直到津大師纔修起律教,以後其所帶出的弟子,皆被稱為得佛之正法者。津大師的大弟子日悟和尚,盡得師道,次補師處,遂為後世宗。接著,柳宗元介紹此日悟和尚,世家於零陵,俗姓蔣。又云:
(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繞,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7-168頁。。
肅宗時代,日悟和尚擇衡山而居,亦因德行深厚故,“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注]同上,第168頁。。則歐陽修所糾結者,仍然是柳之崇佛一事,而非否定其實際上的古文成就。
由上可知,歐陽修確實在治平元年期間,對柳宗元的文章提出了鮮明的批判意見,甚至過激地認為柳是韓門的罪人。考其原因,則實皆由歐陽修不滿柳宗元的崇佛之故。然後人之所以韓柳並稱,是從韓柳二人對中唐古文運動的貢獻和影響而談的,因此歐陽修對柳宗元地位的批判顯然是偏頗的。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檢討筧文生的看法,遂不難看出,筧文生認為歐陽修有關柳是韓的罪人的説法産生的原因之一,是與韓愈排佛而柳宗元佞佛有關。這顯然是正確的。至於説,歐陽修是否是因為柳在政治上加入了王叔文政黨的緣故,而否定其與韓愈的並列地位,這一點至少從文本中,難以看出來,故還應謹慎商榷。
那麽,筧文生又認為,由於歐陽修對柳文的輕視和貶斥,所以北宋以後的很多人對柳文的成就評價都不高。這個説法是否是客觀的呢?本文認為,這個説法也是不確的。
首先,歐陽修在治平元年之前或之後,均曾經高度評價過柳宗元的文章。如其在宋仁宗趙禎皇祐元年(1049)所做的《永州萬石亭》詩中云: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淩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常使鳴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横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下上極沿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跡所罕到,遺蹤久荒頹。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薈,搜尋得瓊瑰。威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為我銘山隈[注]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7册,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80頁。。
歐陽修敘述了柳宗元一生艱危,仕途上因才華過人而榮升,興盛之時又遭貶謫,被流放到偏遠之地。然而“投以空曠地,縱横放天才”,柳宗元在窮山險水間游歷,反而成就其山水文章的語出驚人、不同凡響。“威物不自貴,因人乃為材”,此亦山水之美,不能自發,惟得柳宗元之才乃發之之意。所以歐陽修非常珍惜柳宗元的書寫山水的“奇才”:“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歐陽修高度肯定了柳宗元才華過人、為文“窮而後工”的特點。又宋神宗趙頊熙寧四年(1071),也即歐陽修去世的前一年,其有《薛簡肅公文集序》云: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注]同上,第210頁。
歐陽修在序文中論述了“窮而後工”一説,他認為“君子之學”或在事業中反映出來,或在文章中折射出來,難有人將二者兼顧。遇到好時勢的人,功勳事蹟顯見於朝廷,名垂千古,他們通常認為文章是末事,無暇顧及,如姚崇、宋璟,皆屬此類。衹有仕途上不得志的人,纔能苦心危慮,極於精思,有所感激發憤,皆一寓於文辭。歐陽修認為,劉禹錫、柳宗元正是這類文人。他們雖“無稱於事業”,卻反而“見於文章”。顯然,去世前夕的歐陽修還是肯定了柳宗元的文章。
其次,歐陽修的大門生蘇軾,即對柳宗元有過非常高的評價。如其在《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評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絶妙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注](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84頁。很有意思的是,歐陽修曾經否定的柳宗元為名僧所撰的碑文文字,恰好被同樣受佛教濡染很深的蘇東坡高度贊揚,以為“絶妙古今”。其實蘇軾對柳文評價極高,我們此處再舉幾個例子,如:
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書黄子思詩集後》)[注]同上,第2124頁。
所貴乎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是也。(《評韓柳詩》)[注]同上,第2109-2110頁。
以上兩則材料,顯示蘇軾把柳宗元的詩與韋應物、陶淵明歸為一類,均屬於在淡泊中含至味,在簡古中藴纖穠者,均屬於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者。可見蘇軾對柳詩的崇高評價。又如: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論封建》)[注]同上,第158頁。
蘇軾對柳之《封建論》一文亦是激賞不已的,甚至把它和李斯的《論廢封建》、秦始皇的《封建論》等並列,稱為萬世不改的經典之論。
再次,宋代政治改革家、古文家王安石對柳宗元政治品格也有辯護。王安石在《讀〈柳宗元傳〉》一文中云: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注](宋)王安石著,唐武標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96頁。
在王安石看來,柳宗元、劉禹錫等均是天下“奇才”。他們是因為被王叔文一黨利誘而陷於不義之地的。那些自以為是君子的士大夫羞於談論他們,常攻擊他們的政治品格。然而柳宗元等人雖陷於困境且不被重用,卻能够自立自强以求改變後世對自己的評價。柳宗元等人的努力確實没有白費,他們美好的名聲最終為後世所承認。而那些批判他們的所謂君子,大多數最終還是隨波逐流。因此在王安石看來,這些人没有資格去評議柳宗元等人,後世應珍視柳宗元等身上那種“自强以求别於後世”的精神。王安石對柳宗元的評價也是非常高的,認為非本時代的那些所謂自命為君子的士大夫所能比擬者。
除了歐陽修本人和其他宋代古文家,即使在宋代初年的時候,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也有充分重視柳宗元者,且以韓柳並重,並不偏頗。如穆修《唐柳先生集後序》:
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注](宋)穆修:《河南穆公集》,《四部叢刊初編》第810册,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穆修認為韓愈和柳宗元是直接繼承唐前、先秦兩漢古文傳統者,是真正能够讓文章文采、儒家之道相合,不蕪不雜者。又如《宋史·柳開傳》云:
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注](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023-13024頁。。
北宋初年的柳開,是宋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他讀書頗喜義理之學,不喜五代淺弱的文風。由於追慕韓、柳的文章,還不惜改名以示志。再如宋初古文運動先驅者王禹偁多次並重韓、柳,絶不偏頗:
古文閲韓、柳,特策開晁、董[注](宋)王禹偁撰:《小畜集》,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6頁。。(《寄題陝府南溪兼簡孫何兄弟》)
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注]同上,第153頁。。(《贈朱嚴》)
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注](宋)王禹偁撰:《小畜集》,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46頁。。(《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注]同上,第268頁。。(《送丁謂序》)
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注]同上,第267頁。。(《送孫何序》)
見其文有韓、柳風格,因誇於同列,薦於宰執間[注]同上,第411頁。。(《殿中丞贈户部員外郎孫府君墓志銘》)
王禹偁的古文是嚮韓、柳學習的,他把韓、柳文章的地位等同於李、杜詩歌的地位。他誇耀丁謂時也是把丁謂的文抬高到韓、柳的路數上去的,甚至認為丁謂的文章立意不同尋常,語言不隨五代俗流,故能雜於韓、柳之文中,以假亂真。他稱孫何的文章寫得好,也認為他是韓、柳的門徒,是能够遵奉儒家六經者。又如,慶曆年革新的宣導者范仲淹在《述夢詩序》中云:
劉與柳宗元、吕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禮意精密,涉道非淺。……至於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注](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1頁。。
很明顯,范仲淹也稱柳文和吕温之文一樣,皆是非常之士的作品。可見,早在歐陽修和蘇軾之前,北宋人對柳宗元文章的風格是多有肯定的,且常是韓、柳並重的。
因此,無論是歐陽修本人,還是之前的穆修、柳開、王禹偁、范仲淹,之後的蘇軾、王安石等,這些政治改革家、古文家都曾經給予柳宗元的古文以高度的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筧文生以為由於歐陽修對柳文的輕視和貶斥,所以北宋以後的很多人對柳文的成就評價都不高的説法,有欠全面和客觀,因此也是值得進一步商榷的。
三、歷代文人對陳子昂散文爭論新辯
如前文所引,筧文生以為由於歐陽修對柳宗元的批判,限制了“後世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説,作為散文改革者的陳子昂的評價,後世不太注意,這和無視柳宗元的主張有很大關係”[注][日]筧文生:《關於陳子昂散文的評價》, [日]筧文生、[日]筧久美子著,盧盛江、劉春林編譯:《唐宋詩文的藝術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00頁。。也就是説,筧文生認為,正是由於歐陽修對柳宗元文出現過激烈的否定之詞,後世的人們對陳子昂的評價也就不高了。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看呢?
唐人杜甫《陳拾遺故宅》云:“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杜甫認為陳子昂有聖賢般的品格以及對《詩經》和《離騷》繼承的才華,陳子昂雖出生於司馬相如和揚雄之後,但名聲依舊可以亙古長存,並盛贊其作品云:“千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注](唐)杜甫撰,(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4頁。在肯定陳子昂《感遇》詩篇的同時,亦肯定其人品。唐人白居易在《初授拾遺》一詩中云:“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注](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5頁。白居易將陳子昂與杜甫並舉,亦是對陳子昂才華與名望的肯定。
宋仁宗趙禎嘉祐五年(1060)完成的歐陽修等編著的《新唐書·陳子昂傳》云:
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雅……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注](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4068頁。。
此説完全是繼承姚鉉的説法而來,對陳子昂在唐代詩文革新運動中的先驅作用的肯定也是很明確的,且以正史使臣的身份給予贊賞。
其實,歐陽修之後,宋人肯定陳子昂者亦不乏其人。如宋文人司馬光,其撰的《資治通鑑》一書所録内容起於三家分晉,止於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前未收屈原、陶淵明之文,後未收李白、杜甫之文,卻獨引陳子昂奏議類散文六次,足見陳子昂奏議類散文的重要價值。又如宋人文同首先對《新唐書·陳子昂傳》中對陳子昂諫言武則天修明堂、立太學的指責提出批評,其在《射洪縣拾遺亭記》中云:
庚子秋,同被詔校《唐書》新本,見史策伯玉與傅奕,吕才同撰。謂伯玉以王者之術説武曌,故贊貶之。曰:“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嗚呼!甚哉,其不探伯玉之為政理書之深意也。明堂、太學,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為之,猶愧無以稱其舉,豈淫豔荒惑、險刻殘詖婦人之所宜與乎?緣事警奸,立文矯潛,伯玉之言有味乎其中矣。彼傅吕者,本好歷數才技之書,但能略領大體,顓務記覽,以濟其末學,詎可引伯玉而為之等夷耶。杜子美、韓退之,唐之為人也。杜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韓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其推尚伯玉之功也如此。後人或以己見而遽抑之,人之材識。信夫有相絶者矣文同著,胡問濤、羅琴校注:《文同全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第745頁。
文同指出宋祁、歐陽修等人不探究陳子昂所作《諫政理書》等文章的深刻内容和現實意義,僅僅是指責他勸諫武則天修明堂、立太學之事。在文同看來,陳子昂為文“緣事警奸,立文矯潛”,即指陳子昂為文有深遠的内涵,能够對潛在的問題進行有遠見性的矯正,給奸佞之徒以警醒,陳子昂的文章是有深刻的現實性和政治遠見性的。又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
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黄、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注](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臺灣:廣文書局,1967年,第996頁。。
晁公武肯定了陳子昂對古代典籍的精心研究,熱愛道家、老子、《易象》,不惟承認陳子昂在唐代詩文中的先驅者地位,還特意稱道和矚目他的散文貢獻。唐自建國以來,文章承襲梁代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為代表的駢體文風和宫體詩風。至陳子昂方能追隨《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再如陳振孫亦説:“其(陳子昂)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注](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臺灣:廣文書局,1968年,第967頁。亦與姚鉉等人看法類似。
就筆者的有限視野來看,後人對陳子昂散文成就的否定主要集中在元、明二代。如元代的馬端臨就認為柳宗元對陳子昂的過高評價不當,其《文獻通考》卷二三一中駁柳宗元曰:
陳拾遺詩語高妙,絶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他文,則不脱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怍”,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注](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44頁。。
在馬端臨看來,陳子昂唯有詩歌能够擺脱齊、梁文風,其他的文章則依舊沿襲偶儷卑弱的文體,並不比王勃、楊炯、沈佺期、宋之問的排偶之文更好。但是,韓、柳在盛贊陳子昂時,顯然既贊揚了他的詩,也包括了他的散文。馬端臨對此頗感遺憾,他認為雖然韓、柳從不輕易地贊許别人的文章,但就對陳子昂的評價而言,兩人的觀點並不高明。又明代的胡應麟在其《詩藪·外編四》中亦引馬端臨之語而云:
柳儀曹曰:張燕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馬端臨氏曰:拾遺詩語高妙,至他文則不脱偶儷,未見其異於王、楊、沈、宋也。按:昌黎“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中及李、杜而未言孟郊,其意蓋專在於詩,柳言頗過。故應馬氏有異論也[注](明)胡應麟撰:《詩藪》,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90頁。。
胡應麟的態度是把韓愈與柳宗元剥離開來,他認為韓愈“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的評價,是針對陳子昂的詩,而不是針對陳子昂的文來進行的,因而是正確合理的定位。至於柳宗元對陳子昂的抬舉,則是過分的。就上所引的文獻而言,胡應麟對陳子昂的否定,乃是受馬端臨的影響,而不是受歐陽修的影響甚明。因此,筧文生所謂後世否定陳子昂的古文影響的説法,有兩層意義上的不準確:其一,馬端臨否定陳子昂的古文地位時,並没有推稱歐陽修的話,所以不是受歐陽修的影響甚明。而胡應麟否定陳子昂時,推崇的是馬端臨的看法,因此也與歐陽修對柳宗元的評價無關。其二,現存史料中,除了馬、胡二人外,還没有太多的資料顯示元明人對陳子昂散文成就持反對意見者。相反,如明人王志堅(1576—1633)所撰的《四六法海》是一部駢文總集,收有陳子昂的《為陳御史進奉和秋景觀競渡詩表》《薛大夫上亭宴集》《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别冀侍御崔司議序》《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等文。明人張頤在《陳伯玉文集序》中説:“其文雖有六朝、唐初氣味,然其奏疏數章亦有用世之志。”[注](明)張頤:《陳子昂文集序》,《四部叢刊初編》第103册,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肯定了陳子昂奏疏之文的現實作用。
清人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稱贊他的政治才能時云: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為大臣可矣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737頁。
而清人中明確反對陳子昂文者,當是王士禎。其《香祖筆記》云:
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頽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甿頌》,其辭諂誕不經……集中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彠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注](清)王士禎撰:《香祖筆記》,《四庫全書》第8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0頁。。
王士禎以“節義廉恥”作為評價詩文的標準,雖然批判範圍波及到“表、序、碑、記等作”,但就下文所舉文例,則知他真正反感的是陳子昂為女主武則天所寫的歌功頌德類的文字。這種批判已經不是文學的標準,而是政治的偏見了。故稍後的康熙帝在其《評〈諫雅州討生羌書〉》中云:“言蜀用兵利害,警切動聽。”[注](清)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四庫全書》第12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8頁。康熙《評〈上軍國利害事三條〉》時云:“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洞達人情,可謂經國之言。”[注]同上。都是對陳子昂政論文的現實價值和文學生動性的肯定。清人鄧絳在《藻川堂譚藝·三代篇》中也對陳子昂的文章有過較高的評價,其云:
唐人之學博而雜,豪俠有氣之士,多出於其間。磊落奇偉,猶有西漢之遺。而見諸文辭者,有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之屬,堪與誼、遷、相如、揚雄輩相馳騁以上下[注](清)鄧絳撰:《藻川堂譚藝》,《中國詩話珍本叢書》,清刻本,第21頁。。
後來清代學者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再次肯定了韓、柳對陳子昂散文的評價:
唐初文章,不脱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為,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謂:“張説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脱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諭。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為非也[注](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278頁。。
清代《四庫》館臣的意見非常明確:其一,陳子昂開始奮發自為,追古作者,脱離陳、隋華靡文風之舊習;其二,徵引韓、柳對陳子昂的評價而證明第一點;其三,批駁馬端臨説法,以為是馬端臨誤讀了韓、柳之意,因為韓、柳從未把陳子昂的詩與文分開來説過;其四,肯定陳子昂的散文中,除了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外,若論、事、書、疏之類,實則疏樸近古。所以,韓、柳對陳子昂的高度推崇,並没有錯。就選家而言,清初的徐乾學等編著的《古文淵鑒》收録陳子昂《對利害三事》和《諫雅州討生羌書》。清末的高步瀛,在其《唐宋文舉要》中亦熱情地贊美陳子昂:“雄俊倜儻,韓公先導。”[注](清)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頁。肯定其對韓文的啓發和先導作用。其《唐宋文舉要》分為甲乙兩編,甲編是散文,乙編是駢文。甲編收陳子昂《諫用刑書》《堂弟孜墓志銘》二文。
近人張振庸亦對陳子昂在文風上的功績持肯定意見,其云:
上官婉媚,沈宋靡麗,四傑亦鮮高潔之體、蒼勁之氣。惟陳子昂廁身於四傑、沈、宋之間,而特立獨行,不與同流,以高雅沖淡之氣,清勁樸質之體,抑沈、宋之新聲,掩王、盧之靡韻,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焉[注]張振庸:《中國文學史分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82頁。。
張振庸認為以上官儀為代表的宫廷詩人所創作的宫體詩“綺錯婉媚”,以沈佺期、宋之問為代表的臺閣詩人文風靡麗,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文章少有高潔之體,缺少蒼勁的風格。他認為惟有陳子昂的文風能够與“四傑”、沈佺期、宋之問等靡麗文風不同,陈子昂以高尚雅致、沖和淡泊的文風和清正剛直、質樸純真且不加文飾的體式創作文章,抑制沈佺期、宋之問、王勃、盧照鄰的靡麗文風,追求文章的古樸高雅。張振庸指出了陳子昂與初唐其他文人文風的差異,肯定了陳子昂以高雅沖淡、清新質樸的文風變革齊梁靡麗文風的功績。
因此,在本文看來,陳子昂生活在齊梁文風依然盛行的時期,他能够不隨波逐流而宣導復古革新,並在論、事、書、疏之類散文中實踐樸實流暢的文風,的確堪稱古文運動的先驅者。
綜上所述,歐陽修認為柳宗元為“韓門罪人”的説法是歐陽修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得出的偏頗見解,並不是歐陽修本人對柳宗元散文成就的全部評價。宋代其他文人,尤其是古文家們對陳子昂的評價也並非全部受到所謂“韓門罪人”説的影響。韓、柳對陳子昂散文的態度並不如筧文生所認為的那樣模糊不清,也没有造成後世文人對陳子昂散文的負面評價。本文認為,後人少量的對陳子昂散文的負面評價,多為集中在歌頌武周政權這一點上而給予的道德評價,由於這是明顯的偏見,所以也不是主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