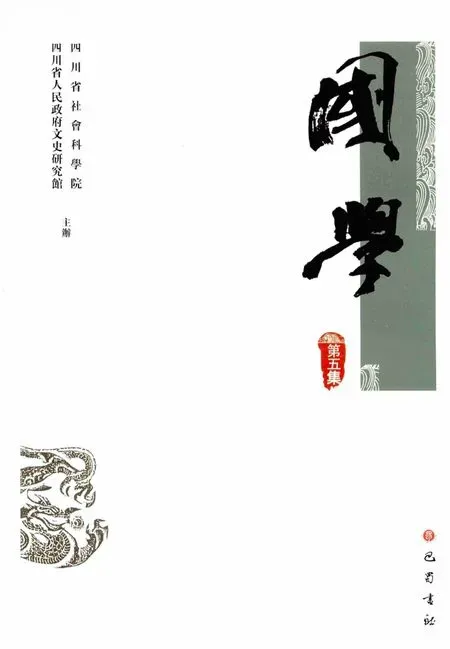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類型、演進及其哲學意藴
2017-01-25孫尚勇
孫尚勇
一、引 言
1985年,德國學者顧彬對中國文學自然美作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他參考日本學者青本正兒、小尾郊一、小川環樹、前野直彬等的研究成果,分“自然作為標志”“自然當作外在世界”和“轉嚮内心世界的自然”三章,討論了先秦兩漢、魏晉南朝和唐代詩文中的自然描寫,並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國自然觀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特性的社會學緣由[注][德]顧彬(Wolfgang Kubin):《空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Der Durchsichtige Berg∶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in der Chinesischer Literatur,Stuttgart : F.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5.)。 此書中譯本題作《中國文人的自然觀》,馬樹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此書中譯本出版同一年,劉小楓撰文對顧彬提出了含蓄的批評。劉小楓認為,在中國,“‘自然’一詞更多地與精神行為相關,而不是與作為實體的客體相關”[注]劉小楓:《空山有人跡——讀〈中國文人的自然觀〉斷想》,《讀書》1990年第12期。,古代中國人很少將自然視為與“主體”相對的“客體”來看待,故對中國文學自然美進行分别主客的討論並不合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國曾經將人的思維之外的一切事物,包括外在的自然物、社會和人的軀體,都視作相對獨立的客體來看待。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問題,反映在古典詩學領域,即唐宋以來詩家常常討論的情景交融問題。它發端於南朝劉勰《文心雕龍·物色》,至盛唐,王昌齡在《詩格》中明確提出了包括“物境”“情境”“意境”在内的“詩有三境”説[注]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頁。。就近代以來的學術史來看,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問題同樣是可以討論的。較早時候,王國維、朱光潛、錢鍾書等已經先後借鑒西方哲學、美學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重大論題。
王國維《屈子之文學精神》説:
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故純粹之模山範水、流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於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於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注]王國維:《靜安文集續集》,《王國維遺書》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本,第32頁。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8—99頁。。
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説:
早期詩歌在各民族中大半都是從叙述動作開始(史詩、民歌等),偶爾涉及自然事物,大半衹把它作為背景、陪襯或比喻。到了山水詩,自然便由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繪畫的發展也有類似的情形。在中國,山水詩是從晉宋時代陶潛、謝靈運等詩人纔形成詩歌的一種特定類型。到了唐朝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詩人,山水詩就達到了它的成熟期,在詩歌中成為一種强有力的傳統,由唐宋一直到明清,幾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詩人没有寫過大量的山水詩[注]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文學評論》1960年第6期。引據《朱光潛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29頁。。
錢鍾書《管錐編》説:
參之仲長統欲卜居山涯水畔,頗徵山水方滋,當在漢季。荀(爽)以“悦山樂水”,緣“不容於時”;統以“背山臨流”,换“不受時責”,又可窺山水之好,初不盡出於逸興野趣,遠致閑情,而為不得已之慰藉。……詩文之及山水者,始則陳其形勢産品,如京都之賦,或喻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頌,未嘗玩物審美。繼乃山水依傍田園,若蔦蘿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謝靈運《山居賦》所謂“仲長願言”“應璩作書”“銅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棲盤”,即指此也。終則附庸蔚為大國,殆在東晉乎[注]錢鍾書:《管錐編》(第三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036、1037頁。。
1980年之後,中國學術界對文學中自然山水題材的系統研究逐漸興盛起來[注]其中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丁成泉:《中國山水詩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李文初:《中國山水詩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陶文鵬、韋鳳娟主編:《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章啓群:《論魏晉自然觀:中國藝術自覺的哲學考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這些論著或著力於自然山水文學史的構建,或側重於從哲學層面探討中國文學自然美及其演進的緣由。與顧彬等人關注中國文學自然美問題相先後,在1980年代文化熱大潮的引領下,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次有關古典詩歌情景關係的大討論。這一討論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具有總結性質的是王德明的《中國古代詩歌情景關係研究》、郁沅的《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王德明考察了遠古至漢、魏晉期間文學自然景物描寫的演變,指出自然景物的情感特徵在漢末開始明顯起來,認為此種轉變“一方面與人們對於自然的哲學看法有關,另一方面也與詩人們自己的創作感受有密切的關係”[注]王德明:《中國古代詩歌情景關係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26頁。。郁沅從歷時角度將情景交融分為“情景組合與情景互融兩個階段”,並視前者為“低級階段”[注]郁沅:《心物感應與情景交融》,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48、63頁。。
本文擬在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類型、演進及其哲學意藴作較為系統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二、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類型及演進
參照上引王國維等人的研究,可以明確,建安時代、謝靈運的時代、王維和李白的時代是中國文學自然美演進歷程中三個重要的轉捩點。以下依時代次序,簡略看看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基本歷史進程。
遠古神話傳説時代,人們一方面對自然進行著具象化的觀察和思考[注]許慎《説文解字敘》:“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53頁。;另一方面,人們在想象中賦予自然以神格,並在功利心態的驅動下,嘗試以巫術驅使、儀式乞求等手段改變和利用自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群的發展以及對自然規律的大致掌握,中國人選擇了依存於自然的生命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崇拜物和生存空間的自然在《詩經》中獲得了普遍的文學表現。
《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在朝陽照耀下,東邊的山岡上梧桐枝葉茂盛,棲於梧桐之上的鳳凰鳴聲和諧。自然物之欣欣嚮榮,與天子、賢臣相得的景況相類,故詩人將二者相比。《詩·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春天過去,夏天來臨,梅子成熟了,掉落在地上,樹上還有七成未落,年輕女子看到梅子落地,便對追求她的男子説,趁著吉祥的日子,趕快娶我吧。《詩·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看到太陽和月亮升起落下,落下又升起,這讓人不由得想念起遠方的親人或朋友,為什麽别離這麽長時間,他還不回來呢?上引以梅子掉落、日月運行來起興的例子,都是自然帶給人的情緒感受:梅子從樹上掉落下來與青春容易衰老的感受是相通的;日月有規律的運行與人對遠方親戚朋友的思念也是相通的。
《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是由河水的流動激發而出的生命感受。《莊子·秋水》記載了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的故事,這則故事的哲學内涵是,莊子主張自然與我在生命情態與生存心理上相通相融,惠子則從概念和邏輯的角度予以否定。在莊子看來,如同他從容地在濠梁之上游玩一樣,“出游從容”的魚在濠水之中也從容地游著,莊子的從容便是魚的從容。
上舉各例當中,梧桐如何茂密,詩人所看到梅子落地的情態如何,詩人所觀望的日月情態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孔子所見水流的狀貌如何,莊子眼中的魚究竟是怎樣從容地游著呢?我們也不得而知。明人徐渭説:“詩之興體起句,絶無意味……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説者。”[注](明)徐渭:《奉師季先生書》其三,《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458頁。即便被後人稱作具有“華麗的意境”的《卷阿》“鳳凰鳴矣”數句[注]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832頁。,其實也屬於“不著色相”的“鏤空之筆”[注]姚際恒:《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93頁。。也就是説,早期文學中的自然衹是人的一個叙述起點和情感象徵物,自然本身的“意義”是“不可説”的。
《詩經》比興的表現手法,古代以山水玉石比喻人之道德的比德思維,都是早期中國人與自然之間依存關係的反映。比興與比德説直接影響了後來的楚辭。小尾郊一説:“在《詩經》《楚辭》中,也不是没有對於自然美的吟詠,但這種吟詠是非常簡單的,其所描繪的也衹是樸素的自然。而且,這種吟詠不是為了吟詠自然美本身,而是為了引起其他事物,是一種比興式的吟詠方法。”[注][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19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7—368頁。雖然“由狀物進而寫景”[注]錢鍾書:《管錐編》(第二册),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613頁。,但“《楚辭》中,自然山水的美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作為道德精神的比擬、象徵而出現的”[注]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501—502頁。。因此可以説,先秦文學中,自然並不是獨立的,它是人表達思想感情的起點和依托,它還遠没有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孔子“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説法表明,在先秦時期,“一定的自然物件之所以引起人們喜愛,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和人的精神品質相似的形式結構的緣故。智者之所以樂水,是因為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動的特點,而智者不惑,捷於應對,敏於事功,同樣具有動的特點。仁者之所以樂山,是因為長育萬物的山具有闊大寬厚、巍然不動的靜的特點”。“不論山、水、北斗、松柏或其他自然現象,衹要它同人的某種精神、品質、情操有同形同構之處,都可能為君子所樂。”[注]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44頁。
漢代的代表文體是賦。大賦家司馬相如曾説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相如《子虚賦》雲夢澤一段描述了雲夢澤中的山,雲夢澤東南西北的地貌物産,極盡誇張,而相如《上林賦》對天子上林苑的山川物産的描寫則更加誇張。顯然,這種“視通萬里”的寫法,目的不在於紀實,而在於鼓吹淮揚大一統的漢文化精神。在漢賦的這種極力誇張式的描寫中,自然雖因其闊大而獨立於人之外,但它仍然服從於人的目的,服務於人的行動。顧彬將漢賦中的自然描寫視為“與朝廷和宗教意圖的密切關聯”,並認為“賦作者是朝廷指派的官吏並依附於朝廷,因此便不能隨心所欲地觀察自然,也感受不到自然之美。這樣自然就成了雙重統治的象徵,一方面被限制在苑囿之内,另一方面又代表被征服或尚未被征服的世界各地”[注][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2頁。。此論將漢賦自然美觀念解釋為皇帝和賦作者個人的局限,有一定見識,但似乎未能深刻認知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漢大賦創作的深層自覺及文化精神。這一點程世和有非常透徹的分析[注]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讀》,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編:《長安學術》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更重要的是,這種描寫過於宏大,很難引發一般人的審美感受和情感體驗,故司馬遷明確指出相如賦“多虚辭濫説”[注](漢)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073頁。,左思《三都賦序》則直接批評説:“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兹。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虚而無徵。”[注](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3頁。劉勰《文心雕龍·誇飾》亦批評漢代大賦“莫不因誇以成狀,沿飾而得奇”,“虚用濫形,不其疏乎”。也就是説,漢代大賦中的自然不是自然而然的自然,不是自然秩序當中的自然,而是超自然的政治秩序當中藻飾想象的自然。到了東漢中後期,短篇小賦開始流行。張衡《歸田賦》寫了仲春原野之景,仲長統《樂志論》亦寫了他理想的居處環境。然而借用前引錢鍾書的話來説,東漢的這類作品,乃“喻諸心性德行”,實“未嘗玩物審美”。葉維廉指出:“我們必須瞭解,不是所有具有山水的描寫的便是山水詩。詩中的山水和山水詩是有别的。譬如《荷馬史詩》裏大幅山川的描寫,《詩經》中的溱洧,《楚辭》中的草木,賦中的上林,或羅馬帝國時期叙事詩中的大幅自然景物的排敘,都是用自然山水景物作為其他題旨(歷史事件,人類活動行為)的背景;山水景物在這些詩中衹居次要的位置,是一種襯托的作用:就是説,它們還没有成為美感觀照的主位元對象。我們稱某一首詩為山水詩,是因為山水解脱其襯托的次要的作用而成為詩中美學的主位元對象,本樣自存。”[注]葉維廉:《中國古典詩和英美詩中山水美感意識的演變》,《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37頁。中國文學中的自然由“襯托的次要的作用”到成為作品中“美學的主位元對象”的轉變是從建安時期開始的。
建安文學中,經過擬人化處理,山水自然逐漸由作為人的情感發端、生存背景和政治道德比附,發展成為用以訴説人的思想感情的載體。如王粲《七哀詩》“荆蠻非我鄉”,“展現了人類境遇和自然景觀之間廣泛的聯繫……大自然和旅行者的心境完全相符:日暮,猿猴吟啼。而沾濕衣襟的白露隱含淚水之意”[注][美]傅漢思著,王蓓譯:《梅花與宫闈佳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56—57頁。。這首詩中的自然純粹是人情感的投射物,並未獲得獨立的審美地位。王粲的名作《登樓賦》可視作《七哀詩》的另一種文體顯現,賦中的自然景物同樣是作者情感的代言。與王粲同時代,另外一首為我們熟知的描寫自然景物的詩是曹操的《觀滄海》。王國維以為“純粹之模山範水,留連光景之作”始出現於建安時期,當主要就此類作品立論。但《觀滄海》詩中壯麗的自然景象事實上是作者宏大氣魄的代言,作者明確告訴讀者,其核心意旨在“歌以詠志”。也就是説,在《觀滄海》詩中,“志”是核心,自然物則僅僅是一個輔助。
東晉南朝時期,自然逐漸獲得了較為獨立的審美地位。首先表現出來的是,文學作品中自然與人的感情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分離。自詡“一吟一詠”的孫綽的《秋日》詩可以作為代表: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疏林積涼風,虚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葉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詩中情、理、景的割裂表明[注]孫尚勇:《〈維摩詰經〉與中古山水詩觀物方式的演進》,《西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與清談家口中山水即玄理不同,在以孫綽為代表的東晉玄言詩人的筆下,山水不再是“玄”本身,山水景物的獨立審美品格已經逐漸得到體認。其次有慧遠佛教集團的山水游記散文創作,既描摹山水之美,亦暢敘佛玄理趣[注][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19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1—232頁。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507—509頁。。再次是謝靈運,他努力表現自然物之間的動態關係,自然逐漸成為文人筆下獨立的審美對象。人們常常批評謝詩情景不能統一,這恰恰説明,謝詩中自然是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而存在的。齊梁陳隋時期,在謝靈運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少純粹描摹自然的詩文,在這類作品中,我們輕易看不到作者的主觀情思。如隋煬帝《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此詩中各種自然物之間純粹是動態的和諧共生關係,而人則完全是一個觀察者[注]孫尚勇:《〈維摩詰經〉與中古山水詩觀物方式的演進》,《西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李澤厚等一方面籠統地説:“在中國歷史上,把自然美作為獨立的欣賞對象和藝術的表現對象,是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注]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44頁。另一方面又明確説:“魏晉對自然山水美的認識,就大的方面説,經歷了一個由‘以玄對山水’到‘以佛對山水’的發展過程。”[注]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二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509頁。兩處表述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本文開端所引王國維、朱光潛、錢鍾書等觀點差異的緣由。這一緣由是,在經歷作為感情起點到感情載體之後,自然在魏晉時期經歷了作為玄理載體和佛理載體的變化之後,逐漸表現出獨立的審美品格。
到了唐代,詩歌逐漸强調追求客體自然之景與主體感情的交融和諧。總體來看,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四大類型:以自然為發端、以自然擬情、以自然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自然與人的感情抒發和諧相融,在唐代文學中,都得到了反映。這極大地影響了宋以後的詩文。顧彬説:“唐代文學以自然嚮内心世界的轉化,標志著到公元1911年為止的中國傳統文學中自然觀發展的終結。在後世的幾百年間,自然觀基本上没有新的發展,衹是在細部及通俗過程中,‘唐代傾嚮’表現得更加明朗、更加强烈罷了。”[注][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7頁。顧彬的判斷大致合乎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實際狀況。王德明認為,宋代是中國文學“再次走嚮情景分離”的時期[注]王德明:《中國古代詩歌情景關係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90—202頁。。然而,北宋梅堯臣《東溪》“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兩句,以經濟的筆墨描繪了自然物及其帶給人的審美感受,作者衹是用“有閑意”和“無醜枝”點明了自然物本有的那種意味,情景結合得很完美妥帖,並未分離。更重要的是,梅堯臣提出“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的主張[注](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何文焕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7頁。,這一主張分明是在强調“難寫之景”與“不盡之意”的兼顧,二者不能偏廢。又比如南宋四大中興詩人之一楊萬里的誠齋體便在自然審美和情感兩個方面都作出了極大的開拓。如《凍蠅》:“隔窗偶見負暄蠅,雙腳挼挲弄曉晴。日影欲移先會得,忽然飛落别窗聲。”《鴉》:“稚子相看衹笑渠,老夫亦復小胡盧。一鴉飛立鉤欄角,子細看來還有鬚。”《觀蟻》:“一騎初來隻又雙,全軍突出陣成行。策勳急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杭。”《宿孔鎮觀雨中蛛絲》:“空中仰面卻飛身,寂似毗耶不動尊。忽有一蚊來觸網,手忙腳亂便星奔。”這些作品表現出來的情趣是之前没有過的,其中所展現的人與自然物之間的感情頗令讀者感動。上述足以證明宋詩追求的是情景交融而不是所謂“情景分離”,王德明的説法並不可信。
大略來説,唐代以後表現自然美作品的主體特徵是,人與自然完全實現了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和諧之美。其間最重要的一項變化是,人成了與自然平等對待的審美對象。王維的名篇《山居秋暝》是其代表。王維在詩裏為我們描寫了春芳已去的初秋山居之景,這景與春日之景同樣美好,同樣值得人留戀,所以他決定仍然住在山中,而不是回到熙熙攘攘的城市。為什麽呢?因為游客漸去的初秋的“空山”,不僅有松間明月、石上清泉之美景,更有浣女、漁人歸來的人性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之美。詩中,浣女、漁夫實際上跟明月、清泉一樣,也成了審美對象,他們與自然和諧相依,他們融入了自然,成為作者描繪的山居景致的一個組成部分。
根據上面的分析,中國文學自然美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大類型:以自然為發端;以自然擬情;以自然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自然與人的感情抒發和諧相融。它們大致對應人與自然關係的四個歷史階段:先秦兩漢時期,自然作為表達人的思想、觀念的起點,缺乏獨立的審美品格;建安時期開始,自然作為人感情的載體,此後作為玄理和佛理的載體,在此過程中,自然逐漸表現出相對獨立的審美品格;晉宋之際開始,自然與人平等,擁有獨立的審美品格;盛唐以後,相互獨立的自然與人的情感意志進而與人自身交融無間。
三、中國文學自然美演進的思想動因
在瞭解了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類型及基本演進歷程之後,也許我們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從《詩經》至謝靈運的時代,為什麽經歷了一千年,中國人纔正式將自然視為獨立的審美對象?這似乎有些不可思議。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説古代儒家因重視社會問題而忽略對自然美的領略,這尚可理解,但是,我們不是還有與自然極為親近的道家嗎?
縱觀人類數萬年的歷史,文明以來數千年的歷史,可以説,人對自然採取純然無功利的審美態度的時間是極其短暫的。較早的時候,因為敬畏自然,人類仰視自然,不可能侈談自然之美;晚近的時候,科學昌明,人類轉而凌駕於自然之上,自以為美。這兩種態度,或仰視,或鄙視,都必然與獨立的自然審美多少存在著隔膜,與真正的自然美發生不了多少聯繫。衹有在一種情況下,這就是,人類對自身和自然達成互為主體性的平等觀念的時候,自然和人相對獨立,人纔有可能真正接近、認知進而以文學來表現作為獨立審美物件的自然的美。
葉維廉説:“山水在古代詩歌裏,如《詩經》《楚辭》及賦仍是做著其他題旨的背景,其能在詩中由襯托的地位騰升為主位元的美感觀照對象,則猶待魏晉至宋間文化急劇的變化始發生。當時的變化,包括了文士對漢儒僵死的名教的反抗,道家的中興和隨之而起的清談之風,無數知識分子為追求與自然合一的隱逸與游仙,佛教透過了道家哲學的詮釋的盛行和宋時盛傳佛影在山石上顯現的故事——這些變化直接間接引發了山水意識的興起。”[注]葉維廉:《中國古典詩和英美詩中山水美感意識的演變》,《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45—146頁。此論以儒教中衰、道家清談、隱逸求仙和佛教思想為影響山水詩興起的思想背景,考慮較為全面,但自然之能成為獨立的審美觀照物,有一些關鍵的推動力。事實上,在儒道二家思想之外,佛教思想對中國人的自然審美觀曾發生過重大影響[注]國内外相關研究約略,參見蕭馳:《大乘佛教之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中華文史論叢》總第七十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談談道家自然觀與佛教自然觀的差異問題。一句話,二家自然觀似同實異。道家説道無處不在,自然萬物無一不是道的體現。《莊子·知北游》中,莊子對東郭子説,(道)“無所不在”,道在碎石屎溺之中,碎石屎溺與人一樣都是道的體現。這典型地代表了道家萬物皆是道的體現的自然觀念。佛教則説,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中國禪宗説,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黄花無非般若。在佛教看來,自然萬物與人一樣均有成佛之可能性。也就是説,與存在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一樣,佛性同樣存在於翠竹、黄花當中,翠竹、黄花自身都天然具有佛性,千差萬别的自然萬物就是佛性本身。顯然,與道家萬物皆是道的體現的説法不同,佛教認為,萬物皆是道,而不必是道的體現。兩相比較可知,在佛教的觀念中,萬物自身皆具有獨立的價值並相互關聯;而在道家的觀念中,萬物皆是道的體現,因而萬物自身需要道的支撐,萬物自身並不普遍具有獨立的價值。《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這就是説,儘管都是道的體現,但人不如天地自然與道更為接近。莊子的物我相融主客不分並不建立在物我、主客相對獨立的基礎之上。正是在這一層面上,纔有了老子强調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纔有了栩栩然的莊周蝴蝶之夢,纔有了道家主張的人與自然的親近[注]1980年迄今,《莊子》審美生存和審美接受思想研究頗為突出,《莊子》當中也的確有大量的較《老子》更為“客觀”的自然景象的描寫,這些自然景象也的確給人們帶來了一定的審美感受。史華慈説:“Yet while these images never are introduced solely for their own sakes, these poetic invocations of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certainly do betray an enormous delight in the speatacle of nature as such.”(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20.)然而,正因為《莊子》中的自然“never are introduced solely for their own sakes”,即使它是“poetic invocations”,但人們感受到的衹是“an enormous delight”,而不是美。。魏晉玄學家的“以玄對山水”正是在這一點上生發出來的。
可以説,老莊道家思想、以老莊道家思想為重要方法論來源的玄學都不能自為地引導中國人真正將自然視作獨立的審美對象,佛教則很好地填補了中國思想的空白。佛教對中國文學自然美的促進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佛教禪定的實踐,促使中國人開始對山水自然進行相對獨立的觀想;其次,佛教萬法平等的思想,對中國文學中山水自然獨立審美品格的體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注]佛教的萬物平等思想植根於古印度文化當中,也就是説,中國文學自然美的演進得益於佛教東傳所帶來的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積極影響。印度自古以來便秉持人與自然萬物平等的觀念,故印度文學中更多對自然美的客觀表現。如迦梨陀娑(生活年代大致相當於中國東晉時期)的長詩《羅怙世系》對春天的描寫:“先是花生出來了,然後是嫩葉,繼而是蜜蜂和杜鵑的鳴叫;春天下凡到樹木茂密的林間,依次顯露出自己的形體。/不僅僅是無憂樹(紅綿樹)當春而發的花朵惹得愛侶調情,連新發的嫩葉也能點燃愛情的火焰,它是情人的耳飾令人心迷。/綴滿了花苞的芒果樹,被來自喜瑪拉雅山的風搖曳著樹葉,它好像在努力模仿各種手勢,讓那些已戰勝了愛與恨的人也如癡如狂。/森林邊上的藤蔓仿佛在低吟著動聽的歌曲,花兒是它們細小而潔白的牙,那是蜜蜂的吟唱;風吹動了藤蔓的嫩條,好像是舞女們變幻的手臂。/新茉莉好像是樹的嫵媚的情人,她以甜蜜的笑使人心醉;花就是她的笑面,嬌嫩的新葉就是她的唇,那笑容帶著蜜香和酒香。”(引自段晴:《印度人的自然觀初探》,《南亞研究》1998年第1期。)。
建安時期是中國文學自然美演進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時人們擺脱了此前以山水自然作為情感發端和道德比附的思維習慣,轉而以自然擬情。這一轉變的實現,老莊思想在漢末的流傳是重要因素,東漢三國時期小乘禪學的傳播則是另外一個值得重視的影響因素。桓帝時安息人安世高翻譯了《安般守意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等專門介紹禪法的經典,大力弘揚小乘禪法。安世高小乘禪法的核心是數息和觀想。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六載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論“四禪”觀想説:“自頭至足,反復微察:内體汙露,森楚毛豎,猶睹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衆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注](南朝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43頁。漢魏流行的小乘禪法之“四禪”,重在觀想自身“不淨”,並由自身“不淨”進而觀想自然的盛衰無常,從而信佛悟道。在“四禪”中,觀想自身是主體和核心,以此為階,進而觀想“天地人物”,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體意義,將人與自己的軀體分離了;不過,就悟道而言,觀想自身和觀想“天地人物”同樣重要。三國康僧會、東晉釋道安等的相繼推闡,進一步擴大了安世高禪法在三國兩晉時期佛教實踐層面的影響。前引錢鍾書“玩物審美”之山水詩由“附庸蔚為大國,殆在東晉”的觀點,於此亦可獲得一定程度的理解。杜繼文等指出:“佛教禪學的開拓,顯示出人的主觀方面對於整個精神世界及其支配的實際行為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有助於豐富人們對於認識主體的理解和全面估計主客雙方在認識過程中的相互作用。”[注]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頁。這可以説明佛教禪學實踐對漢魏兩晉自然審美觀念産生積極影響的緣由。
謝靈運的時代,追求“形似”成為時代風尚,自然美“成為人們自覺的審美對象”[注]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504頁。,中國文學中自然山水的獨立審美品格逐漸清晰。佛教平等思想是這一進程的重要促成因素。謝靈運與佛教平等思想有著怎樣的因緣呢?佛教平等思想,在以普度衆生為口號的大乘階段得到充分發揚,而這一思想最簡明的表述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中所説的“入不二法門”。對這一思想作出最直接易曉的詮釋的是羅什的兩大弟子僧肇和道生。前者被譽為“秦人解空第一”,後者曾在南本《涅槃經》正式問世之前大倡“一闡提有佛性”,他們對佛教平等觀的理解集中保存在《注維摩詰經》當中(説詳下文)。晉安帝義熙六年(410),僧肇和道生對佛教平等觀的理解由長安傳到廬山慧遠僧團,此後慧遠僧團將“以玄對山水”發展成為“以佛對山水”,作為慧遠俗家弟子的謝靈運正當其時[注]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第385頁;何劍平:《中國中古維摩詰信仰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第116頁。。可以説,謝靈運正是在大乘佛教平等思想的影響下,以他的創作實踐推動中國山水審美走嚮新的境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説法,正强調了佛教思想對山水詩巨大的決定性影響。
同樣,正是在佛教萬法平等思想的指導下,唐代詩人王維的部分詩篇,如《鹿柴》《竹里館》《辛夷塢》《鳥鳴澗》《酬張少府》等,纔真正完全擺脱了對自然的畏懼,達成了人與自然平等的交融無間,而這在謝靈運那裏未曾實現。朱光潛論王維《鹿柴》和《辛夷塢》説:“這是兩首典型的山水詩,表面上很客觀,好像衹各托出一種畫境,但是畢竟有詩人自己在裏面。這首先見於詩人對事物注意的總的傾嚮,不在於熱鬧的現實生活,而在於‘世外桃源’,在於一些孤獨幽靜的景物;其次見於詩人在事物的這種‘靜趣’裏,仿佛如魚得水,獨樂其樂;第三見於詩人在這類孤獨幽靜的景物裏見出他自己性格的化身,他的隱逸理想的體現。”[注]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文學評論》1960年第6期。引據《朱光潛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4頁。此處將王維的佛教思想説成是隱逸思想,失之籠統。
在佛教平等思想影響下,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處理自然與人關係的做法是,賦予自然跟人一樣的生命力。如果説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衹是從人的角度客觀地體察自然物之間的互動關係;那麽,李白的詩句“相看兩不厭”,就是賦予敬亭山與李白一樣的人格情感了。李白此類作品還可舉出一些更加明確的,如《勞勞亭》:“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别苦,不遣柳條青。”《對酒》:“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嚮我開。”《待酒不至》:“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嚮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窗下,流鶯復在兹。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這種表現自然美的手法,在唐以後的文學中得到廣泛運用。當然,李白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由與自然山水平等進而走嚮與自然山水親切交流的觀念,除了大乘佛教的影響之外,還應該同時接受了莊子自然與我相通相融相互親近的思想傳統的影響。李白詩“原無主客之關係”的特質[注]羅宗强:《自然範型:李白的人格特徵》,《晚學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5—197頁。,正是佛教平等觀和道家親近自然思想綜合影響之下的産物。
四、中國文學自然美演進的哲學意藴
董仲舒最早總結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以中國人對天的敬畏,以及採取與自然和諧相處策略為背景的。如果從中國哲學傳統所關注的天人關係的角度來看,上文討論的中國文學自然美的演進歷程及其思想動因問題,就可以理解為古代中國人關於天人關係的哲學思考在文學中的交互反映。也就是説,本文關於中國文學自然美的類型、演進及其動因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重要側面來理解中國哲學中天人關係的進程。
由天人關係的視角來看,謝靈運之前的中國文學山水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與“聲色”無所分别,屬於哲學上的天人不分,這是中國文學所反映的天人關係的第一個階段;謝靈運時代的中國文學山水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漸隱,聲色大開”[注](清)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03頁。,屬於哲學上的天人相分或天人對立,這是中國文學所反映的天人關係的第二個階段;王維、李白時代的中國文學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與“聲色”相統一,這種統一是“性情”與“聲色”在經歷無所分别到截然分立之後重新實現的,屬於哲學上的天人合一,這是中國文學所反映的天人關係的第三個階段。
談天人關係,必須提到張世英的研究。他的《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一書,以天人關係為綫索,以西方哲學為參照,審視了先秦至近現代的中國哲學史,是一部追求貫通中西哲學的力作。《天人之際》認為,中國哲學長期以天人合一為主導,明清之際,中國哲學纔出現了清晰的主客二分思想。這一觀點與本文根據中國文學自然美的演進及其思想動因的探討所提出的上述見解大不相同。
拙意以為,《天人之際》關於中國哲學天人關係的結論,雖然是在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透闢分析之後得出的,但其分析過程似有需要檢討的地方。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書中對佛教思想的認識不够充分,不够準確。這部書僅在第一章提到了佛教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而且主要以慧遠、僧肇、玄奘、法藏、慧能等幾位中國佛教徒的單篇或單部撰述為主[注]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1頁。,並未注意到這一時期佛教徒對佛經的注釋類撰述,尤其是忽略了《注維摩詰經》中所載羅什、道生、僧肇等人對大乘佛教平等思想的闡釋,也忽略了對唐代禪宗思想的論述。其實,《天人之際》中屢屢表彰的明中期王陽明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天人思想,都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注]潘桂明説:“雖然王守仁没有停留於禪宗的心性學説,但是禪宗的思想資料和思維方式在王學建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是學界公認的事實。”“王夫之對佛教也並非作簡單化處理,事實上他在批判禪學的同時,對唯識學卻表達了濃厚的興趣。”見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700頁。。
我們可以瞭解一下僧肇等人是如何理解和分析佛教的平等思想的。《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説:“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内外諸法,行於平等。”[注](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説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四卷,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第545頁。此處的“我、我所”,《注維摩詰經》卷八引僧肇曰:“妙主常存,我也。身及萬物,我所也。”[注](後秦)僧肇選:《注維摩詰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十八卷,第376頁。據此可知,《維摩詰經》中的“我”,乃指人及人的主觀意識;“我所”,則指“我”賴以存在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萬事萬物。《注維摩詰經》卷五引道生曰:“内者,我也。外者,一切法也。此則相對為二矣。謂不念之,行於平等,為離也。”[注]同上。按照道生的理解,“離我、我所”的“離”,指將“我”和“我所”分離,“相對為二”,這樣便實現了“我”和“我所”的“平等”。很顯然,《維摩詰經》的“我”相當於天人關係中的“人”,“我所”則相當於天人關係中的“天”;“離我我所”,即摒棄自我與外界事物之間的隔閡,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自我和外界事物。由天人關係的視角看,《維摩詰經》的“離我我所”即摒棄人對天的敬畏和依賴,以平等的態度來對待天和人,這正是天人關係中的天人相分。因此,中國哲學在晉宋之際曾出現過明確的天人相分的思想,衹不過,這一思想並非本土傳統的儒家、道家和道教思想所能促成,它更多依賴於佛教的推動。
當然,上述《維摩詰經》所代表的天人平等的思想是以“離”為前提,即天與人之間仍然是有隔閡的平等。在僧肇等人發明了這種以“離”為前提的天人相分的平等觀之後,先有三論宗創始人隋釋吉藏(549-623)提出“不但衆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注](隋)吉藏:《大乘玄論》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五卷,第40頁。,接著唐代中期天台宗大師湛然(711-782)提出“無情有性”説[注](唐)湛然:《金剛錍》,《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六卷,第782頁。,在更普泛的層面上肯定了“無情”的自然物亦有佛性。吉藏和湛然的主張反映了隋唐思想的巨大變化,這一變化的實質便是,佛教原本天人相離的平等,在佛性本質上走嚮了天人相合的平等。這既是前文所提到的禪宗翠竹黄花之説的淵源,也是王維、李白作品中“聲色”、“性情”相統一的哲學前提[注]賈晉華《皎然論大曆江南詩人辨析》(《文學評論叢刊》第二十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44—145頁)曾簡要論及湛然“無情有性”説對盛中唐之際劉長卿、嚴維、皇甫曾等人的山水詩歌創作的影響。稍後,蔣寅《走嚮情景交融的詩史進程》(《文學評論》1991年第1期)則進一步强調天台宗的止觀和禪宗真如緣起的認識對劉長卿等人的影響更大更直接。。
學界一度熱衷討論的中西文學自然觀的差異,實際上正是中西哲學思想差異在文學領域的表現。瑞士學者布克哈特分析西方自然美的表現説:“在古代人中間,藝術和詩歌在盡情描寫人類關係的各個方面之後,纔轉嚮於表現大自然,而就是在表現大自然時,也總是處於局限的和從屬的地位。”西方文學對自然的關注始於但丁。西方文學對自然美的集中表現還要等到十六世初前後。“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初那時到來的意大利詩歌的第二個偉大時代,和同時期的拉丁詩歌一樣,充分顯示了自然對於人類心靈的巨大影響。”[注][瑞士]布克哈特著,何新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92、293—294、300頁。王一川、朱立元先後以上引布克哈特的論述為依據[注]王一川:《中西方對自然美的發現》,《江漢論壇》1985年第6期。朱立元:《自然美:遮蔽乎?發現乎?——中西傳統審美文化比較研究之二》,《文藝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借鑑張世英哲學天人關係的思路,比較了中國和西方文學自然美表現的演進歷程,指出自然作為獨立審美對象,中國文學比西方文學早了將近一千年;進而將中西自然美表現上存在差異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奉行“天人合一”,西方推崇主客二分。根據上文的研究,王一川、朱立元對中國文學自然美歷程的概括並不全面,他們同張世英一樣没有充分考慮佛教哲學對中國天人關係的獨特貢獻。不過,朱立元又進一步分析了中西自然美表現之間細微但深層的差異:“在西方,不僅人們自然美的意識發生較晚,而且在人與自然的審美關係中,對立因素也明顯大於和諧因素,對崇高美不僅發現早於秀美,且感受、體驗的深廣度也遠遠超過秀美。”“中西兩大審美文化傳統,對自然美的態度是相反的,概而言之,西方是疏離、遮蔽的,中國則是親近、洞開的。”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西自然審美的差異及其原因。
綜合上面的引證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如下兩項基本事實:
首先,中西自然美觀念在年代和内涵上表現出巨大差異的原因有二:第一,由西方海洋文明與中國農耕文明的根本差異所導致的對不同群體生存能力的高下要求之分,決定了中國人早期面對自然主要採取了順應依賴的態度,而西方人面對的自然環境遠比中國人惡劣得多,因而,跟中國人不同,西方人對自然主要採取敵對或對抗的態度[注]羅素説:“希臘人最初便是在這些海上城市裏作出了對於文明的嶄新貢獻;雅典的霸權是後來纔出現的,而當它出現的時候也同樣地是和海權結合在一起的。希臘大陸是多山地區,而且大部分是荒瘠不毛的。但是它有許多肥沃的山谷,通海便利,而彼此間方便的陸地交通則為群山所阻隔。在這些山谷裏,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區域社會就成長起來,它們都以農業為生,通常環繞著一個靠近海的城市。在這種情況之下很自然的,任何區域社會人口衹要是增長太大而國内資源不敷時,在陸地上無法謀生的人就會去從事航海。”“(希臘)也有純粹農鄉的地區,例如膾炙人口的阿加底亞,城市人都把它想象為牧歌式的,但它實際上卻充滿了古代的野蠻恐慌。”([英]羅素著,何兆武、李約瑟譯:《西方哲學史》(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0、36頁。)據羅素的意見,作為西方思想發源地的古希臘並非以農業為依托,其發展受到自然資源的嚴重制約,在本質上它屬於海洋文明。而中國地處東亞次大陸,屬於與以農業為主的大陸文明。中西思想的差異,在本源上是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差異。錢穆從“源頭處”將人類文化分别為游牧、商業和農耕文化三型,游牧、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一類。游牧和商業文化,“無論其為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强烈之‘對立感’。其自然則為‘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為‘敵’‘我’對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學心理上之必然理論則為‘内’‘外’對立”(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弁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3頁)。。第二,兩漢之際,佛教輸入,數百年之後的晉宋之際,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哲學實現自然與人兩分,自然與人獲得平等對待的地位。同期的西方哲學卻不曾有這樣的機緣。法國漢學家侯思孟認為,中西之間對山水自然美領略的時代差異,受制於各自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存在一個久遠的“走嚮大自然的傾嚮”,而歐洲人則延續了漫長的“背離大自然的傾嚮”。他從山水與真理的追求角度,比較了慧遠、謝靈運時代與歐洲的不同。那時中國人傾嚮於在自然山水中尋求領悟真理,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上古時代末期最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可能如當時的慧遠之於中國——聖奧古斯丁(354-430)教導他的弟子們要在自己心靈中——即他所謂的記憶的宫殿——尋求真理,而不要去大自然中尋求。他甚至認為當人去看山頂時就會産生錯誤的觀念,還不如内省以求得真理和永福(slut)。就這樣,在古代世界的兩端,人都在尋求真理,但方式截然不同:在中國,人走嚮大自然的懷抱;在歐洲,人卻背離大自然,轉嚮自己的内心世界”[注][法]侯思孟撰,武佩榮譯:《山水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作用》(提要),收入臧維熙主編:《中國山水的藝術精神》,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第261頁。。更重要的是,西方哲學長期隸屬於宗教神學而不曾獨立,在西方宗教觀念中,人和神一樣,是高於自然的,這便是人們常説的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由於受基督教、古希臘哲學影響,人的那種特殊地位在西方真是根深蒂固。上帝造完世界後,最後告訴人,這一切都是供你享用的。”[注]張祥龍:《現象學導論七講——從原著闡發原意》(修訂新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2頁。故西方對自然美的思考、西方文學自然美的表現要晚於中國。
其次,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很大不同,除先秦名學、初期玄學和佛教哲學之外,古代中國基本上不存在純粹的形而上的哲學,中國哲學通常與現實政治社會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繫。董仲舒正式總結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能便包含著應對現實專制政治的深刻思考。這是天人合一説在中國古代佔據統治地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北宋士大夫常常希望以董仲舒天人感應的災異思想來控制君權,但效用已經大不如前。富弼企圖以災異警戒宋神宗,但是有人對神宗説:“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富弼聽説之後感嘆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注](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55頁。參看葛兆光:《洛陽與汴梁》,《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1—42頁。此外,“蘇軾駁斥否定天人相關論的言論,也是擔心失去那種能制止人君的恣意行為的東西”[注][日]小島毅:《宋代天譴論的政治理念》,[日]溝口雄三、[日]小島毅主編,孫歌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5頁。。類似事例足以説明,至遲在北宋中期,天人相分的思想已經極其流行。出身於士大夫階層的哲學家們仍極力主張天人相合,並不是他們單純在哲學層面思考所作出的選擇,而是經過審時度勢、權衡利弊之後作出的現實選擇,這一選擇有著明確的現實政治目的。這雖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但同時也完全暴露了秦漢君主專制政體完全確立以後中國本土思想整體的懦弱習性。因而,討論中國哲學問題時,不能以哲學家的著作為單一依據,還應該結合古代社會政治的實際狀況來綜合考察,更應該考慮到佛教思想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就後一點來説,中國文學史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不應忽視的資料。
五、結 論
中國古代文學自然美大致包括四大類型,經歷四個階段:先秦時期,自然作為表達人的思想、觀念的起點,没有獨立的審美品格;魏晉以後,自然作為人的感情載體,此後作為玄理和佛理的載體,在此過程中,自然逐漸表現出其獨立的審美品格;謝靈運以後,自然獲得了與人平等的審美地位,擁有了獨立的審美品格;王維、李白以後,相互獨立的自然與人的情感意志進而與人自身交融無間。這中間,大乘佛教“離我我所”的平等思想是中國文學中自然獨立審美品格實現的最直接的推動力。這彰顯了佛教哲學對中國文學自然美演進的巨大意義。
由天人關係的視角看,謝靈運之前的中國文學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與“聲色”無所分别,這對應於哲學上的天人不分或原始的天人合一;謝靈運時代的中國文學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漸隱,聲色大開”,這對應於哲學上的天人相分或天人對立;王維、李白時代的中國文學自然美的特徵是“性情”與“聲色”相統一,這種統一是“性情”與“聲色”在經歷無所分别到截然分立之後重新實現的,對應於哲學上的天人合一。中國文學自然美的演進歷程表明,中國哲學曾有過清晰的天人相分或天人對立的思想,其出現年代在公元5世紀初謝靈運的時代;中國哲學也曾有過經歷天人相分之後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最初出現的年代在公元8世紀盛唐王維、李白的時代。
本文“引言”部分所提到的古典詩學情景關係的研究,事實上應該從中國文學自然美之類型與演進的角度來進行宏觀把握。與中國文學自然美的四大類型相一致,情景交融至少也可以被區别為相近的四大類型,即以景發端,以景擬情,以景為獨立的審美對象,景與情和諧相融。因此,本文關於中國文學自然美的演進歷程、思想動因及其哲學意藴的考察,對進一步研究情景交融理論及與之相關的意境、境界、意象等古典審美範疇的歷史内涵當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