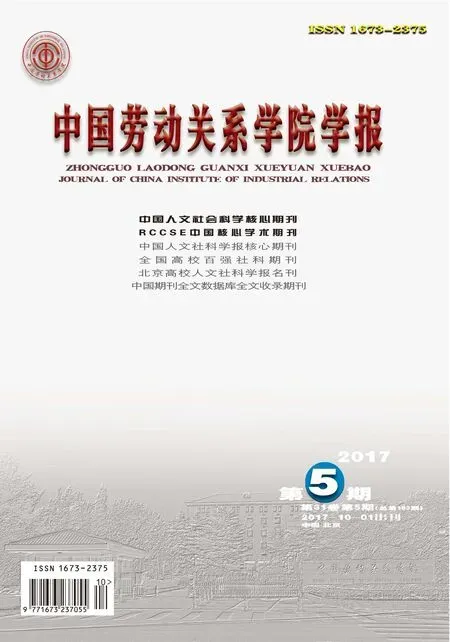民国时期集体劳动合同立法述论*
—— 以1930年《团体协约法》为中心
2017-01-24张秀芹岳宗福
张秀芹,岳宗福
(1.山东工商学院 法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2.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民国时期集体劳动合同立法述论*
—— 以1930年《团体协约法》为中心
张秀芹1,岳宗福2
(1.山东工商学院 法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2.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民国时期,通常将个别劳动合同称为劳动契约,而将集体劳动合同称为团体协约。中国劳工立法较迟,团体协约立法则更晚。国民政府有关团体协约的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929年《劳动法典草案》的编纂,其后在《工会法》起草过程中也有团体契约权的规定。延至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颁行《团体协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集体劳动合同的专门法律。《团体协约法》的出台因应了当时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的实际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
民国时期;集体劳动合同;团体协约法
集体劳动合同简称集体合同,又称集体协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常称为团体协约。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立法最初开始于英国等工业先进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发展较迟的国家,劳工立法起步较晚,集体合同立法则更加滞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正式颁行的《团体协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集体劳动合同的专门法律①台湾当局曾于2008年1月9日对该法进行修正。。近年来,随着当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劳资争议及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开始从历史视角研究民国时期的劳工立法,其中有些论著已涉及到团体协约立法的内容②饶东辉《南京国民政府劳动立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田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争议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研究报告,2005)、周卫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资争议处理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等论著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到《团体协约法》。,但目前学界对于这部法律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及其制度安排尚缺乏专题性的研析。
一、民国集体劳动合同立法的国际背景
集体劳动合同是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工业社会早期,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一切风险均由其本人承担。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当劳工们发现无法通过个人力量与雇主抗争以保护自身利益时,他们就开始自发地组织劳工团体,这是工会的雏形。雇主面对劳工的联合组织也开始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从而产生了雇主协会[1]。劳工组织与雇主组织通过集体谈判签订劳动合同最早出现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工业先进国家。英国雇佣劳动者组织与工厂主于18世纪末期签订的劳动协定可谓是集体劳动合同的最早萌芽。美国费城的制鞋工人代表也于1799年与雇主进行过有关劳动条件的谈判。英国的纺织、矿山、炼铁等行业的工会组织也于1850年通过与雇主谈判达成协议。德国书籍印刷工人联合会则于1873年通过与雇主谈判成功地签订了第一个集体劳动合同。最初,由于集体合同得不到政府的认可,所以并没有法律效力,法院也不受理因集体合同争议提起的诉讼。但随着工业社会的进步和劳工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工业先进国家开始对于集体劳动合同进行规制,逐步启动了集体劳动合同的立法活动。1875年,英国政府颁布《企业主与工人法》,规定允许工人团体与雇主签订劳动契约,可以说是集体劳动合同立法之滥觞。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集体劳动合同立法,如新西兰于1904年即颁布有集体协议法,奥地利和荷兰则于1907年分别制定了关于集体协议的法律[2]。但这一时期,新西兰、奥地利、荷兰等国家都明确规定由民法调整有关集体合同的签订与实施问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体劳动合同法才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
检视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前半叶的集体合同立法,其立法模式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一种是单独立法模式或单行法模式,即制定一部单行法专门规范集体合同问题,当时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有德国、芬兰、瑞士等国家。德国在1918年底颁布了《劳动协约、劳工及使用人委员会暨劳动争议调停令》,1921年4月又颁布了《团体协约法(草案)》,对团体协约做出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芬兰和瑞士分别在1924年和1928年颁行了《集体协约法》。另一种是综合立法模式或法典模式,即国家在制定的综合性劳动法典中设专门部分(例如专设一章)规范集体合同问题,这种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有苏俄、法国等国家。苏俄曾于1918年7月公布集体合同法令,后于1922年颁布的《苏俄劳动法典》中设专章对于集体合同做出了规定;法国曾于1919年颁布了《劳动协约法》,后来又将该法并入《劳动法典》。当然,当时也有许多国家既没有采取单行法模式,也没有采取法典模式,而是在劳动关系法、工会法等劳工立法中设置相应的条款规制集体合同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分散立法模式或法条模式,即关于集体合同的法律规制以法条的形式分散在一部或多部劳动法规之中,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二、民国集体劳动合同的立法进程
中国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已将劳工问题纳入其政策及纲领。1923年1月,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并发表改组宣言,宣示要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平等”[3]。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其中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其劳工政策及立法目标,如制定劳工法、工会法、劳动保险法,限制工时、废除包工制,设立劳资仲裁会、劳工补习学校,改良劳工居住条件等[4]。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国民党奉行的是比较积极的劳工政策。但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其劳工政策逐渐趋于保守,特别是对于工会组织及其罢工问题开始持谨慎或限制态度。不过,从巩固政权及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国民党政府依然把推进劳工立法及倡导劳资合作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甫一组建,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劳动法典》。1927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劳工局,劳动法起草委员会遂并入该局,并编定《劳动法典大纲》;翌年1月,国民政府又公布《劳动法起草委员会组织条例》,要求6个月内将《劳动法典》全部草拟完成,呈送国民政府核定。但嗣后由于起草委员会人员变更,劳动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也时断时续,延至1929年春,《劳动法典草案》最终起草完成。
此草案共计由7编、21章、863条构成,开篇的第一编及第二编即分别规定了个别劳动合同和集体劳动合同的内容。其中将个别劳动合同称为“劳动契约”,包括一般劳动契约和特种劳动契约两章;而将集体劳动合同称作“劳动协约”,当时仅仅完成了第一章团体协约法草案。团体协约法草案规定,只有雇主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团体与劳动者团体,才具备签订团体协约的能力,才能成为团体协约的主体,并限定劳动者团体不能属于某一特定经营且不许雇主参加其中。同时,该草案还借鉴德国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将“劳动关系”规定为团体协约的客体。
在明确团体协约主体和客体的基础上,团体协约法草案分别规定协约的期限、效力及标准协约问题。关于团体协约的期限,当时的起草者考察了国外的相关制度,发现法国规定为5年、德国规定为3年。该草案最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德国的成例,规定签订团体协约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关于团体协约的效力,该草案规定包括了团体协约效力所及范围、民法上物权之效力、民法上债权之效力、团体组织上的效力等方面。标准团体协约实际上就是将团体协约标准的效力扩张至非协约所属者的一种立法行为,但团体协约毕竟不是法律,其有时间、地方与职业的限制,且能因时因地宣告适宜的劳动条件,较之法律运用起来更加灵活自如,因此该草案采用了标准协约的规制。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选择了劳动法典的立法模式,所以团体协约立法也被纳入《劳动法典草案》之中。《劳动法典草案》完成后,即呈交国民政府立法院审议。但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已决定放弃法典化的立法模式,而改采单行法的立法模式,立法院遂将《劳动法典草案》留作起草单行法时的参考资料。此草案“虽未成为法典,而旁搜约采,寻源竟委,汇编别章,提情蕴理,实开我国劳动立法之新纪元”[5]。团体协约立法也由此从法典模式转向单行法模式。
实际上,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192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通过并由孙中山大元帅公布了《工会条例》,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处于对等之地位、并拥有对于雇主的团体契约权,这可谓是国民党政府对于团体协约进行立法规制的最早萌芽。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劳工立法采取单行法模式之后,团体协约立法虽然启动较晚,但在此期间的工会立法及劳资争议立法均已经涉及到团体协约立法的相关内容。
国民政府于1928年6月公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当时劳动法学界将劳资争议区分两种,一种被称为“法律上之争议”,类似于当今学界所谓的“个别劳动争议”;另一种被称为“事实上之争议”,也被称为“集合争议”或“团体争议”。《劳资争议处理法》开篇即规定,本法适用于“雇主与劳工团体或劳工30人以上,关于雇佣条件之维持或变更”所发生之争议[6]。由此不难看出,《劳资争议处理法》的目的在于预防劳资集体交涉演变为劳资冲突或对抗,实质上是一部劳资团体争议调解仲裁法,也是一种劳资团体协约签订及履行的保障机制。
工会通常是代表劳工签订团体协约的重要主体,所以工会立法与团体协约立法密切相关。1928年9月,国民政府法制局拟具的《工会法草案》即明确承认工会享有团体缔约权,但此案后被搁置。1929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拟具的《工会法原则草案》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审议,其中也明确规定工会享有缔结团体协约权,但对于军事军工、公共行政、公用事业等特殊行业所组织的工会,则限制其缔结团体协约之权。因此,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于1929年颁行的《工会法》,虽明确承认工会的主要目的为劳动条件之维持改善,与雇主订立修改或废止团体协约是其对外最主要的任务,但又限定团体协约的订立改废必须经政府主管部门认可才能生效,同时对于前述特殊行业之工会组织的团体协约权仍持禁止态度[7]。
综上所述,在《团体协约法》颁行之前,国民政府在《劳资争议处理法》、《工会法》等劳工立法之中对于团体协约做出了规制,这些规制均为《团体协约法》的制定和颁行奠定了一定的法制基础。同时,通过签订团体协约以决定劳动合同的内容及标准的做法,在当时中国各工商重镇及各大商埠已“风行一时”,“惟未立有完密之法规,协约无所准绳,纠纷莫由解决”[8],所以适时制定和施行《团体协约法》也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立法院劳工法起草委员会以劳动法之起草前经决定采用单行法模式,且《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均已完成公布,遂于1930年5月提出了《团体协约法草案》。
该草案由劳工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史尚宽起草,立法院将该草案付诸初读并讨论后,即议决交付“法制委员会”与“劳工法起草委员会”一起审查。经过两委员会共同讨论,略加修正后通过。该审查修正案在立法院召开的二读会上进行了逐条讨论,并省略三读,最终全案通过,然后呈由国民政府于1930年10月28日公布。至1932年10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该法于当年11月1日起施行。实际上,《团体协约法》从制度框架安排到基本内容条款多取材于《劳动法典草案》相关内容,只不过立法模式已经由综合立法演变为单行立法而已。
三、民国《团体协约法》的制度安排
《团体协约法》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并借鉴了当时德国、奥地利、苏俄、法国、新西兰等国家的立法成果和经验,同时也考虑和结合了当时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其立法主旨在于“顾及劳资双方之权利义务,保持协约期间之和平,而预防劳资纠纷于未然,并为解决劳资纠纷之准据”[8]。《团体协约法》全文共计31条,分为5节,依次为总则、限制、效力、存续期间、附则,其法律设计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协约主体的设置和安排
团体协约主体即进行团体交涉、签订团体协约的双方当事人。根据《团体协约法》的规定,团体协约是指“雇主或有法人资格之雇主团体,与有法人资格之工人团体,以规定劳动关系为目的”所缔结的书面契约。因此,团体协约的签约主体,在资方限于“雇主个人”及“有法人资格的雇主团体”,在劳方仅限于“有法人资格的工人团体”。这里强调协约主体的法人资格主要是考虑到此类团体存在的合法性及长久性,有利于稳妥履行协约义务。由于团体协约的拘束力往往涉及到全体团体成员,所以团体成为协约主体在事前尚需获得订约的权限。这种权限的获取通常有三种渠道,一是依据团体章程的规定;二是依据团体成员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授权;三是逐个得到团体全体成员所授予的特别委任书。如果团体未能在事前通过上述渠道获得订约权,其所缔结的团体协约必须得到其“团员大会之追认”,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协约客体的设置和安排
团体协约的客体即团体协约规定的范围,当时团体协约俗称“劳资条件”,世界各国关于团体协约客体的规定不尽一致,法国用“劳动条件”的字样概括其范围,德国则用“劳动关系”的字样概括其范围,其具体内涵又有广狭义之分,但核心含义则不外乎“劳动契约之内容及其标准”。《团体协约法》借鉴德国的成例,使用了“劳动关系”的概念,并明确团体协约有规定劳动关系以外之事项者,对于其事项不适用本法之规定。但该法并未对“劳动关系”的内涵做出清晰的界定,从其相关的各个条款来看,主要包括对于雇主和工人团体劳雇关系、工人加班工资、工人参加工人团体的活动时间、雇主采用新式机器或改良生产等方面。此外,职业介绍机关的利用、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学徒关系、劳资纠纷调查机关或仲裁机关的设立或利用等也属于该法所称的劳动关系。因此,当时所谓“劳动关系”之内涵与当今中国大陆学界所谓“劳动关系” ,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三)协约成立的规制与安排
团体协约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从理论上讲,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不论是口头协约还是书面协约,均应当有效。但是,如果要明确彼此权利义务关系、预防将来发生劳资争议,自然以书面协议妥当。当时德国、法国等国均要求团体协约必须是书面契约,《团体协约法》在制定过程中亦借鉴了国外成例,做出了类似规定。但是,《团体协约法》将团体协约成立与否的最终决定权赋予了政府主管部门。根据规定,团体协约签订后,当事人双方或一方需报政府主管部门“认可”,若发现协约有违背政府法令、超越雇主经营事业范围、不利于维持工人通常生活标准等内容,主管部门有权“删除或修改”;删改后如能得到当事人同意,则主管部门对删改后的团体协约予以“认可”。这一规定借鉴了苏俄关于集体协议的立法经验,而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盖以吾国劳动运动,尚属幼稚,劳资各走极端,不免有损彼此之协定,惟官署处于第三者之地位,自可以顾全双方之利益”[8]。这种解释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将政府主管部门“认可”设置为团体协约成立的最后一道程序,未免有将政府意志强加于团体协约双方主体之嫌,也明显有违于集体协商制度的基本宗旨。
(四)协约限制的设计与安排
团体协约的内容由劳资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民政府却以“我国产业尚属幼稚,劳资双方未明协约之本旨,每走极端,大反勤业兴工之意,驯至陷于两败俱伤,破坏生产秩序之原则”[8]为由,在《团体协约法》中特设“限制”一节,对于团体协约的内容做出了诸多限制。譬如,团体协约一方面规定,雇主雇用工人“限于一定工人团体之团员”,并应“由工人团体介绍”;另一方面又规定,雇主对工人团体介绍的工人,有权自由选择是否雇用;如果出现工人团体的成员不足供给、不愿应雇、不具备雇主所需专门技术等情形,或者雇主需雇用学徒、需雇人为其管理财务、印信、机要文件者时,均可不限于劳工团体之成员。再如,出于对工人加班工资的保障,团体协约一方面明确规定雇主于休假日或于原定工作时间以外需要工人工作或继续工作时,其工资“应加成或加倍发给”;另一方面又明确限制其加班工资“不得超过2倍,超过2倍者视为2倍”。表面看起来,《团体协约法》中这些限制性内容是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格局,但如果考虑到劳方和资方不同的社会地位,其立场不言自明。
(五)协约效力的规定与安排
效力是指团体协约成立之后所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团体协约的效力一般包括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的效力。时间效力是指团体协约从何时生效、何时失效。团体协约一般应自成立之时发生效力,但根据《团体协约法》第4条的规定,已经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团体协约“自认可之翌日起发生效力”;前项规定,“于团体协约之变更或废止”时同样适用。显然,这是将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作为生效的要件。空间效力是指团体协约对于哪些地域、哪些职业的劳工、雇主具有约束力。《团体协约法》并没有专门条款规范团体协约的空间效力,但在规制团体协约冲突的处理规则时涉及到其空间效力问题,其中第5条规定,当出现劳动关系同时受到两个以上团体协约调整、且先生效的团体协约无特别规定的情形时,处理规则有两项:一是职业范围较小的团体协约优先;二是地域或人数适用范围较大的团体协约优先。前者适用于职业性的团体协约,后者适用于非职业性的团体协约。团体协约对于人的效力不仅及于当事人,而且及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这是团体协约的特点。《团体契约法》明确,作为“团体协约当事人”的雇主与属于“团体协约当事团体”的雇主及工人均属于“团体协约关系人”,同时规定在团体协约成立后加入该团体的雇主及工人也受团体协约的约束,其约束力的发生日期依据协约规定,如协约没有规定,则从雇主及工人取得“团体协约关系人”资格之日起发生效力。
(六)协约期限的设计与安排
关于团体协约的存续期间,通常区分为“定期、不定期、以一定之工作定期”三种情形。除了不定期的情形外,各国立法对定期及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团体协约,一般都会对其最长期限做出限定,如当时德国限定为不超过3年,法国限定为不超过5年。《团体协约法》借鉴了德国的立法经验,也考虑到经济现象变化无常,如果期限过长恐怕不利于当事人一方,因此设定3年为定期团体协约的最长期限,如果超过了3年的期限,则视同为3年。这种限定对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团体协约同样有效,如果该项工作在3年内未能完成,则视同双方签订了一个3年的定期团体协约。同时根据该法的规定,团体协约成立后,作为签约主体的劳方团体或资方团体,如果发生合并、分立及解散等情形,一般不会影响团体协约的存续期间及效力。关于团体协约的终止,《团体协约法》实际上设置了三种情形:一是期满正常终止,即定期或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的团体协约,因期限届满或工作完成而终止,或因超过最长期限于期满3年时终止;二是订立1年后随时终止,这是针对不定期协约的特别规定,劳资双方当事人都享有协约终止权,但应依据团体协约所规定的期限提前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提前通知的期限应不少于3个月;三是非正常终止,不论何种期限的团体协约,如果协约签订后经济情势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劳资双方或一方签约的目标无法达成,甚或与之相背离,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应协约当事人一方的请求废止相关的团体协约。
(七)违反协约的责任及法律救济
根据《团体协约法》的规定,团体协约当事人如果违反了团体协约,需要承担罚金、损害赔偿金等责任。罚金是针对当事人违反团体协约中不属于劳动条件之约定的一种处罚措施,是否处以罚金由法院决定,但前提是一方当事人提出了相关申请;罚金的标准,在劳工方面不超过50元、在雇主方面不超过500元。损害赔偿金则是针对当事人不履行团体协约中属于劳动条件之约定义务时的一种处罚措施。关于法律救济渠道,《团体协约法》规定了以团体名义请求损害赔偿及进行诉讼的机制。作为团体协约当事人的劳方团体及资方团体,如果发现有违反团体协约的情形出现,不论违反者是团体还是个人(也不论该个人是本团体成员,还是其他团体成员),均可以本团体名义向违反者请求损害赔偿;作为协约当事团体,只要事先通知本人且本人没有表示反对,就可以为本团体任何一位成员提出涉及团体协约的一切诉讼请求。
(八)团体协约与劳动契约关系的安排
劳动契约即个别劳动合同,团体协约即集体劳动合同,集体合同效力高于个别劳动合同,这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根据《团体协约法》的规定,团体协约所确定的“劳动条件”(主要指其中的标准化条款),自动成为该协约所属雇主及劳工之间订立的个别劳动合同之内容;如果个别劳动合同所定“劳动条件”与团体协约相偏离,则偏离部分无效,自然以团体协约的相关内容取而代之;只有这些与团体协约相偏离的内容被该协约所容许或其中包含对劳工利益保护更有利的条件时,这些偏离的内容约定才是合法有效的。这实际上借鉴了德国劳动法上 “有利原则”[9]。同时,《团体协约法》还明确禁止协约所属雇主及劳工在个别劳动合同存续期间,放弃其由团体协约所定的个别劳动合同上之权利;如果劳工基于团体协约所产生或衍生的权利而进行维权行动,协约所属之雇主不得以此为由终止其个别劳动合同。
四、结语
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是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制定并颁行《团体协约法》应当说是顺应了当时中国工业化的客观趋势,也适应了当时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冲突的实际需求。中国是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与工业化相配套的法规制度都需要从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移植而来,但如何处理外来法规制度的本土化问题始终是中国近代以来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历史课题。集体劳动合同制度也是一种“舶来品”,当时的立法者同样面临着上述历史课题,他们在团体协约立法过程中,详细考察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同时也力图结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做出适当的取舍和借鉴,最终完成了团体协约立法。尽管其中某些法律条款及制度设计还存在不足,但若单纯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这种立法精神和取向并无不妥之处。自工业社会到来以后,劳资对抗和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如何缓解劳资矛盾并稳定社会秩序成为任何政权都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社会问题。集体谈判和团体协约制度正是适应了消除劳资对抗的社会需要才应运而生的,所以通过集体谈判构建稳定均衡的劳动关系必然是团体协约立法的根本要求。因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团体协约法》制定过程中所追求的平衡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合作的立法理念,我们也没有必要做过多的政治评判和责求。
当然,“始生之物,其貌必丑”。《团体协约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集体劳动合同的专门法律,必然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局限。首先,团体协约是雇主或雇主团体与劳工团体通过集体协商、自愿达成集体劳动合同的一种机制,但是该法赋予了政府部门过多的行政干预权,比如团体协约的成立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团体协约的废止需要向政府主管部门声请,特别是该法还专设“限制”一节对于团体协约的内容规定了多种限制,使得该法不像保障团体协约的立法,而更像限制团体协约的立法,几乎完全背离了团体协约的立法宗旨。其次,该法对于团体协约内容的规定过于简略。团体协约是劳资双方围绕就业条件、劳动条件和劳资关系达成的集体协议,通常应当包括工资报酬、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劳工福利、职业安全卫生与女工保护、劳动合同管理、团体协约的期限、变更及解除团体协约的程序、团体协约争议的协商处理机制、违反团体协约的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但是,该法当中并没有规范团体协约主要内容的专门条款,即便从全部法律条文来看,其关于协约内容的规制也显得比较粗疏。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国民政府的团体协约立法不可谓不理性,但要想正常发挥其应有作用,尚需有完备的社会政治体制、成熟的法治环境、健康的经济状况作为基础,更需要同步推进实施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配套性的劳动法律制度。但是,当时“劳资纠纷和劳劳纠纷,像乱丝般交织成一个大黑网,笼罩着整个产业界,使劳资双方本身及主管劳工行政的当局,终日穷于应付,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人力去推行积极性建设性的劳工政策”[10],所以身处乱局的南京国民政府往往“有心立法”却“无力施法”。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有法不依”的乱象在民国时期仍十分普遍,不能因为国民政府推出了《团体协约法》,就断言其处理劳资集体交涉问题就一定会“依法”进行;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国民政府在处理劳资集体争议方面“无力施法”而否定其在团体协约立法方面的积极举措,因为在集体谈判和集体劳动合同方面,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毕竟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
[1]姜俊禄.集体合同——历史演变、理论评述及利益共享理论提出[EB/OL]. http://www.lawtime.cn/info/laodong/ jitihetong/2010110471245.html.
[2]常凯.劳动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97.
[3]江亮演.社会安全制度[M].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49.
[4]江亮演.社会安全制度[M].中国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52-53.
[5]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M].张知本,校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64.
[6]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M].张知本,校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130-1131.
[7]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M].张知本,校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90.
[8]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M].张知本,校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141-1142.
[9] [德]曼弗雷德.魏斯,马琳.施米特.德国劳动法与劳资关系[M]. 倪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9.
[10]邵心石,邓紫拔. 上海市劳工年鉴[M]. 上海:大公通讯社,1948:5.
Collective Labor Contract Legislation in the R.O.C Era: Focused on Group Agreement Act of 1930
ZHANG Xiuqin1, YUE Zongfu2
( 1.Shan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2. Shan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
The individual labor contract are often called labor contract and the collective labor contract is called the group agreement in the R.O.C era. Chinese labor legislation is late and the group agreement legislation is later. The group agreement legislat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reation of Labor Code Draft of 1929, there is a regulation of the group contract rights in the drafting of Labor Union Law. In 1930,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fi cially enacted the Group Agreement Act. As the fi rst special law on collective labor contract in Chinese history, the Group Agreement Act was introduced in response to the actual demand of labor conf l icts duri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but it was also inevitable that there wer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the R.O.C Era; Collective Labor Contract; Group Agreement Act
D922.53
A
1673-2375(2017)05-0044-07
[责任编辑:补 拙]
2017-06-25
张秀芹(1966—),女,山东菏泽人,法学学士,山东工商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法;岳宗福(1967—),男,山东成武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