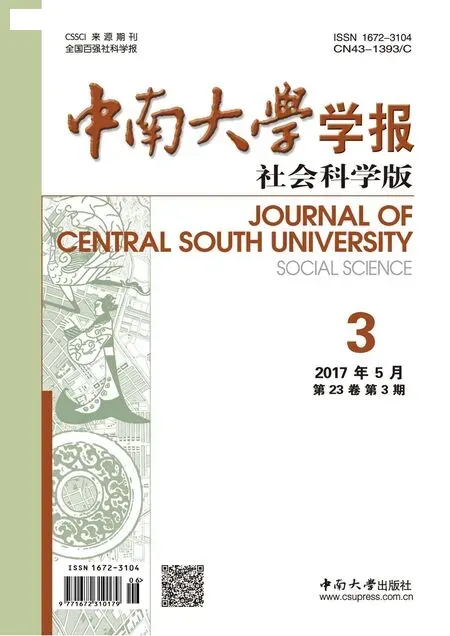春秋时期“德”观念中的“事神”
2017-01-12谭笑
谭笑
春秋时期“德”观念中的“事神”
谭笑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源自周公时的“德”在春秋时期仍是重要的思想观念,内涵“事神”和“抚民”两种倾向。多数学者因以春秋之时“德”与抚民的言论多次关联出现,甚至有“民为神主”的表达,而认为这说明了春秋时抚民的发展和事神的衰落。这种看法一则不全面,忽略了在春秋之时“德”的事神倾向也有增强的表现;二则忽视了抚民与祖灵信仰、祭祀、事神的有机关系,对关键史料解读不足。抚民作为“德”的一面,与事神一起关联着农业生产、最终服务于“保祭祀”的目的。“保祭祀”的本质仍是事神,与春秋时期氏族的组织机制的存在相生相伴。彼时萌芽的个人化的新“德”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和旧“德”在春秋时是共存的。
德;事神;抚民;春秋时期;氏族组织机制
在春秋时期思想史上,“德”是一个地位显著的观念。其原型来自周公制礼作乐时的相关论述,简要来说有“事神”和“抚民”两种内涵。有关“德”观念在春秋时期的演化特征,学界的看法很集中,即认为事神面日渐弱化、消亡;而抚民的一面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内涵,在不断发展、壮大。
但本文认为,春秋时期“德”观念中事神的一面并未衰落,学界对“民为神主”等材料的解读有可商榷之处,且春秋时期的思潮里也有“事神”回潮的一面;关键在于,需要把事神和抚民二者放到祖灵信仰的背景下,才可以看出它们互相依存、共同服务于“保祭祀”——这归根还是事神。
当然,春秋时期“德”的原理也在发生变化,表现在出现了“个人化”的新“德”。文末将简要对比这种新“德”与“保祭祀”之旧“德”的原理差异。
一、“德”在春秋:抚民独秀?
“德”在殷商鼎革之际变得重要。虽然完成克商的是周武王,但周人认为上帝是因文王的德性,将统治中原地区的天命“赐予了文王本身”[1],周人子孙后代也得以享文王之福继有天下,或受封成为一方侯伯。“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2]把属于文王个人的“文王之德”转化为周人政权具体的政治规范,发生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周公所确立的“德”中,包括以下两个面向。
其一是事神。如杨向奎先生分析周公的氏族国家中“礼神”行为规范的观点时,觉察到德是“对礼的修正和补充……礼不应当仅是物品的交换,仪也不应当仅是外表的仪容,他(周公)把它们伦理化、美化”[3]。事神是祭祀行为当中的政治规范,即:神祇对活着的后人如何祭祀的多方面要求。这一“德”的内涵,在人与神的不对等关系中展开,即人(氏族核心成员)应孝敬祖灵,祖灵据人的祭祀情形决定以灵力降下福祸,影响氏族的存续状态。
其二是“抚民”。典型如余英时先生对傅斯年等许多前辈学者的观点的引申,认为周公所论之“德”的核心体现为上帝对周人在如何对待被统治之“民”的统治政策上的伦理要求:
“天”将“命”托付于一个新的王朝之后,并不从此袖手不问,相反地,“天”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民”的动向。如果受“命”王朝努力工作,建立起一个使“民”满意的“礼”治秩序,这便证明它“敬德”,因而可以继续保有“天命”。反之,它将失去“天命”,即所谓“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4](96)
抚民树立起了一种超出以讨好祖先神灵来求福避祸为目的的政治规范,将对有无“德”的直接关注点,从人神二者的关系下移到了如何维护、改善被统治的庶民的生存状况上,即在神、人、民三个对象间建立了一种三方关系。
对周公之“德”在春秋时期的沿革,学者们多认为带有人文主义特征“抚民”的一面在不断上升、发展;而事神的一面在不断弱化、消亡。如徐复观先生引《左传·桓公六年》含“民为神主”这一短语的史料论证“周初已经将天命与民命并称,要通过民情去看天命。这种倾向,在春秋时代,因道德的人文精神的进步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以神的道德性与人民性,是一个性格的两面。《左传》桓公六年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上面是说,民站在神的前面,亦即人站在神的前 面”。[5]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论述春秋时期的政治新特点时,引用《左传·成公六年》鲁国大夫臧文仲对六、蓼国亡国的评价,用以说明如臧文仲等春秋人物认为是否行德政以得民心是政治成败的关键。[6]又如陈来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中论述春秋时代的祭祀时,引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中鲁僖公与臧文仲讨论是否应该焚烧巫尪以求雨,臧文仲论述此举无益的例子,以说明巫尪地位的下降体现了神本思想的衰落、人本理性的上升。[7]
这样把抚民与积累“德”联系起来的史料还有很多,如春秋中期楚共王即位后,国际形势倒向晋国,令尹子重建议修德惠民:
先君庄王属之曰,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责(债),逮鳏,救乏,赦罪。[8](807)
使晋国复霸的政治天才晋悼公,在即位后除了选贤任能以外,大部分政策都属于重修德政:
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债),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8](808)
又如春秋晚期齐国晏婴劝说齐景公抚民,景公一度听从:
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 责。[8](111)
可是,这样的论证充分吗?
二、春秋事神:消亡?回潮?
本文认为春秋时期事神仍然重要。这样的史料实在不胜枚举。但要证明这一观念并未消退,首先要对学者们常引用来说明抚民崛起、事神衰落的关键史料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譬如上文提到了陈来引用鲁国臧文公认为六、蓼两国被灭国是因为未得民心,体现出以“德”的抚民面为政治中心的史料,全文如下:
冬,楚子燮灭蓼。臧文公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8](540)
臧文公感慨六、蓼两国被楚灭国,但他的重心并非两国亡国国人或者庶民的境遇,而是两国祖灵的绝祀。德不建、民无援,是对“皋陶、庭坚不祀”原因的分析。若以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来,抚民是国家政治的中心,那未抚民的国家,被灭也实属理所应当。只有把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祭祀,或者说祭祀体现了氏族国家本质,而修德、包括抚民莫不服务于此,才能把对臧文公所感慨的这段话解释得通畅。祭祀,无疑是事神。
而在鲁僖公十九年,即鲁僖公与臧文仲讨论大旱求雨该不该焚巫尪的两年前,与鲁国同样历史悠久的姬姓国卫国也发生了旱灾,但解决之道却完全相反: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8](111)
卫国大旱,占卜祭祀山川的神祇,结果不吉。卫国大夫宁庄子不同于同时期的臧文仲认为的旱灾只要抚民即可,他提出了一个事神的方案:替天伐无道,对邻国发动战争。对本国而言,战争无疑是抚民的反面。但是这条史料的结果是,卫国整军待发,老天就降下了雨水。宁庄子揣摩神意,做出了和抚民抵触的决策,但是结局导向的是神灵的降福消除了干旱。从结果而言,这比起两年后鲁国抚民抗旱减少损失是个更好的结果。这至少表明春秋时期,从事神面去处理自然灾害仍然并非罕有。
《左传·桓公六年》“民为神主”史料,也需要看其所属的整体语段: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8](111)
随国大夫季梁劝阻随侯不要追击想诱随国出兵故意示弱的楚师,认为楚国强盛有得天命的迹象,而随国弱小。小国必须有道,即忠于民、信于神才能自保,随君逞欲害民,在祭祀中不诚实,因此不道。随君认为自己事神丰厚,神会降福。季梁则提出了民是神的主祭,成民是为了有财力来致力于神,奉牲、奉盛、奉酒醴,都是为了向神灵展示生者治国生财的成效,祭祀的丰盛应当同民生丰裕、国人团结匹配。民馁却祭祀丰盛是欺骗鬼神,而鬼神不受欺。如果生民富足,鬼神才会享用祭祀,福佑国家行动成功。
在这里,如果把“民为神主”按学界主流观点理解成“民”才是政治的重心,“民”的作用高于“神”,那么事神的部分应当轻描淡写,论述的主体应该围绕“民力为何才是政治能量的本质”展开。但在季梁从“夫民,神之主也”开始,整个语段都是以“什么样的祭祀才被鬼神认可”为中心,这无疑是在讨论事神。固然,抚民是季梁施政理想中逻辑顺序上的首要举措,但抚民政策的目的却是为了“信于鬼神”的“丰备”祭祀,最终所求还是通过祭祀以得到鬼神灵力的降福而“动则有成”, 使民挨饿的丰厚祭祀则无法讨好鬼神。此外,鬼神被赋予的关注庶民生存的政治伦理,是自周公时期“德”的观念即具备的一面,并无新意,很难说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进展。
同时,与“抚民”相对的“事神”传统在春秋时期也有“回潮”的趋势。殷商时期商人和东夷地区大量广泛地用人牲献祭以取悦鬼神和祖灵,周人在克商的过程中也曾沿用,但周人灭商后革新了这一祭祀礼仪,伴随着周人的王权和扩张而扩展着影响力,“西周贵族墓里和墓地上,罕见用人祭祀,宫殿宗庙建筑中,也未见奠基牲。但与殷人关系密切的东夷旧地,用人祭社的习俗仍长期流行”[9]。因此,在春秋时期,将民、甚至一国之君视为可供神灵食用的牺牲,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事神之殷商传统的复归和对西周确立的抚民文化最大限度的背离。而这一回潮在春秋周王室式微之时,自宋襄公到楚灵王屡见不鲜,反映了当时诸国为求天命与自存,也有采取殷商祭祀传统的尝试: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8](381)
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8](1327)
最为讽刺的是,周公的后人、鲁国执政季平子,在对邻国莒国获得军事胜利后,于鲁国的亳社重新祀以人牲: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8](1318)
因此,春秋时期并非“德”观念抚民一面单方的高歌猛进,事神面被统治者重视、甚至以“人牲”的方式复归,也同时在上演。
三、“德”“保祭祀”:抚民与事神
春秋时期的国家机制、政治形势虽然在不断变迁,但各国仍然延续了氏族国家的基本架构,围绕祭祀机制展开。国家的祭祀,是我们理解春秋时期“德”观念事神、抚民二者关系的钥匙。
(一) 鬼神灵力与事神
春秋时期,人们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大体而言,人死将成为鬼神,鬼神有灵力来影响人间,尤其是对直系血缘后裔所在与鬼神生前居住之所。对一国而言,除了祭祀祖先神灵,境内的山川之神、土地神、农神等与自然有关的神灵也与一国的生产、存亡密切相关。
鬼,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10](759)白川静《常用字解》则强调鬼字“特指人鬼……大头形表示鬼与活人形态不同”[11](66)。死亡即人所归处,归而后成鬼。联系活人与鬼的是人的魂魄。郑国的伯有在卿大夫阶层的斗争中惨死,一度家族覆灭,伯有的祖灵化作厉鬼预言了两个仇敌的死期并先后应验,使得郑人非常恐惧。子产认为伯有化作厉鬼是失去了祭祀所致,所以复立伯有的后代(以有资格祭祀),由于伯有有了祭祀(归),它化作的厉鬼被平息了。当子产出使晋国,晋卿赵景子询问子产伯有化作厉鬼的事情,子产解释了生者的魂魄和死后成为鬼神的关系: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8](1291)
《说文解字》释:魂,阳气也;魄,阴神也。[10](760)结合子产的解释可知,人在活着的时候,主宰身体器官性能强弱的是魄,而精神能量强弱的主宰是魂。生时用物精多,则魂与魄的能量强大。即使普通人强死(不得好死)也能成为厉(鬼)害人,如果所属的氏族强大,则人死后,魂魄会成为更加强大的鬼。鬼对人世的干涉能力的大小即鬼能量的强弱。指代这种威能的词是灵(靈)。白川静先生结合灵的小篆,与多种灵字的甲骨、金文异体字后认为,灵字造字本意,是“雨”“口口口”和“巫”合成的会意字。三个“口”是三个放置了向神祷告之祷词的巫术用具(白川氏认为汉字中绝大多数“口”的部件,都起源于这种意涵),整体表现巫者求雨的仪式。但后来,求雨成功的这种有效能力,开始成为了生者(未来的鬼)、死者(已成之鬼)之威能的同义语。[11](453)此外,白川静还在《汉字百话》中引用了春秋时期齐大宰归父盘的铭文,内含“灵命难老”[12](74)(“祖先之灵保佑万寿无疆”)的祈祷词,即祈求死去祖先之灵力的保佑。伯有化作厉鬼托梦、预言、害死政敌的能力,即人鬼的灵力。
神(祇)是指相对于人鬼的自然之灵。称为天神、地祇。陈梦家先生按《周礼》把殷墟出土的卜词中商代所祭祀的“神”分类总结了出来:天神包括天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等;地祇如社、四方、四巫、山、川等。[13]故鬼神并称。神祇不同于鬼的特点是它本体的非人格化,往往和自然的力量结 合。[12](92)《说文解字》释: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10](5)神灵所掌虽和自然有关,但祭祀神祇,其实仍和人鬼密不可分。如,传说周的先祖弃,是本族农业史上做出最突出贡献者,故鲁国作为姬姓之后,把弃作为“稷(农神)”来祭祀;传说上古共工氏后人后土,曾经平九土,因此后世持有这种记忆的氏族广泛把后土当作“社(土地之神)”来祭祀: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14](154)
又如,封、嵎山之灵最早由汪芒氏祭祀,并由该氏族后人世守这一祭祀,因此该族的祖灵成为了封、嵎二山的神(祇):
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 姓。[14](202)
可见,神(祇)往往不是这些自然灵本身,而是在遥远记忆中曾经最早生活于此并与具体自然对象建立起关联性的氏族祖灵。祭祀本族祖先人鬼或者通过“山川之守”的后代祭祀神祇,说到底,都是祭祀祖灵。
在解释世界时,自然的节律与灾害、与别国的和战,都会被归结于神灵的灵力。按其直接或间接对本族的利害来区分,效果可以分为福与祸。如郑庄公灭许国后,在对与许同为姜姓的齐国前来责问的外交辞令中,就把自己出兵的合法性奠基于“代神降祸”:
(郑庄公)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8](74)
而在《国语·楚语下》中楚国大巫观射父与楚昭王的对话谈到了神明降福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14](512)
祖灵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一国的本质是其国的祖灵,与一国的外交会当作希望向其国家的祖灵徼福: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伯禽),以事君。[8](588)
由于一国君主或卿大夫死后会成为鬼神,在表达托他们的帮助时会用“以君之灵”:
既飨,楚子问于公子(重耳)曰,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14](332)
而多国会盟时,对盟誓的盟书效力的见证者是诸国的鬼神,若有与国违背,施加惩罚的是诸鬼神的灵力:
乃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薀年……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8](989)
把自然和政治的后果当作神灵的灵力的影响,尤其是对神灵降祸的恐惧,使得春秋的统治者们在相对于人间政治关系中的其他对象而言,将鬼神看得尤为不可抗衡。人无法对抗天祸,又依赖天福,因此拥有灵力的鬼神会被当作高于人间政治主体——特别是高于被统治的“民”。一直到春秋后期的周灵王时代,有贤名的周太子姬晋仍把神的灵力降祸看作大于民怨: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民有怨乱,犹不可遏,而况神乎?[14](22)
但神灵并非完全不可沟通。除了巫术、巫者以其知识来沟通人与鬼神外,人间的统治者与鬼神最重要的日常沟通是祭祀行为。
祭祀是什么?按《说文解字》:祭,会意,从示,以手持肉;祀,祭无巳。[10](5)白川静先生认为:“祭”指代在祖庙以牺牲的肉(月部)供奉上祭坛(示部),请祖先享用;“祀”则是对自然神灵(“巳”部来自蛇形,推广指代一切自然神)的供奉祭拜。[11](155)祭祀的原理,是鬼神“需求祭品”、也会“饿(馁)”,因此有楚国大夫屈到在病死前叮嘱本族的宗老在今后祭祀自己时,奉上自己爱吃的“芰”为祭品: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曰,祭我必以芰。[14](488)
楚国大夫子文在死前推演本族将受难绝祀时,为本族祖灵将(因被灭族)永远挨饿而痛哭:
子文……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这都是认为鬼神对后代生者祭祀的需求。前文所引伯有化作厉鬼作祟,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就是因为祖灵失去了后人祭祀而报复仇人。
由于春秋之时人们的观念中鬼神与人在力量上仍然非对称,以及向鬼神求福避祸主要以祭祀鬼神、缓解其“饥饿”来达成,所以无数古代统治者把事神看作最重要的日常政治行为。即使是赐予周文王“天命”、在周公那里哀悯“四方民”的皇天上帝,也不免会饥饿而需要殷周王室祭天。因此,在西周王室用以“保天命”、在春秋诸国公室、卿大夫家族拿来“保国(家)”的“德”之中,含有事神的一面,且仍有很多国君、卿大夫把丰厚地祭祀鬼神当作保家保国的第一政治任务,不足为怪。
(二) 抚民与得财得民
重视周公阐发之“德”的另一重内涵——抚民,如学者们早已发现的,在春秋时期所见不鲜。持这种观点的臣子往往规劝君主把改善庶民的生活状态摆在施政的第一位,认为抚民是神灵庇护的前提。除去前文所引随国季梁的论述,鲁国曹刿也留下了经典言论。
长勺之战,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数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14](143)
在曹刿的长篇大论中,虽然逻辑上是要把“布德于民”——即抚民放在施政的第一位,神灵表面上仅沦为了保障这种政策的理由,但仔细分析,抚民是为了得财,即通过政治上的爱惜民力,使庶民创造财富。有了充足财富的前提下,才既能施舍于民、保证民和,同时使神能享有优裕的祭品。鬼神希望得到丰厚祭祀的观念并没有改变,生者需要以祭祀获得鬼神灵力降福的目的也没有变。这和季梁论述祖灵希望从祭品的丰厚中看到民力(财)充裕如出一辙。
因此,抚民之所以重要,毋宁说是一个浅显的经济理由:即春秋时期的财富,主要通过农业产生。农业需要事神以保自然层面的风调雨顺,但也需要庶民耕作土地。西周的王室卿士虢文公曾论述过农业(得财)与事神、抚民的关系: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14](15)
抚民能带来财货,除能让民安心生产外,也能吸引来本国内其它氏族、甚至别国的民归附本族本国,在农业生产中增加劳动者数量。春秋时期,血缘氏族仍然是组织人口的基本结构,各国尚未建立起如战国以后官僚国家时代以地缘行政单位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因此,无论是零散的庶民,或者一国、一氏族的举族迁徙,都频繁见于史书。[15]如果本国、本族政治抚民有方,那么远人来归更加证明了一国、一族的有德;如果本国、本族政治无德,则人民将起“携贰”之心,成为“远人”出奔他族或者他国。得民则强,失民则弱:
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14](28)
民在一国国内的流动而导致族与族之间的强弱颠倒,最经典的例子是春秋末期齐国的陈氏崛起。陈氏借贷于民,大斗出而小斗进,暗中给予优惠;而公室敛聚,人民三分收获两分归公。晏婴因此评价,齐侯所敛已朽坏生虫,公室的三老们却在受冻挨饿。在公室不抚民而卿大夫力行德政的情况下,公室之民纷纷依附了陈氏:
晏子曰……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8](1134)
(三) “保祭祀”下事神与抚民的统一
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有氏族组织的人只要不是横死在外而未葬入本族墓地,死后就能与历代祖灵团聚,获得“不朽”,如晋国大夫知罃被俘,对楚王说希望能回国接受晋国国君或者宗族首领、其父荀首的 处死:
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8](813)
古代人观念中鬼神的永恒特性使得鬼神需要永恒的祭祀。可是,祭祀的“不朽”却需要祖灵的一代代后人能保持氏族组织的存在,如此才能有组织“保祭祀”,范宣子与叔孙穆子一次经典的对话中,范宣子把自己祖先“保祭祀”不绝的历史看作不朽,叔孙穆子总结为“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8](1087)
在春秋时期,一个氏族国的宗室或者卿大夫家族,其追求的是一种射线般的永恒。即从某个作为氏族始祖的端点开始,子子孙孙放射开来永世不坠、氏族的祭祀不绝。每一代氏族领袖在生前都服务于这一永恒的再实践。他们和祖灵的同理心是,鬼神现在的愿望即自己将来的愿望。故古人最大的恐惧不是个人成败得失,而是氏族的祭祀的断绝。
如楚国大夫鲁阳文子,推辞了位于楚国边境险要位置的封地——梁。他担心自己的后代若凭借梁或有不臣之心,自己所属氏族会因罪灭族绝祀:
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14](528)
前文所引臧文公感慨“皋陶庭坚之不祀”,子文死前感慨“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盟誓的载书中诅咒违背同盟之国家的后果是“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也是同理。所以“保祭祀”和“德”观念中事神的关系很自然:事神即无限的“保祭祀”事业中完成好每一次祭祀,让鬼神满意从而福佑后人能把“保祭祀”进行下去。
但如何理解抚民和“保祭祀”?
其实,回到虢文公论农业和曹刿论抚民的史料,二者的关系就显现了:祭祀除了需要氏族组织,还需要丰厚的祭品,而祭品来自农业。农业运转良好(得财),在前提上又需要抚民和事神,两者分别从民力和灵力(自然规律)上保障农业丰收;得财之后的目的,是能进一步保持抚民和事神,从民力和灵力上保证下一次农业生产(得财)。所以,灵力和民力作为农业生产(得财)的两项条件,本身又需要消费农业产出(“夫民求不匮于财,而神求优裕于享者也”)来再生产。因此,事神、抚民——农业生产(得财)——事神、抚民——农业生产(得财)……形成了一个互为条件和目的的循环。“德”所能“保祭祀”的道理,即同时重视保证农业生产的两项要素,使“得财”的这个循环不发生断裂,祭品源源不绝。
如前文所述,由于以氏族国家为基本观念的政治中对灵力的依赖更广,所以对以财事神的偏重可能会妨害以财抚民。强调“民为神主”,事实上是指出了轻视抚民对农业生产(得财)循环的伤害,终将伤害到未来的“保祭祀”。从这个思路就能理解,为什么前文所引的季梁、曹刿在强调了抚民的重要性后,言论中的重心却在讨论财力(祭品)和祭祀的关系。神灵要求氏族首领抚民,与其说是对民的哀悯,不如说是在意“民和”才能“生财”,“生财”才能“事神”。周厉王时期王室大夫芮良夫的一段评价可以作为后世春秋时期的氏族领袖们如何以“德”的两面来“保祭祀”的参照: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14](13)
重视祭祀建立在信仰祖灵的基础上。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到春秋末期,相比已出现的县制等新组织体制,各国仍以氏族作为框架性的组织方式,因此终春秋时代,保有氏族组织的王室、公室、卿家很自然地会传习周公之德。如春秋晚期,楚平王仍然把“抚民人”“事鬼神”等同于修国政的同义语:
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8](1361)
四、“保祭祀”之德与“个人化”之德
周公之德在春秋时期的持续传播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产生有关“德”的新观点。因为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等因素,使得“以本族存续”为中心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在知识阶层的观念中被边缘化,“德”的机理也随之变化——此即余英时先生所谈的“个人化和内在化”的德的出现。[4](221)
这种德将人们的思考对象从如何获取鬼神灵力的福佑以“保祭祀”转移到关注个人德性的内涵本身,在深化、细化的具体德目当中,建立起实践特定德性与获得相关后果的关联,无关神灵。如东周王室卿士单襄公论晋国公孙谈之子姬周(即晋悼公)的“德”,完全在谈姬周的举止和后果: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且夫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
因此,德所关联的不朽之物,也从氏族祭祀的存续,位移到了个人的德行实践。如前文所引叔孙穆子否决了范宣子“保祭祀”式的不朽观,以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为例,论证“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全不落一氏一姓“保祭祀”的窠巢。他口中不朽的“德”,意义来自个人之“德行”本身,具备在某种范围内普遍有效的智慧。一如臧文仲之言,即使在他死后仍长久地得到了诸国外族贵族们的认可、传播以至于“虽久不废”,如此依托于个人的“言”本身,在时间上产生了如“世不绝祀”般的“不朽”。这即是春秋时期的卿大夫阶层中发生的内在化、个人化的新“德”的机理。
这种普遍有效又个人化之“德”的形成,与春秋中期以后,来自不同族姓国家的贵族群体在不断的会盟聘问中,形成了基于周文化的公共文化有关。这样出现了一批贵族,开始能超越本族的特殊主义眼光,对列国间公认的优秀贵族何以优秀,不只停留在论证其祖灵福泽,更进而从其德、功、言本身的内涵中寻找答案。对比此后不久孔子之“德”较周公之“德”彻彻底底地个人化及以“仁”为首发展出的诸多修养德目,可以料想孔子的“德”和叔孙穆子的“三不朽”之间在原理上的亲缘之处。当然,这也同孔子及其弟子许多出身于士阶层,生来无关周公之德“保祭祀”适用范围的情状有关。
五、结语
“德”有事神和抚民两个面向,一同服务于氏族国家“保祭祀”的目标,这种机理来自周公之“德”。春秋时期,使用“德”的群体超出了周王室,普及到诸国公室、列国卿大夫家族,用以指导本族“保祭祀”,留下了很多重视抚民的论述。但综合考虑春秋时期诸国仍以氏族机制为基本的组织方式,且祖灵信仰仍然无处不在的背景,在仔细分析有关抚民的经典论述后可以得出结论:“德”观念中抚民和事神一起,在以“得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中有客观的重要性;但“得财”的主观目的仍是为了“保祭祀”。因此,抚民思想在春秋时期,与事神不仅不对立,相反服务于事神。这一旧“德”伴随氏族机制存在于整个春秋时期,即使春秋后期出现了个人化之新“德”。
[1] 李峰. 西周的政体: 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98.
[2] 方玉润. 诗经原始·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490.
[3] 杨向奎.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331−332.
[4] 余英时. 论天人之际[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5]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C]//李维武. 徐复观文集·第3卷.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60.
[6]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51.
[7] 陈来.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11.
[8]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9] 黄展岳. 古代人牲人殉通论[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48.
[10]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11] 白川静. 常用字解[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2] 白川静. 汉字百话[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13]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562.
[14] 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5] 巴新生. 春秋贵族“出奔”所见之周人国家观念[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 36−45.
“Worshipping gods” in the concept of “D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AN Xiao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The concept “De” derived from the time of Zhougong, but was still influential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worshipping god” and “appeasing people”. Most scholars hold that the latter aspect was flourishing whilst the former one was declin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there were a lot of sayings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e” and the aspect of “appeasing people”. However, this view is not complete as there were also a lot of sayings about the strengthening of “worshipping god”. Nor is the view accurate as it neglected the organic relations among “De”, the belief of ancestral spirits, sacrifice and worshipping gods. “Appeasing people” as an aspect of "De", together with “worshipping gods”, shared a connection with agriculture and served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worship”. But the essence still lied in “worshipping gods”, coexisting with the organizing mechanism of clan through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There was a sprouting and individualized form of “De” indeed with the transi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These two forms of “De” coexisted at that time.
De; worshipping gods; appeasing peopl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rganizing mechanism of clan
[编辑: 颜关明]
B82
A
1672-3104(2017)03−0178−08
2016−11−02;
2017−01−25
谭笑(1989−),男,湖南湘潭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