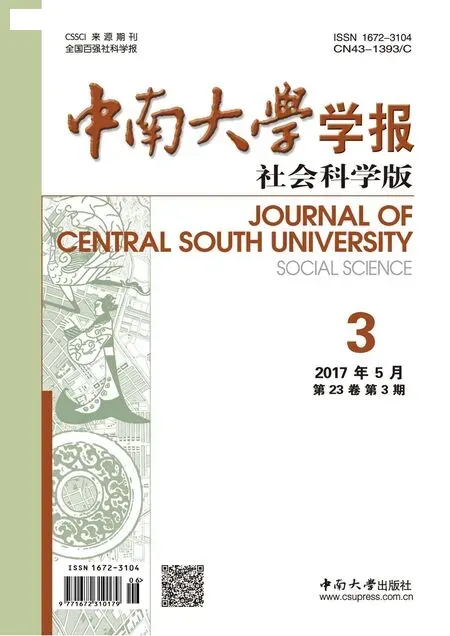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2017-01-12戴路
戴路
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戴路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南宋五山禅林的四六疏文包括劝请、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作者多为临济宗大慧派僧人,主要用于公共交往。首先,宋代释疏撰制经历了由文人疏向僧人疏的转化过程,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出现于南宋后期,表现在文体类别的细化、应用场合的增多、文本载体的丰富。其次,五山禅林住持的选任制度推动了世俗政权与寺院的互动,围绕人事变迁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影响了四六疏文的表达策略与辞章结构。第三,五山禅林的寺院建设为募施化缘的疏文提供了广泛应用空间,作者藉助亦僧亦俗的四六语言随机设教,开启了超越凡圣的解脱法门,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南宋;五山禅林;公共交往;四六疏文;住持选任
禅林疏文用于住持劝请、开堂说法、修造募施、斋会节庆等场合,通常用四六文书写,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将其概括为法堂疏和募缘疏两类,其下又可细分为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1]。日本五山僧人虎关师炼(1278—1346)在康永元年(1343)编成《禅仪外文集》,主要收录宋代禅僧的四六文书,包括疏、榜、祭文三类。它为日本五山僧人撰制日用文书提供了范本[2](37−72),也是后人认识南宋禅林四六的重要窗口。从入选作者看,北磵居简(1164—1246)、淮海元肇(1189—1265)、藏叟善珍(1194—1277)、物初大观(1201—1268)、无文道璨(1213—1271)均属临济宗大慧派禅僧,大都拥有住持五山十刹的经历,其四六写作是南宋五山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宋代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①。物初大观的法孙笑隐大(1284—1344)在元代江南禅林具有广泛声誉,其四六技巧形成“蒲室疏法”,影响到日本五山僧人绝海中津(1336—1405)、仲芳圆伊(1354—1413)、惟肖得岩(1360—1437)等人的四六写作,呈现出明晰的传播线索[3]。因此,追溯日本中世禅林汉文学的源头,探讨南宋五山禅林四六风貌,对南宋文学、禅宗文化、东亚文化圈的研究都有帮助。在禅林四六中,疏文的撰制、传递、应用涉及僧众的公共关系,包括丛林间的社群交际、僧俗互动、国际交往等。因此我们以公共交往为切入点,关注这种交往与四六写作的关系,在两者的相互阐释中把握南宋五山禅林四六的文体属性与精神意蕴。
一、从文人疏到僧人疏:南宋禅林四六的兴盛
从文体源流看,禅门诸疏存在一个从文人疏向僧人疏的发展过程。禅僧在住持、开堂等环节所需文书,最初基本由文人代笔,随着丛林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学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开始壮大,疏文的种类不断细化,禅林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禅林象器笺》第廿二类“文疏门”云:“禅林请住持疏,韶州防御使何希范等制请疏,令云门偃禅师(864—949)住灵树为始”,“僧疏则九峰韶公作疏请大觉琏(1009—1090)和尚住阿育王山,此为始矣”[4]。在晚唐五代农禅向宋代文字禅的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僧人加入到禅林文书的写作队伍中来。从《禅仪外文集》的选文数量看,据黄启江统计,北宋九峰鉴韶1篇,惠洪14篇,南宋僧人共88篇[2](51),折射出禅林四六在两宋的发展趋势。而根据这一时期禅僧笔记、语录的记载,我们也能看到从文人疏向僧人疏的演化过程。
北宋文人士大夫撰写的疏文往往因其文笔流畅、描述精当在僧众中赢得声誉,如徐禧(1043—1082)劝请晦堂祖心(1025—1100)之疏:
徐龙图禧,元丰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既归分宁,请黄龙晦堂和尚就云岩为众说法。有疏曰:……今之疏带俳优而为得体,以字相比丽而为见工,岂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黄太史为擘窠大书,镵于翠琰,高照千古,为丛林盛事之传云[5]。
徐禧的文风加上黄庭坚的书法使这封请疏广泛流传,成为“丛林盛事”。再如俞紫芝(?—1086)为西余净端(1031—1104)开堂所作疏文:
师初开堂,俞秀老作疏叙其事曰:“推倒回头,趯翻不托。七轴之《莲经》未诵,一声之《渔父》先闻。”师听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6]
像徐禧、俞紫芝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北宋的释疏撰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对而言,北宋僧人所作疏文在禅林笔记中的记载偏少。时至南宋,“丛林盛事”的主角更多由僧侣来担当,如以下几例:
昙橘洲者,川人,乃别峰印和尚之法弟。学问该博,擅名天下。本朝自觉范后,独推此人而已……故别峰自金山来雪窦,诸山一疏,乃昙撰之,其词曰……此话江湖竞传之[7](160)。
普慈闻禅师,豫章人,姿貌不凡……暮年,再奉旨归雪峰。鼓山升老次山作疏云……闻福缘甚胜,近世罕及[7](160)。
雪巢一和尚,自号“村僧”,嗣草堂清。久住平田,后长芦力命不赴,以皎如晦一疏而往[7](138)。
遯庵演,闽人……闽帅赵汝愚待以福之秀峰,坚卧不起。别峰作疏劝请,有“幽兰林下,岂无人而不芳?至宝道中,盖具眼而始识”之句,一时罔不高其清节[7](166)。
可见在南宋丛林间,僧人撰疏已较为普遍,文人士大夫作品的“丛林盛事之传”变为文学僧辞章的“江湖竞传”。除了禅林笔记的记载,南宋禅师语录的相关文字亦显示出这一趋势。如《虚堂和尚语录》卷三《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语录》:
拈诸山疏:刹竿标处,钟梵相闻。要知暖气相嘘,总在里许。
拈山门疏:同门出入,未尝谩尔诸人。苟或粉饰太过,山僧只得掩耳[8](1004)。
又如《虚舟普度禅师语录·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拈江湖疏:人相忘于道术,鱼相忘于江湖。既曰相忘,拈起疏云,却要这个作什么②。
这种针对疏文而发的法语,在淮海元肇、无文道璨、环溪惟一、希叟绍昙、痴绝道冲等南宋禅师的语录中均有保存。前引西余净端针对俞紫芝疏文的点评,为我们提供了北宋住持开堂仪式的生动场景。但“拈疏”作为入院升座的固定仪轨,应当发生在南宋禅林四六普遍兴盛之后。在此前的语录中,我们基本上找不到“拈诸山疏”“拈山门疏”“拈江湖疏”等记载,而此后的元明禅师语录中,“拈疏”法语已较为普遍,诸如《敕修百丈清规》《列祖提纲录》等对此类清规仪节的记载也更加详尽。可以说,南宋是禅林公共礼仪发展和完善的重要转折期。拈疏说法这种开堂仪式的固定化,离不开疏文的大量撰制,因为越来越多“学问该博”的文学僧加入到禅林四六的创作队伍中来。 除笔记、语录外,在元明人所作题跋中,我们也能寻觅到不少南宋禅僧创作疏榜四六的踪迹。如元僧元叟行端(1255—1341)所作《书颜圣徒手抄四六稿后》:
四明颜圣徒,宋建绍间,由毗尼而天台,由天台而禅肆,当时号为俊人。其《达磨疏》有曰:“日居月诸,曾根源之罕究;齿摇发脱,犹枝叶之徧寻。”能自知入海算沙之困,庶几可无愧焉③。
颜圣徒活跃于南宋前期,所作《达摩疏》与前述劝请疏、山门疏等稍有不同,但仍属禅林四六文书的一部分,其四六手稿一直保存到元代。另外,晚宋藏叟善珍所作茶汤榜文的遗稿也流传至元代,元叟行端与笑隐大均有过目。元叟行端称“天和首座得其偃溪茶、汤二榜,十袭以为至宝”③,笑隐大称善珍“以善骈俪称之”,“其里人天和首座得其为偃溪作茶、汤二榜,甚秘惜之,以示予”④。这些四六疏榜均以单篇稿本的形式流传下来,而南宋后期亦有专门的禅僧四六别集刊刻,如释道璨曰:
四六,词人难能之伎,变为榜疏,尤词人之所甚难能者……太虚之赴中峰也,以其手编寄予于径山。既没之明年,属四明观物初择其工致精粹者,付其孙讷刻梓以惠后学[9](159−160)。
太虚德云亲自编定的四六疏榜文集,经过大观的汰择、道璨的题序,最终由讷和尚刻印。南宋后期诗词小集的刊印为人熟知,这种丛林内部刊刻流传的疏榜小集又让我们看到禅林四六发展的另一种面貌。
以上从笔记、语录、序跋中引述诸多材料,旨在表明两宋禅林四六演化的总体趋势:从作者看,文人士大夫主导四六写作的局面被日渐壮大的文学僧群体改变,骈文技巧在更广泛的地域和僧众中得到普及。从文体看,疏文的类别更加细化,榜文逐渐兴盛,与此对应的住持上任、开堂、化缘、修造等禅门仪节轨范在南宋得到新的发展。从载体看,在语录、灯录、僧传、会要、偈颂、拈古、颂古等宗门文献之外,疏榜四六的独立版本形式开始出现,作为专门文学样态的价值得以彰显。在此背景下,南宋后期五山禅林的四六文章开始登场。物初大观在为石田法熏(1171—1245)所作行状中写道:“至词章骈俪,丛林所需者,虽不从事乎此,或有所为,操笔立就。敷腴调畅,非凡浅者所能到也。末叶雕零,人物眇然,长于此或短于彼,若师者。可谓兼之矣。”[10](989)事实上,像石田法熏这样长于骈俪,兼擅“外文”“内文”的僧人在五山禅林中比比皆是,诸如居简、元肇、大观、道璨、善珍等人都留下了丰富的疏榜文字。
二、禅林公举与士僧互动:疏文的交际性
五山十刹制度的基础是官方主导寺院住持的选任,僧人要获得提名,需与皇室、宰执、地方官等保持密切联络。官方在处理山门人事问题时,又会征询耆宿与僧众的意见,新住持要成功上位,需在丛林享有较好的声誉。对一位出家僧人而言,其正常上升途径为:取得僧籍——供职两序——出世住持——迁转名刹,终其一生离不开寺院等级体系。因此在心性修悟、游方参学之外,僧人必须协调好丛林内外的公共关系。公共交往需要有效的话语策略,包括主宾心态的关联、身份地位的暗示、古今境遇的比拟、彼此忌讳的遮蔽等。在这方面,禅林四六疏文以其特有的语词符码参与了僧俗各方关系的建构和互动。劝请、山门、诸山、江湖等疏用于恭贺住持上任,涉及对举荐者的颂扬、对寺院渊源的追溯、对法系门风的称赞等。其中,最具互动性的是对当事各方身份的暗示。
在晚宋丛林间,僧俗共选寺院住持的情况较为常见,所谓“制府力持公议,诸处有缺听诸山举人;同盟责在强宗,一士作兴如一佛出世”[10](900),各级官员的甄选、丛林寺院的推举、宗门法眷的支持,在禅门人事议题上都具有影响力。如“嘉定十年三月,妙胜虚席,制府下诸禅期集,师(普济)膺其选”[10](991),这是制阃主导的禅林公选活动。又如“天童虚席,朝命诸禅公举,以师(了惠)名奏,特差补处”[10](999),这是朝廷推动的丛林“公举”。再如“宝祐戊午,育王虚席,禅衲毅然陈乞。有司节斋尚书陈公嘉其公议,特与敷奏,是年四月(智愚)领寺事”[8](1063),这是以丛林“公议”为基础,主管官员顺势奏举的选任情况。另如“适通之光孝席虚,郡侯杜公霆徇乡缁白,请命师(元肇)瑞世”[10](1002),这是知州与地方僧众商议住持人选。世俗权力与丛林公议在寺院人事安排上相辅相成,此过程在善珍笔下有详细记载:
前守赵大监一日集诸禅主首曰:“法石坏于暗封久矣,欲革斯弊,非得江湖名衲子不可。”某等退而举三人,愚谷元智其一也。时愚谷谢事常之芙蓉,居灵隐为第一座,有声丛林间。守焚香,拈得之,且询其出处,喜甚,亟驰书招致。寺僧咸谓泉取浙二千里余,如费何?某谕之曰:“昔以暗封,今以公举,计道路费,视暗封不能十之一,何患焉?”愚谷至,众果悦服[11](466-467)。
泉州地方官赵氏向各禅寺首长征询法石寺的住持人选,善珍推荐了愚谷元智,因其担任灵隐首座时在丛林间享有声誉。赵氏最终选定元智,但却引起法石寺僧的非议,认为远调浙僧花费不小。善珍尽力说服异见寺僧。从中可见地方官、邻寺住持、本寺僧人在选择寺院首长时的互动过程。其中,僧俗之间的互动以掌故典实的形式在四六疏文中得到体现,如大观的《莹玉磵出世饶州光孝疏》:
如参寥受知于东坡,非许询难酬于支遁[9](231)。
在僧与士的交往中,彼此引用前代典范以自况,本是常见的交际策略。但如果回到前述人事选拔中僧俗互动的历史场景,我们可以挖掘出此种比拟在四六疏文中的独特意涵:丛林对世俗权力的足够认可。后者不仅是僧人获得住持身份的基础,更能加快其向上迁转的速度。如大川普济,“其岳林则丞相史忠献王钦其道价,延见而迁。大慈则忠献之子同知恭惠公敷奏给敕而迁。净慈则京尹赵大资敷奏起乳窦之隐而迁。灵隐则序迁也”[10](991)。在循资进秩的“序迁”之外,普济的晋升更多地依赖宰执、京尹的荐引。由此返观上述疏文中裴休、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故实,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其背后政权官宦的身影。
与上述“士+僧”对“士+僧”的句法稍显不同的是,五山禅林疏文在处理僧俗关系时还有另一种句式,即出句用“士+僧”,对句用“A僧+B僧”,这样将官员、住持、劝请者的身份都包含进来,使疏文更富交际性。如法舟所作劝请智愚之疏:
闾丘向前作礼,在丰干岂饶舌之人;黄梅勉为下山,代马祖说非心之偈[8](984)。
出句用唐台州太守闾丘胤寻访丰干、寒山、拾得之典,对句用大梅法常作偈婉拒盐官齐安禅师邀请之事,分别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卷七。其中,闾丘胤被用来比拟劝请智愚的世俗官员,“饶舌”的丰干代指丛林诸山的举荐者,寒山、拾得对应被荐者虚堂智愚。此句重在僧俗互动。据法云所作《行状》,“忠献史卫王秉钧轴,嘉禾天宁别浦以师名闻之,出世兴圣,实绍定二年也”[8](1063)。嘉兴天宁寺别浦禅师即劝请疏的作者别浦法舟,他将智愚举荐给史弥远,史氏与嘉兴地方官共同推动,使智愚得以出世住持兴盛寺,所谓“大丞相亲曾问我,贤邦君不妄予人”。可见,闾丘与秀州知州,丰干与别浦法舟,寒、拾与智愚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黄梅勉为下山”之黄梅应为大梅,借用齐安与大梅禅师之间的劝请关系,对应法舟与智愚的关联。此句的人物身份全为禅师,突出丛林内部的“公举”“公议”现象。疏文将古今境遇合理融合,在亦僧亦俗的人物典故中,将嘉兴兴盛寺住持选任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清晰呈现出来。同时,疏文撰者本身又是新住持的推荐人,作者隐含于字里行间,体现出四六文书充分的交际性。
与上文句法相似的还有善珍所作《崇福请虎穴疏》中的一联:“为闾丘远招大士,获偈空归;举首座堪住当山,下语不契。”[11](480)出句为“士请僧”模式,用上述闾丘典。对句为“僧举僧”模式,用九峰道虔禅师勘验首座之典,事见《禅林僧宝传》卷五:
诸殁时,虔作侍者。众请堂中第一座嗣诸住持,方议次,虔犯众曰:“未可,须明先师意旨乃可耳。”众曰:“先师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庙香炉’‘一条白炼’如何会?”第一座曰:“是明一色边事。”虔曰:“果不会先师意。”[12]
善珍用闾丘的“空归”与首座的“不堪”来反衬虎穴和尚荣膺新任的难能可贵,所谓“镇浮薄正须铁汉,俄姓名跃出金瓯”,其背后仍是僧俗各界参与寺院事务的复杂过程。总之,这种僧俗交融的语词序列能够有效表达晚宋禅林的人事关系。王铚《四六话》云:“四六须只当人可用,他处不可使,方为有工”[13],强调故实语典与当下人物身份境遇的妥帖对接。五山禅林四六虽不能实现一人一事完全对应的效果,但从疏文用典与对仗的精心布置中,我们已能察觉古今人物多重纽带的建构,它避免了交际应酬文字的空泛 俗套。
除了僧俗互动,丛林内部的推举商议也是住持上任的重要基础。在新僧上任后,“公举”“公议”的热情又会转化为交相恭贺的礼仪。如笑翁妙堪(1177—1248)的出处备受瞩目,“海内视其去留占丛林盛衰”[9](86);太虚德云新任住持后,“故巾峰之命下,则交相贺,意其速施为,化瓦砾为宝坊,一泚尸素相踵之颡”[10](968),丛林各界均期望他有所作为。兀庵普宁(1197—1276)有《跋弈东岘住常州横林净慈贺颂轴》,该颂轴是杭州净慈僧众对常州横林新任住持的恭贺,“引得西湖群英,扬清激浊,风波遍地”⑤。即便如“两序”中知藏职位的选定也会引起禅林各界的关注,“大川老子住净慈之三年,于五百众中命东嘉知无闻掌法藏。江湖之士美丛林之得人,大川之知人,说偈赞数,百喙并响”[9](185−186)。所谓“海内”“江湖之士”等名号足以说明禅林公共空间的成熟。在此背景下,江湖、诸山、山门诸疏在语词遣造上,也会注意禅门人事关系的隐喻。于是前述僧俗交互的句法就变为禅林内典的组合,如元肇所写:
记长年柏岩住,其志虽高;为九峰一疏来,则吾岂敢[14](607)。
上联用唐僧清塞赠柏岩禅师“多年柏岩住,不记柏岩名”[15]之诗句;下联则用著名的九峰鉴韶劝请大觉怀琏之事。这两句的主宾双方均为僧人身份,“住”与“来”流畅衔接,亦折射出禅林内部互动的热络。总之,上述三种句法:“士僧”相对、“士请僧”对“僧举僧”、“僧僧”相对,其背景都是南宋五山禅林“公举”制度的完善,以及由此带动的僧俗各界公共交往礼仪的成熟。禅林四六疏文通过故实的编排、古今人物关系的映射,以典雅方式参与了这种人际互动。当然,正如前述“拈山门疏”“拈江湖疏”等法语,新任住持在听完各方恭贺文章的宣读后,便会马上否定它。诸如“既曰相忘,却要这个作什么”“屋里有金,外头有秤。盐醎醋淡,斤两自定”等语无不显示出禅师斩断牵绊、返求自性的独立精神。受到世俗礼仪影响的禅门交际,如何在与世周旋的同时做到与世无涉,这事关祖训宗风的维系,也影响到禅林四六作为独立文体的生命力,将在下文有所涉及。
三、募施化缘与禅机启悟:疏文的观念传递
如果说上述疏文的撰写主要以人事为中心,那么禅林四六的另一种类型则围绕物事展开,涉及殿堂修造、日用品筹集、典籍刊刻等,旨在化缘募捐。在五山禅僧四六中,《修塔疏》《建殿疏》《造桥疏》《化香烛疏》《化笋疏》《化炭疏》《化刊语录疏》等占据了较大比重。这在呈现丛林日常生活细节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公共交往。劝缘募化的对象包括王公贵戚、宰执臣僚、京尹制帅、郡守县令、乡绅富商以及中土、高丽、日本禅林等,文书、财务往来的范围更广泛。在此过程中,四六疏文的书写策略便不仅仅停留在当事人地位身份的比拟,而重在愿景的描述、功德的颂扬、佛理的传布、禅机的揭示。出于互动的需要,儒释道各家理念以常识化的形式被融入四六辞章之中,杜甫、苏轼、黄庭坚等著名作家的语句与禅门公案、话头交错杂陈,形成活泼俊朗的四六文风。同时,作者随机设教、超越差别、追求圆融的立场又使四六疏文体现出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五山十刹制度在使禅林选拔制度官制化的同时,也扩大了各寺院的僧众数量和经办规模,使其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在南宋后期得到极大改善。众所周知,五山时代是宋代禅宗文献集大成的时期,《五灯会元》的编纂,《古尊宿语录》的重刻,《枯崖漫录》《人天宝鉴》等笔记的成书等,都显示出宗门文献整理的丰富成果。与此同时,塔殿、寮庵、道路、接待地的营造也达到新的水平,寺院对钱财物资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筹款募资之举在五山住持间极为普遍:
钟阜去东阳六十里,玉山实介其间,由润而升,禅锡经从,曾无驻足放包之地。师诛茆结庐,凿石开径,倒囊钵所有,不足以给土木之费。京湖制帅无庵孟公、秋壑贾公闻而为之助,京尹节斋赵公继捐金粟,以相其成⑥。
师乃葺乃理,不徐不亟。移书荆湖制使孟侯,得钱百万,不数年,内外更张几五之四[9](84)。
荆湖制帅孟侯珙,蜀之思、播二郡与夫海外日本,皆遣使委施[9](94)。
当嘉熙庚子之饥,锐欲创接待,遣其徒可仍相攸西溪闲林间,得坞焉,地主因以施,遂倾衣盂办集之[10](988)。
上述募施行为分别发生在道冲、妙堪、师范、法熏等住持径山、灵隐、育王等寺期间。募施对象包括制帅、京尹、乡间地主等,募集区域遍及两浙、京湖、西蜀、日本等地。从修造内容看,它们既有寺院内部设施,又有山林之外的道路、接待所等。频繁的募施行动为疏文写作提供了丰富空间。大观在为法熏所作《行状》中云:“见他处持疏鹭候俟人门,呫嗫纵臾,以希施予者,直鄙而笑之”[10](988),虽不无厚此薄彼之意,但“持疏鹭候”着实反映出募施疏文的盛行。在此背景下,化缘募施既是财物的交换,又是机智的较量和才华的展示,这从劝化诗偈可见一斑:
(西岩了惠)当东嘉能仁劝化僧堂之役,有偈云:“尊者从空与么来,神通用尽却成呆。看来不似维摩老,一默千门万户开。”寓公节斋陈文昌一见赏音,亦以妙语助化云:“南赡部洲一尊者,一云一雨遍天下。今朝为众入城来,霡霂相随散春野。有田无雨田不收,有僧无堂僧不留。众僧既堂田既雨,盖覆东南三百州。”由是施者响答而速成焉[10](1000)。
了惠反用维摩显神通之典巧妙表达求助募捐之意。陈文昌受到了惠启发,化用《法华经·药草喻品》之喻,将雨水润田与僧人建堂结合起来,使意思翻进一层。了惠的文才与陈氏的帮助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由此可见文词与智慧在化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除诗偈外,文辞精妙的四六榜文也有助于寺院财务的筹集,如济颠禅师所为:
长老看了大喜,交侍者,把榜挂在山门,往来看者如蚁。越数日,济公曰:“我已化了,明日艺主至。”次早,果见朝廷差太尉押到宝钞三万贯,言:“夜梦金身罗汉募缘,故朕完成胜事。”长老众僧谢恩讫,库司收了三万贯钞,斋了太尉,送出山门,择日兴工,诸府州县官员、财主无不布施。未二年间,殿宇房廊屋舍皆已落成⑦。
皇帝夜梦募缘之事不无神异之处,但“挂在山门,往来看者如蚁”无疑是四六榜文迅速传播的重要条件。酒后“挥笔立就,文不加点”体现出济公的才思,其才华最终促成皇帝、州县官员、财主的慷慨捐助,使寺院的修造工程顺利完成。诗偈、榜文如此,疏文犹然,它考验撰写者对佛禅观念的巧妙传达。
劝化疏文以物品为出发点,寓禅机于物象、将物事引向人事,是获取“施者响答”效果的前提。在五山禅林四六中,钟楼、浴堂、锅灶、柴荡、菜蔬、席帐等无不唤起人之自性,昭示解脱之径。在农禅时代,行住坐卧、运水搬柴都蕴含悟道的契机。到了文字禅高度发达的南宋后期,四六疏文通过语言符码的编排将更丰富的日常物象纳入启悟和书写的范围,将众多实践真知向更广阔的人群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劝缘募施又是一个禅理的普及化过程。居简《蕲州东禅干钟楼疏》云:“客愁千绪,断魂白叟洪撞;何许一声,开眼黄粱未熟。”[16]395高楼钟声牵动客愁,但更惊醒红尘迷梦,使人洞彻世事空幻。道璨《西湖相岩寺化僧寮疏》曰:“散黄金错落,开碧户玲珑。收天地于六窗,自张白眼;倚阑干之一曲,闲看青山。”[9]234僧人的闲澹在于六根清净,祛除物欲的遮蔽,以求透彻圆通。大观《行堂岁修化香烛疏》云:“俯仰折旋,直下顿明自己;香花灯烛,莫非助发本光。”[10](889)“俯仰折旋”语出汉徐干《中论·务本》“体骛乎俯仰折旋之容”,此处用以形容香烟烛焰飘移摇曳的形态。香花灯烛是献给佛的供品,但成佛不假外求,只在自性的清净与内心的启悟。正如龙潭灭烛、德山悟道的著名公案一样,大观正是要用香烛来指示禅机,所谓“用世语言,入佛知见”。
僧人募施的对象主要为方外世界,疏簿的传送是禅林公共交往的一个环节,和前述禅林“公举”礼仪一样,各类劝化疏文也注重处理僧俗关系。它善于将经史名言、诗词警句、著名公案等杂糅在一起,注重儒禅思想的融会贯通。谢伋《四六谈麈》云:“四六全在编类古语”[17],和通常制诰表笺不同的是,禅门化疏不追求深厚尔雅,其编类的对象都是常识化、易于传诵的语典。例如大观代大川所作《净慈建正徧知阁疏》,“孰不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试更看南山起云,北山下雨”[10](892),上句语出《小雅·何人斯》,用兄弟和睦之意表征偃溪与大川先后住持净慈、主持修造之意。下句为云门文偃示众之语,此处借指灵隐(北山)大川与净慈(南山)偃溪的相互呼应。两句都运用了内外典中的常见语汇,向施主传达出寺院工程的延续性。类似的联句还有:
舞雩声里,咏归三月和风;无垢人前,着得一杓恶水[16](368)。
施祇地,拓金园,陋贤于之插草;拽南辰,安北斗,笑愚叟之移山[10](862)
举事直须中的,闻弦必遇赏音[10](899)。
细味扬子《太玄》,更透赵州公案[10](902)。
透顶揭翻,全仗东风齐着力;从头盖覆,大庇寒士俱欢颜[14](600)。
和前述劝请疏、开堂疏身份比拟的句法稍显不同,这些联句一俗一僧,两端都指向同一意义。如洗浴:儒家“浴乎沂”与佛门“无垢”;修建:俗界之愚公移山与禅林之贤于插草;造屋:儒者之庇士与禅门之助力;参学:儒家之《太玄》与丛林之公案;领悟:方外之“知音”与方内之“中的”。上下两句实为一体之两面,相互发明。
如果考虑到劝缘募财中的僧俗交往以及寺院建设过程中的儒禅合作,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对仗句法的现实意义;但若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意涵,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力图昭示一种亦俗亦真、不分彼此的圆融境界。习禅者藉助外力光大丛林,在家者通过捐助与佛结缘,两者都能体验随处为主的自在,感受转凡成圣的透彻,最终臻于解脱之境。于是在劝化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表达:
京都富贵,具十华藏海庄严;真俗混融,瞻普光明殿殊特[10](880)。
东海西西海南,补怛化城水澄天碧;是法住住法位,阖闾故国剑老池深。圆通何彼此之分,岧嶤出云雨之上[10](917)。
万里浮海于东,幸有化人之国;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之居。佛法不隔丝毫,境界何分彼此[9](240−241)。
无论是萃集荣华富贵的都城、文化厚重的吴都故地还是路途遥远的海东,只要诚心施为,便无处不是梵刹;只要返归自性,便无人不修得圆通。禅悟超越僧俗,佛法不分彼此,这正是四六疏文承载的最高境界。道璨云“圣凡如海,纳百川于涓滴之中”[9](233),上述诸联一禅一儒、即真即俗的对仗句式,正如浴堂的包容圣凡、海纳百川。
上面以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为依托,以四六疏文用典、对仗、言理为解读重心,在两者的互阐互释中把握南宋禅林日用文书的深层意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宋代禅僧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使宗门文献的整理、诗词创作、四六书写同步繁荣,到南宋后期,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开始发挥影响。以四六疏榜为代表的南宋五山文学改变了长期以来僧人创作依附士大夫文学的局面,以流畅明快为语言风格、以公共交往为基本特征的禅林四六在明清和东亚佛教文化圈内亦具有典范意义。
第二,五山文学僧的四六写作成果,推动了南宋后期“士大夫周边”文学的繁荣,标志着精英文化向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普及。四六写作号称“敏博之学”,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对典章制度、历史文献、经典文本的熟悉。南宋后期,幕僚、馆客、乡绅、胥吏、游士等纷纷加入四六文书的写作队伍,加速了文化下移趋势。承担禅林日用文书撰写的五山禅僧,与这些社会群体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文坛的重组。
第三,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提高了禅林的公共化程度,包括寺院之间的群体交往,禅林与世俗政权、地方社会的交往,以及中土与日本、高丽禅林的交往。公共交往礼仪的逐渐细密,为禅林四六文书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空间,影响了其表达策略、辞章结构与话语形态。同时,文书的撰制、传递与宣读,又充实了人际交往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引领和重塑了群体 风气。
第四,从文体演变看,五山禅林疏文的交际性与应用性,丰富了宋体四六的交往功能,巩固了它在中国骈文史上的特殊价值。明清骈文批评中有所谓“六朝体”与“宋体”之辨,后者往往因为审美属性的减弱而招致偏离“正体”的评价。但伴随审美属性弱化的恰好是公共交往功能的提升。事实上,宋体的制诰、表笺、启札最终成为明清公文写作的基本范式,官员除授、岁时通候、吉凶庆吊等场合的四六应用也成为近世社会的普遍礼仪。与此相呼应的是,南宋禅林的劝请疏、开堂疏、劝缘疏、茶汤榜、“小佛事”等四六文体的分类逐渐繁密。由此视之,禅林四六的交往功能为我们重新评价宋体四六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五,从文体特性看,四六疏文垂示机缘、接引信众的隐含意图使其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无论文章体制还是应用方式,禅林疏文都受到世俗四六文书和交际礼仪的影响,如何保持其宗教文体的独特性是每一位撰写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禅宗的生命活力在于反体制、破拘执、无依傍、重自性,如何“用世语言,入佛知见”,如何“与世同波,与世无涉”,时刻考验作者的智慧。在这方面,五山僧人留下了不少精妙的回答,在超越圣凡区隔、趋向圆融境界方面为四六文保持了禅性。
注释:
① 关于南宋“五山文学”的概念,参见朱刚,陈珏《宋代禅僧诗辑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汝娟《南宋五山文学研究》,复旦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本文思路受此启发,特此鸣谢。
② 《虚舟普度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71册,第90页。
③ 《元叟行端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71册,第544−546页。
④ 《笑隐大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69册,第719页。
⑤ 《兀庵普宁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71册,第19页。
⑥ 《痴绝道冲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70册,第75页。
⑦ 《济颠道济禅师语录》,《卍新纂续藏》第69册,第612页。
[1] 王汝娟. 南宋禅四六论略[C]// 王水照, 侯体健. 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 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380−398.
[2] 黄启江. 南宋禅文学的历史意义[C]// 王宝平.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3] 石观海, 孙旸. 疏文的接受美学: 再论中国文学东传的中介“日本临济僧”[J]. 长江学术, 2007(4): 61−73.
[4] 无著道忠. 禅林象器笺[M].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一辑子部四.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771.
[5] 释晓莹. 罗湖野录[M]. 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一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232−233.
[6] 释惠洪. 石门洪觉范林间录[M]. 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8.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07.
[7] 释道融. 丛林盛事[M]. 全宋笔记第七编第一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6.
[8] 释妙源, 等. 虚堂和尚语录[M]. 大正新修大藏经47. 台北: 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9] 释道璨. 无文印[M].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8.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10] 释大观. 物初剩语[M]. 珍本宋集五种: 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 释善珍. 藏叟摘稿[M].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52.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12] 释惠洪. 禅林僧宝传[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52.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63.
[13] 王铚. 四六话[M]. 历代文话第一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
[14] 释元肇. 淮海外集[M]. 黄启江点校.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13: 607.
[15] 计有功. 唐诗纪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102.
[16] 释居简. 北磵集[M].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51.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2.
[17] 谢伋. 四六谈麈[M]. 历代文话第一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35.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wu shan zen buddhis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writing of four and six proses: With Shu as the center for study
DAI 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China)
The four and six Shu proses of Wu Shan Zen buddhis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inly consist of persuasion, mountain gate, mountains, lake and river, and alms, the writers of which mainly belonged to the doctrine of Da Hui Zong Gao and mainly functioned as public communication. First, the composition of Song's Shu proses had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hu composed by men of letters to that by Buddhists and the appearance of Wu Shan Buddhists as the independent group of composition happen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 Song Dynasty. The Shu represented itself as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the increase in the occasion on which Shu was used and the richness of writing styles. Second, the system of leader selection of Wu Shan's Zen temple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mples and political power, leading to the maturity amd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act of express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Four and Six Shu. Third,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 of Wu Shan Zen Buddhism provided wide space for the Shu which functioned as alms, for the writers used four and six proses to set up theory of Zen casually and opened the gate to the Zen intelligenc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keep the character of Zen literatur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u shan zen buddhists; public communication; shu of four andsix proses; the selection of temple leaders
[编辑: 何彩章]
I207.99
A
1672-3104(2017)03−0164−07
2016−12−08;
2017−02−1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 批面上资助项目“南宋后期四六文与骈体文章学研究”(2016M590308)
戴路(1986−),男,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