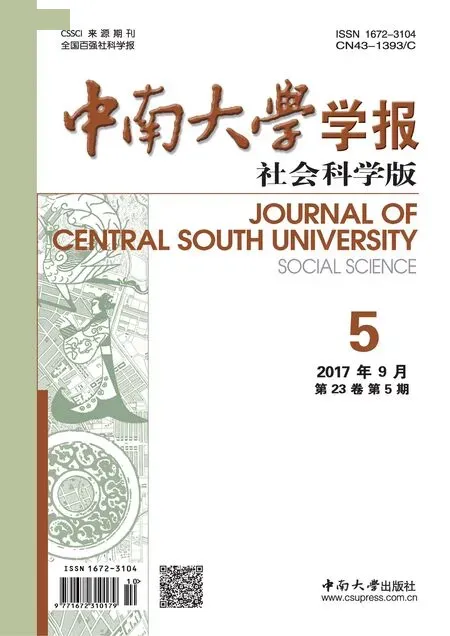论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
2017-01-12刘光斌
刘光斌
论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
刘光斌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指出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法律和道德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提出了重新探讨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现实依据。他从法哲学视角指出自然法主张法律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实证法坚持法律与道德的中立关系,两者都片面理解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他从商谈理论视角指出法律从功能上补充了道德的不足,道德为法律合法性提供了理由,明确指出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互补关系。哈贝马斯为我们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商谈论证思路。
哈贝马斯;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商谈理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道德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一个令人备感困扰的问题。许多思想家,诸如韦伯、福勒、哈特、凯尔森、德沃金、庞德、波斯纳、卢曼等人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做出了各种解释,然而很难说就已经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更多地只是为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某种思路。哈贝马斯就是其中的一位思路贡献者。尽管国内已有学者探讨了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但结合哈贝马斯的社会学、法哲学相关观点和商谈理论进行论证的相关成果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化。哈贝马斯注意到社会进化导致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他既不同意自然法传统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视道德为法律基础的观点,也不同意实证法传统在法律合法性问题上所持的道德中立立场,而是采用商谈理论论证“法和道德的互补关系”[1](136),主张法律缓解了道德重负,道德为法律合法性提供了论证理由。
一、社会学视角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关系
哈贝马斯主张生活世界和系统是社会的双重结构,社会合理化依据这双重结构而呈现出两大发展方向,这一双层社会解释构架为哈贝马斯开辟了一条从社会学角度探索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路径。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社会是生活世界,它主要以语言为媒介而达成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为特征,包含文化、社会和个人三种结构成分。文化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世界观;科学、技术、自律的艺术、法律以及道德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个人层面表现为个人的社会化和自我认同的形成。从观察者角度看,社会也是系统,哈贝马斯以系统理论补充生活世界的视角,他着重关注经济和政治系统,分别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以工具理性导控下的工具理性行为为特征。这一社会双重结构理论既解释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及其社会整合功能,又解释了系统适应复杂社会的需要以及系统整合功能。就本文的旨趣而言,它需要解释清楚社会双重结构的区分与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有何联系。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演化图景描绘了社会双重结构的形成,揭示了法律和道德的合与分关系,他认为社会最初以生活世界形式出现,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分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导致传统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并促成社会双重结构的出现,这对后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重构提出了理论要求。
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最初以生活世界的形态出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导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区分。生活世界存在一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其背后的逻辑受制于社会的理性化学习的符号再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在生活世界内的交往行为再生产了生活世界,完善了三种生活世界的功能:“使用并更新文化传统、认同于社会团体并强化社会整合、内化团体的价值取向并获得行动能力,此种再生产过程使得新的情境与生活世界的现存情况相联结。”[2]生活世界的再生产适应了社会新的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推动了生活世界的不断合理化并促成世界观合理化、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以及个人的日益个体化的不断分化。在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过程中,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承受了重负。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在社会演化中的优先性,指出生活世界合理化到一定阶段,即传统法律和道德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时候,便推动了社会向系统结构模式的方向性变化,即经济和政治子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社会形成了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元结构。
哈贝马斯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两者是同源共生的关系,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传统法律和道德从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具有自主的逻辑。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吸收了韦伯合理化理论中的祛魅思想,“韦伯力图把道德从法律中分离出来,提出一种独立于道德的法律概 念。”[3](931)具体来说,随着宗教伦理的世俗化,“道德律令再也无法从上帝的超验角度出发公开作出论证了”[4],而法律威信也不再需要一个神圣的权威,于是法律和道德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当生活世界得到充分合理化,发展到后俗成阶段的时候,道德变成了具体的、主体道德实践关怀的私人事务,而法律则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成了全社会的规范准则。在道德与法律关系逐渐分离的过程中,系统出场了,其中法律发挥了关键作用,即法律使权力和货币的导控功能取得制度形式,经济和政治子系统独立于生活世界,具有自主性逻辑,“系统只有将它们各自的媒介法律化,从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结起来,才能独立于生活世界而自行运作”[5](30)。换句话说,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必须借助法律才能制度化。私法使经济系统得以独立出来,使交易关系在财产法和合同关系中得到规定,公法使政治系统独立发挥功能,科层制的官方机构取得法律形式并得以制度化。
在上述哈贝马斯关于社会演化的图景中,生活世界合理化在社会演化中具有优先性,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共存于生活世界之中,是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以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为条件,是生活世界充分合理化的结果。在这一社会演化图景中,道德与生活世界保持着联系,法律显示出独特地位。法律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又回归生活世界,经济和政治子系统必须取得法律形式才能实现制度化,其实就是法律规范给经济和政治划定了界限。如此一来,“通过那要求公民共同运用其交往自由的自决实践,法律归根到底从社会团结的源泉中获得其社会整合力量。另一方面,私法和公法的建制使得市场和国家权力组织的建立成为可能”[1](48)。由于法律与三种社会整合资源的关系,因此不得不面临来自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重影响,所以他指出:“现代法律仍然是一个两重性极强的社会整合媒介。”[1](49)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法律一方面必须自身获得合法性,保持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必须成为系统取得合法性的媒介,他认为即使经济系统和国家机器的系统整合也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与公民自觉实践的社会整合保持连接。面对双重影响,法律如何才能保持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巴尔指出:“在任何法律理论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问题。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就涉及这种关系。”[5](109)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哈贝马斯为了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重构法律体系,重新解释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传统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同源地存在于生活世界中,法律合法性不成问题,法律和道德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去之后,必须重新考察法律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在后传统社会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或道德与法律无关?在这方面,自然法与实证法在法律与道德关系上的立场给他带来诸多启示。
二、自然法与实证法在法律与道德关系上的立场
实证主义法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哈特等人坚持法律合法性的道德中立立场。奥斯丁强调人们实际制定的,并在现实生活中对人们产生实际影响,得到证实的法律。这种实证法以政治权威对人们施加的威慑和惩罚的命令形式迫使人们服从法律规范,“将法律体系界定为由一个立法者直接或间接颁布的所有规范的集合”[6](144)。奥斯丁坚持认为有一个叫“主权者”的立法者,是该体系所有法律的终极渊源,他明显地忽视了公民自主的影响,排除了法律合法性的道德规范性条件,甚至提出“恶法亦法”的观点。这种法律合法性的观点影响到了凯尔森。凯尔森指出:“只要讲到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冲突时,严密的考查就表明,这并不真正是指两个程序同时有效力。”[7](447)在他看来,法律与道德是相矛盾的,在考察法律合法性时,必须排除道德规范,他说:“一个规范体系只有在所有其他具有同样效力范围的规范体系已被排除后,才能是有效力的。”[7](448)凯尔森主张存在一个叫基本规则的规范,它是该法律体系所有法律的渊源,认为在一个封闭性的、自洽的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合法性完全可以从自身的合法律形式中获得合符逻辑的论证。哈贝马斯则指出:“凯尔森将整个主观权利确定为受客观法保护的利益和有客观法保障的选择自由。”[1](108)在一个完全自洽的法律系统中,法律主体只能是法律人而非道德人,由于在该法律系统中,法律赋予主观权利,必然造成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间的内在矛盾,法律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合法律性。哈特无疑注意到了法律规范的有效性不能仅仅停留于命令式的惩罚威慑,或其自身的外在形式、逻辑上的论证形式,还必须考虑人们对法律的可接受性,因此他提出“承认规则”并以此作为判断法律规范的标准。他意识到不承认法律规范内容包含的道德属性,就较难说明人们服从法律规范的理由,“不能否认法律之稳定性部分地有赖于与道德的一致性”[8](199)。但哈特并不认为两者就存在必然联系:“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真理。”[8](182)哈贝马斯指出在凯尔森和哈特那里,“一种‘基本规则’或者‘承认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毫不含糊地确定哪些规则在一个特定时期属于有效的法律”[1](249),然而基本规则和承认的规则本身却无法做合理论证,因此“把法律的有效性同它的起源绑在一起,合理性问题就只能做一种不对称的解决。理性或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被置于历史之下了”[1](250)。在哈贝马斯看来,实证法在法律合法性问题上持道德中立立场,虽然他本人也“拒绝法律的合法性完全由道德理论确立的观点”[9],但不认同实证法完全中立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合法性的根据在于道德,认为在法的效力与道德正当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自然法的初衷与目的都是维护个人的主观权利,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生活方式。“按照古典的自然法,道德的和法律的行为规范,从内容上讲以公民的良好的——也就是说,富有道德内涵的——生活为依据;近代的成文法则制定了物质生活秩序(无论是城市的物质生活秩序,还是等级的物质生活秩序)的各类义务。”[10]哈贝马斯指出自然法强调法律主体的道德自主,成文法为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提供了保障。阿列克西谈到自然法与道德的关系,他说:“在法的效力(或法的正确性)与道德正确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11]自然法传统主张人们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个人主观权利,个人主观权利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基于法律之外的道德权利。法律不过是为了保障私人自主或私人主观权利,防止遭到多数人的暴政。霍布斯之后,作为法律原型的资产阶级私法原则,以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为基础,法律保障主观行动自由免于受到侵犯。在康德那里,私法要从自身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在道德自主性中找到依据,他采用法权原则解释法的合法性,这仍然属于自然法传统。然而自然法成为成文法,导致法律合法性与道德的退缩,在哈贝马斯看来,成文法使公民在道德中立领域内采取相应行为,这些行为脱离了道德理由,也就是说内心意识到的义务不是他们行动的理由,公民仍然受制于外部施加的影响。成文法赋予国家强制力的合法性,所有强制力的合法运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再由拥有权利的个人直接行使,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自然法过渡到实证法,对法律合法性的思考也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过渡的过程中,法律有效性的两个成分,即自由与强制之间的矛盾关系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们自由,另一方面,法律效力必须采取强制的方式。于是,法律的有效性涉及了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根据其平均被遵守情况来衡量的社会有效性,另一方面是对于要求它得到规范性接受的那种主张的合法性。”[1](37)在这种情况下,同一法律共同体成员面对同一条法律时将可能采取两种态度,或者是违反规则带来的可计算后果,或者是规范性行为期待的义务论上的约束性。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得到保障,即行为的合法律性和规则本身的合法性应该同时得到满足。自然法和实证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反映在法律合法性问题上表现为双方各执一端。自然法传统认为法律的合法性体现在法律维护个人权利之中,着眼于人的自由,法律的合法性以道德为基础,侧重于法律规则本身的合法性;实证法主张法律的合法性就是合法律性,着眼于国家的强制力,陷于法律合法性来自合法律性的论证悖论中。哈贝马斯注意到自然法没有正视传统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关系,过于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基础地位,实证法虽然看到了传统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关系,但割裂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哈贝马斯一方面不同意自然法主张把法律合法性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立场,另一方面也不同意实证法坚持的道德中立立场,他认为生活世界合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但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毫无关系,“现代法并没有理性化为彻底的功能实体,而是需要根据涉及规范正确性的实践商谈获得道德的正当理由”[12]。法律促使经济和政治子系统从生活世界分离出来,法律有脱离生活世界规范的趋势,道德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但其自身仍然属于生活世界领域,需要获得道德的规范理由。自然法和实证法片面理解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无法合理解释法的合法性问题,这促使哈贝马斯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三、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关系及商谈理论的论证
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法和道德的互补关系”[1](136)。他认为:“在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层次上,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是同时从传统的伦理生活分化出来的,是作为两个虽然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类型的行动规范而并列地出现的。”[1](129)在他看来,传统法律和道德之间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都是从伦理生活中分化出来的,分化后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视为一种不同且相互补充的关系。
一方面,哈贝马斯注意到法律和道德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则。哈贝马斯指出:“一般的行为规范一分为二,成为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1](131)传统法律与道德关系发生分离,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并列的规则。第二,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不同。道德没有时空限制,具有普遍性,法律总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即一定的法律共同体内发挥作用。第三,道德与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道德是普遍的规则,适用于所有人,带有义务论色彩,法律维护正义寻求利益之间的平衡,带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第四,道德与法律所属系统不同。道德是知识系统,道德合法性需要进行论证,法律既是知识系统又是行动系统,法律不仅需要得到合理论证而且需要事实上得到人们的遵守。第五,社会整合的功能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和政治系统利用法律媒介从生活世界分化出来,法律作为一种组织复杂社会结构的机制,具有一种类似于经济和政治系统结构的地位,这使得那些依据法律行动的人们可以依据法律行为而预测到相关者的行为。在现代社会,道德成了个人生活选择的事情,道德规范发挥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依据生活世界而进行社会整合。相比较于道德,法律更多地发挥系统整合的功能。依据上述区别,哈贝马斯认为后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同的两种规范。
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和法律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他分别从道德需要法律功能补充和法律需要道德论证理由两个方面进行商谈理论论证,前者表明在复杂社会中,仅仅依赖道德整合人们行为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方面的作用,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德法并举,相得益彰;后者表明法律的合法性需要获得道德理由的支持,法律行为不能无视道德规范,这类似于法理和情理兼容。
第一,道德需要法律提供功能补充。哈贝马斯指出:“我想从道德和法之间的那种在社会学上得到澄清的互补关系出发,来加以理解:法律形式的构成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弥补随着传统的伦理生活的崩溃而出现的缺陷。”[1](138)他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法律可以弥补道德功能上不足而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道德功能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自我决定的问题。人们依靠道德进行判断并采取行动面临认知、动机等方面的压力,比如理性道德提供了一个程序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评判,却无法标出规范的等级次序或提供一个义务目录,需要道德主体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对情境的把握尽可能选择、诠释和运用合适的规范,这在解决行动冲突问题上给道德主体带来了负担,他面临着自我决定的压力。第二,意志强弱问题。道德主体在解决冲突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依据道德理由、原则等而行动,把义务和道德责任结合起来,这就关涉意志力的强弱,要避免受到情感不肯定性以及一些事实性利益的影响,道德主体必须要有强的意志才能把道德责任和义务结合起来。第三,可期待问题。考察规范有效性时,仅仅从规范意义上获得可期待性是不够的,有效的规范要代表可期待的东西,必须能够在事实上针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而强制实施。哈贝马斯指出自我决定问题、意志强弱问题和可期待问题标志着后俗成道德的限度,这种限度恰恰可以通过法律来补充。发挥法律调节社会的功能能够缓解社会道德压力,利用现代法律来调节人们之间的行动,可以避免事事都要进行规范论证,法律以制度的方式确保人们采取行动,免除了行动者在行为判断上的道德负担,行为期待上的困惑。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道德已经无法成为法律的基础,难以形成道德优先于法律的等级秩序。他指出:“道德不再像理性法理论所设想的那样作为一套超实证规范悬在法律之上,它进入了实证法之中,但并没有与之重合。”[1](585)虽然道德不再处于法律的基础地位,但也不像实证法主张的那样,道德与法律完全无关。
第二,法律需要道德论证理由。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在宗教权威瓦解的情况下,法律要重新获得合法性论证,道德是其不得不考虑的理由之一。现代法律调控的事务不仅涉及道德问题,而且涉及经验的、实用的和伦理问题以及诉诸谈判实现妥协的问题等,因此法律合法性论证就不仅需要道德理由,而且需要伦理政治的理由。在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情况下,哈贝马斯不同于实证法立场,他并不放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借助于法律有效性当中的合法性成分,实证法仍然保留着同道德的关联”[1](130)。不过道德不再作为法律基础出现,而是作为法律合法性的理由之一以符合民主原则的程序要求进入法律合法性的论证之中。哈贝马斯指出:“不仅与法律相互补充、而且也在法律扎下根子的道德,当然具有纯粹的程序性质;它已经摆脱了全部特定的规范内容,而升华为可能的道德规范内容之论证和运用的一种程序。”[1](585)。借助于法律合法性的论证程序,道德成为法律合法性的理由。在宗教权威瓦解的情况下,哈贝马斯认为所有规范的合法性都必须通过商谈原则的检验,商谈原则要求“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 范”[1](132)。商谈原则应用于道德领域形成道德原则并充当决定道德问题的论辩规则,意在论证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形成民主原则确定合法的立法过程的程序正当性。哈贝马斯指出:“道德原则是延伸到全部只有借助于道德理由才能获得辩护的行动规范的,而民主原则只适用于法律规范。”[1](136)从这个观点看,道德理由可以成为法律规范论证理由,只不过法律的合法性论证理由还包括实用的、伦理−政治的理由。“民主原则产生于对于这样一些行动规范的相应的具体化,这些规范以法律形式出现、并且有可能借助于实用的、伦理−政治的和道德的理由——而不仅仅从道德的理由出发——而进行辩护。”[1](133)民主原则确保实用的、伦理−政治的和道德的理由通过一定的程序进入到论辩之中,并就论辩最后达成的共识以法律建制化的方式确定下来,法律合法性是不能忽视道德理由的,要求“运用实证法手段,以便分担举证责任、把可以受到道德论辩影响的论证过程建制化”[1](584−585)。如果说道德原则使商谈原则内在化,那么民主原则使商谈原则实现了建制化。法律合法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民主原则确立了一种程序,使法律的承受者同时也是那些法律的制定者,这样法律规则本身是合法的,人们的行为也会符合法律的要求。
四、对哈贝马斯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的几点评论
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主张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为理解法律与道德关系提出了一种商谈论证思路,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采用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探讨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现实依据。哈贝马斯把法律与道德关系置于社会进化中来考察,认为传统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同属于生活世界,是一种同源共生关系,随着社会进化,法律和道德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分离关系,法律规范不再是衍生的道德规范,却也无法摆脱道德规范的影响,即也不可能是道德中立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律秩序对自主化了的道德是一种同源的补充这种观点,是有经验依据的”[1](131),所谓经验依据就是社会学分析的现实依据,法律与道德虽然分离了,但在社会功能上相互补充。
第二,反思了法哲学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哈贝马斯主要反思了自然法和实证法这两种法哲学传统。自然法和实证法都比较关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分歧在于法律与道德之间有没有存在一种必然关系。自然法强调所有法律都具有价值,“按照一些自然法理论,法律之所以是规范,是因为它们在道德上有效”[6](184)。主张实证法的理论家不接受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法律的有效性与道德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采取道德中立立场。哈贝马斯认为道德不可能成为法律的基础,同样,道德与法律无关同样也不可能,法律秩序的功能,它的效率,要求法律获得经验上的合法性,它的可接受性又反过来要求法律与当时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和观念之间的某些本质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法律的合法性需要道德理由。
第三,提供了论证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商谈思路。哈贝马斯对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关系做了一种程序性的商谈论证。哈贝马斯不认可道德理由的优先性,“法律的存在不能再依赖于道德传统的当然权威,而需要独立的论证”[13],但认为道德理由可以进入法律的论证之中,与其他理由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依靠内在于法律规则之中的民主程序论证了法律合法性,“哈贝马斯的方案是一种程序合理性观念”[3](932)。这种程序性的商谈论证思路带有明显的调和自然法和实证法的特点。一方面,哈贝马斯接受了实证法的观点,否定道德成为法律的基础,另一方面,他接受自然法的观点,主张法律与道德之间存在关联。然而他关于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的论断又使他既不同于实证法的立场也不同于自然法的立场,我们认为哈贝马斯借助于程序性的商谈论证调和了自然法和实证法的方案,“自主的道德和依赖于论证的实定法,毋宁说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之中”[1](130)。
当然,哈贝马斯的商谈论证思路也遭遇一些批评,暴露了其理论限度。首先,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容易形成双重法律观,带来理解上的模糊性。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的法律存在于生活世界中,以制度的形式体现了其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规范,需要从道德角度加以正当化;另一方面,认为法律是一种媒介,作为媒介的法律以正式的一般规则控制着国家和经济系统,为国家和经济系统提供合法依据,媒介之法是脱离道德关怀的系统。哈贝马斯并没有阐释清楚作为制度之法与作为媒介之法之间的关系,而且“哈贝马斯虽然认为它至关重要但有些语焉未详,模糊不清”[5](38−39),甚至“有人批评他对法律作为实现社会融合的媒介信心过大”[14]。其次,商谈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商谈理论重视民主立法过程,主要彰显了理论价值,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对民主发展程度有限、商谈政治基础单薄的国家而言,让人们成为法律的创制者,无论从专业知识还是从重叠共识来看都是不易实现的。”[15]伯恩哈德·彼得斯认为哈贝马斯强调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一致,“这种主张狭隘地将重点放在程序性要求,其代价是牺牲了对于某些权利和原则的实体性诉求”[5](42)。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倾向于主张哈贝马斯更多地是为解决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商谈论证思路。道德和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习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主张法治与德治并举,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此种背景下,我们了解哈贝马斯的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也是不无裨益的。
[1] 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童世骏,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 阮新邦. 解读《沟通行动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21.
[3] Klaus Eder, Critique of Habermas’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law[J]. Law & Society Review, 1988, 22(5): 931−944.
[4] 尤尔根·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7.
[5] 马修·德夫林. 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M]. 高鸿钧,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6] 拉兹. 实践理性与规范[M]. 朱学平,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7]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沈宗灵,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8] 哈特. 法律的概念[M]. 张文显, 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9] Baxter, Hugh. Habermas: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7.
[10] 尤尔根·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M]. 郭官义, 李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4.
[11] 罗伯特·阿列克西. 法与道德: 告别演讲[J]. 雷磊, 译.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5): 5−12.
[12] Deflem, Mathieu. law i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niversitas, 2008: 277.
[13] David, Ingram. Dworkin, Habennas, and the CLS movement on moral criticism in law[J].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1990(4): 237−268.
[14] 瓦克斯. 法哲学: 价值与事实[M]. 谭宇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89.
[15] 刘光斌. 论哈贝马斯对法律与政治权力关系的理论批判与建构[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 270−275.
[编辑: 谭晓萍]
On Habermas’ theory of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LIU Guangbi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Haberma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pointing out from the view of sociology that, with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real world from which law and morality deri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 He argu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law that law is based on the morality, that empirical law in a neutral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and that both views misunderstood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He started from discourse theory, and pointed out that law made up for the defects of morality in its functions and that morality provided legitimacy for law, thus clarifying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Habermas's theory of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enriches the resources of legal philosophy.
Habermas; law and morality;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discourse theory
B82-051
A
1672-3104(2017)05−0001−06
2017−06−09;
2017−07−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哈贝马斯的政治权力与法律互动关系研究”(15BKS076)
刘光斌(1978−),男,湖南洞口人,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