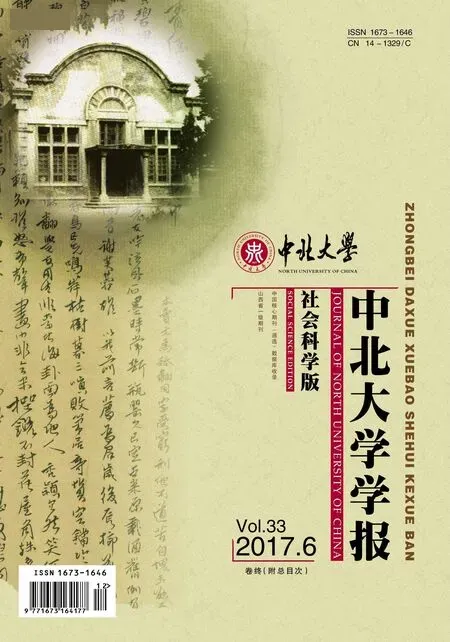《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解辖域化研究*
2017-01-12孙晔
孙 晔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08)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解辖域化研究*
孙 晔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08)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讲述了主人公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实现思想和情感升华的故事, 批判了英国社会中产阶级保守刻板的思想观念, 揭露了工业进步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肯定了主人公打破阶级局限, 努力追求自我和爱情的勇敢尝试。 从解辖域化的研究视角, 通过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循环演变过程, 构建出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和情感逃逸, 凸显了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时代变革性。 小说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理念在全球化的今天依旧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中产阶级; 解辖域化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家。 他把小说中一个个或狂妄自大, 或隐忍压抑, 或渴望自由的中产阶级人物塑造地有血有肉。 同时, 他注重人文关怀, 提倡平等自由和鼓励个人发展, 并将这种开放自由的价值观与其清新自然的写作手法相融合, 创作出兼具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的小说。 他所倡导和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是英国中产阶级试图打破维多利亚时期思想枷锁的有力武器, 同时也符合当今时代变革和全球化发展的潮流。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是福斯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以保守冷漠的英国和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为故事发生地, 讲述了英国中产阶级主人公莉莉娅、 菲利普和卡洛琳在英国和意大利的经历, 并实现主人公在观念上封闭——开放、 偏见——包容、 讽刺——欣赏、 敌对——友好的蜕变故事。 本文借助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千高原》(以下简称《千高原》)中所提出的解辖域化理论, 从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角度分别对主人公莉莉娅、 菲利普和卡洛琳进行分析, 旨在体现福斯特在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的变革精神。
1 失败的抗争——莉莉娅
莉莉娅是沙士顿小镇上最显赫的赫里顿家族的长媳, 她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一方面,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和丈夫的早逝, 她对婆婆赫里顿太太的话言听计从; 另一方面, 骨子里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又促使她试图摆脱婆家的管教和中产阶级的礼教束缚。 小说开篇, 众人为莉莉娅送行的场景热闹欢快, 对比莉莉娅的结局, 不禁令人唏嘘。
1.1 屈从
莉莉娅受中产阶级刻板保守的思维模式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影响至深, 如同井底之蛙, 被困在“一个被限定的空间”, 同众多和她相似的人一起重复着周而复始的生活。[1]441她受制于赫里顿太太, 同时也被中产阶级的礼教束缚, 对于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只能接受, 不敢违背, 而这种惯性思维一旦被固化就难以改变, 形成她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赫里顿太太一开始就反对莉莉娅嫁进来, 千方百计地阻拦这场婚姻; 婚后, 则处处刁难儿媳; 儿子去世后, 也未停止对儿媳的管教。 面对这一切, 莉莉娅只能妥协。 后来, 她偶遇了老实本分的金克罗夫特先生并与之交往, 赫里顿太太再次出面干涉, 并把她送到了意大利, 以断绝她和金克罗夫特先生的联系。
1.2 尝试
来到意大利, 莉莉娅立马就被明媚的阳光和宜人的景色所吸引, 这与英国常年的阴雨连绵截然不同, 她对意大利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摆脱了婆家的掌控, 莉莉娅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全新的环境中, 莉莉娅变得像意大利人一样热情奔放, 不再郁郁寡欢, 她与意大利小伙吉诺相爱并结婚。 她沉浸在甜蜜的喜悦中, 可是很快她就因无法融入意大利人的生活圈而感到孤独, 她怀念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 想念女儿。
莉莉娅在思想上的解辖域化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趋势, 原因之一在于她性格中根深蒂固的软弱性。 面对丈夫的游手好闲, 她选择妥协。 雪上加霜的是, 吉诺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 甚至出轨, 而她再次妥协, 选择沉默。 莉莉娅的处境可谓进退维谷, 她不再是刚来意大利时为爱情义无反顾的女斗士, 而是一个流落异国他乡隐忍度日的无助女人。 她想回英国, 前夫一家不接纳她, 继续留在意大利, 更是无尽的苦楚。 由此看来, 解辖域化也可能无效、 压抑、 碰壁、 固化, 甚至陷入黑洞。[2]41
1.3 死亡
莉莉娅在错失一次返回英国的机会后彻底绝望, 整个秋天都病病殃殃地躺在床上, 最后在难产中死去。 在描写莉莉娅的死亡时, 福斯特惜字如金, 寥寥几字带过, 却突出了死亡带给读者的沉重感和对莉莉娅悲剧命运的叹息。
莉莉娅的思想变化在进入解辖域化的环节时戛然而止, 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自身的性格缺陷。 莉莉娅长期的逆来顺受使她的抗争精神仅仅昙花一现, 虽然摆脱了赫里顿家族的压制, 却又陷入丈夫的冷暴力之中。 尽管她试图反抗, 试图逃离, 最终却因缺乏勇气而放弃。 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 主观因素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而莉莉娅正是由于缺乏了主动改变和适应的驱动力,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2 思想的解域——菲利普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 “辖域化、 解辖域化、 再辖域化分别意指能量在身体和经济的特定领域的投注, 对这一能量投注的撤销以及能量在别处的再投注……有助于引导能量投注的编码、 去编码和再编码的诸过程相伴。”[3]8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三者环环相扣, 共同完成抽象或具体对象的动态的、 不间断的变化之流。 小说中, 菲利普三次前往意大利, 始终在创造块茎, 伴随不停歇的位移来到未知地带进行观念的解辖域; 随着她身份不断地变化: 观光者——阻拦者——拯救者, 其思想形成一种动态的流动和逃逸。[4]在不断的解辖域化过程中, 菲利普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感, 中产阶级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被打破, 形成了更加开放的思想格局。
2.1 与生俱来的“发育不良”
“辖域化”指一个人在某一地点长时期生活, 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在周围的人和事物的影响下开始变得固定化, 形成惯性思维模式并且难以改变, 即社会的“编码”。[3]80菲利普长期生活在沙士顿小镇这个闭塞的地方, 受中产阶级保守思想的影响, 守旧死板, 且顽固不化。 他虽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行为举止儒雅得体, 有着一份人人羡慕的体面工作, 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是孤独寂寞的。 他彷徨迷茫, 人生没有明确的方向, 只会按照母亲——赫里顿太太的要求按部就班地生活。 菲利普思想上的“发育不良”是英国中产阶级的通病, 福斯特试图通过意大利的人文思想来拯救这颗“发育不良的心”。
2.2 三次意大利之行
“解辖域化”是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核心, 它意味着离开家园, 改变习惯, 学习新的技艺。 解辖域化是对辖域化边界的解构与逃逸, 可将其理解为产生变化的运动, 是“去编码”的过程。[2]39菲利普三次前往意大利, 对意大利的认识经历了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客观公正三个阶段, 他逐渐正视了自己的狭隘和偏见, 思想意识上的缺陷在意大利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日趋完善, 通过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逃逸线”来实现解域。[5]21
2.2.1 幻想的构建
数年前的意大利之旅开启了菲利普认识世界的大门, 通过这扇门, 菲利普踏上了一条探索未知领域的道路。 意大利带给他精神慰藉和依托, 那里的一切在菲利普眼中都是完美的, 这种完美在离开意大利之后愈加被神圣化和理想化, 最终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 在菲利普眼中, 意大利不同于死气沉沉的英国, 是一个颇具生机和活力的地方。 他“相信, 凡是游览过意大利的人都会变得纯净和高贵。 意大利是世界的游憩胜地, 也是世界的学校。 莉莉娅想去意大利, 委实值得称赞”[6]6。
那里的风土人情、 自然风光、 历史古迹甚至纷乱嘈杂的市井百态, 都让他觉得如此真实生动, 新颖有趣。 菲利普的思想在新的环境中开始进行“解码”, 原有的中产阶级保守思想在新环境和新观念的冲击之下开始逐步瓦解和解构。[6]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所述:“辖域化了的功能则在通向其他装配的过程中或与其他装配的连接之中被解域, 在辖域主题与对位越来越独立于内界冲动与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中被解域。”[3]80菲利普在将意大利的美好和粗鄙全盘接收后, 像一个先知一般回到沙士顿, 显露出一种要么改造它, 要么舍弃它的架势。 但是没过多久, 这股劲头就偃旗息鼓了, 沙士顿和他自己依然都是老样子, 只是心中对美的追求还有所保留。
2.2.2 幻想的破灭
在得知莉莉娅即将再嫁的消息后, 赫里顿太太立马命菲利普前往意大利进行阻拦。 虽然背负家族使命, 但再度来到意大利后, 菲利普仍然沈醉于对意大利美好的记忆中, 满心欢喜地故地重游。 然而, 在受到吉诺的冷嘲热讽和多番戏弄之后, 他恼羞成怒, 拂袖而去。 他见识了意大利人粗俗不堪的一面, 认识到他们也会为了金钱而算计, 为了利益而说谎。 人性的丑恶尽显无疑, 古罗马圣神崇高的文明荡然无存, 意大利的完美形象也随之破碎。 菲利普对意大利的美好印象被彻底破灭了。
2.2.3 回归现实
莉莉娅死后, 菲利普第三次前往意大利, 此行的目的是将莉莉娅八个月的孩子带回英国。
起初, 菲利普对上次去阻拦婚事时发生的闹剧耿耿于怀, 内心充满了对意大利和吉诺的抵触。 抵达意大利后, 他得知吉诺对之前发生的不愉快感到很抱歉, 菲利普也不计前嫌。 他心中重新燃起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一颗浪漫的种子在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开始萌发。
接着, 在歌剧院, 菲利普彻底融入到轻松欢快的氛围中, 他将任务抛之脑后, 仿佛自己不是游客, 而是地道的意大利人。 这里的人和物不再像记忆和幻想中那样虚无缥缈, 一切都是真实的。 随后, 他与吉诺偶遇, 热情拥抱, 称兄道弟。 在菲利普心里, 意大利民族宽广的胸襟仿若浩瀚的星空, 包罗宇宙万物, 而自己只是徜徉在其中的一粒尘埃。
最后, 在孩子意外死亡后, 吉诺虽然一时无法接受事实, 但最终还是原谅了菲利普, 并在关键时刻帮菲利普开脱。
第三次的意大利之行, 菲利普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通过和吉诺的交往, 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意大利, 其思想的解辖域化进程被推到了顶点。 然而, 顶点并不意味着完结, 任何解辖域都会伴随着再辖域, 最终变成新的形态。[5]22
2.3 终点亦是新的起点
“再辖域化”是指人在新的环境下新旧思想发生更迭后, 新思想取代了旧思想并再次固化的过程; 从固定的关系中寻求自由解放, 构成新的装配与范畴, 即社会的“再编码”。[5]21小说中, 回到英国的菲利普决定去伦敦闯荡, 所代表沙士顿小镇的那颗“发育不良的心”被他彻底抛弃了。 在意大利所接受的人文思想已经固结, 完成再辖域化和再编码, 成为现阶段决定他行为的主导思想。 自我认识的完善和对他人的宽容态度打开了菲利普新生活的大门, 生活对于他而言不再是匆匆一瞥的风景, 而是有意义的真实存在。
当然, 思想的变化永远不会停止, 在他到达伦敦后, 新一轮的能量投注又将会开始, 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的运动过程又将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
3 情感的逃逸——卡洛琳
福斯特笔下的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因循守旧、 冥顽不化的消极形象, 例如小说中的赫里顿太太和哈丽雅特。 她们固守中产阶级的英国中心论思想, 鄙视一切异邦文化, 刚愎自用。 另一种是具有时代特点、 勇于变革的积极形象, 例如小说中的卡洛琳和莉莉娅。 她们在陌生的国度持包容并蓄的心态, 接受并学习意大利文化, 试图融入其中, 吸取新鲜的养分。 对卡洛琳的解辖域化研究主要侧重于自我情感的认识和表达, 通过两次前往意大利, 完成了她在情感方面压抑——克制——释放的动态变化。
3.1 隐藏
卡洛琳的人物形象是丰满的, 作为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她年轻漂亮, 言谈举止得体大方, 身上散发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稳重。 她是地道的英国人, 保守教条, 沉闷无趣。 就连挑剔的赫里顿太太都认为, 不管是多么粗俗不堪的人, 只要在卡洛琳身边待上三个月, 都能被她的美好品德同化。[6]9卡洛琳压抑的性格是生活在沙士顿小镇辖域化的结果, 她所处的阶级背景、 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所信仰的宗教都对她的言行进行约束, 她压抑自己的情感, 在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变化。
3.2 觉醒
意大利这个神秘国度却对她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 她想亲自去看看, 为平淡的生活添点谈资。 到达意大利后, 卡洛琳立马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吸引, 抱着画板四处写生。 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富有生机, 和沙士顿的死气沉沉相比, 这里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她内心充满文艺情怀, 只是在沙士顿, 这种浪漫情怀被规矩和信条所束缚。
如同《千高原》中说到的, 当人的某种功能被辖域化之后, 只有在尝试跳出原有环境或接触新环境后, 被固化的功能才能实现解辖域, 而在解辖域的过程中, 内部的冲动在与外界的不断接触中越来越强烈, 最终冲破辖域主题, 实现逃逸。[3]81意大利, 一个陌生的国度, 没有人认识她, 没有人约束她, 她可以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卡洛琳的自我意识在意大利苏醒, 她不想再假装无私, 不想再做出自我牺牲来取悦他人, 成为他人眼中的道德典范, 她厌恶这一切, 她要学会让自己快乐。
赫里顿太太原本指望卡洛琳看住莉莉娅, 别让莉莉娅在意大利惹是生非。 可是, 卡洛琳非但没有阻止莉莉娅因一时头脑发热而决定的婚事, 反而鼓励莉莉娅勇敢去追求爱情。 她支持莉莉娅发起反抗, 她们两人一起享受着这种叛逆的快感。 但是, 菲利普的到来让她慌了神, 她在新旧两种观念中徘徊和挣扎, 最终, 她仓惶地逃回了英国。
卡洛琳再次来到意大利, 带着一种纠结复杂的情感。 事实上, 她爱上了吉诺, 卡洛琳的情感像“清除一个又一个障碍……破坏了两岸并在中间加速的没有源头或终点的一股溪流”[8]41, 她试图通过愤怒来掩盖这种情感。 她无法面对自己的情感, 没有勇气表达这份情感, 只能极力去抑制。 卡洛琳的情感好似一个圆圈, “在圆圈上打开一个缺口, 敞开它, 让某人进入, 召唤某人, 或自己走出去, 奔向外部”[3]81。 这个过程是情感从界限内向外逃逸的动态之流, 也是情感的解辖域化和解码。 通过内外两个界限的交换和转变, 情感的抑制和情感的释放进行着力量的角逐。
在歌剧院, 卡洛琳逐步放开自己, 她和所有观众一样, 鼓掌欢呼, 身体伴随着音乐不停地摆动, 完全融入其中, 而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一旁不停抱怨的哈丽雅特。 卡洛琳与哈丽雅特的对比, 也是卡洛琳与解辖域化之前的自己的对比。 这种绝对的解域, 不是从这种或那种教条或形象之中解放出来, 而是更加自由的流动和形象的无限创造。[9]84福斯特通过设置卡洛琳的影子角色——哈丽雅特, 实现了两种女性人物的横向和纵向对比, 使卡洛琳的人物形象在情感变化上有了质的飞跃。
3.3 释放
在教堂, 菲利普和卡洛琳畅谈未来, 此时的她, 再不会像当初那样因意识到自己爱上吉诺而不知所措, 她勇敢地向菲利普吐露了自己对吉诺的情感。 情感的“发展需要跨越一道道分水岭, 每次的成功跨越都会推动功能的自主表达”[3]80。 卡洛琳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爱意终于从道德的束缚中逃逸, 卡洛琳的情感最终实现了麻木——觉醒——克制——释放的过程。
卡洛琳在经历了善恶美丑、 生离死别之后, 在此刻, 她跨越了最后的一道分水岭, 自由表达出自己的情感。 她的情感需求得到了释放和表达——大胆去爱, 不惧世俗的眼光, 抛开阶级、 金钱、 学识和职业, 只是单纯的爱吉诺这个人。 最终也没有向吉诺表白, 最终决定回沙士顿小镇, 看似一切都回到原点, 但卡洛琳的情感已经被唤醒, 从一沉不变的生活中逃逸, 她的激情被点燃, 她对生活呈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即使是在循规蹈矩的沙士顿, 卡洛琳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10]
综上所述, 小说通过英国和意大利的思想文化差异和碰撞, 真实地展现出不同阶级、 不同民族之间愈加激烈的矛盾隔阂, 无情地讽刺了英国社会对于物质生活的狂热追求和对于精神财富的冷漠淡然。 透过小说, 福斯特意图表达他对处于时代大变革之中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担忧和批判, 也传达出他试图利用人文主义精神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分歧、 隔阂与背离的尝试。 小说主人公前往意大利的经历推动了他们在思想和情感上的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过程, 使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步从中产阶级的固化思想中获得逃逸, 打开了新的认识视角。 福斯特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共存理念和求同存异的文化态度正是当今全球文化交流所需的思想, 具有明确的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
[1] [法]德勒兹, 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 姜宇辉,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2] 麦永雄. 德勒兹哲性诗学: 跨语境理论意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美]尤金·W·霍兰德. 导读德勒兹和加塔利《千高原》[M]. 周兮吟,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4] 张中. 自由的踪迹, 或域外之思——论德勒兹思想中的“自由”观念[J]. 河北学刊, 2016(5): 18-23.
[5] [英]戴米安·萨顿, 大卫·马丁·琼斯. 德勒兹眼中的艺术[M]. 林何,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6] [英]福斯特.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M]. 马爱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7] 杨海鸥.《阿罗史密斯》的解辖域化叙事策略[J]. 外国文学, 2010(6): 88-94.
[8] 陈永国.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9] [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 导读德勒兹[M]. 廖鸿飞,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10] 王虹. “近女性”与“流”的解辖域化[J]. 社会科学研究, 2012(5): 129-133.
AnalysisofWhereAngelsFeartoTreadfromthePerspectiveofDe-Territorialization
SUNY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08, China)
WhereAngelsFeartoTread, the first novel of Edward Morgan Foster, depicts a story that two British middle-class protagonists, inspired by the Humanism in Italy,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and distillation of ideology and emotion. It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conservative view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estrangement caused by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praises the protagonists for their endeavors to break the class limitation and to pursuit love and self-awar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the spiritual growth and emotional release of the protagonists have been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cyclical process of territorialization,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the novel. As such, the revolution of the time in Foster’s novel has been manifested. The multiculturalism shown in the novel still has actual and direct sense in the modern time.
WhereAngelsFeartoTread; Edward Morgan Foster; middle-class; de-territorialization
1673-1646(2017)06-0048-05
2017-09-29
孙 晔(1988-), 女, 硕士, 从事专业: 英美文学和文学批评。
I106.4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