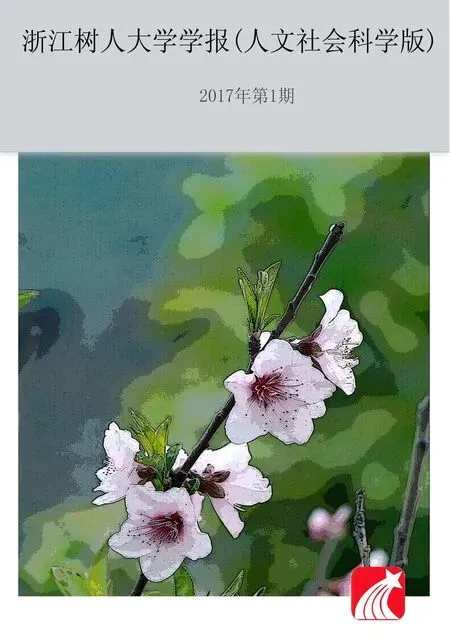经典的新释:《共产党宣言》译介的悖论
2017-01-11尤云弟
尤云弟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思政与法律
经典的新释:《共产党宣言》译介的悖论
尤云弟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共产党宣言》译介过程中产生了语义新阐释。文章对比《共产党宣言》的多种译本,分析其中的主要代表观点,认为不同学者译介《共产党宣言》存在着理解的意义与原文的意义互相对立的悖论,主要表现为个人与私有的悖论、标准与对象的悖论、实用与研究的悖论、决裂的内涵悖论、译本版本的悖论、财富来源的悖论、历史的逻辑悖论、自由的关系悖论、个体与社会的悖论以及目的与方法的悖论。《共产党宣言》本身并不存在以上的多种悖论,可见悖论产生于多位学者的译介过程中。
《共产党宣言》;经典译介;悖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学者译介传播《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过程中,赋予了经典著作时代烙印的新阐释。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宣言》“当代价值、科学性、现代性和中国化”等议题,甚至有些学者简单认为21世纪初“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全球化和中国特色①潘惠香、王永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研究新动向》,《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第261-266页。,忽视经典著作当代译介过程中多种多样的新变动。迄今为止,在讨论经典论著的当代译介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对当代译介的过程缺乏探讨;其二,误读经典论著。因此,本文考察多种《宣言》的译本阐释,从中概括学者译介经典著作的过程中产生的10种悖论。认真解析译介过程中产生的悖论现象,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领会《宣言》的精髓,达到学以致用。
一、个人与私有的悖论
在译介经典方面,横向发展的思维模式常常导致人们对不同内涵的概念进行简单类比,甚至互换。以理解《宣言》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为例,表面上看来,《宣言》既主张消灭私有制,又主张实行“个人所有制”,这似乎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译者把“个人所有制”和“私有制”混为一谈。“它既指每个劳动者都平等地占有共同的生产资料,也指社会总劳动产品在做了必要的扣除后,作为消费品分配给个人,个人作为‘各个私的个人’拥有私有财产。”②关锋:《“共产主义”存在私有财产吗——对<共产党宣言>和“个人所有制”的新解读》,《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3年第6期,第181-186页。这一片面理解的实质,在于错误地把“个人所有”与“私有财产”画等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个人”与“私有”是两个概念。不仅《宣言》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而且在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都试图揭示“个人”的价值。“个人财产”的神圣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与个人物质存在的“神圣性”是统一的。其神圣性在于它是个人创造的仅供个人再生产以及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种财产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财产”①恩格斯:《反杜林论》,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7页。。相反,“私有制”一词在《宣言》中是有明确界定的:“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6页。正是有这样明确的区分,《宣言》才主张消灭私有制,保障“个人财产”。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个人财产”才有可能得到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individual private property)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individual property)。”③王振中:《论<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译法的正确性》,《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2期,第5-6页。
二、标准与对象的悖论
当代译介具有此刻时间意义的概念范畴,即一切都要以当下的意义为准则进行价值判断。此刻是主体进行思维的临界点,正是在当代这个过去与未来的临界点上,主体认识的价值判断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片断性。
有学者对《宣言》进行文体分析,其分析的价值判断恰恰不是文体学意义上的历时价值,而是分析者强烈的主观认知。聂锦芳提出:“就《宣言》的定稿而言,第一,四个章节之间的层次划分不分明,在论述的内容上有重复;第二,叙述风格不一致,有的偏于说理论证,有的则只是罗列材料和观点;第三,篇幅长短不均衡,第一章最长,最后一章最短,相差竟有11页之多;第四,论证节奏不一致,有的徐徐道来,视野宏富,有的则以句为段,只提出论点、措施而没有分析……这种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是由后继者对它总体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④聂锦芳:《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第5-10页。实际上,这种以文本结构为标准的批评——“叙述风格不一致”是武断、任意的,实则乃狭隘的理解视角,以主观的认知水平作为标准来判断博大精深的经典。另外,武断认为经典地位的确定不完全是由其自身思想和内容决定的,这种分析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一部思想内容不深刻的理论著作如何能让如此多的人接受它,如何能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若干国家政党的思想武器?同类文献汗牛充栋,从莫尔的《乌托邦》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经典之作比比皆是,为什么唯独《宣言》能够产生如此广大的深远影响?原因恰恰在于《宣言》的语言是一种深刻地拨动人心弦的精湛艺术,说理透彻、明晰,论证简洁、干练,同时又以其思想内容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屹立于众多社会主义学说著作之上。一部著作的传播程度固然有传播的因素,但决定因素还是著作本身的艺术及其思想内容。
三、实用与研究的悖论
当代译介临界点上的思维稍纵即逝,使得主体的价值判断以眼下目的为判断标准,从感性的功利角度来确定事物的价值,而不管其历时的意义。
有学者将《宣言》的实用与学者研究之间进行割裂式的分析,受到其他学者强烈反对,认为经典作品不在于其结构形式,而在于其思想内容。这就是说,承认别人对《宣言》结构的批评,不承认别人对《宣言》内容的批评。这种观点依旧是不成熟的译介思维。譬如,马拥军提出:“聂文不是把《宣言》看作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理论武器,而是看作学者书斋里的高头讲章。”⑤马拥军:《<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读法——与聂锦芳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5-10页。这种观点把“理论武器”看成是实践上“实用”的东西,而把学者书斋里的“高头讲章”看成是“不实用”的东西,不仅表现了对学者“高头讲章”的轻视(即对理论研究的漠视),而且把“理论武器”与“高头讲章”割裂开来。持这种观点者忘记了《宣言》也是马克思这位“学者”在“书斋”里写出来的“高头讲章”。
四、决裂内涵的悖论
夸大语义内涵,产生对“两个决裂”的误读。俞吾金认为,将《宣言》第二章关于“两个决裂”一段话中的德文词berliefert翻译为“传统的”是不妥当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这种曲解“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种曲解即“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文化虚无主义了①转引自宋书声、杨金海、蒋仁祥:《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论断的翻译和理解——与俞吾金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第34-37页。。
宋书声对俞文进行了富有学理的反驳。应当说,宋文的反驳既坚持译文的正确性,又正确地阐释了翻译的学理问题。但在译文正确性的前提下,宋文对“两个决裂”的理解依然存在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②宋书声、杨金海、蒋仁祥:《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论断的翻译和理解——与俞吾金同志商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第34-37页。
第一,“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不等于要“打破”旧世界。从“决裂”到“打破”的引申,正是对《宣言》误解的核心所在。“决裂”是从“传统观念”中分离出来或是分道扬镳,并不一定就要完全“打破”,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要“彻底决裂”,又要集中抓主要矛盾,即“消灭私有制”。这里“决裂”的是观念,是信仰问题,是指由信仰私有制的“合理性”转向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
第二,误解还表现在对“观念”内涵的理解上。无论俞文还是宋文,对观念这个中心词的理解重心都转移到“传统”这个修饰词上了。在他们看来,《宣言》“与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等于把传统的一切都剔除。正是在这个误解的语义思维逻辑上,俞文把“文化虚无主义”这顶大帽子扣到译文身上,而宋文又难以更有力地批驳俞文。“传统的观念”“等于”“传统的一切”这种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是导致误解的根源。事实上,马克思这两个决裂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潮背景的。在《宣言》诞生的时代,宗教信仰在欧洲经历着深刻变化,各种思想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传统观念”含有对传统宗教反叛的意义。巧合的是,在1847年前不久,一个英国小女孩马丽安·艾文斯为了不去教堂做礼拜,不惜与相依为命的父亲翻脸,这可以看作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最好例证。那是否可以把艾文斯看成是“共产党”人呢?显然不能,但她的实际言行正符合“两个决裂”。这充分说明“两个决裂”是时代的呼声,代表了广大人民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因此,“与传统决裂”是席卷欧洲思想界的大趋势,而《宣言》只不过是顺应这个大趋势而加了“彻底”的语气词,以与那些妥协的“决裂”相区别。正是这个原因,《宣言》一经问世,才会立即成为经典。
第三,两个决裂的语义逻辑常常被误解者忽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很显然,因为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必须与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可见,观念的“决裂”绝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和措施,而且决裂的是观念,不是像俞文所说的等同于观念的文化,因为观念只是文化内涵的一个部分。在这两句语境中,还有前后一致的重大问题:其一,这种观念是形成传统所有制的观念,而不是像宋文所理解的一切观念;其二,传统所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只是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其三,所有误解者都忘记了重要的限定词“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这个语境。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是历史性的,它在发展进程中意味着不断“决裂”,当然也会与自己形成的传统“决裂”。这种“决裂”是一种创新思想的体现,是社会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对传统不断超越的过程,当现存的观念严重阻碍“共产主义革命”时,“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同传统的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
综上所述,“两个决裂”体现的是创新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像俞文和宋文误解的那样,把“两个决裂”推向极左和极右。
五、译本版本的悖论
在对《宣言》的译介中存在着研究对象设定的错误,在译本版本上发生偏差。有学者忽视《宣言》的原创语言,在讨论汉译本时,要么把汉译本看成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要么把英译本当成作者的原创语言。“通过比较《宣言》英文本与汉译本,可发现汉译本存在几处重大缺陷。”①罗伯中:《关于<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若干问题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第20-22页。该文在对照译本时,忽视了两个事实:其一,如果汉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那么这种汉译本就不具备进行对照的必要,因为转译本根本不具备作为讨论的“问题”的条件;其二,如果汉译本是从德文本直接译过来的,那么用英译本中的句子对照汉译本的句子,也不具有可比性。这是译本翻译比较的重大问题,又是常识性的问题,在这种常识性错误的基础上,认为汉译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结论自然是毫无价值的。
六、财富来源的悖论
对《宣言》立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存在片面理解。将“剩余价值理论”错误地理解为工人用暴力方式进行革命的必然理由,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方向较为片面,即不加区别、不审时度势地一律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或者理解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必然尖锐的斗争。这些误解将在实践上导致严重的问题,在理论上也会把马克思主义引向错误的方向。
事实上,马克思这一独创性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从理论上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核心命题,是财富来源的本质规律。这一理论的创立,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内核。这一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制度,都必须建立在以“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创新的内核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宣言》才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是革命的、创新的和尊重劳动的,但背离了“劳动创造财富”这个起点。马克思正是在这个起点上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换句话说,任何社会制度,只要背离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最本质的人类社会价值观,都必然灭亡。可见,马克思政治价值观的核心正是创新思想,并不是用来斗争的思想武器。
七、历史的逻辑悖论
对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有种种误解。《宣言》只是阐明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和主要矛盾,并不等于把总体特征和主要矛盾与具体特征和具体矛盾不加区别地画等号。《宣言》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独家发明,而是19世纪英国社会普遍使用的一个词。《宣言》的诞生,正是对当时社会总体特征的总结。对这一论断的片面理解,会导致政治价值观的极左偏向。
误读阶级斗争理论,主要是忘记了《宣言》序言中的重要原则:“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阶级斗争是社会的总体特征,但不是说阶级斗争总表现为激烈的冲突。阶级斗争因时因地而表现程度不同。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劳苦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除了暴力革命根本无法解决。“而这个斗争现在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因此,毛泽东科学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但若不审时度势,总是把阶级斗争的理解推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则是对《宣言》的片面译介。
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正是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结果。《宣言》旨在消灭阶级,而消灭阶级的前提是消灭剥削。然而,社会主义阵营中却存在着一批毛泽东所尖锐批判的那种“资产阶级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的背叛《宣言》的腐败分子。正是这种思想和在实践中存在的代替资产阶级的新贵族阶级,才导致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因此,社会主义一经建立,它的基础就是消灭剥削,社会的一切施政目的都要以人的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为根本,而剥削则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要障碍。
八、自由的关系悖论
《宣言》对于自由精神的误解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与法治割裂并对立起来。“自由”一词自19世纪初从西班牙传到英国后,引发了英国巨大的政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英国当时国力达到世界第一的内在动力之一。“孟德斯鸠谈到英国人时说,他们在三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①韦伯·马克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自由必然引发管理与自由的紧张关系,无政府主义就被当成十恶不赦的大敌,在阿诺德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眼中,自由甚至成为与文化相矛盾的“群氓”的习气②阿诺德·马修:《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页。。但不管保守知识分子如何批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引发的无政府主义似乎并没有减少它们向各领域进军的势头。自由主义首先进军的是政治领域,引发了英国政治的现代化改革。至少,在“自由”的旗帜下许多旧党派最终形成联合大党,结束了英国19世纪30年代持续10年之久的政治自由化式的动荡。自由主义最大的市场是在经济领域找到了广阔天地,它引发的经济革命,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丝毫不亚于英国工业革命在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被看作“《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③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4-14页。。
显而易见,译介在对《宣言》关于自由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是拼命抹杀《宣言》的自由精神;另一种是拼命拒斥对自由的限制。这两种译介的情感动机,正是源于译介主体的悖论情感结构。
九、个体与社会的悖论
在解释经典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例如,对于《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有学者误解为:“个人的发展是在共同体中实现的,通过共同体个人才能获得和控制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才有个人自由。”⑤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4-14页。这一引申,恰恰背离了《宣言》这个核心命题的主旨。按照这个“通过……才能”句式的理解,共同体成了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一直以来对个人自由与集体控制悖论思维形成的惯性表述。《宣言》强调的前提条件正是尊重人的创造力,由创造力形成生产力,由生产力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共同体”“社会”这些概念只是过去一切统治阶级的统治话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再到霍布斯的《论公民》,尽管表面上一再强调个人,但始终跳不出社会这个圈子。无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民为了“善”的目的组成“共同体”,还是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恶”的目的组成“共同体”,几千年来,人们都在反复强化这样一个推断模式:个人必然组成“共同体”,“共同体”必然组成“国家机器”。他们反复证明的一个核心命题,正是国家永远存在的必要性的体现。正是在与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彻底决裂”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组织目的应当转变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服务”,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手段,而不是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因此,“以人为本”的政治价值观,并不是要使人受到控制才能实现其创造力,而是首先要充分发展其创造力。
《宣言》的本旨在于:第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前提条件,一切发展都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第二,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自由的联合,这种联合不以加害对方为前提;第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自由发展是前提条件,组成社会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社会是手段,是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而不是用来控制个人发展的、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正确解读。
十、目的与方法的悖论
有学者认为,《宣言》“两个必然的论证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①蔡晓良:《<共产党宣言>与“两个必然”理论的论证》,《理论月刊》2005年第2期,第11-13页。,这正是仅从当代资本主义视野来否定未来发展趋势的表现。事实上,从剩余价值的发现到唯物史观的形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是手段。它作为方法论,充分阐明了人的创造性是高于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必须从“劳动创造世界”这个根本命题出发,即人类的创新本质出发。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创新的物质基础,这一唯物主义观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个体组成夫妻,再组成主仆,然后组成社团”这样一个朴素的唯物史观。但马克思的核心要旨不是重复亚里士多德的推论和命题,而是追根溯源,找到人类社会巨大力量的根本之所在——人的创造力。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全都是因为个人的创造力。“两个决裂”充分说明了创新,两个“必然”充分说明了创新的力量,而这一个前提条件最终落到创新的主体上。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阻碍创新力量发展的制度,所以它必然灭亡,社会主义是全面解放创新力量的制度,所以它必然胜利。至于近期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只不过因为它在阻碍创新力量的程度上没有达到尖锐的程度;而某些社会主义没有胜利,只不过因为它没有解放创新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在《宣言》的当代译介中存在着理解的意义与原文的意义互相对立的悖论。本文抛砖引玉,对已发现的悖论进行概括和总结,希望引起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并研究经典著作译介中的悖论现象。通过解析存在的悖论,给经典著作的读者带来指导,以便更全面、更辩证统一地看待《宣言》多种译本传达的蕴意。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tudy on the Paradox of the Translation of Communist Manifesto
YOU Yundi
(Marxism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28,China)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reated new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This paper compares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analyzes the main viewpoints.It is considered that different scholars translate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h paradoxes between the understood and original meanings,including the paradoxes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standard and object,research and practical criticism,the paradoxes of connotation of break,edition,the source of wealth,logic of history,relationship of freedom,and the paradoxes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purpose and method etc.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tself does not exist a variety of paradoxes which came from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s.
Communist Manifesto;classic translation;paradox
10.3969/j.issn.1671-2714.2017.01.016
(责任编辑:毛红霞)
2016-09-10
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
尤云弟,女,浙江温州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