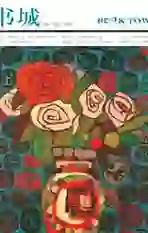穿越时间的宅男
2016-12-01李炜
李炜
0
最近的其他文章想必不尽如人意。不然,阁下岂有可能阅读此文?
无论原因为何,大人来访,是敝人前世修来之福。不知您能否听见,为了表示欢迎,这些文字已“咔刺咔刺”启动起来:一次一个齿轮,一个字。然后,经由这一个字,下一个字也开始啮合、运转。当阁下的眼珠扫过这些字时—就像您现在所做的这样—所有的齿轮就能连动起来。多亏您,这台机器开始运行,语义开始表述。这些零碎文字成了一篇文章。
但一旦阁下转开眼珠,这些文字就停止运行。机器逐渐生锈。敝人面临失业。人生也毫无意义。
只因为您不肯多花一点时间。
@%(*)$^#@!!!
0.5
我不由地想到:这其实也是马查多(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晚期小说的一大特征。他的叙述者爱跟读者闲聊,偶尔用甜言蜜语哄他们几句,但也时不时侮辱一下他们的智商。《库巴斯死后回忆》中就有这么一段:
我开始后悔写这本书了……它的主要缺陷就是你,读者。你急着老去,而这本书却慢慢吞吞。你喜欢直截了当的叙述、流畅又有规律的文字,而这本书和我的风格却像一群醉汉,他们跌跌撞撞地左歪右倒,一路走走停停,喃喃自语或是大喊大叫,有时咯咯地笑了起来,有时又向天空挥着拳头,磕磕绊绊着,最后摔得四脚朝天……
为了避免阁下被冤枉成酒鬼,让我们进行得更有序些。
这边请。
1
文学编年史记载,很久以前,葡语土地上有这么一个人:马查多。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优秀的作家,无论是在巴西、葡萄牙,还是安哥拉。
仔细想想,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在大西洋的彼岸,在同样一个说葡语的国家里,还有一名作家也能享用这头衔:埃萨(José Maria de E?a de Queiroz)。
要解决这道难题,就必须说得更确切些。来自葡萄牙的埃萨是葡语世界里首屈一指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巴西土生土长的马查多则是—
其实这是个更令人头疼的问题。要如何定位马查多才好?他不但不属于现实主义,还特别看不惯埃萨的早期风格。至于最适合他的那个标签,用起来同样不妥当。毕竟,马查多是十九世纪的作家,要再等一个世纪,后现代主义才会出现。
2
文学编年史从未试图解答这道难题;它只记载了马查多曾受到这位或那位作家的影响。当然它会这样说。马查多自己就在《库巴斯死后回忆》中承认了三大影响。
不管还有多少影响他没提到,都不会改变事实—两件事实。一是文学系谱的枯燥乏味,仅适合供专家消遣;二的范围大了一点,因为牵涉到考古学与动物学。那些影响了马查多的作家:是谁影响了他们?而谁又影响了这些后来影响马查多的作家?
确实可以继续挖下去,一代接着一代,直到我们回溯到第一只咕哝出一声类似文字的猿猴。问题是,既然没人知道那只天才动物的名字,这样的追溯又有何用?
3
不过,为了做做样子—都混得这么熟了,我也就不瞒你了。确实有必要装个模样。天知道我们也有可能沦落到需要在学府里找份工作……
所以,先憋着你的哈欠,让我提一下影响马查多最深的那本小说: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的生平与见解》。因为小说的叙述者既唠叨又糊涂,整本书从东扯到西,从南聊到北。或许是出于任性,斯特恩拒绝了扣人心弦的情节,但绝不是因为懒散。恰好相反。作者通过叙述者解释道:
离题脱轨,无可争议地带来阳光;它是生命,是阅读的灵魂。拿掉这些章节,你干脆把整本书一起拿走;一个无休止的冰冷冬天将笼罩此书的每一页。把它们归还给作者,他便会像新郎一样踏出书页,和大家打招呼,还能保证文字嚼起来滋味无穷,读者也食欲大增。
4
与斯特恩不同的是,马查多并没有一味地想要娱乐读者。他还希望引起歧义。所以他才创造了那么多个无法信赖的叙述者。这些人物始终搞不清—或拒绝厘清—自己所说的事情与故事的真相其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给你个例子:《午夜弥撒》。短篇的叙述者详述了自己十七岁时如何与一个三十岁的有夫之妇度过平安夜。尽管青涩尽去,他还是无法理解多年前那天晚上的谈话。为了等一名朋友一起参加半夜举行的弥撒,他用《三剑客》来打发时间:
我跃上达尔达尼央骨瘦如柴的马,开始了冒险。很快我就沉醉在大仲马的小说中。时间分分秒秒飞过,没像通常在等待时那样缓慢;我听到钟敲了十一下,但只是碰巧—我什么都没留意。不过,屋子里传来的细微声音还是让我从阅读中醒过神来。有人从客厅那里穿过走廊走进餐室,我抬起头来……
不消说,他看见的正是屋子的女主人,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袍。继而发生的谈话都很空泛,但从他的叙述来看,她显然在勾引他。只可惜他毫无经验,完全没猜到她的企图—哪怕是多年后依然大惑不解。
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也有可能此情此景从未发生,全是叙述者一人的臆想。马查多在故事里布满了线索,似乎在暗示整个故事不过是春梦一场。
不信你就把上面这片段再读一遍。
5
还没看出问题?也许在读《三剑客》时,我们的叙述者就开始打盹儿了。借用他自己的隐喻,他骑上了男主角的马。一眨眼的工夫他便“沉醉”在大仲马的小说里。疲倦的老马“咯噔咯噔”地向前行。被马蹄的声音—大仲马的句子—催眠着,他“什么都没留意”,因为他已经睡着了。他开始做梦。她出现在梦里……
只不过,整篇小说也有可能在描绘另一码事。有一次,马查多替读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一座只有摆锤没有表盘的钟,让你看不到时间。摆锤来回晃荡,但时光看来却没流逝。”
这么一来,我们只知道时间在溜走,无法确定量度。这足以解释为何《午夜弥撒》中的时间可以一再延长。女主人与叙述者之间的对话,包含那些尴尬的沉默,理应耗掉大半夜;在故事里,他们却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独处时间。为什么马查多要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缺乏时间概念;他写过多出舞台剧,想必清楚一页对白需用多久说完。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把时间的“嘀嗒嘀嗒”与阅读的“咯噔咯噔”融为一体。他是在暗示小说的情节总是发生在虚幻的空间里,在那里时间是快是慢,甚至存不存在,都只有作家一人说了算。
我承认,我读了《午夜弥撒》许多遍,但还是摸不清它的门道。它既是个直白的故事,又似乎是对小说艺术的评注,同时还讽刺了不少男人对女人的幻想。
6
既然扯到了男人的幻想,或许我还得说说马查多的—总比说我自己的要好。
值得庆幸的是—好像也可说是遗憾—只有他笔下的人物喜欢出轨。在现实生活中,马查多却是个模范丈夫,甚至社会栋梁。他是巴西最重要的作家。他帮助建立国家文学院,全票当选为第一任院长。他去世后还享有近乎国葬的待遇。
成就如此之高绝非易事。对马查多而言,更是难能可贵。有些人命中有福星高照,他却生来就运势不佳。家贫如洗的他,没什么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身体状况也始终不理想(除了眼疾和结巴,他还患有癫痫症)。仿佛劣势还不够多,他又是黑白混血,成长在一个奴隶历史悠久的国度。直到一八八八年—马查多快迈入知天命之年时—巴西政府才废除了奴隶制。换言之,即使不是一生一世,也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他时时需要克服针对黑人的偏见与陈见。
7
但我想谈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马查多那种难以捉摸的微妙笔触。怎么一下子会说到这里?
不管怎样,他的微妙再加上他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偏爱:这意味着他的读者必须自己判断他作品中讲述的东西是真是假。在马查多看来,不动大脑反而会冒更大的风险。长篇小说《乖戾老爷》中有这么一段:
“上帝击伤,却又医治!”后来,当我知道了阿基里斯的长矛也能治疗它所造成的伤,我突然想写篇论文讨论这话题。我甚至找出了好些老书、旧书、破书,翻开它们,比较它们,为的是查出原文和意义,找出异教神喻与希伯来思想的共同源头。我甚至逮到这些书中的蠹,也许能告诉我它们啮咬的东西意义何在。
“我亲爱的先生,”一条又肥又长的书虫回答我,“我们对自己啃的文本完全不知情,也从不选择啃些什么,甚至谈不上喜不喜欢:我们只负责啃。”
换言之,别像这些蠢虫一样,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读了些什么。在下一部长篇《伊索与雅各》中,马查多说得更彻底:
真能沉思熟虑的读者,他的脑子里有四个胃,让他可以反刍再反刍一切情节与事件,直至他发现(似乎被隐藏的)真相。
8
至于马查多自己,他应该从小就打定主意要胜过一头牛。还不到十八岁他就在印刷厂里当了学徒。
在今天看来,这份工作并不怎么样。但在一个由文字称霸的时代,能在出产印刷物的地方吸尽墨水应该是穷书生最好的选择。
果然,马查多的大名很快出现在一家又一家报纸、杂志、期刊上。他的野心不仅体现在他的产量,还能从种类看出。几乎从一开始,他就尝试了所有文学体裁:诗歌、戏剧、歌剧、散文、评论、小说。一旦有闲暇,他还会用来学外语,没多久便熟悉到能把外文小说和戏剧(主要来自法国)译成葡语。
才三十出头,他已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9
我知道,我知道。写出上面那句话是几秒钟的事情,要做起来却不是一般作家能力所及。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该把马查多的生命形容为一场障碍赛;他需要不停地跨越一个又一个栏杆。哪怕是爱情也来之不易。他未来妻子的家庭就反对他俩在一起,应该就是因为他不是白种人。
考虑到他描绘事情的微妙手法,他是不可能在作品中迎面攻击他所遇到的不公正的。不像大仲马—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混血作家—马查多甚至没留下任何回击种族歧视的名言。
难怪有些批评家会声称马查多对种族问题不感兴趣。事实上,对辛辣幽默情有独钟的他,爱用喜剧来包装严肃的社政评论。比方说,他发明了一个名叫博尔巴的疯子哲学家,还一口气让这家伙出现在两部小说里。这绝不只是为了制造滑稽场面—
10
这倒提醒了我。要是你还一心想着那个该死的影响问题:这一招,马查多应该是从巴尔扎克那儿学来的。后者常让笔下人物从一本小说中游荡到另一本……
9
说着说着我自己也想游荡到别的文章去了。让我们回到博尔巴身上吧。他是“人类主义”之父。在《库巴斯死后回忆》中,马查多让他一边啃着鸡翅,一边解释这门他一手开创的学问:
我的体系是如此崇高,只需要用这只鸡便可证明。它以谷粒为食,而这谷粒是由一个非洲人所种;让我们假设他是从安哥拉进口的。那名非洲人出生,长大成人,然后被卖掉。一艘船把他运到这里;造船所用的木头是由十或十二人在森林里砍伐下来,推动这艘船的帆则由八或十人缝纫。这还不包括航海所需要的索具及各种装备。这么一来,这只我在午餐中刚吃完的鸡,是各方努力奋斗的结果,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厉害吧?寥寥几行文字就揭穿了奴隶社会的真面目。多少人得一辈子当牛当马,才能让一个兜里有点钱的白人吃香的喝辣的?
10
没错,有些小说家会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或《无巢之鸟》这样的作品来打抱不平。但马查多不是这种作家。
不过也没关系。这世上已经有了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和马多女士(Clorinda Matto de Turner)。
11
马查多轻描淡写的习惯刚好吻合他的文风,既简洁又直接,与当时流行的繁复风格刚好背道而驰。你只需读两句雨果或詹姆斯(Henry James)写出的句子—复杂漫长又拐弯抹角—便知道马查多有多不寻常了。阅读他就像凝视一股清流,流畅的文字明晰到让你觉得能看到他思想的河床。
也许这就是他把那么多条进口鱼放进河流的缘故:为了使花样更多,景色更宜人。在他的作品里,你会遇到几乎所有西方经典著作,从古希腊到马查多自己的时代。这么做确实不无炫耀之嫌,但至少马查多有这权利。凭借自身勤奋,仗恃海量阅读,他自学成才,成为顶尖知识分子,哪怕代价是一双使用过度几乎瞎掉的眼睛。
12
一个拥有国际视野、学养与品位还如此“欧化”的人,却从未跨出国门—你说这好不好笑?事实上,马查多连故乡里约都不常离开,最多只是在附近走走。
或许这全与他的健康状况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读了万卷书,觉得没必要再行万里路了。
此外,他一直深信能从特殊性中提取普遍性—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过,没事套几句哲学术语,无疑能让自己显得厉害。
我想说的是,尽管马查多写的都是巴西人,但那些人物每一个都够矛盾、够复杂,可以代表全世界的人。所以他才会有句格言:“保留自己的传统—即使在处理遥远时空的问题时。”
在人生后段,他还会提倡一种新的美学观,既含本土风尚,又融合了异国风情。以受法国影响的作品为例,马查多辩道:
法-巴艺术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艺术家的出生地,而是因为它融合了里约与巴黎或波尔多……它不再具有这种或那种语言的特征。它传承了两个起源的要素。它是生灵……是当地的果实。
马查多的结论是:“我不需要其它的出生证。”
13
毫无疑问,他尊重的是那些无论受谁影响都能保有自己个性的作品。他受不了盲目的模仿。这是他攻击埃萨的一大原因。
哪里又冒出一个埃萨?
我就知道你没用心读!文章一开始我就把他介绍给你了!
所以,马查多严厉批评了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五百遍的葡萄牙作家。在他看来,埃萨只是在效仿当时最时髦的法国小说,特别是那些从现实主义分支出来的自然派作品。
以左拉为前锋的自然主义发誓要推翻艺术的主观性,用一种貌似科学的客观手法来取代。可惜在马查多看来,自然派著作有如蜻蜓点水,只关注水面上的景色,或许还能栩栩如生地描绘碧海青天,却没本领测出大海的深度。要做到这一点—要了解宛如大海、起伏不定的人生—唯有向内发展,挖掘人心。
不消说,马查多的靶子其实是左拉。埃萨只是他评级中的“附带打击”。这对埃萨来说当然不公,尤其考虑到那时他才刚崭露头角,尚未找到自己的风格。
此外,马查多似乎忘了自己刚出道时,同样膜拜了法国文学。当然不是自然派的作家,而是他们的老前辈,浪漫派的大师……
14
老实说,光是写上面这两句话就让我泪水盈眶。这么无聊的内容,还是留给文学编年史吧。
让我们重新来过,好吗?
13
基于我个人对埃萨的膜拜,我必须说:马查多完全搞错了。埃萨其实跟他一样,痛恨缺乏主见的跟屁虫。在他成熟的小说《马伊亚》中,埃萨狠狠地讥讽了这种人:
那些靴子的形状解释了如今葡萄牙的一切。它展示了事情的真相。一旦抛弃了传统……凄惨可怜的葡萄牙决定要现代化,但缺乏能打造出自己风格与模样的材料—创意、活力及个性—它只好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款式:有关观念的、裤子的,有关风习的、法律的,有关艺术的、烹调的。因为它毫无判断力,又十万火急想要变得时尚高雅,便瞎改一通,把这些款式都搞得滑稽可笑。靴子的最初样式来自国外,脚尖有点窄,于是葡萄牙的型男就把它弄得更窄更尖,活像个针头。至于作家,阅读了龚古尔(les frères Goncourt)和魏尔伦(Paul Verlaine)那些精雕细刻的作品之后,他们马上就开始折磨自己的句子,直到没人能看懂才罢休。立法委员呢,听说他们国外的同行提高了教育水平,马上开始教小学生玄学、天文学、文字学、埃及学、理财学、比较宗教等等的高谈阔论。在其它领域也并无二致。无论是演说家还是摄影师,法官还是运动员,统统都来这一套。
14
如果连一度是海洋强国的葡萄牙到了十九世纪都成了文化的不毛之地,做了它三百年殖民地的巴西又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每当有外国游客夸奖他祖国的自然美,马查多只能感叹:
他们其实很少谈起我们。即使谈到,也很少说好,更常说糟。但他们都同意这里是人间仙境。在我听来,这简直是在践踏巴西人和他的一切成就。
15
不好意思,我都忘了你还在这里。
真的不能怪我。什么是文章?我的定义是作家的独白。
说到独白,好像也没什么好补充的。但如果话题是改善一个落后国家的形象,我倒是可以再说几句。
所以你看,又是一场独白……
15.5
为国争光是表明爱国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替祖国效劳。始终是模范公民的马查多,两件事都做了。三十出头,他便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政府机关里工作,包括农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行事可靠谨慎的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个模范官僚。
对别的作家来说,一份日常工作只有可能挤占用来从事自己事业的时间。一向勤劳的马查多,自然有办法应付。
我知道我在赘述,但我得替下面的理论先铺好地板。不然,你想必会嫌那里的思想过于简陋。
16
稍微研究过马查多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之前”和一个“之后”。一八八○年前,他是个传统的作家,常写些中产阶级的苦命鸳鸯。这些作品不乏文采,但也没多少创意。一八八○年后,他突然变了。他不再遵守传统。一夜之间,他比先锋派还要先锋。如此大幅度的转变要如何解释?
文学编年史在这个问题上沉默不言。它单单指出,在一八七八年底,马查多因积劳成疾,与妻子一起离开了里约。在一个度假山庄里他休养了一段时日。
我们所知的差不多就这些。没有人清楚在那几个月里,马查多有无阅读。
鉴于他读书成瘾,很难想象他每天闭着眼睛休息,没与书做伴。即使被眼疾困扰,他也会请妻子读给他听。
假定他有看书,《项狄的生平与见解》应该是其中一本,甚至唯一的一本。因为一八七九年的春天,马查多返回里约后,很快就动笔写《库巴斯死后回忆》:他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作,也是受斯特恩影响最多的一部。结构零碎又缺乏顺序,写法俏皮又令人惊奇,它不像当时任何其它作品,无论是巴西出产的也好,别国进口的也罢。它更像一本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抑或二十世纪晚期的后现代著作。这样一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17
文学编年史—算了,还是靠自己吧。让我们用逻辑来想象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既然我已铺好地板,现在就剩下墙壁和天花板了。
在马查多一跃成为大师之前,他休息了一阵子—这我们确定无疑。在休假期间,他读了斯特恩的小说—这我们只能推测。至于他之前是否翻过《项狄的生平与见解》,这一点也不重要。只有在那时候—一八七九年—这本书才派上用场。马查多将近四十了。尽管他手捧铁饭碗,但公务员的工作还是味同嚼蜡;毕竟,他是个有自己想法的艺术家。尽管他已享有声名,但他应该清楚自己尚未写出一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毕竟,他是个熟知文学史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做出了选择—唯有这才能解释他惊人的蜕变。他决定释放自己。他不会再被世俗约束,不会再去迎合大众口味。他要写一本自己也会想读的书。他要继续拓展斯特恩已经开辟的土地,创造一件划时代的大作。他已经有了爱妻,有了名望,甚至一份固定的收入,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难道不是他把小说命名为《库巴斯死后回忆》的真正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已亡;他是在阴间和我们说话。但这正是马查多自己的处境。之前的那名传统作家已离世,新作家还在等待出生。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能成功写出这本书。
《库巴斯死后回忆》一八八○年开始在一家期刊上连载。命运终于向马查多让了一步。
18
没错,马查多在一八六九年出的第一本短篇集里就在玩弄读者了。以《道勒小姐》为例。它彬彬有礼地邀请你坐下来听故事—只为了突然抽掉你屁股底下的凳子:
如果本文读者是个多愁善感的青年男子,他会把道勒小姐想象成一个纤细苗条、肤如凝脂的英格兰小姑娘,睁着一双蓝色大眼睛,微风吹拂着她的金发,扫过她鲜花般的脸庞。这样的一个姑娘应该像雾一样虚无缥缈,像莎士比亚的人物一样完美无缺。她的名字和英式烤牛肉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茶与牛奶是这种仙女的基本食物……她的谈吐该像竖琴那样柔美动听……
这意象颇有诗意,却不是故事的女主人公。
结果道勒小姐只是一条狗。无论有多可爱,这样的玩笑还是没《库巴斯死后回忆》中的那些高明。
要说得俗气点的话,我们可以把马查多比作一棵早期发芽的花树,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但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生长,然后才会盛放。
但这棵树成熟后开出的花朵是如此怪异,十九世纪无法为它们命名。即使时至今日,我也不确定该如何称呼。
19
停下来想想,还真有点奇怪。英国在十八世纪创新小说的写法后,几乎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例外当然还是有,但哪个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能跟斯特恩、斯威夫特或笛福相提并论?
这话题显然超出了本篇小文的范畴;它唯一的目的是介绍一个葡语国家之外没多少人听说过的大师。
至于为何如此,难道你真不明白?大部分人都极其势利。他们宁可吃过期的狗食—只要罐头上注明了原产地是一个超级大国—也不愿去品尝另一个国家的三星级料理,如果这国家的武力不够强大、经济不够发达。
美国小说大肆流行不也就这么回事?
20
真正的谜题其实藏在马查多的绝笔之作里面。发表于他一九○八年去世前的两个月,《阿伊雷斯的追念》毫无疑问是在死亡的阴影下写就的。不是他自己的死,而是比他早去世四年的妻子。就这一点而言,这本小说绝对是他最私人的作品—也许是他唯一这样的作品。马查多很少在书中流露心声,更不会泄露隐私。他坚称自己的生活与作品毫无关联。
这令《阿伊雷斯的追念》既矛盾又难解。矛盾,是因为马查多自己向朋友承认作品中的一个角色是以他妻子为原型。难解,是因为书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似乎也是她的替身。
证据是马查多送去印刷厂的手稿。虽然稿件由他亲笔书写,但哪怕是临近出版,他似乎还没拿定主意自己到底在写谁。一下子他把一个女人的名字换成另一个的,一下子他又把另一个的改成这个。这样的替换有将近两百处。
这意味着什么?想必不是他不熟知自己的老婆或不知道该怎样描绘她。他们的婚姻长达三十五年之久。如果他还能犯下这种基本错误,而且如此之多,那他不仅是最糟糕的丈夫,还是不入流的作家。
所以,要怎么说通这件事?他突然后悔透露太多有关爱人(甚至他自己的婚姻)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或那个段落里,他索性让一个角色来做原本是另一个角色所做的事,说另一个角色要说的话?问题在于,要想抄这样的近路,小说中的两个女主角需要相似到可以互换。你自己说说看,还有哪件文学作品可以随便把一个重要人物的言语与行动指派给另一个角色,而且如此改过后不但顺理成章,还能赢得好评?
我也不瞒你,《阿伊雷斯的追念》中确实有几个地方的转折发生得有点突然;你以为会出现的是一个人物,却遇见了另一个。不过,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在作弄你:因为你事先知道马查多在小说里动过了手脚。
21
还有一种可能:马查多在尝试一种新写法。甚至在居丧期间,他都无法抵制这诱惑。如果这确实是他的目标,要等到一九七七年,而且还是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阿伊雷斯的追念》才会找到一件能与它做伴的作品。我指的当然是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Luis Bu?uel)的经典大作《欲望的隐晦目的》。
这部电影之所以经典,主要是因为它的女主角由两人同时扮演。某些场景露面的是一个演员,某些是另一个。谁也说不准哪张面孔会出现在哪一幕。电影里的人物没有一个为此感到困惑,甚至没注意到这些变换。只有观众觉得莫名其妙。
在自传中,布努艾尔揭示了这么做的原因:
如果我要列出酒精的所有好处,恐怕这辈子也说不完。一九七七年在马德里,我和阻扰《欲望的隐晦目的》、不让它拍完的女主角大吵一架之后,陷入了绝望。制片商决定放弃电影。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让我俩深感沮丧。有天晚上,我们泡在吧里借酒消愁,我突然有了个想法(多亏两杯干马提尼):用两名女演员来饰演一个角色。这种做法没有人试过。虽然我是在开玩笑,制片商却很喜欢这点子,于是电影有救了。这再次证明酒吧和杜松子酒是无可匹敌的结合。
布努艾尔到底还是喝多了;他没完全说对。他的做法十之八九已被马查多抢先了一步。
但无论谁先用了这一招,含意都一样。也许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刻都不是单独一人。难道这不是我们老是自相矛盾的缘故?我们是在跟不止一个“自己”闹别扭。让两名演员同时演一个角色: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阐明这一点?尤其考虑到在《阿伊雷斯的追念》中,两个女主角隔了一代。这么一来,马查多可以同时用她们来代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爱妻。
22
好像我也没完全说对。马查多最具私人性的作品应该不是《阿伊雷斯的追念》,而是《致卡罗琳娜》,一首在他妻子去世后写成的十四行诗。这里是敝人自己的拙译,请别见笑:
亲爱的,向最后这张
终于能让你安寝的床
我再一次走来,
带给你这颗伴侣的心。
那里依然悸动着真情,
它一度减轻了生活的艰苦,
助我们寻找到快乐,
以及仅仅属于你我的避风港。
可怜的,我带给你鲜花,
摘自曾经看守我们的大地,
如今却放弃了生死离别的你我。
以至于快要失明的我,
如果还有任何念头,
那些念头也都随你而去了。
这无疑是鸡群中的仙鹤,马群中的独角兽。整体来说,马查多的诗歌都很冷;他对形式和措辞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其它方面的考量。《致卡罗琳娜》却不然。它发自内心深处,由最悲伤的情感促成。但这不意味着马查多忽略了形式。事实上,原作使用了四组“双韵”(每行诗的结尾都押了两个韵),以“abba abba cdcdcd”的顺序出现。
换言之,他是在用诗歌来抒发悲伤,用技巧来遮掩泪水。这首诗理所当然成了马查多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
23
这就是马查多消愁的方式:探索文字的巧妙。不像布努艾尔,他不需要酒精。身体脆弱的他,甚至不碰巴西的国饮:咖啡。
但无论他爱喝什么,喜欢什么,他应该知道到头来都无关紧要。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不可能把幸福押在身后的名誉上。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更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最让他庆幸的,想必是自己是家族的最后一人。就像库巴斯以及他几乎所有重要的书中人物那样,马查多也可以同样夸口说:“我没有孩子,所以不可能把我们的痛苦传递下去。”
24
上面这句话其实是《库巴斯死后回忆》的结尾。我也想用它来结束本文。唯一让我三思的是:那部小说让马查多名垂青史,而我这篇文章连你的掌声都没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