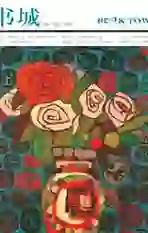在圣徒与恶魔之间
2016-12-01郁隽
郁隽
一、“无法想象的”极限选择
假设一个恐怖分子在城市里分别安置了核弹,核弹即将爆炸,几百万人可能死伤。你将如何对待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让恐怖分子说出核弹的位置,以便及时拆除它。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曾经在其广泛传播的公开课“论正义”(On Justice)中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美国影片《战略特勤组》(格雷格·乔丹执导,2010年上映)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将上述问题呈现在观众眼前。一个非典型的恐怖分子,白人、男性、美国公民、前特种部队的炸弹专家,名叫杨格(迈克尔·辛扮演),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优素福。他在美国的几个大城市里安放了几颗核弹,独自录制了“预告”视频后,站立在某大商场中等待被捕。此时距离设定的核弹爆炸时间还有四天。
联邦调查局将杨格关押在一个秘密审讯场所里,等待他的是两个人:海伦·布罗迪(凯莉·安妮·莫斯饰),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探;亨利·汉弗莱斯(塞缪尔·杰克逊扮演),绰号H,来历不明、深不可测的刑讯专家。亨利接手之后,一不做二不休,立刻用利斧砍下了杨格的一根手指,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海伦被亨利的做法震惊了,认为他侵犯了杨格的人权,是无法接受的。随着时间的推进,虽然亨利使用了各种酷刑手段—电击、拔手指甲,但是杨格丝毫没有打算吐露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此时,联邦调查局找到了杨格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如果你是负责刑讯的亨利,你会对他的妻子动手吗?影片中的情节更为让人震惊—亨利直接将她割喉。杨格目睹这一切痛不欲生,但依然没有说出核弹的位置。此时,亨利命令手下将杨格的两个孩子带进审讯室……假设你是亨利,你会对这两个无辜的孩子动手吗?
在影片中,当杨格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被带进来时,精神几近崩溃,歇斯底里地咒骂着亨利和所有人。他在说出了三颗核弹的安放位置之后,趁乱从看守手中夺过枪饮弹自尽。联邦调查局和军方根据杨格所说出的位置,的确找到了三颗核弹,并在引爆前都将之成功拆除。
这部电影中的很多场景的确像它的片名一样,是无法想象的(unthinkable)。它让人不仅目睹了血腥揪心的刑讯场面,还不得不将自己代入必须做出抉择的处境—做圣徒还是恶魔?人被逼到了道德选择的极限。
二、反恐与虐囚
二十一世纪最开始十年,在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反恐战争”。为了报复“九一一”事件中的恐怖主义行径,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美国以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绕开了联合国授权,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到四月中旬,美国宣布伊拉克战场上的主要战事结束。同年四月底五月初,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刊出了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的照片,随后不少美国媒体也陆续披露了几组虐囚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让人看了之后难以忘怀:一个全身赤裸的囚犯被黑布袋罩住了头。他站立在一个铁皮水桶上面,张开的双臂上连接着电线。根据报道,负责看管囚犯的美军士兵告诉囚犯,如果他从水桶上摔下来,就会被电死。虐囚事件中的大部分照片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在《战略特勤组》中,海伦和亨利进入秘密刑讯场所后看到的一个场面,非常类似上述那张照片。可以说,该片是对“反恐战争”和虐囚事件的直接反映和反思。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事件是关塔那摩拘留营。关塔那摩是美国在古巴的一个军事基地,也可以说是一块海外飞地。美国将反恐战争中抓获的重要囚犯转运到关塔那摩。由于反恐战争并非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战争,被俘人员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战俘”(prisoner of war,缩写为POW)定义。此外,因为关塔那摩不在美国本土,所以美国本土的一些法律不适用于该拘留营。换言之,这些前提都打破了人道对待战俘的底线,使得美国有关部门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些恐怖分子。十分讽刺的是,早在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就承诺当选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关闭关塔那摩拘留营。然而,奥巴马两届任期即将结束,它依然存在在那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关塔那摩拘留营已经创造了人类虐待人类的手法巅峰。网络上曾传出过所谓“CIA十大酷刑”,其中包括水刑、睡眠剥夺等。此外,为了防止囚犯自杀,美国人也想尽办法,使用了针对狂躁精神病人的拘束衣。而为了防止有人绝食自杀,则引入了“鼻饲”(即将营养液通过鼻腔直接注入食管)的方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一部美国电影《X射线营地》(Camp X-Ray,2014)来了解。
三、“坚硬的”头脑
今天我们的话题慢慢过渡到伦理学的领域,伦理学又称为“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是哲学学科当中一个很大的分支。如果不留意的话,我们经常会混淆两个词—伦理(ethic)和伦理学(ethics)。伦理是什么呢?它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人民生活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当然其中必定包括一些标准和规范—什么是对的、可以做的,什么是错的、应当被禁止。伦理学并不告诉你对具体事情的判断,而是对上述伦理准则的研究。换言之,我们不再简单地说什么天然是对的,而是要问为什么做某件事是对的或是错的。伦理学是对伦理和道德的研究、分析和反思。《战略特勤组》中展现的问题既是一种极端的伦理困境,它也促使我们思考伦理学问题。
道德哲学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分别对和错。在生物界当中占统治地位的似乎是弱肉强食原则;然而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原则,人要分别对错。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很难定义,但是当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情景或者语境下,就会发现自己的恻隐之心。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去。这时候不需要很多思考,你不大可能希望这个小孩掉到井里,而会不由自主地想救他。这是我们作为人的直觉反应。我们内心有这样一种冲动,不希望糟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周边的人身上—不管这个人自己认识还是不认识。这在伦理学上被称为“直觉主义”。
我们经常用一个比喻说,人的内心同时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天使战胜恶魔,人就行善;反之则作恶。但是这种直觉主义有一个问题,善恶对错是绝对的,也就是非常清楚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从直觉主义的角度来看,恐怖分子无疑是恶的,但要对无辜的儿童动用酷刑同样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似乎用直觉主义只能诉诸当下一瞬间的“感觉”,无法处理复杂的处境,似乎只会陷入两难的死胡同。
此外我们也发现,不少民族对同一件事情的道德判断,有时候是大相径庭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有些地方对婚外性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在另一些地方可能要对当事人处以“石刑”。即便是在一个小小的教室里,也并不是所有人的伦理准则都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当中成长起来,我们会天然地认为,我相信的伦理准则就是对的。换言之,我们认为绝对无误的伦理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自己以往教育、家庭和成长环境的重复和确认。所以说,我们的头脑是非常坚硬的—不仅对老师来说,好的东西不容易装进去,差的东西不容易拿出来,而且在道德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极少承认自己是错的,或者说我们天然地认为自己是对的,但其实除此之外别无理由。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要反思这种不证自明的“正确”。
道德哲学还要问何谓正义、何谓正当?这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在西方传统当中的正义女神,大概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她必定一手持剑—如果要声张正义,必须有强制性的惩罚手段;其次,她手里拿着一个天平—这意味着她要进行权衡比较,什么错得更多一点,什么错得更少一些;第三,她的双眼是蒙起来的—这表示她的一视同仁,无论谁站到她面前,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样的,绝对公正的,没有偏向。有时候正义女神还有第四个特征,就是脚踏一部法典,表示依法办事、有法可依。
四、“滑坡论证”场景
《战略特勤组》有很巧妙的编剧设定,我把它称为“滑坡论证”场景。在批判性思维中,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是一种典型的谬误论证,也就是一种无效论证,有些翻译为“斜坡论证”:假设有一个斜坡,斜坡顶端有一个静止的小球。此时,你只要稍稍给它一点推力,让它滚到斜坡上,受到重力的影响,它在斜坡上必定越滚越快,以至于到最后,什么东西都挡不住它。这个逻辑用在论证上是不成立的,但运用在电影中却是非常巧妙的。影片中编剧设计了一个“滑坡论证”场景:
一、一开始有一个大多数人通常能接受的场景(对恐怖分子用刑);
二、然后逐步升级,让人感到越来越难以接受(对恐怖分子的妻子用刑);
三、直到最后情感上几乎完全不能接受(对恐怖分子的孩子动刑)。
很多人在面对第一个问题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对恐怖分子施以酷刑;在面对是否要对恐怖分子的妻子动刑这个问题时,开始面露难色;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否要对恐怖分子的孩子动手,大部分人表示很难下手。这表明,一开始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理由,并不能在所有情况下一以贯之。当某些边界条件被打破之后,这些所谓的“理由”也就不能成立了。道德哲学就要追问,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应当、不言而喻的东西,其更深的理据或者更大的前提性假设和边界条件究竟是什么。
影片中有很多精彩对白。其中有一场是海伦和亨利两人之间的“狭路相逢”。海伦一直质疑对恐怖分子动用酷刑的合法性,而亨利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酷刑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从影片的铺陈来看,似乎亨利曾经经历过非常多极端残酷的事件。他也已经无数次地经历类似的无法想象的内心斗争。亨利对海伦说,是否要对杨格用刑,“并非关乎敌人,而是关乎我们”。道德哲学似乎也有类似的指向,它要求每个人将矛头转向自己,来直接拷问我们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诉求。
上世纪末生态领域曾经有一个“生态膜”的说法:地球表面的环境是如此之特殊,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稍近一点或稍远一点,地球上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了。要保持稳定生态环境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到道德领域:其实道德环境的边界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我们绝大部分人生活在相对正常的环境里,但是只要把边界条件稍微改变一点,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遵守道德。人和人可能就会进入狼与狼的关系。要倾覆这个天平是很容易的。海伦和她的上司之间有一段对白。海伦说,亨利对杨格的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而她的上司则回答说:如果核弹爆炸的话,就没有宪法了。接着影片提出的难题,我们需要一点勇气来问一下:我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以及我们的道德依据是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动作片,而我将《战略特勤组》这部影片看作一种“思想动作片”。
五、亨利:功利主义及其局限
西方的道德哲学大致有三种理论路径—后果论(consequentialism)、义务论(deontology)和德性论(virtue ethics)。和《战略特勤组》比较有关的是前面两种。而德性伦理学(例如亚里士多德)会提出人的一些基本的美德,例如诚实、节制、勇敢等,这些和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所以不展开讲。在我心目中,影片中的海伦和刑讯专家亨利分别代表了义务论和后果论。
什么是后果论和义务论,如何来区分两者呢?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判断你做出的一个行动是否道德,换言之要提出一些判断的标准。这里的一个基本图景是这样的:人之所以会做出一个行动,是出于人所理解的意图、诉求(应激性行为除外),同时它必定会造成一些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结果。后果论认为,判断一个行动是否道德,要看它造成的后果,无需去看它的出发点或动机;而义务论则认为,行动是不是道德,不能看它的后果,而要看它最初的意图是什么—动机善,行动就为善。
如果进一步来加以界定的话,影片中刑讯专家亨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个翻译已经约定俗成,好像略微有点贬义。因此有人建议将它翻译成更为中性的“效用主义”。古典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位: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边沁最主要的道德哲学著作是《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在他看来,人的最基本的本性的特征是“快乐主义”(hedonism)。当然这里的快乐是比较广义的,并不仅指身体的快乐,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边沁认为追求快乐是人天然的本性,换言之,人是趋利避害的。此外,他还反对天赋权利,反对一切先天的东西。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时毅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57页)
关于“功利”他是这样定义的:“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同上,第58页)基于上述的定义,边沁提出了其著名的“功利原则”:
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则,或简言之,符合功利。(同上,第59页)
而共同体利益指的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同上,第58页)。后人将边沁的这些原则归纳为“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原理:我应当如何行动呢?就是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简而言之,如果有两件事情,只能选一件,哪一件事情更应该做呢?如果A比B带来的幸福更大,按照边沁的原则,显然应当做A。这里还涉及一套幸福计算法:按照边沁的看法,痛苦是负的快乐—将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相加如果得出正数,意味着快乐,如果得出负数,意味着痛苦。这意味着自然引申出的结论—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可以牺牲个体的。
事实上,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已经不由自主地运用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在面对场景一时,我们的头脑中做了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如果核弹爆炸会造成一千万人死伤(痛苦),也就是负一千万;如果我们对一个恐怖分子施以酷刑,即便他死了,也仅仅是负一。一比一千万,其结论“不言自明”—要拷打恐怖分子,逼迫他说出核弹的下落。功利主义的好处在于简单明了,具有可操作性。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任何快乐和痛苦始终是相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的。影片中考虑问题的共同体是美国。如果改变了讨论的共同体,其幸福计算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完全贯彻边沁的原则,必然会导致影片中刑讯专家亨利的做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边沁的功利主义有一些隐含的前提性的假设:第一,人是自私自利的。这非常类似经济学当中理性人的假设。第二,等价原则,即所有人是同等重要的。简单地说,所有人他在幸福计算下取值都是一。换言之,人人价值平等,绝无尊长显贵。按照他这些前提性的预设,必然会导致一个结论:我们不仅应当毫不犹豫对恐怖分子动手,哪怕把他的妻子、小孩搭上,也只不过是负一千万比负三、负四—孰轻孰重,哪个造成的痛苦更大,哪个带来的快乐更大,似乎是道很简单的算术题。而要进行边沁式的道德判断,是无涉行动者的(agent-neutral),即与任何行动者的判断与视角都无关,好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上帝,可以轻易地计算。
边沁的这些前提性假设是可以被质疑的。首先,人只追求幸福(快乐)吗?如何解释很多人愿意自我牺牲,成全别人?如何看待人的利他行为?其次,人都是等价的吗?等价原则看上去很崇高,在那个时代有其意义。因为在当时主要的看法是人不等价,帝王将相高于平民百姓。所以边沁反对给某些特权阶层赋予太高的价值。但是,如果扪心自问,我们真的认为人是等价的吗?我们的直觉判断似乎不总是这样。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份最新的实验药物,它可以给瘫痪在轮椅上的天才物理学家霍金用,也可以给一个普通的人用。你会如何选择?好像直觉告诉我们,应该给霍金用。也就是说,我们隐隐感觉霍金的生命比一般人更重要,更有价值。在涉及亲人、家人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接受等价原则。此外“可以牺牲个体”的原则会导致荒谬的结局。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杀死一个健康的人,将其器官移植到七八个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身上,这样就可以用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七八个人。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是可以这样做的,但实际上这就是谋杀。
对边沁的几个前提进行集中质疑,可以观看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它表面上是一部战争片、动作片。二战当中,有一个家庭的五个儿子都去当兵。不幸的是,前面四兄弟全部战死。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签发了一道特殊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家仅存的儿子(大兵瑞恩)从德军战线之后救出来。为此,美军派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然而,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很多人。我们不禁要问,人真的是等价的吗?如果我们把边沁的那些前提性假设逐一否定掉,那么边沁的幸福计算法就没法计算了,他追求的最大幸福的原则也是没有办法贯彻的了。
六、海伦:义务论及其局限
今天我将康德作为义务论的代表,他写了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绕不开的一座高峰。其义务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1785)一书中。
康德首先区分了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他认为真正的道德律令必须是定言的。假言是有条件的:如果怎样,我就怎样。但定言是无条件的,不能因为语境变化而改变。例如说不能骗人,就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骗人。一旦说我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骗人的,这就变成了假言,就是有条件的,很容易导致人人都找借口,于是任何道德都没有办法得到贯彻了。但定言命题也会遇到问题,后来法国哲学家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批评康德,指出坚持定言命令会背离道德的初衷:例如二战中有一个游击队队员抵抗纳粹。他逃到你家里,而纳粹也追到了你家门口:请问,是不是有一个游击队员在你家里?按照康德的定言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撒谎,即便面对纳粹也要如实相告。萨特会说,康德你不是在害人吗,难道仅仅是为了坚持定言命令,就要出卖游击队员吗?
但是我们要反过来问,康德为什么持义务论的观点。功利主义是很明确很典型的后果论,但是对义务论而言,判断一个事情道德还是不道德,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不应该看它所造成的后果,而要看它的动机和初衷。
善的意志并不因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它适宜于达到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为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自身而言就是善。……它也像一颗宝石那样,作为在自身就具有其全部价值的东西,独自就闪耀光芒。(《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第401页)
康德进而提出了“绝对命令”的原则:“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同上,第428页)也就是说,判断是否道德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可以被普遍化。我这样做没有问题,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做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就是道德的。由这条绝对命令,他推出三条派生命令。第一条:“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同上,第429页)第二条:“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当作手段来使用。”(同上,第437页)第三条:“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意志……必须被视为自己立法的。”(同上,第439页)
第二条派生命令被称为“人性命令”—可以表述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按照康德的看法,在影片中刑讯专家亨利的做法,直接违背了这个原则,是不道德的。因为无论亨利对杨格下手,还是对他的妻儿下手,都把他们当作了手段。其目的是要拯救其他的人。这在康德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运用其普遍律令法则,如果所有人都把其他人当作手段的话,社会就会崩塌。“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本身是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求所有人在和别人的交往当中,都把别人当作目的本身,不要把人当成手段。
此外,当我们想要通过拷问杨格、逼迫其妻儿,来达成救人之目的时,可以说我们已经被恐怖分子绑架。此时,我们自己的道德底线已经被他拉低。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加害无辜的人来达成目的,那么我们和恐怖分子有区别吗?站在康德主义的立场来说,我要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对杨格动手。可以说在影片中,女干探海伦·布罗迪是一个典型的康德式义务论者。所以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亨利对杨格动用酷刑。当杨格的孩子被带到刑讯室内后,她说:你不能这么做,我们是人啊!让炸弹爆炸吧!我们不能这么做!她道出了一个底线,如果我们做了,就不是人了。换言之,不对无辜的孩子动手,是她作为人最基础的要求。康德式论证说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你打破了某条底线,就不能再称为人了。但是,我们又会发现这样的康德式义务论做法,在实践中很难坚持下去。
七、黑色结局的隐喻
上面我进行了一种过于简单化、脸谱化的对号入座—把亨利理解为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将海伦作为康德式义务论的代表。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从心里厌恶亨利,会认为他手段毒辣,没有底线。但这其实并不是一场正邪之战。亨利不是简单地代表邪恶一面,海伦也不简单地代表正义那一面。或者没有人是单纯的圣徒。人很容易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之后,还来承担道德责任。亨利与海伦的对立是边沁和康德之战。究竟谁是圣徒,谁是恶魔?我假设我们顺着海伦的方式继续下去,听任核弹爆炸,而对恐怖分子无所作为,其结果是一千万人死伤。难道这就可以全部归罪于杨格一个人吗?可能在影片中表现更为卑鄙的是那个没有名字的白宫官员。他时刻在逼迫亨利进行更为残酷的刑讯,却不愿意脏了自己的手。但他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在执行以总统为代表的国家意志。这似乎是对现代国家和官僚制度的讽刺。要看到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行事的,因为国家面对的是无数的抽象个人,而不是少数的具体个人。如果落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似乎对我们来说,功利主义是一种默认设定,是理所应当、不言而喻的,而康德式的义务论太少了。
必须看到,义务论和后果论这两种道德哲学的立场是很难相互通约的,也就是说一种立场没有办法转换为另外一种,它们的基本的假设和立场截然不同。但是同时,每一种道德哲学的基本假设都是可以被挑战、被打破的。杨格仅仅是一个恐怖分子吗?这似乎也过于脸谱化。在当今社会中,说某人是恐怖分子,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消灭他。然而,编剧和导演也在暗示我们,杨格是一个非典型的恐怖分子: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或更高的道义。可能在大多数人眼中,杨格是个疯子。因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甚至他已经准备好牺牲他妻子和孩子。从一开始,他就已经设定了一条“无法想象的”底线—因为他知道政府会步步逼近,直到最后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现代政治哲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国家垄断了暴力,并且具有运用暴力的正当性。正义女神之所以持剑执法,是基于一个很简单的人性预设—人是怕死的。这几乎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默认前提。然而现代的恐怖主义语境打破了这一前提。
这个影片又让我们回过来反思所谓恐怖主义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理解”(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verstehen)恐怖分子的行为,而是采取了面具化和病理式的说明。所谓理解,并不是同情,而是要尝试分析一个人成为恐怖分子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使得一些人—他们原初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不再惧怕死亡,愿意牺牲自己。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极为不对称的理解。在我们整个价值排序当中,绝大部分人是将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即认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但这并不能排除,有极少数人将其他的价值放到了生命之前。
在影片的结尾处,在杨格透露的三颗核弹之外,还有第四颗核弹。这颗核弹引爆装置倒计时归零,影片也就此戛然而止。《战略特勤组》的结局非常黑暗,充满隐喻,让人倒吸一口冷气。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理论,并不是轻飘飘的支持、赞成、反对可以涵盖的。因为道德判断,必然同时意味着有人要承担该道德判断的一切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后果,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我个人是非常反对道德相对论的,因为再往前跨一步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这对任何社会都很危险。但其实,道德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个人的逃避—没有对没有错,但人还是要作判断,还是不得不做出行动。即便你尝试逃避这些问题,其实并不能真正回避问题。这样的电影的作用不仅仅是让我们三观崩塌,或者让我们面临道德危机,而是要让我们夯实道德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判断,哪些前提对你来说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你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最后我想说,在道德哲学中一个原则通常表述为一个命题,你可以表示接受或反对。但它在现实生活当中却需要一个具体的判断和行动。在命题和行动之间永远存在一条鸿沟。仅仅依靠明辨事理是不足以跨越这条鸿沟的,最终还需要勇气和责任感。任何一种道德,也必定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代价。没有无代价的道德。对人而言,归根到底要回答的问题是to be or not to be。
本文为作者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在季风书园“人文讲堂”第一期“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感谢季风书园“人文讲堂”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