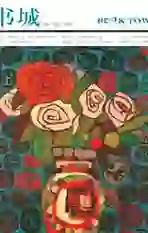一件晚清涉外社交信函
2016-12-01燕宏博
燕宏博
一
近日,从英国网络书商得到一件英文信函,颇有些意外之喜。
这封信写在专用笺纸上,红色的笺头印有英文“CHINESE LEGATION, 49, PORTLAND PLACE, LONDON, W.”,意即“伦敦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公使馆”。信函正文用斯宾塞体英文书写,经朋友吴杰先生和Jason Halprin先生帮助,依照手迹释读原信。
18th June 1884
Dear Miss Portman:
I write to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the 16th instant and to say that I and my family have now come to town. I regret however to state that owing to previous engagements, I shall not have the pleasure of being present at the party of Mrs Lewis on the 24th instant. I shall be obliged to you if you will kindly thank her on my behalf for her kind invitation.
With kind regards in which all my family join, to you and compliments to Mrs Lewis and Miss Chapman,
I remain yours sincerely,
淑懿L. Tseng
据Jason Halprin先生说,此信是古典英文。经他帮助,试译如下:
亲爱的波德曼小姐:
专呈此函,谢您本月十六日来信,并告您我与家人现已回城。非常遗憾,因早先有约,我无法出席路易斯太太本月二十四日宴会。若您愿意,请代我谢她盛情邀请。
我和家人向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向路易斯太太和查普曼小姐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您最真诚的
淑懿 L.Tseng
乍看这封短笺,内容很普通,无非告诉收信人不能参加一个聚会而已,并未透露特别有价值的信息。但综合各方面资料,笔者认为这封普通的信笺却承载着某些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
先说写信人。
落款署名“淑懿L. Tseng”,此人未见任何记载。据我推测,此人应是晚清著名外交家曾纪泽的夫人。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晚清名臣曾国藩次子,袭父一等毅勇侯,故称曾侯。他一八七六年出使英法,稍后兼使俄国,驻欧达八年。曾纪泽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虎口夺食,收回了被沙皇俄国占领的部分领土。著名学者萧一山在《清史大纲》中称:“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英国驻俄大使称赞他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他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台湾学者李恩涵在《曾纪泽的外交》中说:“……自以光绪六七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最为人艳称。他挽救了一次迫在眉睫的中俄战争,并以较少的代价,索还了已经丧失的部分要地。”湖湘学者钟叔河说:“虽说‘弱国无外交,但是曾氏以他精明干练的才力,在出使期间还是替国家捍卫了权益。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同沙皇俄国重开谈判,收回了伊犁和帖克斯川大平原。……这在近代清代外交史上,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曾纪泽驻欧期间,其夫人积极参与他的外交、社交事务。曾夫人系曾国藩密友、陕西巡抚、桐城派散文家刘蓉之女,一八五八年由彭玉麟、唐义渠为媒,成为曾纪泽继室。一八七六年,曾纪泽出使英法,曾夫人随行。由于曾纪泽身为外交使节,在欧期间往来拜会极其频繁。曾夫人出于礼节,频繁接见、拜谒英法达官贵人内眷。据吕海寰撰《刘侯太夫人墓志铭》:“居海八九年,博识多闻,谙习语言文字,燕见各国君后,受旨进退无紊于仪容,间出议论以佐惠敏(曾纪泽谥号)所不逮。西人皆称之益知。”由于曾夫人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以至到达英国的第二年,曾纪泽在寓所二楼特别布置了“女客厅”,专门用于会见女客。曾夫人在欧活动,据台湾学者林维红《面对西方文化的中国女性:从〈曾纪泽日记〉看曾氏妇女在欧洲》概括,大致包括“一般拜谒、茶会、外交礼仪、就医、其他社交活动五大类”。但这些活动,《曾纪泽日记》(以下称《日记》)记载极为简略,基本是一些流水账式记录,如:“日本公使之夫人来拜内人,传语良久”“达尔毕格立斐次夫人暨阿尔福夫人来谒内人,传语良久”“携内人、仲妹出门拜客,阿尔福家、达尔毕格立斐次家、金登干之夫人家、诸盘生之夫人家,各久坐”“申初,偕内人、仲妹拜沙尔芒之夫人;申正,拜罗林荪之夫人;酉初,拜安白尔之妻”“女客来,与内人、女儿陪谈极久”,等等,既没有会见谈话的内容,更没有细节上的敷陈。
不过在曾朴《孽海花》的“小说家言”中,留下了曾夫人外交活动的传神描述:“当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国,那时英国刚刚起了个什么叫作 ‘手工赛会。这会原是英国上流妇女集合的,凡有妇女亲手制造的物件,荟萃在一处,叫人批评比赛,好的就把金钱投下,算个赏彩。到散会时,把投的金钱,大家比较,谁的金钱多,系谁是第一。却说这个侯夫人,当时结交很广,这会开的时候,英国外交部送来一角公函,请夫人赴会。曾侯便问夫人:‘赴会不赴会?夫人道:‘为什么不赴?你复函答应便了。曾侯道:‘这不可胡闹。我们没有东西可赛,不要事到临头,拿不出手,被人耻笑,反伤国体!夫人笑道:‘你别管,我自有道理。曾侯拗不过,只好回书答应。……看看会期已到,你想曾侯心中干急不干急呢?哪晓得夫人越做得没事人儿一样。这日正是开会的第一日,曾侯清早起来,却不见了夫人,知道已经赴会去了,连忙坐了马车,赶到会场,只见会场中人山人海,异常热闹。场上陈列着有锦绣的,有金银的,五光十色,目眩神迷,顿时吓得出神。四处找他夫人,一时慌了,竟找不着。只听得一片喝彩声、拍掌声,从会场门首第一个桌子边发出。回头一看,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边一把矮椅上,桌上却摆着十几个康熙五彩的鸡缸杯,几把紫砂的龚春名壶,壶中满贮着无锡惠山的第一名泉,泉中沉着几撮武夷山的香茗,一种幽雅的古色,映着陆离的异彩,直射眼帘;一股清俊的香味,趁着氤氤的和风,直透鼻官。许多碧眼紫髯的伟男、鬈发蜂腰的仕女,正是摩肩如云、挥汗成雨的时候,烦渴得了不得。忽然一滴杨枝水,劈头洒将来,正如仙露明珠,琼浆玉液,哪一个不欢喜赞叹!顿时抛掷金钱,如雨点一般。直到会散,把金钱汇算起来,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数。曾侯那时的得意可想而知,觉脸上添了无数的光彩。”
遗憾的是,这位光彩照人的时代女性,其姓名却成为历史的缺失。谢琰、谭剑翔在《曾侯刘太夫人小传》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氏病逝,诰封一品侯太夫人。一代名媛悄然逝去,淹没在历史的灰烬中,她的才学和美好德行操守堪为女性楷模,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却没有留下一个完整的名字供后人凭吊。”笔者略翻《日记》《曾纪泽遗集》《曾国藩日记》《曾国藩书信》《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年谱》《养晦堂文集》《曾国荃年谱》《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诸书,但均未有所获。后读潘德利、王宇著《曾纪泽年谱》,提及曾夫人名刘鉴,字慧淑。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名、字与曾国荃次子曾纪官的夫人刘鉴(字惠叔,著有《曾氏女训》《分绿窗诗文集》)名字均太过相似,似为误植。向潘、王两位老师求教,但两位作者早已不再研究此课题,也忘记相关资料具体出处,只能存疑待考。
回到这封信,笔者判断写信人是曾纪泽夫人,主要是通过综合考辨,剥茧抽丝得出的结论,具体论证过程如下:
第一、写信人是曾姓人士。曾纪泽在欧期间,对外署名一般为“Tseng”或“Marquis Tseng”(Marquis乃侯爵之意译)。如一八八七年寄英国法学家莱昂内·利瓦伊(Leone Levi)函署名Tseng;发表英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署名为Marquis Tseng;吾友崔建先生藏有一件曾纪泽签名卡片,签名为“毅勇嗣侯曾”及英文“Tseng”。这封信英文署名为“L. Tseng”,对照曾纪泽英文署名和签名,可以确定此信写信人是曾姓人士,且非曾纪泽。
第二、写信人是曾纪泽家眷。信函写在中国公使馆专用信笺上,当时使用此信笺之人,只能是曾纪泽、曾纪泽家人、曾纪泽僚属(参赞、翻译)等相关人员。既然此函署名为曾姓,且非曾纪泽本人,那只能是曾纪泽在欧家眷。
第三、写信人是曾纪泽夫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曾纪泽在欧家眷只有曾夫人未留下名字。曾纪泽在欧家眷,包括曾夫人刘氏,一直随伺在欧;仲妹曾纪曜,一八七八年与夫陈松生(二等参赞)随曾纪泽赴欧,一八八一年在巴黎去世;长女曾广璇,又名福秀,字幼卿,一八八二年随夫李经馥赴欧与曾纪泽团聚;次女曾广珣,又名宝秀,时年十八;嗣子曾广铨,字敬贻,时年十三;长子曾广銮,字君和,时年十一;幼子曾广钖,生于欧洲,时年五岁。上述诸人,曾纪泽三子皆有名字,且年幼,未独立参与社交,可排除。曾夫人、广璇、广珣皆可能为写信人。然而,广璇、广珣皆有名字,似不应再有另外署名。二是,这封信英文署名与曾夫人合,与广璇、广珣不合。信函英文署名是“L.Tseng”,其中“L.”显系某中国姓或名的英文简写。曾夫人娘家姓刘,如有正式名字,即称曾刘××;如名字缺失,则应称曾刘氏。刘姓按当时拼音为Liu或Lieu,“曾刘”用当时拼音书写则为Liu Tseng或Lieu Tseng,简写为“L. Tseng”。同理,若写信人为广璇,英文署名为娘家姓加夫家姓,即Tseng Li,简写应为“T. Li”;广珣未适人,英文署名应为Miss Tseng,无简写。三是,这封信所述事实与曾夫人合。此信写于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国纪年为光绪十年五月廿五,据《日记》光绪十年五月记述,曾纪泽初三日,回到海滨小镇福克斯通寓所,“与内人、女儿一谈”;十六日,“回到伦敦使署”,“写一函寄内人”;廿一日,到火车站接夫人到使署,“申正,至车棂克罗斯车栈迎内人,酉初到署”。这与信中所述“我与家人已回城(指从福克斯通回伦敦)”正相合。四是,这封信收信人与曾夫人不久前有交往。据《日记》光绪十年二月初三日:“波德蛮姑娘、柏尔斯太太先后来谒内人。”此函收信人“Miss Portman”,译为中文正是波德蛮姑娘(笔者译为波德曼小姐)。至于这位波德蛮姑娘,曾纪泽日记中只有这一处提及,故身份、地位不得而知。
综上,这封信写信人应为曾纪泽夫人。由此也解决了曾夫人名字缺失的问题。按此函署名,其名字应为“刘淑懿”。当然,这个名字未必为曾夫人本来就有,也可能是曾纪泽为方便夫人在欧生活交往,专门给夫人起的一个名字。
此函虽以曾夫人名义写,似由曾纪泽代笔。理由有二。一是曾纪泽多次代夫人写信。据《日记》光绪七年七月初一:“为内人写一函答日本公使夫人。”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为内人加写一函寄黄子寿之母,影相数幅。”光绪十年正月初三:“为内人写一函致达尔毕格里飞太太。”正月廿九日:“代内人写一函致费兹结罗太太,谢网巾。”二是这封信英文笔迹与曾纪泽寄莱昂内·利瓦伊信函英文笔迹相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三
其次,谈一谈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除了收信人波德蛮小姐,还提到两个人:路易斯太太和查普曼小姐。其中,查普曼小姐的身份已不可考。至于路易斯太太,应是福克斯通当地医生路易斯的夫人。
光绪九年八月,曾纪泽一家搬至福克斯通别墅居住,至次年五月离开。其间,曾纪泽常常赴伦敦、巴黎公干,曾纪泽夫人、子女则基本居留福克斯通生活。福克斯通是海滨胜地,英国官员多在此期间赴福克斯通度假。因此,曾纪泽一家与在此度假、生活的英国官绅交往相当广泛。据《日记》光绪九年八月十六日:“申初,偕内人率次女拜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之夫人。”九月十三日:“申初,偕内人率次女至本城公廨,受绅民颂词,又答词谢之。”九月十五日:“未初二刻,偕内人率次女往外部丞相格兰斐别墅。内人在格相夫人处坐谈。余与格相至别厅,谈公务良久。”九月十七日:“偕内人拜福克师登府尹夫人。一谈。”九月廿三日:“饭后,偕内人率次女拜客,播尔师夫人、梭尔特夫人、配登夫人、费子解拉尔夫人处入谈,余投刺,申正二刻归。”由此,曾夫人也结识了不少贵妇人。据《日记》九月廿日:“未正,女客来谒内人者十人,先后陪谈。”十月初四日:“女客十人来谒者十人,陪谈甚久。”十月十一日:“申初,女客来谒内人者约廿人,陪谈极久。”
路易斯一家应是此期间与曾纪泽一家有交往的。交往之始,应是曾纪泽请路易斯医生给曾广钖看病。据《日记》光绪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医士路易斯来诊钖儿。”三十日:“医士路易斯来,一谈。”之后,两个家庭交往逐渐深入,以至于曾纪泽女儿与路易斯女儿也结交了友谊。据《日记》光绪十年正月十四日:“路易斯姑娘来拜璇女,陪谈良久。”十九日:“酉正一刻,偕内人率两女陪费兹结罗太太母女、柏尔斯太太并两女及路易斯姑娘便饭。”二十一日:“申初,偕内人率璇女至柏尔斯太太家,留女儿与主人坐谈,余与内人至新宅看屋。拜勒塞尔太太,不晤。复至柏尔斯太太家久坐。拜路易斯太太,一谈。”廿九日:“听闺秀路易斯、二力师姊妹弹琴。”三月廿三日:“与两女在客厅陪闺秀路易斯姊妹一谈。”
信中说曾夫人不能参加路易斯太太举办的宴会,原因是“早先有约”。据当日(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记》:“巳正起,茶食后,阅广东寄来函牍。写行书屏两幅,共八幅。至客厅抚视钖儿。饭后,写楷书、行书屏各四幅。抚视钖儿。医士马克勒衣来诊钖儿,陪谈甚久。听女儿奏乐。饭后,写对联四副。至松生室一坐。观仆从安置座后屏风。写零字。入上房一坐。夜饭后,小坐。亥正一刻,偕清臣赴法国驻英公使瓦定敦茶会,又赴伯爵爱楞不拉茶会。子正归,丑初睡。”“早先有约”可能指“法国驻英公使瓦定敦茶会”,“伯爵爱楞不拉茶会”,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另外两点:一是可能曾广钖生病,母亲爱护幼儿,无心前往赴宴;二是曾夫人不便从伦敦单独乘火车前往福克斯通。
四
最后,谈谈这件信函的价值。
个人认为,这件信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证物。
中国走向世界,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的,是被迫的历史进程。在“被开放”过程中,虽然有屈辱、有失落、有阵痛,但也促动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之初,中国从不适应到适应,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当时囿于传统,中国女性基本不参与社会交往,更不可能参与对外交往。因此,少数先行者成为异类,更不能为国内习俗所接受。姜鸣先生《社交季的新客人》一文,讲述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伦敦举办一次招待会,因其如夫人梁氏参加,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曾纪泽是郭嵩焘的继任,当时的社会风气其实是一样的。国内对女性参与对外社会交往,未必会多宽容到哪里。曾朴的小说家言虽然光彩夺目,但毕竟是小说家言,况且小说发表时距离曾纪泽出使英法已过了近二十年,社会风气已有很大变化。因此,曾夫人频繁参与欧洲的社会交往,是中国女性真正意义上登上对外交流的舞台,标志着中国思想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中国外交史、社会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先行者”总有其局限性,在曾夫人身上就是其对外交流不具有“主体性”。林维红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中国女性:从〈曾纪泽日记〉看曾氏妇女在欧洲》中认为:《曾纪泽日记》的局限是“没有女性自己的声音”。她说:“这些女眷除了二妹纪曜,没有留下自己的片言只字……女眷自己可能有的一些活动,即使与接触西方社会文化有关,但如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日记里。……尤其遗憾的是因为曾纪泽出门在外,其妻女反而可能有了独立自主活动的机会。没有这部分的信息,实在可惜。”这其实不是《日记》的问题,而是人的选择不能超越当时社会发展状况。事实上,曾纪泽逝世后,曾夫人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即便如此,曾夫人其实也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如《日记》所记,曾纪泽代夫人所写的数件信函,严格来讲,就是曾夫人作为主体发出的“声音”。但由于致日本公使夫人、达尔毕格里飞太太、费兹结罗太太等信函已不知所踪,这些“女性自己的声音”也就消逝在历史长河中,致使曾氏妻女“没有留下自己的片言只字”。如今这件信函的面世,彻底改变了这一历史,弥补了“没有女性自己的声音”这个遗憾,更见证了中国近代女性作为主体,登上对外交流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