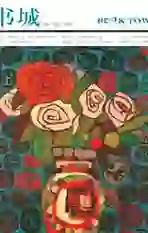江南的早期城市化
2016-12-01樊树志
樊树志
城市古已有之,中国亦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把中国城市发展划分为三个大阶段。从城市兴起到宋朝是第一阶段,从宋朝到十九世纪中叶是第二阶段,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第三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近代化工业逐渐兴起,再加上政治不安定,迫使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涌现出一批新型城市。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从人口密度、劳动分工、技术运用、商业化和地区内部贸易、地区间贸易、行政等方面,探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城市化,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城市化。
可见,当代官方与民间既兴奋又诟病的城市化问题早已有之,并非现今时代所特有,当然也并非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就是当时城市化的浓缩写真。这一切,与宋朝的商业革命密切相关。
费正清与赖肖尔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说: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这种对历史解读的方式,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言之有据。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一个棋盘状的封闭结构,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由围墙封闭的居民区—“坊”,商业活动在封闭的“坊”内进行,这就是著名的“东市”“西市”。宋朝的东京,把这种封闭结构打破了。这是划时代的变革,它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是无可估量的。它适应了商业革命的趋势,把商业活动从封闭的“坊”“市”中解放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沿线,形成了近代都市商业街的雏形,为都市商业拓展了新空间,也为都市增添了繁华的商业气息与市井色彩。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观:政府宣布取消关于夜市的禁令,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限制,开封城内十字大街有所谓“鬼市”—通宵达旦的商业街;马行街至新封丘门大街,夜市营业到三更,五更时分新的一天的营业重新开张;至于“耍弄去处”(娱乐场所),营业“通宵不绝”。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西方学者把它看作中国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标志。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杭州,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都城,与以往都城的方正结构截然不同:皇宫位于城市的南端,不再有坐北朝南的架势,具有浓厚的商业市井色彩。从皇宫北面的和宁门向北通往城市中心的是一条用石板铺成的南北向御街,与东西向的荐桥街、三桥街相交,与后市街平行;东面又有贯穿全城的市河、盐桥运河,由此形成了以御街为中心的繁华的商业街区。正如《梦粱录》所说:“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御街中段的街市最为热闹,有名的闹市如清河坊、官巷口、众安桥等,店铺密布,人群熙攘。《都城纪胜》说:“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这样的盛景,不独令古人神往,也令今人叹为观止。
黄敬斌先生的新作《郡邑之盛:明清江南治所城市研究》,用非常丰富而细致的史料、珍贵而罕见的地图和图片,为我们描绘了明清两代江南的城市化图景。我把它称为江南的早期城市化,是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相对应的。
二○○○年,李伯重教授出版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他的结论是:一八五○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十九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他写道:“早期工业化在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成为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并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创造了许多必要的条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与此相当的是明清工业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在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国外关于‘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屡被涉及,并在一些具体部门(特别是纺织业)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许多‘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学者也因而认为中国已出现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工场手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致伊懋可(Mark Elvin)怀疑明清中国的农村是否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这些都使人相信在明清中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也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特别对“早期工业化”作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用这样的视角来审视黄敬斌所研究的“江南治所城市”,也许是别有意味的。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一共四章:第一章,“规划情结”与“城墙视角”—中国城市形态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第二章,江南治所城市的地理形态;第三章,生产与贸易—江南治所城市的经济职能;第四章,近代江南的市场层级与城镇体系—以嘉兴、湖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每一章都以丰富多彩的史料为依据,进行缜密地分析,提出与前人迥然有别的观点,使人信服,发人深省。
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论述的“规划情结”与“有机生长”,是有感而发的。当前一些地方官把城市化作为政绩来追求,热衷于“规划情结”,企图用规划来“造城”,造了一些“死城”“睡城”。症结就在于,他们无视城市化的规律,不懂得城市发展的历史,忽略了城市“有机生长”的道理。因此,我建议有志于城市化的地方官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本书。倘使诸位公务繁忙,无暇细读这本五十余万字的大书,在下愿意导读,把该书的精彩之处,略选若干,以飨诸公。请看:
与典型的规划城市相比,有机生长城市在明清江南占有更大的比重。这些城市的外部地理形态在整体上系长期自然发展的结果。少见礼制、风水或其他象征主义因素的影响,城区缺乏规划,城墙与街区的总体形态不规整,主要街道基本上沿自然河道生长,官方建筑的选址即使在城墙内部而言也多不具有方位上的趋同性和礼制色彩,就整个城区而言更是如此。在前文讨论过的三十五座城市中,可视作有机生长城市的有吴江、常熟、昆山、松江、上海、青浦、金山(朱泾镇)、太仓、嘉定、常州、无锡、江阴、靖江、嘉兴、嘉善、海盐、平湖、崇德、桐乡、湖州、德清、武康、杭州、海宁、余杭,数量上占了三分之二强。
江南地处三角洲水网地带,自然地理环境无疑是形塑上述城市形态特点的决定性因素。在河网密布的地区,传统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高度依赖水运,主要的通航河道具有交通干线的地位,城市街区和村庄聚落沿河建造,并形成线形长街,符合交通、商业及生活便利的原则。相反,不顾水道走向及水系形态实施理想化的“礼制规划”,则意味着较高的工程成本。
无论在哪一种形态下,沿河道生长的线形街道都是构筑城市建成区的基本要素。在水系简单的条件下,街区的线形特征表现突出,在复杂水系条件下,则容易形成成片的团状街区。凡此均与此前的研究中对于江南市镇地理形态的观察无大差异。实际上,明清江南的治所城市中,相当数量正是从市镇发展而来,如上海、太仓、嘉定、金山、嘉善、平湖、桐乡等地,有明确的史料证明在设治以前已有繁盛的聚落和商业街区。
明清时期设治的县城,其聚落发展的早期历史比较清晰:青浦、嘉善、平湖、桐乡都是在“力量雄厚的集镇”设置县治;金山、奉贤、南汇、宝山明初置有卫所,雍正年间设为县治,但其中至少金山、青村在成为军事驻地之前可能已经发展出非农聚落,金山县城并且旋即迁至著名市镇朱泾;崇明、靖江县城最大的可能是置于农业聚落。唐、宋、元时期初次成为治所的城市中,上海、太仓、嘉定、崇德在设治前或已经是繁荣的沿海贸易港口,或已是重要的内地商业市镇;吴江、华亭、嘉兴、德清、长兴等地在设治(或迁址)之前,很可能已有居民聚落,而且已不是普通村庄。
朱泾镇成为金山县的治所(县城),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该镇在明朝属于松江府华亭县,顺治十三年(1656)由华亭县析置娄县,朱泾镇改归娄县;雍正二年(1724)分置金山县,朱泾镇改归金山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金山县的县治从金山卫移至朱泾镇,从此朱泾镇成为金山县政府的所在地,升格为县城(但朱泾镇作为一个建制镇依旧保留至今)。这是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
元末明初,随着经济的繁荣,朱泾这个地方迅速发展成为市镇。洪武六年(1373)在此建立税课局,是一个显著的标志。成化、弘治年间,朱泾镇俨然巨镇气象,号称“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置邮走两浙、达两京者不少辍,实为要津”。万历年间松江经济日趋发达,朱泾镇进入鼎盛时代。朱泾镇街市长约三里,东至周家埭,西至秀洲塘,南至漩子泾,北至小泖港。朱泾镇东南的吕巷市、杨巷市,与朱泾镇构成一体,成为发达的棉纺织业中心,号称“朱泾锭子吕巷车”,所谓“锭子”者,指朱泾镇的纺纱织布所需的纱锭;所谓“车”者,指吕巷市的纺车业。从明朝以来,朱泾镇就是著名的标布(优质棉布)的生产贸易中心,镇上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布商云集,交易额动辄白银数万两。清人赵慎徽有诗称颂朱泾镇的繁华景象:
万家烟火似都城,
元室曾经置大盈,
估客往来多满载,
至今人号小临清。
其自注云:“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
所谓估客,即各地前来采购标布的布商,也称客商;所谓小临清,意为可以和山东运河沿线商业城市临清相媲美;所谓标行,即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布商字号有数百家之多,盛况可见一斑。乾隆《金山县志》说:朱泾镇“烟火稠密,商贾辐辏,有城市气象”。乾隆二十五年(1760)把金山县治迁移到朱泾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它具备“城市气象”在先,成为“治所城市”在后。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治所城市”的“有机生长”过程。
现今以旅游观光、怀旧文化、戏剧音乐闻名遐迩的乌镇,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乌镇,明清时代称为乌青镇,由相隔一河的乌镇与青镇构成。乌镇属于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于嘉兴府桐乡县,隔河相望,近在咫尺,所以当地人习惯于合称为乌青镇。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奇特,介于江浙二省,湖州、苏州、嘉兴三府之间,二镇的四栅八隅又为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六县错壤之地,交通便捷,物流顺畅,百货骈集。它的历史悠久,大约兴起于南宋淳熙(1174-1189)、嘉定(1208-1224)年间,到明朝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5)年间,日趋繁荣昌盛。嘉靖十七年(1538),地方官鉴于乌青镇经济繁荣、地位重要,请求朝廷批准在此建立县治(亦即“治所城市”)。地方官给朝廷的《请分立县治疏》写道:“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富所出甲于一郡”;“乌程、归安、桐乡、秀水、崇德、吴江等六县辐辏,四通八达之地”;“本镇地厚土沃,风气凝结,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阛阓,不烦蚊改拓,宛然府城气象”。
“宛然府城气象”六个字,写尽了乌青镇的“有机生长”,已经具备了湖州府城或嘉兴府城的架势,在此建立县治是绰绰有余的。令人遗憾的是,朝廷没有批准这一合理的请求。
到了万历时代,乌青镇充分发挥蚕桑丝织支柱产业的优势,一举成为居民万户、万商云集的超级大镇。全镇有东街、西街、龚庆坊、积善坊等几条大街,另有街巷五十八条。乌镇东街至北栅有十三条街巷,乌镇西街从安利桥至西栅有十三条街巷,乌镇龚庆坊有十条街巷,乌镇积善坊有八条街巷,青镇从南栅至北栅、东栅有十四条街巷,可谓星罗棋布,密如蛛网,远非今日乌镇可以比拟。细观内部,更有令人惊讶的信息,例如:“波斯巷旧名南瓦子”,万历三年“辟为大街”;北瓦子巷原先是“妓馆戏剧上紧之处”;又如“沈侍郎百花庄”“顾尚书花园”“乌将军庙”“监镇衙前”等,都饱含丰富的历史内容。这些陈迹,在如今已经高度商业化的乌镇,早已无从寻觅,所以值得一提。
入清以后,乌青镇继续蓬勃发展,规模日趋扩大,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共有四个门坊(类似于城门):
南昌门—青镇之南门,通杭州;
澄江门—乌镇之北门,通苏州;
朝宗门—青镇之东门,通嘉兴;
通霅门—乌镇之西门,通湖州。
所以当时人说,乌青镇“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到了清末民初,街市又进一步拓展,乌镇有常春里大街、澄江里大街、通霅里大街,青镇有南大街、中大街、北大街、观前街、东大街。此外还有一些商业街区,如嵇家汇、西长明巷、寺后巷等。规模之巨大,已非一个市镇可以管理,一度分为七个市镇。乌镇一分为四:澄江镇、通霅镇、通津镇、长春镇;青镇一分为三:青南镇、青北镇、青东镇。这种“有机生长”的势头令人叹为观止,表明它成为“治所城市”绰绰有余,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它始终没有成为“治所城市”。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仰赖湖丝(辑里丝)出口贸易的乌青镇而言,是致命的打击,蚕桑丝织业急遽衰落。随之而来的连年战乱,使得它盛况不再。茅盾《林家铺子》笔下的乌镇,早已今非昔比。此后的乌镇,历经沧桑,逐渐化为颓垣断壁。如今作为旅游胜地的乌镇,不过是重新装修的一个盆景,供人观赏而已。
该书的结论,也会给读者很多意想不到的启示。作者写道:“江南治所城市在空间形态上虽有‘规划和礼制观念色彩,但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有机生长是江南城市形态发育的主要推动力,城市在街区形态上与江南市镇的高度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而城墙筑成的年代一般较迟,因此往往是适应于已有的城市建成区而非反过来决定之,城墙作为实用主义工程的特质也十分突出。江南治所城市固然都是行政‘治所,但绝非仅仅是‘治所,它们一般而言还是市场中心地,相当数量的城市还是本地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甚至是宏观区域内的贸易中心,手工业经济发达的‘生产城市也有不少重要的案例。”
于蓼花汀花园
二○一六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