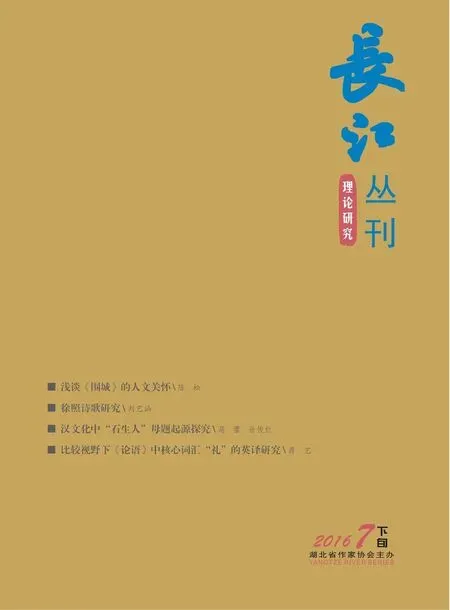中国山西省盂县“慰安妇”特征
2016-11-26李敏
李 敏
中国山西省盂县“慰安妇”特征
李 敏
中国山西省盂县的“慰安妇”,通过“强掳”、“摊派”、“俘虏”的方式被征集,身处于日军正规“慰安所”外。这些包括“普通女性”和“抗日分子”在内的女性们,身心受到摧残、遭到社会的歧视。山西省盂县的“慰安妇”们,是遭受到日军性暴力的中国广大农村女性的缩影。
慰安妇 盂县 日本 伤害 特征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产生的罪恶毒瘤。其始发于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策,也是摧残亚洲国家乃至于世界女性的一种恐怖政治。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发动了如此体制完备、规模宏大的“慰安”女性集团。而且,当日本本国女性明显不能满足战争需求时,日军便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被殖民、被侵略国家的女性,使这些女性受到了身体及心灵上的极大摧残与伤害。中国是在二战中,遭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生命、财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日军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慰安妇”制度,具有同日本、朝鲜、台湾的日本“国家”属性的“慰安妇”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山西省盂县村庄里的“慰安妇”,体现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在中国农村的鲜明特征,是日军对中国农村女性性暴力的一个缩影。本文以张双兵的著作《『慰安妇』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记录的山西省盂县中,受到日军性暴力的女性调查记录为基础,分析指出中国山西省盂县48名有实名记载的“慰安妇”特征。
一、征集方式的多元性——“强掳”、“摊派”、“俘虏”
中国作为被侵略国家,在日军的铁蹄下,人民的基本生命、财产安全等得不到保障。在被侵略期间,中国人没有任何权益可言,中国的农村“慰安妇”多被驱使为性奴隶。这类女性数量多、非常普遍,多没有被记载。盂县,位于山西省的东部,地处太行山西侧。因县境山峦回合,中低如盂得名。1938年1月,日军第一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占领了盂县县城,成立了帮助其进行侵略统治的维持会。日军占领开始后,盂县的人民便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其中,最为丑恶的就是日军的性暴力,日军通过多种方式搜集“慰安妇”。
首先,强虏型。盂县的“慰安妇”们多是无缘无故地被日军强虏到据点,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性暴力。在48人中,多达30人,其比例高达62.5%。严谨地说,这种在前线上遭受日军强虏、被长期或短期强暴的女性,跟日军一手炮制的真正的日军“慰安妇”并不相同,把她们叫作“慰安妇”确实有点牵强。然而,她们所遭受的性暴力,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延伸,属于日军底端士兵们如法炮制的、强迫中国广大女性充当“慰安妇”的性暴力行为。
其次,通过“维持会”等组织进行摊派。日军到达一个地方,首先想到的是征集“慰安妇”,在南京等大城市中,有许多从日本本土来的慰安妇和殖民地慰安妇。但在一些中小城市,或是偏远农村地区,没有那么多日本的慰安妇。日军则通过“维持会”等组织强征当地的女性。为了维护村子的集体利益,不受日军的骚扰,“维持会”的干部们只有“上缴”满足日军兽欲的女性。侯金良和张二妮就是因村子里的“摊派任务”被交到日军魔掌中。“维持会”满足了日军的要求后,村子里能获得一时的安宁,若满足不了日军的愿望,日军则会变本加厉,骚扰普通民众。“维持会”这种做法的背后,也显示出了被侵略国家女性的无奈与悲哀。
最后,抓捕型。这类女性自身或家属是共产党员。在汉奸的告密下,她们成了日军蹂躏的对象。48人中有16人,占30%。她们分别为侯冬娥(共产党,被抓时没有暴露身份)、周喜香(共产党)、万爱花(共产党)、陈林桃(游击队长妻子)、侯巧良(父亲是抗日分子)、郭喜翠(姐夫是地下党)、李喜梅(丈夫是共产党,被当普通人强虏)、韩银梅(丈夫是共产党)、王改荷(丈夫是抗日干部)、李壮林(儿子是抗日分子)、王贵青(丈夫是抗日分子),周润香、侯二毛、赵变梅、侯玉桃、陈喜云的调查是通过第三者转述的,被认为是“抗日分子及其家属”[1]。作为共产党员的“抗日分子”成为日军抓捕的口实,所以这些人一旦暴露,就会完全成为日军迫害的对象。她们中只有侯冬娥、周喜香、万爱花是共产党员,其余8人都因家属中有共产党员,被抓捕审问、强暴,成为日军的临时“慰安妇”。
二、管理模式的随意性——“慰安所外”的管理模式
日本的慰安妇制度,在日本公娼制度的基础上,从发端到正式确立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历程。在其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从“妓院”到“慰安所”、从“娼妓”到“慰安妇”的蜕变。日军的慰安所有具体的管理模式。作为应召的军医少尉配属于低十一军兵战医院的麻生彻男为曾经拍下了当时的“慰安所规定”。其除了规定了使用权限、金额等之外,还规定了相关的纪律。如禁止饮酒、禁止扰乱军风纪、必须使用避孕套等。[2]这些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慰安妇的人身安全。
然而,在“慰安所”外的盂县“慰安妇”们的情况颇为复杂。她们有的被监禁在日军的据点内,有的在自己家中长期遭到日军的性暴力,有的在日军随意指定的地方遭受一人乃至多人的性暴力。这种在占领地内才能看见的“慰安妇”模式,基本毫无管理可言。日军不用交费、没有时间限制,不用给“慰安妇”定期检查,更没有固定的“工作”期限。
这种随意式的慰安所外型的慰安模式曾在日军中大量存在,导致中国女性遭受了悲惨的性奴役之苦。然而,日本历史学者秦郁彦等人认为她们的证言“多是无法核实的自身的申诉,即使她们说的是事实,也是违反军规的个人乃至于少数集团的性犯罪,应该都可以归结到强奸事件的范畴”[3]。表面上来看,这些发生在前线的性暴力,不受日军上级军官的指挥,属于自发的、随意式的性暴力行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日军将女性集中看管起来,进行性暴力的形式,模仿了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对中国女性的集团式施暴行为,是日军的慰安妇制度的一环。也可以说,这属于占领地内的次生型慰安妇制度。
三、构成人员的双重性——“普通女性”与“抗日分子”
日军虽然侵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但无法得到中国人的顺从,一大批共产党员跟日军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斗争。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员避开敌人的围剿,努力开展抗日运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1937年9月21日挺进晋东北抗日前线,不久即以五台山为中心,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11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盂县隶属于晋察冀的北岳区。”“到1937年底,全县已有48个村庄建立了中共党支部。”[4]随着抗日活动日益开展,盂县各村镇也成立了抗日政权,成为共产党员的村民日益增多。
盂县的这些“慰安妇”们多是普通的无身份、无背景、无党派的良家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妇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她们被拉进日军的据点,成为日军战地的消耗品。她们中有的通过家人的帮助,逃离了魔窟,获得了自由,有的在慰安所内被折磨致死。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女性是作为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的家属,被日军抓捕到据点,受到残酷的性暴力。因为她们是女性,跟男性共产党员俘虏相比,她们又多了一层价值,那就是成为日军奸淫的对象。她们遭受的苦难比一般女性也多了一层。为了从她们口中得到有效情报,她们被日军拷打,受尽酷刑的折磨,还不得不遭受日军性暴力。
如前所述,盂县48例“慰安妇”证言中,有16人(占30%)被俘的与“抗日”有关系的人员中,侯冬娥、周喜香、万爱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侯冬娥被抓时没有暴露身份,只因日军听说她人漂亮。周喜香和万爱花因为被汉奸出卖,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日军的俘虏,并被充当日军的临时“慰安妇”。其他13人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被抓入日军据点,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四、受害因素的多样性——身体疾病、精神摧残、社会歧视
在中国众多“慰安妇”中,目前勇敢站出来的人中,以山西省盂县的人数最多。这些女性们在和平年代中,依旧与自己、家人、社会做着斗争,顽强地生活着。“慰安妇”经历带给她们的苦难是多重的、深重的。
在肉体上,由于她们是被侵略国家的女性,在日军面前,她们毫无尊严可言,是随时可以被杀死的动物。如果她们稍有反抗,就会受到严重的暴力。这导致她们的身体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有的人的身体上,留下了终生难以恢复的伤疤。另外,由于她们被残酷虐使,导致她们中的一大部分人丧失了生育能力。在农村里,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非常浓厚,没有自己的后代,年老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疾病侵袭,她们中一大部分人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在精神上,被日军囚禁的日子里,她们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暴力,有的人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即使经过了长久的治疗,稍有刺激,就会让她们精神失常。她们无法看有关战争时期内容的影视作品,时常被噩梦惊醒,并为自己曾经的经历无法释怀,过着自责的生活。周喜香就“因日本兵的残暴行径而受到惊吓,大脑受到严重挫伤,基本上丧失了记忆力,思维和表达能力受到严重影响。”[1]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另外,由于被日军充当过“慰安妇”,她们被家里人、村里人歧视,有的甚至连同下一代都遭受了鄙视。家里人不理解、村里人的歧视、社会上的否定,给她们的心里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甚至要比身体所受到的伤害更为严重,更为让她们无法释怀。因此,大多数的人都默默地忍受着自己痛苦,不告诉别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暴露自己“慰安妇”经历的人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因为她们有过成为日军“慰安妇”的经历,是“日本娼”、给日本人生过孩子,被定性为反革命,经常被揪出来批斗。其中,有的人最终不堪文革中的屈辱性折磨和疾病的困扰,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南二仆就是其中的一例,由于她给敌人当过“慰安妇”,还生过日军的孩子(夭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劳改关押两年,后来虽然得到平反,但终因经不起社会舆论的压力,带着满肚子的冤屈,上吊自尽。”[1]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受到日军侵害的女性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后,还要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这对她们而言,无疑就是再次伤害。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以山西省盂县为代表的“慰安妇”们,是遭受过日军性奴役的中国广大农村女性的一个缩影。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慰安妇”们多被埋没。如今,日本政府仍不愿意承认中国这些具有中国被侵略国家特色的这些“慰安妇”们的存在,而把她们当作“违反军纪”的部分军士的战地强奸行为,逃避日军本身具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式农村型“慰安妇”们的存在,是对日军摧残人性的慰安妇制度的控诉,也是日军侵略中国时期肆意践踏人权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张双兵.『慰安妇』调查实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35.
[2]千田夏光著,林怀秋等译.随军慰安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6.
[3][日]秦郁彦.慰安婦と戦場の性[M].新潮社,1997:377.
[4]刘萍.关于日军强征山西“慰安妇”的调查报告[J].抗日战争研究,1999,4(2):181~182.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战前日本风俗业与慰安妇制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SL15-003)。
李敏(1985-),女,辽宁朝阳人,历史学博士,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日本近代社会、日本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