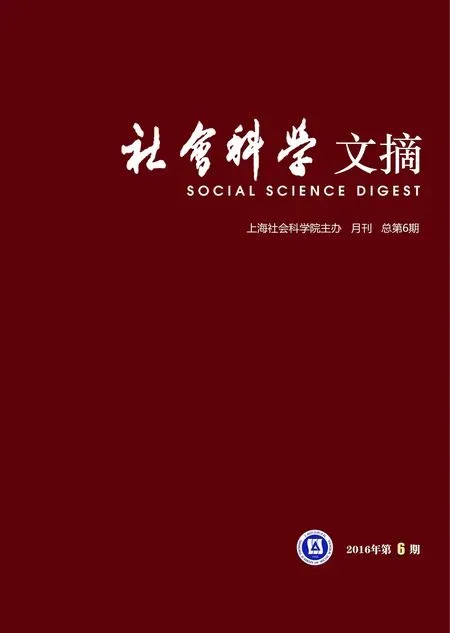以“生活文学化”对抗“日常生活审美化”
——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美学思想探赜
2016-11-26曾洪伟
文/曾洪伟
以“生活文学化”对抗“日常生活审美化”
——哈罗德·布鲁姆后期美学思想探赜
文/曾洪伟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当今享誉世界的文学批评家,其批评领域和文化身份在其文学批评生涯中经历了多次转向与嬗变,如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批评家,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家,再到90年代的宗教批评家等。而90年代以后,即其批评生涯后期,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又发生了重要转型,其批评的受众、批评风格、文化身份、美学思想、美学理念与其前期相比又具有了很大的不同,其美学主张与传统唯美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貌合神离。那么,这一时期布鲁姆的批评面向、形态、内涵、性质以及身份等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异?其特定美学的内涵和本质与唯美主义、后现代主义相比又有何差异?这些是本文将着力探讨与廓清的问题。
从学院批评家到大众美育家,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艺术而生活”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布鲁姆的美学历程(或曰美学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作为学院批评家的“为艺术而艺术”阶段和后期作为大众美育家的“为艺术而生活”阶段。前者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审美的自主性,关注的是艺术本体内在构成,其视阈是封闭的;而后者关注的重心在于艺术的目的指向,即倡扬生活的审美化、人生的艺术化、强调艺术面向生活、审美走向社会,走近生活,走入大众,其本质是主张审美感性对日常生活工具理性的渗透、颠覆与控制,其思维模式与形态是开放的。因此,与其前期美学思想相比,布氏后期美学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奥斯卡·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的影子。从本质上讲,与佩特及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一致,布鲁姆在美学理论与实践上也存在着相似的悖论,即在理论观念层面主张艺术与生活的区隔与对立,而在生活实践层面又通过施行艺术/审美的物化与对象化,提倡“生活模仿艺术”,实现艺术与生活的融合与统一。
作为特立独行、个性独异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虽然与王尔德等都同属现代主义美学阵营及流派,其美学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他们(即后期布鲁姆与传统唯美主义者、后现代主义之间)在美学思想尤其是生活艺术化的观点与主张上还是存在着重要差异甚至对抗的。
以“生活文学化”对抗唯美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
首先,布鲁姆将其论题对象域仅限于“文学”。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生活”的理论命题对于布氏而言更准确地讲应该置换为“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学而生活”。即布鲁姆虽然认同唯美主义的上述主张,但唯美主义广义的“艺术”对于他而言只指文学,而不包含其他艺术门类(即狭义的艺术)。虽然“文学”“(狭义)艺术”在本质上均是以张扬审美感性为特征、坚持自为为原则的学科门类,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文学”是以文字为媒介的学科门类,而“(狭义)艺术”则是以线条、音符、色彩、画面等为媒介的门类。布鲁姆之所以终其一生不越规,不逾矩,唯独钟情于文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笔耕不辍,并一直从文学的层面或视角接受、思考、理解、践行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生活”的美学理论与主张,这与他从小深受文学熏陶、对文学这一古老艺术门类一往情深,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学“惯习”有着直接而深切的关联。这从其后期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审视生活即可见一斑。因此,对于布鲁姆而言,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理念其实是“生活文学化”(包含“文学生活大众化”)。当然,无论是生活艺术化,还是生活文学化,其本质都是生活的审美化。那么,布鲁姆强调生活的文学化而非艺术化又有何特别用意呢?这就涉及到布鲁姆与传统唯美主义者以及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另一个重要差异。
早期的唯美主义者由于秉持“生活模仿艺术”的理念与理想,这样就导致他们在生活实践上自然走向生活审美化,并的确身体力行,王尔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与他们在艺术自律问题上的理论凌空高蹈姿态与精英色彩迥然不同的是,唯美主义者在生活的艺术化问题上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审美的泛化、日常化、时尚化、视觉化、实用化,这充分显露出唯美主义者凡俗化生活美学思想的一面。在此一阶段(工业化时期),唯美主义者们野心勃勃,怀抱雄心壮志,试图通过审美(形式)的物化、视像化和日常化,以艺术改造和颠覆机械、庸常、乏味、“铁笼”般的日常生活,以感性对抗、刷新日常工具理性,从而重构多向度、完整、感性与理性兼具的社会主体,并通过使审美向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与扩张来实现艺术对世界的掌控,建立乌托邦似的审美王国,并最终实现对人类的(精神)救赎。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的主张与实践已为审美走向生活开启了重要的篇章,并为之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全面、深入展开、到来与兴起作好了思想、社会、文化、心理准备。
当代社会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是艺术家与资本家、艺术与资本共谋、共同运作的结果,它在“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培育他们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冲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是艺术自主性、独立性的消失与审美的贬值。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是审美形式与日常生活功利性、实用性、工具性的结合,或者说是后者对前者的挟持与压倒性控制,而它们又一起最终为资本或利润的再生产服务。也就是说,此时的审美必须服从于商业逻辑与市场法则,而在审美产品的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被资本剥夺殆尽,荡然无存;另一方面,为赚取最大额度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对审美产品进行大批量复制,而随着艺术商品稀有性、神圣感的消失,审美的贬值现象也随之发生。其次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审美表层化(视像化、快餐化)、大众化、粗鄙低俗化,并使传统审美精神丧失,审美体验变味。日常生活审美化实际上是审美的扩张与泛化,其本质是审美形式的扩张,在后现代社会中主要表征为视觉化、图像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充斥与泛滥,而基于此语境的审美主体的美感体验方式则是视像化、直观化、快餐化、表层化的,也就是说,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社会的审美模式已由传统的“阅读——认知”深度模式向“观看——感知”浅度模式转变。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或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最终导致的是理性对感性、生活对审美的反控制和商品/物对人的反占有,它的风行并不意味着审美的勃兴和繁荣,相反,它意味着艺术危机时代的到来。而这正是由于唯美主义在不经意间打开了艺术危机的潘多拉之盒。
作为生活于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现代唯美主义者,布鲁姆正是察觉和意识到传统唯美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生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和所引发的现实危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生活文学化”“文学生活大众化”的美学主张,对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主张具有一定的纠偏补弊作用。
首先,布鲁姆的“生活”并非是指(或主要是指)日常生活,即“‘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包括自然情感、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基础,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等日常生活领域”,而是指“由科学、艺术、哲学等构成的‘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即非日常生活。很明显,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是生活的一种高级、复杂形态和升华阶段。因此,他的“生活文学化”更多地是关注审美主体内在精神与心灵景观的审美化,而非如早期唯美主义者所提倡和践行的时尚化、日常化、表面化、实用化。也就是说,布鲁姆更关心主体的精神和意识层面的生活以及个人人格的成长。因此,布鲁姆的“生活文学化”主张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内在精神的审美化对抗后现代外在社会对人的物化、异化、商品化、工具理性化,冲出、超越消费社会构织的物质欲望包围圈与重重罗网,走向审美的乌托邦,并重建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缺乏或正在流失的“自由精神、独立意识、完善人性”。一句话,布鲁姆意欲改变的不是当代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景观),而是其精神生活(景观)。
其次,布鲁姆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文学化”主张,反对、抵制传统唯美主义、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视像化、虚拟化、表层化、庸俗化倾向。布鲁姆通过着意强调“文学”的出场与在场,凸显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的中心与主导地位,有意排斥以图像、线条、色彩、音符为媒介的艺术品,尤其拒斥视觉艺术产品和电子、数码虚拟产品。在《西方正典》中,他曾多次表达了他对图像时代的到来和拟像/声像产品泛滥的反感、忿恨和对文字文化时代以及文学作品的眷恋。而在《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影响的解剖》中,他对文学(阅读)不遗余力的鼓吹与宣扬,可以视作是他逆图像文化时代的大潮,以文学奋力声讨、抵挡消费社会中图像、电子文化对审美领域侵蚀、侵占的一篇篇战斗檄文。原因之一则是基于他对文学审美与视觉图像审美的比较结果:前者具有一种深刻的内视性特征,而后者则以虚拟化、表层化、肤浅化的外观性为其特色。另外,他还以纸质文学的(物)质感、真实感、亲近感对抗电子文化产品的虚拟性或者说拟像性、隔膜性,即以传统媒介文化、文学反对现代电子媒介文化、文学。
更进一步看,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话语只指高雅文化文学(文本),而不包括其他如主导文化文学(文本)、大众文化文学(文本)、民间文化文学(文本),并奉“崇高”为其唯一或主要美学内质与特征——其具体表现形态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具体范围则是他在《西方正典》中所罗列的、类似宗教圣典性质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从神权时代到贵族时代、从民主时代到混乱时代的“唯美”经典文学文本。深奥性、原创性、陌生性、独特性、关注彼岸性是其突出特征。他特别反对对于带大众文化性质的通俗文学、畅销文学作品的阅读,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生活的此岸性、现世性和日常性,而复制性、肤浅性、快餐性则是其显明的表征。
因此,通过强调文学的文字以及(高雅)文学图像化转换的难度(如诗歌),布鲁姆着意反对图像化、数字化阅读,并抵制这种倾向;通过强调文学、内视性审美和宗教式崇高精神关怀,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视觉化(追求、沉迷于视觉快感)、外观化、表层化和物质化;通过强调文学审美品格的高雅性,审美欣赏的难度性,经典作品的独特性、个性、陌生性、未来指向性,有意制造审美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与张力,形成陌生感,以经典性、原创性、高雅性、审美的纯粹性对抗大众文化的大规模复制与模式化、类同化、快餐化、低俗化、商业化,反对日常生活审美体验的麻痹化和庸常化,使审美主体在(高雅)文学生活中摆脱日常生活审美中图像和物质对人的束缚与操控,重新恢复其主体性、主动性和积极的审美感知,重新体验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所具有的“韵味”“震惊”“恐惧”等体验,重新获得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意识、完善的人性,升华的人格和涤荡的心灵。简言之,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物质化、表层化的审美化,那么布鲁姆的生活文学化则代表着一种精神化、深层化的审美化;而种种迹象表明,他正企图以此引领审美大众走出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引发的审美与生活困境。换言之,布鲁姆不赞同人们生活在“艺术”的世界里,以“异在”(马尔库塞语,即艺术)对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马尔库塞的观点),而是呼吁人们生活在“(高雅)文学”的世界里,以经典文学的“陌生性”反抗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异化”,从而实现被拯救的目的。因为“艺术”已被“日常生活化”了,已与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文化现实或“异化”的社会合二为一或被同质化,“异在”已不可能。
再次,与传统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和当代后现代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同的是,布鲁姆“文学生活大众化”的“大众化”并非是指审美的通俗化,甚至庸俗化,而是指文学的普及化,即使高雅文学、纯文学向尽可能多的大众覆盖,使最大范围、最广层面、最多数量的社会大众接受经典文学或者说具有彼岸指向性文学的审美教育。因此,相对于传统唯美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布氏的文学生活大众化不仅不是意味着审美品位与格调的降低,反而意味着审美品位的提升——对于日常生活(审美)的超越。因为无论是旧唯美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试图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与大众之间的界限,使审美走向生活(尽管其初衷并不一致),再加之消费社会中资本的渗入,伴随着对利益/润的渴求与追逐,审美与艺术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也一步步沦为媚俗的、弥漫着浓厚商业气息和透露出强烈功利/用色彩的平均质文化。而布鲁姆则坚持其精英主义审美立场,坚决维护文学与大众之间的界限、距离与张力,拒绝文学的通俗化、浅易化、功利化(道德说教化)、平庸化、资本化,坚持其超越性的审美品格。因此,布鲁姆的“文学生活大众化”既使审美走向了大众,同时又吸取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车之鉴,使文学与大众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样态,尽可能防止文学的继续滑坡与堕落,阻止文学困境的进一步加剧与恶化。如果说王尔德等可归入旧唯美主义之列,他们为反资产阶级的平庸生活和工具理性而提出的“生活艺术化”主张,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初步萌芽;那么哈罗德·布鲁姆则是传统唯美主义的革新者,是旧唯美主义的修正者,是一位新唯美主义者,他为修正旧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主张和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图像化、大众化、庸俗化汹涌浪潮而提出的“生活文学化”口号,是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现代主义美学逆流,它以其思想的独异性和独特的理念设计,对后现代美学的偏颇与缺陷起到了一定的矫正和弥补作用,同时也一定程度地维护了当代美学形态的多元性和生态多样性,维持了其动态平衡和健康发展。
结语
总的来讲,布鲁姆的“文学”代表着一种精英主义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而“生活文学化”“文学生活大众化”实际上是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审美文化、力图在社会大众中推广、普及其精英主义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理论与主张,同时也代表着现代主义美学(潮流)对后现代主义美学(潮流)的一次反击与倒算:布鲁姆以文字(代表着深层话语模式)对抗图像(代表着浅层话语模式),以严肃对抗游戏,以高雅对抗平庸,以精神对抗物化,以审美感性对抗工具理性,以恢复完整自我对抗异化、碎片化,以经典对抗庸常,以经典性对抗复制性,以永恒性对抗快餐性,以浪漫想象对抗庸常现实。哈罗德·布鲁姆的“生活文学化”主张无疑对后现代社会与文化语境和美学困境中的理论家与文化大众具有积极的启迪、反思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自《国外文学》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