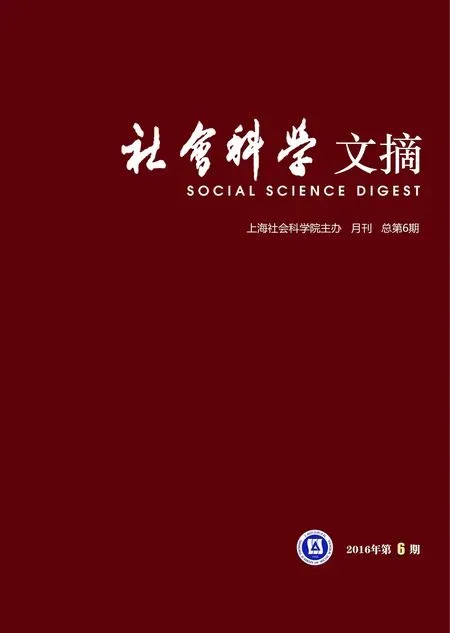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
——开天诗坛风貌的另一考察维度
2016-11-26杜晓勤
文/杜晓勤
从“盛唐之音”到盛世悲鸣
——开天诗坛风貌的另一考察维度
文/杜晓勤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用“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来说明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认为盛唐诗人大多在作品中表现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和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但这些形象化的表述,只是对盛唐时期诗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的共时的静态的描述,难以揭示出盛唐诗坛风貌的复杂性和历时性变化。如果我们对开元天宝年间的诗歌作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所谓的“盛唐之音”或“盛唐气象”之下,还涌动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盛世悲鸣的创作潮流。
将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
开元十五年后,盛唐诗人大多怀跻身朝阙、参与国政的政治热情,高唱着“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理想之歌,或决策于朝廷,或立功于边塞,大有一展宏图之志,诗歌风格上则表现为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学界多称之为“盛唐之音”。但是,“盛唐之音”到开天之际即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不独标志着所谓的“盛世”已初露黑暗专政的端倪,而且使此前诗坛一味的高唱、宏响中混入了不安的和声。
首先,张九龄、王维等较为了解朝政的上层士大夫,最先在盛唐诗坛上唱出了对国事、时世忧虑的歌声。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入朝,使得张九龄、王维等人诗中的这种忧思激化成对长安政坛黑幕的全面曝光。同时,开天间久不擢第的一些布衣诗人,也发出了“明代遭弃”“自伤不早达”的悲鸣。虽说玄宗朝已经为广大寒士提供了广阔的仕进道路,但皓首穷经,并不能保证仕途一定得意。所以,开元中已有不少诗人将这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发为悲声。在颇能代表盛唐诗风的《河岳英灵集》中,我们不但可以听到王维 “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旷达之音,亦多能感受到孟浩然、薛据、王季友等圣代不遇者的悲愤之辞。
如果说开元中科举制度尚带有相当程度平等竞争的性质,那么到开元末年则开始颓坏,弊端日显。李林甫当政,嫉贤妒能,强压才士,遂于天宝六载(747)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丑剧,暴露了科场的欺骗性。而当时的士子们也什什伍伍,大开干谒请托之风,以致贡举失公,伤风败俗,一些清贫、刚直之士就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元结及其编选《箧中集》中诸诗人所发出的盛世失意者的呼号,使我们看到了常人所忽视的唐代开元天宝间所谓“盛世”“明代”时灰暗阴冷的一面。
但是,由于处世观的不同,盛唐诗人对于仕途受挫的心理反应亦不相同。其中,受儒家积极入世观影响较深者,如杜甫,多能屈己求人,汲汲于功名仕进,表现出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发为歌吟,孤愤悲慨;元结及一些刚直贫贱之士,则落拓回乡,愤世嫉俗,声情激切而高古;而另外一些受佛道思想浸淫较深者,如王维、孟浩然,则走向山林、田园,或在禅悦的境界中消磨自己的锐气,或借自然界的胜景寄寓他们洁身自好的情怀,诗境冲淡、空灵,流露出一种寂寞和失落。至于那些科场失意后远走大漠者,亦非人人得遂心愿。边塞上、军旅中日渐黑暗的内幕,使得许多边塞诗人,亮开啼血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悲伤、愤激的征戎之歌。这种越来越浓烈的悲怨情调,显然是“盛唐一味秀丽雄浑”和“盛唐之音”这样的传统评语所概括不了的。
“盛世悲鸣”的内在心理机制
开天诗风由“盛唐之音”转为“盛世悲鸣”,是整个社会心理的反映,更是盛唐诗人文化心态集体演变的结果。盛唐诗人的主体,是一批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庶族寒士,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无特权可以依恃,无家世可以炫耀,迫切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寻求政治地位,实现自古以来文士梦寐以求的“士志于道”的政治理想。由于盛唐前期的政治、文化政策的吸引,他们可以选择多种入仕途径:或参加科举考试,或立功边塞,或走“终南捷径”,在求仕过程中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和热情,发而为诗也就成为高昂、激奋的理想之歌。
然而,盛唐文士这种渴望跻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政治热情并未持续多久。到开元后期尤其是天宝年间,理想与现实的强烈碰撞,使他们开始思考自身在所谓“盛世”“明代”的命运,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愁怨和愤懑,渐渐取代了早年的幻想和热情。
首先,开元中前期入仕的庶族士子在仕途上大多未能如愿。即便是张说这样一个能文能武且与玄宗私交甚厚的开元名相,也未能完全实现其政治理想。开元十五年后,在宇文融、崔隐甫等人的排挤下,张说离开了政治中心。再如张九龄,到开元二十五年(737),也没能避免被李林甫排挤出朝的政治命运。而且,张九龄被贬,标示着开元盛世辉煌一时的文人参政的高潮成为过去。依传统观点分析,盛唐政坛及文人心态的变化,主要是李林甫当政、朝事日非的结果。实际上,更反映出玄宗朝为政观念的“吏治和文学之争”。李林甫当政,代表重“吏治”一派得宠,以文学入仕的诗人便遭排挤,心态低沉、失落。
其次,透过初盛唐朝廷“广开才路”的表象,我们还可以发现,庶族寒士真正参与国政的希望仍是十分渺茫的。科举虽是盛唐寒士实现政治理想的要道,但此时朝廷选官的主要渠道却是流外入流和门荫,后者对世族子弟更为有利。而且,世家大族往往具备悠久的家族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考场上也容易取胜。庶族寒门之士要想走科举取士一途,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容易。盛唐诗中出现诸多仕进无门的愁苦之音,便不为无因。
再次,立功边塞,虽说是盛唐诗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又一条途径。然而,从开元初到天宝末的四十三年间,中下层文士出将入相的却寥寥无几。这与此时朝廷军事政策上的变动有关。府兵制从武后朝即开始破坏。张说在开元十年(722)向玄宗建议停止府兵番上,改用募兵制代之。而募兵者则是职业军人,不需再授大量勋田,对兵士更少加以军功。加上,李林甫入相后,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重用蕃将,入幕的文士鲜被重任。所以,开元末和天宝年间,中下层文士要想由边塞直取朝廷,也比登天还难。
再看走“终南捷径”者,在天宝年间亦鲜有成功者。初盛唐诸帝“坚回隐士之车”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点缀升平、表演太平戏,并不是真心要起用所谓的世外高人。李林甫当政后,出于巩固相位之本能,更是害怕草泽之士入朝,遂于天宝六载导演了一出“野无遗匿”的丑剧,文士要走“终南捷径”就更难成功了。
总之,在整个盛唐时期,庶族士子大多没能实现参与国政、“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文化心态整体上呈现出渐变的趋势:由开元中前期的渴望风云际会、建功立业,向天宝中后期的仕途蹭蹬、理想失落的渐变;由他们年青时对“圣代”“明主”的厚望,到中老年对功业难就、壮志冥寞的怨愤的渐变。这种文化心态的渐变,是整个一代士子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个貌似能实现政治理想的“盛世”“明代”,为追求自身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的心灵历程的反映,也是盛唐诗风由前期的“盛唐之音”,向中后期“盛世悲鸣”的转变的内在心理机制。
政治理想集体性失落的政治文化因素
盛唐诗人“致君尧舜”政治理想的集体性失落,不只是开天年间具体的社会政治制度束缚或者权奸当道压制才士的结果,也因为他们作为“志于道”的文士、儒生天生具有的一些政治弱点,更是这些新生庶族士子的文化特质,与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封建国家集权体制之间矛盾冲撞的结果。
首先,盛唐士子大多是随着南北朝后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新兴政治力量,其文化心理中积淀着传统知识分子“士志于道”“以道自任”的价值取向,因而他们大多以“致君尧舜”为政治理想。但是由于庶族士子尚处于新生期,他们身上不但留有春秋战国以来“士”的先天性弱点,也未能克服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所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儒家重自身修养而轻外在事功的传统,桎梏了盛唐不少文士。初盛唐之际渐重诗赋之后,进士和以进士为鹄的文士们普遍“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大多数文士不太精研历史和治术,他们对政事自然也就不太内行。而开元中期以后,政事日益纷繁,边境日益紧张,原先的一些制度需要调整,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是当时大多数文士所无力也不愿解决的。这也许是唐玄宗最终弃文士而重用“吏治”派的一个潜在因素吧。
其次,盛唐文士作为新兴的庶族士子群体也存在着自身的政治文化弱点,即政治上“独立意识”的丧失。盛唐文士们不敢废君臣之大伦,“致君尧舜”更成为时人的口头禅,都标志着此时士子对先秦儒家所持“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一古老观念的彻底放弃,丧失了士阶层应有的政治独立意识。因而,他们在追求政治理想时,就不能不受皇权意志的任意摆布,容易成为封建国家政治机制中的牺牲品。
因此,盛唐诗人在作品中所发出的“盛世悲鸣”,就不仅仅是由当时的一些具体历史因素引起的,也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文化意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高度集权政治下,新生的庶族文士主观和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反差和强烈冲突。盛唐文士政治命运的悲剧,可以说是隋及唐代中前期新旧社会结构剧变时士人群体旧悲剧的尾声,新悲剧的序幕,对后来的封建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摘自《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