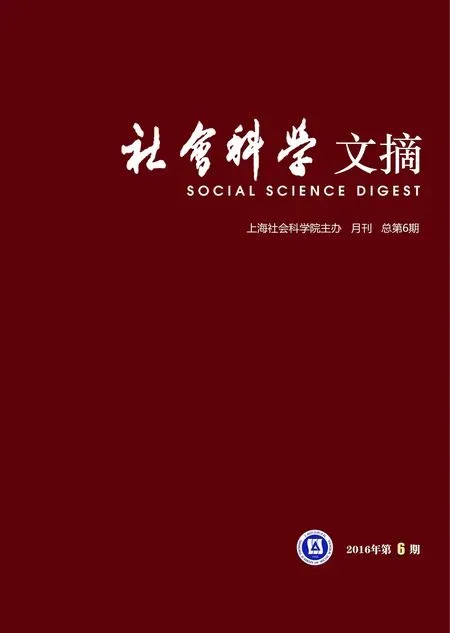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2016-11-26王君柏
文/王君柏
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文/王君柏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东西南北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发展先后之差异,贸然地说农村如何,都难免有例外的情形出现。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那就是广大的内地乡村,已然开始衰落,越是远离经济中心,衰落的程度越是迅速、决绝、彻底。
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对于当前乡村衰落的趋势,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首先有一部分人是不承认这一趋势的,认为农村这些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收入一直上升,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等等,毫无疑问,这是只做纵向比较的,但这种观点总体而言是少数。其次是认可这一趋势,但对此趋势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权且把它们叫做理性派和乡愁派,或者叫做经济派和文化派,前者以经济学为主,后者以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为主。
理性派的典型就是从舒尔茨到盖尔·约翰逊,到林毅夫的研究传统,其基本观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毫无疑问,这是从根本上保证城乡人口平衡的要求,因为该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农民是明智的,同样会进行理性选择。而要达到两者收入的相当,就需要减少农业人口,具体的方法一方面就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即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改善教育,为农村人口城市就业提供知识准备。所以,政府对三农的作用,主要是基础设施、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上。在此逻辑下,中国目前乡村的衰落,可能还是不够彻底的,毕竟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还是远远偏高,如何通过科技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就是该派认为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土地问题,口粮问题,文化问题,都不是问题。
乡愁派成分复杂,支持者众多。首先是一般的文人雅士式的乡愁观念,但这实际上往往都是脱离乡村的人士的一种回忆,是所有的人都有的一种情绪,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会对自己儿时的生活环境、玩伴师长产生一种念旧的情绪,在乡村表现为乡愁,在城市表现为旧时街巷弄堂的难以割舍。其次是正式的号召与弘扬,一方面有官方提倡“留得住乡愁”,就是从乡村建设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也算是对乡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的一种提醒吧。一方面是一些出于旅游宣传的目的,利用人皆有之的乡愁情怀,打造“老家”“乡愁”等概念。最后,更为主要的是学术研究中的,典型的是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因为以文化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那么在急剧变迁中文化的蜕变,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是最敏感的,于是有对各种村落文化进行研究,细到生活习俗、民间工艺、人际关系冷暖等等,总之,认为各乡村文化都有其价值,它们的消失是巨大的损失,感到痛心疾首,认为需要抢救,甚至退而求其次,认为对这些消失中的文化哪怕做点“临终关怀”,也是义不容辞的。
乡村真的失落了吗?
从纵向比较,中国农村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就更是有目共睹。但从横向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现在很多人所说的乡村衰落问题。究其实质,目前中国乡村的失落只是一个相对衰落的问题,但这种衰落,却有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的趋势。具体的,乡村衰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裂痕很大,乡村人口难以为继。老人留守村庄,干农活,带孩子;中年人处于外出打工和回乡之间,城乡两边对他们都是鸡肋,在外难以找到轻松赚钱的事情做,回家已经对农田没有热情;青年人在外打拼,状况也是千差万别,有适应良好的,大多数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但同时对回乡已经毫无兴趣,于是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徘徊于城乡之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而幼小一代,大多随老年人留守,隔代教育,在家长、学生和老师的三角关系中,难以沟通顺畅,教育状况也就大不乐观,学业不佳,性情不良,这又直接预示着这一代的未来,未必能够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人口在代际继替上出现脱节和恶性循环,同时又因为计划生育,在数量上也开始青黄不接。乡村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人口的质与量的难以为继,还表现为精神状态上的未来希望不可期。
二是各种资源的流失。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物质财富向城镇集中,如果说上一辈的物质财富是以建造一幢房子作为积累,那么当前一辈已经以到县城或者小镇买一套房为上,于是集老少几代人的积蓄,到城镇买房,用乡村的微薄积累,灌溉城市建设。其次,还有间接的物质财富流失,如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大部分利润落入中间商和工业生产者手中,广大农民丰产不丰收。此外,各种公共资源的中心化,乡村就边缘化了。如学校、医疗这些涉及民生的关键资源,都集中在城镇,子女上学,还需家长赁屋围校而居,是谓陪读;医疗方面,小病自己扛着,大病奔县城省城,中心镇上连阑尾炎都治不了。边缘化就意味着空心化。
三是基层组织涣散,无法应对市场大潮。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基层党政组织不强,越是衰败的乡村,村级财务账上越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数,既无法行政,村民也无所期待,加上家族因素掺入其中,更有偏离代表所有村民的公意之初衷;二是村民各自为家,眼睛全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既无先进带动后进,又无合作精神,哪怕修条小小马路,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困难重重。然而市场却是无情的,没有合作,就难以形成力量,在市场大潮的冲刷下,乡村这一盘散沙就不断地被侵蚀,如何不走向衰落?
当然,衰落的表现,远远不止这些,其他比如自然环境、民风民俗、传统手艺等等,都有江河日下之势。
务实:超越理性与乡愁
现代化过程并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变迁,在文化上如何衔接,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的传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文化的传承,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应该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始终处于变迁之中,文化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对待乡愁,应该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即如何增加人的文化适应性,而不是为保留文化而保留文化。面对失落的乡村,应该兼顾乡愁与理性,或者说超越乡愁与工具理性,才是务实的态度。
费孝通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大变迁,概括为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跳到信息社会。三级两跳中,第一跳就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中外差距、国内地域差异都很大。而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跳,与广大的内地农村还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充当快递员。虽然费孝通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但实际上乡镇企业的成功,只是沿海地区的事情,即人口流入地,对于广大的内地农村,恰好与费孝通这里讲的西方道路没有什么不同。从区域发展来看,这就是因为一步慢,步步慢,内地(尤其是乡村)在三级两跳中顺应失当,相对陷入衰落。
有鉴于这一大趋势,对于乡村而言,无论进退,都要积极顺应,而不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以致彷徨无所归,既不安其位,又失其发展。发展的方向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积极态度融入城市,真正适应城市,在城市有所作为;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追求有质量的留守。
积极融入城市。首先取决于城市的吸纳能力,吸纳能力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能够吸附足够的人口,产业结构取决于创新,否则,进城也只能从事建筑、快递、小摊小贩之类,终归难以融入城市,以超过两亿流动人口在城市,却只有极少数能够在城里生根,这不仅仅是政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创新不够,没有足够的产业体面地养活这个庞大的人口。其次,从农村人口这一端看,是否具备良好的素质,足以在三级两跳的过程中能够适应环境,是问题的关键,这一方面是正式学校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资格的获取,这其实无助于快速变迁中的适应能力的提高,更何况这种敲门砖式的教育,对乡村青少年来说,资源也稀薄得很;一方面是品格教育的问题,毕竟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一些没有受多少学校教育的青年,在城市里凭借自己的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也闯出了一片天地,迅速适应了城市的生活。遗憾的是,正式教育与品格教育,在内地农村都是缺失的。
追求有质量的留守。首先,对农业需要重新认识,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宜规模经营的,应该走规模经营的路,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但对于不宜规模经营的,应该走品质的路子,在追求特供的时代,高品质的农产品应该是有其价值的,这也是目前我们很多学者提出的社会生态农业。其次,要减少人为的边缘化,如果说市场的边缘化是不可避免,那行政方面的人为边缘化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的投资是远远不足的,对乡村的护持应该在这些方面,而不是直接上马项目,加强地方社会建设,积聚人才,才是关键。最后,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尽量维持乡村社会的生态平衡,这既包括纵向乡村文化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形的如传统手工艺,无形的如桑梓情谊、乡贤精神等),也包括横向上各种力量的结合,从一盘散沙走向合作,在这一方面,英国、日本等域外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摘自《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