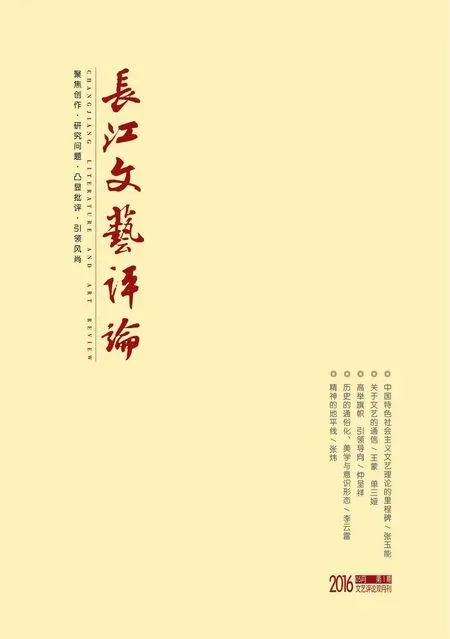亦真亦幻的“梦”世界
——评舞剧《临川四梦》
2016-11-25刘三平
◎ 刘三平
亦真亦幻的“梦”世界
——评舞剧《临川四梦》
◎ 刘三平
如何表达一份真挚的感情,如何用身体语言诉说一种缠绵的爱恋,如何让这种爱恋穿越梦境与现实,穿越生与死的界限,汤显祖已用戏剧语言《临川四梦》告诉我们。四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戏曲学院的原创戏曲舞剧《临川四梦》以戏曲舞蹈身段的唯美深沉,结合中国古典舞的委婉柔和,共同讲述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梦”的世界。
作为舞剧的新《临川四梦》与作为戏曲经典的《临川四梦》一样演绎了四个唯美、虚幻的故事:紫钗记——侠梦、邯郸记——道梦、南柯记——佛梦、还魂记[1]——鬼梦。只是这里的舞台表现不仅是以舞蹈形体美的展示代替了戏曲声腔的艺术表演;同时也把四出颇具规模、浅唱低吟的传统剧目改编成一部舞剧,让观众们依次在四个梦境中游走徘徊,从而集中体验了四梦的幻灭与苍凉。四梦此时,已不是四出戏、四个梦的简单组合,而是已经成就了一部新的作品,一部用身体语言描绘的关于人生爱的领悟。
戏曲与舞蹈作为有着不同表演范式的艺术门类,在这样的一部戏曲舞剧中却难以摆脱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首先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二元对立:戏曲与舞蹈;其次纠缠在这部舞剧中的还有关于作品结构的二元对立:时间与空间。著名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曾谈到过他对“二元对立”的热情,他认为当概念成双成对的时候,就建立了写作的可能性。诚然,写作的开始总是探索的开始,总是在对文本怀着极大热情和兴趣之后,转入一种冷静和理智的思考,于是要把这些莫名的感动装入概念的盒子,贴上标签。但最重要的恰恰不是标签,而是这些盒子在碰撞、变形之后,构成了新的造型,这时候这个新的造型将重新充盈艺术作品空灵飘逸的审美韵味,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戏曲——舞蹈
舞蹈与戏曲,本就是有着重要亲缘关系的艺术形式。“一般认为,和戏曲艺术的不断繁盛相反,宋以来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艺术却相对衰落。但此时,由于戏曲艺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民间,大量吸收舞蹈的因素,则使融入戏曲中的舞蹈,追随时代发展而为自身找到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它导致中国‘古典舞’在急骤的嬗变中发生某种质的跃进,中国‘古典舞’被置于戏剧的结构中进行了一次新的整合。其显著特征是舞蹈为表现戏曲的内容及刻划人物的思想感情服务。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于舞蹈走向现代提供了某种艺术美学与技术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准备。”[2]中国古典舞的发展本就是在戏曲艺术的发展中风生水起,所以用舞蹈的形式演绎戏曲的故事会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和表现力。加之古典舞还从武术、壁画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营养,所以古典舞的创生可谓是“二度抽象”的结果。它超越了戏曲、武术等的一度抽象,更为注重“气韵生动”(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称其为“六法”之首)的中国古典美学品格。
在作为舞剧的《临川四梦》中,舞蹈道具的使用和舞蹈动作的配合把传统戏曲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舞蹈的舞台没有了“唱”和“念”的声音审美和剧情描述,对舞台布景、舞台道具和身体语言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个梦、四场舞蹈、表面看来都讲述了男女之情,但是又各有怀抱。本场舞剧正是通过别致的背景、别致的道具、不同于戏曲程式的身体语言表现了四场梦不同的悲欢故事、不同的人生领悟。
《紫钗记》,开场就一改传统戏曲一桌二椅的极简布景,呈现出舞蹈背景的华丽转身,舞台上随意点缀的低矮的红灯笼,勾勒出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喜庆气氛,既不过分喧闹,又凸显传统文化的韵味。红色灯光辉映着初坠爱河的青年男女含羞的面庞;确定紫钗作为信物后,二人持钗而舞,吸收了戏曲意蕴的古典舞,通过委婉地身体语言表达心心相印的感情:二人一方面各持折扇,通过扇子的平行、重叠、托举表达情意;另一方面,二人伸向背后的手各执紫钗的一端,凸显了紫钗记的主题。
《邯郸记》的背景主体是两片巨大的浮萍,卢生与女子相会其间,也共舞其上。浮萍本身就是漂泊、动荡的化身,暗示这段感情也注定是无根的幻梦;油纸伞在这段舞蹈中是重要的道具:他们头上撑开的伞宛如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他们在伞下拥抱、旋转,表现出平静生活的和谐美好。法场上的卢生依旧想躲到伞下,重回到安逸温暖的生活中,但是弱女子无论如何勇敢的举起伞去驱赶这场灾难,都终究无法阻止伞的最终滑落,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南柯记》中醉酒公子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有幸娶得公主,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本已奢侈的幸福,画外音说:“念情公主许终身,才知淳郎好色心,一仆一主一郎君,总伤情。”于是长长的粉绸带将三个人:一仆一主一郎君,共同牵动,构成了被彩绸包围的三角形结构,暗示出三角的恋情。本段舞蹈最后大幅的红布铺在舞台上,淳于棼慢慢从中爬出,暗示出他脱离了滚滚红尘,实现顿悟。
《牡丹亭》为了表现后花园的地理空间,设计了一个古典的花门,春香和丽娘从中走出,发现了闺阁之外的“春色如许”,这个门既是重要的布景,也是丽娘生命的关节点,踏入春阳园林的丽娘从此经历了生死相许的爱情。为了暗示梦境的虚幻,一条长长的白绸带从舞台上空垂下,丽娘也就从现实走入了梦境;还魂之后的丽娘与柳梦梅共舞缠绵时有白色的烟雾在脚下流动,他们仿佛在世外桃源畅饮幸福的甘露,烟雾的梦幻色彩凸显了这场爱情的唯美和易逝。
时间——空间
在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有所谓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划分,戏曲和舞蹈作为舞台表演艺术,通常被认为是时空艺术,这里的时空观念主要是说明舞台表演的空间造型感和故事情节发展的时间线性脉络。在舞剧《临川四梦》中,笔者所要讲述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时空,而是一种抽象的时空,是舞剧作品自己建构的一个独特而虚幻的时间和空间。
舞剧的开场,画外音首先传达了这样的声音:“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在下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氏,诸位看官,你我也是这梦中之人。”舞剧结束时,假托汤显祖的声音又传来:“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此四梦者乎?此四女子,悲凉凄婉,摘艳古今,是有“四梦”,曼妙之情,敬献看官。”舞剧由第一人称的讲述者“在下(我)”开始叙事,但是,故事的情节中又不包含“我”,实际的叙事呈现为第三人称的状态,叙述者看不见摸不着,如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幽灵。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给舞剧的展开提供了便利。“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叙述空间的转换十分自如。唯其如此,第三人称叙述是全方位叙述的基础,当小说家打定主意采用所谓‘上帝式’无聚焦模式来展开故事时,他就必须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只有在这种叙述中,叙述话语才能由此及彼地进入各个人物内心深处,去向读者透露出他们的所爱与所恨。”[3]所以之后舞剧的展开,从霍小玉与李郎邂逅的元宵灯会,到淳于棼的大槐安国,到杜丽娘动情的后花园,观众被引领,穿越到不同的叙述空间之中;第三人称的叙述还可以清晰表达叙述者的爱憎,每一梦开始的画外音都可以让观众感觉到叙述者的情感指向:比如邯郸记中“美娇娘真堪女英雄,男儿汉反做了小”;南柯记中“痴女子难逃她情多”;舞剧最后“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第三人称的叙述还会造成间离性的效果,和第一人称的“进行式”不同,第三人称的叙述带有“完成式”的特点,使得故事展开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脱离了关系,因此舞剧的观看者获得了一种超脱性,似乎可以居高临下地与舞剧的讲述者一起依次品评这梦中故事。四梦的前后排列之间虽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却仿佛是一种如桔瓣般展开的空间结构,构成了叙述者对生死、情爱、男女乃至人生的感悟。
由四个独立的梦合成一梦,由戏曲文学到舞剧的改编,四个梦不是零乱地组合在一起,不是向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相同的主题、人物或情感上,四个并置的梦具有同等的价值。叙述者在同一主题“梦”之下并置叙述了时间不确定,空间相隔甚远的四个故事。这些故事都讲述了梦中人、梦中事,都有痴情女子,都具备爱情的悲欢离合,并且共同凸显了女性的至情至性和为爱痴狂的性别特质。由于“梦”的主题本身禀赋的虚幻色彩,一切情爱与功名利禄也都变得空幻无常。所以四梦围绕叙述的既是爱的主题也是人生虚幻的主题。针对这样的主题,本场舞剧采用的主题——并置的叙述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独特而抽象的空间结构[4],是与叙述时间的不确定性相伴随的一种空间叙事。本舞剧呈现了元宵灯会、邯郸道上、大槐安国、后花园四个不同的场所[5]以及其间的爱恨情仇,共同支撑了对主题——梦——虚幻的艺术展示。基于此,舞剧《临川四梦》在抽象的时空经纬中获得了独特的意义。
刘三平:中国戏曲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注释:
[1]还魂记即《牡丹亭》。
[2]刘青弋:《论戏曲舞蹈的美学创作》,原载于《北京舞蹈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3]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版,第316页。
[4]“主题——并置叙事”,参见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8页。
[5]主题(topic)这个概念由场所(topos)这个概念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