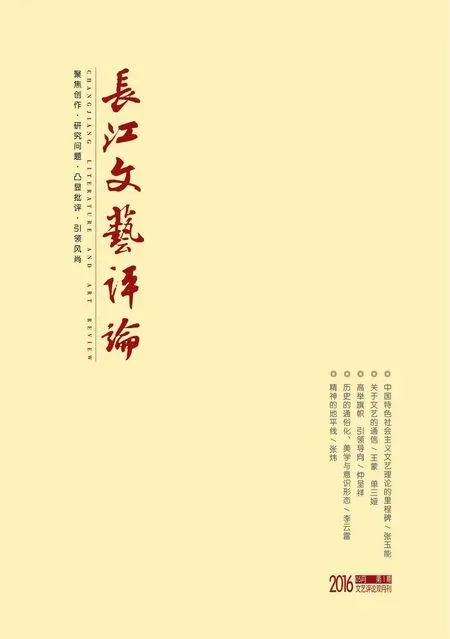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
2016-11-25◎傅谨
◎傅 谨
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
◎傅 谨
文艺评论有多重功能,针砭文艺界的时弊,激浊扬清,是今天我们从事文艺批评事业最重要也最直接的社会责任。但文艺评论还拥有更强大的功能,评论不仅是为了指出个别作品的成就和缺失,健康有力的文艺批评,更要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褒贬和评价,引导读者观众形成正确的文化立场和艺术理念。因此,一个时代以及文艺评论家秉持怎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如何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彰显这一文化观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批评如何发挥其效用,实现其功能,以及发挥和实现怎样的效用与功能。中国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邃的美学内涵,然而却在近百年来遭遇外来文化强烈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又是通过诸多戏剧评论家对传统戏剧的错误认识与评价起作用的。通过健康与正确的戏剧评论,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这是改变民众对传统戏剧的深刻偏见,进而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生存的舆论环境,促进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
一
中国传统戏剧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的重要门类,凝聚和浓缩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宋元至今的八百到一千年历史中,传统戏剧发展几经沉浮,然而唯有在20世纪,戏剧的命运最为坎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20世纪以来不同年代的戏剧评论家如何看待传统有密切关联,而各时期戏剧批评家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尤其重要。
当代戏剧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始于清末民初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和繁荣,除了如《申报》《顺天时报》等影响广泛又关注戏剧表演的大众媒体之外,还有以《20世纪大舞台》和《春柳》等杂志为开端的一系列专业戏剧报刊。戏剧评论大量出现并且与普通民众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互动,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观众的审美趣味与观剧选择,是中国戏剧自成熟以来面临的新语境。而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这些近代以来其社会与艺术观念影响迅速扩张的媒介,主要是由一批崇尚新学的知识分子创办且经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固然有救国热情,但是其知识背景以及思维与理论的基础,却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西学的。《20世纪大舞台》和《春柳》都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戏剧爱好者有密切关系,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专门组织的对传统戏曲的系列批评更是其代表。在《新青年》这份因为集中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精华而影响巨大的杂志中,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发表的多篇简单粗暴地否定传统戏曲价值的文章,完全是基于西方文化至上的观点立论的,对中国传统戏剧肤浅和漫画化的归纳,在学理上和观点上都漏洞百出的文章,居然得到相当多的拥护。
诚然,新兴的大众媒体对传统戏剧并非都像《新青年》诸公那样完全抱持敌意态度,如同在《顺天时报》和《申报》上撰写剧评的冯叔鸾、郑正秋等人努力发抉传统表演中的精湛内蕴,张厚载继在《新青年》发表数篇率先揭示了传统戏剧独特的艺术表现规律而引致围攻的文章之后,仍在从事他的相关研究,在其他大众化报刊里也撰写不少文章,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传统美学在20世纪的守护者。然而,他们的影响力仍远远不能与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启蒙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因此在整体上,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传统戏剧的意义与价值,具体到那些脍炙人口的戏剧经典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遭受了一轮又一轮批判。肇始于新文化运动的这类批判,在20世纪50年代又和苏俄的工具论相呼应,成为“戏改”运动的思想指南。从“戏改”到“文革”,在学术讨论的空间十分逼仄的背景下,对传统戏剧的褒扬和肯定,经常需要用一种十分曲折委婉与含蓄的方式传递给读者,所谓“继承精华、扬弃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口号,多数场合,其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在客观公正地对待传统戏剧,而是为了强调那些不朽的经典剧目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而经历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破四旧”为开端的“文革”之后,思想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又一次把中国传统戏剧作为批判的靶子,是在通过对传统的批判,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传统戏剧经历了20世纪这三次大规模的批判,千百年来深受中国各阶层热爱,体现了中华文明最精湛的艺术创造,深蕴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的传统戏剧,包括其中的那些杰出的经典作品,受到的摧残无以言表。在戏剧理论上,从20世纪初对易卜生的功利主义解读,到50年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观念的垄断,再加上新时期对西方现代派戏剧的盲目崇拜,构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消解传统戏剧的合力。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经历的这三大劫难,对中国人的审美选择,尤其是那些审美趣味正处于形成时期的青年一代的审美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要彻底改变传统文化在中青年几代人心目中的负面印象,最为急迫和关键的前提,就是从事戏剧批评的文艺评论家们,需要以更专业和更少偏见的视野,重新认识与客观评价传统戏剧,还它以本来面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人类的创造物是找不出缺点与不足的,因此,我强调的是认识与评价的客观性。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像民族属性和仅仅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这些非艺术的理由,漠视传统戏剧中确实存在的种种问题。
二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举着放大镜从传统戏曲中那些为几亿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里的“糟粕”,苛刻地指责那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足以跻身于人类最优秀的精神创作之列的艺术经典的种种与某种教条化的理念不相符的方面,不仅扭曲了戏剧界和整个文艺界的艺术评价体系,同时还严重挫伤了传统戏剧领域的创作演出者的文化自信,直接间接地导致了大量貌似“进步”的伪劣作品的泛滥。而且,正由于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也严重挫伤了各传统剧种的演员们常年刻苦训练、努力掌握传承经典之精粹的积极性。所以,尽管数十年来各级政府用各种不同方式呼吁“振兴戏曲”,但是,由于评论家们对传统戏剧的积极意义与正面价值没有正确和充分的认识,这样的“振兴”只能是缘木求鱼,其措施也多有如隔靴搔痒。
宋元以来,中国戏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特色。其中那些经历了时间和观众淘洗的经典剧目,就是中国人用自己喜爱与熟悉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最重要的结晶,同时还是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构建基本的社会人生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与手段。这个伟大的传统,既代表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共同维护的基本价值,体现了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同时更创造出一整套极具魅力的表现手法。因此,无论是从思想情感的内容层面,还是就舞台表现的形式层面上,传统戏剧都具有无与从伦比的人文价值。
传统戏剧遭受的诸多批评中,在思想内容方面最集中的批评,就是认为大量传统剧目都以张扬“忠孝节义”的道德内涵为主题,认为传统戏剧中的正面人物,突出表现了愚忠愚孝的性格特征,因而必须批判与扬弃。诚然,忠孝确实是传统戏剧最核心的主题,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那些优秀传统剧目中通过丰富多彩的故事和人物所彰显的“忠孝节义”,才让民众分清了好人和坏人、好事和坏事,因而生成了小到对日常生活大到时代巨变中的事件和人物正确的判断力,然而彰显“忠孝节义”主题的剧目能够让观众对之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是毫无疑义的。简单化地、不分场合和不辨是非地强调“忠”和“孝”、“节”和“义”,或许会导向机械的和僵化的道德至上主义观念,然而我们同样不能简单化地、不分场合和不辨是非地反对“忠”和“孝”、“节”和“义”,毕竟忠诚相对于奸佞、孝顺相对于忤逆、有节操相对于没有基本的原则和信念、讲义气相对于言而无信的背叛,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肯定的优良品德。况且在优秀的传统剧目里,还有像《上天台》这样表现滥杀功臣的帝王灵魂备受煎熬的剧目,有像《打龙袍》这样表现敢于当面斥责皇帝之非甚至要给予惩治的剧目,有更多以皇亲国戚为反面人物的剧目;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水浒”题材剧目,基于《隋唐演义》改编的众多剧目,也强调正义高于皇权。
因而,“忠孝节义”本身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在传统戏剧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剧目都有这样的价值导向。我们且以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剧目为例。首先,是元杂剧纪君祥的剧本《赵氏孤儿》,后世有以它为蓝本的《八义图》等剧目,民国年间京剧名家余叔岩的《搜孤救孤》更具影响。该剧着重表现了赵盾一家遭受灭门之祸时,他刚出生不久的幼子得到各阶层义士的保护,终于长大成人为家族报了血海深仇的故事。在一个时期内,这个剧目曾经引起广泛争议,批评家质疑这些义士为保护赵家的一枝血脉而牺牲是否“值得”,尤其是江湖医生程婴用自己的儿子换取了孤儿性命,两个孤儿的生命是否等价等等,却完全忘记了这些前赴后继的牺牲者的义举本身,是否体现了一种人世间最高尚的品德,是否激动人心。其次是很多剧种都有演出的《三娘教子》,它讲的是女主公在丈夫弃世,大夫人和二夫人都置幼子于不顾时,毅然承担起将孩子培养成人的重任。批评家认为这是在鼓励女性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尤其是在多妻制背景下丈夫离世,大房二房都已经改嫁,女主人公不仅在守节还要放弃自己选择新生活的权利、留下来养育非自己所生的孩子,简直愚昧到了极点。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这样的担当中,不仅有善良,还有责任,无论在什么社会哪个时代,她这样的行为都应该得到正面评价,而其他那两位急急改嫁的夫人,纵然有再多高尚的借口,也不值得称颂。其实,这两个广泛流传的经典剧目,所体现的都只是人世间最普通的道理,就在传统戏剧的“忠孝节义”受到批评时,这个道理居然也非夷所思地成为批判的靶子,是非之颠倒莫过于此。
多年来传统戏剧所遭受的批评中,还有种流行很广的观点,有理论家认为传统戏剧是“脸谱化”的,所以只偏重于表现人的社会性和共性,不能充分表现人的个性,甚至认为这种“脸谱化”的戏剧在其广泛传播的过程中,误导了观众,妨碍了人们个性的发展,因而在更重视个性的现代社会中,它们理应被扬弃。这样的观点不仅在有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是错误的,而且也完全不符合传统戏剧实际情况。诚然,戏曲中的净行和丑行人物多是勾脸谱的,但是也仅限于这两个行当,而且脸谱的运用,主要是净行。但是净行的脸谱十分丰富,大多数在舞台上深入人心的戏剧人物,都有各自独特的脸谱,以致人物仅靠装扮就能够让观众认识到不同人物的个性之差异。传统戏剧中的众多人物确实有共性的一面,即使在不同的剧目里,经常也会有性格和情感模式非常相似的人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优秀演员能够表现出同一行当不同人物的个性,才受到观众拥戴和欢迎。人们用“活曹操”、“活张飞”、“活云长”等称呼来褒扬那些将戏剧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的优秀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正说明了对戏剧人物个性化的表现,是所有民族和国家戏剧表演的共同追求。其实,将无可限量的戏剧人物归纳成有限的种类,尤其是从每一类型的人物中总结出突出的形体特点,是戏剧表演走向成熟的标志。不仅中国传统戏剧如此,西方戏剧、印度戏剧同样如此。因此,用“脸谱化”批评中国传统戏剧,不仅是对民族戏剧表现方法的误解,同时也是因缺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戏剧的深入了解所致。
传统戏剧的表现方式中与脸谱相关的程式化表演,也受到多种多样的激烈批评。某些戏剧理论家们看不到(或许是不愿意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表演艺术都具有程式化要素这一事实,片面而又粗暴地认为中国传统戏剧的程式化表演手段是反现代性的,认为传统戏剧具象征性和写意性的表演,不符合“现实主义表演”的要求,因此必须彻底改造。从民国初年钱玄同等人把它看成是“野蛮人的玩意”,到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非现实主义”为理由对传统戏剧表演方法提出非议,除了由于受到某种狭隘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支配外,还有就是因为文艺观念上只执一端、无法领会多元艺术各自拥有不同价值。按照这样的批评,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就只能有一种模式,戏剧的舞台表现就只能有一种方法,这简直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要让所有鲜花都变成同一种颜色”一样奇怪。
多年来,在中国传统戏剧遭受各种非理性的批评的过程中,这门优秀的艺术及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戏剧界的业内人士,都已经很难用平和坦然的心态欣赏和评价这门艺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面对的重要工作。
三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中国无数代优秀的艺术家创造了精妙绝伦的戏剧艺术,同时又将发达的文明和包含优良品质的民族特性灌注其中,所以这门艺术才有其光华,才有不可替代的人类价值。当代文艺批评家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同样具有创造性的研究与介绍,阐发传统戏剧中那些优秀保留剧目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内涵,揭示优秀的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家的舞台演绎传神写意的精彩手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消除对传统戏剧的偏见、走进剧场,有机会欣赏和感受我们自己民族独一无二的经典剧目和精彩表演的无穷魅力。
每个时代的文艺评论家都有时代所赋予的特殊的任务。进入21世纪初以来,曾经弥漫全社会的鄙薄传统的风气得到了有力的矫正。在戏剧领域,人们逐渐改变了对百年来思想文化界的粗暴批判的盲从心理,从事传统戏剧创作与表演的艺术家们对那种民族虚无主义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警惕,民族戏剧传统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也开始逐步成为新的共识。然而,要真正实现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目标,除了在理论上廓清是非,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认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意义,还需要引导民众通过客观、公正地认识民族文化传统,在感性层面重建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情感认同。对今天的戏剧评论家而言,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是时代最为迫切的要求。
肩负民族文化的这一重托,我们当然要在理论上阐明民族戏剧的特色与价值,让中国戏剧中无数优秀的经典作品为更多人所知。同时,还需要基于民族戏剧优良传统的立场,通过对当下的创作与演出的评论,阐发中国戏剧的特殊魅力。让越来越多人学会欣赏戏剧,尤其是通过对作品的实际欣赏认识与把握传统戏剧经典作品和精彩表达的魅力。这里所说的评论,首先是指那些无数观众早就用他们的喜爱充分证明了其价值的传统保留剧目,同时也包括当代戏剧作品的创作演出的评论。而涉及当代创作演出的评论,清晰地指出那些杰作与传统的密切关系,十分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往还是当下,那些优秀的传统戏剧作品及其演出之所以有其魅力,都与艺术家不同程度且以不同的方式创造性地继承传统相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未来,始终是优秀戏剧作品常演常新的关键。而揭示当代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这一内在的规律,更是优秀的戏剧评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一样,应该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华民族的伟大戏剧传统,是否能够站在充分尊重本民族特有的戏剧美学的文化立场上评论传统戏剧的创作与演出,就是当代戏剧评论是否具有正确的思想导向的重要指标。当然,精彩的戏剧评论还应该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应该努力从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的层面,充分发掘优秀的戏剧作品的魅力之所在。通过这样的评论,吸引与召唤越来越多的观众回到剧场,重新激发他们对优秀戏剧作品和演出发自内心的热爱。这样的评论,需要在文化理论和艺术实践两方面的充分准备,这就是当代戏剧评论努力的方向。
当然,首要的关键,是文艺评论家本身要正视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尽管传统戏剧被妖魔化的现象,是与传统文化在整体上被欺凌同步的,然而戏剧因其表现形式上的特异性,受到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其他领域,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演出环境的急剧恶化,又使它丧失了观众和市场的支撑。因此,戏剧界正本清源的重任,要比一般的领域更艰巨。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天活跃在戏剧评论界的大多数评论家和理论家,都是在20世纪鄙薄和歧视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完成其教育的,几代戏剧评论家和理论家在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深受浸染。在20世纪前述数次对传统戏剧大范围的批判中历史地形成的错误观念,不幸成为人们评价与批评当代戏剧的创作与演出的主要的理论资源。因此要重新认识与客观评价传统戏剧,比起纠正和改变普通观众的审美选择来,是更优先和更迫切的任务。文艺评论家自身要改变对传统戏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自觉主动地承担起通过评论让传统戏剧重新获得当代观众和社会重视与珍惜之时代责任。
因此,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不仅是为了让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和更多渠道欣赏传统戏剧,分享其中的精彩与伟大,更需要唤醒戏剧理论家、评论家的文化良知,让新一代戏剧理论家、评论家重归正道,热情和真诚地拥抱传统戏剧,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守护者。
傅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