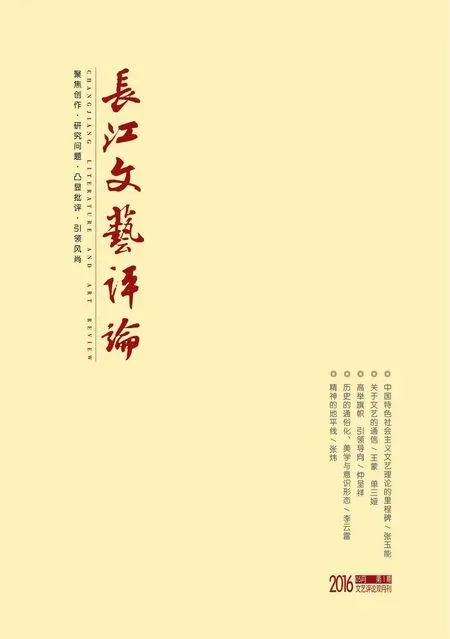杨光祖的文学批评
2016-11-25李建军
◎ 李建军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
◎ 李建军
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否则,他就有可能知而不言,或者言不由衷,以至于以歪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也就是说,批评家一定要克服患得患失的恐惧心理,努力摆脱外部的压力和内心的怯懦,以真诚的态度和真实的表达,来陈述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认知和评价。
事实上,直到今天,古人所说的“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就文学批评方面来看,情况似乎更加严重,——很多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而高贵的文化行为,业已沦为缺乏自由精神和尊严感的“谀评”,甚至沦为一种纯粹的寄生性的现象。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接受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哲学,接受他者的“社会订货”,用一套永远不变的话语模式——诸如“高峰”、“巅峰”、“杰作”、“极品”、“经典”、“奇书”、“完美”、“伟大”、“辉煌”、“天才”、“震撼”甚至“地震”等——来赞美一部并不成熟甚至完全失败的作品。这种批评的根本特点就是“谀”和“谄”,就是“不诚实”和“不坦率”,缺乏对事实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敬畏。那些“谀派批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任何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的判断和表达,都是对批评的道德原则的背叛,都是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非谀派批评家。杨光祖就是这不多的批评家中的一个。最新出版的批评文集《杨光祖集》,就很集中地彰显着作者的个性、才华、文学理念和批评风格。三代以下无完人,崤函以西少批评,在西部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批评家中,杨光祖无疑是特立秀出的佼佼者。
从批评伦理的角度看,杨光祖的批评具有正直、坦率和诚实的品质。他曾写过一篇近乎宣言书的文章——《文学批评要讲真话》。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底线伦理”这一概念,认为“文学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底线”[1]。他尖锐地表达了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失望和不满:他批评现在的批评家“缺乏独立品格”,[2]对杨光祖来讲,独立和尊严、诚实和正直乃是批评应该遵守的首要原则。“正直”甚至就是他评价作家和作品的一个稳定尺度,例如,他批评贾平凹的写作缺乏正气,“一种不正的东西被释放出来了”[3];在《废都》里,“庄之蝶玩弄女性,而作家玩弄读者”[4];贾平凹身上有一股邪气,“正是这种邪气成就了《废都》,但也让他没有成为文学大师的可能。”[5]
同样,“真诚”也是他评价作家和作品的重要尺度。他引《中庸》里的话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杨光祖认为,这段话“说道尽艺术之奥秘”[6]。他用这段话来说明文学批评的标准,并以它为“准的”,阐释了杨显惠的《加边沟记事》等作品的“真诚”、“真实”、“苦难意识”和“宗教精神”。也正是以“诚”的尺度为参照,他发现了莫言的《蛙》和贾平凹的《带灯》在叙述方式和细节描写上的做作、虚假和无聊。在《<带灯>: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贾平凹的小说普遍缺乏情怀、意义和真实感,普遍存在趣味上的败坏等等问题。《带灯》里的虱子,从头到尾,铺天盖地,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别的意义。只感觉到一种恶心。我们读马尔克斯,读鲁尔福,他们的魔幻里有情感,有思想,有不平,有反抗。而贾平凹的魔幻里多的是肮脏、萎靡、恶俗、无聊。”[7]由于坚守正道和直道,所以,在杨光祖的批评文章中,你就很少看见言不由衷的夸赞、不着边际的妄断和投其所好的逢迎。在他的批评文字里,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作者自己的真诚态度和坦率性格。
真诚意味着发现问题和直面问题。在一个乱象纷呈的转型时代,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拿出眼光和勇气,敏锐地发现问题,坦率地指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从而对自己时代文学的成长和成熟,提供积极的“支援意识”。杨光祖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严重问题。他发现那些追求“纯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常常将“技巧”和“形式”当做一种自足的价值来追求,而忽略了那些更为本质的东西。
战争是人类生活中最为悲惨的灾难,也是文学叙事的重要主题和题材。关于战争的想象和叙事,考验着一个时代的文学,考验着作家在追求人道主义精神、洞察人性、创造道德诗意等方面的能力。然而,在中国的汗牛充栋的战争题材和军事题材作品中,却很少看到真正伟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呢?杨光祖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发现,中国的作家常常陶醉于对暴力——包括战争暴力和性暴力——的渲染,而不是深入地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他点名批评了莫言、红柯、贾平凹、杨争光、孙皓辉、姜戎等人的暴力叙事。
恶俗是当代文学叙事中极为常见的严重问题,也是杨光祖特别着力解剖的一个文学病象。在批评这一现象的时候,他的正直和坦率,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令人无法不击节称赏。长期以来,由于很多批评家无原则的赞赏和辩护,由于市场的接纳和鼓励,甚至,由于文学体制的纵容和奖赏,文学中的那些可怕的恶俗,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空间。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严重的后果:那些获得声望资源和市场认同的作家,继续肆无忌惮地以粗俗方式写作,而读者也对这种羞辱自己尊严和智商的粗俗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在一部恶俗的作品后面,不仅站着一个“著名作家”,同时还站着许多“著名批评家”。谁如果想批评恶俗,想对《废都》《檀香刑》《兄弟》这样的恶俗作品宣战,那么,谁就等于要同时冒犯恶俗的作家与赞赏恶俗的批评家,甚至还得冒犯一部分已经习惯了恶俗的读者。然而,杨光祖偏偏就有这样的正直和勇气。他常常“敲明叫响”地向那些“著名作家”发难,向那些名头很大的“学院派”学者和批评家发难,对他们进行尖锐的质疑和驳诘。这一点成功地体现在对余华的《兄弟》的解剖上以及关于它的“批评”的批评上。
作为批评家,杨光祖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就是“直”。他清醒地与那种煞有介事而又华而不实的“学院派”批评保持距离。他在解读作品的时候,严格根据自己的具体感受和作品的具体事象,来展开分析,来进行判断,绝无大而无当、言不及义的“话语空转”,也很少感染随意概括、妄下雌黄的流行病。
在对作家和作品展开批评的时候,杨光祖很善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抱着一种体贴入微的态度。他在分析张爱玲的《小团圆》以及她的“阴影”和“创伤记忆”的时候,就入情入理地分析了她的“两面性”,分析了人心和人性的不可言状的复杂。同样,他对张贤亮的“冷漠”、“罪感意识的缺乏”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批评虽然尖锐,近乎不留情面,但是,因为能以伟大的经验作比照,据实道来,因而,就显得很有人情味,也很有说服力。
杨光祖读书多,学养好,但从不卖弄知识,或者故意把文章写得云里雾里,以显示自己的博雅和高深。他坚持用清楚明白的语言,甚至近乎口语的家常话,来表达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感受和评价,例如:“贾平凹《废都》《白夜》之后,就几乎没有什么好作品,《高老庄》还差强人意,《病相报告》《土门》《高兴》基本是失败之作,《秦腔》《古炉》有人评价很高,也得了很多奖,惭愧得很,我真得没有看出‘伟大’来。《带灯》2012年岁末买的,2013年2月末才强迫自己阅读,读完上部山野,就很失望。语言倒还通达,不像《秦腔》那么艰涩,但文字没有力量,人物对话汤汤水水,读了40页,整整一个上部,仍然没有一个人活起来,没有一句话,让人记住的。”[8]这样的语言,毫无“学院派”拿腔作调、半通不通的滞涩和乏味,读来但觉亲切和可爱。
文学批评的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无个性化,一直就是个大问题。有的批评家下笔洋洋洒洒,满纸烟霞,但就是听不见他自己的声口,看不见他自己的身影。他被那些高深“理论”的给淹没了,被作家和他的作品给压垮了。然而,杨光祖的批评却与之不同,属于处处有我的个性化批评。他运情入文,始终在说自己的话,阐述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在他的文字里,总能感到他作为“我”的个性化存在,总是能感受到一种沛沛然的激情和正气。他在《形式与文学的生长》中说,“文学形式最本质的意义,就是对生命本体的观照”,然后,他立即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体验,对这一判断做了具体的说明:“2008年11月12日车过董志塬,满眼苍黄,一望无际,司机忽然打开秦腔CD,时高亢,时低回,或壮怀激烈,或柔情似水,正与这山川契合。这真是一种生命的歌哭。那一刻,我内心里一阵感动,泪水都涌上来了。而在甘肃甘南,车行草原,雪山,白云,绿草,只有藏歌最适合那片土地。试想在杭州西湖吼秦腔,会是什么感觉?身处田田荷叶里,只有越剧、昆曲,从生命深处流出,欲唱秦腔口难开,因为根本没有那种生命的冲动。”[9]这样的文字,是有温度的,有感染力的,是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的。在一篇理论性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就像在无边的沙漠里看见绿洲一样,就像在寒冷的冬夜里看见篝火一样,是会让人特别欣悦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充满绿色的生机,应该散发出火的光热。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挑战人的才华和创造力的文体,而好的批评家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好的作家。所以,将批评文章写得枯燥乏味就是严重的失职,其罪错一点儿也不比判断失误和识见浅薄为轻。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2][3][4][5][6][7][8][9]杨光祖:《杨光祖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252页,第251页,第173-174页,第174页,第177页,第83页,第231页,第229页,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