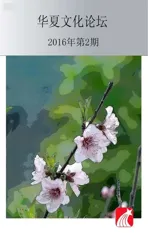汉语史研究新版图:构想与实践
2016-11-25刁晏斌
刁晏斌
汉语史研究新版图:构想与实践
刁晏斌
我想讲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对我所了解的汉语史及其研究提几个看法,不完全是肯定。在我看来,以后的汉语史研究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最后形成一个新版图。
对现在的汉语史研究,我有几个认识,可能不准确,但是我想大胆地提出来。
首先,我认为现在的汉语史是一个异质的汉语史。完整的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内部应该具有同一性,然而,我们都知道汉语史最基本的划分就是三个阶段,即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这样的划分有什么不妥吗?我认为是有一定问题的。比如,有一个问题大家始终在争论,但却没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上述三个阶段的划界问题,特别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起点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上边所提到的“异质”使然。简单地说,传统的汉语史三个阶段的划分内部不具有同一性,所以就没法按某一或某些既定的标准对它们各自的起讫做出科学的界定和划分。我特别关注现代汉语的起点,我在自己的书中也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已有的观点认为现代汉语最早是从元代开始的,而最晚的则认为是建国以后才开始的,时间跨度特别大。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谁都说不好各阶段的交界处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划分,自然划分不清。
其次,现在的汉语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半截子、不完整,主要是有头没尾。很多汉语史著作基本都是讨论到清末就结束了,也有的略为涉及一点“五四”时期,像《简明汉语史》等书,只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小节,列出“五四”以后的若干发展变化,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至于一般的汉语史研究论文,考察和叙述的下限通常都在有清一代。我做的是“现代汉语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想补上传统汉语史研究中所缺的从清末至今的这一段。这一段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很短(与几千年的汉语史相比),但它毕竟代表和反映了离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汉语发展变化的实时情况,有了它,我们才能看清从远古直到今天汉语发展的全过程,而如果缺少了这一段,我们的汉语史无疑是不完整的。
再次,我们的汉语史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也是不完整的。这一点,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应该是不会否认的。比如,研究古代汉语,主要着眼于“先秦”的文言,东汉以后考虑得基本就不多了,也就是说,人为地确定了一个古代汉语的截止点,到了这个点,所有的研究基本上就戛然而止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文言在中国使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它也没有消亡,也就是说,文言有自己完整的发展史,但是却被我们的研究拦腰斩断了,有很大一部分完全被排斥在研究之外。近代汉语所研究的古白话一定程度上也有这个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对它的来龙去脉并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它,并未进行完整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一点认识,我才提到了汉语史新版图的问题。
为了给以上所说各点提供一个依据和佐证,我们不妨找一个参照,这就是著名的《剑桥英语史》,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格局。它有三条线索,第一个是时间的线索,即从上古开始一直写到交稿时的1997年,这一点和上述半截子的汉语史对比强烈。第二个是地理的线索,从第五卷的“世界各地的英语”,到第六卷的“北美的英语”,即美国英语,在以前美国英语是不被承认的,它在第六卷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美国英语。这个线索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本人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德国具有260多年历史的高端学术出版机构德古意特出版社合作创办了一个中英双语的国际学术期刊“GlobalChinese”(《全球华语》),而我们对全球华语的研究实际上和这个英语的线索所反映的东西是相同的。第三个是内容的线索,其所讨论的对象涉及语音、形态、句法、语义、专名(人名、地名)等,因此比我们传统的汉语史范围更加宽广,同样也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这是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接着说汉语史。除了刚才提到的不足,对现有的汉语史还应该有更多的认识。比如,谈到现在我们的汉语史,其实主要是汉语书面语的历史。虽然人们在近代汉语研究中重视并强调口语,但是不要忘记即使这样的口语也是用书面语来记录和表达的。所以,汉语史其实就是汉语书面语史。
谈到书面语及书面语史,我们想简单谈一下双文现象。以前,提到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想到拉丁语,因为拉丁语书面语和欧洲一些民族的书面语言长期并存,构成双文的格局。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台湾学者写的文章,她在哈佛毕业后拿到的毕业证,上边的字不认识,问别人才知道用的是拉丁文。文言文曾经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拉丁文”,而与之长期并存的,则是古白话。所以,中国历史上也曾经长期存在双文现象。
通过比较,我们基本的认识就是汉语的文言文也经历了和拉丁文差不多的发展过程,由发展到“消亡”,它有自己完整的历史,当然,古白话也有自己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如上所述,既然汉语史其实是书面语史,而我们的书面语长期以来双文并存,那么,我们的汉语史就应该有两个,即专门研究文言发展演变的文言史,以及专门研究白话发展演变的白话史。换句话说,我们的汉语史应该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如果把两条线索掐头去尾地捏在一起,必然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上述几个问题,基本也都是由此而造成的。
刚才说到文言“消亡”,以前人们在论及现代汉语的形成时,往往会用到“文言寿终正寝”“白话文登上了历史舞台”之类的表述,而研究古代汉语(文言)的人也经常自嘲,说自己是研究死了的语言的。所有这些,似乎都指向了一个相同的结论,这就是现实中文言已经消亡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我做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研究有20多年了,在做了很多的研究以后,我坚信一点:文言仍在,从未离开。
这个问题有专门讨论的必要,限于时间,我们就此打住。不过这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孙德金教授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版),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就回答了现代汉语中文言是否消亡的问题。
以下就说到本次演讲的题目:汉语史研究的新版图。2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在为江蓝生先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所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长期的言文分离,给汉语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这样也许比较容易论述。”本人以为,吕先生的话大有深意,非常值得重视,循此以往,可以建构一个全新的汉语史体系,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语史新版图。
在语音、文言、白话三史中,语音很大程度上是口语的反映,但中国的语音及其发展又是很复杂的,所以两者并不能画等号,因此语音史有很强的独立性。另外二史都是书面语史,二者有共同的起点,根据一般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姑且把汉代看作传统的文言分化的开始,或者说是白话的起点。整个文言史基本是“波澜不惊”的,即一直没有太大的起伏,但是也有很多具体的变化,特别是着眼于文体,后来进一步分化为“同质”的文言(包括先秦的“正宗”文言和后来历代的“拟古文”)和“异质”的文言(包括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以及近代以来的“欧化文言”等)。异质文言相较于同质文言自然有较大的变化,就是同质文言内部的正宗文言与拟古文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而这些就构成了文言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白话史则有更为明显的曲折变化,基于一般认识,多数学者认为其起点应在唐代,主要是因为这时候的古白话作品反映的当时口语面貌比较完整,与前面有也较为明显的差异。白话从文言脱胎、分化而来,与文言渐行渐远,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词汇及语法系统和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史。
我们讨论汉语史的新版图,主要是立足于现代汉语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即试图回答现代汉语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代汉语是由文言史与白话史共同汇入而成。二史汇入现代汉语各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表述为两座桥,一个是“欧化文言”,一个是“欧化白话”。“欧化”对于我们来说耳熟能详,平常说的都是欧化的白话,实际上文言也是有欧化的。文言经过欧化,所形成的与传统文言大异其趣的欧化文言,对其后现代汉语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并且最终作为其重要来源之一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现代汉语,而白话经过欧化后也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现代汉语。
实际上,现在我们提出文言史和白话史,都是有了一定基础的,即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进行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说,汉语史的新版图不仅只是一个构想,其实也已经进入研究的实践环节。比如关于正宗文言,就有徐朝华的《上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姚振武的《上古汉语语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关于拟古文的,有谢序华的《唐宋仿古文言句法》(中华书局2011年版);关于白话史的,则有徐时仪的《汉语白话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当然,对于完整的文言史以及白话史的建构而言,上述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文言史,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端,即从远古时期汉语书面语言产生,直到先秦时期文言定型,这期间有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发展过程;二是后端,即明清以来在外来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欧化文言”所反映出来的对传统文言的发展和改变;三是两端之间的漫长时期,这一段时间内则主要是文言系统内部的“微调”。
以上三个阶段,都没有搞得特别清楚,大家所做基本还是一些碎片化的研究。后端的研究,欧化文言很多人都还很陌生,而在我们看来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与现代汉语的来源直接相关。另外,作为学术概念,欧化文言本身也是很有深意的,也值得深入探究。
欧化文言主要是因受外语的影响和冲击而生,由此也与传统文言拉开了距离,它是文言发展的转折点,传统文言正是借由这种转折“变身”进入现代汉语中。至于文言史两端之间的长期存在,虽然主要是系统内部的微调,没有造成基本格局的改变,但是小的发展变化也有很多,而因为长期以来文言无史,所以今天总体上对其还不得而知。
关于白话史,徐时仪也分为三期,即秦汉到唐的露头期、唐到明的发展期、明到清的成熟期。我们想作一补充的是,清代以后,白话史并未结束,而是一直延伸至属于今白话的现代汉语。在这个过程中,欧化同样也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文言史一样,三个阶段本身以及它们经过怎样的发展,最后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样貌融入现代汉语之中,都有很多的未解之谜,因而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究。
最后,对我们以上所说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传统的汉语史及其研究,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它基本是“文体拼接式”的,即第一阶段古代汉语对应的是文言,而第二阶段近代汉语对应的是古白话,第三阶段现代汉语对应的则是今白话。这样,整个汉语史势必就成了文言——古白话——今白话这三种不同的文体首尾相接的历史,而这三者之间显然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因此把它们硬串在一起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三者中的前两者各有自己完整的历史,并且最终共同汇入现代汉语,一直沿用下来,从而成为延续到今天、仍在继续发展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赞同吕叔湘先生的汉语史三分说,并且特别强调分别建立文言史与白话史,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语史新版图,并且认为借由这种新版图及其研究,我们的汉语史才能把各方面的关系理得更顺,才更加科学、合理、完整。
刁晏斌,男,1959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本文根据刁晏斌先生2015年4月13日在吉林大学学术演讲的演讲稿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