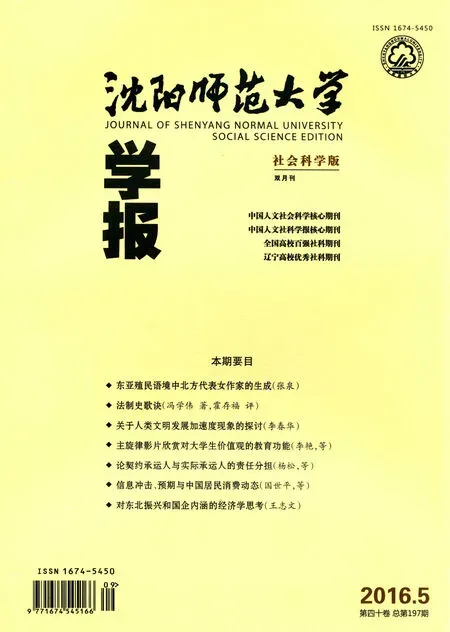殖民语境下东北新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以梅娘在伪满文坛的两种文学身份标签为中心
2016-11-21王越
王越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青岛266109)
殖民语境下东北新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以梅娘在伪满文坛的两种文学身份标签为中心
王越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青岛266109)
梅娘的文学之路始于伪满洲国。这时期梅娘在文坛上具有两个身份标签——“文丛派同人”与“满洲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1936年至1940年,梅娘与《大同报》副刊作者群关系密切,成为伪满汉语文坛重要文学社团文丛刊行会的同人。但仔细考察梅娘这一时期的作品可发现其文学观念与受左翼文学影响较大的文丛刊行会不完全一致。这种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被韩护称为“自由主义文学”。梅娘的存在代表着殖民语境下东北新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这也是沦陷时期新文学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证明。
东北新文学;伪满洲国;梅娘;同人
无论是作为“见证百年中国风雨历程”的知识分子,还是20世纪40年代便以“南玲北梅”的称号惊艳于文坛的作家,抑或是在历史动荡中将一生铸成传奇的女性,梅娘的每一个身份都非常独特。从东北到日本,从沦陷时期的北平到日据时期的台湾,从作为殖民地的伪满洲国到新中国,梅娘以多重身份跨越了巨大而复杂的历史时空。研究者不论从历史或文学角度进入梅娘的生命,所见到的景观都极为复杂。本文将研究范围定位在梅娘文学生命的初期,旨在考察伪满文坛中的作家梅娘,描述梅娘踏入文学之路的初始姿态。已有部分相关论文通过文本细读详细考察过梅娘的从文之路,本文关注的是梅娘在伪满时期汉语文坛中的位置与评价问题。
一、作为“文丛刊行会”同人的梅娘
梅娘的文学之路始于伪满时期。1936年,梅娘开始在《大同报》上发表作品。1937年益智书店出版其处女作小说集《小姐集》。在梅娘文学生涯初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有两位,其一是梅娘在省立女子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孙小野①孙小野(1908—1994年),原名常叙,又名孙晓野,祖籍河北乐亭,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毕业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任省立女子中学国文老师,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篆刻家。,孙参与了《小姐集》的辑集、出版并为其命名。值得注意的是,《大同报》的重要副刊之一《文艺》的刊头画创作者即为孙小野,可推断孙小野应与《文艺》副刊部分编辑与作者有所交集。梅娘进入《大同报》工作是否与其有关尚未有史料可考,但至少可以将孙小野看成梅娘与《大同报》文学副刊之间的关联。这种关系使她与一般投稿人有所不同,梅娘在从文之初就与一个作家群落有一定联系。

1938年5月7日《大同报·文艺》
另一个对梅娘文学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她的丈夫柳龙光。早在赴北平成为华北沦陷区文坛举足轻重的领导者之前[1],1938年,在伪满洲国任《大同报》编辑长的柳龙光就已经成为伪满文坛的核心人物之一。有研究者认为,伪满时期汉语文坛最大的一场文学论争——文丛派与艺文志派关于“乡土文艺”论争的幕后策划者是柳龙光,而这场论争直接塑造了伪满文坛的格局[2]。
孙小野为《文艺》副刊创作刊头画,柳龙光在《文艺》副刊任编辑,这两个梅娘文学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在梅娘从文之初就为其确定了一个基本坐标。梅娘开始与《大同报·文艺》及与之相关的“文丛刊行会”越走越近,“文丛同人”逐渐成为梅娘在伪满文坛一个比较醒目的身份标签。
文丛刊行会是伪满时期汉语文坛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研究者通常称其为“文丛派”。文丛派形成于1939年,成员以《大同报·文艺专页》①《大同报·文艺专页》由《文艺》副刊编辑作者群策划创办。本论文依据的《大同报》各个文艺副刊均来自辽宁省图书馆1989年制作的缩微胶片版《大同报》。作者群为主,核心作家为山丁,成员十余人。文丛派的形成可以向上追溯到伪满初期的“北满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主要活动于1933年至1935年,成员有罗烽、白朗、金剑啸、舒群、萧红、萧军、山丁等,从作品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表现底层普通民众在沦陷区的苦难生活,隐含控诉社会黑暗、表达抗争与希望之意,承袭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关注社会现实、表现人生的传统。在“北满作家群”大部分作家相继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之后,他们的创作风格和文学观念由留守东北的山丁等人在文丛派的文学活动中继续践行。
吴郎在《大同报·文艺》上发表过题为《关于“文艺丛刊”》的文章,文中描述了文丛刊行会的成立过程:
这是犹落着寒雪的北地的二月底春,局促在大都市一隅的子夜旅舍的小屋中,山丁和我(指吴郎——引者注)翻弄着在半年以前系己弄的那点成绩(指《大同报》专页——引者注),翻着翻着,就偶尔触动到“也应该每个人整理一下过去的东西了”的话题,室里的三个人——山丁、吴瑛和我——使一种不知名的热识促使着,便无计划的做了一个较美丽的梦。
……所以从几多丛刊的名词当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史实名词“文艺丛刊”,简称就是“文丛”[3]。
……为了更激起全满文笔人的共鸣,曾向日满文笔者九十余人发送文艺丛刊发刊的致辞函件,这是以编审会同人的同义来发送的(柳龙光、梁世铮、氏森孛雄、小泽柳之助、孙鹏飞、冯稼椐、李庚、梁梦庚、季守仁等九人),并将该函全文刊登在《斯民》上,作为向全满全文笔人的致辞,以补遗漏的遗憾,这是七月上旬的事情[4]。
吴郎文章中所提到的编审委员会成员,就是文丛派的主要成员——山丁、吴郎、吴瑛、梁世铮、鹏子、坚矢、冷歌以及当时身在日本的梅娘和柳龙光。后来《文丛》的出版计划流产,考虑到当时的出版环境——伪满洲国实行纸张配给制度导致纸价高涨,文艺政策又异常严酷——所有杂志出版须官方审批,加上作者和编辑都是非职业的,稿源不稳定,这些都可能成为《文丛》流产的原因。虽然《文丛》没有问世,仍可从《文丛》当时的广告和宣传中窥见这个大型文学期刊的大致面貌。在“文艺丛刊”之一吴瑛的《两极》中写道:“《文丛》——迎着一九四○年的来临,贡献于满洲文坛的综合新刊,内容是纯文艺作品”[5]。
《文选》第二辑的书末广告中曾经登出“《文丛》一辑要目”:
新进作家论吴郎
满洲文坛现状及展望坚矢
短篇小说
觅苏克
人群冷歌
落雁梅娘
白骨吴瑛
禹德田琅
同流戈禾
末世纪的患者杨叶
故人娜娜方之荑
黑马崔束
没有太阳的家方格
中篇小说
水流山丁
蛇吴郎
日记系己
野火洪流
杨五爷徐徐
文评集鹏子
杂文三题陈刃
文艺杂感铮郎
海与兵队(译文)序阿部知二
散文
空间与人金音
人和狗的纠纷也丽
(未定)君猛
无题姜灵非
其他
由目录可知,文丛刊行会在成立之初企划的文学编辑出版活动相当具有野心,也的确成功地集结了当时文坛的一大批优秀作者。但伪满洲国的言说环境和政治文化的限制致使这些文学理想在最终实现程度上大打折扣,未能问世的《文丛》成为伪满时期汉语文学的一个巨大遗憾。
文丛刊行会另出版短篇小说集四种,分别是吴瑛的《两极》、山丁的《山风》、梅娘的《第二代》和秋萤的《去故集》。梅娘的《第二代》作为“文艺丛刊”之三出版,当时梅娘和丈夫柳龙光已身在日本,《大同报·文艺》的《文化动静》中曾有报道:“‘文艺丛刊’第二集,系梅娘的创作集《第二代》,原稿已由东京寄到,不久即将提出版审委员会。”[6]
从1936年5月在《大同报》文艺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作品《花弄影》到1940年出版《第二代》,梅娘逐渐由一个文学青年变成真正的作家,并具有“文丛派同人”的身份标签。文丛派与艺文志派是伪满汉语文坛最重要的两个新文学社团。作为“北满作家群”文学精神的承袭者,文丛派作家充分认识到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强调文学的使命在于再现现实、改造社会。正视人生现实,揭露黑暗社会的真相,揭示东北被殖民的本质,揭开侵略者和傀儡政权统治者的真实面孔成为这个文学社团创作的主要出发点。这种诉求使得他们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创作方法的选择上,偏重“写实”与“暴露”。文丛派这种“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学观念,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在殖民地背景下的特殊发展。
再来看梅娘,1938年初至1939年末,《大同报·文艺》(包括《文艺专页》)是梅娘前期创作较为高产的时期,《大同报》成为她的主要发表平台,这期间梅娘共发表作品如下表。

1938—1939年梅娘在《大同报》发表的小说

1938—1939年梅娘在《大同报》发表的译作
这些作品共同反映出梅娘文学创作前期的基本面貌。《花柳病患者》写因宿娼而患花柳病的老瓦匠就医的经历。《六月的夜风》描写两个铁匠与暗娼间的感情纠葛。《最后的求诊者》讲述了迷信“小病靠抽大烟”“给小孩子洗澡伤气”的无知父母求诊的过程。《傍晚的喜剧》写裁缝铺学徒小六子饱受冷酷严苛的内掌柜与蛮横霸道的少掌柜的侮辱和屈打,过着名为学徒,实为下人的悲惨生活。中篇小说《第二代》更是塑造出一群底层民众的下一代们的苦难生活。
文学题材的扩展是《小姐集》后梅娘创作的突出特点。这种创作变化得到山丁的称赞,他充分肯定梅娘关注底层苦难的创作视角,指出“《小姐集》描写着作者小儿女的爱与憎,《第二代》则横透着大众的时代气息,……泼剌剌地描写着一群游尸似的男女和一群浮浪的孩子”,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小姐集》到《第二代》,梅娘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前进的意识”[7]。山丁所说的“前进”是指梅娘的这些作品发现并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平民的苦难”,与文丛派重视时代性、强调文学书写底层与暴露黑暗的文学观念相一致,这成为《第二代》被收入“文艺丛书”的原因。
梅娘在伪满时期的从文之路可谓顺遂,在当时纸张匮乏、刊行困难的不利环境下能够出版处女作《小姐集》已经非常难得,“文丛派同人”的身份标签更是大大提升她在文坛的地位。韩护在文章中将梅娘与萧红、吴瑛一起列为“对满洲文运有着不可否认的推动的功绩的女性作家”,对其肯定可见一斑。对伪满文坛的“同人”问题,山丁这样说过:“满洲文学活动,说是个体的飞跃,无宁说是集团的蠕动”[8]。和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架构相似,伪满文坛的社团流派众多,各社团手中握有不同的发表平台和出版资源(文丛派的发表平台以《大同报》文艺副刊为主,另一个重要社团艺文志事务会则依靠日本人城岛舟礼领导的月刊满洲社和古丁创办的艺文书房出版期刊和单行本),同时各个文人圈子的流派之辩和意气之争也同五四时期相似[9]。这种文学运作方式使“同人”的身份显得愈发重要,尤其对青年作者来说,能否成为某一社团流派的同人直接影响其文坛地位和作品发表平台。这使得山丁、古丁等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热衷建立同人社团,同时一些青年作家也乐于追随加入。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同人之一,梅娘的文学姿态和文学立场与文丛派之间完全一致吗?
二、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梅娘
仅从发表平台、编审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和山丁的批评文章就得出作为“文丛派同人”的梅娘的文学姿态与文丛派高度一致的结论未免略显草率。山丁在评价梅娘时提到“前进的意识”,从“前进”这种表述方式看,山丁受左翼文学影响较大,这种文学观念通常以“进步的”或“落后的”来评价文学价值取向。从文丛派与艺文志派的文学论争中也可看出,阶级的标准是文丛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准则,写无产阶级平民大众还是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成为文丛派评价作品优劣与作家文学观高低的标尺。正因为如此,梅娘从《小姐集》中关注自我情感和内心世界展现,到《第二代》中题材扩展至描写社会底层的妇女与儿童,才会被山丁认为是“前进的”。山丁的这种结论是将梅娘的创作纳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总体背景中,注重其创作与现实主义文学或左翼文学的关联程度。
实际上,如果以文丛派“描写黑暗、暴露黑暗”的文学创作观念为批评标准,在《第二代》中,除《傍晚的喜剧》之外,梅娘这类题材的创作并不是她的水准之作。这与作家尚未进入创作成熟期有关,更多的则是因为梅娘与文丛派其他作家不同的文学诉求。
梅娘16岁丧父之前作为大户人家的庶出子女,在主母精神虐待之下生存的生活经历极大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对爱、关怀的寻求和表达成为她重要的创作主题。这就决定了梅娘在描写社会黑暗和生存苦难时没有选择控诉和批判,也规避了阶级的叙事,而更多的是关注女性和儿童,表现对爱的缺失,表达对爱的渴求,这种创作倾向使作品时时弥漫着苦难中有温情的氛围。后来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41年10月发表于华北沦陷区的《中国文艺》第五卷第二期的小说《侏儒》。《傍晚的喜剧》和《侏儒》的主人公都是受主人苛待、侮辱的学徒,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在于故事层面都描写了被当作下人使唤的少年悲惨的生存境遇。《傍晚的喜剧》描写了学徒小六子的屈辱生活。为了生计,患有眼疾的母亲将14岁的小六子送到杂货店做帮工,瘦小的小六子除了在残暴苛刻的掌柜和内掌柜的打骂中忙于烧炭、打杂等各种活计之外,还饱受与他同龄的少掌柜的欺辱。少掌柜“一手拎着耳朵,一手操起了领子”,小六子便“跟一只鹅似的叫那胖大的男孩子给拖出去”。梅娘在小说中展现出较强人物塑造能力,塑造出风骚、苛刻的内掌柜,好色、懦弱的掌柜以及暴戾的少掌柜等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
《侏儒》的主人公也是在油漆店做学徒的少年。不同之处在于,《傍晚的喜剧》停留在悲剧的展现上,作者将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判断隐藏在描写之后。《侏儒》则加入了叙述人女大学生“我”,作家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房东的患智障和侏儒症的私生子,小说的故事重点部分变为“我”基于同情与侏儒的交往。房东太太、邻居们对智力残缺的侏儒恶意相向、动辄打骂,侏儒的生父对其悲惨境遇视而不见,“我”则对侏儒心生怜悯,成为他黑暗冷漠世界里唯一的光亮,侏儒从“我”的关怀中获得温暖并最后因救“我”而死。
如果把《侏儒》看成是梅娘在两年以后对同一故事的重新创作的话,那么从中能够看到作家将这个故事的内核由借个体生存境遇展现社会性生存苦难,转化为对人性中善、关怀、爱等普世价值的宣扬和表达。
对相似故事情节的反复书写往往最能展现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文学价值取向。进入创作成熟期之后,梅娘选择将这个题材中蕴含的对爱、对关怀的寻求作为深入挖掘和阐释的重点,没有像文丛派其他作家一贯始终地坚持书写底层的生存苦难。由此可见,尽管伪满时期梅娘的部分创作在题材选取上与文丛派有相近之处,但从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看梅娘与其他文丛同人是不完全一致的。
《第二代》出版之后,除了山丁的评论之外,还有另一篇比较重要的批评文章——韩护的《〈第二代〉论》。这篇批评被收入《满洲作家论集》,编者是伪满时期文学批评界重要人物王秋萤,该书是伪满时期重要文学评论集之一。在文章中韩护用“自由主义文学”评价梅娘的作品,这种判断显然并没有将梅娘看作“文丛派同人”,而是将其作为游离于几个主要作家群落之外的创作个体进行评价。韩护这样评价梅娘:
以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基点。它既异于个人主义的文学,更异于社会主义的文学。然而它并不舍弃个人的自由的要求,也不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以热情与哀怜的情绪作为文学的骨骼,多方面的捕捉人生的动静。它的至高无上的目的,仍是在发挥文学的技能,以求人类自由权柄之恢复[10]。
这里韩护将文丛派承袭的“东北作家群”文学创作观念概括为“社会主义文学”,将古丁为代表的艺文志派同人的文学创作概括为“个人主义文学”,认为“梅娘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文学之在满洲文学存在的地位”。韩护在《〈第二代〉论》中比较了山丁与梅娘的不同创作风格,认为山丁秉持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念贯穿其作品始终,从题材的选择到艺术的表现都贯彻着“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文学追求。梅娘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的美学风格呈现为“自然的”和“浪漫的”,从选题上看,梅娘关注的是“没有阶级的阶级的人们”的苦难生活。韩护又将梅娘与萧红比较,认为萧红是“满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的先锋,其文学对象偏向于人生的争斗方面的,其文学手法是写实主义的”,梅娘的作品同样偏向表现人生,但“夹杂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成分”,这就是韩护“自由主义”文学的内涵。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到,韩护敏锐地发现梅娘前期作品中哀怜与热情交织的矛盾情感表达,同时也肯定这种文学观中“为人生”“为人类”的诉求。同时,他也发现了萧红、山丁的创作与梅娘创作不同的特点。阶级的文学观念使得山丁、萧红将目光投向底层无产阶级民众,通过再现的文学表现手法暴露伪满民众在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迫之下的黑暗生活。梅娘则以特有的女性意识观照社会人生,抛开阶级的标签,将笔触集中在女性与儿童群体,揭示出这两类殖民地弱势人群的精神苦难与生存苦难。
应该说韩护对梅娘伪满时期文学创作的评价是较为准确的,吴瑛也援引韩护观点,认为梅娘“给予了自由主义在‘满洲’文学上以存在的地位”[11]。尽管“自由主义文学”的说法值得商榷,但韩护和吴瑛是将梅娘的创作放在伪满汉语文学中去看,这起码说明当时的文学者已经意识到梅娘与山丁等文丛派其他作家在总体文学价值立场和取向上的差别。
三、殖民语境下东北新文学发展的一种可能
如何评价梅娘不同于文丛派的独特文学姿态?如果把这种区别放在殖民地背景下,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梅娘的创作至少能够表明新文学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殖民语境下本土知识分子的处境艰难而尴尬,他们既要在当局残暴苛刻的文化专制下求生,又无法违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身份认同。张泉先生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指出,与苏青、张爱玲的创作相比,“梅娘的作品与中国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更为密切”[12]。的确,对梅娘、山丁、古丁等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之下进入文坛的作家而言,在殖民语境下坚守自身的文学立场成为他们共同的努力方向。
抛开对新文学具体发展道路、走向的看法的区别,梅娘与文丛派、艺文志派在当时的整个伪满文坛上,属于同一个阵营——新文学阵营,与这个阵营并存的是主打言情、消闲的通俗文学、遵从日伪殖民文化统治的附庸文学、日籍作家以中日两种语言的文学创作等。这几类文学中,通俗文学因读者群和发行平台占有量较大,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要阻力。因此,这时期的所有新文学者所迫切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新文学如何冲破阻碍,从出版平台和读者群两个方面扩大新文学的影响。
面对这一局面,许多作家都发出过冲破“笼罩文坛的粉饰堆砌”的呼声。在当时的东北沦陷区文坛上,将文学与大众联系起来,强调为大众创作、以文学教养民众是许多文学社团标榜的口号,这其中有文选派的“文学是教养群众的利器”,有艺文志派的“以文学缩短万民的距离”。这种追求的背后,是知识分子作家的一种尝试——他们试图在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中寻求一个契合点。不同作家从不同角度强调文学与读者的联系,因此对“大众”的理解成为考察不同作家及作家群落文学观念的关键词之一。
先看文丛派。文丛派的文学渊源可追溯到罗烽、白朗等东北作家群,并且与北满早期左翼文学运动相联系,因此文丛派受左翼文学观念影响较大。在“文艺丛刊”四种作品集中附有《文艺丛刊发刊之辞》:
有人说:我们的文坛是贫弱的,但却有着繁荣的气运。有人说:我们的出版界是幼稚的,但却有着淳朴的蠕动。有人说:我们这块荒地,没有作家;但却有着一群活泼的生命。
“新的永久是替代旧的”,我们的愿心也是这样。从熟的果实里寻求新的种子,植新的种子,重于采已成的果实。
爱好文艺的朋友们,希望您:
提供您的作品,充实它的质量。
不吝您的意见助它的成长。
我们在丛刊之前,谨这样忠实的期待着[13]。
发刊词中文丛派呈现出的是希望繁荣、推动“满洲”文坛的姿态,并且面向“爱好文艺的朋友们”。吴郎将文丛派文艺主张中对文学与大众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做出阐释:“我们该不应当忽略了那熟长的果实,不但不应当忽略,而且更要在大众中间展开下去,以坚决的建立起,这种力量的基础”[4]。文丛派作家重视通过文学探讨民众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在创作中强调文学认识社会的功能,试图通过文学,让大众读者认清社会,进而实现宣传、启蒙的社会目标。
萧红在《生死场》中对沦陷后的东北地区底层民众精神世界有过这样的描写:
宣传“王道”的旗子来了!带着尘烟和骚闹来的。
宽宏的夹道树;汽车嚣着了!
田间无际限的浅苗湛着青色。但这不再是静穆的村庄,人们已经失去了心的平衡。
……
对着前面的洼地,对着山羊,王婆追踪过去痛苦的日子。她想把那些日子捉回,因为今日的日子还不如昨日。
……
“爱国军”从三家子经过,张着黄色旗,旗上有红字“爱国军”。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14]!
这些遭受殖民压迫程度最为严重的底层民众尽管能够感受到“今日的日子还不如昨日”,但他们对于被殖民境遇的认知仅仅限于坐在车上的日本兵所散发的花花绿绿的“王道”传单,以及从未见过的异国旗子。这些民众无法理解侵略、殖民,也不知如何反抗与爱国。底层大众荒芜的精神世界、面对殖民统治不知觉悟、不知抵抗的状态往往令本土知识分子作家痛心疾首。这个庞大的群体既可能成为反抗异族侵略的强大力量,也可能陷入殖民者炮制的“王道乐土”等殖民谎言中不知自救。文丛派知识分子作家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大力主张“教养群众”,以此实现自己抵抗殖民、重建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
再看艺文志派。1938年《明明》第三卷第一期发表了《城岛文库刊行辞》:
我们的出版界,虽贫绌而浪费,从来无人留意文化之所求为何物,亦不理解万民之所需在何处,只是使万民敬远了“文化”,只是使文化隔绝了万民。
然而万民断非文化的绝缘体,文化倘离绝万民则自行枯萎,本社为缩短文化与万民间之距离,乃刊行《明明》,问世后即蒙国内的识者推许,始有今日的微果。此次更推广此意,刊行城岛文库。本社资本固有限度,但感愿竭其所能,举凡文学、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尽量包容,作历史的计划。唯借此创行之始,拟现行注重于最易接近万民的文学,选辑国内作家的创作及国外名家的巨著的译文。源源而进。
此种计划,倘只偏重出版者一人则无所依凭,是必须仰赖海内爱真理好实学之士的援助的。
在刊行本文库之始,略陈数言,愿宏达有以教我[15]。
《刊行辞》中指出文化是“万民之所需”,主张以发行单行本来“缩短文化与万民间之距离”,正与古丁所倡导的多创作、多出版文学作品的“写印主义”思想契合。“万民之所需”“缩短文化与万民间之距离”体现出古丁对文学与读者关系的思考。在思考如何建设东北文坛的问题时,古丁一直没有忽视文学受众的问题。在《论文坛的性格》中,他对新文学读者的构成有过基本判断,认为当前的读者主要是新士大夫,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从当时东北沦陷区民众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看,文学的受众仍以青年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为主。古丁由此得出结论:“大众非读众”,据此他批判了文丛派文学观中“文学为大众”核心观点的模糊性。古丁指出:
他们在使用着的“大众”这语汇,已经化成暧昧已极的语汇。根据这种解释,他们对于作品胡乱地妄断。他们或以“大众”为“穷人”,或以“大众”为“自己似的人”,他们只是以这暧昧已极的“大众”这语汇,在无可如何的时候,拉了出来。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你不是为了大众的”,——在他们的口中说出来,并没曾超越了“你没写穷人”“你是我们永远看不起的作家”以上的意义[16]。
由于“大众非读众”,读众只是大众的一部分,因而古丁指出,针对读者群,新文学应该有两个面向:第一是针对作为新文学读者的新士大夫阶层,新文学作者“应当向这一点做求心作用”[16]40。这是说,新士大夫阶层本身已经是新文学的读者,对这样的读者来说,新文学应该追求的是“变革”读者的灵魂,即通过观念的传递达到影响读者价值取向和判断的目的。第二,针对通俗文学的读者,新文学应该打破题材的狭窄,利用这类读者熟识的通俗文学形式,承载新文学的思想内容。
总之,古丁认为在处理新文学与读者关系的问题上,应该本着以文学启迪心灵、引导价值观的目的,并通过吸收、转承传统文学、民间文学艺术形式的做法,向尚未成为新文学受众的通俗文学读者传递新文学精神,使其向新文学阵营靠近。这就是满足“万民之所需”“缩短文化与万民间之距离”的意旨。
梅娘也对大众有自己的解释:
政治与文化的本身,自然就免不了有生发与扬弃,在它生发与扬弃的过程中我们要抓住它,认识它的真价值,那就只有看一看它的存在有没有恒久性,所说的恒久性就是说它是不是能恒久的属于大众。……在文化人属于为政者时,与属于大众时,对于那助长与抑制,期间所产生的效果是有着绝大的不同的[7]4。
梅娘把文学和大众的关系与作家的文学选择并置理解,当作家选择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么此时的文学便打上政治的烙印,只有当作家选择文学为大众,这种文学才有恒久性。因此抛开政治元素,坚持文学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这是梅娘的文学立场。由此可知,梅娘理解的大众,与左翼文学理解的“普罗大众”“无产阶级”有一定的区别,与艺文志派理解的知识分子和市民群体也有所不同。联系梅娘创作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梅娘所言的大众,更多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如妇女和儿童,这是梅娘关注的对象。
殖民地的特殊性、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使得伪满洲国文学呈现出丰富而独特的文学景观,不同作家的文学选择和创作立场各不相同。梅娘、文丛派的山丁和艺文志派的古丁等人不同的文学选择根源在于他们面对异族殖民统治采取的应对策略不同,展现出的文学姿态各异。
新中国成立后梅娘在一次采访中发出“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的感叹:
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侵犯了我们的民族,这是由不得我们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占领的时间要过多久,我们只知道做事不能违背民族良心[17]。
一方面,如梅娘所言,作为同样承袭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些作家和作家群落不同的文学选择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表达同一种文学诉求——在异族殖民统治、文化同化政策下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血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虽殊途却同归;另一方面,梅娘的存在,代表着殖民语境下东北新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这也是沦陷时期新文学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证明。
[1]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229.
[2]蒋蕾.精神抵抗——以《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207.
[3]吴郎.关于“文艺丛刊”[N].大同报,1939-12-05(6).
[4]吴郎.关于“文艺丛刊”[N].大同报,1939-12-07(6).
[5]吴瑛.两极[M].长春:益智书店,1941:扉页.
[6]佚名.文化动向[N].大同报,1939-10-3(6).
[7]山丁.从《小姐集》到《第二代》[M]//梅娘.第二代.长春:文丛刊行会,1940:1-4.
[8]山丁.《去故集》的作者[M]//陈因.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280.
[9]刘纳.社团、势力及其它——从一个角度介入五四文学史[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15-26.
[10]韩护.《第二代》论[M]//陈因.满洲作家论集.大连:实业印书馆,1943:307-314.
[11]吴瑛.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J].青年文化,1944(5):26.
[12]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202.
[13]山丁.山风[M].长春:益智书店,1940:扉页.
[14]萧红.萧红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75-105.
[15]城岛舟礼.城岛文库刊行辞[J].明明,1938(1):2.
[16]李春燕.古丁作品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88.
[17]邢小群.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M]//陈晓帆.又见梅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2.
Another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of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 In the Colonial Context——A Case Study of Mei Niang’s Two Literary Identity Labels in Manchukuo
Wang 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266109)
Mei Niang’s literary creation has begun in Manchukuo.At that time,Mei Niang has two identity labels in the literature,which are Company of Wen Cong Literature Society and Representative of Liberalism Literature in Manchukuo.From 1936 to 1940,Mei Niang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uthors of Datong Newspaper Supplement,so she has become a company of Wen Cong Literature Society,which is an important literary commu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anchukuo.But through the careful research of Mei Niang’s works in this period,it finds that Mei Niang’s literature concept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Wen Cong Literature Society,which has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Left-Wing literature.Han Hu has called this different literary value orientation as Liberalism Literature.The existence of Mei Niang represents another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of new literature under the colonial background,and also the proof of diversity and variety of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occupied period.
New Northeast Literature;Manchukuo;Mei Niang;Company
I206.6
A
1674-5450(2016)05-0008-07
2016-06-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1046);青岛农业大学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614Y11);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项目(1116703)
王越,女,黑龙江青冈人,青岛农业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殖民地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詹丽责任校对:杨抱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