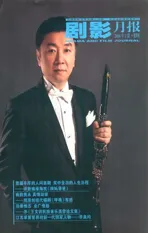试论昆曲的文化空间及物质遗存
2016-11-21王美诗
■王美诗
试论昆曲的文化空间及物质遗存
■王美诗
摘要:明清时期,昆曲成为园林里士人们寄托性情、展现才华的重要生活方式。文人们宴饮交流、诗情雅兴往往都和昆曲家班演剧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江南私家园林不仅见证了昆曲的兴盛和发展,还见证了昆曲从“剧曲”繁荣向“清曲”繁荣转型的历程。旧时大户人家的私宅园林更留给我们丰富精致的昆曲题材物质文化遗存。由于江南地区民间传统手工技艺和士人们对昆曲的热爱紧密结合,一大批巧夺天工的昆曲文物应运而生。江南私家园林作为昆曲兴盛的“文化空间”,见证了昆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的辉煌。
关键词:文化空间昆曲戏曲文物园林
明清时期的江南,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自明中叶以来,江南缙绅阶层多兴造园林以自适,由是各式各样的私家园林成为江南建筑中独特的风景线。缙绅们兴造园林与豢养昆曲家班,作为一种风雅之事,一开始即同时共存。退隐缙绅、文人雅士纷纷在园林宅第中蓄养家班,于宴饮会客之时声歌消遣。一时间,“置买田园”、“私蓄优人”1、“广亭榭”、“饰歌舞”2形成风气,昆曲成为园林里士人寄托性情、展现才华的重要生活方式。在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中,私家园林见证了昆曲的产生、发展和式微的历程,承载了丰富的昆曲文化遗存,明清私家园林堪称昆曲兴盛的“文化空间”。3
一、园林孕育了昆曲
文人雅集时欣赏表演的传统由来已久。西周时“鹿鸣”之宴欣赏“小雅”4,汉魏时建安七子竹林雅集弄琴5,《韩熙载夜宴图》中表现的南唐重臣举办家宴的情形,出土青瓷堆塑罐中诸多人物奏乐场景,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即雅集与表演结合的贵族审美传统随着文士阶层的日益壮大而越来越普遍。明清时期,随着私家园林的兴建,一大批地域性的富裕知识分子将这里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这个场所成为常汇聚骚人墨客、清客曲家的“文化沙龙”。昆曲以其优雅唯美的音乐特征,和曲牌填词的诗意特征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使得昆曲在它产生之初就和这种优质人文环境相得益彰,在艺术与人文环境的共鸣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昆曲的前身“昆山腔”的产生即与元末明初江南著名私家园林“玉山草堂”有着一定关系。“玉山草堂”位于江苏昆山绰墩山一带,是文人顾阿瑛耗费巨资兴建的私家园林。顾阿瑛和昆山腔的“创始人”顾坚、杨维桢、倪元镇等人经常在这里举行聚会,调音弄弦之间,对顾坚“发南曲之奥”应该有极大的帮助。这直接推动了流行于当地的民间小曲蜕变成流行一时的“昆山腔”。6
私家园林的人文环境还为昆曲的第一部剧本《浣纱记》和之后的《桃花扇》的诞生起到辅助作用。《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生在当地名门望族,壮年之时“营华屋”、造“楼船”、筑“庭”院,汇聚“四方奇节之彦”。7骚人墨客伴梁辰鱼“度曲”为乐,共赏他的“转喉发音”与“声出金石”的唱功。他除了学习魏良辅的音乐成就,“得魏良辅之传”,还和许多善音律的人一起钻研,从而第一个把“水磨调”运用到《浣纱记》的曲词创作中。在他与屠隆的交往中,屠隆也以上客礼之,命优人演其新剧,助推了《浣纱记》的传播。和梁辰鱼一样,昆剧作家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曾居住在江苏泰兴李清枣园里,修改剧本草稿。8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听说孔尚任住在李清枣园,便专程来到这里与孔尚任相聚,畅谈他所亲身经历的侯方域、李香君故事,《桃花扇》中的内容也因冒辟疆的到来得到完善。这样一个文人相聚的雅致场所,对剧作家们创作剧本、修改剧本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私家园林不仅为昆曲的产生提供了优质人文环境,还是昆曲从剧本走向舞台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昆曲从案头走向场上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职业戏班的商业演出,主要集中在庙台、专业戏场里;二是家班的自娱性演出,主要集中在私家园林里的厅堂等较为私密性的表演场所里。苏州拙政园“卅六鸳鸯馆”、上海豫园的“乐寿堂”和“玉华堂”、江苏如皋冒辟疆故居“水绘园”、南京夫子庙“瞻园”等等都有昆曲搬演的历史。其他诸如《栖霞阁野乘》记载的扬州张氏“容园”、《甫里志稿》记载的苏州甪直许自昌“梅花墅”、《三冈续识略》记载的苏州徐乾学“遂园”、《巾箱说》记载的金陵“曹寅府”等,演出昆曲的事例数不胜数。离开了私家园林这个重要艺术场所,很难想象,在职业戏班表演之外更多的昆曲文人剧本,是怎样被搬演到舞台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女乐家班兴盛起来,成为文人剧本走向舞台的实践者,昆曲和文人之间的天然关系,在园林中的戏场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园林滋养了昆曲发展
自昆曲产生以来,明清私家园林就一直作为昆曲表演、传播、革新的场所而存在,昆曲发展的每一步都在这个空间里得到了历史的见证。
1.明清私家园林见证了昆曲的流布传播
明清时期,昆曲在私家园林里的传播存在着这样一条轨迹:首先从以昆山、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人园林”里发端,再北进和南下。北进流布到常州、南京、扬州、泰州、北京等地由富商和在朝官员兴建的园林之中,如长洲申时行家班于申府中演《鲛绡记》、《宸垣识略》记载的清初吏部侍郎孙承泽于北京修建的“孙公园”(光绪年间为安徽会馆)、《燕都丛考》记载的安徽昆曲名家方成圆于北京修建的“方盛园”、《宸垣识略》记载的清初刑部尚书“龚鼎孳别业”、《孔尚任评传》提到的清宗室“岳端府第”,都是这类私家园林。昆曲南下流布到浙江杭嘉等地的私家园林里,如包涵所在杭州的私宅园中宴请金陵名妓马湘兰并演剧,上海豫园主人潘允端在家中观演昆曲。这条私家园林里的传播路径显示出昆曲在兴盛时期传播的广度遍及明清时期南北主要发达城市,传播的深度上达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阶层。康熙年间,北京园林里昆曲的兴盛到达巅峰,“索得姑苏钱,便买姑苏女,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9这些文字生动描绘了当时北京富有人家购买姑苏女乐、学唱昆曲的盛况。江淮流域的盐商为了拉拢当地官僚士大夫阶层,投其所好地选择昆曲作为交际方式。此外,由于政府对商人在家里征歌选伎几乎没有限制,他们蓄养的昆曲家班通常比文人家班的规模更大、装备更奢靡。清初号称“南季北亢”的泰兴盐商季振宜,最是铺张。季沧苇本是官员,回乡后开始经营盐业,很快成为南方巨富。他家的“女乐”就有三部,皆是服饰华丽的韶颜女子。10
2.明清私家园林见证了昆曲“雅俗共赏”的历程
昆曲在明清私家园林里充分汲取着文人给予的养分,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典雅精致、清丽梦幻的风格,发展到明末清初,这种风格更强烈地表现在园林里的舞台表演上。阮大铖家里的昆剧表演就是舞台典雅、精致风格的代表。《陶庵梦忆》记载,他的家班表演“与他班孟浪不同”、“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阮大铖的戏剧文风辞情华赡、文采飞扬,是竭力追步汤显祖典雅一派的代表,他的家班演出在他的亲自调教下,自有一段清雅气度。再如客居金陵的徽商吴琨,他要求家班表演尽可能要一字不漏地遵循汤显祖的剧本。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记载“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同社吴越石,家有歌儿,令演是记,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缥缈之余,以凄怆于声调之外,一字无遗,无微不及。”11他对汤显祖《牡丹亭》典雅风格的推崇可见一斑。而班主的审美要求通过家班表演反馈到舞台上,对舞台风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昆曲在园林里雅化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停止深入民间的脚步。生活在园林里的一部分士大夫,并没有排斥或贬低在村镇的庙台广场或城市的茶楼、戏馆一直存在着的与普通民众趣味更接近的通俗“昆曲”(或称“草昆”)。以沈璟为代表的戏剧理论家,还提出了具有市民立场的戏剧理论。12他在“属玉堂”中提出的“本色”、“合律依腔”的戏剧理论,创作的《义侠记》、《博笑记》等剧作,都体现出通俗化、市民化的气息。从沈璟的私宅园林“属玉堂”里产生的戏剧思想,带动了“吴江派”、“苏州派”等昆曲剧作家创作具有市民审美趣味的剧本。鼎盛时期的昆曲,“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深宅大院、粉墙黛瓦之外,有着另一片天地。
三、园林见证了昆曲转型
晚清时期,昆曲剧曲式微,而昆曲清唱却相比之前更为繁盛,昆曲存在形态开始逐渐转型,而这一改变,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清廷对私家园林主豢养戏班的禁令。
昆曲剧曲演出在清代中期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其历史原因,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是它在“花雅之争”中受到蓬勃发展的地方戏曲带来的冲击。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冲击了昆曲的大众受众群,而昆曲剧曲作为典型的文人戏,它衰落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丧失了以私家园林主及其关联的文人群体——精英受众群。这是昆曲剧曲走向式微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种情形在清雍正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清王朝采取的禁养家班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昆曲戏班的生存状态。雍正二年(1749),皇帝下达了清廷第一个限制官员蓄养家班的诏令:“其有先曾畜养,闻此谕旨,不敢留存,即行驱逐者,免其具奏。既奉旨之后,督抚不细心访察,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及提镇家中尚有私自畜养者,或因事发觉,或被揭参,定将本省督抚照徇隐不报之例从重议处。”13雍正认为官员蓄养家班是一件浪费钱财、耽误公务、易滋生事端的事情,所以决定禁止此行为。在此之后,清廷接二连三地又下达了多道相关诏令处罚违纪官员、禁止蓄养家班。14
受此影响,府邸园林之昆曲戏剧演出大都只能在富商私宅中进行,与鼎盛之时相比大有减少的趋势。不少昆班表演渐渐转移到戏院茶馆中与地方戏竞争,在“花雅之争”中再次受到冲击。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各种外来思潮的不断涌现,社会又开始发生剧烈的变革,昆曲擅长的才子佳人戏与话剧等各种时代剧相比更缺少时代气息,其诗意、婉约、靡丽、舒缓的风格也不适应时代的审美趣味。昆曲戏剧演出因为丧失了生存的土壤而日渐式微。
但昆曲在这种形势下并没有死亡,而一直以来和“剧曲”相对的“清曲”活动,却在这种环境下别样发展起来。清唱昆曲不需要养家班,不存在违反朝廷禁令的情形。所以在传统喜庆宴饮活动中,以前是表演剧曲的场合,渐渐被清唱昆曲所替代,即产生了“唱堂会”的说法。晚清时期,堂名班遍布江南城乡,为数之多超过戏班。15而唱堂会的装置用品也随着富裕士绅家庭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奢华。为了填补富裕士绅家庭不养家班也能赏昆曲的市场需要,产生了一批装置豪华并以此谋生的堂名世家。
四、园林的昆曲文化遗存
昆曲与其说是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喜爱,毋宁说它的精致雅丽更加符合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创作和欣赏昆曲成为了士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江南富庶的生活中,巧夺天工的民间传统工艺和昆曲融合,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昆曲题材文物。
1.戏场建筑
江南文脉昌盛、经济繁荣,观众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赏戏场所的特殊。明代计成在其园林建筑著述《治园》中就曾说:“造园必先造花厅,花厅兼作观剧听曲之用”。自昆曲与私宅庭园在明代一同兴盛之时起,两者就形影不离,苏州私宅庭园中主要为欣赏昆曲的戏场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是“有园必有戏场建筑”。
私宅庭园中的昆曲演出氛围,既不同于戏院演出,也不同于酬神演出,体现了文人特殊的审美情趣。这种情趣只有借助园林这样的环境,才能达到曲境与园境的互通。正如曲论家王骥德的相关描述:“曲之亨:华堂、青楼、名园、水亭、雪阁、画舫、花下、柳清宵、皎月、娇喉、佳拍、美人歌、妾童唱、名优、妓旦、伶人解文名士集、座有丽人、佳公子、知音客、鉴赏家、诗人赋赠篇、座客能闺人绣幕中听、玉危、美酝、佳茗、好香、明烛、珠箔帐、绣履点笙、主妇不惜缠头、厮仆勤给事、精刻本、新翻艳词出。”16此情此境,既是园境,又是曲境,是昆曲与园林的“珠联璧合”。在园中演出“气无烟火”的昆曲,恰似文人对赏心乐事的长吟永叹。
园林中常见的是戏台大体分二种:露台式和厅堂式。
露台式戏场是比较常见的戏场形式,同时也是早期戏场平地做场的一种延续。如拙政园远香堂前后的小型广场,坐在堂内观剧正好可以将对面的山水及雪香云蔚亭作为舞台背景;留园林泉耆硕之馆后的小型广场,正好可以将冠云峰及烷云沼作为背景。在演出的时候,往往会在露台上铺一面红氍毹,演出就在其上。此时的演出空间范围就由这氍毹来界定。观赏者也可以四面环视。明万历顾曲斋刻本《古杂剧》中收录有《梧桐雨》露台式戏场插图,形象地记录了当年庭园中戏场的形式以及演乐场景。
露台演出讲究时节,在春意盎然和秋高气爽之时,露台式戏场便为诸多演出场所之首选。沈德符《网师园图记》谓园主宋宗元:“每当风日晴美,侍鱼轩,扶鸿杖,周行曲径,以相愉悦。时或招良朋,设旨酒,以觞以咏。”17道出文人雅兴往往有赖自然成全。园中山水相映,花木繁阴,四时皆有美景,但总体而言,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最能发人游兴,也最能保证园中演剧的外在条件。听曲的地点在不同时节效果亦不同。秋高气爽时,主人选择在露天赏曲,此时往往露台式戏场便能派上大用。文震亨曾言松石间最宜于琴音,松石间度曲听曲亦臻于妙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不同的风物不停地更换着戏场的背景。园境与曲境在此达到了最完美的交融状态。
厅堂式演出是园林演戏的另一种情形。廖奔在《中国古代剧场史》中解释“堂会戏”时认为,“堂会演出最常见的场所还是在厅堂内:大厅中间摆上地毯作为演出场地,周围设桌席供宾主坐赏,另有地方供女眷观看,而用帘子隔开”。18庭院式戏场在补园中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据张岫云的《补园旧事》所言:“大厅前有天井,张履谦特意在中间部分加棚盖,并设有栏杆、地板,可兼作演出昆曲的舞台用。大厅两边楼上隔墙有可拆木板,演出时是最好的包厢……大厅两边有一对小方厅,都是昆曲习曲的好场所……家人、亲友经常在此踏戏(排练)或彩串。”19
明清园亭池馆似乎专为选伎征歌而设。清代华岳画作《度曲小桃园》描绘士大夫度曲便是如此场面:半山坡上,草堂一椽,松石相映,景致萧疏,七八个人物中大致包含了主人、清客和乐工,列坐两侧,奏乐度曲。此中情境极富文人意趣。“一片红毺铺地,此乃顾曲之所。草堂插图里乌巾岸,好指点银筝红板。”20由此,舞榭歌台成了园林中必不可少的场所。在这理想与现实结合的园林建筑中,还遗存了大量以昆曲故事、典故为题材的建筑构件,如砖雕、木雕等,它们作为建筑的装饰,记录了那时文人们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昆曲的一片痴迷。
2.戏曲纸质文献
有了靡丽巧思的戏台,自然要配上美轮美奂的表演。在园林建成之后,园主甚至会亲自去各地挑选演员,或“自掐檀痕教小伶”,或延聘曲师教习,征歌度曲。《红楼梦》中就曾写道,大观园造好之后,贾蔷便到苏州采买十二个擅唱昆曲的女孩来组建家班。家班由主人、教习、伶人三部分组成,主人们(文人)对于自家家班的演出务求雅致,教习们则负责将主人们的审美落实在实际演出之中。家班常在园林中举办堂会与坐唱,其中,既有班社成员参加也有清客们参与。戏曲文献——昆曲摺子最初产生的情形应和他们密切相关。
在昆曲诞生之后很长的时期,家班以及职业戏班总体上都是按照文人剧本打谱和演唱,但在不断演唱的过程中,出于场上演出效果等方面的考虑,伶人的演出本常常会与文人原本有不少差异。这些演出本便于藏纳,便于伶人们“忘词”时随时翻看,于是做成了小巧精致的手抄摺子的样式。同时,随着文人之间的应酬雅集,清客串曲活动的发展,谱有工尺谱的手抄摺子形式也渐渐在清客间流行,成为他们日常雅兴的辅助品。很多摺子都是清客、曲家亲自书写,字迹文雅,装帧精巧。
清代末期,专门的昆曲工尺曲谱集诞生,大量的手抄摺子往往抄自某曲家校订后的曲谱,而这些曲家往往都和园林主人有着极深的联系。以《粟庐曲谱》为例,该曲谱是俞宗海之子俞振飞对俞派家传昆曲的代表剧目进行编订整理所成的昆曲工尺谱,在昆曲界被奉为昆曲唱腔的正宗。而俞粟廬就在光緒中期被聘到蘇州儒商張履謙的补园内任西席,教授昆曲四十余年。张履谦与其孙张紫东均酷嗜昆曲和书画,常与吴门画派诸公交往,并与俞粟庐切磋曲艺,多次在卅六鸳鸯馆内举办昆曲清唱会。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手抄摺子,有很多都出自该曲谱。
除了大量的戏曲褶子,文人们创作的手抄剧本、收藏的音律学典籍、戏曲木刻刊本、戏曲戏画及书法评点等都是珍贵的戏曲纸质文献。中国昆曲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图书馆都藏有不少此类戏曲文献,尚待系统整理研究。
3.昆曲题材工艺精品
在富庶的江南之地,缙绅们已不满足仅仅享受昆曲的声色,他们还通过江南地区巧夺天工的传统手工艺,将昆曲题材匠心别具地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家用摆件、把玩品,让昆曲全方位地美化他们的生活,达到登峰造极的艺术享受。
水声隐隐,月华浮动,士人清客们要以昆曲行令。这种类似于“行酒令”的游戏涉及一种独特的戏曲道具,即“昆曲暗戏”。昆曲暗戏在中国昆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都有收藏,不同的套系中涉及的昆曲折子不同,道具的多少亦有很大的差别。但统观之,皆由苏州玉工制作,材质有白玉、墨玉、翡翠、青金石、水晶、玛瑙、红珊瑚等珍贵之物,细致精微,令人叫绝。传统苏州玉工和扬州玉工不同在于扬州玉工多为山子大件作品,苏州玉工多为巧雕小型把玩件。因此,苏州玉工是最适合制作“昆曲暗戏”的,而发源自苏州的昆曲和苏州玉工两相结合产生的“暗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戏曲文物代表作。南京博物院所藏全套“昆曲暗戏”,共十三匣,117件,涉及34个昆曲折子戏,每件约大拇指大小,巧夺天工,是目前已知全国各地收藏中最多的一套“昆曲暗戏”。明汤显祖《牡丹亭》的《游园》一折中,南宋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时年十六,平素身居闺阁,偶与婢女春香游览花园,目睹春景,感动情思。暗戏中小巧的松耳面盆、刨花刷、玛瑙镜子、梳子与金星石盘即是此折戏中使用的道具。戏迷如见到此五件道具,即应猜出是《游园》一折。21从此套暗戏的珍贵用料以及精致考究用工上看,它昂贵的资费绝对不是平常百姓所能负担的,应为富裕的士绅在园林中宴饮观戏、清客串曲之时所用。通过凭赏精巧制作的昆曲道具,他们互猜戏曲名牌,玩耍方式或为猜中者诉剧情,猜错者罚唱一曲。
在家居摆设上,园林主人们也于细微处留心。那些以戏曲故事为题材的屏风、雕刻戏曲故事的漆器、象牙摆件,甚至是闺房用品,处处都记载着宅第主人的雅趣。
江南地区丝质工艺发达,丝质工艺中不少都有以戏曲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盛行于明清时期的缂丝工艺,以其艰难耗时的制作工艺,在当时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之盛名。而消费缂丝的人群多以有文化品位的富裕知识分子为主。他们日常生活中有缂丝制作的扇套,在家居摆设中更是相当奢靡地使用缂丝制作戏曲故事作品。南京博物院藏清代戏曲人物故事“天宝遗事”缂丝四条屏,就是十分罕见的昂贵的家居摆设。
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和五彩瓷都十分盛行,产生了一大批人物故事瓷器。有瓷罐、瓷瓶、花盆、插屏等家具用品,也有水盂、笔筒等文房用品。从传世的瓷器来看,戏曲故事题材中,以《西厢记》等生旦戏和祝寿题材戏的瓷器作品所占比例最高,刀马戏和《西游记》等题材比例较小。充分体现了富裕阶层消费倾向对于戏曲瓷器的引导性。南京博物院所藏清康熙景德镇民窑五彩《西厢记》双面插屏,为宅园中大空间中使用的木质隔断装饰插件,充分说明了《西厢记》在江南大户人家中的影响,也是昆曲家班演出中重生旦戏的一个佐证。
苏作红木制作技艺发达,产生的戏曲人物故事木雕十分丰富,自不必多讲。而中国昆曲博物馆所藏的“宝和堂”昆曲堂名灯担,正是昆曲清唱繁盛的实物例证。昆曲在江南地区不仅剧曲繁荣,清唱昆曲更为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富裕士绅家庭清曲观众的深厚土壤滋养了剧曲的发展。“宝和堂”堂名灯担制作于清晚期,采用紫檀木、黄杨木雕镂而成,可拆卸,四周嵌玉石栏杆、缀琉璃灯,采用扬州漆器髤饰技艺装饰细部面板,可通电亮灯,演出时灯彩辉煌、华丽缤纷。旧时苏州大户人家若有婚庆做寿等喜事,时常邀请堂名班子到家中唱堂会。清末已是昆曲剧曲衰微之时,而清唱堂名的世家仍然投入巨资制作堂名专用移动舞台,可见清唱昆曲仍然有十分深厚的观众基础,且存在大量能够消费的人群。这是晚清昆曲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美园、美曲、美物,共同铸就了戏曲的园林、园林的戏曲。在江南私家园林这样一个汉族文人创造的美妙绝伦的文化空间里,流淌着昆曲的时代交响曲,这首交响曲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更是有形和无形共同谱成的,点点滴滴无不显示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士大夫对昆曲的热爱。他们对昆曲一掷千金的奢靡,对昆曲显示出的高雅的艺术修养形成了昆曲和园林共生的“文化空间”,铸就了汉族审美的集体记忆。在这样的空间里,昆曲愈加高雅化,这一方面使它脱离了世俗,成为隔世之音,甚至在清末日渐式微;另一方面却极好地保存了明清的士族文化,使得士族文人们的“清雅”在案头、在书斋、在檀板箫笛声中温文流淌,绵延不息。
注释:
1康熙十八年(1679),御史罗人琮于《敬陈末议疏》中云:“今之督抚司道等官,盖造房屋,置买田园,私蓄优人……”见: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329.
2屠隆.《鸿苞》[M].卷二十一“醉梦”:“余见士大夫居乡,豪腴侈心不已……广亭榭,置器玩,多僮奴,饰歌舞。”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八九》[C].山东:齐鲁书社.1995.352.
3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
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鹿鸣为小雅始。”[M].湖南:岳麓书社.1988.419.
51961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中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中,稽康等人抚琴啸歌。
6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21.
7《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M],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6册[C].第512页。
8徐振贵.《孔尚任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1~74.
9王政尧.《满清入关与清前期戏曲文化》[J].《清史研究》,1994.2.
10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67.
11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引自王廷信《昆曲与民俗文化》[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86.
12顾聆森.《沈璟与昆曲吴江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80~109.
13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中的《雍正上谕内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1.
14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中的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330.
16沈宠绥.《度曲须知》[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9.
17沈德符.《归愚文钞余集》[M],转引自裁庆任.《网师园》[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
18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63.
19张岫云.《补园旧事》[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l,67~75.
20(清)孔尚任.《桃花扇》[M].见:《中国古代四大名剧》[C].南京:江苏古籍社.1998.448.
21徐建清,于成龙.《凭石说戏,以玉乐友——罕见的玉玩精品<昆曲暗戏>》[J].东南文化,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