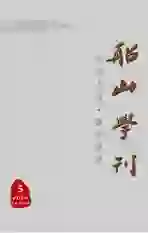王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人性论意义
2016-11-17田丰
田丰
摘要:
船山将同由诚而不息的健顺之德分化出的德、理分殊为不同层面,前者为体为能,后者为用为实,并将德虚化为形式性概念,或曰待充实体认的虚灵良能,以此方式,做出了“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的天人之辨,既保证了伦理政治的基础,又无寻求现成不变先天本体之虞。
关键词:四德;性日生日成;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天人之辨
前言
王船山对道之本体的理解与我们所熟知的宋明理学基本架构大相径庭,无论是朱子的由事事物物上求定理到有朝一日豁然贯通全体大用无不明,还是阳明孜孜以求言必称之的复其心之本体,都从逻辑上预设了一个人对道之本体的终极把握或同一。而在船山看来,这种预设来自人为地对虚妄本体的设定,终必导致人僭越于天。不过,因为朱子的道路是下学上达之渐进,是以流弊尚不显著,阳明之法门却会开顿悟狂禅,所以船山批驳不遗余力。① 那么船山是如何既保证儒家由天而来的价值基础不会动摇,同时又不会让人妄与天同,僭越于天的呢?在船山看来,儒家区别于异端之处在于其对天命的回应是贯穿其一生始终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直窥某种本体的一蹴而就。如果不是将“生”理解为日夜不息的生成,而是一瞬间的获得,那么就“性”而言便会理解为初生之顷,就境界而言便会认为,当有朝一日达到“上达”境界之时,之前的下学工夫便都成为佛家所说的“敲门砖”,成为外在于目的的工具手段。换言之,如果将体理解为物中固定现成不易之本质,用只是由此发出的外在性功能,那么不管如何强调体用一源或即体即用,都不能由用而反生其体,用也最终必将与体分裂,物成为无性之死物,工夫成为上墙抽梯的工具性存在,人的在世生存都塌陷为通向终极之境的渡桥。即便这种终极之境声称它自身是不离日用伦常的先天未化,鉴于前此的一切工夫历程都将被忘却遗弃或仅是作为去除后天遮蔽的消极剥落,那么最终也不过只剩下一个仅仅生存于当下的无历史无世界的虚灵之浮明。所以船山以为,“豁然贯通”或“上达”的终极之境是不可期的,所谓不可期并不只是意识到生而有涯或自身禀赋分限不足,而是说,它们只能被作为一个路标式的指引形式存在,而决不能被立为一个终极境界。所谓圣人之纯也只不过是如同天之不已,如同乾道积众阳而劲健不息。正是在此诉求下,船山提出了其著名的“性日生日成”之说,然而此论会带来一些内在困难。
如果就宋明道学的传统性论来说的话,尽管人初生之顷被赋予了气质之性,但其本初的天地之性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人的身体每日新陈代谢,但只能说是气日生日成,绝不能说理日生日成。正是这个不变的天理落在人身上所成的先天之性保证了人向善的可能性基础。船山的“性日生日成”之说,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先天根基作为保证,则容易泛滥无归而成支离之学,而一旦接受一个初生之顷一成而不变之性,那么就可能带来上文所述的一系列问题。
进一步说,“性日生日成”之说最根本的困难在于,如果说“气质中之性”就大始而言有共同根源造成其“性相近”的话,那么犬牛之性同人一样皆来自天命大始,何以犬牛之性与人之性不可言相近,而只能说人性善,犬牛之性不善呢?船山对此质疑当回答说:“人有其气,斯有其性;犬牛既有其气,亦有其性。人之凝气也善,故其成性也善;犬牛之凝气也不善,故其成性也不善”②。但针对这个回答,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质疑,既然人之气异于犬牛之气而彼此相近,那么人之气中必然有某种共同之处使得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人都称之为人,这个共同的东西如果理解为某种先天不变本体,则又将回到传统理学的窠臼中去,如果否认其不变性,那么它究竟为何,又是何以能够成为规定人性共同之处的呢?
对于这些困难前人研究基本未有触及,除了陈来先生在其著作中对船山“气质中之性”概念提出质疑,但并没有深入考察此困难在船山这里是如何解决的。本文试图从船山“四德”天人之辨的角度考察上述困难是否可能在船山思想框架内获得解决。首先我们先对船山的人性论做一些必要的考察。
一、人性论
船山认为性的生成不是一次成型而无可损益的过程。
夫天命者,岂旦初生之顷命之哉?但初生之顷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一日,俾牢持终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劳劳于给与;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无可损益矣。……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侀,揣之曰:“无善无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呜呼!岂不妄与!③
万物的生成都是来自天命,这是任何道学家都不会否认的,但之前的学者在理解“天命之谓性”的时候都将天命理解为初生之际的一次性事件,其直接逻辑后果就是将性相应地理解为在初生之际从天获得的原始存在状态。对这种存在状态不同层次或角度的理解带来了不同的性论基础。而在船山看来,所有这些性论的共同点在于将性理解为一种静止的现成之体。在他列举的这些性论中并没有包括性善论,这是因为他也部分地赞同性善论(却并非在道学的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详于后)。然而,整个宋明道学传统的性善论,就对性理解的现成性而言,与此处船山批评的对象并无二致,在道家与佛家亦然。甚至可以说,自魏晋以至宋明,儒释道各家学派对性的理解几乎都是初生之顷不易之侀。所谓“侀”,本通“形”字,《字彙·人部》:“侀,即形字”,但与“形”字相比更加着重在已成而不可更改之意上,《广韵·青韵》:“侀,成也”,是以《礼记·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孔颖达注曰:“上刑是刑罚之刑,下侀是侀体之侀。训此刑罚之刑以为侀,体之侀言刑罚之刑加人侀体。又云‘侀者成也,言侀体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后,若以刀锯凿之,断者不可续,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变,故君子尽心以听刑焉,则上悉其聪明,致其忠爱是也”。由此可见,“侀”字既有物体形体之义,又有已成不变之义,按照《礼记》的描述,还有一个引申的意义,即是对人体的肉刑造成的后果:残破而不可再生之体,这便是为何船山特意使用这个字来表述一种对“性”的一成不变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之前的各家学派皆可谓“生之谓性”,而非“生生之谓性”。船山“性日生日成”之论,是欲破除此千余年性论传统,可谓绝大见识之所在。endprint
告子乃“生之谓性”学说之源头,孟子批评说这样就无以区分人之性与犬牛之性。上文所论船山以不息的生成来反对初生之际一成不变之侀,是在纵向的生成性意义上批判的。接下来我们从船山对告子的批评入手,来理解船山所理解的生生之德就其自身而言与告子生之谓性的差别,以切入船山所理解人性的根本规定性。
朱子谓告子只是认气为性,其实告子但知气之用,未知气之体,并不曾识得气也。告子说“勿求于气”,使其能识气之体,则岂可云“勿求”哉!若以告子所认为性之气乃气质之气,则荀悦、王充“三品”之言是已。告子且以凡生皆同,犹凡白皆白者为性,中间并不分一人、禽等级,而又何有于气质之差也!④
朱子在其自身的框架里,以理为性,故认为告子把气当作用而不知性。在船山的框架里,气才是性之为性的基础,所以他不能同意朱子尊性贬气的说法,而声称告子其实并不知气之体,而但知气之用。而荀悦、王充的性三品之论相较之下显然是试图以分析差异性的方式来理解性,这里所谓将性认作气质之气的思路在第三节分析过,指的是,将性仅仅理解为个体初生之际的现实实存状态,那么性的三品区分是就气凝结为质之后的所有属性特征来做出的。船山认为,并不是气质之气的一切属性都可以称之为性,其中还包括情、才,只有气质中之生理才能称得上性。性三品说的问题在于将情、才皆含混进来而论性,看起来是有差异有区分的讨论,其实因为在根基上就已经将诸多问题含混一起未加区分,那么在此含混基础上的任何区分都只能是表面随意而不具有思辨严格性。而告子的问题则在于仅仅以气之用为性,这里的气之用指的是“生”,而且是无差别无区分的“凡生皆同”,无分于人之生与禽之生。更进一步地说,告子对“生”的理解也是停留在最表层的气之运动攻取而已,此即船山所谓的情、才,所以告子实际上是就情、才而论性:
天不能无生,生则必因于变合,变合而不善者或成。其在人也,性不能无动,动则必效于情才,情才而无必善之势矣。在天为阴阳者,在人为仁义,皆二气之实也。在天之气以变合生,在人之气于情才用,皆二气之动也。(此“动”字不对 “静”字言。动、静皆动也。)繇动之静,亦动也。
告子既全不知性,亦不知气之实体,而但据气之动者以为性。动之有同异者,则情是已;动之于攻取者,则才是已。若夫无有同异、未尝攻取之时,而有气之体焉,有气之理焉,即性。则告子未尝知也。
故曰“性犹杞柳也”,则但言才而已。又曰“性犹湍水也”,则但言情而已。又曰“生之谓性”,知觉者同异之情、运动者攻取之才而已矣。又曰“食色性也”,甘食悦色亦情而已矣。其曰“仁,内也”,则固以爱之情为内也;爱者七情之一,与喜怒哀乐而同发者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可以为善,则可以为不善矣,“犹湍水”者此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为不善非才之罪,则为善非才之功矣,“犹杞柳”者此也。杞柳之为杯棬,人为之,非才之功。即以为不善之器,亦人为之,非才之罪。⑤
气之生理必须通过变合才能实现,变合中便会有一隅之偏颇不善,在人而言亦然,性之生理必须通过情才方能发用,情才同样不能保证必善。在天之阴阳对应于在人之仁义,这是天德与人性的对应,变合则对应于情才。在天阴阳作为气之实为静,变合作为气之动为动;在人仁义作为性为静,情才为气之动。不过船山自注说动静是相对而言的,其实没有静,因为阴阳、仁义都不是静态规范属性,说静亦动也,第一层意思指的是它们具有生成能动性,第二层意思指的是它们自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只是相较变合而言未若其动之昭著而已。而告子以气之动者为性,显然指的是变合之动,这种动是仅仅就一种实然的现成性变化而言的,就其不同方面又可以分殊为情才:“动之有同异者,则情是已;动之于攻取者,则才是已。”
情在船山常见的意义有两个,一是情实之义,一是七情之义,而这里船山通过“同异”将两个意义关联了起来。动则必然有情实之差异,既然有了情实之差异,则人的知觉七情也会相应地生出好同恶异甘食悦色的不同情绪:“知觉者同异之情”。情因为出于对气在一隅偏至的同异判断,而不必然来自对全体大用的理解,是以不必然为善,仅只是可以为善。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诚明篇》中又说:“质生气,则同异攻取各从其类。故耳目鼻口之气与声色臭味相取,亦自然而不可拂违,此有形而始然,非太和絪緼之气、健顺之常所固有也”⑥。这是认为质与气因同异而有攻取,就太和絪缊之气本身而言是没有同异攻取之分的,只有在一隅成形成质,方能谈得上质气或质质间的攻取关系。由此而言,才与情并非截然无关,“运动者攻取之才”说的是气凝于质后产生对于同异之气的某种倾向性禀赋,这种禀赋可以推动质与气的攻取运动。
总而言之,船山认为情、才的本质是质对于气的同异攻取作用,此作用源自气凝为质之后,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太和絪缊之气的健顺之能,无法完全像太虚之气一样生生不息又虚灵无滞。告子仅看到了质的这种作用能力及其所生成的攻取运动,并以此理解性,却没有看到性并不是气质之气的攻取运动或推动此运动的禀赋,即气之动,而是气之静——所谓静是相对气之实然性攻取运动而言,其实性是能主持调剂气之生理。气凝为质之后并非完全丧失了健顺之德,根据其保留健顺之德的程度之多少可以分别出草木、禽兽与人的差别,人从天禀受的“性”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健顺之德的整全性,此整全的健顺之德使得质不会沦为死物,能够运化天地清明之气,从而变化自身气质。现在我们便可以了然船山何以认为告子只知气之用,不知气之体。盖就天而言,气之体即为周流六虚而无方所的宇宙全体,气之德为劲健不息虚灵无滞之知能或者更具体的展开即为元亨利贞四德,气之用乃是其在局部的运化变合聚散显现;就人而言,气之体即为人的理气身心整体,气之性是仁义礼智,气之用是人与外界事物的往来行为。人的行为可能为善,亦可能为不善,告子以此为性,故认为性如湍水,流动无分东西,他没有看到,人的整全之体不仅仅有此运动能力,更有从天德秉承元亨利贞所成的仁义礼智之性。所以说“夫告子之不知性也,则亦不知气而已矣。”⑦endprint
二、德、性、理之辩
在朱子理学的结构中,宇宙之体为太极,太极为静态天理,落在人这里即为性。船山则将体与理分殊开,整全个体对应宇宙全体,性对应的不是太极,而是天德。这种体用关系与理气关系扭转的意义需要结合下面材料继续分析。
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理善则气无不善;气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类。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气之善;天之道惟其气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气也,唯其善,是以可仪也。所以乾之六阳,坤之六阴,皆备元、亨、利、贞之四德。和气为元,通气为亨,化气为利,成气为贞,在天之气无不善。天以二气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温气为仁,肃气为义,昌气为礼,晶气为智,人之气亦无不善矣。
理只是以象二仪之妙,气方是二仪之实。健者,气之健也;顺者,气之顺也。天人之蕴,一气而已。从乎气之善而谓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⑧
阴阳之气为道体之全,理(严格说来当是德)不再是内在于气的静态本体,而是标识指示气之妙。船山并没有说“理是二仪之妙”,而用了“象”字,依笔者拙见,这是为了刻意将“理”字虚化,消解掉其本体意义,而突出其象征指示的形式意义,这种形式意义后文详论,此处仅先以譬喻作形象说明:理作为气之文理,譬若树之年轮叶脉,人可以通过它直观地理解气是如何年复一年运行生成于树之中,却不能说年轮叶脉即是树之生机本身,而人愈是多地与树木打交道,栽培灌溉并细心照料观察树木的生长,便愈是能精微地理解年轮叶脉中昭示出的树木的生长变化。年轮叶脉作为树之纹理提供的象征形式需要人在实践中不断去充实丰富对它的理解,才能在各种风霜雨雪的境遇中懂得当如何照料树木使其健康丰沛地成长,而非执定此理便可成为优秀园丁。在天而言,气之于理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优先性,理或曰天德必然是在气化运行中显现出的某种势态,所以“惟其气之善,是以理之善。”但就已成形质的个体而言,则理或曰性的主持分剂功能对于运行于其中的气起到主导作用。所以当船山说“气之不善,理之未善也。如牛犬类。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气之善”的时候,并不是在理学意义上认为有一个在先之性理决定着气的本质,只是在强调气质中之性反过来对气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在天为二气之良能,即和气、通气、化气、成气分别昭示的元亨利贞四德;在人为温气、肃气、昌气、晶气之仁义礼智四德。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船山性论最核心的部分,即如何理解人从天所禀之性,才能从人性中给出伦理政治的坚实根基,又不会陷入船山多次强调的回复不变本体思路的诸多流弊。
我们首先分辨德与理的差别,上文船山言理只是一个泛泛的与气相对的称呼,是为了突出归根结底理仍只是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船山虽然也在非严格意义上用理来称呼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但他更倾向于以德来称之,德相较于理更加突出的是一种大化之良能,理则更加偏于指向在分殊中包含有更多具体规定性的条理。所以船山常常论及天德,却罕有提及天理,并认为程子用理来言天是不恰当的:
太极最初一○,浑沦齐一,固不得名之为理。殆其继之者善,为二仪,为四象,为八卦,同异彰而条理现,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繇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是理唯可以言性,而不可加诸天也,审矣。⑨
只有在具体的同异条理中,理之名方起,有了个体才进而有性之名。浑沦之天固然无所谓理,即便是人性因其整全地承继天德,那么所谓的理其实即是仁义礼智之德:“若夫人之实有其理以调剂夫气而效其阴阳之正者,则固有仁义礼智之德存于中,而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所从出。此则气之实体,秉理以居,以流行于情而利导之于正者也。”⑩仁义之性与情才的差别在于其本源自阴阳健顺,不滞于形质,所以没有同异攻取:“夫在人之气,唯阴阳为仁义,而无同异无攻取,则以配义与道而塞乎两间”B11。船山以为这种仁义健顺之德在天而言不宜称其为理:
天为化之所自出,唯化现理,而抑必有所以为化者,非虚挟一理以居也。所以为化者,刚柔、健顺、中正、仁义,赅而存焉,静而未尝动焉。赅存,则万理统于一理,一理含夫万理,相统相含,而经纬错综之所以然者不显;静而未尝动,则性情功效未起,而必繇此、不可繇彼之当然者无迹。若是者,固不可以理名矣。无有不正,不于动而见正;为事物之所自立,而未著于当然;故可云“天者理之自出”,而不可云“天一理也”B12
所谓理是在化中显现出的气之条理,而刚柔、健顺、中正、仁义诸天德并非化,而乃所以为化者。如果非要用理这个传统道学概念的话,那么天德只能说是赅存万理的一理,而经纬错综的万理还没有在当然中显著出来,是以“固不可以理名矣”。所以为化者不是理,而是赅存万理的理一,所谓静而未尝动并不是说真的有那样一个时间中的起始状态,静与动,理一与分殊都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就其整全源始状态来说,经纬错综都未尝显现,所以不能称之为有理,这个理一其实不是一般意义的理,而是刚柔健顺中正仁义这样的一些形式概念,也即是德。《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里的道就是船山所说的德,船山以为阴阳刚柔仁义都是指气之德而言,具体变合运动中的万理方能称之为理:“仁义,一阴阳也。阴阳显是气,变合却亦是理”B13。一定要说阴阳仁义是理的话,也只是理一:“纯然一气,无有不善,则理亦一也”B14。既然无有不善,则不宜以善称之,“且不得谓之善,而但可谓之诚”B15。此即本章第一小节所论的在天之“无善无恶”,“大要此处著不得理字,亦说不得非理”B16。所以船山更倾向于用“诚”“几”这一对概念来名之:“所以周子下个“诚”“几”二字,甚为深切著明。气之诚,则是阴阳,则是仁义;气之几,则是变合,则是情才。情者阳之变,才者阴之合。若论气本然之体,则未有几时,固有诚也。”B17
“几”指的是气化变合,之后遂有善与不善分化,“有变合则有善,善者即理。有变合则有不善,不善者谓之非理。谓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则亦何莫非理哉!”B18我们看到,这里对“理”字的使用很大程度上祛除了传统道学中很强的伦理意义,而仅仅是就气化变合中呈现出的条理而论的,气无论如何变合,情才同异攻取,终归会有条理呈现,所以无往而非理也。对理的这种祛伦理倾向自然不代表船山是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恰恰相反,船山是出于为了让性不会成为僵化现成之物这样一个更深的考虑。在船山看来,情才攻取皆是出于理,乃是气之用层面,所以他不是如道学传统那样将性奠基于理,而是要将性奠基于气之体层面的德。“气本然之体”之诚对应于人即是“本然之性”(如前所论,同时也是“气质中之性”):endprint
唯本有此一实之体,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贞,故一推一拽,“动而愈出”者皆妙。实则未尝动时,理固在气之中,停凝浑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气,便是“万物资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故孟子言“水无有不下” ,水之下也,理也,而又岂非气也?理一气,气一理,人之性也。B19
此段数个“理”字,显然指的是“理一”,也即是“天德”,它既是推动气之动的妙用本原,气之良能,也是人之性。所以船山总结说:
告子专在俄顷变合上寻势之所趋,孟子在亘古亘今、充满有常上显其一德。如言“润下”,“润”一德,“下”又一德。此唯中庸郑注说得好:“木神仁,火神礼,金神义,水神信,土神知。”康成必有所授。火之炎上,水之润下,木之曲直,金之从革,土之稼穑,十德。不待变合而固然,气之诚然者也。天全以之生人,人全以之成性。故“水之就下”,亦人五性中十德之一也,其实则亦气之诚然者而已。B20
现在我们可以对船山德、性、理三者关系做一个小结:鉴于宋明道学传统对理字极其广泛的使用,船山对理字的运用也并未有做出严格界定,往往既可以指天道、理一、天德,也可以指性、情、才,所以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其所指。而在前文分析中明确的是,狭义的理就人而言并不能够直接对应于性,而应当对应于情、才。如果说广义的理包括了德、性,那么当船山以元亨利贞、健顺五常、仁义礼智来讨论人对于天的秉承关系之时,即便他也会使用理这个概念,究其所指是与传统理学的理之意义完全不同的。从上段材料可以看出,他认为,告子单单是以“势之所趋”理解性,在船山概念中,势与理是相关的,船山曰:“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理与气不相离,而势因理成,不但因气”B21,又曰:“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B22差别在于,势是更大范围内的对气更加具有能动性之理。所以告子所理解的性可以说是就情、才而言的理,是从气之用出发的;孟子则是就古今上下之常显现出的德来言性,是从气之体出发的。就气之体出发,则德乃是气内在之健顺良能,是所以然者,属静;就气之用出发,理是气运动显现出的条理,是实然者(亦有攻取之能动性),属动。当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时候,他指的是水内在之能,而非水流东西显现出的条理,所以此之谓德,而非理。此外,水之就下之性仅仅是其德之一,还有润之性;且水又只是五行之一,五行之德皆来自气的诚然大德。如果说具体的水之理,则因清浊大小不同而千差万别,只能因地制宜,在具体境遇中不断地充实深化对各种分殊之理的理解,决不可只因润下的空灵之德便可筑堤治水造福一方。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都要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为对形式性之德的充实与丰富。
三、四德天人之辩
理解了船山的德、性对应关系,与德、理之别,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在天之元亨利贞与在人之仁义礼智的关系。
在传统哲学中,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相对应几乎是个毫无异议的论题,只是在什么意义上相关联各家诠释皆有不同,不能将这种差别理解为一种前启蒙时代半迷信式的任意阐释,正如不能认为西方思想家们对希腊神话的解读是不严格的肆意发挥。其实,每个思想家都是从自身哲学体系的严格思考出发来做出其独特诠释路径的,须细微剖析方能理解其用心所在。
船山在不同地方将天之四德与人之四德做出不同的对应。因为谈到人之德的时候,传统的说法往往是五常仁义礼智信,所以在对应于天德时无法直接对应,就需要做出取舍。船山在《周易外传》中认为人之四德应当是仁义礼信,而非仁义礼智,其理由在于“智”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德,它在五行对应于水,必须依于四德才能发挥作用:
是故夫智,不丽夫仁则察而刻,不丽乎礼则慧而轻,不丽乎义则巧而术,不丽乎信则变而谲,俱无所丽,则浮荡而炫其孤明。幻忽行则君子荒唐,机巧行则细人捭阖。故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B23
这种对“智”的理解有些接近康德所说的知性,而非理性,它本身并不能给出自身的内在目的,也没有综合统一的能力,必须借助于四德的引领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德性。反过来说,四德也必须通过“智”才能够着实地发用:
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终非智则不知终,始非智则不知始。故曰“智譬则巧也”,巧者圣之终也。曰:“择不处仁,焉得智!”择者仁之始也。是智统四德而遍历其位,故曰“时成”。各因其时而藉以成,智亦尊矣。虽然,尊者非用,用者非尊,其位则寄于四德而非有专位也。B24
这样理解的“智”看似任何一种德都离不开,非常尊贵,而其实是一种贬低,以为它只是一种附属工具性的虚浮灵明,异端便是因为太过看重此浮明而有弊:
惟不知此,故老氏谓上善之若水,而释氏以瓶水青天之月为妙悟之宗。其下者则刑名之察,权谋之机,皆崇智以废德。B25
由此可知船山此立论乃是出于批评异端而发,恐偏于激扬文字之辞,而非平心静气之论,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理解的“智”极少有现代工具理性之意。故而此论颇为罕见,在其大部分著作中都还是将仁义礼智对应于元亨利贞,即便是在提出仁义礼信四德说的《周易外传》亦然。所以下文不特别讨论仁义礼信之说,而还是就传统的仁义礼智四德而论,我们先来看船山对“元”的论述。
船山在《周易外传·乾卦·三》中批评了前人对“元”的理解:
先儒之言“元”曰:“天下之物,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有得而后有失,非得而何以有失也?”
请为之释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则既推美于大始矣。抑据成败得失以征其后先,则是形名器数之说,非以言德矣。B26
这里所称先儒指的是伊川先生。此说法出自《程氏易传·大有卦》:“元之在乾为元始之义,为首岀庶物之义,它卦则不能有此义,为善为大而已。曰:元之为大可矣,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岂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兴而后有衰,衰固后于兴也。得而后有失,非得则何以有失也。”又《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朱文公易说·卷十五》中朱子将此二说合一曰:“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传》曰:‘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得而后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想来船山是从朱子所引程子之说而立论的,不过朱子此说倒也无异于程子原义。船山的批评所指在于两点,其一,以成败得失立论,会流于法家之说;其二,以善为始而非终。而且前者是基于后者的。船山认为以程子以成败得失立论是为了破释氏:“意者,立成败得失之衡,以破释氏之淫辞耶?则得之尔矣。……奖成与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效,使知败与失者,皆人情弱丧之积,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则双泯理事,捐弃伦物之邪说,不足以立。”B27然而,此论却非的论,“虽然,于以言资始之‘元,则未也。”因为“执成败、据得失以为本,法家‘名实之论也”B28,之所以“执此说者之始于义而终于利矣”B29,究其根本是因为对“元”的理解问题,“以成为始,以得为德,而生生之仁不著”B30。船山提出他对“元”的理解:endprint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就善而言,元固为之长矣。比败以观成,立失以知得,则事之先,而岂善之长乎!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元者,统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予之者,已臻于成与得矣,是人事之究竟,岂生生之大始乎!……夫一阴一阳之始,方继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来之际,止此生理为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赞其德曰“元”。成性以还,凝命在躬,元德绍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终无间,亦且日生于人之心。唯嗜欲薄而心牖开,则资始之元,亦日新而与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顷。B31
船山承认“元”作为开端资始的意义,“元”作为先于具体存在事物的资始者是整全之体的大德,所以可以说“物皆有本,事皆有始,所谓‘元也”B32,而且,“纯乾之为元,以太和清刚之气,动而不息,无大不届,无小不察,入乎地中,出乎地上,发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兴起有为而见乎德;则凡物之本、事之始,皆此以倡先而起用,故其大莫与伦也。”B33但他认为所谓“善之长”不能理解为实存事物的成与得。“形未成,化未著,神志先舒以启运,而健莫不胜,形化皆其所昭彻,统群有而无遗,故又曰‘大也。……温和之化,恻徘之几,清刚之体,万善之始也。以函育民物,而功亦莫伴其大矣。”。所以它也贯穿物之始终,是人事之究竟。在天为“元”,在人为“仁”,就一阴一阳之始,就天人授受之初,皆是此生生大德所为。而万物成得之后,人一生始终,此“元”“仁”之德又不断日生于人物之中。“天无心,不可谓之仁;人继天,不可谓之元;其实一也。”B34天无心,则其乾元之德自然而作用于人物;人有心,须得努力作为方能继善成性,所以终生持守方能让“仁”德在自己身上不断发挥其生生之用。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船山《春秋家说》中对“元年”之“元”的论述来理解。其曰:
凡数之立,以目言之则二继一;以序言之则二继初。目以相并而彼此别,序以相承而先后贯,其理别矣。故《易》言“初”言“二”以达于“上”,《春秋》书“元”书“二”以迄于终。乾始不可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一也。……夫乾之资始,坤之资生,仁也。唯仁以始,唯仁以终,故曰“乃统天”。统天者,统天之所有造,而六位时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贞”终,则始无“贞”而终无“元”。俯仰以观天地之化,曾是各有畛而不相贯乎?故夫人君以仁体元也,自践祚之初迄顾命之顷,无异致也。初年而元,将二年而不元矣,其将取法于亨乎?而体仁长人之德,岂一年而竟乎?志学之事,在谨于始;凝道之功,必慎于终。故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载,历终如始,而大始者不匮。故春夏生而亦有杀,秋冬杀而固有生。有序成,无特用也。仅然以始居仁而莫统其后,则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贞者倚于谅矣。B35
分析这段材料之前先要理解其论述所指,在于道学传统中以《程氏易传》与《朱子本义》为典型的对元亨利贞的理解。伊川将元亨利贞理解为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B36。贞者,万物之成。”B37这与上文船山批评的程子观点显然如出一辙。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偏于象数吉凶:“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 所以胡氏炳文曰:“元、亨、利、贞,诸家便作四德解,唯《本义》为占辞”B38。不过两先生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分歧,朱子对《象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注释说:“盖尝统而论之,‘元之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B39这也是就事物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可以说这种理解方向在两先生并无二致B40。这正是船山此段材料批评的观点。
船山在其《周易外传·序卦传》中曾对《序卦》做出批评,分别条理与序的差别在于,条理无先后次第,是太极全体自身显现所致,序则表现为逻辑或因果意义上的先后关系。六十二卦并无先后关系,且任何一卦中都有整全的太极有于其中,只因隐显不同而显现出条理差异。这里船山要讨论的是《春秋》之纪年,爻位所代表的事物发展过程,以及四德在具体事物上发用流行,这些不再是空灵的卦象形式,而都与时间以及实存事物相关,是以必然有其生灭始终之过程,也必然有先后承接关系。船山特别强调“序”之特点在于“先后贯”,他将序与目比较并认为诸如一二三四这样的数目只能叫做目,因为它们之间仅仅是并列性的差异,而没有先后一贯之道。而序则既有先后关系,又有一贯之道。“元”作为大始既是万物生成的源头,又始终与万物同在,所谓同在是既从内在构成万物生生不息之良能,又从外在以气化流行发育万物。显然,这依旧是船山全体大用之义在“元”与万物关系上面的体现,也即是说,如果将船山体用关系在此做一个类推的话,“元”乃是最原初整全意义之德,以“元”为首,不能只理解其原初之义,还应当体察其始终不断地包有并作用于万物的整全之义。所以,元亨利贞不能判然划分畛域,“春夏生而亦有杀,秋冬杀而固有生”,元为始为春,亨为长为夏,利为遂为秋,贞为成为冬这样一个四分法是不足取的。“有序成,无特用也”,说的即是原初与整全无偏至的双重意义。犹为重要的是落在人身上后,“谨始慎终”,“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这样终身不倦不止的志学道路。
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元”的贯通涵盖性,程朱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程子认为:“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B41朱子也说:“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B42不过,虽然就“元”包四德而言,程朱与船山表述相似,然而一方面,如果分言四德,则程朱显然还是偏于将其理解为事物的不同实然阶段;另一方面,程朱也没有像船山那样特别强调“元”在万物中不断的生成作用,而是如船山所批评的,更倾向于作开端式的理解。
船山对亨、利、贞的解读秉持着类似的精神:
“亨”,古与烹、享通。烹饪之事,气彻而成熟;荐享之礼,情达而交合;故以为“通”义焉。乾以纯阳至和至刚之德,彻群阴而欣合之,无往不遂,阴不能为之碍也。endprint
“利”者,功之遂、事之益也。乾纯用其舒气,遍万物而无所吝者,无所不宜,物皆于此取益焉。物莫不益于所自始,乾利之也。
“贞”,正也。天下唯不正则不能自守:正斯固矣,故又曰正而固也。纯阳之德,变化万有而无所偏私,因物以成物,因事以成事,无诡随,亦无屈挠,正而固矣。B43
这几段话论述明白,无需赘言,只请读者注意其诠释仍旧是紧紧扣住“通”“遍”“正”“固”这样的方向,且亨利贞都被诠释为纯乾之气展现出的不同良能,如亨为“至和至刚之德”,可以通万物而无滞,利为气对万物的舒益,贞为气之无私而变化万有。如前所论,此诸种良能并不能被划分到气之用的层面,因为气之用乃是实然的攻取运动,却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气之体,因为气之体当是太极整全大体。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讨论过,善标识的是由体生用的生生不息之德,唯有气之全体在绵延相续之“继”中不断生成万物端体,方能就此称其为善,因此善而成物,气凝为成形之质,则有性生焉。现在我们可以明了,气之体所以能生用,是因为气中有一种劲健不息的大能,能够推动气不断流行化生。此能纯然至善,所以可以称其为良能,或曰天德。只有气之全体才能充沛无间不息不滞,所以只有在全体来说此良能天德方是整全而纯粹的。气分化流行的时候会进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于是天德也会相应地分化为不同的四德,元亨利贞仁义礼智,究其根本,则仍是乾元劲健之德。所以船山区分了大德小德:
仁、义、礼、信,推行于万事万物,无不大亨而利正,然皆德之散见者,《中庸》所谓“小德”也。所以行此四德,仁无不体,礼无不合,义无不和,信无不固,则存乎自强不息之乾以扩私去利,研精致密,统于清刚太和之心理,《中庸》所谓“大德”也。四德尽万善,而所以行之者一也,乾也。B44
仁义礼智(信)之所以能够行,仍是因纯全之乾德。如前所论,此德亦可称之为“诚”,故船山又说:“盖诚者性之撰也,性者诚之所丽也。……性有仁义礼知,诚以行乎性之德。”B45此种诚、健之乾德是体生用的根本动力,也是人从天所继者,是为继善成性。性中并不具备万物具体之理,需要通过格物致知去发见;其所谓秉承天理,也不是如阳明所言自然无不知无不能;而是秉承诚健之德,或者,更具体些的话,是仁义礼智信之德。天德天理乃至元亨利贞固然可以说包有万理,在人之仁义礼智却不尽然,它们可以说是人性中的不变者,却又尚未获得具体规定性,只是一种形式性的规定与引领。我们可以从对下面材料的分析获得说明。
乃性为天之所命,而岂形色、嗜欲、得丧、穷通非天之所命乎?故天命大而性专。天但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但以元、亨、利、贞为之命。到人身上,则元、亨、利、贞所成之化迹,与元、亨、利、贞本然之撰自有不同。化迹者,天之事也。本然之撰以成乎仁义礼智之性者,人之事也。此性原于命,而命统性,不得域命于性中矣。
形色虽是天性,然以其成能于人,则性在焉,而仍属之天。属之天,则自然成能,而实亦天事。故孟子冠天于性上以别之。天以阴阳、五行为生人之撰,而以元、亨、利、贞为生人之资。元、亨、利、贞之理,人得之以为仁义礼智;元、亨、利、贞之用,则以使人口知味,目辨色,耳察声,鼻喻臭,四肢顺其所安,而后天之于人乃以成其元、亨、利、贞之德。非然,则不足以资始流形,保合而各正也。故曰:此天事也。B46
要理解这两段话,须得明了“撰”字之义。从船山其他材料来看B47,撰最主要的意思有两个:作用显现,具备固有。从这里与本然二字连用,又与化迹对言来看的话,撰字应当指的是具备固有B48。
此两段话的重点之义在于人之仁义礼智与天之元亨利贞不同,因为在天来说,元亨利贞会自然分殊在万物中成化迹,由此即可生成万理,所以天之元亨利贞可谓体用兼备且两者自然相成而不可分。元亨利贞落于人身上之后则其德用分化,其德(此处理指德)成为仁义礼智,其用则成为人感官的同异攻取,即前文所论情才。当情才为性德所贯通引领时,德发为用,用还成德。
换言之,天以阴阳五行之气作为人之形质来源,而此气运行中自然具备之德元亨利贞作为人之为人者。元亨利贞作为气化运行的基本形态,既有条理的一面,亦有流行的一面,前者偏静而能主持分剂,后者偏动而能生成感应。是以前者在人即为仁义礼智,后者在人而为感官欲望,两者在人身上相合而又成在人之元亨利贞。船山下文又说“天命不息而人性有恒”B49,也即是说,人性之仁义礼智为恒而不变者,然而这个不变不是离乎气之不变,而是气自身具备的运行形式。当我们说形式的时候不是指法则,恰恰相反,它并不是一种直接具备具体规定性的法则,而是只有在具体情境下才会显现出具体规定性的空灵形式。此形式与具体规定性之间并没有一种严格的知性逻辑关系,而是在情境中当下生成的决断。也即是说,它并非是绝对的定言命令形式,却也不是有详细规定的假言命令。不顾具体情境的言必信行必果者在儒家看来其实是硁硁然小人哉,儒家也不认同法家式的将一切可能条件与相应判断都严格规定好的行为指引大全,真正的中庸之道应当永远是在情境中权衡决断的无可无不可。而人在实践中对中道的追求又能够反过来丰富充实其性,也就是对仁义礼智的领会与适宜地运用,这才是真正的性之生成。
在道学传统看来,当天理落于人而成其为性之后,混杂入了许多属于气质层面的东西,所以其惯用的词是“蔽”,也就是“多”了些东西遮蔽在本然之性上,所以会说“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合在一起构成现实中的人性。而在船山的思路下,命大而性小,当天德成人性之后,并非“多”了些东西混杂进来,反倒是“少”了些东西。传统道学与船山都以为在天为纯,在人为杂,但他们对纯杂的理解大相径庭。道学传统理解的杂是相对于不变本体而言的杂多现象,故尔比纯要“多”;船山理解的杂则是气化流行在一隅显现的条理,所以比纯全大体要“少”。这样一来,他所谓的“本然之性”和“气质中之性”,就其相同点来说,皆持有健顺五常之德;但是,此人德与天德相比,尽管就诸种良能而言并不缺失匮乏,却仍旧不如天德自然而包有万理,而只能在一隅之攻取变合中发用。也即是“仁义只是性上事,却未曾到元亨利贞、品物流行中拣出人禽异处。君子守先待后,为天地古今立人极,须随在体认,乃可以配天而治物”B50。所以人要做的是让“本然之性”能够在人不断发用生成,不忘不执,方能继承乾坤知能,让此性日生日成,致广大而尽精微。圣人所能不再是发见其先天本体,而是就其所处之境遇让仁义礼智与具体条理恰到好处地相合,由此又可创制发明,从而丰富仁义礼智的内涵。仁义既然不是现成本体,人就只能在实践中体认之,所以“孔子作《春秋》,何曾有仁义作影本!只权衡来便是仁义。”B51endprint
由本文所论,已基本解决“性日生日成”说的两难问题:船山将同由诚而不息的健顺之德分化出的德、理分殊为不同层面,前者为体为能,后者为用为实,并将德虚化为形式性概念,或曰待充实体认的虚灵良能,以此方式,既保证了伦理政治的基础,又无寻求现成不变先天本体之虞。
【 注 释 】
①可参看《周易内传·渐卦》:“世之为学者不知此义(渐),灭裂躐等,而鄙盈科之进为不足学。自异端有直指人心见性之说,而陆子静、王伯安附之,陷而必穷,动之不善,宜矣……渐者,学、诲之善术也。世岂有一言之悟而足为圣之徒、俄顷之化而令物皆善哉!异端之顿教所以惑世而诬民也。”(《船山全书》第1—427页)。
②④⑤⑦⑧⑨⑩B11
B12B13B14B15B16B17B18B19B20B21B22B45B46B49B50B5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卷,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56、1054、1055、1057、1054、1112、1055、1056、1112、1057、1057、1057、1057、1057、1057、1057、1058、992、994、543、1139、1139、1029、1029页。
③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卷 ,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99页。
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卷 ,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12页。
B23B24
B25B26B27B28B29B30B31B32B33B34B43B4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卷 ,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824、824、824、826、826、826、826、826、825、50、50、51、43、59页。
B3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卷 ,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9页。
B36 遂字的解读可参看朱子对于遂与成的差别说明:“利”者生物之遂,“贞”者生物之成。遂与成,如何分别?《论语》遂事不谏,注云,遂谓事虽未成,而势不能已也,则知遂是方向成之势,而贞则成矣。故曰“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清,李光地撰,李一忻点校:《周易折中》,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B37 程颢、程颐:《二程集·易传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5页。
B38B39B41B42李光地撰,李一忻点校:《周易折中》,九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0、495、495、495页。
B40 朱子相关论述尚有许多,不便一一列举,此处仅再举其代表作《周易本义》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和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B47 系辞下传第六章:“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本义》以撰为事。《周易内传》注释说:“阳卦体刚,阴卦体柔,体立而用因以著也。“撰”,其所作也。凡物理之不齐、人事之至颐,皆天地健顾之德所变通而生。”《外传》“天地之德合。合以成撰,撰备而体不缺,德乃流行焉”“有体乃有撰。阳亦六也,阴亦六也。阴阳各六,而见于撰者半,居为德者半。合德、撰而阴阳之数十二,故《易》有十二;而位定于六者,撰可见,德不可见也。”“乾坤必有而知数位之十二皆备,居者德而见者撰也。……阴阳各六以为体,十二相通以合德,而可见者六以为撰。”从这些来看,撰的意思应当是显现,显露,发用。此外,在《四书大全说》中撰的一些典型用法如下:《中庸》:“尽人之能,成己成物。而固与性合撰,功必与效而不爽”,作,“乃君子推而小之,以至于一物之细、一事之微,论其所自来与其所自成,莫非一阴一阳、和剂均平之构撰”,作,“仁、义之有撰,礼之有体,则就君子之所修者而言也”,显现,“只此不思不勉,是夫妇与圣人合撰处,岂非天哉?”,具备,“如“动容周旋中礼”四事,皆推本其性之撰,而原其所以得自然咸宜者,性之德也,而非以性为自然之词也。 ”,具备,“盖诚者性之撰也,性者诚之所丽也。”,具备,“天地之所以为道者,直无形迹。故君子之道:托体高明,便不悖于天之撰;流行不息,便不悖于天之序;立体博厚,便不悖于地之撰;安土各正,便不悖于地之理。然而天地之所见于人者,又止屈伸往来、阴阳动静之化,则已非天地之本体。”,此处撰字与理序对言,当是指外在的发用显现,如同上面十二时位的地方与内在隐德对言。“彼但欲绝圣弃知,空诸所有,故将有生以后,德撰体用,都说是闲粉黛。”此处又是与内在之德对言,“智礼,文也;仁义,质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质者迹微而撰著:则固并行而无衰王之差矣”这里和作用义近似。
B48 鉴于船山在选择一些独特的字表达其用意之时,通常是双取其两个相反相成之义。元亨利贞既然是诚健之德,则其具必然同时蕴含有发用之能,是以当同时体会船山此意。
(编校:章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