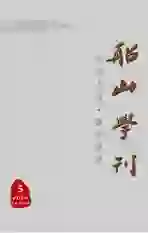论庄子的自由与逍遥
2016-11-17梅珍生
梅珍生
摘要:
在中国道家思想中,自由意味着个体将生命当作无功利的游戏,“游”就是生命的本质。尽管每个个体的自主性会对他者产生制约,但个体之间是“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的。道家“自由”的“原点”就是要合于“天钧”与“道”。有己、私智、语言等是自由与逍遥的限制因素。道家要求个体超越于“心知之灵”;依从各自的条件,“各如其分”,各“凝其神”;超越一切功利的关系,“以无用用无用”,最终与道相合,休乎天钧。
关键词:王夫之;庄子解;道家;自由;逍遥
“自由”的价值在现代西方所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的公民应当被允许去选择他们的价值和良善生活的观念而不受外来干涉。这样理解的自由表达了人类的一种基本渴望,当代自由主义的巨擘以赛亚·伯林把这种渴望描述为:“个人希望成为他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决定是依赖我自己的,而不是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行为的工具。我希望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我希望被理性,被我自己的有意识的目的而不是被外因所驱动。我希望……作出决定,而不是被决定,自我导向而不是按外在的自然而行动。”①自由这种价值不仅仅为现代西方所独有,在中国道家思想中,自由的价值更有超越于西方个体权利的视野,对于人类的自由精神有着更深刻的表达。本文拟聚焦王夫之《庄子解》的智慧洞观,勾勒王夫之所照应的庄子自由思想的光芒,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自由与逍遥何以可能?
自由就是“休于天钧”。即使按照自由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觉醒这种现代思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庄子自由思想中一样包含着这种价值觉醒的自觉,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自得”。“自得”之“得”是“得”什么?既不是自得于“物”,也不是自得于“事”,更不是自得于“实”,而是自得于“天钧”,并且这种自得,甚至不是分享“天钧”所赐,而仅仅是与“天钧”合一,所谓“休于天钧”就是使自我的价值成为“天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小小的部分,甚至是体现“天钧”的工具。
“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②
自由其实就是个体行动的无目的性,将生存当作无功利的游戏,“游”就是生命的本质。这种“游”它排斥世俗的“立”,无论是“立己”、“立功”,还是“立名”,都不是“游”所追求的,“立”就是将自己的价值,交付给世俗标准,行则依乎世俗标准而行,图则依乎世俗价值而求,“立”是个体在世俗生活中张扬自己的世俗“所得”,而“游”对于价值、对于事功,都不把世俗的标准作为首要或唯一的标准,“游”具有“无定性”,不受世俗的羁绊,“无所息”就是无所“依附”。虽然也最终要“休于天钧”,但它不是依附“天钧”,而是“天钧”的呈现,“天钧”也是生命的“本质”。所以,“游”即“天钧”,“游”即生命的本质。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庄子最高的“游”,是不屑于世俗权利的伸张的,而是真正返还到生命的非功利的意愿,他将这种“游”扩展到“寓形于两间”这个生命的场所,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国,而是“天地”两间,一个赤裸裸的人该何以自处,何以心安的问题。
有条件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有条件的自由中,外在的支撑因素不足以肩负起主体自身愿望时,追求自由就会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造成不对称,所凭借者能否支撑所希翼者,正是自由可能遇到的障碍。
水浅而舟大,则不足以游,大为小所碍也。风积厚而鹏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也。两言‘而后乃今,见其必有待也。负青天而莫之夭阏,可谓逍遥矣;而苟非九万里之上,厚风以负之,则亦杯之胶于坳堂也,抑且何恃以逍遥耶?③
“大之所待大”正是对“自由”条件的期许,有待的“条件”必须是与主体的愿望相一致,才可能“莫之夭阏”,“逍遥”才不可阻挡。
只要逍遥是有条件的,那就不是真的“自由”。各种条件即是“逍遥”的边界,“有涯”的客观限制,让“大知大年”这些令人羡慕的生存状态,也变得像“小知小年”一样不能达到真的“逍遥”之境。王夫之顺着庄子的思路指出:
蜩与鷽鸠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适莽苍者,计尽于三月;称长久者,寿止于彭祖;则所谓大知大年亦有涯矣。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许九万里之飞、五百岁八千岁之春秋为无涯之远大。然则‘三飨而返,腹犹果然,亦未尝不可笑‘三月聚粮之徒劳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适于逍遥者也。④
“有待”的生存就是一种局限,即使是“九万里之飞、五百岁八千岁之春秋”,又何足道哉。
在个体与他者或者“物”的关系中,每个个体的自主性会对他者产生制约,这种来自他者的制约与宰制是摆在每个追求自主性的个体的面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宰制?在追求自由与逍遥中能否突破这种宰制?或者是否存在这种个体自主性之外的真宰?在王夫之看来:
一人之身而有异知,耳目不相喻,内外不相应矣。既非散寄,则必依其一以为主,而私有所悦。将特指此官骸窍藏,何者为主,而何者为臣妾?于是而疑之曰,官骸窍藏之外,有真君焉。而虚而无倚者,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君且不得,而况其真?历历求之,了无可据。⑤
其实,没有什么主宰,只有个体的自主性,而且这种自主性正是“道”的自然展开:
“然则莫知其萌者,果非有萌也。天之化气,鼓之、激之,以使有知而有言,岂人之所得自主乎?天自定也,化自行也,气自动也,知与不知无益损焉;而于其中求是非之所司,则愚甚矣!⑥
在道的自然展开中,我们如果一定要探究何者为主宰,“求是非之所司”,正是不相信个体自主性的能力,个体的自主性与他者关联所构成的宰制与制约,又何尝不是个体之“天自定也,化自行也,气自动也”的表现呢?在个体与他者的交互作用中,个体的自主性固然会受到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会感觉到被外物所宰制。但是,个体之间又是“虚而无倚者,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的,自主性的让度与自主性的扩张,正是基于自我选择的结果。endprint
自由超越于“心知之灵”。真正的自由,它可以超越于心知之灵,是要突破“心知之灵”的局限的,所以,它所达到的高度与远度,不是一般的“心灵自由”所能概括的。“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皆吻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⑦但是,道家的“自由”又是有“原点”的,这个“原点”就是“大宗”、就是“天钧”,就是“道”,就是对于主体“得失”的消解,“以忘生死”即是真正的“自由”,而普通人不自觉于“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⑧如果没有肉体的羁绊,如果没有“心知之灵”的束缚,则天地“两间”之大,“无不可游也”,这才是无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游”。生命不以保存生命为目标,或者生命本身没有目标,“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⑨
二、自由与逍遥的限制因素
通常人们谈论自由的时候,认为没有外在强制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强制也可以是内在的。“如果个人受到难以抗拒的冲动、嗜好和非理性的偏见或者无法控制的和迷失方向的激情的支配,而且如果他们作出的真正的选择充满了无知、愚蠢、操纵和宣传,那么他们之缺乏自由就如同他们屈从于外在的强制是一样。”⑩
有己的意识是自由与逍遥的首要限制因素。在王夫之所阐释的庄子视野里,自由与知识存在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超越“心灵之知”,不为个体的一得之见所限,是自由与逍遥的起点。所以,一旦我们把“辨”作为知识的工具的时候,就会加入我们的私意,就是“有己”,这个“自我”无论是大我,还是小我,所带来的纷争,恰与逍遥相距甚远。当我们在“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自由的,就是“有待”于外在的功、名、利、禄,导致“辨复生辨”的无穷追问当中,自由就在追问当中丧失殆尽:
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则有所择,有所择则有所取,有所舍。取舍之情,随知以立辨,辨复生辨,其去逍遥也甚矣。有辨则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辨而立,名于所辨而成;六气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鹏与斥鴳相笑而不知为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已矣。B11
“鹏与斥鴳相笑”是一种分辨,“神人之所笑”同样是一种分辨,我们唯有取消一切“辨其所辨”,才可能真正达到“逍遥”之境。所以,与现代自由相比,道家的自由不是要伸张自我的权利,厘清自我的权利,恰恰的要求取消“有己”的主体意识,与道合一,而不是跳出“道”的构成之外。
个体彰显自我的价值,在世俗的认识中,将自我与“他者”或者“物”进行划界,心存物与我的分辨,有“己”则“物”都处在“己”的附属或依附的地位,由此导致用自我狭隘的视野来看待“物”的价值。所以,王夫之遵从庄子的思路,反复措意于消解自我,消解凸显自我价值的“功”与“名”。王夫之认为,“己不立则物无不可用,功不居则道无不可安,名不显则实故无所丧。”B12因为“有己”的意识必然导致“居功”,贪天功为己有,以为所谓的“道法自然”只是个体努力的结果;“有己”的意识,也容易在意自我的声誉与名望,一旦世俗的虚名与个体存在的实际状况发生偏差时,个体往往就会患得患失,甚至难以平复心中的怨气。所以,“功”与“名”这些外在的价值支撑着个体“有己”的意识,从而使自己陷于世俗的虚荣与俗念中难以超越。而真的自由与逍遥,绝不是将“有己”的意识插入宇宙大化之流,相反,它要求的是依从“物”自身的价值:
天高地下,高者不忧其亢,下者不忧其汙,含弘万有而不相悖害,皆可游也……寒而游于寒,暑而游于暑,大火大浸,无不可御而游焉;汙隆治乱之无穷,与之为无穷;则大亦一无穷,小亦一无穷;乡国可游也,内外荣辱可游也,泠然之风可游也,疾雷迅飚、烈日冻雨可游也。B13
没有物我的分辨,没有大小的局限,没有内外荣辱的判断,心中了无挂碍,才有个体精神与肉体的逍遥与自由。
私智是自由与逍遥必须跨越的鸿沟。“知其所知”看起来是“知”对于人的认识起着正向支持的作用,但是,也恰恰这“一己之得”会成为人的自由与逍遥的羁绊与障碍,人们常常会因为自我的经验而陷于一种“有知的无知”的困局当中,个体的知识导致人们“以己用物”,这往往是把“物之用”局限于自我的知识视域,而不是物性的对于世界的敞开中,这就是洞穴偶像对于自由与逍遥的制约。王夫之指出:“唯知其所知,是以不知。知以己用物,而不以物用物,至于无用而必穷,穷斯困矣。一知之所知,则物各还物,无用其所无用,奚困苦哉?”B14从物性出发,摒弃自我的私智,即使是“无用其所无用”,那么,“物”与“我”才能够在平等交互中,成就各自的价值。事实上,世俗往往从物的大小本身来判别物的特性和价值。但是,对于每种物自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抑斄牛能为大,狸狌能为小,斄牛愈矣,而究亦未能免于机网,则用亦有所困。”B15所以,私智的扩张恰恰是对物与我关系的扭曲,在我与世界之间横亘着个体私智的鸿沟。或者个体欲将私智作用于外物,或者私智受制于外物,我与物的关系相互胶着,自然界中,“物各还物”的轻灵因着私智而不经意间变得无比沉重,人所追求的自由与逍遥,由此注定要落空。
语言是束缚自由与逍遥的藩篱。见闻经验是人类心灵自由的边界。在庄子的话语中,强调对于“重言”的运用,在于用“言”来破除见闻的经验。“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尽于闻见,而信所见者尤甚于闻。见之量有涯,而穷于所不见,则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省者多矣。”B16信于所见,拘泥所见,对于自己因经验所拘“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省者”,这些超越于个体见闻经验之外的世界,则尽可以不信、不求、不理解。以自己的见闻来排斥自己所未见未闻,正是培根四偶像中所揭示的“洞穴偶像”。洞穴偶像是个人专有的错误。个人有自己的知识的极限,每一个人却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我们总可以知道真正有学问的人,往往知道自己的“无知”。培根提出洞穴偶像的意义,是要人提防自己的自傲,提防自夸这种知识的错误。
“有是言则人有是心,有是心则世有是理,有是理则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为言者,不一而止,则勿惘于见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B17人的言说与客观世界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我们往往会因为“惘于见所不及”而否定那些客观存在,其实,语言既是表达心声的,也是架起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言语帮助人们增加见闻之外的经验,但也有可能构成培根的“市场偶像”。而所谓“市场偶像”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的幻象。人们往往对在市场之中的传闻以及“人云亦云”的错误,道听途说的知识不去探究它的可能性及其真实性,以为人人都相信如此,就当作是客观的真实。培根认为市场偶像是起于人类在互相交易共组社会时用语言文字表达意见,语言的创造完全以群众的理解力为根据;因群众的理解力而生的语言文字,也意想不到地成为公众健全心灵的最大障碍。endprint
言语是“芒昧”的。所谓芒昧就是说言语之意总是模糊不清,不易辨识的。如果一定要在这种“芒昧”的言语中分出是非,那是不可理喻的。逍遥与自由是与“君”和“宰”这些外在主体或力量相对立的。但是,所谓的“君”和“宰”究竟是私智的抗拒,还是客观的支配力量?当我们认为受外物制约时,是不是先有自我抗拒的预设?王夫之“所谓君者无君也,所谓宰者无宰也。天吹之而成籁,天固无益损,而人恶得有是非乎?”B18在这里,无论是庄子,还是王夫之,都没有考虑“天籁”之音与人的言说之间的差异。“天籁”是无主体的无意识的碰撞与声响,而人言则是主体“私智”的外化,人言中自然地包含着“是非”判断。在指示性的陈述,如“那是…”“这是…”,这类句式它排除了“那不是…”“这不是…”的内容,是“智”的运用与显示;在疑问句式中“那是…?”“这是…?”正是对“智”的确证,而祈使句“你必须…”“你应该…”更包含了“是非”的分辨,哪怕独自的喃喃自语,也是自我对于“是非”的强化。正因为人言自带价值、自带“是非”,所以,要使对待人言与对待“天籁”相同,就必须泯灭“是非”,降低人言的是非分别,才有达到“天之静”的逍遥状态。所以,不逍遥与不自由就要求我们看淡语言的标识与分辨功能,走出“因知立言,因言立辨,以心阔斗物,以物斗心,相刃相靡,形化心亡而后已”B19的困局,摆脱以“私智”为智而陷于“芒昧”而不自知的状态。破除因言语而带来的分辨,对自我的“芒昧”与他人的“芒昧”带着完全接受的心态,深刻认识到:“我与之俱昏昏,而何能使人昭昭?人无有不昏昏,而何用使之昭昭耶?天之静而不受人之益损者,儒听其为儒,墨听其为墨,朗然大明,自生自死于其中,而奚假辨焉。”B20世间本有“朗然大明”之道,可是私智却使得儒墨各家都汲汲于“辨之不胜辨”,这种过分相信语言而远离大道的悲剧,在人间世时时发生着。
为什么会出现由语言而阻隔自由与逍遥之途呢?审视语言的特性,可以看到,语言的分辨区分功能给人的思维带来了一道真理的幻光,它使得如此言语蒙上了自欺的性质。这使得每一个自以为垄断真理的人,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辩论场域中,希望独占话语的主导权,在不足以说服他人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成心”私见与他人激辩不已,使得凭借言语兜售“己信之情”,或以己之“闲闲间间之知”贩卖“炎炎詹詹”之言。于是,个体所追求的自由与逍遥便因着“成心”与“笙簧聒耳”之言而愈发离自由与逍遥而远去。王夫之对这种因带有“私智”性质的言语导致个体自由与逍遥的消解,是怜悯,是无可奈何。他指出:“乍作乍已,而终芒于所自萌,一言不足以立而炎炎詹詹,且无穷焉,其所挟以为己信之情者,成心而已。成心者,闲闲间间之知所成,于理固未有成也。无可成而姑逞其词,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一气之所激,笙簧聒耳,辨之不胜辨也,无容奈何者也。”B21言语本来是思想攀越的阶梯,是与“道”相合的津梁,但由于“私智”或“成心”杂处期间,导致人在语言的牢笼下,失去了与道同一的自由与逍遥的可能。
三、通向自由与逍遥之路
“游”对于“无己”与“有己”对立的消解。在道家的自由中,支撑“无己”的意识是“忘”,是“无辨”,没有人己的对立,没有事功的显赫,“悠然忘其有事”是人生的常态。所以,自由不是自我意识的张扬,而是自我意识的消解。“尧不以治天下为功,尧无己也。庖人游于庖,尸祝游于尸祝,羹熟祭毕,悠然忘其有事,小大之辨忘,而皆遂其逍遥。”B22能够“忘”,在于人们是以“游”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游”是心灵愉悦、己所甘愿的态度,各自的工作带有诗意的韵味,既劳作,又审美,唯其“游”则可以消解人生的苦役。庖人“游”于庖,尸祝“游”于尸祝,因而“游”具有表演性。庄子在《养生主》中所揭示的“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就是这种诗意人生的最佳表述。正如马尔库塞指出,“消遣和表演作为文明的原则,并不表示劳动的转变,而表示劳动完全服从于人和自然的自由发展的潜能。”B23劳动的“消遣和表演”的性质,正是人的自由得以彰显的基础。
自由与逍遥必须突破认识的局限。看待外物,我们往往会将私意的实用态度加诸对象的身上,但这种不从是“即物而物物”的认识,必然是错误的,是心智为自我经历所限的片面认识。因而,无论是自我心智的完整性,还是对他者认识的完整性,都要求主体的“其神凝”,才能洞彻物性的奥秘,还一切物性以逍遥与自由。王夫之从功用的角度一样揭示了庄子的自由精神:“五石之瓠,人见为大者;不龟手之药,人见为小者;困于无所用,则皆不逍遥也;因其所可用,则皆逍遥也。其神凝者:不惊大,不鄙小,物至而即物以物物;天地为我乘,六气为我御,何小大之殊,而使心困于蓬蒿间耶?”B24这种逍遥与自由精神,从对象或者“他者”来说,就是要“即物以物物”,或者“物尽其性”;从自由与逍遥的主体来说,它要求的是“其神凝”。当然,道家的逍遥与自由是“无主体”的,是不分物我的,“我”即“物”,“我”为万物中的“一物”,所以,尽性同样是包含尽自我之性的。
个体的自由是依从各自的条件的,“各如其分”,各凝其神。不以一己的私意来裁度他人,不附着于他人,正是自由之“游”可以无所不至,无所不存的前提。王夫之在解读庄子的神人之说时,“夫岂知神人之游四海,任自然以逍遥乎?神人之神,凝而已尔。凝则游乎至小而大存焉,游乎至大而小不遗焉。物之小大,各如其分,则己固无事,而人我两无所伤。”B25他认为道家警惕世俗的人我关系中,人们往往从自我出发,“张小而大之,以己所见之天德王道,强愚贱而使遵;遏大而小之,以万物不一之情,徇一意以为法;于是激物之不平而违天之则,致天下之怒如烈火,而导天下以狂驰如洪流;既以伤人,还以自伤。”B26如果不正视“万物不一之情”,人我之间除了追求宰制“他者”之外,必然要遭遇来自每一个欲遵“己意”的他者的抗拒,“致天下之怒如烈火”,自我随性所“游”的人生永诺就会落空,不仅不能“任自然以逍遥”,恰恰可能在人我关联中,遭受自我招致的伤害。endprint
自由与个体精神的完整性相联系。马克思在讲人的自由时是以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础的,道家同样强调只有完整性才有自由。因为保持个体精神的完整性才是源自内在的自我欲求,而不是依靠外在功名利禄的牵引与规制。尧舜的“治迹”并非是尧舜的自由的规定性,如果将外在的“治迹”当做尧舜的规定和价值,那么,尧舜就是有待于外物的,而真正体现尧舜价值的是尧舜的“神之凝”,是个体精神的完整性。所以,王夫之在阐释庄子的自由精神时,认为“视尧舜之治迹,一尧舜之尘垢粃糠也,非尧舜之神所存也;所存者神之凝而已矣。”B27王夫之把这种完整性甚至提高到庄子自由哲学的核心地位。在注释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其神凝”时,下注“三字一部《南华》大旨”,这种个体精神的完整性与道的完整性是相一致的。所以,自由是自我的意愿,纯粹具有个体性,而不必外求的,在道家这里,自由多少与意志自由的相近的。
但是,这种个体性又不是区分内外、己与天下的标准,相反,是在个体性促使的是“物各有所适,适得而几矣”B28,对于道的接近,是在承认个性的基础上,容许个体的自由发展,否则,“不予物以逍遥者,未有能逍遥者也。唯丧天下者可有天下;任物各得,安往而不适其游哉!”B29逍遥与自由不是独占天下,不是强物就己,而是“任物各得”,在个体与世界的关联中,反对“有天下于己,则以己治天下:以之为事,居之为功,尸之为名,拘鲲鹏于枋榆,驱蜩鴳于冥海,以彭祖之年责殇子之夭”B30,自由与逍遥是基于对道的体认,而不是将个别物性扩展为普遍的标准,相反,是一切物性依照自我本性的展现。一切物性都具有等同的价值,都是“道”的分有,是“道”的体现。
在人与世界的关联中,超越一切功利的关系,“以无用用无用”是自由与逍遥的重要方面。王夫之在阐释庄子的自由观念时,从功用的立场看,“因其所用”是尽物之性,是张扬“自主”的自由精神,但是,这种基于物的功用的“尽性”与自主,它同样是不自由的。一旦物的功用对于人来说,不足以满足人的需要时,“穷于所不可用,则困”,人所希翼的自由就会戛然而止。相反,只有放弃对外物的依赖,真正地从物的自主性出发,自由与逍遥才是现实的。王夫之分辨了庄子对于无用的两种态度,指出“前犹用其所无用,此则以无用用无用矣。以无用用无用,无不可用,无不可游矣。凡游而用者,皆神不凝,而欲资用于物,穷于所不可用,则困。神凝者,窅然丧物,而物各自效其用,奚能困己哉?”B31如果以完整性的“神凝”来考察万物,物与我,我与物都是了不相关的。如果能够“以物观物”,让个体的智慧洞彻“物性”的自足,那么,“物”在自主中就可以“各效其用”,以“物”的完整性来成全“物”的自主性,正是我与“物”各自逍遥与自由的前提。逍遥与自由其实很简单,就是主体与“物”之间“相忘于江湖”,“窅然丧物”,物自为物,我自为我,甚至能够由“丧物”到“吾丧我”“丧天下”,“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物与我动静都能够“与道相合”。所以,郭象注坐忘时,指出:“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B32
从个体因遵从“道”而无所作为方面看,逍遥与自由是对“万物并作”的“道”的认同。面对最高意志的“道”,如果外面只接受世俗所谓好的价值,而力求排斥那些所谓的负面价值,那么,任何“以天下为事”,“以己治天下”,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违背“道”本身的。“物之灾祥,谷之丰凶,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胼胝黎黑,疲役其身,以天下为事,于是乎有所利,必有受其疵者矣;有所贷,必有受其饥者矣。”B33与世俗的“利”相伴,必有相对价值“疵”的存在;有人们所欣然接受的“贷”的富足,自然有“饥”的不足。任何分辨、偏爱,都只会让自由与逍遥大打折扣。逍遥与自由可以是“道”的显现,也可以是“道”的存在方式。虽然逍遥与自由一样不是无对的,一样有其对立的价值判断的,比如,逍遥与牵挂、自由与枷锁。但从逍遥与自由的本义来看,它必须超越它的对立面,才能够体现逍遥与自由在完整性层面上,与“道”具有等同的最高价值。道家的“道法自然”之“自然”,正附着逍遥与自由的意蕴。
【 注 释 】
①参见以赛·柏林著,陈晓林译《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41页。
②③④⑦B11B12B13B14B15B16B17B22B24B25B26B27B28B29B30B31B33王夫之:《庄子解·逍遥游》,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3、1、4、5、5、8—9、8—9、2、2、6、8、6、6、7、7、7、7、8—9、6—7页。
⑤⑥B18B19B20B21王夫之:《庄子解·齐物论》,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5、15、15、15、15、16页。
⑧⑨《道德经》第十三章、第七章。
⑩约翰·凯克斯著,应奇译:《反对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B23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B32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5页。
(编校:章敏)endprint